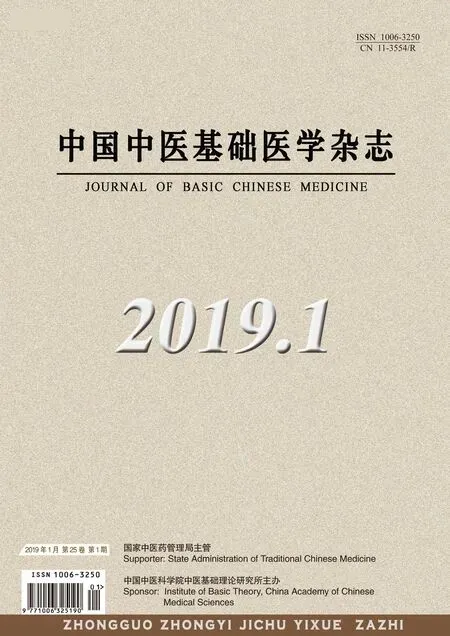法家论治思想对《黄帝内经》防治理论的渗透和影响❋
龚雪敏,朱祝生,黄 高
(贵阳中医学院,贵阳 550025)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学派在“争鸣”过程中相互融合吸收,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内核,并渗透影响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法家作为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一个学派,以极强的现实感和实用特征成为当时颇受重视的一个流派。该流派力主“变法”、崇尚“法治”,对社会稳健运作提供了重要条件。可以说法家文化在推动社会变法的同时,也深刻融入到我国政治、经济、医学、军事等诸多方面,对《内经》防治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现就法家文化对《内经》的影响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剖析。
1 法家以法治国与《内经》的治疗思想
法家力主“变法”和“以法治国”[1],其思想的最高社会价值与同时期其他思想流派一样,都体现为安民定世平天下,只是在操作层面各派思想侧重不同。其中法家思想崇尚法治,把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力主以“法”来维护社会机体正常有效运行。《韩非子·诡使》有言:“道私者乱,道法者治。[2]”即顺应个人意识的统治,必将导致国家秩序被破坏,顺应法律统治才会使社会有序。因此,他提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臣无法则乱于天下。[2]”强调法律对于违法乱纪者必须时刻有强制约束力,以保证法的强制性与普遍性。很显然,法家把法治看作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最佳保障,在维护社会秩序上十分重视法律约束作用,这在《内经》论治思想中也有突出体现。
《内经》中有丰富的论治思想、原则与方法,这些思想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灵枢·九针十二原》强调“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即疾病是一个可以被终止的过程,要想祛除疾病应用合适之法。“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灵枢·逆顺肥瘦》);“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人体有自身调节生理功能活动的规律和法则,不能违背,否则就会产生疾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与《素问·异法方宜论》还进一步总结出根据气候、地域、季节和人体本身的具体情况制定治疗原则,即三因制宜的基本原则。“神不使也”(《素问·汤液醪醴论》),强调人体形神统一、形神共治的治疗法则等。
可见,《内经》在治疗思想上首先是把人体和外部环境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局部病变必须放在整体环境中加以考虑,并指出结合外部环境情况,依照生理功能的活动规律和法则行事,才能维护身体健康。因此按照生理规律进行自我约束是促进身体机能良性运行的根本。此外,在以上治疗思想指导下,《内经》还提出了中医治未病、治病求本、调节阴阳、标本缓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补虚泻实、寒热温清、扶正祛邪、因势利导等治疗原则,这些原则如同法律一样,约束医生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法家的帝王权威与《内经》的脏腑理论
法家分法、术、势三个流派,韩非综合三派所长,颠覆传统以道论君的君道关系,为君主权力的不受限制进行了形而上的最高论证。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法家的概括:“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3]”推崇君主,这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特性,也是帝王文化[4]的核心,而法家作为帝王文化的灵魂,捍卫君主至尊地位是其推行法治理想的必由之路,所以无论商鞅的“权制独断于君”还是慎到“民一于君,事断于法”的“国之大道”,都强调君王的权势,区分君与臣、臣与民、君与民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主张以“礼”和“法”加以维系,并提出防止君权旁落、臣子篡权的权术。在法家看来,社会细胞有明确的主次之分,君为主、臣民为次,君主的地位越稳固社会秩序就越有序,国家“机体”就越健康,因此法家致力于为君主提供治国工具,以确保君主权势。这种区分主次、尊主安国的思想反映在《内经》中,则以脏腑理论为代表。
《内经》脏腑理论主要论述了脏腑的功能及相互关系,强调“心”在脏腑中的“君主”地位,如“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本篇中还提到“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以封建王朝官职制度类比脏腑生理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给各脏腑官职定位,将帝王文化思想植根于医学理论实践中,突出君主神气与臣使的主次关系,确立了心神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导地位。“心”主导各脏腑功能活动,以维护机体内整体统一的生理环境,维护人体自组织系统。申明养生必以养心为要务,而心神失常则会危及生命。所谓“心者,生之本”(《素问·六节藏象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灵枢·邪客》),充分说明“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主宰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完成统一生理活动的思想。
由此不难看出,古代医家一直视“心”为整体观念的核心部分,主宰着人体各部生理功能,为神志活动提供场所和物质基础。可以说在《内经》中,“心”之于人体的地位及作用,正如法家思想中“君”之于国家与社会。
3 法家富国强兵的重战观与《内经》发病原理
法家从兼并战争的需要出发,采取重战立场,形成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战争观[5]。法家认为,外敌入侵是造成国家动乱的直接原因,而以暴制暴是结束动乱、稳固国势的最有效手段,所以法家视战争为“尊主安国之经”,并强调战争是“外以诛暴,内以禁邪”的“不可废”问题。而要战胜守固,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是“固国”之根本。《管子·参患》说:“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则“地必亏”“国必乱”[6]。其次,还需掌握战争的原则。管子指出,无论治国还是用兵都要依据一定的原则,要认真分析掌握,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否则“战之自败”。在具体作战实施行动问题上, 《管子·禁藏》中强调应“先慎于己而后彼”的“节制之兵”逻辑, 主张“至善不战, 其次一也”[6],追求慎谋以不战而胜,注重保国。最后,法家在重战的同时也能理性认识征战将带来的物资损耗和人员损失。《管子·参患》指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6]”
法家的重战观以及围绕重战立场形成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思想为《内经》发病原理的探索带来很大启发。《内经》认为,发病是邪气与正气相互斗争的过程,“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参以虚实,大病乃成”(《灵枢·百病始生》),指出当正气充足、邪气不犯,故机体不发病,若正气不足难以抵抗病邪则发病。这种观点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等观点相同,均突出了正气在发病中的主导作用,从而奠定了中医学以内因为主的发病观,因此中医治病以讲求固守正气为首。
《内经》的发病观和法家富国强兵思想一样,都把外侵视为引发问题的直接动因,但却都强调固本是第一要务,于法家而言就是要增强国家军事实力,于《内经》而言则是要固守正气。
4 法家的利义观与《内经》的朴素唯物主义
商鞅变法,始以“利”为诱,树立“法”之威信;韩非用“利”解释人类一切行为,为实行“法治”奠定理论基础。所谓“人无羽毛,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胃肠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2],人性好利的天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皆为利害关系,因此“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2]”法家总结出法治的施行需要以物质活动即“赏罚”为基础,可见法家在利义观上坚持“人性好利”,强调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物质为基础,人的逐“利”行为是人社会活动的基本驱动力。
《内经》的生命观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生气通天”等论断,指明人需要不断从自然界获取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的物质,需要在社会环境中完成自身社会属性,同时人体内也存在一个相互逐“利”的统一系统,并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念。因为人体各脏腑形体官窍都需要利用先后天产生的“利”,即精微物质来维持与壮大自身的生理活动,所以顺应其“逐利”需求,进行“赏罚”“予夺”就是中医养生的内核。如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容……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即春天是万物生长发育推陈出新的季节,因此对于春天赋予人的生发之气就不能随便损害、劫夺和惩罚,应该培养、给予和赏赐,这就是与春季相适应保养“生气”的法则。所以养生之道就在于顺应人体的“逐利”需求,并用“赏罚”“予夺”等手段,为这种“逐利”行为规定正确导向。
总之,法家的利义观体现了以物质为基础的法治,同样《内经》中也强调人体功能活动正常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治国也好,养生也罢,其要义都在于尊重活动主体的物质性,并用“赏罚”等手段对这种物质性加以规范和劝导,使其符合主观目的性。
5 法家的识变从宜与《内经》的诊治法则
从魏国李悝变法到楚国吴起变法,从秦国商鞅变法再到赵烈侯的改革,法家推行法治的实践无不从变法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旧的土地制度不能再实行,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变旧的奴隶主统治,确立封建制度,改革生产关系。法家变法的实质就在于用地主阶级的新“法”取代贵族的旧“礼”,打破宗法等级特权,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法家变法从根本上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正所谓“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6],法家主张君主立法以当世之情为依据, 因地、因时、因事制宜。基于这种政治认知,法家思想表现出强烈的识变从宜的理论品质,并将其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影响深刻而广泛。
《内经》在诸多方面也体现出相应的理论品质。在哲学基础方面,《内经》坚持事物恒动发展的观念,《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就是说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和五行之气的生克制化决定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各自的特征,而气本身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既然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那么作为实用科学的中医学就必须随着作用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具有识时通变的特点。
从疾病传变来看,《内经》总结疾病传变有表里传变、经络传变和脏腑传变等不同方式。在诊法方面,主张四诊合参、识变从宜。“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论》),指出人体疾病类型多种多样,导致表现症状大不相同,究其原因是阴阳失调偏胜偏衰所致,故后世建立的中医诊断学八纲辨证便以阴阳为总纲,因此应根据阴阳所表现出的不同证型对疾病采用不同的治疗之法,可见《内经》从疾病传变到疾病诊法,都贯穿了因变制宜的思想。
在论治方面,《内经》基于天人合一理论,提出养生与论治疾病应讲求“法天之纪”“用地之理”“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在“治未病”思想中,《内经》在充分肯定疾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十分强调对疾病的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强调治疗疾病时应遵从顺应疾病发展变化的自然趋势,加以疏利引导的治疗原则,同时也提出了如针刺、放血、药物、按摩、熏浴等丰富多样的治疗手段。
讲究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一大特点,所以中医既是一门实用科学,也是一门哲学文化学,而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中医理论奠基之作《内经》,无疑从多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对此,已有的研究大多从儒道入手,而涉及法家思想的研究很少,实际上法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分量很重。众所周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始于秦,而秦国的崛起全在于运用法家学说为其治国的指导思想,但强秦暴亡之后才有了以“德治”为理论核心的儒家的崛起,而此时法家的思想精髓已融入到儒学思想之中。史学家们对此也评论说,中国历代实行的统治皆是“外儒内法”或“儒表法里”,法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探讨法家思想对《内经》的影响,既有助于从哲学层面进一步理解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读《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