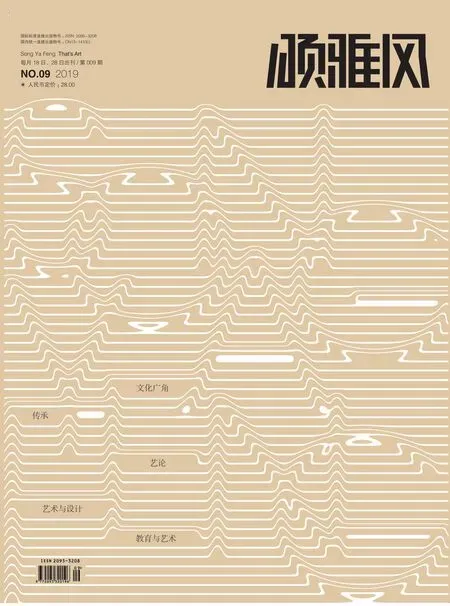荒原怒问天 雪摧冷月残
——浅析《大雪地》中意象化言说方式
◎王永芳
“意象”这一概念,原是汉语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南北朝文艺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句话中,“意象”得到了清晰明确的表达。“‘意’指的是客体化的主体情思,‘象’指的是主体化的客体物象。‘意象’就是‘意’‘象’这彼此生发的两个方面的相融和契合,是艺术构思活动中创作主体心意与客体物象交融合一的艺术表象。”
在《大雪地》一剧中,杨利民运用意象化言说方式来传情达意,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既达到了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又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拥有极大的蕴藉之美。恢弘浩大、意韵深长的意象的运用使得该剧通过形象的表层折射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本文通过荒原、严雪、冷月三个意象对该剧意象化言说方式进行解读。
一、荒原
该剧一开始便出现一片苍茫的荒原。“年轻时的黄子牛背着军人的行李,嘴里‘哩呀哩呀’地唱着,走在白茫茫的大雪地里。他坐在雪丘上系着鞋带,把帽耳朵卷起来,朝四处望望,感到劳累了,口有点渴,俯身用双手捧起雪吃。”此时的环境气候是恶劣的,人民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冰天雪地中,没有挡风的小屋、取暖的篝火、怡情的小酒,口渴只能以雪解渴。
然而,在凛无生气的荒原上,年轻的黄子牛充满朝气,生命力蓬勃而旺盛。他系鞋带、卷帽耳朵、四处张望等一系列动作,为冰天雪地的荒原添上一笔生命的气息。此时的他,自然坦荡,身体里流动的血液是沸腾的,与大荒原的本性一脉相承。在饕风虐雪的肆虐下,他坚守在荒原,踽踽独行,用心灵亲合着天地万物。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动作中可以捕捉到。此时此刻,他的心是温暖的,像一团火焰,熊熊地燃烧在这片荒原中的雪地上。
三十年后,同样是那片荒原,同样是冰天雪地,同样是那个人,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年的黄子牛独自行走在白茫茫的大雪地里。他是在一个下等酒吧喝醉了酒,回家的途中迷了路,鬼使神差地走进了荒原的大雪地的。他转圈地走着,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着什么……”大荒原神秘、苍凉,人物亦被不安、悲凉的氛围深深笼罩着。
老年黄子牛醉酒后迷了路,不小心进入了大荒原。物如旧,景如旧,人已非。确切地说,人还是的那个人,只是已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压低了头,压垮了背,失去了当年蓬勃与朝气。他死气沉沉,油尽灯枯。他是真的迷路了,还是潜意识里不愿回家,不愿面对大翠,不愿面对自己凄惨的人生?他匍匐前行想要努力辨认着的方向,是他回家的方向,还是他迷茫的人生的方向?他是真的想要找到回家的路,还是对这个他奉献了全部心血的社会绝望之至,想要寻死以求解脱?
在空阔的荒野上,黄子牛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有人吗?有人吗?”然而回答他的,只有自己苍凉悲壮的回声。为了满足时代需求,他封闭、压抑真实的自我,只有“在梦里啥事都干过”。然而,当他失落迷茫,需要帮助时,时代却静默无声。
时代需要这么一个“好人”,于是黄子牛成了这么一个“好人”:他将好友推进监狱,以示自己的“忠心”;将深爱的姑娘从身边推开,以示纯洁;放弃深造的机会,以示无私;娶一个与人有染、自己不爱、也不爱自己的女人,以示驯顺。他扼杀了意志,放弃了意愿,出卖了灵魂,成了一枚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螺丝钉,成了一块想往哪儿搬就往哪儿搬的砖。然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年代久远的螺丝钉已然毫无用武之地,废弃的砖块儿亦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大荒原无情地吞没了。
大荒原剥夺了他青葱的年华,剥夺了他自由的灵魂,却在不再需要他时,将他推向深渊。在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无论怎样躲闪、逃避、挣扎,最终都无可遁逃。
荒原这一意象的运用,使剧作真实自然,合乎人情人性,展示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又无丝毫矫揉造作的痕迹,使这一沉重的话题,得到了自然流畅的表达。
二、严雪
有人称杨利民先生是戏剧诗人,“而《大雪地》的诗意,体现最浓之处就是黄子牛徘徊的那片雪地”。
单单一个“雪”字,已经使剧目有较为浓厚的诗意了。黄子牛在回忆往事时,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雪。他孑然一身走在皑皑白雪中,与萧条悲凉的自然环境做着斗争,即便凛然无畏、顽强不屈,却也清冷萧瑟、孤独悲凉。这幅淡墨渲染的中国画,把那种苍凉冷峻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狂暴的风雪尖厉地嘶叫着,仿佛要把这块土地和生灵都生吞活剥。雪浪像无数条巨龙翻卷着,在空旷的荒野上肆虐地狂奔着。一道道雪丘冰岭逶迤起伏着,显示出神奇的力量。”风雪狂虐,工人们的声音不断交织在风雪怒吼的声音之中:“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他们需要黄子牛。需要他冒着风雪到各个帐篷为大家修理胶皮,需要他任劳任怨地服从组织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需要他把进修的名额让出去,需要他关爱工友无私奉献……
黄子牛这么做了。
飞雪乱舞于天地间,如同一位暴君,粗野狂暴、横行霸道,用铁血手腕统治着这片广阔无垠的大雪地。风太急,雪太紧,劳碌了一辈子的孱弱身躯,经不住身心的双重摧残,终于累垮了,倒下了。
传说中,快要冻死的人会看到神奇的火光。黄子牛看到了。那一只只乱舞的银蝶,在他渐渐涣散的瞳孔之中,幻化成一只只红色精灵,直逼双眸。他看到美丽的少女,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手臂,他认为是秀玲在接他回家。他伸出了双臂。然而,真正迎接他回归的,竟是死神。终于,他死在了荒原中,死在了雪地上。
大雪依旧下着,仿佛在为这个奉献了一生的人唱着悲情的挽歌。生于雪地,死于雪地,那些晶莹剔透的六瓣花朵,是他来过这世上的最好见证者。
风雪这一意象的运用,使读者心生悲凄、荒凉之感,进而产生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刻思考。黄子牛的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荒原之上,横行肆虐间的风雪交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命运之网,扑向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谁都无法逃脱。正如江国梁所说的那样,“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碾着一些人的肉体和灵魂前进。”
三、冷月
《大雪地》中,剧作家对月亮的描绘别具一格。
月光如水,静静流泻于那片宁静的雪地上。冰雪在月光的照耀下,折射出静谧、柔和的光芒。在这个宁谧的夜晚,黄子牛与他的初恋秀玲相遇。月光落进秀玲明净的眼眸中,为她年轻、靓丽的脸庞晕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秀玲:“听人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人。不知道天底下的人都咋活着……”
黄子牛:“咋活着?都在水深火热中。我们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秀玲:(仰望星空)“要是那两颗最亮的,就是你和我该多好啊!”
黄子牛:“那有啥意思,吊在那儿难受着呢……”
在月光下,秀玲含蓄地表达着对黄子牛的爱意,而他却不太懂,或是不愿去懂,即便他已深坠爱河。他的心灵如同月光,似乎从未被尘世上的污垢沾染过,洁白如玉,晶莹剔透,明净可爱。可是,谁又能说这种可爱不可怕呢?
正是这种单纯,让他诚实地向领导汇报大海与大翠的不正当关系,以致使大海身系囹圄;正是这种单纯,让他把自己深爱的姑娘拱手相让,使其另嫁他人;正是这种单纯,让他无条件迎娶自己不爱也不爱自己的大翠,使双方痛苦一生;正是这种单纯,让他把高楼大厦让给别人,使自己的老婆孩子贫困潦倒;正是这种单纯,酿就了他自己一生的悲剧,也酿就了无数身边人的一生的悲剧。
月亮一直照耀着他,伴随了他三十余载。三十年后,月亮如旧,他的心境却不复明彻。月光下,黄子牛开始思索的人生价值与存在的意义。此时,他眼中的月色,已变得冰冷与苍凉。他迷茫了、动摇了,他不知道,他这样战战兢兢地生活着,竭尽所能倾其所有地奉献着,究竟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他那单纯善良的生活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都成为了他迷茫的根源。”他此生都在追逐着忠诚与服从,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回头看看自己的所有:妻非所爱,子非亲生,恋人陌路,工作无着……
月亮再亮,终究冰凉。明月高悬,像在冷冷地讥讽他的惨淡,无情地嘲弄他的落魄,全然不顾他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凄凉。
冷月这一意象的运用让我们窥探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所塑造的可悲可叹、可敬可怜的人物。为顺应时代的需求,他们封闭了内心情感。当不再被需要时,如同咀嚼过的甘蔗,已被榨得精干,成了历史的牺牲品。“剧作家把社会性与人性既对立又统一的浑然一体地呈现出来,其中有献身的崇高与悲壮,又有异化和失落带来的悲凉和哀痛。作家力图抛弃主观褒贬,而把一幅从时代深入流淌过来的生命流程图画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去判断和遐思。”
结语
除了荒原、严雪、月亮三个意象以外,该剧还运用了其他意象:探照灯、影子、酒瓶、旧照等。这些意象的运用,让该剧情节的发展更加紧凑,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真实,这里不再赘述。
意象化言说方式的运用,使《大雪地》不仅拥有一般戏剧所拥有的戏剧性,而且拥有诗一般的画面感、可观性,具有感人的艺术气息。意象化的言说方式所拥有的魅力是无穷的,并不仅仅拘于文中所述。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我们可考虑其运用,这会为作品增色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