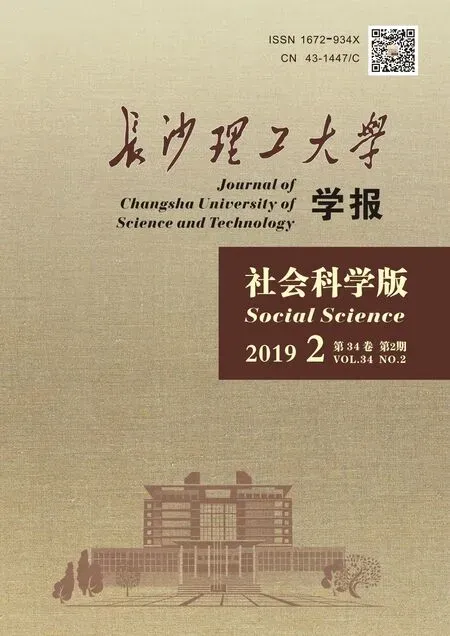郭沫若新诗创作的“颓废”审美
——基于民国报刊里读者批评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田 源
(四川美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重庆 401331)
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对中国诗坛造成强烈的震动,与象征派并行的一股新诗潮流即是标榜“普罗”的无产阶级诗潮。郭沫若等左翼诗人尝试着将热血与战火融为一体,依托“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欲赋新诗以社会的使命”[1](P331),借大众化的无产阶级诗学视野传递着革命的诉求。
然而,读者对左翼诗人诗歌批评却不完全遵从革命的政治话语,与之相抵触的个人情感成为“颓废”批评的焦点。创造社诗人在倒向革命阵营后,往日悲观感伤的情绪尚未完全消退,郭沫若喟叹动荡不安的时代对人们生存的威胁,匮乏的物质条件令日常生活变得举步维艰,微末的意识“好像浮荡着的一株海草”,贫弱无依的凄苦处境导致饥饿彷徨的身心疲态。郭沫若又要坚决破除“梦想者的乌托邦”与“唯美主义者的象牙宫殿”[2]。转型后的诗歌保留了《女神》《星空》时期的悲观情绪,诗人的矛盾心情如蒲风的评论:“他分明晓得了悲哀不是出路,他是咽着悲哀而喊着向前,向前,还憧憬着新社会的出现的。”[3]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知识分子的内心造成严重创伤,“五四”的反叛激情在昏暗的政治格局中偃旗息鼓,创造社的一批在日本留学的成员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诗歌创作逐渐弱化前期浪漫象征的虚幻风格,贴近大众和社会生活的时代主题,身为创造社领袖的郭沫若预感作家肩负的革命使命,前瞻性地“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4](P83)。后期创造社的“每一个分子都是一个斗士,也许有人会说某人衰老了、颓废了,可是就把这所谓衰老的颓废的来说,他们的活力还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5]。创造社诗人角色转换并未引发情思的质变,读者批评揭示郭沫若在前后期创作的某些相似性,他的新诗创作中在诗歌情绪、诗人气质和革命动机中均潜藏“颓废”的迹象。
一、“颓废”情绪的炽烈爆发
郭沫若的转变在大革命失败之前便已完成。蒲风以郭沫若1924年译介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界,之后遂“形成了一个转换的时期”[6]。蒲风认为郭沫若在转变之前“有小市民的悲哀,颓废”,但以留学生的特殊经历竭力为其堕落的生活开脱:“那是因为他那时过的是学生生活,不免也就有了小市民的情感的流露,有一点颓废,悲哀。”郭沫若在“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出版(一九二四)以后虽然在意识上他自己也自认为是新的,革命的了,而在实际生活的工作上,他却还是不够的”[3]。郭沫若投身社会革命的思想觉悟与实践行动并不匹配,创造转型并非彻底蜕变,诗歌延续着“女神”时期悲观的颓废情绪。
郭沫若的左翼革命火种从《女神》的创作开始便已萌生。蒲风在向郭沫若的发问中,指出诗人创作《女神》和《星空》时还处于学生时代,深感校园的局限以及涉世未深的青涩,难以免除的感伤情绪让诗人转向“对于大自然的赞唱”。蒲风似乎在为郭沫若初期颓废找外部客观理由,但郭沫若在回答中毫不避讳日本左翼思想冲击,《播种人》《改造》等期刊逐渐起势,诗人坦承受到这些“日本的新思潮”[6]熏陶。
然而,读者批评则披露了郭沫若的诗歌背离左翼意识形态的死亡、忧愁、狂躁的颓废情绪。王世颖认为郭沫若“是‘死’的崇拜者”,读者列举《死》中的诗句:“嗳!/要得真正的解脱呀,/还是除非死!/死!/……/你譬比是我的情郎,/我譬比是个年轻的女/……/我心爱的死!/我到底要几时才能见到你!”诗人借死亡来终结枯燥的生活,将死亡喻为郎情妾意的甜蜜爱恋,可见郭沫若对于死亡的憧憬是多么的强烈。读者继续列举《死的诱惑》中的诗句:“我有一把小刀,/倚在窗边对我笑/她向我笑道:/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亲我的嘴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诗人对死亡的引诱毫无抵抗力,甚至欢欣雀跃地张开胸膛,渴望用利刃结束苦恼烦闷的人生。读者还摘录《凤凰涅槃》里的诗句:“一切都已去了!/一切都要去了!/我们也要去了!/你们也要去了!/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呵呵!”逝去的世间万物连同陈腐的生命,都被卷入时代革新的浪潮里,诗中的“悲哀”“烦恼”“寂寥”“衰败”都是颓废情绪的体现,在消陨的死亡想象里,诗人欲扫除颓废的落叶,又或多或少地对这些颓废情绪有着某种不舍的留恋。王世颖也许受到“五四”精神的感召,称赞郭沫若的死亡膜拜:“他的死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死。”[7]可是,死亡本身是令人恐惧的颓废标志,郭沫若对死亡的向往隐含着逃脱纷乱尘世的颓废之感。
死亡的呼唤引发的悲伤情绪在读者心间振动,化作点点惆怅的泪水。张资平在评论郭沫若诗集《女神》时感叹:“我中国太少有泪的人,也少有泪的诗,尤少有泪的新诗!”读者对《湘累》里的一段感伤的诗句大为赞赏:“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诗人借助自然的云水意象,隐喻动态的聚散涨落情绪在内心的收缩与波动,这种悲哀的颓废情绪好像自然潮汐的升降,是“永远”无法消停的,诗人悲观的情感指向与当时青年感伤的情绪发生共鸣,张资平因此鼓动广大读者将之“多读几遍好做泪潮的材料”[8]。
郭沫若在《女神》里呈现出破坏与创造、沉沦与新生、高歌与低吟等一组组对立的情感,颓废情绪也正是在矛盾的态度中滋长。郭沫若深陷消极绝望的困境,张扬反抗不屈的意志,可是“黑暗”与“悲哀”的颓废情绪时刻牵绊着励精图治的决心,兴奋的狂喊之后是蕴藉曙光的漫漫黑夜,闻一多借用《凤凰涅槃》里的四句诗:“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净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将郭沫若的感伤发散至整个社会无穷无尽的悲惨丑态,它预示着中国现代青年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水与火的冲突正是郭沫若内心矛盾的征兆,他的颓废情绪在摇摆不定的价值观念里渐渐地生成,闻一多认为郭沫若等青年偶然的冲动压过理性的意志力,振作的斗志可能迅速坍塌,他们沉溺于酸甜苦辣的生活滋味,安逸享乐的习惯与不服输的性子在内心深处拼得鱼死网破,有限的内心被两股对立的胀气填塞,只剩下“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9]。好不容易鼓起的抗争勇气被过度的贪恋击溃,诗人尽管在外表上保持着昂扬的精神面貌,心中却充满了苦痛与哀伤的颓废情绪,内心的“冲动”只是短暂的进取,悲哀沮丧的情绪也随之迸发。闻一多抄录《湘累》里借屈原之口说出的一段话:“哦,好悲切的歌词!唱着我也流起泪来了。/流罢!流罢!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出来,/好像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血泪交织的愤懑把郭沫若这样的青年彷徨无助的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泪水混同着生命之泉只是一味地外泄,它熄灭了反抗的熊熊火焰,只留下冰冷的颓废之躯,悲凉的意味显得格外浓厚。
郭沫若矛盾的颓废情绪还表现为迷离癫狂的反叛意识,《女神》里歇斯底里的狂躁情绪奠定了颓废的基石。子潜认为:“《女神》首二辑里的作者便像个神话中的巨人,喝醉了新生酿成的酒浆,在太平洋边上对着光海放号。他一方面在澈心澈肺的享乐新生,一方面在澎湃发展出去。”[10]郭沫若幻想获取神话故事里的原始伟力,以超强的个人能力去拯救孱弱的世界,他在激情喷薄的强烈情绪助推下猛饮由死亡酿制的琼浆玉液,酒精的刺激放慢了突进的步伐,安享沉醉的快乐衍生出迷乱癫狂的自我幻觉。子潜引用《天狗》里的名句:“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上飞跑”,飞速奔跑的诗人看似奏响了“五四”狂飙的号角,但高速运行的代价却是肉体和器官自虐式的戕害与衰颓,诗人完全抛弃自我来迎合时代精神的狂热态度遭到读者的质疑,子潜批评郭沫若在诗里“乱跳乱嚷,眼泪鼻涕,像个疯妇人在地上打滚”,从神志清醒的男人向意识恍惚的疯女人的滑落,诠释出颓废的自我形象,疯癫狂乱的分解与破坏丧失了常态的艺术伦理,子潜提出严正的抗议:“艺术家底职分是表现给我们一个有生机的整体,缺一枝便成残废,多一叶即嫌赘疣,不是随便杂凑几个漫不相关的滥调词法即可称为想像或描写的。”迷狂的颓废情绪扭曲了健全的生态机体和规律,形成残损不全的意象,在《女神之再生》里也存有类似“想像贫薄之征状,随处都是一个营养不足的小孩没有病伤,也不是残疾;但我们见了他嶙峋的瘦骨,心里总满不舒服”[11]。读者审美的不愉悦感源自诗中贫瘠的幻想,它抽离自我完善的躯壳,遁入重构神话的回溯空间,尽管新生的太阳在不远处显现,但诗剧结尾的合唱依然伤感:“万千金箭射天狼,/天狼已在暗悲哀,/海水中早听着葬钟在响:/丁当,丁当,丁当。”海水撞击着礁石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暗示着诗人落寞忧伤的意识流,哀鸣的天狼星与瘦骨嶙峋的幼童一样让人悲怜,迷狂的想象逐步被颓废的情绪取代。
郭沫若新诗的读者批评将“颓废”情绪注入诗集《女神》的阅读接受,诗人火山喷发状的“颓废”情感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诗学表征。死亡的恐惧和憧憬构成“颓废”情绪的矛盾内核,进而演变为狂热的叛逆情绪,进一步凸显出颇具悲剧意味的创造者形象。
二、“颓废”气质的沉寂隐匿
如果说迅猛的“颓废”情绪只是一种时代造就的生命冲动,那么在一种本能的冷却与平复,加之时代浪潮的回落之后,郭沫若高涨的诗歌情绪逐渐向低徊的诗人气质聚集,《女神》里弥漫着拥抱死亡、痛感惆怅和追求残缺的复合感情,渗透进郭沫若悲观颓废的隐秘气质。
左翼革命思潮与早期浪漫情愫的含混,培育的气质正如诗人自我分析,诗歌《棠棣之花》《巨炮的教训》《匪徒颂》的某些地方“成为了矛盾的现象”[6]。郭沫若颓废情绪的萌生与延展均建立在矛盾的张力之间,《女神》之后的这种矛盾的颓废情绪愈发明显。洪为法认为《星空》《前茅》里的诗里寄托的“悲哀的分子更沉痛而着实”。读者列举《星空》诗集里《献诗》的诗句:“我努力地效法了你的精神:/把我的眼泪把我的赤心,/编成了一个易朽的珠环,/捧来在你脚下献我的悃忱。”如果说《湘累》中的“泪潮”尚有圆润的浑厚感,这里的泪珠则变成了容易腐朽的泪花,溅落在卑微的步履下,泪水腐蚀着滚烫的心,可是用被揉碎的泪心敬献自我的诚恳显得极为矛盾。洪为法又引用《前茅》中《力的追求者》的诗句:“你个可怜的卖笑娘,/请去嫁给商人去者!”诗人试图告别“低回的情趣”和“虚无的幻美”,却让普通民众葬送在资本家手中,“卖笑娘”的搔首弄姿或许令人作呕,但她也是为了生计不得已而为之,郭沫若却把这群弱势群体当作一件商品,贩卖给“商人”,又回归到低俗与虚幻之中,这种实实在在的悲哀让读者内心倍感沉重。洪为法还摘录《前茅》里《黑魆魆的文字窟中》的诗句:“我这点没有价值的泪珠,/不敢作为你们宽恕我的谢礼,/我明天还要来陪伴你们,/要死我们便一齐同死!”若论及《女神》中的死亡想象,它还伴随着对新生的渴望,而此处的死亡则谈不上丝毫的“价值”,因为它既失去了祈求他人谅解的勇气,又鼓动他人同自己共赴死亡,惨烈的悲痛犹如密密麻麻的文字黑洞,被压缩吸入其中的人们转瞬间化作“中铅毒而死的未来的新鬼”。郭沫若转变之前“唱着自我之毁灭,自我之再生”,但在“女神以后,作者便渐次将这悲哀,郁闷,激怒,……推阐开去,于是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旧道德,否定人生的宗教,奴隶根性的文学,……一齐下猛烈的攻击”[12]。怒不可遏的抑郁和悲哀由诗人小我深发至社会的每个角落,实际而具体的伤感不仅扩大了悲观情绪的范围,更加剧了矛盾的颓废程度。
穆木天全面系统地批评了郭沫若从《女神》向《星空》《瓶》《前茅》以及《恢复》的转变中矛盾的颓废情绪。首先,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是向着两个不同的,相矛盾的方向发展的”。一般读者或许只注意到其反封建迷信的积极意义,而忽略了悲观颓废的一面,穆木天认为郭沫若诗歌里的泛神论思想“在消极的方向,他是如卢梭一样,高叫着:返到大自然,要回到原始的共有的社会里,要像原始人似地不停地劳动,这就是他的出世的倾向了”。回返原始自然的怀抱不仅暗含诗人面对残酷现实一蹶不振的松懈念想,又在回归远古的过程中否定现代的一切文明,这种逃出升天的畅想无疑是时代的倒退,它决定了郭沫若诗歌转型的不彻底,诗人的转变在穆木天看来,封建贵族的残渣与新生腾飞的美好未来并存,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矛盾地然而是混在一起地,同时发展着现实世界的创造和原始世界的回归”。
其次,穆木天在郭沫若矛盾的颓废特质的基础上阐述其过渡时期“忧国忧民的悲观的情绪”。郭沫若在转变过程里回首往昔的玄想成分远远超出了脚踏实地的现实因素,在悲观压到乐观的颓废情绪主导下,诗人“力的诗歌转变为泪的诗歌了。他由廿世纪摩托车的运转手,革命的喇叭手,新时代的Pioneer而渐成为一个瞑想的人道主义者,成了遁世的伯夷,叔齐,最后,就是des-illusion的悲哀了”。《女神》时期的“朝阳”被《星空》时代的“暗夜”更替,郭沫若在明暗转换中的颓废“矛盾的心理,是诗人的光明的憧憬和现实社会的黑暗之间的矛盾所生出的结果,那就是追求的幻灭的悲剧了”。穆木天指出《星空》中的《广寒宫》“就是表露出他的小布尔乔亚理想的此路不通”,表现希望破灭的《月下的故乡》更“是幻灭的悲哀”。
最后,穆木天揭示出《星空》之后的《瓶》《前茅》《恢复》中的颓废情绪。读者认为在《恢复》的“《我想起了陈涉吴广》的里边,小布尔乔亚的旁观的情绪也在支配着”[13]。诗人在该诗中只是漠然地观察北方农民破败的生活:“他们的住居是些败瓦颓墙,/他们的儿女就和猪狗一样;/他们吃的呢是草根和树皮,/他们穿的呢是褴褛的衣裳。”这些衰微颓败的村庄与民众好似一个个镜头在诗人眼中快闪而过,在现代社会的变革进程里回想起封建英雄的暴力运动,诗人转变后袖手旁观的冷漠态度在之前种种矛盾的颓废情绪里便已孕育。
穆木天谈到《瓶》时援引了郭沫若回忆的感言:“五卅一来,那‘瓶’也真如‘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了。”[14]诗人所谓“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是长诗《瓶》的最后一句诗,歪斜的瓶身搭配悲凉的坟墓,又回到冰冷的死亡里。郭沫若在长诗第三十九首感伤地写道:“我昨天还好象是个少年,/却怎么便到了这样的颓龄!”衰颓的身心转瞬间逼近迟暮的消亡;诗人在第四十首幻想:“我待愈的心伤又被春风吹破,/我冰冷冷地睡在墓中痛醒。”郭沫若已经躺在坟墓里回味心碎的痛感;诗人在第四十一首里彻底摧毁了自我的生命:“空剩着你赠我的残花一枝,/它掩护在我的心头已经枯死。/到如今我才知你赠花的原有,/却原来才是你赠我的奠礼。”凋残花朵祭奠凭吊着诗人衰竭枯萎的内心,也将郭沫若矛盾的颓废情绪渲染到极点。
郭沫若的“颓废”气质在《女神》之后的《星空》《瓶》《前茅》以及《恢复》中暗流涌动,以隐蔽的方式绵延着《女神》时期的“颓废”情绪。以穆木天为代表的读者,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视角批判郭沫若及其新诗脱离现实的个人主义精神。无论是回返原始的趋势,还是“小布尔乔亚”冷漠卑微的处境,都在不同程度地转述颓废主义的“有意识地拒绝现实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对社会生活漠不关心,满怀着反人道的和反民主的情绪”[15](P29)。
三、“颓废”意识的革命点缀
从“颓废”情绪的爆发到“颓废”气质的沉潜,暗含着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颓废”意识,这种一以贯之的悲哀情思融入左翼的时代浪潮,郭沫若利用新诗“强调了真正颓废艺术的‘意识形态的’和‘虚假的’特性”[16](P222)。诗人在以政治性媚俗姿态装潢革命主张的同时,也将革命视作“颓废”意识的庇护所。
郭沫若的革命观念随着创造社的转型,经历了从高亢向低徊的转变。《女神》时代的郭沫若期望借助革命的威力整顿黯淡凌乱的社会格局,张扬正义与自由的精神。闻一多列举《匪徒颂》里的诗句:“一切……革命底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郭沫若对所有革命匪徒报以崇高的敬意,将他们捧上至尊的神坛,欢欣雀跃地高呼“万岁”。诗人在歌颂这群伟大的破坏者前区分“匪徒”的真假,借用《庄子·胠箧》里“盗亦有道”的师徒对话,揭穿“口谈忠孝节义”的匪徒虚假的嘴脸,但即便是郭沫若崇尚的真匪徒也无法彻底摆脱盗贼凶残狡黠的本性,他们只不过摘下了“圣”“勇”“义”“智”“仁”的面具,明目张胆地偷盗、抢劫、杀人、放火。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匪徒:“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这是郭沫若在1928年编订《沫若诗集》时修改后的三句诗,诗人眼中的革命没有周密的纲领,只有冲动的叛逆。闻一多评论《胜利之死》是“血与泪底结晶”,读者摘录第四组诗,其中“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亲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你把我敬爱无暨的马克司威尼早早救了!”塑造了爱尔兰革命领袖飒爽的英姿,他的阵亡令人扼腕叹息,用鲜血铸就的革命壮举在闻一多看来是“何等地疾愤!何等地悲哀!何等地沉痛”。郭沫若在诗歌结尾高呼:“‘自由’从此不死了!”以牺牲换取“自由”的赴死之心遮盖了通常意义上的死亡恐惧。闻一多从诗中感受叛逆的20世纪,“自由”成为了重新审视与破除经典的武器,伸张与获取“自由”权利的“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9]。《女神》的革命诉求仅仅是为了“自由”,诗人所推崇的“革命就是这种自由主体的改造现实的最激烈的生命实践行为”[17](P16)。正如读者子潜的评论,带有革命意识的“《湘累》《棠棣之花》《匪徒颂》《胜利之死》等篇是生之欢乐底发展——冲突”[10]。理性精神引导的缺失造就了扭曲与悲壮的颓废情绪。
蒲风认为郭沫若转变后推出的诗集《前茅》和《恢复》迎合诗人“革命文学”的主张,读者援引郭沫若寄给成仿吾信函中的一段话:“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立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豫期的欢喜。”郭沫若的这段关于革命文艺的描述本身存有矛盾,一面是被逼迫的局促感和穷困潦倒的悲惨画面,另一面却是强力的魔法符咒编织的美好愿景。郭沫若在这之后还将革命文艺归结为“过渡的现像”和“不能避免的现像”,革命在诗人看来既是短暂的,又是无法回避的,“现像”不是本质,它是相对的零散要点,嫁接在“现像”上的革命证明诗人散乱的意识,在“今日的文艺”后遥想“明日的文艺”是“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2]。跨越革命的唯美幻想模糊了革命的真谛。因此,蒲风批评《前茅》和《恢复》“内容仍欠充实,没有深刻的表现,总是事实”,郭沫若也不否认两部诗集的颓废弱点,拼凑而成的《前茅》是零散的意识组装,未开化的混沌想法里残存着一点“左倾的意识”,《恢复》的价值微乎其微,它是在革命态势停顿与挫折里的零星希望,也是郭沫若卧倒病榻且不能入眠的只言片语,它们“不免有浓厚的感伤情趣”[6]。郭沫若对革命的理解并不透彻,在浪漫与左翼含混的只言片语中繁衍矛盾的革命意识,当大革命受挫时,诗人以生病为由掩饰杂乱的革命想象,“感伤情趣”的诗作便是混杂零碎的颓废革命观的佐证。
穆木天从郭沫若泛神论的思想中引申出其泛泛而谈的革命认知,转变之前的“诗人是一个泛革命者,对于一切都取一种反抗的态度,然而,他的革命的目标,有时是向着积极的方向,有时是向着消极的方向”,分散且矛盾的革命方向正如闻一多对郭沫若渴求“自由”的抗争言论,是一种懵懂盲目的内心躁动,穆木天指出《晨安》一诗“反映着他的泛神主义,泛革命主义的精神”。郭沫若在诗人要问候的对象繁多,有朝气蓬勃的“年青的祖国”与“新生的同胞”;有自然孕育的“扬子江”“黄河”“恒河”“印度洋”“大西洋”;也有让人尊崇的“俄罗斯”“Pioneer”“泰戈尔翁”;还有让人感伤的“比利时的遗民”和“华盛顿的墓”“林肯的墓”“惠特曼的墓”,诗人用广博的胸怀容纳革命,把自然和人伦都混入革命的范畴,普遍广泛的意象群或许给读者营造出崇高的审美感,但却分散了革命的重心。郭沫若在一声声“晨安”的道贺中沉醉,双眼惺忪迷离于朦胧虚幻的想象,广泛的革命意识逐渐消融在高远空旷的自然意象里,郭沫若似乎还未觉察到“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18]。诗人尽管没有用鲁迅所说的“高逸”“放达”来命名浪漫的革命情怀,但读者批评中“泛革命”与“泛神论”等同的诗歌创作,已经为读者审美提供了飘逸奔放的颓废情绪。穆木天还认为郭沫若的“泛革命”理念中寄托着“悲观否定的倾向”。《胜利之死》讲述爱尔兰革命领袖马克司威尼被捕后在狱中绝世而亡的故事,闻一多将之与《匪徒颂》的革命情结相提并论,可是穆木天却比较内部的分化,叱咤风云的赞歌急转直下而沦为“悲壮的哀歌了……那已表露着相当悲观的情调,死的解脱的憧憬已对于生的斗争的要求占了优势了”。最后,穆木天批判了郭沫若对待革命的英雄情结,读者认为郭沫若“在他所要求的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中,他给与他自己的任务,就是作一个革命英雄。小布尔乔亚革命者的诗人,当时,还没有深深了解新的革命的真义,然而,他的方向已确定了”。在没有真正弄懂革命的本真含义的前提下便判定革命的方向,郭沫若的革命只遵从个人英雄式的拯救要求,脱离了社会大众的客观需求。穆木天摘录《前茅》里《力的追求者》的最末一节:“别了,否定的精神!/别了,纤巧的花针!/我要左手拿着可兰经,/右手拿着剑刀一柄!”宗教关怀和暴力反抗的合体,矛盾地构成郭沫若英雄革命的左膀右臂。穆木天还指出《恢复》里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愿,但助推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还是在支配着”[13]。郭沫若在革命里彰显着自我英雄化的伟岸姿态,幻想用一己之力改变世界,这种看似强劲的自我武装已经抛弃了大众的力量,理想的革命构想实际上又回归矛盾的颓废情绪。
综上所述,郭沫若诗歌的读者批评聚焦《女神》,觅得“颓废”的诗人情绪,它象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与呼唤自由的时代精神,难以遏制的暴烈激情中包裹着“颓废”的情感内核。《女神》奠定了郭沫若“颓废”的深沉气质,大革命的挫败尽管摧毁了狂躁激进的变革热情,却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消沉不振的“颓废”情绪,《星空》《瓶》《前茅》《恢复》的出版进一步佐证了隐秘的诗人气质,读者也针对郭沫若的诗歌转型进行“颓废”情绪的甄别与批判。转型的历史语境是左翼与革命,郭沫若等后期创造社诗人向革命阵营的偏移,诗歌中或多或少充斥着“颓废”的痕迹,革命似乎不是郭沫若诗歌转型的真正社会意图,它反而成为彰显“颓废”意识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