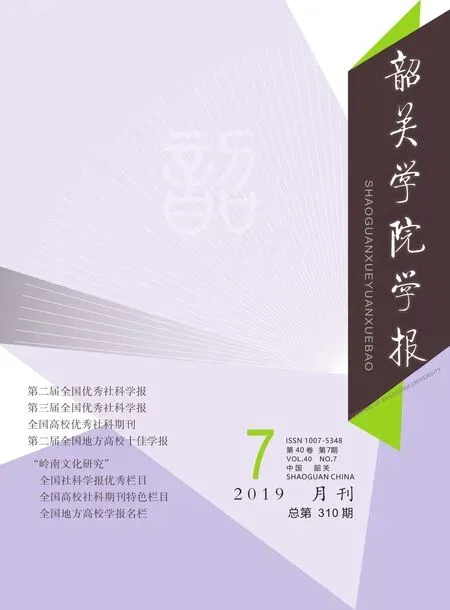乡村宗族道德权威的治理影响:一项修谱案例研究
何子文
(韶关学院 旅游与地理学院,广东 韶关512005)
198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日益增多的祭祖、建祠、修谱等宗族复兴现象,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宗族传统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变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族传统既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宗族的文化网络曾长期作为乡村的权威秩序结构而发挥社会治理影响。此种乡村社会治理传统被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称为“皇权和绅权”的“双轨政治”[1],亦被历史学家杜赞奇概括为“权力的文化网络”[2]323。而“权力的文化网络”亦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权威形成的合法性基础。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王铭铭、贺雪峰等进一步讨论了乡村精英的角色权威在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3]与“社会关联”作用[4]。张静则把这样一种依托乡村宗族精英的权威认同所形成的基层治理秩序概括为“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认为地方权威授权来源的改变,也就意味着改变了地方体的共同利益结构,也即改变了乡村精英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从而引起地方体的解体[5]17-46。自近代以来,乡村宗族传统经历多次运动的打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成功地深入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的治理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宗族文化网络难以再独立地对乡村社会治理发挥主导性的影响。因此,在当今所谓宗族复兴的社会背景下,面对乡村治理秩序结构构成方式的变化和“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的改变,宗族精英是否如传统乡绅一样仍然能够在乡土社会和国家之间充当权力沟通的桥梁角色?[6]299宗族精英同村干部如何进行治理权力的沟通与互动,甚至在乡村重塑一种权力制衡的新格局从而推进乡村社会善治目标的实现?本研究以华南山区一个山村的修谱过程为讨论对象,基于对该村修谱理事会核心成员的田野访谈材料及相关背景材料的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一、道德实践为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
使权力运行的双轨制、乡村社会相对自治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得以发挥治理影响的机制,实际上是宗族社会普泛化(主要是宗族精英)的道德实践。宗族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共同的祖先崇拜为信仰根基并体现儒家“礼”的规范性要求的伦理共同体。“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7]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中说:
“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所尊也。……古代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8]
“礼”的使用最初是在祭祀当中,指一种威仪的实践(通过身体仪态的表演和礼器的使用),实质是一种道德实践。古人“行礼”以“敬德”,敬德而有天命。而“德”源自对宗法之礼的践行,是值得族人敬效的一种神圣品质,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人格魅力。如周文王周武王(有“德”有威仪)“曾因为礼仪规范的实践而获致神圣性,而终有天命,终成为天下的支配者”[9]。可见,践 “礼”即道德实践,可以使个体展现某种具有神圣性特征的威仪——“德”的品质;而“德”也就成为个人威仪和公信力的源泉。
从“礼”更为广泛使用的含义即生活中的礼仪规范的角度来说,礼仪即人道,是与先天相贯通的人性之自然展露。因此,践礼也即德性的增长。宗族个体成员遵行这种“礼仪”的道德实践即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
对伦理性的“礼”的遵行由宗族个体推展到宗族集体,则成为一种社会秩序模式,即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特有的“礼治”秩序。“礼治讲求的是个人的修身,讲求的是人人遵守传统上的规矩。”[7]296维持这种秩序的是一种教化性的权力而非法律和政治的强制,对应的权威模式则是长老统治或道德权威[10]54-68。
因此,在宗族共同体里,诸如“尊祖敬宗”“敦宗睦族”“尊尊亲亲”“长幼有序”等儒家礼仪道德既是个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也界定了他们彼此的责任与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11]依梁漱溟关于“以道德代宗教”的观点,“礼”作为宗族社会伦理的核心,实际上内涵了宗教性、伦理性以及身份秩序的要求,落实在祖宗崇拜、人际交往和社会组织等的具体过程中。其实质即一种道德实践,是个体涵养“德”之灵性威仪、获得权威性身份认同的途径。用杜赞奇的话来说,也就是权力合法性的文化网络基础[2]160。对于乡土社会来说,宗族传统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及其道德实践所体现的合法性权威和责任性要求,既是善治的合理资源,也是善治的应有之义。
二、案例村的修谱事件:道德与治理问题
(一)村情背景与治理结构的变化
本文讨论的案例E村位于华南山区R县偏西南方向,村子四面环山,离镇大约12公里。全村常住人口1 312人,360户。E村是一个李姓单一姓氏村落,也是当地有名的水果种植村,户均水果种植面积7-8亩,全村水果年均总产量约500-600万斤,每户水果平均纯收入5 000-6 000元,水果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60%-70%[12]。据李氏族谱记载,E村李氏初祖在明朝洪武至永历年间为躲避灾乱挈妻携子与两个胞弟由江西吉安吉水G村迁徙至此地居住,繁衍至今已有28代、600多年的历史。与其他乡村一样,近年E村外出进城务工的年轻人逐渐增多,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带回村里的不仅是打工挣来的钱,也包括人际交往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样化的村民群体经历、包括国家政策扶持在内的各种外部资源的引入和村支两委制度性权力的运作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子治理结构的变动。
(二)被撕裂的宗族社区
在E村调查中,不少村民都很气愤村内水果收购问题。本村几个水果营销大户通过挤兑、施压外地来村收购水果的商人,逐渐垄断了本村的桔子、柚子等大宗水果生意。这些可能还没有出五服的同宗村民在收购其他村民的水果时,预扣很高的残损费(指残次桔子,往往扣10斤,而外地收购商则一般不扣)而且克扣斤两。这种明显的欺诈行为令村民们气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村干部顾忌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此事。虽然村里也响应上级号召成立了水果协会,设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但实际上E村水果协会会长、副会长、协会秘书长分别由村干部担任,协会副理事长由村妇女主任担任,只有协会理事长由本村的一个体工商户担任,在水果收购季节他是村里几个主要的水果收购商之一。协会办公地点设在村长家里,章程贴在村长家房子外墙上,很多村民反映不知道村里成立有水果协会。
村干部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操控相关的资源和利用信息,与村内有财力者利益共谋,从而使公共资源私利化,私人利益最大化,加剧了村公共服务的短缺程度。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加速了E村村民财富地位的两极分化,也造成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对立,造成村支两委合法性权威的流失,加剧了村庄社区精神和宗族意识的淡化。村民PY提到:
有一年屋场里的山(指E村集体山林)着火了,要大家赶去救火。大家不肯去,说救了也是村干部的(指村干部有一年私自卖掉一千多亩村集体山林,后又不公布账目并私分公款),就让它烧掉算了。
至今村民谈起村干部偷卖村集体山林资源、私吞公款的事情,还痛骂这些村干部是“卖国贼”。被村民们陆续揭发出来的还有村干部假造名册骗取政府退耕还林款并私分等腐败问题。
2008年秋季村里争取了一些县里的支农资金,想整修一下农田水渠,但响应参加义务劳动者寥寥无几。2009年夏季发洪水把村旁河面上一条联结外面的重要桥梁给冲垮了,村委会号召全村人捐钱重修一座水泥桥,规定每户村民出200元份子钱,鼓动村民乐捐。但村民们回应消极,不愿意捐钱,有人至今连份子钱都没有交。
由于长期积聚的矛盾冲突得不到化解,2008年7月爆发了一场被戏称为“保皇派”(前后几届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和“改革派”(普通村民)之间的激烈冲突。代表普通村民利益的“改革派”要求彻底清算集体历年账目、惩处贪腐分子、改选村委会。双方各使手段,张贴大字报相互攻击,搞串联和制造舆论。最后县乡两级政府、民政和公安等部门直接介入村委会的改选过程……但矛盾依旧、裂痕依旧。
(三)新的道德权威中心:修谱理事会的运作
民间历来重视修谱,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说法。族谱有“敬宗收族”及伦理教化之功用。“谱系之作何为也,所以教仁也。……谱也者,通宗族于一身,使之相亲相睦而无不爱者也。”[13]修谱既是个体的一种道德实践行为,也是宗族社会治理秩序的构成内容。
E村李氏自1943年合族修谱以来,已经有80多年没有修过谱了。前些年也有人提过几次说要修谱,但都没有成。2011年促成李氏后人重新修谱的因素,先是邻村分支房分几位年长者的倡议、后E村几位热心老者共同组织而成。据修谱组织者TL回忆道:
修谱就是这样子(开始的),首先是几个比较老一点的人,开头书成——就是留屋那个书记,有两个老人一开始就提倡修谱(这件事),就总是来动员我们(修谱)。动员我们(修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祖籍的原发地,他们后来是从这里分开出去到另外一个屋场(去住),就是对面那个屋场。但是他们现在年纪也大了,另外也还是认为应该要我们这边来牵头、来为主,来操这个心(指修谱),就(多次跟我们)说这个谱要怎么来修一下。
重修族谱的倡议首先得到了E村TL等人的肯定,并由TL等人为首很快初步组织起来了一个有7人参加的修谱班子,拟定计划并向全村人发出重修族谱的倡议。开头,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还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修谱背后矛盾重重。不少村民放出话来,说如果此次修族谱理事会中有村委会干部参预的话,他们就不会出一分钱的修谱份子钱。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谁为人正派、做事公道,彼此都知道。因此有部分村民公开地点名说,要ZT(后成为修谱理事会出纳)来管钱,他们才放心。
现年68岁的修谱理事会出纳ZT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是E村的文化精英和热心宗族公共事务者:祖父、父亲分别是E村李氏第七届、第八届续修族谱理事会的核心成员。他为人公道正派,在村民中有很高的道德威望。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想担任(出纳一职),但有人就说,如果有村干部插入进来,他们就不捐钱。一定要我去管账,他们才放心。其他人信不过。
从这次E村修谱理事会的主要成员构成来看,校对TL是水库退休在家的老工人,其父曾是上届修谱理事会成员;LW是现任村小学校长;YS是曾经的村小学民办教师;会计HW据介绍为人本份老实,是个木匠;出纳ZT,祖、父曾两代修谱,村民的口碑好。出纳ZT:
我们这里修谱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前几次的修谱倡议)如果村委会插入了的话,就各个人都不会派钱。……尤其是以前,(大家认为)凡是集资村委会里面就会有贪污的现象。群众相当反感。
当我们谈起村里修谱的事情时,修谱理事会担任编辑一职、修谱当年59岁的YS很有兴致地向我们介绍了他在族谱世系图设计方面的改革和创新,谈起历届村干部的贪腐问题引起群众对集资问题的反感,说他们这届修谱理事会是如何做到清正廉洁,又尽心尽力从设计世系图谱、校订人丁信息、编排、纸张印刷等方面做好各项族谱续修工作。“不廉洁,怎么喊得人动?”他说。
在理事会里面,收集资料的、编修的、校对的、财务、出纳都各自分开,分工明确。理事会的人都不拿工钱,完全是自愿的,是义务工。
(由于)历届(村干部)的腐败现象,(使)群众对集资比较反感。(因此)在这次修谱的事情上,村委会成员(只是)作为顾问,与修谱的核心人物冇关系。一切核心事情他们不沾边,只是做些边缘的事情。
“所谓村干部只做边缘的事情是指什么?”他说村干部只在修好谱后,在分发族谱的仪式上担任宣传和安全保卫工作。
访谈对象在话语中透露出的几方面意思很重要:第一,村干部及其它被普通村民视为既得利益者的人被排除在修谱理事会之外。这说明由于历届村干部的贪腐及利益共谋行为,村支两委的权威效力正在丧失。第二,与贪腐之人及贪腐行为划清界限是此次修谱的重要的道德议题。第三,修谱中的道德策略不仅使修谱转变成为了E村的一个公共治理事件,也强化了修谱本身的神圣性。可以看到,围绕修谱这一神圣事件以及理事会成员的道德楷模行动,一个新的道德权威中心已然出现在E村。
(四)修谱之后:道德舆论与权力争夺
2013年10月2日,E村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发放新谱仪式。发谱仪式再次把村干部排挤在主要的仪式过程之外。此次E村修谱扣去各项开支费用之后结余26 964元。当时围绕这笔结余款如何使用的问题,修谱理事会坚持把结余款全部退回族人,每人退回10.4元。村民PY说:
退钱以后,村里人都纷纷议论说,自从“文革”(在村里发生)以来,四十多年来集体账目从来没有像这样干净过。
修谱的整个过程为理事会成员收获了极高的道德声望。由于理事会成员的廉洁自律和踏实有效的修谱行动,修谱过程透过对历史记忆和宗族道德的双重诠释,实际上对规范权力的合法运作、为村庄治理权威的建构,树立了一个具有公共意义的典范,在E村重新形成了一个有助于乡村治理的道德舆论环境。理事会通过修谱这一宗族神圣仪式所展现出来的道德批判及权力地位的公共性象征,显然使村干部们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和权力危机。为了掌控这场由修谱而引起的“权力关系的转移”过程,一场围绕宗族传统这一象征资源的权力争夺开始了。
2013年5月10日,由现任村干部带领E村寻祖源的族人代表一行14人,根据族谱的记载,携族谱到江西省吉水县寻祖联宗。确认为同族后人之后受到热情接待,双方一起到唐公祖坟举行了简朴的认祖祭祖仪式。
2014年清明前夕,由村主要干部和LH等人倡议和组织,每人出人丁钱10元,再以100元为乐捐起点,每户再乐捐的集资方式,对村内开基祖良可公及祖母的墓地进行了整修。重新刻了墓碑、立了纪事碑、香炉、拜台等,在墓地四围修挖了排水沟,把两座祖墓修葺一新。
2015年清明节前夕,祖源地江西吉水G村代表回访E村,双方一起祭拜了E村的始迁祖良可公及祖母。由此前代表E村去G村寻祖的村支书、村长等人出面热情接待。2016年3月30日,LH及村支书、村长再次组织E村46人的清明祭祖团到G村回访祭祖。
三、讨论:宗族精英的道德权威与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
在广大乡村,基于宗族传统的文化网络曾长期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两种治理权威结构之一。宗族精英依托宗族文化网络沟通了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之间的治理联系,在乡村发挥着实际的社会治理功能。其所拥有的治理权力则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是一种依托宗族伦理形成的 “教化的权力”[10]64,是一种道德权威。因而传统宗族精英的治理实践往往体现的是一种根源于宗族信仰传统的道德行动——既修身以德,热心宗族公共事务,也常常作为社区利益的代言人同国家正式权力机构进行协商。
在E村的修谱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围绕族谱重修的仪式事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道德权威中心,一个普通村民参预村治公共事务的场域或公共空间。从修谱理事会的成员构成及仪式过程看,修谱实际上隐喻了E村治理的现实问题,表达的是村民对改变E村治理现状的一种道德期望——村民们希望借助宗族修谱形成一个能够维护村民利益、坚持原则、热心公益的道德权威中心,打破村里目前主要由村干部掌控的已固化的权力-利益关系格局。所以,修谱实际上成了乡村治理的一个隐喻性事件,ZT及其他理事会成员则成为了一种道德权威的象征符号,象征着村民对村干部的道德区隔与反抗不合法权力压制的集体抗争方式。因此,场域的逻辑——修谱理事会的道德实践,包括理事会成员的廉洁自律及对现、往届污点村干部所采取的道德区隔策略,既是修谱理事会的组织运作方式,也对村支两委的权力合法性产生了相当强的规范性影响。这种公共性指向表明宗族传统对农村社会治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正面价值,它有助于规范基层社会制度性权力的合法化运作,事实上起到权力制衡的治理效果,有助于以宗族集体的名义维护村民的集体利益并重建社区认同。因此从治理的角度来说,村支两委——体制权力的拥有者们和传统的宗族道德精英,是否能够积极合理地回应这种道德舆论和治理期望,就乡村的公共事务开展治理协作并将此种治理协作进一步制度化,是对双方的考验。
E村修谱的案例也同时表明,由于地方权威授权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乡村权力结构的改变,修谱理事会的组织运作主要依赖宗族精英个体的信仰和道德自觉。出于对政治敏感性的回避,修谱并没有对宗族传统形成明确的集体认知和价值认同。而且重要的是,修谱理事会的组织运作体现出临时性的特点,以具体的修谱事务为中心,没有作为一种常规公共议事机构保留下来。虽然理事会的成立和实际的运作表现出了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关注与批判,对正式的制度性权力施加了一定的道德压力,但仅仅限于道德批判的范畴,没有赋予理事会处理宗族修谱事务之外更多的公共性功能。这使得宗族精英的道德实践和治理影响缺乏可靠的组织载体,不具有持久性。更为重要的是,负责E村此次修谱的宗族精英们也没有主动地去沟通同村支两委这一正式权力系统的分歧,而是采取了道德不合作和借助道德舆论以影响村里现前的权力——利益格局的做法。由于缺乏传统乡绅的结构性位秩,没有在宗族的修谱理事会与村支两委之间建立一种权力沟通机制,因此依托个人道德自觉的宗族精英还难以真正实现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角色影响。
四、结束语
历史上宗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同现实的乡村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祖宗崇拜的信仰同世俗制度之间的深层嵌构,使二者在功能及存在形态方面都表现出来高度的同构性。然而伴随着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进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2]180要摧毁代表一种旧的法统秩序的宗族传统的权威影响时,必然导致宗族社会原有文化网络的秩序功能逐渐消失,宗族不再是乡村治理的权威。但在传统宗族道德秩序衰落之后随着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泛滥,在乡村亦演化成对经济利益和权力的追逐。因此,随着乡村日益深入地加入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当前乡村出现的原子化、“无公德个人”[14]、基层权力腐败以及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随着权威的授权逻辑由宗族转向国家,传统宗族精英逐渐失去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宗族精英也不再成为国家与乡村地方社会的中间桥梁。宗族精英作为宗族传统的诠释者、继承人和维护者,自然,其权威地位的失去也就意味着宗族传统在乡村社会治理角色的全面衰落。而当前乡村社会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实际上反映了面对乡村社会存在的诸多公共治理难题,村民试图从熟悉的宗族传统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文化策略。
就此而言,E村的个案清楚地表明,宗族传统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仍然构成了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他们身份记忆和历史感的文化载体。基于个体信仰所形成的记忆与认同,由具体宗族事件和仪式过程的激发而可能成为乡村公共生活的中心,并由此继续展现宗族的道德秩序对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实际影响。而能否实际产生影响,则取决于宗族精英能否协调处理好同村支两委这一正式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能否在宗族传统的道德实践与乡村治理目标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制度化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