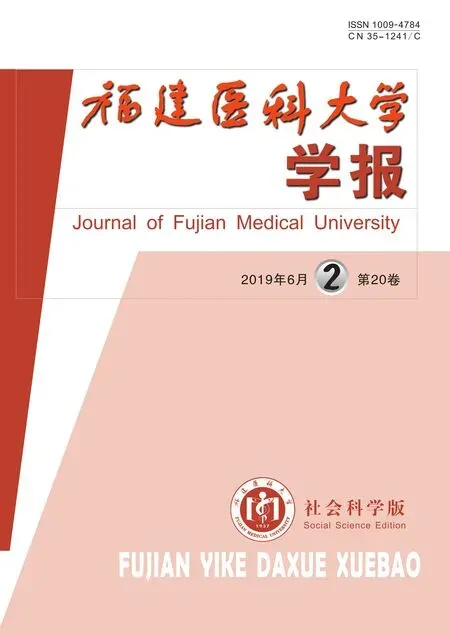论女性文艺作品中的特定身体经验呈现
——以月经叙事为视角
吴 昳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长久以来,在以男性为主的文学与艺术领域,女性囿于各种条件限制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身体形象虽然时常见于文学与艺术之中,但那往往是男性依据自己的想象和欲望塑造的。在男性的创作中,女性身体形象往往被刻板地归于“母亲”“纯洁的处女天使”“致命的敌人(女巫)”等几种类型。幸运的是,女性在被压抑了千年之后,还是借着革命的东风开始进入文学与艺术的领域。民国时期,就有女画家与女作家大胆地表现了自己的身体,例如潘玉良的自画像、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新中国成立之后,男女平等虽然被反复提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的“男女平等”仅仅指女性向男性形象的无限靠拢与追随,女性独特的身体形象与身体经验并没有得到展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禁锢的解除,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又一次开始大胆地展现女性自己的身体、身体经验以及身体的欲望。1990年代,身体写作名噪一时,尽管遭受了许多批评和质疑,身体写作以及身体艺术依然极具意义。月经,作为女性身体独特的生理现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污秽与不祥,难登文学艺术大雅之堂。女性艺术家和作家们却冲破遮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了月经这一独特的身体经验,无异于是对女性身体的自信与尊重,对女性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迫切需求,也是对既有的父权文化的挑战。
一、月经禁忌与月经不平等
关于女性月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大类之中。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人类学主要负担着月经研究的任务,人类学领域的月经研究基本集中于“月经禁忌”领域。月经禁忌指的是女性在每个月的生理期出血期间,其行为受到各方面的限制。玛丽·道格拉斯是月经禁忌理论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在其著作《洁净与危险》中,道格拉斯将人们有意识地回避月经期的女人(不与其性交,不允许其进入森林或是靠近炉火)等,视为一种“性污染信仰”[1]。在“性污染信仰”中,女性来月经往往和通奸等行为一样被视为一种极端不洁的行为。与此前对月经进行考察的人类学家不同的是,道格拉斯将月经禁忌和其他禁忌放在同一种结构下进行考察。道格拉斯指出,对于月经的禁忌恰恰是一个团体共谋的结果。这种有意为之的禁忌是保证团体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因此,可以认为,月经遭到禁忌,被认为是污秽的、不可言说的,完全是人为塑造的结果,是男性对于女性性力量和生殖力量的恐惧,月经禁忌和月经这一生理活动本身关系甚少。对女性性污染的恐惧和信仰存在于许多民族之中,在我国,汉民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存在这种“性污染信仰”。李金莲认为,绝大多数人类社会都存在月经禁忌,这种禁忌往往将女性身体视作禁忌文化的表征[2]。
除人类学家以外,许多女性学者也对月经禁忌和月经反映出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始终认为妇女的性功能是不纯洁的[3]。这种观点至今仍根深蒂固。在当代的俚语(西方)中,月经被称作“该诅咒的”[3]。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在《如果男人来月经》(If Men Could Menstruate)一文中,假设了男人如果来月经会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境遇。她指出,首先,月经会变成一件值得嫉妒的(类似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阴茎嫉妒)、充满男子气概的事情。年轻的男孩子们会谈论月经,宗教和家庭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纪念月经的到来。总而言之,月经会成为男性巩固其男性话语和父权统治的又一手段[4]。
在当代,对月经的恐惧以及有意识的忽视不仅仅是一种远古的朦胧无意识的延续,这种恐惧与忽视是现有的男权文化有意识构建的。对于月经的避讳与禁忌等行为并不仅仅是针对月经行为本身,而是针对女性的身体,正如李金莲指出的,月经现象带来一种真正的心理危机——某些时候,女性会导致男人的毁灭[2]。比起生理意义上的未知与禁忌,月经禁忌在现代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对女性身体的贬抑与忽视。
二、月经是女性文艺作品中的独特身体经验
男性在创作文艺作品的时候,尽管对女性的身体多有表现,但是对女性的月经几乎完全忽略。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男性对于月经的各种禁忌与恐惧。此外,男性创作者也没有任何体会月经的机会。虽然,“遗精”也可以作为男性青春期性成熟的某种标识,但是,月经的持续性、频繁性,以及给女性身体造成的影响是男性创作者永远无法体认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月经及其相关的身体经验成为了女性文艺创作的一大特点,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对于女性独特生理现象的细腻描写与独特展现填补了文艺作品中女性身体独特经验的空白。
女性创作者的月经呈现是直白的,可以只是女性生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是每个月都有的身体经验,而不是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或是禁忌的内容。向京的雕塑作品《初潮的处女》表现了一位经历初潮略显惊慌的少女:少女双目圆睁,眉毛上挑,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巴,整个面部表情都呈现出面对月经初潮的无措。但这种无措倒不是痛苦的,而是一种少女特有的可爱的迷茫。少女的另一只手不自然地搭在裙子上,那里正是靠近阴部的位置,试图掩盖自己初潮的事实。这件雕塑和向京同系列的其他作品一样,女孩的身体和面部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它们呈现的都是平凡的女孩子的样貌,初潮的小女孩看上去和学校里任何一个面对青春期的小女孩一样。虽然作品呈现出的是一种“普通”的样貌,但这种“普通”恰恰因为艺术化的呈现而变得不再普通,这一女性的时刻从日常中脱离出来,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女性来月经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女性在现有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极力不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己身体的变化。女孩的初潮来临之后,往往是母亲与女孩在卧室或是厕所悄声进行对话。向京的作品则将这一本来秘而不宣的时刻极大地凝练出来,呈现在众人面前,让众人都可以感知到一种尴尬而慌乱的氛围,这种氛围正是女性的身体在现实中多方面遭受压抑之下女性本身的感受。
陈羚羊的装置艺术作品《越晶晶》,名字取自“月经”的谐音,艺术家试图将观众带入到一个正在经历着生理期出血的女性(化名为越晶晶)的生活之中。这件装置艺术的每一样物品上,都有经血的痕迹(说明月经常常是突如其来,给女性生活带来不便),卫生间里播放着女性换卫生巾撕拉的声音,床边播放着女性重复说“腰很痛”“腿很酸”之类的低语。陈羚羊谈到,她在这个装置艺术中放置了几百本的女性杂志,她在里面每一页有腿的地方,都画了红色的线条来代表月经的血迹。这种行为可以被看成一种有力的控诉:在女性身体占了绝对主要地位,并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时尚杂志中,月经(以及其它女性身体中的缺陷、疼痛等)被极大地忽略了。时装杂志呈现了精致完美的、毫无缺陷和痛感的女性身体,这种身体,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批判的那样,是一种完全能拜物的、极具功用性的物体,是一种“神话”式的对女性身体的物化[5]。
女性文艺创作者对月经的呈现,将女性曾经隐秘的身体经验置于公共话语之中。这样的表现无疑给广大女性传递出一个信号:来月经并不可耻,也不意味着污秽与不可言说。相反,月经作为大多数女性共享的身体经验,有其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价值。
三、月经在文艺作品中的美学呈现
女性的身体形象常常和植物,特别是花卉相联系。在传统的男性文本中,将女性比作花朵的文学与艺术呈现早已有之。这种联系潜在的观点是认为女性躯体是柔弱的,可以任人采撷赏玩,一般认为,这种比喻是男性对女性的物化。有意思的是,女性艺术家与作家同样也将自己的身体与花朵相联系,却有着与男性不同的表达意义。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两次描写到月经,都以花来做比喻:“起身的时候,我忽然看见那只大口袋的废纸中,有一团血淋淋的纸卷,非常夺目,泛着耀眼的红光,仿佛是一只含苞待放的花朵,埋伏在一堆白花花的废纸中。”“我起床时,忽然就看到了我的褥单上有一小片红红血迹,像一大朵火红的梅花,真实地开放在绽满花花绿绿假花的褥单上边。”[6]陈羚羊的艺术作品《十二月花》是对月经的艺术呈现,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陈羚羊选择了12幅彩色照片,这些照片的内容集中于女性的生理期出血,包括被鲜血染红的阴部、血流淌过的大腿等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每张照片搭配了当月盛开的鲜花,以表示女性一年十二个月每月一次的行经规律。画面的布局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什锦窗样式,画面底色昏暗,女性用来梳妆的镜子也多次出现在画面中,使观者感觉正在窥视女性昏暗的闺房。月经在传统意义上来说属于绝对的私密,女性不愿意自己的月经被人看见,男性也不愿意接触女性的月经以及来月经的女性,但月经又是每月一次的女性生活日常。陈羚羊的作品大胆掀开了笼罩在女性日常生活与身体经验之上的“遮羞布”,将最私密的“闺阁之事”带入到公众的视野。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大多数艺术和文学表达当中,只有“好看”的女性容貌与身体才能与花朵相联系。例如,《牡丹亭》里柳梦梅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施耐庵描写潘金莲:“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因此,当女艺术家与作家将月经与花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时,这种美学表达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贾方舟提出,花在男画家笔下是一个绝对的客体,出于“被赏”的地位,而女性艺术家则是将自己代入“花”的地位,作为自我的替身。花是女性艺术家自我观照身体的方式[7]。陈羚羊将月经称作每月一开的花朵。陈染写月经是“夺目的”“泛着耀眼的红光”,这是明显带有褒义色彩的形容。陈染以第一人称描写了少女倪拗拗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月经,感觉那是“一朵火红的梅花”,开放得很“真实”,在床单的各色假花之中显得格外瞩目。在这样的女性呈现中,花与女性身体以及女性身体的特殊之处——月经,形成了意义之链,月经在艺术化的意义之链展示中脱离了“肮脏”“污秽”“不可言说”的既定宿命,成为了被女性承认、肯定的身体的本质之一,月经与女性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可以与花做比,阴部的流血也成为了具有美感的事物。
月经为美,月经如同绽放的鲜花,这种大胆的言说是女性对于男性主导的大众审美意识的挑战。在女性的身体上,并不是只有飘逸的秀发、坚挺的乳房、纤细的四肢才是美的。女性身体中流出的血液同样也是女性生命力的象征。
四、月经叙事中的女性身份认同
在一些女性作家的笔下,女孩子们多多少少都因为观察到其他女性的生理期出血而受到震动。这种震动一方面是心理的,小女孩对于女性的生理期既感觉神秘(原因不明的下体出血),又有隐约的期盼。陈染在《私人生活》里写:“以前,我在公共厕所里,看到过年长的妇女有那种东西,她们更换卫生纸的时候,非常大方,一点也不回避别人,好像大家都有这些事情,没什么需要遮掩的……但是用余光依然可以看到,她们把一团红红的纸卷丢进毛坑里。我觉得格外神秘。”而真正触动“我”(倪拗拗)的是目睹了同伴伊秋的月经:“当我看到我的同伴伊秋也有了这个问题时,非常震惊,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将与我有关,不免心里慌乱起来。”魏微的《在明孝陵乘凉》中展现了小女孩对于来月经的异样的盼望。小女孩观察到成年女性月经期间不同于往常的举动,隐约生出某种期盼。这种“我也要成为一个女人”的期盼带有女性对自我的肯定。于是的小说《今天你的手很暖》中,描述了女孩发现同龄人都来了月经之后自己没有来月经的恐慌:“我知道班上所有女生都来了,但我一直没有。这件事让我紧张……我就有种深深的孤立感,好像明明在同样的年龄,她们都拥有成为女人的资格,只有我没有——明明不是小孩了,却被排斥在女性团体之外,就是那样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群的卑怯……”[8]
女性作家和艺术家为什么要表现女孩对进入成年女性世界的渴望,魏微的《在明孝陵乘凉》给出了一种可能性:成为一个女人,将拥有曼妙的身体,而这曼妙的身体,正是撕开男性话语的武器。小说中,少女小芙对月经的期盼是因为她的理想是成为女性、拥有女性特有的曲线,进而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此外,与西方的女性艺术家和作家不同,中国的女性作家和艺术家身上带有一重“痕迹”:在不久之前,她们的身体还被束缚在“身体集体主义”之中,她们穿着不能显示身材的衣服,剪短了头发,极尽所能地压抑自己的女性特色,向男性形象无限靠拢。小芙之所以会如此强烈地想要成为一个女人,是因为她渴望优美的、专属于成年女性的身体曲线。魏微在小说中为小芙对于女性身体的渴望陈述了理由:小芙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城市充满了一种“禁欲”的味道,女人们穿着不显露身材的衣服,成为革命话语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女人,拥有分明的曲线,似乎就可以对这种男权制的革命话语所带来的压抑环境做出重大挑战。
成为一个女人,拥有自己的身体曲线,就意味着女孩脱离了“雌雄不分”的状态,女孩们在自己的身体上找到了确证自己为女性的坐标(月经、隆起的乳房、生殖器官等),女性身体的特有性征使女性站在了男性无法到达的一端,因为女性拥有了男性无法认知、无法感受到的身体经验。而月经初潮,正是青春期发育的开端,也正是月经“带来了”女性的身体曲线。正如南帆在《躯体修辞学》中所表达出的观点:女性的躯体之美存在着扰乱男性正常秩序的危险,在男权制的话语体系下,女性的躯体之美往往不是值得称赞的美好品质[9]。曲线毕露的女性身体,天然地对终将走向禁欲的父权制身体提出了挑战。
五、月经意识形态
月经被男权话语认为是污秽之物,在生理上的一种可能是因为它和尿液粪便等一样是一种排泄物。
然而,在男性创作领域,对尿液的书写比月经来得常见得多。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中有大量关于尿液的描写,先祖的一场“屎尿战”让母亲颇为自豪,男人们搜集了自己的屎尿,在“太爷爷”的指挥下,将屎尿兜头浇在了入侵的“德国鬼子”头上。屎尿雨尽管污秽,但是让德国人吃了瘪,男人们成为了十里八乡的英雄。滚烫的尿液与男性的雄壮与性能力相联系,男性的性能力又转化为男性拥有的一切力量,与民族的气度相结合,尿液从污秽摇身一变成为了对抗外侮的有力武器。在视觉艺术中,尿液的出现比文学来得晚上许多,这和尿液在视觉形象中的确不雅观是分不开的。但是,尿液在视觉艺术中的存在依然比月经常见许多。血液也从来不是文学和视觉艺术中的忌讳。文学作品中出现关于鲜血的描述屡见不鲜,电影和电视剧情节中出现鲜血与伤口的镜头也比比皆是。然而,同为血液的月经却很少出现。
同样是阴道出血,女性处女膜破裂时的出血被认为是纯洁的象征,被男性创作者频繁地提及、表现。一般认为,处女膜破裂发生在女性第一次与男性性交的时候,出血的原因是阴茎进入阴道造成了处女膜的撕裂。这种出血被认为是由男性造成的,表示着男性是这名女性的第一个“拥有者”(这是一种将女性物化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表示着男性主动地行使着某些被认为是男性所拥有的“权力”(“刺穿”与掌控女性等)。男性笔下的“破处”行为往往带有沾沾自喜的意味。而月经在男权话语主导的文艺创作中并不能享受与处女之血同样的地位。在女性作家与艺术家开始表现自身的身体体验之前,月经几乎不能在文学艺术中占据任何出场的可能。偶尔的出现,也只能和污秽、疾病、不幸等联系在一起。在争斗和远行中流血的男性被人讴歌,而每个月流着鲜血的女性则长期以来无人赞颂。男权话语对待鲜血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待月经之血与处女之血的不同态度,恰恰反映出他们对女性身体的看法:女性身体应该为男性所用,成为男性的所有物。当女性身体的某一部分对男性有“好处”时,那么它就是好的,值得赞美和呈现;而当女性身体的一些部分让男性觉得“神秘”或是“未知”,那么它们就应该被掩藏、被忽视,甚至被摧毁。
六、结 论
对女性月经的压抑禁忌,从本质上来说是男权话语对于女性身体的敌意与不信任。“女性的性力量会造成男性的毁灭”是一种早已有之的男性中心主义认知。对于女性性力量和身体的禁忌认知起始于蒙昧与迷信,之后则被男权话语不断强调与放大,直至今天依然颇有拥趸。在这种话语条件下,女性往往以自己的身体为耻,羞于表达与展露自己的身体,放大身体的缺陷与不足。对于女性身体多有贬抑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在传统的男性创作中,女性的身体仅仅展现出有限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是以男性的眼光来审视女性之后的审美取向。
文艺作品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女性身体的种种苛求和不解是造成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过分苛求“瘦”、以整容为追求等种种行为的原因之一。女性艺术家与作家的文艺作品对女性身体做出的表达与揭示,有助于女性接受自我,不再一味追求男性审美中的女性美。这种突破与尝试,无论在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