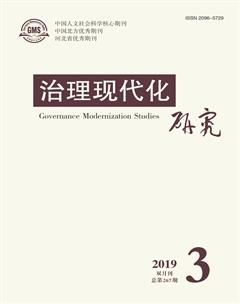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运行机制与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以河南省D市为例
丁辉侠
摘 要:精准扶贫要求对贫困村和贫困户实行精准帮扶,为此政府启动了中国特色的内部动员机制,形成以驻村帮扶工作队为关键主体的新型贫困合作治理模式。本文在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运行机制与贫困治理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河南省D市的入户调查数据,从贫困户精准识别度、脱贫成效、帮扶满意度和精神变化四个维度对其贫困治理绩效进行评价。针对因社会参与不足、驻村帮扶工作队资源有限等原因,影响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治理绩效,文章提出从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加强精神帮扶和提高其对扶贫项目的参与力度等方面改进其工作的对策。
关键词: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队;贫困治理;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45-08
一、引 言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2014年3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2014年5月,在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办、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和中国残联制定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中,明确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是“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基础”。[1]同时要求建立干部驻村工作制度,并要求在2014年6月底前派驻到位。按照要求,每个贫困村都要有駐村帮扶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要有帮扶责任人。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扶贫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一具有明显时间节点的贫困治理目标的提出,给各级政府反贫困施加了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成了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因动员而产生的驻村帮扶工作队成为贫困治理的关键主体,其贫困治理绩效,成为实现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保障。
这种因政府内部动员而产生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在精准扶贫中的运行机制是如何设置的?帮扶效果如何?所驻村的贫困户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工作是否满意?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在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形成过程、工作机制与贫困治理模式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6年11月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对D市10个乡(镇)39个村庄322个贫困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和对驻村帮扶工作队员的深入访谈资料,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贫困治理绩效进行评价与分析,从而提出绩效改进建议。
二、精准扶贫中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运行机制与贫困治理模式
(一)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历史演变
驻村帮扶工作队是定点扶贫的一种形式,也是在中国特色的内部动员机制推动下形成的贫困帮扶精细化运作模式。定点扶贫始于中国开始大规模政府扶贫的1986年,到2010年,全国200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总共定点帮扶了400多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早期定点扶贫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并且优先考虑西部地区,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重点县。为总结定点扶贫的工作经验,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每年都要求各省报送上年的工作总结和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其中工作总结明确要求包括进展情况、主要做法、成效、经验、问题及建议。可以说,中国在定点扶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良好的帮扶效果。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原来以贫困县为帮扶对象的定点扶贫已经不能适应精准扶贫工作的要求。精准扶贫要求“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深入分析致贫原因,落实帮扶责任人,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集中力量予以扶持”。[1]2014年4月,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24号)中提出结对帮扶的思想,要求在对贫困村建档立卡的工作步骤中实行结对帮扶,“在省级人民政府指导下,各县应统筹安排有关帮扶资源,研究提出对贫困村的结对帮扶方案,落实结对帮扶单位。”[3]这也可以说是驻村帮扶工作队和精准扶贫相结合的最初构想。2014年5月,《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中要求“各省(区、市)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工作制度,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帮扶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并建立驻村帮扶工作队、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数据库”。[1]自此,驻村帮扶工作队帮扶到户到人的驻村精准帮扶工作机制正式形成。
(二)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运行机制
1.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构成。不同地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组成人员可能有所差别。如湖北省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员主要由派出单位的人员组成,一般2-3名队员。安徽省“驻村帮扶工作队由包村帮扶单位派驻的驻村帮扶干部、联系贫困村的乡(镇)干部以及所在村的大学生村官和‘三支一扶有关人员组成,队长由驻村干部担任”。[4]本文调查样本D市根据其直接上级政府的要求,每支驻村帮扶工作队原则上包括三名常驻队员,也就是1名队长和2名队员(调研中发现,如果第一书记与驻村帮扶工作队来自同一个派出单位,则包括1名第一书记,1名队长和1名队员),若干名非常驻队员。常驻队员和非常驻队员都有固定的帮扶家庭。常驻队员在保持工作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与原单位脱岗,吃住在村;非常驻队员根据贫困村人口的数量不等,一周有固定两天入村了解贫困户情况的时间要求。
2.目标任务。各省市为落实驻村帮扶工作队制度,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明确驻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目标是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脱贫。如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省驻农村工作队(扶贫工作队)组派工作的通知》(鄂办发〔2015〕43号)、《省驻农村工作队(扶贫工作队)指导和管理办法》(鄂农队办发〔2016〕1号),安徽省委组织部、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下发的《安徽省驻村扶贫工作队管理办法》(皖扶办〔2014〕103号)等,都直接把驻村帮扶工作队定位为精准扶贫工作队,驻村队员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扶贫工作[5]。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驻村帮扶工作队实际上承担了贫困村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一是协助所在村组织开展贫困户核查认定、建档立卡、制定与实施帮扶村发展规划和贫困户脱贫计划;二是协调派出单位落实干部对贫困户的结对帮扶工作;三是协调落实并指导实施各类扶贫开发项目;四是向贫困户传达、解释各级政府的支出政策与贫困治理政策,向政府汇报贫困动态变化与扶贫进展情况。
3.保障机制。各级政府把落实驻村帮扶工作队定点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河南省郑州市要求“帮扶单位的主要领导要切实加强对定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形成队员当代表、单位当后盾、领导负总责的工作机制,帮扶对象不稳定脱贫,帮扶不脱钩”。[6]为了使驻村帮扶工作队安心工作,各级政府还出台了驻村帮扶工作队保障机制,以解除驻村队员的后顾之忧。如河南省规定每人每天生活补助70-90元、安排集中体检、报销往返常住地与派驻村之间的差旅费等[7]。
4.监督考核制度。为保证驻村帮扶工作队员真正融入所驻村庄,高质量完成精准扶贫工作任务,各地都出台了严格的管理、监督与考核机制。如《云南省驻村扶贫工作队管理办法》规定:“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及队员吃住在村,每年在岗时间不少于200天(含因公出差)。建立和完善驻村扶贫工作队日常管理工作台账……不得随意请假离岗……请假期满后要及时销假。”[8]各地还对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在组织培训和定期抽查等方面做了专门规定。
比较各地的规定,监督考核机制设置相差不大。D市要求常驻队员与原单位脱岗,全职驻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实行“五天四夜”工作制,即周一至周五的五个白天,周一至周四的四个晚上必须在所驻村,对请销假也进行了严格规定,非常驻队员一周去贫困村两次,每次都要开展入户走访工作。除此之外,由于D市在郑州市的脱贫攻坚任务最重,压力也最大,对驻村帮扶工作队还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督察机制。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驻村帮扶工作队督察小组,每月对102支驻村帮扶工作队督察一遍,并把考核结果作为班子配备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三)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贫困治理模式
驻村帮扶工作队员来自派出单位,不是专职扶贫人员,但由于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管理和运行机制都是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制定和执行的,结果使驻村帮扶工作队在精准扶贫时期成为中国贫困治理网络中,上传农村贫困动态与治理进展,下达各级政府扶贫、支农政策的关键主体。虽然在政策规定方面,要求驻村帮扶工作队协助村“两委”对贫困户进行识别、建档立卡、制定帮扶计划等,但实际上除了协助村“两委”进行贫困户识别外,建档立卡、制定帮扶计划基本都是村“两委”协助驻村帮扶工作队完成的。按照政策要求,驻村帮扶工作队向贫困户传达、解释各级政府贫困治理及支農政策,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远远超出这些工作。魏后凯和王宁指出,参与式反贫是中国贫困治理的方向。[9]驻村帮扶工作队在积极调动贫困户参与的同时,利用派出单位和个人关系,在积极向扶贫办和其他部门争取扶贫资金的同时,也积极利用派出单位和个人关系吸引企业进行产业扶贫,吸引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家庭扶贫。实践中,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努力下,现在的精准扶贫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注重与村民委员会、企业、社会组织等合作,共同致力于贫困治理工作,体现出典型的中国式合作治理模式。
合作治理既是治理模式也是治理理念的创新。正如Jody Freeman所观察的那样,中国的合作治理是“私有化”与“公共化”双向并行的过程。[10]在中国,各种形式的合作治理体现出以政府为主导、其他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特定作用的基本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协作治理更符合中国语义环境。[11]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各主体间的相互依赖性,也迫切需要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及其部门之间开展更为积极的协作。在这种形式下,合作治理不仅体现为政府与社会间的横向关系,也体现为政府间的横向关系。[12]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合作治理通过政府、贫困户、驻村帮扶工作队、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主体的共同参与,使贫困治理制度、方法和路径都有较大的改善。可以说,在脱贫攻坚压力下,动员式驻村帮扶促进和强化了扶贫工作的合作治理,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以驻村帮扶工作队为关键主体的新型贫困合作治理模式。在这种贫困治理模式下,更多地体现为以扶贫办为协调主体,以驻村帮扶工作队为具体实施主体,双方主动协作、共同决策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等各种主体参与到精准扶贫当中。同时,在不脱贫不离村的硬性规定下,又使这种多方合作治理模式更多地体现出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关键主体作用。因此,关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贫困治理绩效,也是对驻村帮扶工作队运行机制效果的关注。
三、数据来源、抽样方法与贫困治理绩效评估指标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D市(县级市)位于河南省中西部,隶属郑州市,辖区共有20个乡(镇)级单位,几乎全部地处山区丘陵地带,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较多。2015年,D市有16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26 937人,贫困户7 411户;到2106年初,D市贫困村快速下降到66个,贫困人口和贫困户分别为15 946人(占全市人口的2.9%)和3 338户。由于D市贫困人口几乎占郑州市贫困人口的一半,脱贫攻坚任务压力较大,D市政府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扶工作非常重视。目前,D市共派出102支工作队,分别入驻65个贫困村和37个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非贫困村,此外还有20支郑州市直单位的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帮扶。
本次评估数据来自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受郑州市扶贫办的委托,以第三方身份于2016年11月对D市10个乡(镇)322个贫困户入户的调查,调查对象为2016年拟脱贫贫困户。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收入问卷,为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每户进行调查时都有村干部和帮扶责任人在场,共同核算被调查贫困户的收入和支出项目;另一部分是满意度问卷,该问卷要求所有无关人员回避,只留贫困户家庭成员在场,由调查员进行逐题提问。
(二)抽样方法
首先,在D市范围内,采用多阶段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即PPS抽样法),选取10个乡(镇)为初级抽样单位;其次,以各乡(镇)村级单位为二级抽样单位,抽取要调查的村级单位;第三,以各村级单位中2016年拟脱贫贫困户为三级抽样单位,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要调查的贫困户名单。
(三)贫困治理绩效评估指标设计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在精准扶贫的重要主体地位。鉴于设立驻村帮扶工作队制度下帮扶工作具有典型的合作治理特征,本文对驻村帮扶工作队贫困治理绩效的评估也是从多个维度进行的,既包括精准识别度和以脱贫率衡量的脱贫成效这些需要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协作完成的绩效指标,也包括贫困户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满意度和被帮扶后的精神变化这些直接指标。虽然精准识别度和脱贫成效两个维度所衡量的绩效并不能完全代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贫困治理绩效,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自从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以来,实际上承担了农村扶贫的主要工作,从贫困户识别、建档立卡,到帮助贫困村寻找致富项目,再到帮助每个贫困户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利用各种资源对他们进行帮扶。可以说,自从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帮扶以来,他们就与各类扶贫主体一起共同推进扶贫工作的进展,因此,对驻村帮扶工作队扶贫绩效的评价绕不开多主体合作治理贫困的绩效。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贫困户精准识别度、脱贫成效、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和贫困户被帮扶后的精神变化四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来评价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贫困治理绩效,具体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贫困户精准识别度可分解为程序规范和贫困瞄准两个二级指标。其中,程序规范以被调查贫困户是否填写贫困申请书、参加贫困户评议会两个三级指标来衡量;贫困瞄准以被调查贫困户主观判断本村是否还有贫困家庭尚未受到救助(即瞄准精确度)作为三级指标。
2.脱贫成效用二级指标脱贫率来衡量,包括两个三级指标,一个是贫困人口脱贫率,指截止到2016年10月底已脫贫人口与2016年预脱贫人口的比率;另一个是贫困户脱贫率,指截止到2016年10月底已脱贫贫困户与2016年预脱贫户的比率。
3.帮扶满意度分解为帮扶责任人满意度和帮扶工作队满意度两个指标,其中帮扶责任人满意度用帮扶责任心、帮扶态度和帮扶能力的满意率三个三级指标衡量,帮扶工作队满意度用其总体满意率来衡量。
4.贫困户被帮扶后精神变化分解为幸福感和信心感变化两个指标,分别用幸福感是否提升和预期收入是否增加两个指标来衡量。
四、驻村帮扶工作队的
帮扶绩效评估结果分析
根据对河南省D市的入户调查数据,本文从贫困户精准识别、脱贫成效、帮扶满意度和贫困户被帮扶后精神变化四个维度对驻村工作的贫困治理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一)贫困户精准识别程序较规范,精准度较高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目标任务和监督考核机制设置,使得其队员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贫困村工作。2014年,D市各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完成了对贫困户及其家庭成员的建档立卡工作。在贫困识别程序规范方面,60.4%的被调查贫困户填写过贫困申请书,70.6%参加过贫困户评议会。该调查数据还有校正的空间,因为在所调查的贫困户中,20.1%的贫困户家庭成员最高学历为小学,这部分贫困户家庭成员年龄普遍偏大,有些贫困申请书可能是别人代签的,时间长了他们已不记得(村干部和驻村队员都表示确实有代签情况)。对于贫困户评议会,据有些村干部介绍,存在有些贫困户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不愿意参加或者有其他事情没有参加的情况。在贫困户精准识别度方面(即贫困瞄准),86%的被调查贫困户认为识别比较精准。但根据调查员对其家庭条件的观察判断,被调查贫困户中不符合贫困标准的只有4户,占调查总数的1.24%。贫困识别精准程度和贫困人口数量的测量与分解机制有关。农村贫困人口总数是由国家统计局根据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出来的,每个地方分解的贫困人口数量不等,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对分解到本地的贫困人口数量最多上浮10%。地方政府在缺乏农户准确消费支出和收入数据的情况下,主要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识别该地方的贫困人口数量。郑州市就参考了“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识别标准,这种向地方分解贫困人口数量的方法可能影响了地方贫困识别的精准程度。
(二)脱贫成效显著,脱贫速度加快
驻村帮扶工作队常驻队员“五天四夜”和非常驻队员每周两次固定入村工作时间的规定,使驻村帮扶工作队员有时间对贫困户进行更深程度的了解,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很多驻村帮扶工作队员与贫困户和贫困村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们既利用扶贫办资源,也积极争取本单位资源,甚至还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贫困村和贫困户争取更多的扶贫资源,从而加快了脱贫攻坚的步伐。根据对有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322户2016年预脱贫家庭的收入调查数据,对脱贫成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按照2800元的脱贫标准,81.2%的贫困人口和80.4%的贫困户在2016年10月底就在收入方面实现了脱贫。进一步分析发现,大部分实现脱贫的家庭都有成年劳动力在外打工收入、经济作物收入或者其他稳定收入来源。尚未脱贫的家庭除极少部分因为懒惰外,基本上都是因家里有重病成员或缺少劳动力。
(三)帮扶工作得到贫困户认可,总体满意度较高
在精准扶贫模式下,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对贫困户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形成了一种主动回应机制。帮扶满意度是贫困户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期望与帮扶工作进行比较后的主观感受,直接体现贫困治理绩效。由于驻村帮扶工作队实行帮扶到户,贫困户对政府扶贫工作的满意度主要是通过驻村帮扶工作队员的表现进行感知。被调查贫困户中,对帮扶责任人的责任心、工作态度和帮扶能力的满意率分别90.3%、86.7%和73.2%,对帮扶工作队的总体满意率为81.4%。在调查中也发现,绝大多数驻村帮扶工作队员都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对帮扶家庭的情况比较熟悉。总体满意率只有81.4%的原因主要受到帮扶能力的影响,一些贫困户虽然比较认同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但同时也表示驻村帮扶工作队员解决自家贫困问题有困难。在对驻村帮扶工作队员的深度访谈时也发现,驻村帮扶工作队可支配的资源有限,虽然甚至不惜动用个人关系向派出单位、扶贫办和社会组织、企业争取扶贫资源,但这些资源并不稳定,能争取到时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反之,帮扶工作就会受到影响。目前尚未脱贫的贫困家庭,相当一部分的贫困程度比较深,需要社会保障兜底,而根据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并不是所有的贫困户都能符合条件,驻村帮扶工作队对此也颇为无奈。
(四)贫困户被帮扶后幸福感提高较多,精神状态改善明显
曾有文章指出:“精神、思想的进步及现代化对于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带有更根本性的意义,精神扶贫才是扶贫的根本。”[13]在区域瞄准、县级瞄准和村级瞄准阶段虽然也注意到精神贫困问题,但是没有真正做到对贫困户内心需要的关注。到了精准扶贫阶段,驻村帮扶工作队机制形成后,确定了一对一的帮扶措施,每个贫困户都确定了一个固定帮扶责任人,贫困户的精神需求从而得到更多的关注。评估结果显示,80.7%的被调查贫困户认为驻村帮扶工作队对其家庭实施帮扶措施后,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安全感提高了。但问到未来几年对家庭收入的预期(即收入增加信心)时,只有55.5%的贫困户认为可能提高,这部分贫困户家里都有青年劳动力,而那些对收入预期不乐观的贫困户多是因为家庭成员年龄偏大。在深入访谈中,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多次谈到对于收入增长难以通过产业化和外出务工等渠道解决的贫困户的解决办法,希望根据贫困的成因,采用临时救助(如因病)、生活补贴(如因学业)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如因无劳动能力)等社会保障政策解决。
五、研究发现与绩效改进对策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典型特征。驻村帮扶工作队就是在政府主导下,以动员形式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并成为贫困治理的关键主体,其治理绩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对河南省D市322户贫困家庭的入户调查,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贫困治理绩效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得出以下研究发现,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绩效改进对策。
(一)驻村帮扶工作队在贫困治理网络中地位重要,但应更多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
评估结果表明,驻村帮扶工作队加入政府主导性贫困治理网络中后,对中国贫困治理绩效贡献突出,不仅加速了贫困人口脱贫的速度,也提高了贫困户生活幸福感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驻村帮扶工作队在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扶贫工作得到贫困户的高度认可。根据国家政策规定,驻村帮扶工作队在当前被识别的贫困人口完全脱贫后就会撤离,而贫困是个动态现象,相对贫困人口总是在不断变化的。驻村帮扶工作队任务完成后,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会更加分散,不易再采用这种大规模政府内部动员的形式集中扶贫,这就需要更多地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志愿组织等社会主体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以提高扶贫的效率和精准度。
(二)与物质扶贫相比精神扶贫更为重要,应加强多主体对贫困户的精神帮扶
提高贫困治理绩效,需要把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调查中发现,一些贫困户确实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但调查也发现,这种思想形成有其根源,长期的贫困消磨了贫困家庭战胜困难的意志。驻村帮扶工作队较为重视精神扶贫工作,经常鼓励和帮助贫困家庭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勇气。调查结果发现,99.7%的被调查贫困户表示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到自家介绍帮扶措施至少一次,其中2-4次的达40.4%,5次以上的达到45.5%。进一步分析发现,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入户的次数与贫困户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3。虽然只有55.5%的贫困家庭对未来收入增加持有信心,但在调查中也发现,这些家庭多因受到驻村帮扶工作队的鼓励和帮助,未来会增加经济作物收入或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要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工作队能够接近贫困对象的优势,重点加强精神扶贫,通过多方精准帮扶,让他们树立起脱贫的信心。
(三)驻村帮扶工作队扶贫资源有限且参与不足,可提高其对扶贫项目的参与力度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运行机制对驻村队员的帮扶工作进行了强制性规定。在调查中发现,这种动员式扶贫治理模式使很多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对所驻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真正投入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扶贫事业中去,尽最大努力为所驻村争取扶贫资源。这也是当前农村脱贫速度较快、成效突出的重要原因。但在调查中也发现,驻村帮扶工作队资源有限,除了為贫困户提供咨询、制定帮扶措施、提供精神鼓励等服务外,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必须向扶贫办、工作单位等争取,扶贫资源很不稳定。同时,对扶贫项目资金的使用,如资金使用方向、监督公开、效果评估等,也没有明确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参与范围与程度。因此,应加强驻村帮扶工作队对各类扶贫资金使用方向的参与权与使用过程中的监督权,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绩效。
总之,驻村帮扶工作队是我国精准扶贫时期特殊的农村贫困治理主体,其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积极参与,既加速了脱贫攻坚的进展速度,同时又培养了一批了解农村、农民和贫困情况的干部队伍。随着2020年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动员机制下产生的驻村帮扶工作队,也会逐渐退出其精准扶贫岗位。因此,总结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宝贵扶贫工作经验,丰富我国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中驻村工作扶贫理论体系,为新纳入贫困序列的贫困人口提供更加精准的扶贫理论指导也将成为笔者未来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办,民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中 国残联.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EB/OL]. http://www.cpad.gov.cn/art/2014/5/26/art_50_23765.html, 2014-05-26.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扶 贫工作的通知(厅字〔2010〕2号)[EB/OL].http://govinfo. nlc.gov.cn/lmzz/lssj/xxgb/nmgzb/20107/201108/ t20110802_948063.html,2010-05-06.
[3] 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 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http://www.cpad.gov.cn/ art/2014/4/11/art_50_23761.html,2014-04-02.
[4] 关于印发《安徽省驻村扶贫工作队管理办法》的通知 [EB/OL].http://ahfp.ah.gov.cn/DocHtml/1/Article_ 2013111880.html,2014-11-01.
[5] 省駐农村工作队(扶贫工作队)指导和管理办法(鄂农队 办发〔2016〕1号)[EB/OL].http://office.whu.edu.cn/info/ 1040/3899.htm,2016-03-31.
[6]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做好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郑办〔2014〕31号) [EB/OL].http://zzsfpb.zhengzhou.gov.cn/zcfg/317707.jhtml, 2014-08-31.
[7] 河南:强化“四项”保障 破解“四道”难题 深入扎实做 好驻村帮扶工作[EB/OL].http://www.cpad.gov.cn/art/2016/ 10/10/art_38_54005.html,2016-10-10.
[8] 云南省驻村扶贫工作队管理办法[EB/OL].http://www. fpb.hh.gov.cn/info/1025/3501.htm,2015-12-18.
[9] 魏后凯,王宁.参与式反贫困: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方 向[J].江淮论坛,2013(5):9-17.
[10] Jody Freeman. Extending Public Law Norms through Privatization. Harvard Law Review[J]. 2002,116(5).
[11] 郭道久.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J]. 政治学研究,2016(1):61-70.
[12] 敬乂嘉.合作治理:历史与现实的路径[J].南京社会科 学,2015(5):1-9.
[13] 余德华.论精神贫困[J].哲学研究,2002(12):15-20.
[14]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 2015(5):147-150.
[15] 汪三贵,刘未.“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习 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 究,2016(1):40-43+93.
[16] 虞崇胜,余扬.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 础分析[J].行政论坛,2016(1):22-25.
[17] 庄天慧,陈光燕,蓝红星.精准扶贫主体行为逻辑与作 用机制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5(6):138-146.
[18] 王鑫,李俊杰.精准扶贫:内涵、挑战及其实现路径——基 于湖北武陵山片区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6(5):74-77.
[19] 陈升,潘虹,陆静.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东 中西部的案例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6(9):88-93.
[20] 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 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Work Team in Village:Taking D City of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ING Hui-xia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China)
Abstract: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quires targeted assistance to poor villages and poor families. For this reason,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n intern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form a new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poverty with the work team in villages as the key subje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work team in village,this paper evalua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of work team in village from poverty identification,effectiveness,satisfaction of the poor families and their mental changes with the survey data of household in D city of Henan Province. In view of the reasons of insuffici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limited resources of the work team in village,which affect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the work team in villag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its 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ultiple subjects,strengthening spiritual support and enhanc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Key Words:targeted anti-poverty;work team in village;poverty alleviation;performance eval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