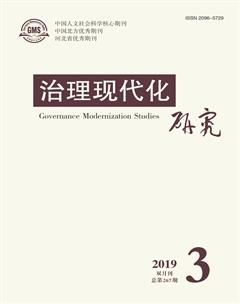新媒体环境下舆情的特点及政府应对策略
曹峰
摘 要: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中,以手机为基本载体的新媒体已经成为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最重要途径。由于新媒体具有自主化、便捷化、实时化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点,舆情通过新媒体生成和发酵的概率大大增加。面对新媒体的汹涌来袭,政府舆情调控面临预警机制不完善、应对程序繁复、研判技术欠缺等挑战。为此,政府要做好舆情调控工作,必须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提升整体防范和综合执行能力,同时还要培养理性平和的社会文化范围,多管齐下,整体推进。
关键词:新媒体;舆情特点;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53-06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较之以往,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从信息传递与沟通的角度看,新时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网络化、信息化。在网络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以智能手机为“器具”的新媒体又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信息传递和沟通载体。在新媒体普及化的大背景下,微信、QQ、微博等自媒体信息源无处不在,只要任何手机用户手指轻触一下,一个新的信息即可瞬间向全世界公开发布并迅速传播。当各种混杂的信息汇集成流,大量传播并造成较大影响时,网络舆情便可能形成。因为所谓“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也就是说,在某个涉及社会性事项的信息被传播并形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下,民众对党和政府就会产生连锁性的社会政治态度,这时舆情就会产生和形成,其主要的焦点在于民众对党和政府施政的看法或议论。显然,这种群体性的看法和议论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引导,就会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构成冲击,严重时还会影响党和政府的执政安全。这种舆情特点在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化、信息化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舆情引导工作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2](P54)舆情的引导和化解已成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必须要应对的事关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会对新媒体环境下舆情的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并就政府应对舆情的策略进行探讨,为党和政府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思路和借鉴。
一、新媒体环境下舆情的特点
在新媒体普及的新时代,舆情(实质是网络舆情)的发生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可能也更容易发生。现就当前舆情发生及产生影响等方面的特点进行简单梳理归纳。
第一,发生的即时性。所谓发生的即时性,就是指舆情似乎在一瞬间爆发,可能没有任何的征兆或前期的显性动因。也就是说,舆情的发生似乎完全在舆情管控部门的“掌控”之外。某种程度上讲,舆情发生的即时性特点,是对舆情管控部门预防工作的一种“否定”,或至少和预防工作构成了一种长期紧张的“张力”关系。舆情的发生为什么会显示出即时性的特点呢?究其原因,这是新媒体技术广泛应用的必然结果。在新媒体普及的大环境中,人人都是可能的信息源,“网民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制作、选择和发布任何信息,甚至可以量身制作和任意编造各种虚假信息,内容上的多元性,既有褒扬赞赏,也有诽谤中伤,各种信息兼收并蓄,良莠不齐,致使网上负面信息泛滥成灾。”[3](P35)显然,当网民(特别是手机网民)可以随时拍照或录视频的时候,各类信息的发布就具有了十分明显的偶然性特点,信息的发布可能跟网民瞬间的体验、情绪、处境等“不确定”因素密切相关。在信息“发布流”中,大部分信息瞬间就被其他信息淹没,但也有某些信息一旦发布,便可能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并被大量转发,舆情由此也在瞬间生成。
第二,内容的聚焦性。所谓内容的聚焦性,就是舆情之所以是舆情,是由于公众的高度关注所导致。也就是说,在新媒体环境下,并非网民发布的所有内容都会形成聚焦效应,相反,大部分的信息发布之后就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不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样的信息内容能够快速形成聚焦效应呢?根据以往舆情发生的多数案例和规律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内容涉及民生的负面现象。民生问题,关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一旦出现与民生相左的负面事件,被网民发布出来,就会在瞬间形成聚焦效应。如与生态破坏相关的事件、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乱收费事件、拖欠民工工资事件,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民众日常关注的焦点,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事件一旦被“曝光”,就会变为舆情事件。其二,内容涉及执法的负面现象。很大程度上讲,执法者代表政府的形象,执法者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如果出现执法者“欺压百姓”的现象,一旦被转为图文信息发布出来,就会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情绪,舆情随即也会发生。其三,内容涉及道德的负面现象。道德事件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特别是公众人物及特殊群体表现出的道德负面现象,是公众关注的聚焦点,因此,一旦这些群体的负面道德现象被发布出来,也会瞬间形成聚焦效应,造成舆情。其四,内容涉及突发灾难事件。这些灾难事件可能是人为的,也可能是天灾,但是只要发生,就会迅速形成聚焦,构成舆情。
第三,影响的广泛性。所谓影响的广泛性,就是在新媒体背景下,某些事件一旦构成舆情,就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几何级增长的点击量,同时被广泛地转发、传播,在全社会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新媒体背景下,舆情影响的广泛性特点,还很容易衍生出一種群体效应,即“群体极化”。“所谓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决策的作用下,个人可能更为冒险或者更为保守,且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容易走极端。”[4]由此推之,在网络事件尤其是影响重大的舆情事件面前,社会公众很容易集体性走向极端,产生“一边倒”的现象,特别是在某些看似正确的焦点观点“引领下”,公众很容易失去正常理智和判断力,出现过度情绪化的群体态度偏向现象。而且,根据有关研究表明,“群体极化”倾向在网上发生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5](P47-51)很显然,这种群体极化的倾向,其结果往往是负面效应要远远大于正面效应,并且这种负面效应像瘟疫传染一样,将会在极短时间内在全社会引起巨大的“共振”效应,这种影响超越了阶层、领域、年龄、社会地位等限制。换言之,新媒体背景下,舆情影响的广泛性特点,如果得不到正确的疏导,将会造成危机性的舆论氛围甚至引发现实性的“群体事件”。
以上所述三点,是新媒体环境下舆情的主要特点。此外,舆情还具有发生源头的多样性、运行的复杂性、影响的时效性等特点,在此不再一一分析论述。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舆情所有特点的生成,均和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应用的广泛性、随意性、便利性和偶然性等特点密切相关。
二、政府舆情调控面临的挑战
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舆情发生的即时性、内容的聚焦性、影响的广泛性等特点,给政府的舆情调控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以下结合舆情的规律和我国政府调控的现状,对当前政府舆情调控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归纳总结。
第一,预警机制不完善的挑战。所谓预警,就是舆情爆发前的预防和警惕。当前,政府在舆情调控方面,面临的最基本挑战就是预警机制的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去几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立法工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涉及网络、自媒体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有较大的突破。但总体而言,相对于现实领域,网络和自媒体方面的法律规范特别是信息发布领域的法律规范仍很不完善,网络和自媒体等虚拟领域的法律法规跟不上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存在较为严重的滞后性。因此,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原本“网络社会本应与现实社会一样受到法律约束,但目前网络乱象丛生,普遍存在法律滞缓和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6](P78)在这种现实情况影响下,政府很大程度上讲只能“坐等”舆情的发生,而很难从法律规范的角度预防和限制舆情的爆发。其二,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素质错位”。所谓“素质错位”,就是工作人员素质和自身岗位的要求不符甚至相差甚远。按照正常的条件要求,网信办工作人员应该同时兼备两种素质:即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但现实情况则是,网信办工作人员往往只具备其中的一种素质,要么政治敏锐性较强,但缺乏信息分析处理能力;要么信息分析处理能力较强,但缺乏政治敏锐性。这种人员素质的现实条件限制,导致了政府在舆情预警工作方面的被动局面。
第二,应对程序繁复的挑战。所谓应对程序,主要是指在舆情发生之后,政府部门应对所必须走的流程。从我国舆情调控的应对机制来看,当舆情发生之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请示程序过于繁复,是舆情调控面临的另外一个现实挑战。因为,这种繁复的程序可能会导致以下几种不良后果:其一,错过了最佳的调控时机。当某个时刻在某个领域发现舆情的“苗头”之后,基层职能部门需“打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等待层层审批之后,才能去干预。换句话说,在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明确“指令”之前,基层部门无法也不敢主动去实施舆情干预。这样的结果,就是很有可能错过了舆情调控的最佳时机,错过了调控舆情于“萌芽状态”的机遇。其二,难以将舆情引向良性的结果,将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由于舆情的发生往往都是始于“小事”,来源于基层,因此,从理论上讲,基层网信机关(人员)对于掌握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但经过层层“报告审批”之后,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可能被复杂化甚至被扭曲。而只能“等待指令(也许是错误指令)”行事的基层网信机关(人员)在接到“指令”之后,严格按照“指令”应对就可能偏离了事件原本可以引导去的良性方向,导致不良结果发生。
第三,研判技术欠缺的挑战。当前,从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来看,网信办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职能部门(一般挂靠在宣传、新闻等主管部门之下),主要负责舆情的研判和调控工作。但是,从实际的工作运行来看,各级网信办尤其是基层网信办在工作中仍面临一个十分明显的挑战,那就是舆情研判技术普遍欠缺。舆情研判技术欠缺的主要表现是,当舆情处在“潜伏期”和“爆发期”等不同阶段的时候,欠缺成熟技术手段进行研判并有效干预:在舆情“潜伏期”,难以通过技术手段研判其发展走向并将其“熄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在舆情“爆发期”,则难以通过技术手段研判其发酵程度并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或引向正面效应。相反,當前使用的技术手段,例如不断封网站和不断删帖,十分机械和僵硬。可想而知,这种机械和僵硬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其结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引起网民和公众的猜疑甚至不满。而研判技术欠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机协调配合不够。当前,舆情管控的部门主要是各级网信办,而政府专业监控和分析数据的人才则主要在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网信办工作人员则主要是理论宣传。在相关职能部门专业人才如此分布的现状下,各部门要有效研判舆情,必须进行有机的协调配合。但在现实工作中,这种跨部门的有机协调难度相当大。其二,大数据专门人才的缺乏。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大面积普及和飞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如何运用大数据来研判舆情,则在政府工作中尚未起步,其主要的原因是大数据专门人才进入政府职能部门特别是网信办工作的数量还十分稀少,大数据人才主要流向了高薪的IT行业。
以上主要是从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角度总结舆情调控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些现实挑战的存在,明显影响了舆情调控的效率和质量,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三、政府的舆情应对策略
较之传统社会,在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发生的概率和可能性大大增加,其发酵和传播的程度、影响的范围等也相应扩大。因此,对于现代政府而言,如何应对舆情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加强舆情应对的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主要就是理念(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面的宏观设计。在新媒体普及的信息化社会环境下,舆情应对的顶层设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建设网络强国。所谓建设网络强国,是时代的要求,是稳定执政之基的呼唤。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7]也就是说,贯彻落实网络强国的顶层设计理念,核心就是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这是应对日益复杂的舆情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政府层面,应特别加大对高层次、高素质(技术素养与政治素养兼备)网络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设立专业技术岗(对应于行政岗级别和待遇),为专业人才提供事业发展的空间。其次,要加强法律规范建设。如果说网络强国是侧重于理念层面的顶层设计,那么法律规范则是侧重于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法律规范建设方面,应着重加强两个方面:其一,完善网络信息发布的法律法规,做到全覆盖、不留灰色地带和死角。其二,完善网络安全的主体责任制。这里的主体应包括政府(机构)主体和公民(个人)主体两个方面。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明确主体发布信息的相关责任,切实推行“谁发布、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在此,特别应严厉惩处发布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危害国家安全信息的主体,从源头上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将舆情发生的可能性控制到最低程度。
第二,提高舆情应对的整体防范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所谓整体防范能力,是指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各部门都具有较强的舆情防范能力。提高舆情应对的整体防范能力,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各部门的防范能力,二是全体公职人员的防范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下,可能引发舆情的信息源无孔不入,因此,要防范舆情,就应该是所有政府部门、所有公职人员都要承担责任,而不仅仅限于网信办、国安局这些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均应设立专门的舆情管控机构,负责所在单位舆情的管控工作。同时,应该赋予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部门“第一时间”管控舆情的权力(先发现先治理,减少审批请示程序)。而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就是要做到杜绝自己成为舆情发生的源头。因此,这也对政府公职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提高自身对各种信息的甄别能力,其次要恪守原则,特别是自律原则。在网络和自媒体生活中,坚决不随便转发和自主编辑各类未经证实或带有不良政治倾向的信息,只有这样,才可能杜绝从公职人员身上产生舆情。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讲,“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道德伦理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在网络中的言行不再依靠现实社会传统习惯和道德标准,而是通过个人内心信念来维系。”[8](P89)所谓综合执行能力,则是当舆情发生时,政府部门有能力运用成熟方案去及时应对和疏导。提高综合执行能力,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是要制订一整套规范、有效的综合应对方案,不管发生什么样的舆情,政府各部门按照这一套规范方案来应对就不会有错误。比如,建立权威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规范的信息发布制度等,特别是应该建立一套与舆情发生地或部门(基层部门所在地)相适应的舆情调控方案,这是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第三,大力培育和营造理性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除了以上所述的两种应对策略外,要从根本上做好舆情应对工作,就要从舆情发生的源头做工作,具体就是“软化”“滋润”各类可能的舆情主体、千千万万的社会个体。而要达到“软化”和“滋润”社会个体的目标,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营造理性和谐的文化氛围。因为我们知道,从主体角度来看,舆情的发生源头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的”舆情制造主体;另一种则是“有意的”舆情制造主体。“无意的”主体往往是出于好奇、新鲜、好玩等心理,多是以围观立场将信息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有意的”主体则是一些居心不良或受到敌对势力控制的人,以“守株待兔”的立场甚至人为制造的行径来制造或捏造“新聞”,并且有目的地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向外界发布信息,以达到引起公众聚焦的目的。以上所述两种主体情况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信息发布的主体都欠缺一种理性平和的心态,可以说,前者是一种“癫狂喜悦”的心态,后者则是一种“阴沉愤怒”的心态。要改变以上两种非理性的社会心态,从源头上减少舆情发生的可能性,政府层面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其一,营造民主平等的“官民对话”生态。很多舆情的发生,是民众对政府的质疑和不满所致,以至于某些人随时“坐等”政府丑闻,制造舆情。因此,民主平等的“官民对话”生态,对于舆情防控十分关键,也只有民主平等了,民众的心态才可能理性平和,才不会随意或蓄意制造“事端”。这种“官民对话”的生态,就是官民对社会事务合作管理的正常生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9]其二,推行信息公开制度。当舆情开始发酵时,政府及时的信息公开显得十分关键,如果是“谣言”,政府应该大胆及时澄清事实,还事实于公众;如果是“真相”,政府则应该及时作出诚恳表态,遏制事态的继续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均应设立专门的权威发布平台或新闻发言人岗位,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可以说,这是一种政府担当的理性治理情怀,政府带好头,公众盲从的情况就会减少许多,舆情的扩散就会得到限制。其三,切实改善民生。纵观众多舆情事件,大多数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很多情况是民众的呼声得不到回应,一旦有与此相关的事件发生,民众就会非常关注,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个人和组织,经常利用民众的非理性情绪,推波助澜,以达到丑化政府甚至颠覆政权的目的。所以说,培育和营造理性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政府首先应该重点考虑民生,切实做好各项改善民生的工作,以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此改善民众的非理性心态,从源头上减少舆情发生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环境下,舆情产生的可能性变大,且内容繁复、影响广泛,各级政府因此面临着巨大的舆情调控挑战。政府要做好舆情调控工作,必须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提升整体防范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同时还要培育和营造理性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多管齐下,整体推进。
参考文献:
[1] 王来华,林竹,毕宏音.对舆情、民意和舆论三概念异同 的初步辨析[J].新视野,2004(5):64-66.
[2] 王正平.生态、信息与社会伦理问题研究[M].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3.
[3] [荷兰]尤瑞恩·范登·霍文,[澳大利亚]约翰·维克特. 信息技术与道德哲学[M].赵迎欢,等,译.北京:科学出 版社,2014.
[4] 孙莉玲.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研判与治理[J].江海 学刊,2016(3):204-209.
[5]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 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M].曹 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 习近平.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 成为网络强国[N].人民日报,2014-02-28(01).
[8] 赵兴宏.网络伦理学概要[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0.
[9] 俞可平.改善我國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J].当 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1):4-10.
The Governments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CAO Fe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Zhongshan Polytechnic,Zhongshan 528404,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era,new media with mobile phone as the basic carrier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release and spread information. As new media have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over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autonomy,convenience and real-time,the probability of public opinion generation and fermentation through new media has been greatly increased. In the face of the surge of new media,the reg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imperfect warning mechanism,complicated procedures and lack of research and judgment technology. Therefore,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do a good job in public opinion regulation,it must not only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but also improve the overall prevention and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ability. At the same time,it should also cultivate a rational and peaceful social and cultural scope,and promote it as a whole under the multi-pronged approach.
Key Words:new media;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counter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