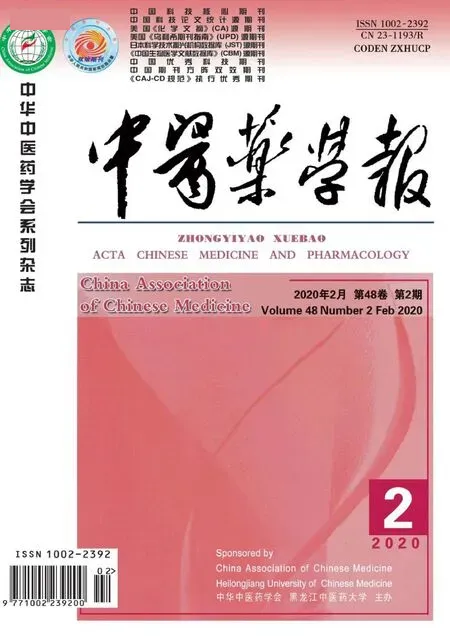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高艳奎,申睿,朱向东,柳荣,王欢,钟兴腾
(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反复发作的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明确的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其病变主要累及结肠黏膜及黏膜下层。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等症状,已被WHO列为现代难治病之一。目前普遍认为UC的发生、发展与免疫功能、凝血功能、脂质过氧化等因素密切相关[1-2]。中医学虽无此病名,但在长期研究中根据本病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常将其归属于中医“肠澼”“泄泻”“痢疾”“肠风”“脏毒”“下利”“滞下”等病的范畴[3]。现代医学治疗UC以氨基水杨酸类、免疫抑制剂、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等为主,但长期使用存在毒副作用大且停药后易反复等问题。中医药具有多系统、多环节、多靶点调控的特点,其疗效肯定、副作用小、复发率低,在预防和治疗复杂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许多学者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借助现代研究方法,在中医药治疗UC的作用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就近年来中医药治疗UC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总结如下。
1 调节免疫功能
免疫调节异常与UC发病密切相关。由于UC患者肠道黏膜固有层中有大量的炎症细胞浸润伴有局部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异常,且临床应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本病有效[4],因此可通过调节免疫功能从而达到治疗UC的目的。对比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后会伴有多种毒副反应,中医药通过调节T细胞亚群、细胞因子及炎症信号通路治疗UC是研究的热点[5]。
1.1 调节T细胞亚群
T淋巴细胞是人体最重要的免疫细胞之一,根据细胞表面分化抗原( CD) 的不同,可将T细胞主要分为CD4+T细胞与CD8+T细胞两大亚群。根据其功能的不同,T淋巴细胞分为:细胞毒性T细胞,其表面主要标志物为CD8;辅助性T细胞(Th),其表面主要标志物为CD4及调节性T细胞(Treg)。在免疫应答中,T 细胞各亚群代表的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不同,只有当T细胞各亚群的各数值比例相对平衡、协调时,机体免疫系统功能才得以正常发挥[6]。免疫调节失衡是引起UC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CD4+/CD8+是反映T细胞功能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二者在正常人体比例为1.4~2.0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将造成免疫功能失调[7]。肠黏膜上皮含有的上皮间淋巴细胞( IELs)主要是T淋巴细胞,分为CD4和CD8 两种亚型[8]。UC发生时,抗原对T细胞抗原受体的反应敏感性增强,炎症部位的T细胞活性增加,黏膜免疫反加剧并释放细胞因子,进而产生一系列组织损伤[9]。较正常或缓解组而言,活动期UC患者的CD8+T细胞明显下降,CD4+/ CD8+比值上升[10]。中医药通过降低UC大鼠CD4+,升高CD8+,降低CD4+/CD8+比值来调节T细胞亚群功能,降低免疫反应程度,从而减轻炎症损伤。Tao M等[11]通过TNBS诱导建立大鼠UC模型,发现加味乌梅汤可明显改善UC大鼠血中(CD4+/CD25+)CD4+T细胞水平。证明中医药可以通过抑制CD+T细胞各亚型Thl、Th2、Thl7及Treg的比例失衡,从而发挥治疗UC的作用。
1.2 调节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主要是由免疫细胞和某些非免疫细胞经刺激后分泌的能够调节细胞功能的小分子肽,作为体内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其产生和相互作用对机体防御疾病和维持生理平衡具有重要意义[10,12]。根据细胞因子的功能可将其分为细胞白介素、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生长因子及趋化细胞因子等[13]。根据细胞因子在炎症反应中的不同作用,又可将其分为由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IL-1、IL-2、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促炎细胞因子,与主要由T细胞产生的IL-4、IL-10、IL-13、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抗炎细胞因子;前者主要通过介导细胞免疫反应,从而诱导炎症发生;后者通过参与B细胞活化与体液免疫反应且下调促炎细胞因子从而发挥其抗炎效应[14]。
中药可通过降低IL-1等促炎因子,上调IL-10等抗炎因子,在协调二者平衡间调节免疫、抑制炎症反应,从而发挥治疗UC作用。罗世英等[15]研究发现白花蛇舌草总黄酮可通过下调UC小鼠促炎因子IL-8和TNF-α的表达,上调抗炎因子IL-10的表达而治疗UC。MENG X等[16]研究发现,复方苦参汤水提取物可改善经DSS诱导的UC模型小鼠的症状与结肠黏膜组织病理损伤,且复方苦参汤可降低IL-1β,TNF-α和磷酸化NF-κBp65的水平,并降低ROR-γt,IL-17A,STAT3,IL-6在结肠组织中的表达。因此,复方苦参汤可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并有效减轻UC模型中肠黏膜的炎症反应。
1.3 调控炎症信号传导通路
Toll样受体(TLR)/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与UC发病机制密切相关。肠道固有免疫反应需要微生物识别区的模式识别受体(TLRs)来识别[17]。TLRs作为免疫系统中的细胞跨膜受体,能够识别并结合病原体固有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通过激活下游信号传导分子,激活核因子-κB引起炎症介质表达,进而介导肠道黏膜的免疫反应[18]。Rachmilewitz等发现UC大鼠结肠黏膜组织中活化的NF-κB及TNF-α和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的表达上调,而核转录因子κB抑制蛋白(IκB)水平下降[19]。
中医药通过抑制TLR4、NF-κB通路活化的、调节免疫功能、减少促炎因子释放的途径,发挥其治疗UC的作用。ZHAO Z J等[20]研究发现,用小白菊内酯灌肠给药可显著降低UC小鼠结肠组织TNF-α、IL-1β含量,阻断κB抑制因子α(inhibitor of kappa Bα,IkBα)磷酸化和降解,抑制p65磷酸化,进而抑制NF-κB通路活化,发挥其治疗UC的作用。FENG J等[21]研究证明黄芩苷可下调DSS诱导的UC模型大鼠结肠中TLR4和NF-kB p65的表达及IL-6与 IL-13的表达,上调IL-10的表达,这表明黄芩苷可能通过阻断TLR4/NF-κB信号转导路径从而缓解炎症反应。
2 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
氧自由基(OFR)致肠黏膜屏障损伤是近年来研究的重要课题。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 oxide dismutase,SOD)和丙二醛(MDA)在氧化-抗氧化平衡系统中最具代表性。SOD是存在于生物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能有效催化超氧化自由基分解为H2O和氧分子,从而抑制肠组织中的脂质过氧化反应,稳定细胞膜;MDA是OFR触发细胞膜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反应的产物[22]。UC动物模型氧自由基含量增加,结肠组织中的SOD活力下降。损伤因子激活免疫细胞,产生有细胞毒作用的活性氧与自由基,非特异性损伤黏膜细胞,同时活性氧参与脂质过氧化反应,产生MDA等脂质过氧化产物,促进前列腺素样物质、白三烯、趋化因子等炎症介质的合成和释放,介导炎症反应,导致肠黏膜损伤[22-23]。
中医药通过升高UC模型鼠SOD活性,降低过氧化物酶(MPO)活性和MDA含量,进一步提升机体抗氧化能力,调节紊乱的自由基代谢,减轻肠黏膜的损伤,从而治疗UC。朱文龙等[24]研究发现,粉防己碱能升高UC 模型鼠SOD活性,降低MPO活性和MDA含量,调节紊乱的自由基代谢,减轻肠黏膜的损伤,从而治疗UC。柳越冬等[25]发现加味通腑汤可增加溃疡性结肠炎大鼠模型中结肠黏膜组织SOD的活性、降低结肠黏膜组织MDA的含量、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从而减轻结肠组织黏膜组织损伤。
3 改善凝血功能
研究发现,血液高凝状态及血栓形成是导致UC恶化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血小板体积缩小、活化增加、促炎和促血栓作用增强,加重肠黏膜的缺血、缺氧,进一步损伤肠黏膜[26-27]。因此,改善患者凝血功能、降低血液高凝状态、促进血液循环,可能是治疗UC的有效途径之一。血栓烷A2(TXA2)具有很强的促进血管收缩和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是临床上常用的血小板活化标志物,代谢产生无活性的血栓烷B2(TXB2);PGI是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释放的一种抗血小板聚集和具有舒张血管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前列环素(PGI2)代谢生成6-前列腺素F1α(6-keto-PGF1α)。正常情况下TXB2、6-keto-PGF1α两者处于稳定水平,从而维持血液正常状态[28-29]。研究表明[30],在UC急性期,UC患者体内TXB2升高,血小板黏附、聚集等功能增强,血浆6-Keto-PGF1α含量降低。
中医药可通过降低血浆中TXB2含量、升高6-keto-PGF1α的含量,以维持TXB2及6-keto-PGF1a两者相对的动态平衡,延长凝血酶原时间、降低血小板活性、降低血液黏滞性等进而改善微循环,发挥治疗UC的作用。有研究[28]发现三七有效成分人参皂苷Rg1可下调DSS诱导的UC小鼠血浆TXB2水平,上调6-Keto-PGF含量,对UC治疗机制可能与其改善机体微循环,从而抑制炎症反应有关。清肠解毒汤具有清热化湿解毒、活血通络的作用,屈杰[31]发现经加味清肠解毒汤治疗后UC模型大鼠血浆TXB2水平下降、6-Keto-PGF1α量上调、TXB2/6-Keto-PGF1α比值降低,这表明加味清肠解毒方可能通过抑制血小板过度活化发挥治疗UC的作用。
4 下调黏附分子
黏附分子作为一种受体型跨膜糖蛋白,能介导细胞黏附、趋化、淋巴细胞归巢等参与炎症反应。其中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l,ICAM-l)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IGSF)。研究发现活动期UC患者外周血ICAM-1显著增高, 在肠组织中表达也增高, 且与病情轻重呈正相关[32]。近年来,ICAM-1 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关系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石科等[33]研究发现参苓白术散可以降低UC模型大鼠结肠组织和血液中ICAM-1与V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的表达,从而达到修复、重建及治疗UC的目的,其原因可能与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结肠黏膜归巢有关。
5 调节胃肠激素
血管活性相关肠肽(VIP) 参与调解胃肠黏膜的机械、化学、免疫屏障及肠道动力,并能有效保护肠黏膜的屏障功能。VIP具有强大的抑制胃肠道平滑肌和括约肌的作用,可抑制胃蠕动和胆囊收缩,其分泌异常可能致使胃肠道动力和分泌功能紊乱。P物质(SP)为11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它既可以是激素的形式,亦可作为神经递质参与胃肠道运动的调控,强烈促进消化系平滑肌收缩, 刺激小肠、结肠黏膜分泌水和电解质等[34-35]。
中医药可通过上调VIP、SP等胃肠激素的分泌,缓解肠平滑肌痉挛,减慢肠蠕动,使肠分泌适当减少,从而减轻腹泻、腹痛等症状。戴彦成等[35]研究发现经参青方给药后UC模型大鼠结肠VIP和SP的表达上调,因此参青方可能通过修复受损结肠黏膜、改善病变部位神经递质VIP和SP表达, 从而调节肠动力。
6 调节一氧化氮(NO)
NO作为一种生物活性较强的免疫分子与炎症递质,广泛存在于胃肠道、食管中,在炎症发生过程中起保护或杀伤毒性及促进炎症的双重作用。生理数量下NO的对消化系统起重要的保护作用,而其产生过多或胃肠道平滑肌对其敏感性增强则可导致UC的发生。NF-KB、IL-6、IL-8、IFN-γ 等细胞因子能刺激炎性细胞诱导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 )蛋白表达上调,从而产生大量NO参与炎症反应,进一步损伤肠道黏膜组织[36-37]。IKONOMI等[38]发现,在UC患者肠黏膜组织中NO合成增加,表明NO可能在UC致病过程中参与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
中医药通过减少NO的生成,减轻NO引起的损伤,进而发挥治疗UC的作用。实验研究表明经四神丸治疗后,UC模型大鼠结肠组织中的NO含量减少且iNOS活性降低,这表明四神丸可有效降低NO的浓度及的iNOS 活性,从而抑制脂质过氧化、降低细胞毒性,以达到消除炎症、修复肠黏膜的作用[37]。
7 调节肠道菌群
近年来,UC与肠道菌群的关系成为其发病机制的研究热点。人体胃肠道内寄居着种类繁多的微生物,称之为肠道菌群。各菌按一定比例组合且互相制约、互相依存,构成一种生态平衡。研究表明[5]UC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失调,致病菌增多,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数量减少,最终导致致病菌及其分泌的肠毒素增多,从而损伤肠上皮细胞,且正常细菌种类数量的改变也将影响肠上皮细胞能量代谢,导致肠上皮细胞受损,诱发炎症反应。又有研究指出[39],肠道菌群会影响肠道炎症性疾病状态下的肠黏膜的免疫系统功能,进而诱发机体产生免疫反应,导致UC的发生。SWIDSINSKI等[40]发现,UC患者的粪便菌群中大肠杆菌和肠球菌的数量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增加。张婷等[41]为研究炎症性肠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变化,在无菌条件下采集新鲜粪便并在培养基上培养后发现,与对照组相比,UC患者高炎性指标组肠道菌群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酵母菌数量显著增高,从而造成肠黏膜微生态失调,肠上皮细胞对肠腔菌群信号感知、传递和做出反应的功能出现紊乱,继而免疫应答失调,同时菌群失调还造成肠黏膜缺乏必要的微量营养物质(短链脂肪酸等)和氧化还原电势,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黏膜损害。
翟月华[42]等观察56例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发现,经清肠愈疡汤经验方口服、中药灌肠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内容物中肠球菌、肠杆菌数量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显著降低,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丁酸梭菌的数量则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显著升高,且患者免疫功能指标IgA、IgG、IgM、CD4+、CD4+/CD8+水平明显降低,CD8+水平明显升高。He等[43]发现黄连可显著增加粪产碱菌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丰度,抑制大肠杆菌、脱硫弧菌C21-C20的生长。再者肠黏膜屏障可被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破坏,UC患者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数量明显升高。实验研究发现清肠化湿汤可显著促进双歧杆菌、鼠李唐乳杆菌的体外生长,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的体外生长,从而有效缓解肠黏膜损伤[44]。
8 其他
除上述机制外,胡义婷等[45]发现UC患者多焦虑、抑郁,以疏肝解郁胶囊治疗后能明显改善患者情绪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及预后,并减轻机体炎性反应水平。纪佳等[46]发现STAT3可通过介导炎性因子的信号来调控细胞的免疫反应,UC大鼠中IL-6mRNA、JAK mRNA、STAT3 mRNA及HMGB-1 mRNA呈高表达状态,黄芩汤通过抑制IL-6、JAK、STAT3信号通路的激活以及HMGB-1的表达,从而降低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减缓炎症反应,从而改善肠道功能。
另外,肠道中Cajal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 of Cajal,ICC)的分布、结构和数量异常可能也是UC患者肠动力紊乱的产生机制之一。戴彦成等[47]通过研究UC肠动力紊乱与ICC自噬间的联系,发现UC小鼠结肠平滑肌条收缩振幅降低、收缩频率增加,这与结肠炎患者肠道的动力学非常相似,结肠ICC内结构较正常组异常,结肠组织中的Beclin1、LC3-Ⅱ蛋白表达增加出现了过度自噬,从而导致了细胞的程序性死亡,表现为ICC标志性蛋白c-kit的表达减少,即此细胞的数量减少。健脾清肠方可有效抑制ICC过度自噬,调控ICC/SCM网络通路,增加平滑肌条收缩振幅、降低收缩频率,使得结肠平滑肌的推进活动趋于正常,有效调节肠道动力。
9 小结与展望
UC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其病程长且易反复发作。当前粪菌移植作为其新型治疗手段,其疗效显著但因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尚不明确[48-49]。中医药治疗UC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且其复方及有效成分种类繁多,具有多靶点整体调节的特色。与当前较为先进的粪菌移植及西药在治疗UC过程中易发生恶心、呕吐、发热、腹痛等不良反应相比较,中医药以其安全、低毒、有效等特点在调控肠道菌群以及改善肠道动力以治疗UC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医药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靶向给药,从而通过调节免疫、抗炎、抗氧化、调控肠道菌群等多种机制治疗UC,明显改善临床症状,且其副作用小、疗效稳定。
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UC方面虽取得很大进展,但在实验研究方面仍有欠缺,主要表现在不同证型对药物的选择、剂量以疗程较为模糊,使得中医药治疗UC缺乏规范化、严谨化。因此,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模型以及更加科学的药效评价标准将成为此病的研究目标,为中医药治疗UC提供更好的研究平台。并且还需继续探索运用中医理论辨证分析并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手段,深入研究中医药调节肠道菌群治疗不同证型的UC的作用机制和靶点,以期为临床上治疗UC提供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