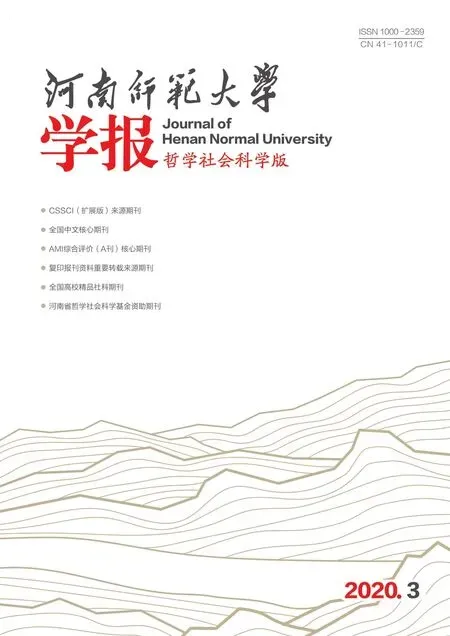在“破坏”与“建设”之间
——论1919-1949年冰心作品中的女性及其女性观
童宛村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作为一个以母爱、童真、自然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女性作家。冰心的女作家身份常因其对儿童读者所发挥的积极影响而被肯定。相较于同时期女性作家,冰心的女性观在今天看来往往被认为是不够进步的。她的作品缺乏“两性”之间情爱的描写,因而被认为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而她通过歌颂“母爱”而创造的“新女性神话”,虽然安慰着新旧交替时代的苦闷青年,但她对妇女家庭责任的强调,又与女性冲破封建家庭藩篱的个性解放思潮龃龉,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改良了的“良妻贤母主义”,是“从问题面前逃走了”[注]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论者往往对此颇有遗憾之词,也因此将冰心与同时期在性别问题上更具辨识度和激进意识的女性作家庐隐、丁玲等人区别开来,认为其作品中旧意识的内容居多,而新意识的内容较少,甚至有海外论者认为:“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幸福的家庭氛围与旧文学的滋养,自然使冰心的作品气质呈现出深厚的国学素养和中庸思想。但仅局限于此来理解冰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她的女性观,也会一定程度上遮蔽冰心所提出的关于女性的更为驳杂的时代议题。对于这位19岁以女学生身份登上文坛,并以“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著称的作家来说,其写作行为本身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意识,不但在思想界造成了中西之间“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的激烈冲突,也造成了对千年来中国女性主要活动场所——家庭的冲击,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所面临的时代新题,成为冰心关注女性问题的出发点,也始终贯穿于其新文学写作过程中。1919-1949年是冰心作品中描写女性形象,探讨女性问题的重要写作时段,本文试图通过对冰心这一时期作品中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意识的分析,探究冰心的女性观。
一、女性问题的提出:破坏与建设时代的新女性
(一)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对“五四”个人主义思潮的反思
1919年,冰心以女学生身份登上文坛之时,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将女学生为代表的一代“新女性”推向“个性解放”的高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将们将新文化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纲常伦理和旧家庭制度,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流行又成为女性冲破家庭藩篱,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最好时代注脚。一时间,反对“包办婚姻”,要求“恋爱自由”;反对“封建大家庭制度”,要求“个性解放”,成为青年中最为时髦的名词。但在冰心的文章与小说中,她对当时女学生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风气并不支持,且多有反思。在初登文坛的第二篇文章中,冰心就以《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为题表达了对女学生“个性解放”的思索。冰心以“破坏”“建设”这一对反义词破题,认为当时以欧美为模范表式的女学生对妇女解放事业造成了“破坏”的影响。她认为女学生飞扬妖冶的衣饰,“好高骛远,不适国情”的言论,不但不能改换社会的眼光,反要惹社会的轻蔑讥笑。造成的恶果是“不论新旧人物,都觉得这女学校,是一个‘女子罪恶造成所’,不愿意他们的子女去沾染这样的恶习,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可怜那些真心求学的分子,便受了不良分子的拖累,只得仍去受那‘旧家庭的教育’”。因此,冰心提出对女学生事业的“建设”主张,她认为,女学生衣着上应朴素稳重,言论上要力戒好高骛远,应着力于“普及教育”、“改良家庭”等稳健实用的主题,多去开导尚未得到知识的社会妇女[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冰心没有将批评的目光转向社会舆论对女性的片面和歧视性的认识,反而将这种心理认知归结为女学生自身的修养问题。这一方面表现出冰心对男性中心的性别立场缺乏警惕,但另一方面也源于冰心对当时中国女学生处境更为务实的思考。冰心于同年连续发表了《秋风秋雨愁煞人》《庄鸿的姊姊》《是谁断送了你》等一系列涉及女学生生活的“问题小说”。在《是谁断送了你》中,怡萱的父母看不惯女学生高谈“自由”“解放”的浮嚣态度,对怡萱接受新式教育始终忧心忡忡,怡萱虽谨记父母的教诲,勤奋好学、稳重得体,也逐渐获得了父母的认可,但在一封男同学唐突的求爱信被父亲发现后,怡萱在惧愧之下竟自我了断[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第130-133页。。在《庄鸿的姊姊》中,勤奋好学的姊姊迫于家计的压力和长辈的陈旧观念不得不将学习的机会让给弟弟,最终在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中正值青春年华就郁郁而终。小说在庄鸿“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的疑问中结尾[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第55-62页。。而《秋雨秋风愁煞人》中,“我”的同学兼好友英云不但道德学问绝特,而且性情清高活泼,志向远大。但自从英云顺从了父母的包办婚姻,就颓丧下去,如同行尸走肉,再也不复旧时的开朗情态。毕业时,英云同“我”袒露心迹,“我”知晓英云被许配的姨母家是完全的旧家庭,英云未来不但无法在社会上立业,学以致用,在家庭内部也无操持家政,改良家风的自由,只能由婢媪们拥着做一个涂脂抹粉的玩偶,眼看着家中弟妹在纨绔恶习中堕落下去。[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第28-39页。怡萱的悲剧使冰心痛诉女学生面对的传统舆论环境的险恶,而庄鸿姊姊与英云的悲惨命运更使冰心体认到女学生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力。随时可能中断学习生涯的女学生自身的危机感,使冰心极为珍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也就不难理解冰心为何要对女学生提出“朴素稳重,稳健实用”的主张。怡萱的悲剧固然是封建意识的父母,唐突的男同学,以及自身脆弱的性格合力造成的悲剧,但冰心哀叹“是谁断送了你”的矛头也直指女学生被污名化的现实舆论,舆论的力量可能影响不了开明的家庭,但对于广大未受教育的妇女群体和依然强大的传统道德束缚,对女学生的“污名”等于断送了更多妇女接受教育的可能。在社会的压力面前,自珍自强是女学生们最务实的选择。因此冰心对女学生们发出疾呼:“敬爱的女学生呵!我们已经得了社会的注意,我们已经跳上舞台,台下站着无数的人,目不转睛地看我们进行的结果。台后也有无数的青年女子,提心吊胆,静悄悄的等候。只要我们唱了凯歌,得了台下欢噪如雷的鼓掌,她们便一齐进入光明。”[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第9页。冰心着眼于已经获得解放的女性对整个女性群体的责任,进而抨击个人主义对于女性整体福祉的损害,她告诫女学生们要牢记易卜生《海之夫人》剧中的话:“我们一面要求解放,一面要自己负责任;否则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解放运动的进行,要受累不浅了。”[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第126页。由此可见,冰心试图采取更为温和务实的改良立场来减少个人主义思潮对女性社会舆论的破坏,从而期待女学生群体成为一座与旧家庭和新社会观念之间沟通的桥梁,逐步扩大“新女性”的范围,并以此改变“新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
(二)“新女性”的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塑造“新贤妻良母”
类似的立场也出现在冰心对“新女性”前途的思考当中,随着晚清至“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性开始通过教育机会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家庭不再成为女性的唯一选择。“新女性”们渴望在社会事业上有所成就,但绝大部分的“新女性”仍然面临着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家庭的处境。于是,“新女性”的个人追求与婚姻、家庭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凸显出来。与冰心同时代的女作家庐隐笔下就有一群恋爱后成立家庭的“新女性”,她们在婚后烦琐的家庭生活中窒息了原来的梦想,进而产生了对爱情和承诺的怀疑。如《何处是归程》中的女主人公沙侣,她厌倦了“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 …整理家务,抚养孩子,哦!伺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注]庐隐:《庐隐文学精品选》,现代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在她眼中,女友学成归国,“施展平生的抱负”,这才是伟大和有意义的。因此,她把自己打入时代的落伍者的行列。而在鲁迅《伤逝》当中,子君婚后的生活也归于平庸,但离开家庭后面临的生计困难却使她无路可逃……在同时期作家的“新女性”书写中,等待着逃离家庭的“娜拉”们的,是依旧狭窄的社会空间和低矮的历史天空。因此,回归家庭生活的无聊与平庸成为一代“新女性”普遍的焦虑,而这种焦虑背后是“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观念带来的强调社会公共领域,贬低家庭日常生活的价值判断,冰心不反对“新女性”在社会上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但在女性的家庭生活领域,她与同时代作家的思考拉开了一定距离。她试图通过对女性家庭责任与家庭幸福的强调,扭转“新女性”书写中看重社会价值而否定和破坏家庭的倾向。冰心在1941年发表的《我的母亲》中曾说:“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的‘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冰心的家庭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她的成长背景,她虽接受了提倡女性解放的新式教育,但父母的慈爱,亲戚的和睦也使冰心时刻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因此,冰心对“五四”个人主义泛滥带来的对家庭的“破坏”始终有所警惕,在1920年6月发表的《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中,冰心就隐隐表达了对宣告脱离家庭观念而置老父老母于不顾的“新青年”们的不满。五四运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的旧家庭制度,当然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由此助长的个人主义思潮与对家庭不负责任的态度却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危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人,上有于己有恩的年迈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女,生活的责任绝不是喊几句“个性解放”的口号就可以推脱掉的,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冰心在面对在“新女性”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之间的矛盾时。重新肯定了家庭的价值,力在弥补激进思潮所造成的社会裂痕,主张“新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家庭责任与获得家庭幸福的可能,在二十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冰心不断高歌“母爱”的伟大,也肯定“新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妻”“母”的积极意义。因而其女性观被众多论者称为一种“新贤妻良母主义”。
冰心登上文坛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就以对比手法塑造了她所理想的贤妻良母式的“新女性”角色。《两个家庭》以思索“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家庭的幸福与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的关系”这一演讲题目展开叙述:陈太太只知交游宴会而不事家政,使陈先生饱尝家庭凌乱无章,儿女啼哭之苦,最终在现实的失意面前软弱下去,染病而死,一腔才干抱负皆付东流。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三嫂亚茜,亚茜精明强干,不但教养子女,治家有方,而且能与丈夫一起翻译书籍,教导佣人念书识字,帮助社会事业的建设。冰心在“两个家庭”痛苦与幸福的对比中抨击了封建宦家太太不事生产劳作的娇堕作风,肯定了亚茜这样既习得现代知识,为建设社会事业出力;又勤于家政,兼具温柔贤淑美德的“新女性”[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第11-19页。。在此后的写作中,冰心也塑造了众多亚茜式的甘于奉献的“贤妻良母”,如《悼沈骊英女士》中冰心的朋友沈骊英,《关于女人》作品序列中的《我的母亲》《我的学生》等。《我的母亲》中,母亲虽是传统的家庭妇女,但却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替同盟会会员传递消息。《我的学生》中,S虽承受着战乱年代繁重的家务劳动,却仍抽时间为小学的孩子们上课,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而冰心的朋友沈骊英更是以一介女流身份跻身中国科学界,但仍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成功为第三”的牺牲精神在家庭中奉献自己。
二、冰心的女性写作策略: 女性问题与民族国家想象
(一)“救亡”与“启蒙”:中国现代性方案中的女性问题
冰心对“新贤妻良母”的褒扬,对女性助夫教子高于自身事业的要求,在女性的现代解放进程中,不免令人认为是一种回到男性中心的封建性别观的倒退。但如上文所言,冰心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和价值衡量往往是以社会整体的“建设”与“破坏”来展开叙述的,因此其女性叙事往往并不只着眼于女性自身,而是常将女性问题放置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中。如《两个家庭》中冰心以“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家庭的幸福与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的关系”这一演讲题目为主题,从家庭到国家,从女子的家庭责任到男子的事业建设,通过这样的逻辑推演将新女性的家庭责任放置在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想象之上,成为其反思“五四”个人主义的立足点。实际上,中国近现代女性解放问题的提出往往与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救亡运动紧密联系。中国的“新女性”肇始于晚清由改良知识分子倡导的“放足运动”“兴办女学”等妇女改良方案之中。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知识分子“母强”即“国强”的救国设想中,女性的国民素养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其女性解放的倡议背后其实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诉求。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母教。”[注]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0页。因此清末女子教育的提倡与开办被提升到了“救国保种”的民族高度,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性的解放进程,随着“女学”的兴起,女性进入社会领域成为可能。冰心的女性书写也沿袭了自晚清以来将女性问题融入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书写方式,但这并不代表冰心的女性观是相对于五四运动中女性个人意识启蒙的一种倒退。实际上,这正是“五四”运动沿袭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面向。正如李泽厚所言,鼓舞冰心登上文坛的五四运动是一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且不论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是否切中中国的现实,但他确实道出了五四运动同时具有以“启蒙”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和以“救亡”为核心的爱国反帝运动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反复出现,并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之中。新文化运动虽然要达成的是“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但“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所以当五四运动以“救亡”为目的将西方“个人的‘天赋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等启蒙概念译介到中国时,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反弹。这种“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张力同样出现在中国女性走向现代的进程当中。在五四时期有关女性解放的讨论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的“恋爱自由,个性解放”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最初“启蒙”,但同时,风雨飘摇的中国要走向现代也必须迅速组织和动员其国民以完成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战争状态需要女性贡献出她们千百年来的劳动与生活经验,而这经验最好的土壤依然是家庭。虽然1918年《新青年》四卷六号特别推出了“易卜生专号”,使走出家庭的“娜拉”作为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启蒙”震荡了中国女性的心灵,但即使是极力主张女子自立的胡适也提醒众人:“我所说的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注]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 1918年第5卷第3期。而作为新文化急先锋的《新青年》,也不乏依旧将女子身上的妻性、母性的优劣作为维系中国前途的重要砝码的文章。[注]小酒井光次:《女性与科学》,《青年杂志》 1915年第1卷第4期。陈钱爱琛:《贤母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期。“五四”精神本身所体现的女性个人意识启蒙与民族国家的救亡运动并存的缠绕关系,体现在冰心的新女性思考中就是所谓“破坏”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冰心是在“五四”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中登上文坛的,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叙述爱国学生被捕受审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从一开始,“救亡”与“建设”就是她的选择,她警惕“启蒙”带来的“破坏”。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冰心为何选择以歌颂“母爱”和塑造“新贤妻良母”的方式构筑她的“新女性神话”。但这是否表示冰心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压抑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而陷入了另一种“救亡”压倒“启蒙”的二律背反呢?进入三十年代后,冰心进一步丰富了她早期提出的女性观点,并在作品中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女性意识,要真正理解冰心的性别立场,依然要回到其小说文本之中。
(二)民族国家话语内部的女性意识:女性的“独身困境”与“双重劳动”
冰心毕竟是一位女性作家,也是一位“最属于她自己”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依然充满了对女性真实生活经验的细腻感知,借用民族国家话语的女性叙事表达并不代表她漠视女性个体的生存处境。相反的是,借助民族国家话语的叙事表达反而成为冰心伸展其性别主张的写作策略,通过民族国家话语在舆论公共空间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冰心得以阐发她对女性问题的更为深刻丰富的思考。随着三十年代冰心本人进入婚姻,为人妻母,她对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之间选择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和丰富,总体上,冰心延续了她早期“贤妻良母”式的新女性理想,但随着冰心由女儿、女学生向女学者、人妻、母亲的转变,她也开始体认到新女性不同选择背后面临的真实生存困境,独身的寂寞和家庭内部的琐碎日常作为新女性选择的两难困境同时凸显于这一时期冰心的女性叙事当中,从而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冰心早期贤妻良母式的“新女性”的神话色彩。在1936年7月发表的小说《西风》中,冰心描绘了独身的秋心在旅途中偶遇当初为了事业而抛弃的爱人远时的复杂心境。与远的重逢加深了时时笼罩秋心的寂寞,秋心回忆当年相爱时的幸福时光,并开始反思自己不婚的决定,以致面对《妇女两个问题——职业与婚姻》时,忽然写不下去,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冰心在《西风》中通过对秋心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刻画了“新女性”顾此失彼的生活困境,秋心虽有顺利的事业,但随着亲人的分离,朋友的零落星散,也面临着“没有伴儿”的孤独寂寞,这使秋心艳羡远美满家庭带来的欢乐。但秋心的心境始终是矛盾的,她明白自己“在决定了婚姻与事业之先,原以理会到了这一切的……”她懂得自己对远的欲望是“一年以来的劳瘁,在休息中蠢动了起来,是海行,是明月,是这浪漫的环境,是我自己脆弱的心情……”而秋心也依然享受工作给予她的快乐,在闭门拟了两篇演讲稿后,秋心一扫此前的烦闷心境,“心里很觉得痛快”。秋心是早有觉悟的,她明白选择事业而放弃家庭所要付出的相应代价[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146-160页。。因此《西风》所展现的只是秋心在航行途中焦灼的意识片段,即使冰心试图证明女性拥有家庭生活的必要,但她依然无法否认秋心在人生道路选择时所经过的理性的深思熟虑。而对于那些选择了家庭的“亚茜”们,冰心在赞扬她们的同时,也开始理解在社会与家庭双重劳动下女性生活的不易,并痛心于她们的自我牺牲。1941年,冰心以“男士”的身份在重庆陆续发表了《关于女人》作品序列,其中的《我的学生》和《我的邻居》所刻画的女性可以看作是对《两个家庭》中亚茜的续写与改写。女性在家庭与事业间面临的双重压力、双重劳动问题浮现在文本之中。《我的学生》中,S热爱生活,开朗坚强,婚后 仍“忙里偷闲,花枝招展”,将料理家政和应酬交际安排得井井有条,抗战后,S在云南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也继续保持着“真好玩”的处事态度和人生观。被作者赞扬为“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的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但这个乐观坚强的家庭妇女却在繁忙家务与助人事业中英年早逝,如蜡烛般燃尽了自己的生命[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265-274页。。而《我的邻居》[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285-291页。中,M一家到达昆明后生活颇为困窘,M先生在外既不能挣取足够的生活费用,在内又不能体谅M太太的家务付出,而M太太又因学生时代缺乏操持家务的练习,被婆婆百般挑剔,可当她提出教书补贴家用时,即使“学校甚至对她比她的先生还要满意”,但还是以孩子无人可带为由遭到了婆婆和丈夫的反对,M太太本是一个颇有文学天赋,极有创作前途的女子,但她在操劳的家务劳动中,只得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以致发出“文章误我,我误爹娘”的无奈哀叹。冰心借助S和M太太的悲剧命运道出了新女性光鲜面容背后的辛苦生活。开朗好强的S在家庭和社会事业的双重劳动下英年早逝,而敏感脆弱的M太太则在家务操劳中耗尽了她事业的理想。冰心不再简单的歌颂亚茜式的新贤妻良母,而是略带无奈的书写这些女性背后的辛苦与牺牲。冰心情感的变化或许来自于她的生活体验。在写作《关于女人》之前,冰心也曾因战乱和家务的繁忙一度停笔。战争带来的流离失所和物资匮乏打破了知识女性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使新女性的生存困境被更大程度的凸显出来。几乎与冰心写作《关于女人》同时,丁玲于1942年3月在延安写下了广受争议的《“三八节”有感》。丁玲指出了彼时延安女性在平衡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类似困境。她们虽有“凌云的志向”,却在婚后成为“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而即使她们“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贤妻良母时”,又不免被人认为是“落后”分子。丁玲的态度是尖锐的,她将批评的矛头直指男性和延安的政治空气,认为男性对女性“落后”的指责和对她们家庭、事业的苛刻要求造成了女性的困境,因此招致了延安将领们对她“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却在背后骂总司令”的批评。其批评背后反映的依然是以“启蒙”为代表的女性个体意识与“救亡”为代表的战争、革命之间的冲突[注]丁玲:《丁玲全集》,第七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5页。。但冰心却免于遭受丁玲被批评的命运,《关于女人》在当时的重庆广受欢迎。这是由于冰心采取了一贯将女性问题融入民族国家话语的写作策略,将《关于女人》的女性叙事放置在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之下,在坦白女性牺牲的同时,也将女性的牺牲看作是大后方战争服务的一部分,从而使她的女性主张获得了更大的舆论空间。除此以外,冰心还以“男士”的口吻和视角写作作品,在《关于女人》的开篇《我最尊敬体贴她们》中,冰心指出:“我以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事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184页。在《我的择偶标准》中,冰心则以“因为我是……所以我希望……”[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188页。的句式含蓄地表达了男性在要求女性家庭劳动的同时也应当承担起自身的家庭责任等男女平等的性别主张。冰心以民族立场,男性视角和轻松戏谑的写作策略表达其男女平等的社会倡议,延续了她一贯不偏不激,冲淡平和的写作文风,也为其作品中的女性主张赢来了更好的舆论环境。
三、东西之间的女性问题:女性品格的再塑造
如前文所言,冰心塑造了一批兼具传统女性美德和现代学识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一方面是冰心“新贤妻良母”的女性理想使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冰心看待女性问题时的中西比较视野。西方一直作为冰心女性书写的参照系存在,并不断的影响着冰心笔下中国女性品格的塑造。西式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使她早年的作品具有一种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情怀,并体现在她的女性书写当中。在1920年发表的《最后的安息》中,冰心以基督教式的博爱思想,将翠儿和惠姑两个“贫、富、智、愚、差的天悬地隔”的精神,联合在一起。并以翠儿“灿烂的朝阳,照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极乐世界”这样的宗教想象,给予了贫苦的童养媳惠姑以“最后的安息”[注]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第76-84页。。但进入三十年代后,冰心留美的生活体验和阅历的增长使她在看待西方文化时开始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识。在面对底层女性时,冰心不再以“同情中带着虚伪”的宗教玄想弥合阶级的鸿沟,而是转而赞颂“冬儿姑娘”那样面对艰难生活野蛮生长的反叛力量[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42-48页。。同年,冰心也用讽刺的笔法抨击了当时社会中模仿西方沙龙文化的女性知识精英“慕洋”生活的虚伪和无聊:仆从的英文名,欧美的宾朋好友,西洋的诗歌与话剧,不过是装点“上流”身份的标签,而对西方哲学的讨论,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也只是追名逐利的注脚[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21-39页。。“五四”落潮后,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使中国知识精英们“全盘西化”的鼓吹在现实面前越来越不具有说服力,而对底层心怀悲悯的冰心也开始对早期接受的西方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并进一步体现在她对中国女性品格的理解当中。
1934年发表的《相片》是冰心创作当中一个颇具症候性的文本,施女士是一位在中国教会学校任教的西国女教员。恋爱失败后,施女士越来越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而她的养女淑贞既是她孤独生活的唯一慰藉,也是她所欣赏的中国文化的感情载体,在施女士的调理下,淑贞不曾沾染半点西方的气息,直到施女士带淑贞来到美国。淑贞在美国结识了雅各太太和她的儿子彼得,还认识了华人李牧师和他的儿子天赐。在淑贞与天赐的交流中,两人因对外国人对中国偏见的同样感受而惺惺相惜,可就当两人感情日渐升温之时,施女士因为看到淑贞照片中从未见过的开朗笑容而战栗,在嫉妒自私的变态心理中将淑贞带回了中国。冰心以含蓄的笔法写出了以施女士为代表的西人在看待中国时的东方主义色彩。周蕾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引用劳拉·穆尔维的性别凝视理论和费边的异时主义来分析西方看待中国的东方主义问题,她认为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正如同电影中作为主体的男性对作为客体的女性的“奇观化”的观看方式,在一种类似于摄像机镜头的凝视动作当中,中国被物化为一个充满女性特质的、“空间性”的而非“时间性”的静止“奇观”[注]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1页。。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分析冰心的《相片》。施女士对淑贞的感情更像是一种对“物”的怜爱,淑贞就如同她买来赏玩的一两件古董,而这个“古董”是她的藏品中最骄傲的中国象征:“她觉得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子,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诗,王太太的一缕绣线,东方的一片贞女石,古中华的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的静默……”[注]冰心:《冰心全集》,第3卷,第56页。。而在教会布道的人眼中,天赐这个他们口中的“中国模范青年”,其实不过像是“他们练过的猴子。”小说中这些西人把中国和中国人的特质理解为静止的古老奇观,他们“总以为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是没有文化的”。而一旦最能代表着施女士中国想象的淑贞在相片中焕发出“满脸的笑,惊喜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露,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时,施女士被淑贞所焕发的茁壮的青春朝气所震惊,她再也无法固执地将自己变态孤独的虚荣寄托在对古老中国的想象之上。冰心借助淑贞这个中国女儿的变化和朝气揭露了标榜宗教博爱的一部分西方人的虚伪。体现出她对早期作品中西方宗教情节的一定反思。身为“五四”一代的知识精英,冰心也处在既要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又要以西方为师的矛盾心态之中,在这种不对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中,她一方面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倡导彰显中国女性的独特魅力,一方面又警惕将中国传统女性特质物化和固化的西方眼光。她笔下的女性品格因此显得丰满而复杂,既有着中国女儿的温柔沉静,也有着变革时代新女性的果敢、康健和开朗。
从1919年冰心登上文坛到1949年止,冰心的写作触及女学生,知识女性,家庭妇女,底层女性等涵盖中国各阶层的广大女性群体,她以一个女作家的细腻笔法,将作为女性的所想所感放置在个人与国家,男与女,中与西等不同的参照系中,描绘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幅珍贵的女性群像。她们温柔笃定,勤劳勇敢,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劳碌、思考、痛苦并快乐。作为登上中国现代舞台的第一代女作家,冰心对女性个性解放的反思,贤妻良母的要求在女性获得更平等地位的今天,似乎多有可商榷之处,但其女性写作的意义已孕育在她对时代的独立思考之中。诚如戴锦华所言,“冰心作为少年中国的女性成长史的第一代女儿,仍然不失独特,她未曾辜负家庭、文化所给予她的全部恩赐,她把这一副经验全副拿了出来”[注]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Between“Destruction”and“Construction”—— Female and feminism in Bing Xin’s works from 1919 to 1949
Tong Wancun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1919-1949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Bing Xin’s writing. As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emale writers who grew up in the trend of women’s liberation, Bing Xin’s works in this period not only shaped a large number of women’s images, but also broadened the thinking about women’s issues at the time. Bing Xin’s concerns to marriage, family and other female groups such as female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 women, as well as “the new female myth” that she called “new wise wife and beloved mother”, reflects the swing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ra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sue of women’s modern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salvation movement. On the one hand, Bing Xin cherished the hard-won liberation process of wome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encouraged women to move towards social construction. On the other hand, she also reflected the trend of individualism and the tendency of total westernization brought b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n reaffirmed the family value of women as “wife” and “m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and shaped a group of new female images that have traditional gentleness, virtue, and self-esteem. However, after entering the 1930s, while valuing Chinese women’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traditional virtues, Bing Xin also realized the specific survival dilemma of the new female’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being suppressed and sacrificed, and then began to advocate the family concept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alert to the western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zing and solidify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emale traits, thereby enriching her feminine outlook.
Key words:Bing Xin;new virtuous wife and good mother;family;female liberation;nation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