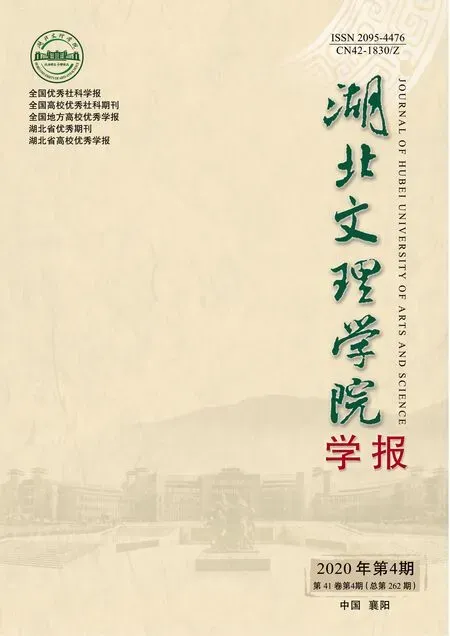余秀华诗歌的“野性”意味及审美价值
杨 扬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世纪以来,人们一边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享受,一边因物欲横流导致的精神迷茫而倍感无奈,异化的社会和人性的压抑是当代诗坛浮躁、疲软以及混乱的一个因素。
当代诗坛面临重重困境,但同时也不乏希望,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样也慢慢改变着人们对于诗歌本身的看法,改变着诗歌的思想开放尺度,逐渐出现了挣脱以往传统诗歌风格与体系的动作。当生活开始丧失原始生命力,人们开始被时代同化,特殊的存在一定会唤起人们心底残存的挣扎。
新世纪下的诗坛,诗歌个性化的趋势明显,各种诗体横空出世,诗坛众鸟齐鸣,余秀华以她残障的身体、农村妇女的形象,带着含有扎根底层的原始生命力量、狂放不羁的情感抒发以及释放野性,展现内在自由精神的诗歌,成为了恢复原始生命力、直击诗坛疲软、释放人性压抑的急先锋,她诗歌中对苦难与疼痛的抒发也正中了中国当代“新伤痕”式文学[1]的下怀,成为了诗坛嬗变的推动力量,她的“野性”力量也唤醒了社会大众麻痹的内心,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的空洞。余秀华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得到文学受众的关注,引发炙手可热的文学事件,震动到当代诗坛自然在情理之中。
各个群体对于突然爆红的余秀华以及其诗歌极高的关注度,看法不一。传统诗人群体和部分文学受众提倡当代诗坛仍要回归“大众性”和“民族性”,需要的是“正统”而非“粗俗”,而新世纪诗歌又以它独有的特色与共鸣性受到另一部分人的青睐,余秀华及其诗歌犹如出头鸟饱受争议,各方对她诗作中体现的“野性”意味褒贬不一,仍有许多值得探究的余地。再者,余秀华作为诗坛新秀,国内对其研究众多,其诗歌“野性”意味的归纳与审美批评,对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当代诗坛的嬗变,具有积极意义。
一、余秀华诗歌的“野性”世界与生命
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尘埃,农村残障妇女余秀华生活在最低处,就如她自己所言,她是一颗稗子,只是一株脆弱的、不堪的生命,在食物链最底层的植物,一颗无法与稻子相提并论的野植。诗作大多带有从自然与日常中萌生出来的质朴,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底层韵味,乡野气息扑面而来。余秀华用文字书写着自己的日常世界和个人的生命体验,不仅焕发原始生命力量的“野性”味道,而且使读者看到了充满“野性”的现实乡野世界与内在精神世界。
她这样的“稗子”同时又是难以除去的。正因她特殊的个人境遇,个人情感无法得到抒发,内心欲望受到限制,诗歌便成为了余秀华精神世界的替代补偿,同时也成为了她宣泄情感的重要工具,在诗作中无处不体现了她决不矫饰、敢爱敢恨、狂放不羁、反叛挣扎的创作特点,无不呈现出她独特的个性。余秀华在自己的诗作中做着属于自己“野性”十足的白日梦。
(一)质朴粗粝的乡野展现
徐鲁曾在与余秀华的对话中提到,她的诗充斥着满满的“土地伦理”。余秀华的诗歌世界是一个以乡村日常经验为基础,十分野性并且生灵浩瀚的生命世界。“在月光里静默的麦子/他们之间轻微的摩擦/就是人间万物在相爱了”[2]129由于扎根底层,横店的一切日常成为了她可以承载深沉爱与恨、苦与闷的载体和她抒发感情的道具。《田野》一诗中,她再一次提到了一个名叫横店的村子,这里有只属于家乡横店的田野庄稼、花草树木、飞鸟鱼虫,甚至还有家乡日常卷起的风雨和轻飘而过的云,每种景物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姓名、动作以及表情。八月的横店,有布谷、八哥和成群结队的麻雀;有被种植的水稻、大豆、芝麻和高粱,它们在村子的某一片田野上晃动身姿;也有被圈养的牛羊和人,有在篱笆上栖息的鹰,这些活灵活现的动植物和生动的景色,充满了原始与质朴。《沙乡年鉴》的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是这么定义乡野的:“乡野是土地的性格,是泥土、生命、大气共同的呼声,乡野也可以很富足,并且在拥有者面前始终保持着超然与自我。”[3]20余秀华笔下的乡村与田野,大到天空和草原,小到花朵和虫卵,仿佛都有自己的性情,自在而不受拘束,独立于人类之外,无时不刻充满着野性与自我。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实,这是一种我们如今难得亲临的野生自然常态,倍感珍贵与稀奇。
“一片荒田里野草繁茂,野花也趁势呼啦而上,我迷恋期间的蚯蚓,麻雀蛋,刚刚会爬行的小蛇。”[4]37“有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这都是田野富饶的部分。”[4]36在诗中能看到野草与野花在荒田里肆意生长的过程,能看到在土壤中穿梭的渺小蚯蚓,能看到隐藏在深巢中的麻雀蛋,能看到妊娠的老鼠和幼雏。余秀华赋予了他们第二层次的生命,简单粗粝地描写并没有使画面感难以捕捉,反而增添了鲜活的味道,使乡野田间图跃然纸上。她在文字中毫不矫饰,逼真自然地呈现,反而放大和丰富了这座横店村,映入读者眼帘的竟是真正属于原始乡村野性风采的生活空间。
“在渡口捣衣的女人,临水自照成为积习”[4]25“我匆匆起身:做饭,喂猪,赶鸡上笼,我就这样把自己迅速的赶进夜色”[2]152这是在横店村生活的人,所拥有的生活场面和习惯,每天借着河边的水洗衣,将水面当镜子,工作是割麦、喂猪、赶鸡鸭,忙活下来,一天就这么充实而平静地结束了,琐碎的农事和闲静的小生活成为了余秀华创作的素材,历历在目的是一幅幅质朴的乡村生活图。
在余秀华的诗中,也提及到多次与父亲母亲的耕作活动,父亲常常在“在屋外劈柴”或者用年老的身躯“扛麦包”,母亲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在湿洼地、田野间。“她埋怨他不肯出力/他说她只会唠叨”[5]23即使是父母劳作时的小小争吵,在余秀华的笔下也变得温馨起来,这就是他们的底层生活,互相牵绊亦有滋有味。
对乡野生态与日常经验的书写,在余秀华的诗歌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与她底层农民的身份有着莫大关系,她对于诗歌题材的选择着眼于真实情景与日常生活,在封闭的横店村内,诗人每天都必须亲临的场面,每天都能观察得到的日常生态。这样的书写虽质朴粗粝,但逼真而丰满,凸显着一种深深植根于大地的野性,一种代表当代贫苦农村常态的野性,一种充斥着原始生命张力的野性,成为了余秀华诗歌上的一大亮点。
(二)狂野不羁的生命书写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作为主体个人的阅历不同,对待事物的认知便会不同,体现的精神追求也不同,而诗歌所体现的正是主体对精神层次的探索。“我在村庄里被植物照耀,你在城市里被霓虹追赶。”[2]86余秀华诗歌中的生命世界与大多数人的生命世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且物质生活丰富的时代中,许多人为了拥有更高的物质享受,追求更高的城市文明,反而被“霓虹”所追赶,在追求物欲的过程中逐渐被物欲所包裹,外加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源源不断的压力,也使得人们被迫拴上发条,被迫捆绑在模式化的生产线上,真实的主体自我被抽离真身,具有自由呼吸精神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把对财富、权力的渴求当成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心理空间被压缩,看待生命的标准逐渐物质化,人们丧失原来的原始生命力——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被遗忘,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变得极其奢侈。
而余秀华则不同,因为生活环境的迥异,或因为身体上的先天差异,余秀华眼中的生命世界是相对原始、朴素、简单的,灵魂中真实的主体自我以及自由的精神,没有被“霓虹”所浸染,在植物的“照耀”之下,发生在她身上这些本该令人唏嘘的深重羁绊,成为了余秀华回归本真、洗涤灵魂、探索生命的强大支撑,生命于她而言不会就此褪色。“我的身体倾斜,如同瘪了一只胎的汽车”[5]16在许多的诗作中,余秀华表达了她对残缺身体的不快,但余秀华十分顽强勇敢,面对着命运的重重打击,她并没有委曲求全,而是在困境中表现出了十足的抗争精神,一步一步在诗歌中让自我生命与灵魂和解。“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2]59在她的意识中,认为人间没有任何的苦痛可以遮蔽她不断发出光芒的内心,即使血肉模糊,她也不甘示弱,强烈地捍卫着她生命的尊严。“我喜欢那些哭泣,悲伤,不堪呼啸出去/再以欢笑的的声音返回”[4]114在命运的围困之下,余秀华似乎渐渐在挣扎中收获平静,并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我救赎[6],开始接受生命中所有的苦痛、悲伤、不堪,热爱着生命中的一切,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面对生命的戏谑,即使我们平凡又卑微,但总有属于我们自身的生存之道。不羁的描写,体现出一种强大的野性力量,这样强大的对抗力,使这位底层弱女子显得格外的高大。她的身体虽然残缺,但是心灵却在对生命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被升华,这样一种看似不太健康的躯体其实可能比正常的人来得更为健康。
“瘦鸟直直落入荒草,仿佛荒芜是它的自我,我也试着就这么将自己,当如山顶的澄明辽阔中。”(《春日练习》)中对生命的书写,是鲜活的,是敬畏的,是热爱的,是狂野不羁的,她的精神层面在诗歌中得到充分展现,真实的主体自我清晰可见,对生命的探索与张扬更是书写得淋漓尽致。
柴静在《看见》中说:“有的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7]余秀华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闭塞的空间,每天都必须咬紧牙关地过活,这样的经历是不多见的,也正是因为余秀华有这样特有的生命体验从而生成的独特视角,才能使她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对生命的意识,让我们既能够体会诗歌中深厚的苦痛,又能够不被局限地去品味其诗歌中耐人寻味的另一面。“我把自己的残疾掩埋,挖出,再供奉于祠庙或者路中央/接受鞭打,碾压”[5]18余秀华从来都不在辞藻上手下留情,面对人生困境,她对命运的不屈抵抗,体现在她诗歌中,便是蕴含着个人超然不羁、不甘被束缚的野性。她用诗作去表现自己抗争生命困境的勇气,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轻松诙谐的情绪,也在化解不同的生活带给她的苦痛,这个坚韧的、野性的女人,这个不屈服于命运的女人,一直在自我救赎。
(三)直言不讳的情感宣泄
徐鲁言:“有真实的生活,就会有真实的悲伤与惶恐;有真实的爱,就会有深切的挣扎与纠结。”[8]女人、农民、残疾人的三重身份,使余秀华不断被这个社会所“边缘化”,乡村生活的单调与物质的匮乏将余秀华困在其中,可是与霓虹泛滥的世俗相较,横店村与相依相伴她四十多年的骨肉亲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着她,温暖着她。
“这不清不白的一生,让我如何确定和横店村的/关系”[5]19诗人在《关系》中,谈到了自己与横店的关系。在部分诗歌中,余秀华对于家乡是这样想的:“我的村庄不肯收留我,不曾给我一个家”[5]122余秀华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情感上都是孤独的,看似和平共处,却好似从未彼此接纳,更像是彼此对峙,她的精神世界好像才是家乡,而横店则算是“异乡”。可是在部分的诗歌中,余秀华又抒发着自己的乡土情结,用柔软、温情的笔触,表达着她对家乡的感情。“动荡的生活和生命是不会褪色的/我的向往”[2]86家乡是余秀华的归宿,她始终扎根于这片原始而野性的大地,她对家乡的情感是深重的,家乡的一切同时也承载着她继续生活的信念,她的内心更希望像这个村子一样,永远野于世俗之外。
更加让余秀华割舍不开的是亲情。外婆早已逝世,哥哥姐姐远在他乡,无法触及,父亲随时光流逝逐渐衰老,就连母亲也因绝症不幸离开,这给余秀华的精神世界留下了好几道巨大的伤痕。“我们走到了外婆的屋后/才知道她已经死去多年”[5]5、“我从来不相信她会这样死去/因为到现在/她的腰身比我粗/她的乳房比我大”[4]132那是生她、养她,不离不弃的至亲,在纪录片中,陪母亲到医院的余秀华是那样的无助,她无解为什么命运突如其来地带走外婆后又毫不留情的要带走母亲,她痛哭了。在诗中越是野性、直白的抒发,越是能使读者看出亲人在余秀华心中的重量,越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到共鸣。
有人曾经统计,在余秀华的诗作中,“爱”这一个字被提过140余次,如今陆续发表的诗作也正逐渐打破着这个记录。而现实中的大多数人,不敢去袒露自己的心声,生活中脆弱、害怕受伤,就连在虚拟的网络中敲击的都是伪装得天衣无缝的字样,人们无时不刻不再压抑本能、压抑情感,自我束缚,自讨苦吃。这与余秀华从诗作中体现出来的直言不讳的情感宣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余秀华对于爱情和婚姻,有自己的衡量标准,正如她那个带有“女性主义”的灵魂。现实中的余秀华,不曾经历过爱情,并有一段苦不堪言的婚姻,“他说,她们会叫床,声音好听。不像我一声不吭/还总是蒙着脸”[4]420年的婚姻,她没有从中享受过一丝甜蜜,丈夫物质、粗俗、家庭暴力,使她在不幸的婚姻中岌岌可危,更因为她是残疾人,便没有说话的权利。“如钉在十字架上/有多少受难日,她抱着这颗柿子树,等候审判”[5]76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农村妇女,在那凄冷漫长的岁月里,承受着和她一样的煎熬,接受着命运所赋予的审判呢?“我相信他和别人的都是爱情/唯独我,不是”[5]69在她的诗歌中,直言着让人不禁长叹惋惜的苦难真实,体现着底层农村妇女的不幸与孤独,更多的还有对于人性、伦理的思考。
但她的爱情诗也多数能让读者触及最真情、最无畏的感动,余秀华毫不掩饰她个人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对性的欲望,并且塑造了许多为爱痴狂、个性鲜明的女性,在其精神世界里,打开了女性心灵的开放尺度。[9]“红掌想抓住的黄昏里有我想抵达的你”[4]32她在《可是,我爱你》中,表达了强烈想要拥有一个人的诉求。在《我想要的爱情》中,余秀华抒发着自己对爱情的执着,即使生活不断打击,她也愿挤出一个位置去爱人。“所以我愿意在与你相遇的路上狂奔/并以此/耗尽后半生”[4]22在余秀华的爱情诗中,那个他往往没有具体的样貌,却有着让人遐想万千的惊喜,充满浓情与蜜意。这样对爱情直白的表露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诗作成为了读者的替代补偿,他们在余秀华的诗中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层次。
斯特拉桑在《身体思想》中对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称其不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互相影响的、共同决定的个体的意向性。余秀华在诗歌创作中,有大量关于“身体”的表达,诗作中体现的“下半身写作”,包含着复杂的内涵,其中延展出来的是对于自我情感的表达、欲望的宣泄。诗作中有许多类似于“我要你踏在我的身体上”[4]159充满强烈身体欲望的诗句。在纪录片中,余秀华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失败,我和爱情离得很远,所以我不甘心,我要写出来。”在她的诗作《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读朵渔的诗》《和村民郑西拉喝酒》中,大胆地用文字摧毁所有的清规,对两性露骨的描绘,以及对异性暴露、直言不讳的表达,都无疑不体现出她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用一股强大的野性,引爆了爱情世界里的炸弹,同时更是表现了女性坚强勇敢、韧性十足、张扬奔放,抒发了她对于恋爱与性的追求和向往之情。这也是余秀华诗歌“野性”意味的又一大代表,她的自我情感与欲望不受压抑,在诗中像奔腾的野马,叛逆前行,绝不顾及任何阻拦。
二、余秀华诗歌的“野性”形态
在《月光落在左手上》的代序之中,诗人沈睿称余秀华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评价她的诗是纯粹的诗,是生命的诗。[5]V一方面,余秀华的诗作大多是口语化、直白的语言,书写其生活最本真的形态,体现了底层常态书写者的本色。在诗歌的创作中,余秀华也体现出了她对语言的掌控力,在其充满质感和痛觉的语言之中,既能饱满又能控制自己的意绪和情思;另一方面,其诗歌中的意象与意境的塑造,都极富表现力,笔法和修辞都充斥着语言的张力,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碰撞,散发着她独有的野性形态。
(一)震撼性的语言美学
“当你恒常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我试图以文字的悬崖瓦解宿命的悬崖。”[10]18台湾作家简媜的表达恰到好处地凝练了余秀华创作的意图。她的诗作大多是自己对于生命及命运的叩问,是对个人情感的祈盼与宣泄。其诗歌的语用,印证着她本人的桀骜不驯、敢爱敢恨。其自身渴望对现实的冲破,外加天赋的助力,使得一切都非同寻常。
“他们是静的。他们举进风里的草也是静的/一些口号声不会高过一些私语/雷霆也让步于一个人骨骼之间的轰鸣/只是时间无语”[2]78余秀华在《下午》这首诗中,给读者带来了震撼性的语言审美体验,将一正一反两种性质的词语融合在语句之中,构建出了词语间的相互碰撞感,使得情感抒发极富冲击力,仿佛眼前不只是“口号声”与“私语”“雷霆”与“骨语”之间的对决,而是在这个静止的午后,命运的不公与个人的不甘之间的矛盾,更可悲的是时间成为了这场对抗中静默的旁观者。语言运用给予人的打击力量,是余秀华精神世界内在冲突与矛盾的体现。
细细品读余秀华的诗歌创作,还会发现其诗歌大多是被提炼与加工过的,丰富的修辞手法展现了其底层写作的诗性气质,使诗歌充满含蓄又意蕴深邃的艺术美感,强大的隐喻力,叩问着人生的种种,使其对日常情感的抒发上升为对生活哲理性的思考。纪录片中,她在范俭的镜头下,迅速写下这句诗:“天空空出的伤口,从来没有长出新鲜的肉/五月的草,绿出自己的生命,一半在根里,一半在草尖/”天空的裂缝从何而来呢,或许就像她与生俱来的伤,没法长出新肉来愈合,青草在最适合它的季节中,尽情释放自我,一半熠熠生辉于外,却也仍有一半挣扎在暗无天日的土壤。这样巧妙的拟人和比喻,开拓了诗歌的隐喻度,也丰富了诗意的审美思考。余秀华用其日常生活中最为原始与野生的意境,加以诗性的打磨,用巧妙的修辞在现实的平静和心境的波澜之间点燃火花,燃起了所有相同境遇的人们的灵魂,让他们随时随地都能从诗中触及生命最本真的情感和对美好的渴望。
在诗歌创作语言中,余秀华的表达是偏向口语性质的,就这一点上,极大地使大众读者从心理上产生强大的共鸣感和亲切感。余秀华的诗,消除了普通大众与诗歌之间的隔膜,拉近了普通大众与高雅艺术的距离。由此可见,余秀华对于诗歌语言的把握以及对诗意空间的架构能力,是独特的,看似平凡的字里行间,却孕育着一个野性十足的灵魂。“不仅仅是/蔷薇的/还有夜的本身,还有整个银河系/一个宇宙”[5]68在其诗歌的艺术形式上,余秀华则采用自由诗的排列布局,通过一种自然、随性,不加纹饰的断行断句,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节奏,彰显了诗作的语言魅力。
(二)富有野性的意象萃取
“横店”是余秀华的乌托邦,同时也是她的修罗场。“横店!一直躺在我词语的低凹处,以水,以月光,以土/爱与背叛纠结了一辈子,我允许自己偷盗出逃。”[5]18余秀华的乡土情结淬炼于“横店”意象之中,40多年来,她从未曾离开,她的生命全是和家乡有关的一切,她爱自己的家乡,这是她这辈子与生俱来的宿命,可是当这份乡情随着成长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悲苦,横店给予她的沉重包袱,使得她陷于尴尬的境地,因此余秀华对于横店意象的描绘,大胆真实,毫不留情,像一头野性十足的困兽,无奈禁足在牢笼中,又依赖于牢笼。“嗯。我在的几十年,它就在。我消失的时候/它会给出一部分,让我带进泥土/一个村民没有那么容易说爱,也不轻易/把一棵树从这个地方/搬到哪个地方”[2]17毫无疑问,余秀华生命的完整有横店的参与,她对命运的抗争与和解,也是在横店完成的,诗中关于“横店”等乡土意象,象征着余秀华对家乡五味杂陈的情意。
“性”这一意象对于余秀华而言,是一种值得期待又害怕的存在。她肉体先天的残障使其灵魂被限制于沉重的身体之中,在爱上,她渴望拥有健康的身体,完美的爱恋,正常的婚姻。身体与灵魂的高度失衡,致使精神世界发出抗议。爱情与婚姻的失败,使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被满足的欲望、无法付出的激情与无法享受的肉欲,转而放置在了诗歌上。从《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的“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题》中的“为了避免我强奸你的嫌疑,我在下面/如果你累了,我就翻上去”、《读渔夫的诗》中的“和他做爱应该在雨里完成/雨越大越好。事后他一定会记下他阴茎的状况”、《礼轻情意重》中的“而我的心早就送给你了,这皮囊多么轻/最轻的不过一根阴毛”等此类诗句中可以发现,余秀华对性爱以及身体私密部分的描写是直言不讳的,“性”这个野味十足的意象,象征着她对性爱惊世骇俗的渴望,对世俗规矩的冲破,她不吝啬用任何的词汇和语言来形容和想象。而多年来,进行身体写作的女性诗人并非没有,但能做到像余秀华这样在诗歌语言中不在乎禁忌,变本加厉暴露,充满野性地进行疯狂描写的,几乎不存在。
“自然之物”等意象在余秀华的诗歌创作中,被大量的引用。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就是《我爱你》中的“我要寄给你一本关于植物的,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2]7自然界中,植物本身是卑微的,可它潜藏的力量是巨大的,余秀华在诗歌中将自己称为稗子,无疑向世人宣告,她是肆意疯长的,是最植根于大地的,是最接地气的,是最野性的。稗子这一意象,既完美地刻画出余秀华的生命体验,同时也象征着她内心像野草般顽强不息、渴望自由的意志。
三、余秀华诗歌“野性”意味的审美意义与影响
(一)审美意义
在对余秀华诗作的文本解读与审美鉴赏之中,发现不论是其诗歌的题材、形态还是情感的表达,都充斥着浓厚的“野性”意味。从诗歌的题材上,可以发现其对于日常经验与个人经验的书写,具有代表底层劳苦大众、毫不遮掩的野,其对于自我情感和欲望的书写,是自由张狂,不受拘束的野;从形态角度上看,可以发现其诗作从语言的运用、意象的使用、意境的塑造、修辞的使用等不同方面都体现出了“野性”的特质;从情感角度来看,乡情、亲情、爱情、生命困境所给予余秀华的种种,使其抒发的情感也散发着浓浓的“野性”意味。
王富仁提出了伟大诗人的“疯”[11],认为诗人是生活在自己情感中的,他们没有被理性禁锢,没有被现实打磨,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神经系统和语言模式。早期众多炙手可热的当代诗歌,多是出自于“疯子”之手,他们特殊、随性、张狂,反对套路与流俗,大胆冲破传统与束缚,却又不失人文精神与超然高贵的灵魂。而纵观如今的当代诗歌,随性与流俗被划分为同一种定义,而诗歌作为“人本的文本”的美感不再,诗歌所表现的对于生命的理解偏离了方向。
而余秀华的诗歌,带着独特的灵魂,再次用“野性”的气质展现出了伟大诗人“疯”的特殊气质。海子曾言:“伟大诗歌是主体人类突入原始力量的一次诗歌行动。”[12]余秀华诗歌中展现的乡野与原始生命、直白与粗粝、狂放与张力、肉欲与性,都是对人类原始本能的回归性建设,是主体人类对原始力量的突入,虽然不能笃定地说,此时的余秀华以及她的诗歌已经是伟大的,足以让后世无一例外传颂与赞叹,但至少她诗歌中所体现的“野性”的审美蕴含,为重启当时诗歌的点滴味道,并且对当代诗歌的重新审视也有了参考意义。
“文学即人学”的理念在余秀华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野性”一部分体现的是她生活的真实状态,一部分是对于家乡、亲情、爱情、性、生命、人生的态度,让很大一部分人都能从诗歌中得到共鸣,虽然不是人人都和余秀华遭受同样的苦痛,但是人人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苦痛。诗歌,是个人独立意志的存在,也是代表千千万万大众共同意志的存在,是一种人的学问。余秀华面对人生的三重挫折却依然乐观向上、敢于对抗的精神,是多少人做不到的,是多少人不敢做的,她诗歌的“野性”意味,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大众,影响着大众,向大众传递着多方面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文美同样影响着当代诗歌。
反观其诗歌中一些“生硬”“粗俗”“刺耳”“放荡”的部分,同样也值得去思考,这样的“野性”蕴含肯定也会对当代诗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口语化与直白的表达,也会对当代诗歌“雅”的部分有一定的冲击,当代诗歌会因为这样的“野性”与正统大观念诗歌又多增添一份距离感。
总而言之,余秀华诗歌的“野性”意味对于当代诗歌的影响是双向的,诗歌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大的争议,与部分学者对大众担忧的负面影响有关联,但另一方面,余秀华诗歌的“野性”魅力是挡不住的,它会如洪水猛兽一般,继续影响当代诗歌,继续撞击着大众读者的心。
(二)在当代诗歌发展中的影响
余秀华及她的诗歌,能够动摇到当代诗坛,能够让沉寂已久的诗坛再次掀起波浪,足以验证了其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当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已经在新世纪的冲击下逐渐退潮,第三代诗人已经开始分化之后,诗坛涌现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景象,各种各样的诗体层出不穷。部分人认为,余秀华诗歌中的“野性”意味,混乱了诗歌界本该正常的秩序,影响了文学界对诗歌基本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的评判,是当代文坛的“黑洞”[13]。而也有人认为,余秀华“野性”意味的诗歌完全符合新世纪诗歌本土性、身体性、公共性的几大特点[14],深化了“底层写作”“身体写作”“自然主义”“女性主义”,是新时代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当代诗歌走向的,同时也会成为新世纪诗歌发展与前进中的重大推动力量。
其次,当代诗歌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形成“平民化”与“精英化”诗歌对立面的阵营[15],新时代的人们内心拥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向关注社会全体阶层转变,特别是对于底层群众与自我的关怀,逐渐意识到回归自然,回归日常与本真的重要性。因而新时代的诗人群体也逐渐意识到了回归现实与大众的重要性。在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下,余秀华的诗歌中追求个人体验和日常情感抒发的部分,重申了自然意义的部分、尊重着生命的多样状态的部分,顺应着贴近生活、贴近大众新理念的部分,帮助中国当代诗歌进行自我解构与建构、强调“平民化”的部分,同时在诗歌的审美上也没有失去“精英化”部分,使得当代诗歌呈现多样化的局面,扩大了诗歌受众对于诗歌的接受范围。
余秀华的诗歌坚守着原始性的情怀,在坚守着乡村文明与自然主义中坚守着自己对命运与生命的态度,这会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注入一种新鲜的血液:诗歌不仅是继续向着看中家国、民族与历史的方向发展,更多了向关注个人自我的内在精神、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态度、关注原始的生命力量延伸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余秀华诗歌中充满原始与激宕的“野性”对当代诗歌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她会带着自己的这份独特,成为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力。
综上所述,余秀华及其诗歌不仅有文化现象的研究意义,更具有其独特审美意义。物欲横流的世界造成了人性的压抑,生活开始丧失原始生命力,当代诗坛也逐渐浮躁疲软,余秀华诗歌的“野性”,冲击着这样的现状,修补着这样的空缺,为精神世界注入了新血液,使读者看到了别样于自身生活体验的原始野性,这样的文学感染力,不是仅靠网络媒体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个体内在与群体内在的共鸣。
余秀华在其诗歌中,为我们呈现了丰满的“野性”世界,其诗歌体现出了独特的诗性美学,为新世纪诗歌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意义。
因此,余秀华诗歌独特的审美蕴含也必将继续影响中国当代诗坛,其体现的“平民化”、回归现实与大众、关注底层的理念会使得诗歌这一形式的文学接受范围扩大。同时,人们对自我精神的追求也将更加重视。当代诗坛在这样的影响下,也会逐渐具有发散式走向,突破传统局限,向更长远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