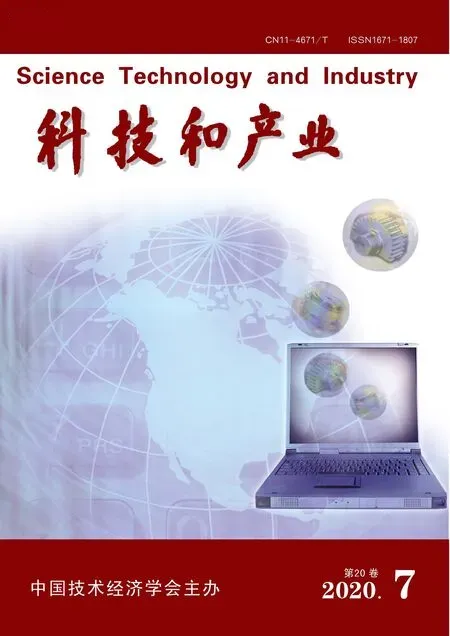新时期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研究
李维维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9)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之本,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科研不端行为也屡屡发生。据统计,2011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共有近1 500篇论文被SCI收录期刊撤稿,占总发表数的5.34%,尤其是2017年4月,施普林格集团(Springer)一次性撤销107篇来自中国的稿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震动。针对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不良学风,国家先后发文治理科研不端行为,例如科技部出台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认为科研不端行为治理是科技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1]。然而科技管理相关部门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缺乏统一标准,调查处理措施也不尽完善,使得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开展科研不端行为治理工作,不仅如此,科研不端行为也随着学科的发展不断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渐近性和实践性,为科研不端行为治理工作更添了一份难度。
本文期望从科研不端行为的概念出发,明确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并结合我国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现状,提出完善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1 科研不端行为的内涵与界定
学术界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英国学者查尔斯.巴贝奇撰写的《英格兰科学的衰落及其原因的反省》,他将科研不端行为分为欺骗、伪造、篡改和主观取舍,并通过案例等形式对这些行为进行了诠释[2]。近现代在科研不端行为领域的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罗伯特.金.默顿,他于1942 年发表的《科学的规范结构》探讨了科学的精神特质,即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并在1957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中将明显背离科学研究规范的极端行为定义为科研不端行为,包括伪造、篡改和主观取舍,并提出科学家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是引发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3-4]。
我国学者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邹承鲁等4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文章,首次涉及“科学腐败”、“弄虚作假”等问题。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次资助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研究负责人樊洪业第一次系统性地分析了科研不端行为的问题,将国外“misconduct in science”直译为“科研中的不端行为”,并定义为“在科学研究与评价过程中, 为骗取科学共同体和社会的承认而出现的伪造和剽窃行为”,认为科研不端行为不仅发生在课题申请、实施研究和提交论文报告阶段,还应包含发表论文、成果鉴定和评奖等环节,同时强调作伪者的欺骗意向[5]。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和科技管理部门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展开进一步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没有脱离“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观念的行为”这一范畴[6-10]。
目前我国政府和教育科研机构没有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统一的界定,有关部门和单位所界定的科研不端行为的范围有较大差别,除了伪造、篡改、剽窃和侵占他人成果等公认的科研不端行为,依据各部门主管业务的范畴,还包括相关科研违约行为和违反科研伦理规定的行为等。例如科技部将科研不端行为界定为:在有关人员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以及其他科研不端行为[11]。教育部将科研不端行为界定为: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12]。通过比较科技部和教育部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可以发现科技部作为资助机构,重视防治项目申请和实施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并关注科研伦理问题;而教育部侧重遏制学术研究过程和成果发表中的不端行为问题。
通过梳理我国科技管理相关部门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本文发现由于各部门职责范围不同,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存在不一致或冲突之处,没有形成统一的格局,并且界定标准较为宽泛,且缺乏明确的判定规则。在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实践中发现,有些不端行为确是“无意之过”,因此有必要区分“诚实错误”和“不端行为”。本文从科研不端行为的概念出发,基于我国科学研究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提出科研不端行为统一的界定标准(如表1)。

表1 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
本文提出的界定范围涵盖了项目/奖项申请、项目执行、成果发表、项目结题各个科研环节,涉及科研工作者、中介机构和管理机构各个行为主体,囊括举报和处理过程中的失信行为,列举较为全面而系统,面向科研全过程,不再受部门管辖权的局限。
2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的现状
科研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从科研不端行为的主体看,包括个体、团体和评议专家三个层次,广泛涉及各级研究人员、高校教师、研究生等群体;从性质上,科研不端行为分为伪造类、剽窃类、骗取荣誉和浪费资源等。本文通过梳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情况,并结合近期典型的科研不端行为案例,探讨新时期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情况统计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最高层级的资助机构,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的监督与管理责任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等情况进行监督和调查,并按期向社会通报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情况。因此,本文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期通报的科研不端行为案例处理决定作为研究样本,探讨科技人员在开展项目研究过程中主要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以及资助机构对其的处理情况。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于2013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披露的83起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决定。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被基金委主要处理的不端行为是“抄袭、剽窃或购买项目申请书”,达到32起,占据样本总数的38.55%;其次是“假造评审意见或同行评议过程造假”,一共有30起,占比36.14%;而“研究基础、论文成果造假”和“冒用、篡改论文署名等重要信息”都有20起,占比均为24.10%;“伪造个人信息/经历/签名”也达到了10起,占比超过12%(详见表2)。

表2 自然科学基金委处理的科研不端行为
通过对披露案例中的12种行为的归纳总结,可以发现科研项目申请、实施、评审和报告中主要存在的科研不端行为是剽窃和同行评议造假。剽窃是指擅自使用他人的研究思想、研究过程、研究结果,但是未予以注明的行为。在披露的案例中,被剽窃的内容除了可以公开获取的学术论文,还包括未公开的项目申请书。由于项目申请书的非公开性,剽窃行为更为隐秘,因此造成的损失也比论文抄袭更为严重。相对于较为容易识别的剽窃行为,同行评议造假行为在治理实践中较难认定,例如在“施普林格集中撤稿案件”中,如果不是由于涉事“第三方委托机构”集中于某一两家公司,并且使用了相同的电子邮箱,露出了明显破绽,否则并不容易被迅速查实。同样,编造和篡改数据、图片等科研不端行为,查证过程也往往会比较困难。
2005年3月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中,对个人不端行为的处理种类包括:书面警告,中止项目,撤销项目,取消项目申请或评议、评审资格,内部通报批评和通报批评。而在实际处理中,通过对披露的处理决定的分析,可以发现基金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措施主要包括“通报批评”(83次)、“取消项目申请资格”(82次)、“撤销项目或撤销项目申请”(49次)和“追回已拨资金”(37次)。基金委对科研不端行为人的处理措施主要集中于禁止科研项目申请,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相关行为人所发表的涉事论文依然在各大论文数据库里安然无恙,并没有被撤稿或删除,反映出在缺乏各部门协同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的背景下,一些惩戒措施由于职责限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的效果被打了折扣。
2.2 典型科研不端行为的案例分析
2.2.1 大规模的同行评审造假——“集中撤稿事件”
2017年4月,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表了一篇撤稿声明,宣布撤回107篇发表在《肿瘤生物学》杂志上的论文。该集团表示,经过调查,已经找到足够证据证明这些论文在同行评审过程中有造假行为。此次撤稿名单长达数页,不仅列出了撤稿的论文题目和刊号,还有作者姓名,涉及的524名医生或研究生均来自中国。
同行评审即评审人评审,是国际论文录用的重要环节。按照施普林格的论文接受规则,作者投稿之后,编辑会安排评审人就论文的科学严谨性作出审议和评价。这些评审人是各领域的专家,并以报告形式为期刊提供论文评价,之后由编辑决定是否录用。此次论文集中撤稿的原因就是评审人造假。论文作者在投稿的同时,推荐一名并不存在的审稿人,并留下自己或合作者的邮箱,也有人推荐真实存在的同行专家,但在署邮箱时造假。这使得“运动员”自己就成为了“裁判员”,从而得到“理想成绩”。
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情况复杂,影响十分恶劣,严重损害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尊严,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学术环境以及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体系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2.2.2 科研成果缺乏可重复性——“韩春雨事件”
2016年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2016年8月,《自然》杂志发表报道,阐述了多国科学家对于韩春雨的NgAgo的争论,指出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的科研人员表示实验不可重复。2016年10月,中国国内13位知名研究学者实名公开了他们重复韩春雨实验方法无法成功的结果,要求韩春雨团队公布基因编辑技术的细节。韩春雨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其他学者无法重复他的NgAgo实验,细胞污染的可能性最大。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布声明称,若干研究者联系该期刊反映无法重复韩春雨的研究,期刊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后,撤回韩春雨团队于2016年5月2日发表在该期刊的论文。2018年8月31日,河北科技大学发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该公告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属于国际前沿领域,存在许多不可预知的问题,因此在形成研究结论之前,要对实验结果进行审慎的验证,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尤为关键。浮躁的功利主义伤害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韩春雨在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存在不严谨的时候,就急于发表,给国内外同行学者造成了误导和人力物力的浪费。作为主管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应该鼓励可靠的、可重复的研究,而不是华而不实的研究,这样才能确保科学研究活动是有意义。
2.2.3 科研伦理原则被践踏——“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2018年11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娜娜”和“露露”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他的团队采用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进行精确定位并修改,使得她们在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贺建奎尚未在有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成果,就开展基因编辑婴儿的临床研究,打破了全球科学共同体在用CRISPER-Cas9编辑人类生殖细胞时谨慎和透明的管理原则。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可能诱发非常严重的伦理问题,被改写的生殖细胞会影响其子孙后代,甚至随着基因编辑的普及,改变整个人类的基因池。该事件造成科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恐慌,《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也将此事件评为“21世纪迄今十大最糟科技”。
根据2003 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因此“基因编辑婴儿”属于被明令禁止的。贺建奎对人体胚胎开展的基因编辑研究,未向南方科技大学和所在生物系报告,也没有经过任何管理部门监管审查,其出示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也是通过他人伪造,该研究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是对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声誉和发展的巨大打击。
2.2.4 高校招生与培养不规范——“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
2019年1月,翟天临在社交媒体晒出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后录用通知书。当年2月8日,翟天临在直播中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不知道“中国知网”,使得广大网友质疑其博士学位的真实性,并随之发现中国知网并未收录其博士学位论文,其硕士学位论文的知网查重结果显示重复率为36.2%。
根据北京电影学院2013年博士学位授予细则,申请博士学位需要公开发表至少两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招聘基本条件为,能够保证在站期间全时从事博士后研究,且需要提交两篇代表作全文。翟天临发表的两篇论文均不是国家认可的学术期刊,且其在《广电时评》发表的《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涉嫌抄袭。事件发生后,北京电影学院撤销了翟天临的博士学位,取消其导师陈浥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北京大学也对翟天临作出退站处理,对其合作导师作出停止招募博士后的处理,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给予严肃的批评。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省级学位委员会和学位授予单位三级质量管理保障体制,然而“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反映出个别招生单位和人员存在招生违规、学术不端、论文作假等现象。导师作为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既要做学术的引导者,指导和激发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更要做人生的领路人,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完善导师制度,强化导师的监督作用,将学术道德和论文规范纳入必修课程,才能铲除制造学术不端的土壤。
3 完善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需要遵循自律和他律的原则。自律是指科研主体对其科研行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而他律就是加强各类科研规范的建设,运用规章、制度、法律和社会舆论等手段来对科研行为进行约束。随着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只有结合自律和他律的治理手段,才能有效遏制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
3.1 完善科研诚信教育体系
科研诚信教育是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的治本之策。科研人员发生科研不端行为的原因,既包括主观的谋求不当收益,也存在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甚了解。2011年中国科协针对科研诚信教育的调查显示,38.6%的科技工作者自认为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缺乏足够了解,49.6%的科技工作者表示自己没有系统的了解和学习过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我国高校的科研诚信教育通常只在入学第一课,以及《学生培养手册》中涉及,这导致绝大多数研究生和年轻科研工作者并不知道自身行为已经构成学术不端,这也更加凸显教育的重要性。
强化科研诚信教育是履行科研不端行为治理自律原则的必然要求。科研诚信教育不应该是一次性的,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特别提出,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在入学入职、职称晋升、参与科技计划项目等重要节点必须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因此,高校和研究机构应该建立系统化的科研诚信教育体系,从师资培养、课程设计、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科研诚信教育资源,譬如引入国外先进的科研诚信规范教材和课程体系,开展科研不端行为的案例教学等;从入学入职、培养晋升和考核评价等阶段融入科研诚信教育环节,譬如将学术规范、科研诚信要求等课程设为必修课,按期召开科研诚信研讨会等。
3.2 建立科研诚信评价体系
科研评价制度对科研人员的行为起到引导作用。过于“量化”的评价体系容易营造出“急功近利”的学术文化,导致科研人员为完成“硬性指标”而急于发表文章,轻视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不利于科研人员开展重大的、长周期的科研活动。
将科研人员的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是实现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他律原则的重要举措。2016年科技部制定了《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定》,建立了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科研不端行为主体采取取消其申请国家科技计划资格等一系列限制措施。除了对纳入“黑名单”的科研主体采取一票否决以外,还亟需建立起覆盖项目/奖项申请、项目执行、成果发表、项目结题各个科研环节的科研诚信评价体系,完善落实合同约定、书面承诺、信用记录等具体制度,对相关主体的科研诚信度、科研合规度和科研践约度进行考核与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院士增选、科技奖励、职称评定、学位授予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3.3 强化科研诚信的舆论监督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和“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皆在网络上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针对科研失信案件的讨论沸沸扬扬。因为科学研究接受了国家和社会的资助,科研人员有责任接受公众的监督,科研不端行为也不应该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私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科研活动的监督,是完善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媒体、公众等第三方对科研不端行为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公开,要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与发布信息的权利,降低科学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针对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科研失信案件,当事人所在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查处理,及时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媒体座谈会等形式,实现多层面的对话与沟通。
3.4 完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2007年3月,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建立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从制度建设、宣传、落实监督等方面合力推动科研道德建设。然而目前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联席会议缺乏连续性,截止2019年底,全国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一共召开过7次,前三次联席会议间隔一年,而第四、第五次联席会议则间隔近三年。稳定连续的联席会议是保障科研诚信建设、督促和协调有关政策和重点任务落实的重要前提。二是联席会议的督查制度有待完善,目前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主要以联合发文的形式发挥作用,具体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工作仍由各单位负责。作为具体领域科研诚信建设的责任主体,各部门的工作难以得到有效监督,科研诚信建设的成效缺乏考核与评价,这不利于日后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工作的改进。
因此,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要从培育契约精神、提升合作协议权威性、强化部门间信息交流和完善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入手,真正发挥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联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