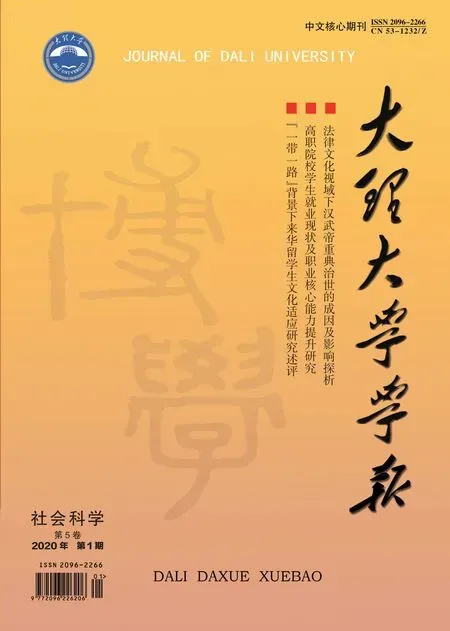“反常译,非常译”:刘易斯反常翻译观之述评
赵美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1985 年菲利普·刘易斯(Philip Lewis)发表题为《翻译效果的界定》(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的论文,为探索翻译的本质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该论文原写自法语,法语题目是“Vers la Traduction Abusive”。文章首先借译名的抉择阐释了翻译中的差异。刘易斯之所以没有使用“Toward Abusive Translation”的英文直译,原因有两点:首先是词意不对等。英文的“abusive”带有强烈贬义,偏离了原法语词的意义①对比英汉辞典对abusive的一般解释“谩骂的,虐待的”与法汉辞典对abusive的一般解释“滥用的,过度的,过分的”。。另外是出于语境适应的考虑。原题目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明确的态度倾向,若要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则应转向对翻译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的表述,以及对翻译差异的理解和评估②比较语言学为所敲定译名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刘易斯借用法国语言学家Jacqueline Guillemin-Flescher 对比英法语言特点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既注重宏观比较又不乏微观分析),逐一列举了英语和法语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与法语相比,英语有以下特点:a.倾向具体性和实在性,避免抽象模糊。b.注重对事实的客观记录和表述,避免主观评论性的语句。c.力求结构的严谨、完整、准确,摒弃松散、跳跃、重心不稳的表达。d.各表述成分紧密契合,前后一致,表意连贯。总之,英语比法语更要求客观准确、完整连贯的表达。。基于词意、表达习惯而产生的语言差异不但决定了翻译的差异,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译文不仅要符合译入语的通顺流畅,也要忠实地再现源文信息。身兼译者的作者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可以在流畅和忠实之间自由穿梭。而大多数普通译者往往只顾及通顺效用,在传递语言差异方面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刘易斯对德里达《白人神话学》(White Mythologies)一文的翻译特点进行了研究,并尝试思考一种新的翻译策略。
一、反常翻译的理论阐述
刘易斯把翻译看作一种必然涉及解释的再表现,其中包括两个相反的解释路径:翻译必须在忠实源语与归顺译语之间做出调和,这是因为语言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性。受传统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意义的简单搬运的影响,译者具有把内容所指置于形式能指之上的倾向。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批判。刘易斯受德里达的启发而提出“反常忠实(abusive fidelity)”③“abusive fidelity”有多个对应汉译。封一函曾将其表述为“妄用式忠实”,任淑坤曾给出“随意的忠实”,但都不甚准确。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曾将法语“non-usage”译成“反常之语言”,王东风进而指出,前缀ab-带有与non-类似的否定意义,于是主张“反常”的译法。本文认为,“反常”二字更贴近源语内涵,是较为可取的选择。的概念。“abusive”一词出自德里达所说的“Une‘bonne’traduction doit toujours abuser”〔1〕269,即好翻译总会有反常的体现。“abuse”与“use”相对,分别指语言的反常与正常,“use”体现了通顺易懂的使用价值观,倡导惯常的大众化表达,“abuse”则把注意力从源文本的所指转向其能指,关注句法过程、动态结构和语言机制的异质力量。特别是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形式是翻译考量的重要因素,没有形式就没有了文学〔2〕。
刘易斯认为,翻译的任务是挖掘差异元素,凝聚并更新意义的指示力量。反常翻译“忠实源语要素,创新表达方式,使译文与源文的多价性、多义性和表述重点相对应”〔1〕270。译文忠实于源文反常的语言表现,专注于对源语文本的反常运用,通过声韵、句法的错位,揭示源文意义的不确定性。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出自《论语·秦伯》)。由于春秋时代的文章没有标点符号,解之需经由句断,而不同的断句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若按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国家统治人民,驱赶他们做事就行,不能让他们知道所做的事。这明显是统治阶级的愚民之术。若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变成如果人民有能力,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没有能力,就教化他们明白。如此,差异化的解读实现了源文意义的扩张与发散,这是译者所应注意的。
反常翻译以源文的某些被强化的意义结构或文本转折、组合等能量集群为导向。译者需要寻找源语中的意义密集的结点。如《孔乙己》中的一句:“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3〕此句的反常集中于一个“排”字。人们一般会说“拿”出钱而不是“排”出钱。这一不合常规的表达显示了孔乙己的“阔绰”,他洋洋得意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如将“排”字译作“took out”,则明显抹去了“排”字的反常,如译为罕与“排”或“拿”相对应的词语“produced”,则更符合差异性的考量。译者应敏锐地捕捉并挖掘源文的反常之处,使之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刘易斯指出,译者不可为了追求译文流畅而磨灭源文的话语特色和锋芒。强大的翻译必须克服“自然”表达的引诱。译者的任务是找到使源文的反常特征浮现于译文的策略,思考如何自如地把控自然表达的程度,如何在目标语中恰到好处地调动源语的异质力量。这是反常翻译观的基本主张。作为一种通过打破常规用法创新语言表达效果的翻译模式,反常翻译在文学和非文学、文本与非文本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4〕。
二、反常翻译的例释
在界定翻译效果方面,反常翻译主张把注意力放在语言凝聚、喷张和扩散的高强度结点上,关注翻译所带来的意义和句法的变形,观察译文是否具有明显反常于原作的文本特质。下面,本文从标点与标记、词语、短语和话语四个层面,选取典型译例对反常翻译进行具象分析。
(一)标点与标记
在翻译过程中,对于目标语境中不存在的概念,译者应在译文之后以括号加注源文,有的译者却直接使用译文,不予标注,以减少人们对翻译的注意。也有译者擅自去除源文的斜体设定,弱化源文的差异性特征。例如佐哈尔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一文在正文之前以斜体呈现了这样一句话:“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James S.Holmes—a great student of translation and a dear friend”。这句对霍姆斯的特别致敬,不但表明了文章的学术承继,也凸显了个人友谊的温情,使文章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然而,一些中文译者在翻译这篇论文时却省略这句话而只保留了正文。文首的个人致意确实不常见于中文论文,但这样的翻译缺失无疑是欠妥当的,也是不负责的。
(二)词语
翻译中有许多推敲用词的案例。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I am still a little afraid of missing something if I forget that,as my father snobbishly suggested,and I snobbishly repeat,a sense of the fundamental decencies is parceled out unequally at birth.”〔5〕。巫宁坤译为:“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的,我现在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6〕姚乃强译为:“我现在仍然害怕有所闪失,怕万一我不慎忘了父亲对我的谆谆告诫,忘了那条我努力地反复诵记的忠告:人的基本道德观念出生时不是平均的,不可等量齐观。”〔7〕在词语层面,巫宁坤的译文给人强烈的异质感,而姚乃强则更符合地道的中文。源文出现两个副词snobbishly,巫译用两个“带着优越感”忠实地还原了原词的含义和词性,而姚译的“谆谆”篡改了snobbish的原义,且无法与“势力地”形成呼应。相比之下,巫译更遵从源文的表达特点,姚译则通过词语的删减、修改和添加,使译文更归化流畅。
又如《红楼梦》第四回的题目“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杨宪益和戴乃迭译为“A Confounded Monk Ends a Confounded Case”,戴维·霍克斯译为“The Bottle-gourd monk settles a protracted lawsuit”。首先,“葫芦”语带双关,寓指“糊涂”。无论是“confounded”还是“bottle-gourd”都只取片面之一义,不能传达双关效果。再者,源文两次出现“葫芦”,杨译通过重复“confounded”保留这一特点,而霍译的“bottle-gourd”与“protracted”不相对应,源文作为题目的特殊节奏感丢失了,相较之下,杨译更符合反常忠实的要求。《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如今,国家方针和时代主题要求对外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色〔8〕,那么保留中华语言文化精髓,让差异发生碰撞的反常翻译方式是对外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更为可取的方法。
(三)短语
短语是比话语稍小的语言单位。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有一处比喻:“Le pauvre garcon est bête come un rhinoceros.”〔9〕傅雷将其中的“come un rhinoceros”译为“(其蠢)似牛”〔10〕。汉语一般用猪而不用牛形容愚蠢。这一差异虽然不符合汉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但有助于他们理解“牛”在法语中的贬义用法。与上例对源文的忠实相反的是,很多归化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直译。如在张友松、张振先所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出现了“八字还算不错”这样的表达,如此过度归化使读者产生西方也讲“八字”的误解。又如西方侦探小说汉译中出现的“福尔摩斯拂袖而去”,其中“袖”字特定的文化意义(中国古代文人的长衫)也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对西式衣着的错误印象。
(四)话语
话语是最宽广的语言单位。译者一般基于两种语言的用法差异调整源文,使之更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这里有颇多反常译法的反例。如傅东华将《飘》中的“Seated with Stuart and Brent Tarleton in the cool shade of the porch of Tarleton in the cool shade of the porch of Tara,her father's plantation,that bright April afternoon of 1861,she made a pretty picture.”〔11〕译为“1861 年4 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小姐在陶乐垦植场的住宅,陪着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个叫汤伯伦,一个叫汤司徒的——坐在一个阴凉的走廊里。”〔12〕以分词结构呈现的状语置于主句之前,这在英语中比较常见,但汉语却不喜欢这样头重脚轻的句设。此外,英文惯用宏伟谨严的整句,汉语却以简洁轻快的散句见长,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节奏特色。于是译者出于对译文接受效用的考虑,对文字结构进行了大幅调整,省去分词,将源文拆分成多个并列谓语。
如果说上例中的归化处理尚属合理,那么为追求汉语流畅而滥用四字结构就是万般不可取的。如张谷若将《德伯家的苔丝》中的“The stage of mental comfort to which they had arrived at this hour was one wherein their souls expanded beyond their skins,and spread their personalities warmly through the room”〔13〕58一句译为“他们那时正到达了欢畅的阶段,所以都觉得神舒心畅,超脱形骸,满眼生花,满室生春”〔14〕。这种丧失源文朴实特性的表达恰恰走到了反常忠实的最反面,可谓“反常背叛”了。但张谷若早前的译本中有一践行反常忠实之处颇值得称道。原作中威塞克斯乡民的方言与标准英语形成了反差,译者为再现这种反常的差异感,尝试以山东方言翻译威塞克斯土语。如“You couldn't expect her to throw her arms round'ee,an'to kiss and to coll,ee all at once”〔13〕76。译文是“怎么,她哪能一下就把你抱上锅,撮上炕的哪?”〔15〕这一译法在后来出版的译本中被去掉了,或是因为以方言译方言的做法是否可行尚存争议,但是,与忽视源文的语言差异而不加区分的翻译相比,译者再现源文差异性的尝试不失可贵。
反常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再现源文的反常之处,承接源语域中被激发的凝聚或抵制的力量,还要将这种反常推进到新的语域,即在向译入语靠拢的同时保持对源语的忠实〔16〕。这么做的难度着实不小。刘易斯指出,翻译之所以能够维持源语和译入语的微妙平衡,是基于语言表达的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翻译中存在着多极力量:原作与译作相互影射,正常与反常两种规态同时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三个运作场域(源语、译入语及两者之间)来回转换,复制与重构两个目标共行并举,这样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体系化的翻译操作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翻译是语言运用的冒险性尝试,是基于实验和偶然性的创举。
三、反常翻译的引申
反常忠实受解构主义的启发,又推动了解构思想的发展。反常翻译主要是基于维护源文修辞和文体审美的考虑,而后现代译论则以此为跳板,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政治语境。
反常翻译观对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韦努蒂于1992 年提出“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的概念。他在评价反常忠实时说:“反常的忠实就要抵制在当代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通顺,提倡一种对立的策略,这种策略可以称为抵抗式翻译。”〔17〕抵抗的策略即是异化的策略,主张以陌生化的表达保留源语的差异。它摒弃翻译透明论,为抵制译入语文化霸权,故意使译文体现出陌生感和疏离感〔18〕。韦努蒂不但积极倡导反常翻译,也踊跃践行反常翻译。在翻译荷马的作品时,他选用古体词汇彰显久远的年代感,并借用斯哥特体、斯宾塞体和詹尼森体等不同的文体形式,以混合文风打破此前荷马译作千篇一律的纤柔〔19〕。刘易斯认为翻译应直接表现源文的异质性,而韦努蒂更进一步地主张翻译必须带来质疑译入语的异质内容,从源语的反常走向目的语的反常,并把翻译的伦理定义为为译入语文化带来创新。韦努蒂认为,英美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决定了英语的强势地位,他提出语言“剩余”的概念,呼吁主流语言接受边缘语言的非主流变体〔20〕。与刘易斯对文本特质的关注相比,韦努蒂的理论更具政治意味。传统的翻译认识是基于一种工具论模式,将翻译视为源文本不变量在形式、语意和效果层面的再现和转移。而韦努蒂在《翻译改变一切》一书中提出“解释学模式”这一核心概念。解释学模式是从解构主义视角审视传统的对等思维,认为翻译是根据接受语境价值观的等级关系改变源文本形式、意义和效果的阐释行为〔21〕。韦努蒂把翻译定义为与源文本建立对应关系的写作实践。他借鉴德里达的文本性概念,指出翻译是对源文本去语境化,然后在接受语境中重构语境的过程。这些论述是对反常翻译的引申和深化。
韦努蒂的思想从反常翻译发轫,突破传统译论的认识框架,推动了翻译伦理观从忠实伦理到差异性伦理的变渡〔22〕,这背后是对翻译本质之理解的超越性进步。差异性伦理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寻求对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替代,翻译不是求同而是存异。以刘易斯、贝尔曼和韦努蒂为代表的翻译理论家曾在西方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异化运动〔23〕。他们提倡含有异质成分的翻译话语,反对以通顺掩盖译者的作用,避免外国文本遁入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通过抑制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挑战强势语言的文化霸权,实现文化间的平等交流。这场后结构主义的反思,使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突破封闭的文本桎梏而进入开放的文化视域,刘易斯的反常翻译观是燃起这一进程的星星之火。
四、反常翻译的评辩
在晚近的翻译理论界,西方结构主义理论早先占据上风,解构主义思想经过翻译研究者的引介和运用后来居上〔24〕。反常翻译突破传统译学的经验主义范式,对翻译本质进行了深刻解构。反常忠实启发下的后现代译论与通顺主流背道而驰,具有浓厚的反叛色彩,长期以来在激发人们的翻译认识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针对其读者接受、译者操作和翻译目标等方面的质疑和批判。然而,面对学界批评之声,反常翻译自有其辩驳之理。
(一)读者接受度
反常翻译首先因其市场效用的不明朗而受到诟病。有学者指出,流畅通顺的译文更便于阅读,陌生的译文一般不易为读者接受,因此,反常忠实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少有采纳。但是,现实不占主流并不代表不值得推行。译者不能只被动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要主动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异质译文不但能使读者获知更多异域信息,也有利于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对提高国民知识视野实有好处。韦努蒂曾谈到异质译文的接受问题,他希望读者能把译文当作翻译而非源文本来阅读,具有一双主动识别差异的“慧眼”,并把译文和源文视为相互质疑的关系〔21〕。这样的理想受众虽为少数,但培养精英读者何尝不是翻译的社会效益呢?在如今以市场和效率为导向的环境下,资本似乎再无耐心容忍无法立刻产生实际效用的人文活动〔25〕。但人类终将从外向征掳再次实现内向溯求的回归。机械的实用思维给翻译画地为牢,反常翻译逆流而上,或许正预示了思辨性的翻译话语实践在当今市场化浪潮之中异军突起的潜力。
(二)译者操作性
有学者担心能力不足的译者可能打着反常的旗号简单直译,生产拙劣的译文。这是对反常翻译的误解。反常翻译要求译者识别并主动挖掘源文的异质内涵,并尽量以读者可接受的方式予以呈现,从而实现忠实与通顺的平衡,这恰恰是对译者能力的更高要求。如在小说《呼啸山庄》中,父亲问凯西:“Why canst thou not always be a good lass,Cathy?”〔26〕方平译本忽视了父亲的语言比之现代英语的反常之处,译为“卡茜,你为什么不能永远做一个好姑娘呀?”〔27〕。王东风则借用古汉语的形式,建议译为“汝总难成淑女,何也?”〔28〕,模拟源文的语言反常。前译抹去源文差异进行简化处理,而后译明显是译者更花心思之作。语言选择必须符合语法规则、社会场合等交际规范〔29〕。反常翻译不是不顾一切,肆意求异,而是追求超出一般译法的出色和非凡。另外,反常翻译观不仅针对翻译方法,也适用于待译文本的选定,即译者故意选择主流文化之外的文本,如一些名气不大的作品。译者要能敏锐体察时代的文化动向,具备选择“潜力”作者和“朝阳”译材的超前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助力翻译引领社会的文化风尚。如果只着眼于当前主流作家的热门作品,翻译的社会效用永远是慢半拍的。
(三)翻译的目标
傅雷曾言:“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用中文完成的创作。”〔30〕如果原作者会讲译入语,译本应该是他用译入语完成的创作,那么是否通顺流畅才是翻译首要目标?一般而言,凡是需要由另外的译者去翻译的作品,其作者往往是不懂译入语的(即使懂也很难做到精通),设想作者以译入语完成创作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设定。译者不该以通俗易懂去欺骗读者,让读者自以为轻而易举就已尽数悉知作品的思想内涵。事实上,大多数通顺流畅的译文往往是以译者擅自简化或修改原作为代价的,要完整再现源文全貌,译者必须注重对源文的差异性解读,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把充实的外来思想和知识带给读者,让没有外语能力的读者得到最大化的滋养,同时激发具有一定双语能力的读者阅读外语原作的兴趣。
五、结语
反常译,非常译。在翻译理论界,刘易斯这一非常态的翻译主张常常受到“刻意标新立异”“不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指责,但它为抵制世界经济和政治势力膨胀所带来的语言文字的工具化,提升翻译理性思辨的高度卓有贡献,其勇于打破传统的批判精神是万般可贵的。读者(译者)要努力发现文本的出人意料之处,挖掘作品与众不同的特性,并予之以充分的尊重〔31〕。我们不妨将刘易斯的反常翻译观与奈达的功能理论作以对比。功能译论立足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视角,关注语言的交际作用。而反常译论在审视翻译本质的问题上广开思路,主张异质交汇,塑造崭新的翻译话语,凸显翻译在文化整合中的力量。解构主义否定语言对等的稳定性和可依赖性,以互文性颠覆了绝对意义的存在,它指出,对等效用是相对于外部的社会文化条件而言的,其本身并不固定,因而并不可靠。
翻译绝非语言形式的简单转换,而是译者在心智上的投入与产出〔32〕。思辨和批判的力量为翻译之所为智性艺术的不可或缺。反常翻译或许在一般接受度方面稍显逊色,但其对语言差异的深入挖掘无疑具有很高的创新价值。通俗晓畅的文字确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但如果文字产出只满足于飨悦一般读者,文学与社会文化就很难取得长足进步。译者作为文字工作者绝不可只把目光局限于实用层面的通顺,也应追求语言之思辨哲理的光辉。或可说,通顺译论是为接受而译,反常译论则是为创思而译。启发思想比之取悦大流,两译论的思维站位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