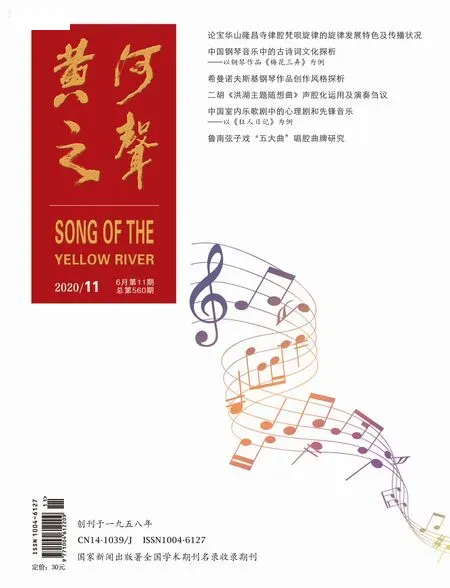德国作曲家拉亨曼音乐中的结构与听觉解析
张莹 (浙江音乐学院)
本文论述的是德国著名的当代作曲家拉亨曼先生的作曲理念。他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独特音乐美学观和新颖的声响效果使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开始逐渐走向国际作曲大师的前列,成为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作曲家之一。
笔者希望能从作曲思维的角度入手来分析探讨拉亨曼的作品中所体现的独特的创作方式和音响观念以及音乐听觉感知方面的看法。
一、关于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有个极端自我更新的愿望,许多新东西一旦出现就得到鼓励和支持。这种气氛影响了作曲技术的发展,在50年代的达姆斯达特现代音乐讲习班中维也纳学派的作品被重新审视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约翰·凯奇给讲习班所带来的偶然音乐的观念也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与以往不同的创作方式一出现便先后涌现许多新流派的追随者。
但这个新游戏法则并未被这个社会所完全接受,战后重新复苏的意识,使人们感受到了文明的种种威胁,特别是在美学感受领域,那些先锋者的作品以及在这个作品里面蕴含的艺术思想对公众来讲已不是感受“解放”而是带来不安,担心极端的决裂会把以往的音乐传统完全丢失,于是人们用“鸵鸟政策”为自己制造一个“安全之地”,试图重新回到市民化价值观念,抓住一些“旧”的东西。
拉亨曼认为,在这样一个立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两种趋势:其一,在1945年之后那个“零点”之后,一些先驱者用了序列的方法,他们期望用使用各种声学参数去发展一个复杂性纯粹技巧的作曲方法,产生一个没有过去音响影响和任何前提的听觉上的体验空间,这是与传统音乐的方式彻底决裂。其二,在利用所谓的好的口号自我标榜:“回到音乐,终于面向人类给他的感受和希望、和良好的表达方式。”他们在后现代主义及新浪漫主义的外衣下,把先锋的经验全部扼杀,从廉价的人们所熟知的手段中取到他们所要的“传统”,当前社会,超商业化大批量生产已使“传统”消失殆尽了。60年代的早期,欧洲处于大战崩溃之后的重建时代,结构主义给作曲指出了新的道路和观点。
拉亨曼认为通过结构主义,音乐开始摆脱枯燥、空洞、反时代的语言特征,把过去我们认识到的这些音乐概念彻底改变,音乐材料开始从声响和时间物理的基本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出发,重新定义了音乐的材料观念,并且把它重新予以表达。
而拉亨曼的音乐,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已经不仅仅以他自身结构的表达为目的,而是更加极端化了:创造新的、自有的材料概念,并把它作为创作对象,通过新的方式反思并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表达。
60年代,拉亨曼提出新的音响分类方式以及对音响组织材料予以新的定义,他从音响自身纯粹的物理条件考虑其声学上的感知,形成了独特的音响结构。随后,他提出一种新的结构思维:结构作为辩证的感知对象,产生音乐的含义。作曲家便是创造一个由不同音响“角色”所组成的独特关系,对于音响的角色之间关系的构思也是对结构的构思。“我们从声响与形式的内在辩证出发,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些作品是作为“语法的草图”来理解的,它们是包含了发展,次序和排列好比在时间上的投影,同时又表达了某些声响类别的发展,扩张。”①这种结构方式拉亨曼把它称做“辩证结构主义”。
“辩证”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拉亨曼作品的标记注释以及他的访谈中,在研究他作品中的音响过程到最终结构的形成以及结构的多样性关联、音乐内容与听觉经验的关系等等这几个层面的问题时,“辩证”成为他作品结构最突出的特征。
提到“辩证”,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的古典奏鸣曲原则,而拉亨曼对辩证特征的挖掘则是通过音响现象的时间冲突和二元紧张度中展开。1975年拉亨曼把美定义为“对习惯的拒绝”,美学上的冲突,对理解他作品中音响结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二、关于听觉
关于听觉的问题拉亨曼在从1971年开始到1985年,每隔7年都对其问题发表过言论,1971年,在斯图加特的音乐理论大会上,当时他的命题是“听觉是无助的,如果没有思想”;1978年补充为“听觉是无助的,如果没有感受”拉亨曼试着更精确的去描述听觉与思想、感受的相关性与相互条件。1985年又过了7年之后他的对语言的信任已经动摇了-因为他认为语言其实经常是自我表达的“拦路虎”,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命题改为这说“听觉是无助的,如果没有听觉”认为听觉就是重新发现自我,改变自我的过程。
拉亨曼在以上言论中所讨论的听觉问题,并不是有关于存在和意识的哲学问题,而是讨论听音乐和创造音乐的人——音乐爱好者和作曲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作曲家的“任务”。
在这个时代音乐爱好者与作曲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在20世纪勋伯格之后便产生了。人们喜爱音乐是因为源自于调性的传统音乐语言所带来的是有关于美的体验,在这里美的对象是被投射或升华的。然而拉亨曼认为,作曲家的任务并不是简单的保留传统而是把传统继续发展,因为对他来讲首要的并不是要去“说”些什么(要说的话意味这你要有一个可用的语言作为先决条件)而是去做一点东西,做一点能够被听到和体验并且能够让大家意识到并觉悟起来的东西。他认为音乐更重要的是把人们的听觉体验拓展,而不是去满足听觉期望,也就是说对作曲家来讲他应该去完成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后被赋予精神使命:不断继续的前行进入到新的未知领域,以此来更好的认识自我。
拉亨曼在北京的演讲中曾经说过: 音乐,最早的时候是人类用于召唤我们周围神秘的力量,在基督教西方国家的精神文明发展史的过程中,音乐改变了其手段并自我发展成一个主观的并能够说的“我”,音乐在这个路径上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会不断的突破已知的范畴,进入未知的“我的”领域,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道路中音乐在不断的对现有的主流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和人类观形成干扰于是作曲在这条路上必然与现在的社会发生冲突。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你很熟悉人的脸让你充满信任,如果他有很大的伤或者性情太变,便会引起我们认真去看这张脸如:面相学的结构、脸的各种线条以及他一些带有特征性的轮廓等等通过这个过程把自己与“脸”以及这个“脸”后面的人的关系重新去认知。他认为当感知离开信任的结构领域的时,你所熟知的东西可能会变为陌生,那个去认知的那个人,把他的关系与被认知的那个人重新审视定义的时候,他其实在改变他自己。于是“听”其实便是在已被发现的创造性结构中建立新的希望。
在拉亨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听觉的关键词就是结构。作为一个结构性的体验,这个听觉不仅仅是以发生对象的结构为导向而且他还关注这个对象与周围环境的对应关系随着其周边近的或远的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关系变窄或者扩张。简单的来讲便是:听觉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通过发声对象以及他周边的关系来实现发声——位置——走向。
拉亨曼认为一个结构的思维是一个通往熟知的或者未知的深处的钥匙,在他的作品中音乐是作为排序的框架,所有的声响和形式是互相渗透与通过彼此来确定的。那个单一的通过结构破坏又重新被释放出来的声响片断都是充满神秘的,因为音响个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结构,其内部就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是,但这个整体又成为作品大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由于音乐语言结构的改变使得人们对这样的一个音乐结构不可能马上理解。他依然认为“听”在一个日常音乐产品过分剩余的时代,必须通过真正进入到被听的对象的内部结构里带有挑衅性的感知来解放自己。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西方艺术的传统:把所有的已知的“安全感”拿来做“赌注”,通过自己感知的结构与之磨擦最后获得自我觉醒。
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不仅仅存在形形色色的威胁,更可怕的是对这些威胁的逃避,导致了一个依附市民的价值观美学感受。在这个社会里绝大部分把一个传统误解为一个物质化的艺术享受,把艺术当作一个很快捷就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错误的安全感的幻觉好比一个通过跳出自由进入“狮子的洞穴”②。我们的艺术必须从这个错误的“正常的”世界里突围出来,就如它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多次,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敏感性,它能够超越表现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游戏”。作曲家角色和责任便是要保护艺术不被商业化和庸俗化。
“感知在自我感知的过程中,跨越它认识到的以及觉悟和感受到的自我的追求真实性以及自我结构的力量,他由此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自由并通过认识去克服实现自由,自我认识(体验)通过创造性的材料与创造性的破坏与爆发达到的精神(体验)认识也就是艺术(体验)认识,反之亦然……音乐当只有在它的结构跨越自己指向其他结构--即围绕着我们以及在我们之中的真实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才有意义。”③
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听”不是关于用来逃避这个世界现实的音乐,也不仅仅是对拉亨曼的音乐中用噪音来控诉一个可悲的世界。而是正如拉亨曼本人所强调创作这样的音乐就意味着:他愿意去走上一个冒险的征途,把美的概念放在没有语言的条件下,重新去捕捉,希望它是来自内心的,即便没有语言,他也会回到心中去。■
注释:
① 拉亨曼,《作为生存体验的音乐》中《结构的问题》,1990,p84页,第一段
② 《伊索寓言》中鹿和狮子的故事:说的是一只鹿为了躲避外来的危险,躲进了狮子的洞穴中,孰不知进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
③ 拉亨曼,《作为生存体验的音乐》中《结构的问题》,1990,p92页,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