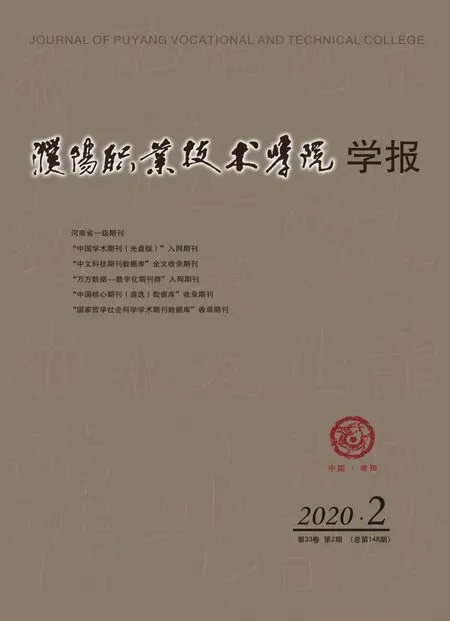罗近溪“赤子之心”思想发微
梁美玲
(新疆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罗汝芳(1515-1586),字惟德,号近溪,是明代阳明儒学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牟宗三先生评价其为“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1](237),其儒学思想建构与同时期的王龙溪相媲美,并称“二溪”。后期泰州学派的心学陷入异化,王龙溪等心学家甚至用一些佛学的思想与心学相贯通。罗近溪在此背景下通过紧紧抓住阳明心学,用“赤子之心”努力实现心学与先秦孔孟儒学紧密结合,防止儒学堕入佛学的危险,保持儒学根红苗正,使得过于强调社会规范的宋明以来的心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罗近溪的 “赤子之心”思想保持着先秦儒家的内圣之道这一根本方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不学不虑”
“赤子之心”最早出现在 《孟子·离娄章句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2](297)在这里,孟子所讲的“赤子之心”更多的指的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成王之道,仁政之端定会保持的状态。而罗近溪则认为大学宗旨、内圣外王等都可以用赤子之心来解释,可以说,“赤子之心”是罗近溪哲学思想的核心,其中,不学不虑作为罗近溪赤子之心思想的基本根据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孟子首先提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1](360)又补充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1](360)孟子视良知良能为人的先天本能,而不是后天学虑所得,认为不学不虑是孩提天生具备的良知良能,这样就把不学不虑提升到了仁义的高度,可以看出,不学不虑在孟子的思想中占有着重要地位。“良知”学说在阳明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作为泰州学派的杰出者之一,罗近溪继承并发展了阳明的 “良知”学问,连接孟子的不学不虑思想,认为“赤子之心”具有“良知”的本然意义,“赤子之心”即是现成“良知”,甚至可以说是“良知”本体,“不学不虑”便可“致良知”,可以说,“赤子之心”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超越性,是“不学不虑”的良知、良心。罗近溪指出:“赤子即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 ”[3](116)他认为,赤子本来就已经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若有不知,岂得谓之良知?若有不能,岂得谓之良能?”[3](116)良知即无所不知,良能即无所不能。罗近溪通过良知良能引出“赤子之心”,承认赤子良知良能的先天性,肯定“赤子之心”本来就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特性。这里所讲的“赤子”可以与孟子所讲的“孩提”进行比较,孟子说“孩提”拥有亲亲和敬兄本能,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及“孩提”的知与能的程度问题。不学不虑只是圣人内圣外王的一种能力,只有圣人能够具备这种品性。罗近溪的“赤子”由孟子而来,“赤子”不仅拥有“孩提”的先天能力,更是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越性。“孩提”的长成之身由赤子而来,而“孩提”长成过程中最难保持的就是最初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也就是人天生的纯净之心,自然天成,没有形色味的腐蚀,只有纯粹的内在。因此可以说“赤子之心”是不学不虑的圣人之心,人一出生所拥有的“赤子之心”自然完满,那么,“赤子之心”的保存并不是仅仅只能是“人上人”,而是人人都有保存的可能,并且成圣之道的关键就在于对“赤子之心”的保存,对其保存的基本根据关键就在于不学不虑。
然而罗近溪所说的“不学不虑”并不是不学习不思虑,而是一种大学,一种大虑,“学亦只是学其不学,虑亦只是虑其不虑。以不学为学,乃是大学,以不虑为虑,乃其虑而能得也”[3](117)。 “赤子之心”天然“不学不虑”,但是在罗近溪看来,“学”与“虑”是有必要的,然而“学”与“虑”的对象并不只是自身外在知识的增长。罗近溪的学习就是在践行这一观点,他在佛、道思想流行时也对佛学和道学有所涉及甚至拜师学道,用佛、道的工夫静坐入悟,然而正是因为对佛、道的痴迷难以保持儒学的纯粹,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晚年重视澄清自己的学问,与佛、道划清界限并告诫自己的孙子罗怀智远离佛、道,行儒学正道的原因。事实证明,过多的外在知识只会成为人的负累,隐藏本心,然而重要的就是纯然不变的心。显然,罗近溪所说的“不学不虑”不是对“学”与“虑”的全面否定,而是对外学与外虑的超越,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内学、内虑。欲望本身是外界音色味带来的,过度重视外在的学习难免被外在世界的其他所吸引,心学研究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出现偏离最初学旨的现象,因此,罗近溪提出“不学不虑”,学是“学其不学”,“学”以肯定“赤子之心”;虑是“虑其不虑”,“虑”以确立“赤子之心”。从根本上来说“不学不虑”的提出是为了摆脱当时“杂学”的诱导,保持心学原有的“赤子之心”,同时,联系先秦儒学,认为“赤子之心”的“不学不虑”就是完善的内圣之道。在此,“不学不虑”可以说是保持“赤子之心”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人抵达内圣的重要途径。明显看出,从孟子提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之后,罗近溪重提“赤子之心”“不学不虑”使得成圣的线索更加清晰,同样也为心学的发展提供了践行的标准。
罗近溪对“赤子之心”的坚定信念建立在先天的“不学不虑”就具备良知良能的基础之上,“赤子之心”是人初生时的自然本性,即是圣人之心。他以“不学不虑”把握“赤子之心”,面对当时心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他认为应该回归传统,抛开杂念,“不学不虑”,始终保持“赤子之心”。不可否认,通过“不学不虑”连接“赤子之心”具有超验价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先秦儒学的圣人之道相契合。
二、“生生之仁”
“仁”是孔孟以来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罗近溪将“仁”与人统一于“赤子之心”,以“仁”为发展线索,主张“生生”的仁爱观。“仁”与“赤子之心”是融为一体的,“心即是仁,仁即是心”[3](22),“赤子之心”即是内在德性的体现。在罗近溪的思想中“生生”与“仁”相互贯通,圣人的养成即是“赤子之心”“生生”的结果,又是“仁”的开拓和发展。
罗近溪以“生生”展开“赤子之心”,但是,“生生”并不是来源于罗近溪的思想,其“生生”思想是受到《易传》的影响而提出[4](15),《周易·系辞上》提出“生生之谓易”,宋代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解释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可以看出,“生生”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循环,无穷无尽。易有太极,太极可生万物,万物生命同样具有“生生”之意,所以,“生生”意味着无限的生命力。罗近溪作为心学的杰出代表,并没有将“仁”与心绝对地等同,在他看来,“仁”就是人心不能够正确解释“仁”的真谛,因为每个人的人心带有自身的特性,难以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持原初状态,从人心的初生、长成来看,惟有人出生之初的“赤子之心”才是最可贵的。前文中也讲到,人一出生就拥有自然完满的 “赤子之心”,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圣人,原因就在于每个人的“赤子之心”同样具有不一样的生命特质,平常人的 “赤子之心”在外界物质的冲击下逐渐消失,而最终能达到内圣境界的人一定是能够在物质世界中保持初生的“赤子之心”,这也是平常心与“赤子之心”的不同之处。因此,“生生之仁”实则指仁即“赤子之心”繁荣的生命力,其外在体现就是孟子所讲的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209),“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3](303)。孟子的仁爱主张在当时主要是对君王治世的献策之言,对圣人之道的养成也应该是有借鉴价值的,孟子将仁爱与圣人相联系,仁爱是内圣之道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圣人所独有的德性,因此,仁爱的实行是有必要的,圣人的养成不能缺少仁爱。孟子强调仁爱,在《孟子》一书中有大量的文字讲仁爱,这不仅是儒学主旨的体现,也是强调仁的一种内在品性,更重要的是说明仁爱的内求过程是对外在行为的指导。
罗近溪就是在回应孟子仁爱的基础上,希望通过“生生”之言自信“赤子之心”,用仁爱放大良知,使得“赤子之心”思想充实而光辉。在罗近溪看来,“孔门宗旨只要求仁,究其所源为易,又只统以生生之言”[2](277)。在这里,罗近溪指出儒家的仁学思想源于易,易有太极,太极化万物,万物生生。因此,“仁”就是在“生生”中悟得的,那么儒学中所讲的天命、人之本性同样是与“生生”相贯通,仁学思想统一于“生生”之中,具有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罗近溪用“生生”解释“仁”,用“心”悟“仁”,所以“赤子之心”发展“生生之仁”,“赤子之心”即是“仁人之心”。天地万物由“生生”而来,生生的天地以“大德”作为仁之原则。“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无尽曰仁,而人则天地之心也”[2](388)。先秦仁学思想主张天命,主张一种外在特定的条件。而到了心学时期所说的就是“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的中心是人,人即“仁”,人“生生”而无尽,在罗近溪看来,“生生”而无尽的人主要强调的是人的内在发展而不是外在单纯的增加。那么,人作为“天地之心”的体现,最接近“天地之心”的内在德性就是 “赤子之心”,“天地之心”即人心,人的“赤子之心”是纯真至善的,在本然意义上与“天地之心”具有同一性。“生生之心,心于人也”[2](388),从天地生万物,万物展现出无穷的生命力,到人的完满内求都可以看出“生生”之“仁”统一天地万物,包括“天地之心”。由此可以看出心、“仁”“生生”三者贯通彼此,“生生”是心的趋势,“仁”即心的本然,“生生”又是“仁”的生机,“生生”之“仁”的发展必然趋向“赤子之心”。
人一出生就带有的“赤子之心”是最干净、最真实的,但是其成长过程中很难不受外界的干扰,就现实而言,由于外在的知识负累,使得“赤子之心”在过度外求的过程中逐渐异化、逐渐丧失变得可能,阳明心学的发展同样如此。那么,如何回归人心的自然状态?如何保持良知学说的本源方向?罗近溪就是在这些时代问题的背景下追溯传统儒家的“仁”的思想并将赤子之心与《易》中的“生生”相联系,主张“赤子之心”符合“生生之仁”。针对现实的问题,罗近溪通过统一的“生生之仁”的传统观念重回原初的“赤子之心”,希望人能够保持真实之心,回归自然本心。人心是天地的中心,“生生之仁”就是人的内在“生生”,那么“仁”“生生”的完整体现只能是“赤子之心”。
三、至善至美
不难发现,罗近溪是孟子之后首倡“赤子之心”的思想家,其很多思想都受到了孟子的影响,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罗近溪思想对孟子思想的继承性。孟子以人性善为立足点,所提出的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都是“赤子之心”的体现。罗近溪的“赤子之心”赋予了阳明提倡的“良知”内涵,具有至善至美的特性,在他看来,人心见善,立地成圣,因此,至善至美的修养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
在罗近溪看来,孟子说性善仅仅局限于人性方面,并且仅仅在于上层阶级,不具有普遍价值,他说:“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为善只称尧舜。 ”[3](153)性善者只在尧舜,常人与尧舜不同,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尧舜,具有尧舜品质的人只是社会上层的少数。罗近溪认为,心与性是存在着差异的。性,天生带来可以善,心却在时间与空间的迁移变化过程中可能善,可能不善,也有可能无善无不善,所以“赤子之心”再次提出的必要在于规避心的不善,保存原初的善。在他看来,孟子所强调的“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并不是说只有“大人”才具有“赤子之心”而是想揭示“人性善”的道理。也就是说,“赤子之心”即是性善之本心[5](229)。罗近溪之所以重视“赤子之心”就是因为这能够保存人善的本心,同时,达到内圣的高度,在罗近溪的思想中,“赤子之心”可以说是最高的至善境界,“圣人穷理尽命,故常存吾性至善之本原”[3](314),圣人之所以是圣人的根本原因就是有至善的本原。与成人世界充斥着的各种欲望和利益不同,赤子的世界本来就是单纯自然的,所以“赤子之心”的本质就是善,在这里,性善就是心善。罗近溪高扬赤子之心就是赞扬它最初的善,这种善是一种至善,一种最高善,一种内圣的品性。“赤子之心”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才可以触及,它具有普世价值,无论君主还是百姓,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人人都可以追随圣人之道,“尧舜与人同尔”[3](153),若人人都保存赤子的向善之心,那么自己会在善的自觉中获得完满,他人也会受到影响得到幸福。同时他也指出,“赤子之心”在人的长成过程中有逐渐丧失的可能,面对现实,人在追逐外物的过程中变得自私自利、弃善从恶的可能性非常大,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应该如何回归“赤子之心”至关重要。因此,罗近溪认为践行阳明的主张必不可少,即“当下反求”,因为人的本体还在。可见,人与人之间善的相互作用能够带来的不是个人的小得,而是一种大得,能够营造和美的社会风气,使得天下太平。善的保持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当下反求,寻归本体。
按照罗近溪之言,赤子至善的本心与生俱来,善心是美的,那么“赤子之心”的至善性就具有赤子本真美、人性美与自然之美。“赤子之心”至善,同时“赤子之心”也应该是至美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罗近溪高度重视赤子,赤子、童子和“赤子之心”,带来的是对人的本真美、人格美的高扬。 ”[6](99-100)在这里,罗近溪的“赤子之心”被赋予了美学的含义,“赤子之心”首先是心美,反观人的整体,联系人的内在,用“赤子之心”养育出至美的人格,这也是对罗近溪至美“赤子之心”的另一种肯定。罗近溪是阳明心学的后派,他的思想依然是沿着心学的主题发展而来,提出的“赤子之心”具有至善的特性,他支持孟子的主张,认为人性生而有之,人性本善。人性善就是对人性美的完全肯定,赤子天然纯真的本心所具有的是一种天然的本真之美,善心实践善行凸显完美人格。虽然“赤子之心”是完满的善的存在,但是在物质世界当中,一个人完全没有欲望几乎是不可能的,欲望有浅有深,因此人心善恶难定,如果用欲望的深浅来断定善的高低,那么欲望由深入浅便可以去恶存善,这也是获得至善至美之心的方式之一。
在罗近溪看来,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但是圣人与世人还是有区别的,圣人是一个榜样的存在,是世人应该学习的对象。只有圣人才能抵达至善至美的修养境界,这也为世人的修养道路指明了方向。而这种修养道路本来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即是对心的超越,终点就是圣人,展现“赤子之心”本来的至善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