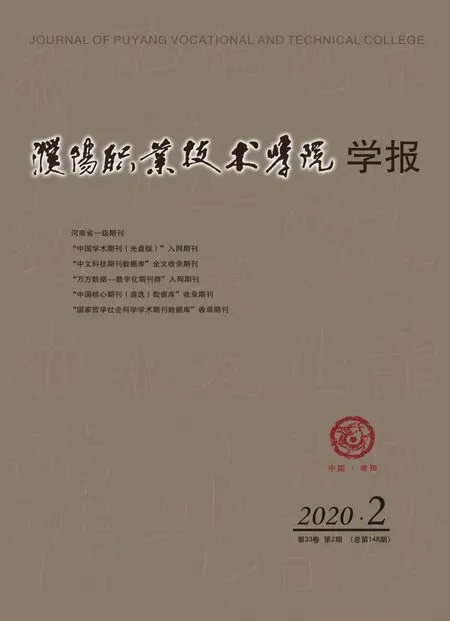清代咸同年间财政体制的变革
蔡 毅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力量强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1](22)。财政乃庶政之母,其对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国之财政制度,取决于其政治制度之性质,但政治制度也反作用于财政走向[2](4)。
清代,经历了由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变,财政体制也完成了由传统封建财政向近代财政的转型。以往研究多关注于清代前期财政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对于鸦片战争后的研究则对光绪宣统年间财政变革关注较多。本文截取咸丰同治年间财政巨变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兼论这一时期的财政思潮。清咸同年间财政,上承嘉道年间传统财政制度之始现危机端倪,下启光宣年间近代财政制度之发轫与转机,而其中的“不新不旧、童牛角马”之形态实为制度变革的过渡形态,为当今制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绝佳案例[3](57)。
一、咸同以前财政体制概况
清袭明制,在基本延续明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中央财政管理机构为户部,满汉尚书及满汉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十四清吏司,分别掌管各省财政收支及地丁漕粮盐课常关等事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机构,捐纳房负责捐输管理;钱法堂负责货币政策与铸币业务,下设宝泉局 (工部为宝源局);井田科负责旗地与内务府庄户。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分掌银钱、布匹绸缎及颜料纸张出纳[4](2)。
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方面,各省设布政使,总管一省田赋杂税,每年两次催征所属州县钱粮杂税。其余税款主要为漕粮、盐课、关税。漕粮即将有漕省份所征之米麦豆沿运河送抵京仓或通州仓,设漕运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巡漕御史、督粮道、库大使等官吏专司漕运。清初于各省设巡盐御史,康熙之后,改为由总督、巡抚兼任,下设盐运使司、盐法道等基层派驻机构。清代常关分为户关与工关,户关税款充入户部银库,工关税款供工部修缮之用。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财政收支款项除一小部分“存留”作为地方日常经费开支,“留贮”或“分贮”以备不时之需外,其余全部作为京饷解缴京师或协解他省。
清代吸取明代皇室过度占用国家财政经费的教训,专设内务府管理皇室开支。下设广储司统筹宫廷所需物资出纳,设银、皮、瓷、缎、衣、茶六库,并辖京师内织染局及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设会计司领畿辅、盛京、热河、归化城等地886处皇庄田赋并庄丁编审[5](95)。由于拥有一大批田庄地租收入、各地岁贡、各级官员报效,外加借给盐商生息的高额“帑息”以及崇文门关税收入,清朝前期内务府经费来源充足,不需要动用国库存储便可满足皇室开销。相反,国家财政支用浩繁之际,内务府屡屡拨款以充国库支用。
财政管理制度方面,存留、起运、冬估、春秋拨、解协饷、漕粮北运、钱粮奏销考成等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四柱清册、赋役全书等较为完备的上报形式。三藩之乱后,内地大规模战事基本结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策鼓励开垦土地与人口增长。历经康雍乾三代君主的励精图治,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至1778年户部库存银达到8,341余万两之巨,成为整个封建时代国库储蓄的最高峰。
这一时期清廷继续秉持量入为出的传统儒家财政思想,即孟子的“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康熙之后的历代君主恪守“永不加赋”的祖制,以此为施行仁政的基础。财政收入方面地丁钱粮几占一半以上,关税杂税等工商税收所占比例极小,支出则以军饷、河工、皇室开支为大宗。且冬估制、春秋拨制及地丁钱粮奏销与兵马钱粮奏销的同时进行,已经显现出清代前期奏销的“预算”色彩[6](69)。
至嘉道年间,财政状况逐步恶化。嘉庆帝从其父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日已偏昃的庞大帝国。盛世难续,衰败之期将临。嘉庆堪称守成之君,但究竟没有其父的胸怀与气魄,“盖极盛之后难为继,清代士大夫辄以乾嘉并称,讵知丰啬不埒”[7](11)。嘉庆元年湖北的白莲教徒以“官逼民反”为号召,首先揭竿而起,很快席卷川楚陕等省,这次大起义前后历时9年之久才被镇压,参加群众多达数十万,抗击了清王朝从全国十六省调来的军队,使清政府耗费了2亿两军饷,相当于当时4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成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8](15)。之后战事频仍,军费及战争赔款不断增加,加之水旱灾祲,河工经费不断攀升,直接导致户部库存银数总体上呈逐年下降之势。更有甚者,职掌银库官吏串通舞弊,中饱私囊,至1843年银库案爆发之际户部存银仅为292万余两。
但将嘉道时期的财政与咸同时期相比,前者的优越性不言而喻。简言之,这一时期的财政虽不似以往充盈,但绝非一无是处,可以将其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性财政[9](375)。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中央与地方各机构尚可正常运转,量入为出、“指臂相联”的传统财政体制得以继续维系。
二、咸同年间财政体制变革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使清王朝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截止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十二日止,银库存银仅22.7万余两,尚不足支付七月份的兵饷。加之此时江南财赋地区已被太平军控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部库既陷于困竭,军前饷需,户部便无法筹措,唯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也知其不济,乃各自为计”,于是就地筹饷之法便起[10](104)。其时将帅用兵,都以“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11](57)。
清王朝为筹措军需,可谓费尽心机。发内务府广储司内帑银以充军需,暂停内廷一切应修工程,裁撤杂役,甚至奏准将内务府库存的三口乾隆年间铸造的金钟熔化[12](9),铸成 8503 块金条,总重 27030 两[12](27)。还大开捐输事例,采用加中学额的方法刺激民间捐输,使得本已江河日下的吏制、科举制度更加腐败不堪。且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有各级官吏勒索绅商,使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银两与制钱的比价不断上升,处于“银贵钱贱”的状况之下。王庆云称,“自嘉庆银之外泄亦日多。由是钱价一贱近三十年即不复贵,至今日每两易钱二千,较昔钱价平时盖倍之,较贵时几及三倍”[13](215)。及至咸丰年间,一方面由于交通线路被太平军切断,云南铜矿难于运出,造钱原料奇缺;一方面出于舒缓财政压力,搜刮钱财考虑,清政府不顾历史上滥铸货币的前车之鉴,不惜饮鸩止渴,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高值大钱并大量印制票钞。因铸钱的工银、料钱有限,所铸大钱的面值越大,收益越大;并规定凡文武官俸、兵饷等各种官放之款均按一定成数搭给大钱票钞,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及部课捐输亦可搭交大钱票钞。由于大钱的含铜量低,制作低劣,致使民间伪造盛行,劣币驱逐良币,制钱壅滞,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币值紊乱,大量民间财富迅速蒸发。由于实际流通中票钞不能兑换现银现钱,以票钞买物,市肆铺户又坚持不收,或倍昂其值,或任意折算,在交纳钱粮课税之时,地方官吏又从中舞弊,尽量少收或不收票钞。在几种情况交互作用下,票钞的壅滞和贬值当然也就难以避免[14](654)。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甚至一些宗室远支也铤而走险,打砸店铺,聚众劫掠,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货币赋税方面,地方督抚另辟蹊径,征收厘金,举借内外债,加强海关税收。在短时间内筹措了大量军饷,源源的现金流成为帮助清王朝渡过难关的一针强心剂,工商业税收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曾国藩在筹措军饷过程中,就曾上书咸丰帝,“敕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于上海关税项下,借拨银十万两,迅解江西,以济眉急。如该处厘金办有头绪,尚可扣还归款”[15](610)。
实物赋税方面,漕粮海运与改折,既打破了太平天国对漕运故道的封锁,又节省了大量的漕运经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紧张局面,并且有利于税收由传统的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转化,降低征收成本。但地方官员借漕粮改折之机浮收苛征,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与此同时,大批失去生计的漕丁、水手揭竿而起,成为补充太平军与捻军的有生力量,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太平天国运动中,地方财政管理机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集中有限资源镇压起义,各地方督抚大员将所辖区域内行政权、军权、财权牢牢掌握于手中。之前严格的奏销制度流于形式,地方财政自主决策权大大增加。督抚纷纷自设粮台、厘金局、官钱局,截留京饷、关税、盐课、漕粮。太平天国运动后,这些机构也多被保留。旧有地方藩司,盐政、漕粮、常关等管理机构由中央派驻地方办事机构沦为地方督抚的附属机构,新旧机构叠床架屋,虚耗大量行政经费。
清代前期,各省已有不报部的“外销”收支,但所占比例很小,且多掌握于地方官个人手中,不能算作“名正言顺”的地方财政收支。太平天国起事后,各省纷纷在藩司外自设机构,兴办洋务,截留关税、厘金、捐纳收入,“外销”不报部款项急剧增加。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理财政,试办全国财政预算时,地方行政经费已达3,770余万两之巨,其中尚未包含漏报及未报部之款项,外销款项已达到积重难返、难以整顿的地步。
财政收支结构同战前相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战争过程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之东南地区多被太平军占领,漕粮北运难以维持,地丁钱粮在赋税中所占比例下降,而以厘金、关税为主的工商业税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之后的光绪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几乎相当于乾隆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的两倍,地丁钱粮收入由乾隆年间的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下降到光绪年间的约占三分之一,而新增的厘金、海关税收则占到了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强。经费支出方面,乾隆年间,八旗、绿营军饷支出约占了总支出的一半。光绪年间,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后保留下来的湘淮军等武装未予全部裁撤,反而成为清廷所倚重的重要武装力量,勇饷支出成为当时数额最大的新增财政支出,与官局经费、外债支出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新增财政支出,约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新增财政支出与旧有支出款项杂糅交错,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因循守旧,恪守祖制,不对旧有支出酌量裁减,如八旗绿营兵饷与新设防军、练军勇饷共同占据了财政支出的一半左右。一方面由于地方督抚坐大,在原有机构之外新设局所,新旧机构庞杂,大量冗官冗员糜费大量行政经费。
此外皇室开支较乾隆年间大为增加,从同治五年起,户部每年都要向各省、关指拨“内务府”经费,由各省、关直接解交内务府充用。内务府还常以经费不敷为由向户部借款,成为这一时期财政支出的另一大特点。
与此同时,地方督抚大都意识到财政的重要作用。李鸿章在给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书信中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16](3665)清王朝在中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地方大员纷纷购买外国先进枪炮,编练防军,组建新式海军,创建机器局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上述“洋务”无一不从厘金、海关税等新式税收中筹措经费,这些新增款项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交通运输业、教育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三、财政新思潮的萌发与财政变革的影响
清王朝前期一直秉承“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王朝财政日益捉襟见肘,被迫采取田赋加征、盐斤加价等手段筹措军饷,百姓负担日益严重,抗捐、抗赋运动此起彼伏。巨额的财政支出,迫使清王朝千方百计增加收入,部分官僚士大夫的财政思想逐渐开始由“量入为出”向“量出制入”转变。
伴随着中国关税主权的逐步丧失,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关税自主,收回利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条约,签约列强商品进入国内普遍实行值百抽五的超低税率,且运销内地的子口税率仅为规定进出口税率的一半,加之外洋商品货美价廉,而华商货物则逢卡抽厘,负担沉重,失去了与洋货竞争的能力。郑观应主张:“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共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则洋人无以藉口,华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 ”[17](321)
冯桂芬在其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也提出了若干财政主张。具体可以概括为筹国用、节经费、杜亏空、裁屯田、利淮盐、罢关征等七个具体问题。主张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漕运、土贡、淮盐等行政体制下积弊;运用行政手段,合理干预经济运行,撤销国内关卡,统一度量衡,节省皇室与八旗兵丁开支,裁撤屯田;杜绝亏空积弊,加征酒税,抑制过度消费[18](244)。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看来仍有不少可取之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浪潮之后,清王朝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统治,收买人心,但吏制却更加腐败。时人赵烈人在日记中有所揭露:“到龚孝拱处久谈,言恭邸颇黩货,胜保在时,曾以二万金为献,误投惠王府,旗人凡赠要津,例不具函。惠王遂欣然纳之,而召醇王与之万金,曰,此非吾辈所有,至则受之,何用辞让,醇亦大喜……宫中近传索金珠翠玉甚众,广储司库银堆积不动,相传留为仓皇奔徙之用,外人逼处肘腋者,动息皆知之,不之避也。 ”[19](21)满洲皇亲贵胄尚且如此,各级大小官员的廉洁与操守也就可想而知了。
工商业税收的比重增加与传统农业税比重的减少,反映了传统封建经济的逐步解体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兴起的过程。虽然官办的洋务企业占了当时企业的很大比重,但是毕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开始出现。厘金捐纳等封建性税收一方面显示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税源的增加,另一方面显示出清廷财政税收制度的滞后性,遍设关卡,画地为牢,虽然一时解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后果无疑于杀鸡取卵。
天平天国起义中清王朝财权下移与其自身的财政体制也不无关系。清朝前期只有国家税,没有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所有地丁、漕粮、盐课等税款由中央委托地方征收。地方按照中央指令,存留部分地方行政开支经费后,余款或解往京师,或协拨临省。从税款征收角度看,所有税款属于地方税;而从税款管理角度看,所有税款属于中央税,这样便产生了管理权与征收权和中央地方享有税款比例分成之间的矛盾[20](68)。在承平之日这种体制还能大体维持,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各地领兵的督抚大员为了本地利益几乎无不欠解京饷,甚至截留通过本地的款项以充军饷,不受户部制约的外销制度更呈愈演愈烈之势。以往的钱粮奏销制度因为战事而难以为继,仅以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奏销案为例,因为迁延日久与防范书吏借此勒索而使将士寒心,数额巨大的奏销也仅奏明存案,不了了之。
如有论者指出的,“解协饷制度是清代整个财政体系运作的中心环节……而只有通过解协款制度的运作,才能实现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1](26)。而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督抚无不截留京饷充做本省军饷,对临省协饷大多置若罔应。解协饷制度的逐步瓦解标志着清政府对各地财政收支调控能力的逐步丧失。
随着清朝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逐步瓦解,实际上形成了中央与各省两级财政,而且财政收支的重心在地方而不在中央,也就是说,财政大权逐步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21](224)。统兵之权与财税之利的互相结合,地方督抚的独立性与离心力越来越大。“东南互保”中南方总督公然抗拒清廷对外宣战上谕,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独立风潮风起云涌,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均接踵而至。
清廷虽吸取明亡教训,设立内务府,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予以分离。但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缺少类似英国《大宪章》之类法律对至高无上皇权的制约,以致咸同以降内务府借支户部事件屡有发生,最典型的事例便是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兴建园囿,使户部不胜其扰。
而与此同时的欧美日各国纷纷取消国内关卡,统一货币度量衡,保护民族工商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国家税收,鼓励科技发明创造,大力发展各层次教育。中国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但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引之下,只是有限度地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遵循祖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反而越来越大。直至宣统年间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分设清理财政局,编订各省财政说明书并试办宣统三年预算,还未等到次年的决算出炉,清王朝便寿终正寝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是传统封建财政体制逐步转向近代财政体制的过渡时期,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财政收支规模较嘉庆道光时期显著扩大,收支结构呈现出新变化。厘金、海关税、外债等新增收入比重逐年上升,传统田赋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勇饷、洋务、外债支出等新增支出比重亦逐步上升,表明中国半殖民程度逐步加深与近代工商业的初步发展。第二,中央集权财政体制逐步开始瓦解与地方财政的逐步形成。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廷被迫默认地方督抚自筹军饷,财权开始由中央下移地方。战后督抚利用手中的财权兴办洋务,扩充势力,外销不报部款项急剧增加,导致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大一统的封建财政体制开始遭到破坏。第三,各省新式财政机构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纷纷出现,上述局所直接听命于地方督抚,逐步把控地方重要财源,与藩司等旧有机构叠床架屋,新旧杂糅。第四,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经世致用的地方督抚与知识分子审时度势,阐发了旨在开源节流的一系列财政思想,颇具借鉴意义。但颟顸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一时期未能从根本上对财政进行彻底整顿改革,财政困难又导致了国家机器运转困难与吏制败坏等一系列连锁政治问题,最终成为清王朝走向覆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