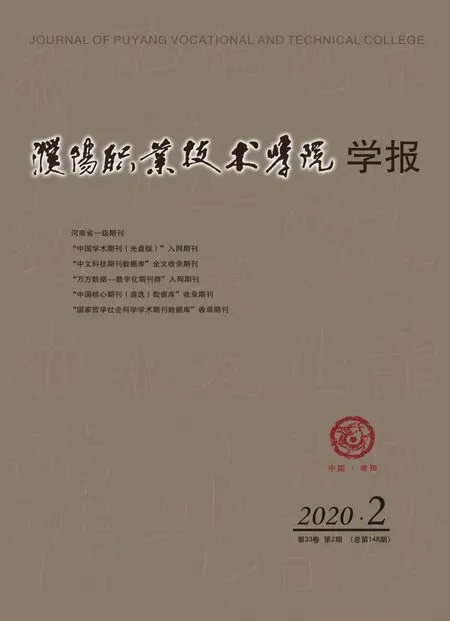探灵魂之林 书印象之华——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独特性
关 莹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现状
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受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随着时间发展呈现出曲线状发展样态,可大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文学批评注重主观感受和思想启蒙,缺乏科学理性分析,其影响主要在“京派”作家群及相关的读者群。当时以意识形态角度切入的社会历史批评是批评界的主流,备受众多作家、批评家推崇。而李健吾是非主流批评家,他的印象主义批评强调艺术的文学性,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与社会历史批评格格不入,所以并未引起较大反响。当李健吾《咀华集》中的评论先行在《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的时候,最先受到了沈从文、朱光潜等文人的推崇,也受到了欧阳文辅等人的批评,认为李健吾是“旧社会的支持者”。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便在赞誉和批评之中获得了关注。
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李健吾文学批评两极分化,在大陆和香港分别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在这一时期,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大陆被边缘化,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很少提及李健吾及其文学批评。但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却对李健吾赞誉有加,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五大批评家中以李健吾成就最高[1](74)。司马长风认为李健吾是唯一一个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阅读并评价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家,这种评价在当时香港引起了不少争议和学术争鸣。
第三个阶段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健吾文学批评形式更加多元化,内容更加丰富,但现代意识不强。温儒敏第一次将李健吾纳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之中,他认为《咀华集》的出版“应当看作是现代批评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印象派批评已经具备不可忽视的实力”[2](96)。 《李健吾传》的出版展现了李健吾传奇的一生,为李健吾文学批评提供了更加详实的研究材料。
第四个阶段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李健吾文学批评更具理论深度和现代意识,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李健吾作为批评家的名声逐渐比他作为作家的名声更大,引起了许多青年评论家的关注。在学术专著方面,更加系统科学,代表作有《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审美现代性》《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京派文学批评研究》等等,这些专著对李健吾现代意识的研究更加具体全面。在学术论文方面,更具深度和创新性,代表有《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现代观》《审美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学批评——以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为中心》《一个中国式的现代文论典型范式——论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等等,这些学术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李健吾文学批评观念以及背后蕴含的现代意识。
通过梳理李健吾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提升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的水平,也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水平。
二、采纳中西,含英咀华:李健吾文学批评方式的生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批评理论、西方文学和西方批评理论的影响。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受到外国文学和理论“科班”训练的李健吾,在长时间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纳中西,将中西精髓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印象主义唯美批评。
(一)中国古典文学和批评理论的因袭传承
在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众多批评家纷纷抛弃传统,转而选择建构西方的理论大厦,李健吾在对法国印象主义批评进行吸纳的过程中,却较多因袭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批评范式,主要体现在批评思维、批评原则和批评方式三个方面。
李健吾批评受到直观顿悟式思维的影响。直观顿悟式思维是指接受者忽略时空要素、文本要素等隔膜,透过语言直接寻求一种心理共鸣的直觉感悟。这是农业文明时期人类认知事物的方式,缺乏逻辑推理和演绎,而是以经验和直观体验为主。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思维特性,如老子的“虚静说”,庄子的“物化”和“心斋”等等都表现了直觉体验。古代文论思维大都遵循批评者自己的知觉去感受和咀嚼作家作品,这种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借用感官直接品评作品,运用身体风貌展现作品美学风貌。例如钟嵘把阅读感受用“滋味”说表达出来,即用舌去体悟,还有利用听觉和视觉等等。
李健吾的批评文本中具有浓重的直观体悟式思维色彩,他多以直观感受作为切入点,在对对象的整体直观把握中,于一瞬间感受到对象的鲜明特征。为了保持阅读的原初体验,李健吾批评文本中逻辑推理和演绎的论述很少,较多的是感悟式的论述,“作者全叫读者自己去感受,他连读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种空气里,在这里不光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3](56)。这段文字运用了感官去体悟,去描绘,调动起读者的感官想象,一同完成文学鉴赏的过程。
李健吾深受评点式批评原则影响。评点式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独有的批评原则,在其背后需要批评者个人的经验、阅历、学识作为支撑,得出的印象是具有个人特色的独特印象。正是由于评点式对于批评者个人能力的高要求,很少有批评家能够将直观印象以精妙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除了要求批评者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领悟力,评点式所要求的文学文本篇章也要短小精悍,而不是长篇巨著。在评点的过程中,着重采用白描的手法对批评对象作快速而传神的勾勒,而不注重对于作品概念、术语的严密分析。除此之外,评点式的明显特征是兼顾读者感受,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一方面批评者将自己放置在一定高度上对作品进行阐释理解;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注重将自己置于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来看待作品。评点式的批评原则首先应用于诗文鉴赏之中,代表作有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清照的《论词》等。而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延续到对诗文、小说、戏曲的点评,成为专门的批评体式,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金圣叹评《三国》、脂砚斋点评《红楼梦》等。
李健吾十分擅长采用评点式的原则勾勒作品整体风貌。他常常一语中的,把握住作品的主要神韵、美学气质和作家本人的审美个性。譬如评价《边城》中的沈从文“是热情的,然而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3](25)。肯定沈从文的自然诗性;评价矛盾作品“如登山揽胜”,具有反复体味的美学效果;点评巴金作品如“流水泛舟”,顺畅而缺乏浓度。他的批评文章篇幅短小,却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在李健吾的批评里,十分注重与读者的交流对话。他认为:“寻美的批评家是在对读者讲话,是要让他们明白一本古书或新书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他不是在对读者讲话,完全用不着说他们的作品令人赞赏。”[4](10)李健吾以从容平和而又充满意趣的态度与读者沟通,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他不仅是一位读者,更是读者的引领者,带领读者游历仙境。
李健吾多采用比喻、比较的方法来阐释自己的批评思想。中国古代就注重运用比较和比喻的方法。钟嵘《诗品》中采用了大量比喻式批评的手法;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运用比喻为二十四类诗文风格作注释;曹丕《典论·论文》中采用比较的方法,用来评价建安诸子,品其优劣。这些批评方法的运用不仅拓宽了批评视野,也加深了批评深度,是古代诗话、词话中常用的批评手段。
李健吾运用比较的方法开启了批评的广博,用比喻的方法丰富了批评的意象。在评价何其芳《画梦录》时,将何其芳和废名加以比较,在比较中展现何的特点。将《画梦录》中的造句和废名的文笔进行对比,先言两者相似之处,后论两者相异之处,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见何其芳的诗文特点。他说:“何其芳先生如何不同于废名先生,单只想想这样长而繁复的造句,就明白了他们的——饶如我的贫乏——文笔和气质最后又是如何的不同。何其芳先生不停顿,而每一段都像一只手要弹十种音调,唯恐交代暧昧,唯恐空白阻止他的千回万转,唯恐字句的进行不能逼近他的楼阁。”[5](36)李健吾善用比喻手法来把握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美学风格,或是阐述文学本身的性质特征和美学风貌。他常常明喻、暗喻等手法交叉使用,共同完成整个鉴赏过程。例如李健吾这样评价沈从文的作品:“《边城》是一首诗,是二姥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6](79)李健吾大量运用比喻不仅因为评点式批评方式需要借用比喻穿搭准确生动的直观印象,还因为顿悟式的思维方式限定。在批评实践活动中,比喻是他的认知,比较是他的机杼,两者相互交融,融入他的批评生命之中。
(二)西方文学和批评理论的借鉴超越
李健吾有深厚的国学底蕴,将中国古典文学和批评理论融会贯通,还有着丰厚的外国文学修养。留学法国,翻译法国文学,这些外国文学的实践经验让他能够将西方文学和批评理论熔铸到自己的文学批评之中,使其批评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西方对李健吾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印象主义、作家福楼拜和散文大师蒙田。
李健吾在批评实践中一再引用“灵魂在杰作中的奇遇”这句代表印象主义的名言,从中可以感受到他深受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印象主义批评流派是西方十九世纪出现的一种批评流派,主要批评家有查尔斯·兰姆、法郎士、瓦尔特·佩特等人。印象主义继承了唯美主义的衣钵。唯美主义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否认艺术模仿人生,这些观念与后来印象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一脉相承。此外,印象主义者很看重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发挥,他们赞同王尔德唯美主义命题,将批评和创作一视同仁。印象主义批评还有一点引人注目,即以个人的情操作为批评的唯一工具,否定批评的任何理性标准。如果考察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他对印象主义理论继承的关系。
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了解广泛而全面。他在翻译研究这些理论和作品的时候,也将印象主义融入自己的批评血肉之中,有自己独特的体悟。其一,李健吾认为印象主义批评的依据是自己的经验,而经验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灵魂的感知。其二,这种感觉是主观的,具有个性色彩。其三,感觉的效果取决于心理体验的程度,也决定了作品的深度。所以一个批评家要有敏锐的感受力和挖掘深度的能力。李健吾考察和参照了诸多印象主义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观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融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方法,即“自我发现”论,将批评视为一种“自我发现”。他试图革新批评的自觉意识,所以提出“自我发现”就是宣告“批评的独立”,批评从附庸地位转变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在“自我发现”的指导下,客观固定的标准也被打破,他更加注重作品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激发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作品中再创造的意义,这种拓展性批评思维十分接近接受美学的观点。李健吾比较集中的评介印象主义批评理论的文章有:评论巴金的《神鬼人》、评价沈从文的《边城》《自我与风格》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消化和吸收印象主义批评理论的精髓。
李健吾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是自觉的选择。李健吾少年时期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随后同朱自清启程赴欧。到了法国之后,李健吾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积累了深厚的外国文学底蕴。李健吾十分推崇福楼拜,并选择福楼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在福楼拜研究上,创作出了见解卓越的《福楼拜评传》。这部巨著旁征博引,结构简略明晰,是后人研究福楼拜无法超越的作品。
福楼拜影响了李健吾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李健吾推崇福楼拜的孤傲,不出卖灵魂,在理想中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李健吾深受福楼拜影响,认为作家得天独厚的精神气质才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朽的根基。李健吾将创作批评视为他的生活,艺术是他的灵魂,字句是他的悲欢。福楼拜的艺术精神也是李健吾欣赏追求的。从李健吾《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中流露出来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都可以找到福楼拜的影子。福楼拜追求“美”和“激情”,将其视为创造的最高生命。而李健吾在文学批评的理论追求和实践中始终保持着“福楼拜式的热情”,对艺术美自觉的追求,并为实现艺术美而不断努力。李健吾除了关注福楼拜对于艺术美的追求,还接受并吸纳了福楼拜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李健吾在批评实践中一直用审美的眼光评价作品,用艺术的形式联系生活,让生活与美相互联通,充满艺术的美和人文的关怀。
李健吾的批评注重印象和感受,在文体上表现出美文式的随性感,带有十分明显的蒙田随笔的特色。蒙田是法国著名的散文家,所著《随笔录》集哲思和情趣于一体。他的随笔以无知作为出发点,对自我进行探索和追寻,具有一种细腻隽永的美感。李健吾在《咀华集》中多次提到了对十七世纪蒙田散文的欣赏,在批评实践中,他积极实践散文诗化的蒙田随笔体。李健吾的评论文章灵活自由,没有固定的格式,语言优美诗意,很少有开门见山式的论述,节奏散漫舒展。李健吾的目的不在于下结论性的评判,而是试图与读者沟通,向读者传达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体悟。他的文学批评入题很慢,文章中大部分篇幅都在陈述与评论对象无关的人和事,如同一个在公园中闲庭信步的游人。李健吾的“游离功夫”让读者对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领略到作家的人格精神,这是李健吾所追求的“最高层次”。以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为例,李健吾用几乎占全篇三分之一的篇幅谈“题外话”,先谈翻译之难,再谈废名隐士之风,最后才转入话题谈到巴金。很多人认为他的批评写得过于散漫,中心议题不突出。但正是由于李健吾随笔式的文体风格让文章更扎实,让读者读后酣畅淋漓。
三、形神相继,独树一帜:李健吾文学批评观念的独特性
李健吾采纳中西,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咀华批评。他在批评实践中努力践行着平等、宽容的批评理念,发扬中国传统的批评品质;他将感性和理性在作品中完美交融,深度挖掘作品中的美与情;他将人本美学观作为自己的批评目标,穷尽一生追求人性之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念吸收中西文化精髓,彰显出独树一帜的风貌。
(一)平等、宽容的批评理念
古代文人崇尚平等的理念、宽容的态度,认为这是为人、为文的境界。李健吾因其骨子里的真诚和良善,对于批评独立地位的认定和对于批评工作的热爱,让他的文字拥有平等和宽容的力量。李健吾不想成为高高在上的裁判者,只想成为一个踏实严谨的分析者。他在正视自己在批评中的位置的同时,也认识到批评的独立性。认为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自为完成的,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的尊严的存在。他一直追求批评的公平:“批评最大的挣扎是批评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深厚的个性,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4](58)
李健吾是一位带着平等和宽容态度接近作家和作品的,无论是同一派别的作家,还是左翼作家,无论是名声显著的文坛大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李健吾都认真倾听,严谨分析,用坦诚而亲切的态度指出不足,肯定长处。李健吾评价李广田的《画廊集》,十分欣赏其淳朴、亲切与平凡的人生气息,认为这是一本帮人度过生活的书,“如同在尘埃的道上随手拾起一朵野花,一片草叶,或漂泊行囊上落下的一粒细沙”[3](34)。将作品中朴素的静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李健吾评价左翼作家萧军《八月的乡村》,既重视独有的印象,又没有忘记自己的平等和宽容原则,参照萧军的人生经历和个性,考虑到作品的写作背景,他将《八月的乡村》粗犷的风格联系到萧军的浪子经历和浮躁的性格。李健吾也同其他批评家一样,注重对文坛大家的批评。他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时,感到这三部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热情”,无论巴金写的是爱情、希望、寂寞还是痛苦,他说巴金“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了他叙述的流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3](27)。这种观点与巴金本人认为的“横贯全书的悲哀”大相径庭,但李健吾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感受,维护批评的独立性。除了关注名人,李健吾也不断发掘文坛新人和被忽略的佳作。所以,许多尘封的作品因为李健吾的赏识而重新获得关注,例如李健吾评论林徽因的《九十九度》。林徽因的这篇小说不大著名,发表后也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当时的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行文散漫,不同于受欢迎的情节小说,连一些大学教授也读不懂。李健吾读后感觉很好,他宁愿相信自己的感受也不愿随波逐流用先入为主的公式去衡量和解释作品。正如李健吾所秉持的原则,他用平等、宽容的眼光看待作品,用心去感受作品,将自己全部的灵魂投入到作品之中,获得作品最直观的印象。于是李健吾从这篇被文坛冷落的作品中读出了人生的横切面,他感受到作品中的平静、亲切,甚至有一种透明感,而女性作者的感情之蕴藉如同水纹般轻轻地滑开。李健吾的“透明感”是自己独特的印象,是抛去杂念,以平等宽容心态体悟后的结果,带有个性化的想象和禅悟。
中国的批评者们自古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但也在努力进行着平等和宽容的实践。这个矛盾随时代并行,直至现代、当代甚至未来的文坛。李健吾用他的批评实践努力践行着平等、宽容、开放的品质,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批评品质的发扬,更是后世批评家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二)感性、理性交织的批评个性
李健吾的印象式批评是直观的,是整体的审美体验。他进入批评接触作品的时候,不是依靠仔细地品味咀嚼,而是依靠直觉和第一印象从整体上体验与把握作品的基本艺术氛围,然后快速地思考和描摹,将整体审美感受进行收缩简化,提取出最突出的部分,形成对作品的评论。李健吾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同社会的、理性的批评有很大的不同,社会批评用理性制约审美体验,带着武器进入作品,先入为主的为作品下判断。而印象式的批评先解除武装,除去外在的干涉和桎梏,不以批评作为武器。这种批评的方式和特色展现了李健吾批评实践中感性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重视直觉的印象式的批评方式中缺乏深度的理性思考。
李健吾的批评处处着眼于印象,但又不是完全没有逻辑,披着感性的外壳,表达理性的内在。首先李健吾对于作品的分析强调整体审美,不流于支离破碎的分析。在述说自己对于作品的感受时,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批评对象和批评方式;在传达印象的过程中,适当加入理性分析,让印象和感受条理化,注入自己理性的思考。李健吾将中西理性推演完美结合,使他的批评既独立于主流的社会历史批评,又区别于西方的印象主义批评。其次,李健吾批评的感性和理性交融体现在他一直坚守的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他本人十分憎恶学究气十足的批评,他反对批评沦为他者的附庸,他主张文学批评成为独立的艺术。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和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曲当前的现象。他的主义是一切,并非若干抽象原则,然而一切影响他的批评。他接受一切,一切渗透心灵,然而扬簸糠麸,汲取精英,提供一己与人类两相参考。”[4](3)最后,李健吾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他的小说、散文等备受推崇,鲁迅赞其文采绚烂。李健吾正因为身份的双重性,才更能够体味作家的创作历程,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艺术精神。他的批评是有温度的批评,包含着脉脉柔情和理性织网。理性的分析搭配感性的笔触,将理论的严密性融入评论文字的抒情性之中,完美地将作品深层次的美解读出来。
(三)人本美学观的批评追求
人的思想标准以原生的意义和渗透的方式进入到传统文学批评体系之中。李健吾将人作为批评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将“人性的发现”视为批评的本质,展现出咀华批评的独特性和与传统批评充分的趋同性。他多次强调“一个批评者,穿过他所鉴别的材料,追寻其中人性的昭示。因此他是人,他最大的关心是人”[6](68), 而批评的过程是 “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李健吾的批评与其说是作品的阐释,不如说是对人性的体悟和对人性的追寻。在对作品的分析时,李健吾时时拿着人性的尺子去衡量。在大部分的文学批评作品中,他关于人性的分析占了大部分篇幅,极少有理论的总结和现象的分析。在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上,李健吾也自觉地选择充满人性的作品和散发着人性气息的作家,无论是萧军、巴金亦或是沈从文,李健吾均以人性作为批评的线索和内容。这种对于人性的看重,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与其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观有着紧密的联系。
李健吾的人本观念没有为人性塑造了一个道德的牢笼,也没有沉溺于偏执的“永恒人性”中无法自拔,他的人本美学观是一种将现实的人性意义和审美超越相结合的产物。李健吾是一个具有现实精神的批评家和作家。他走出自己的象牙塔,到时代的浪潮里去刻画人物、评价人物。在批评的过程中,李健吾将批评者的性格和心理到具体的环境中进行分析。李健吾评价《雷雨》运用的就是环境分析和遗传解读,揭示了命运藏在人物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复杂的心理作用里。李健吾能够正视人生,发掘人性。当时的社会批评着眼于社会、物质等因素,而李健吾则将人物命运、性格的主体内部因素与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相互沟通,形成互补,这种批评具有浓郁的现实情怀和儒家文化精神。除了现实的情怀,还有李健吾对于人生形而上的不懈求索。李健吾在对人性美进行追求的同时,由自身感怀联想到作者,推及到读者,超越自我,推广到整个宇宙。探索个人并不是他的终极目的,人性的理想和人类的普遍情绪才是他执着追求的理想。李健吾的批评中散发着浓重的哲思,这是一种建构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生超越性的理解,融于作品之中,让批评更具深度和广度。
李健吾是中国审美批评的代言人,又是西方印象批评的传声者。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是中西文学批评结合的产物,在对两者的借鉴超越中,具有现代性色彩。李健吾的批评实践对于西方话语中国化,如何构建属于中国的批评理论体系以及如何体现批评价值具有借鉴性意义。李健吾在批评实践中秉承着宽容、平等的态度,将审美维度和社会维度,感性和理性交织在一起,将寻找普遍人性,发掘人性美作为自己求索的目标,他的批评于文学批评之外又包含着社会和时代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