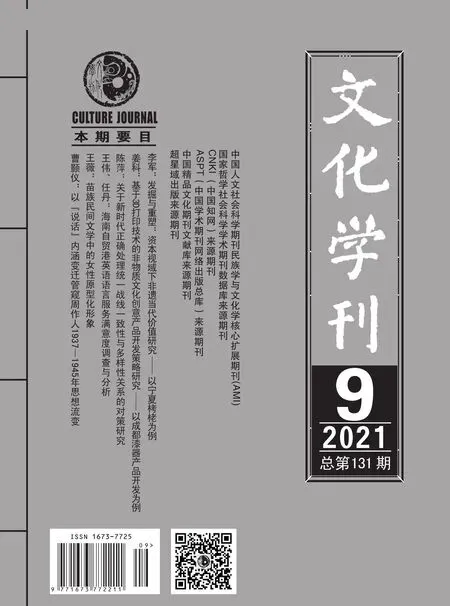苗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原型化形象
王 薇
民间文学作为文学最本质属性的基础,对人类文学的发展有着最深层次的意义,民间文学中的原型化形象也对本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荣格将原型看作“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而“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其进行加工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1]。在苗族民间文学中,女性原型化形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女性原型性格各异、形象鲜明,具有较强的文学表现性和艺术典型性,体现了苗族女性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神格话的女性形象
作为苗族神话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感生神话是“讲述一个民族或部落的首领或英雄是由其母亲感神奇的外物而孕育的神话”[2]。苗族神话传说中的苗族人类之母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就是感生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女神形象。“蝴蝶妈妈”是苗族的创世始祖,也是先民们的一项重要的信仰崇拜。她的形象深入人心,对苗族人民的影响也渗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每逢大型的苗族祭祖活动,巫师都会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上演唱苗族古歌中的《妹榜妹留》来追溯“蝴蝶妈妈”的一生。这一创世神话原型的讲述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差别,但故事的母题结构则是大致相似的。其中,“蝴蝶妈妈”所生的十二个蛋中,有一枚孵出了被苗族人视为远祖的姜央,所以身为姜央母亲的“蝴蝶妈妈”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始祖”,获得了苗族人民的敬仰和赞美[3]。
《妹榜妹留》这一创世神话和族源神话成为苗族所保留的最古老的记忆之一。对于蝴蝶为什么能够成为苗族先民的一种独特的图腾崇拜,杨正伟这样解释说:
蝴蝶是卵生动物,繁殖能力很强。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低下,苗族缺衣少粮,死于饥饿者不少。缺少育婴常识,不懂为生,易于疾病,再加上猛兽侵袭,人口常减。苗族为了生存和发展,最大的需求就是繁衍子孙。希望自己像蝴蝶那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从苗族鼓社节的“追父”“走长凳”,二月二的敬桥节等仪式中,可看出这种迫切感。
由此可见,蝴蝶这种具有超强繁殖能力的卵生动物被苗族人视为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它给予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力,承载着人类种族繁衍的重要使命,同时也被寄托了苗族自身不断迁徙的苦难历程中渴望绵延子嗣、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景;而“蝴蝶妈妈”所代表的女神形象也因其孕育、繁衍和包容的能力受到苗族人民的推崇。
《苗族古歌》中除了具有感生神话特征的“蝴蝶妈妈”以外,还出现了不少神格化的形象,且女性神和男性神数量相当,有制地婆婆、把婆、廖婆、秋婆、绍婆等。她们“巴掌大”“臂力强”,能把天“拍三拍”、把地“捏三捏”,也能“修江河”“砌斜坡”等。远古蛮荒时代,瞬息万变的自然界常以狰狞的面孔威胁着苗族先民的生存。这样的恶劣环境会让人类催生出一种超越自身力量的神力、战胜自然并延续族群生命力的想法。《开天辟地》里的把婆、廖婆、秋婆和绍婆就是一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格化女性形象,她们各司其责、各尽所能,与男人有着平等的地位,和男人一起开天辟地并为天地造型。
《苗族古歌》中的其他一些神虽未指明是男是女,但从其行为中仍可推断出是女性的神,例如《开天辟地》这部分中所吟唱的最早出生的云和雾,它们“诳”“抱”出传说中的两种巨鸟“科啼”和“乐啼”,这两种巨鸟又“诳”“抱”并生下了天上和地下,而“诳”和“抱”的动作就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此外,《运金运银》歌里也唱道:“运金给妈妈,运银给妈妈,妈妈得金银,装满柜和箱;妈妈造房屋,好比龙宫样:长椽两边披,齐象鸭翅膀,青瓦盖房顶,密象鲮鲤甲,桌椅雕花朵,摆满屋中央”[4]。歌中反复出现的“妈妈”是原始社会尊重母性的表现,“妈妈”不仅肩负着修建房屋的重任,而且还对其进行了精心地打理。
被列为苗族审美意识的美学范式之一的“阴柔之美”[5]普遍存在于苗族的传统艺术和生活实践中,通过“苗族母性崇拜意识、苗族个体对对象的神灵化认识、苗族对自然对象的敬畏感和苗族生活中的秩序性等方面体现出来”[6]。由此可见,对母性美的颂扬和对母性文化的崇拜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嵌入苗族人的思想之中。
二、被动顺服的女性形象
在苗族的民间文学中,有很多故事是围绕着女性为中心展开的。有关“洪水故事和兄妹结婚”的创世神话几乎无人不知晓,它在苗族民间流传最广,同时也是一则最古老最庄严的神话传说,叙述了洪水始末以及作为洪水遗民的两兄妹如何结婚并创造人类和繁衍后代的故事。美国苗族女作家张崼在《苗族民间故事:老挝、泰国和越南的各民族》中对这一传说给予了记载。据说在最遥远的古代,天地上下颠倒,整个世界被洪水淹没,世间的一切生灵均未能逃脱这场灾难,只有一对兄妹靠藏身于一个巨大的用于葬礼祭祀的木鼓中才得以幸免。木鼓随着高涨的水位越升越高直至顶着天空,并发出振聋发聩的响声。天上的各路神仙听到巨响并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派遣天兵天将将铜制的长矛用力地掷向人间,地面被戳出许多大坑后,洪水得以退去。兄妹俩藏身的木鼓慢慢地落到了地面,他们从鼓中爬出后却发现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因洪水而淹死。哥哥在绝望中提出和妹妹成亲并繁衍后人的想法,然而兄妹成婚有违伦理,妹妹屡次拒绝了哥哥的请求。妹妹提议兄妹二人各执一枚石子,并同时从高坡的两侧将石子扔下,如果两枚石子在翌日清晨同时出现在坡顶的话,妹妹便会答应哥哥的请求。哥哥于是略施小计,悄悄地跑到山下找到那两枚石子并把它们放置在山顶的同一处地方。第二天早晨,兄妹俩来到山顶,妹妹看见两枚放在一起的石子后,虽心有不甘,但仍信守承诺嫁给了哥哥。兄妹俩婚后不久生下的孩子却不似寻常的婴孩,而像一个圆形的巨卵。夫妻俩用刀将肉球剖割成碎片并向四面八方抛洒。几天之后,但凡抛洒过碎片的地方就有了人烟,而苗族的王、陶、李和马等姓氏也由此而得来。此外,也有一些碎片长成了诸如鸡、猪、牛、马等家畜或是各种门类的昆虫、啮齿动物和飞禽。此后,世间又恢复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南希·唐纳利(Nancy Donnelly)深刻指出:“这则故事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性别问题,即男性的形象往往是精明务实的,而女性虽然固执保守但却唯命是从。哥哥远见卓识,妹妹却目光如豆,这就决定了哥哥可以凌驾在妹妹之上,妹妹却要处于他的统治之下。”可见,苗族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女性被动顺服之基础上的,而“族源传说里的性别象征论(也正)为男女性别认同提供了原始的隐喻,因此被广泛视作是可以信赖的”。这种性别观念也通过类似的神话传说代代传递下去并逐渐成为规范苗族女性行为的标准,对于建构女性形象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苗族民间故事传递出不同的性别观念,塑造了不同的女性人物。比如故事《一对鸟夫妇的誓言》(A Bird Couple’s Vow)中就刻画了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6]。相传很久以前生活着一对鸟夫妇,他们深爱对方并承诺会不离不弃。鸟夫妇筑巢于人类的屋檐下,直至一日雄鸟出言不逊惹怒了人类,夫妇俩才被赶到了田野间。不久以后,雌鸟孵出了一窝幼鸟。可是人类却准备放火烧毁田野,大火逼近鸟巢之时,雌鸟打定主意要和丈夫以及孩子们一起葬身火海、同归于尽。雄鸟劝说雌鸟让自己待在幼鸟的上面因而得以飞走逃脱。雌鸟最终和孩子们一起被烧死在烈焰当中,带着对丈夫背弃诺言的绝望离开了尘世。若干年后,雌鸟化身为国王最年幼的女儿,但她依然能够清晰地忆起自己的前世,忆起雄鸟丈夫的所作所为。这一切都叫她悲愤不已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雄鸟丈夫飞离自己的妻儿后不久也死了,并化身为一个男人。国王一日诏令天下所有男子如能让最年幼的公主开口说话[7],便将公主许配给他。由雄鸟化身而来的男子听见后便带着一位先知的教诲前往国王的宫殿。当他见到公主后,便向她讲起鸟夫妇的故事。但在讲到故事的结尾时,男子却有意颠倒事情的真相,将抛家弃子、违背誓言的做法说成是雌鸟所为。公主闻后大怒,与男子激烈地争论开来,国王看见后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将公主嫁给了年轻的男子。在这个传说中,雌鸟化身而成的公主并不像“洪水故事和兄妹结婚”中的那位妹妹——总是被动地接受和服从[8]。雌鸟忠诚于爱情与婚姻,深爱丈夫与孩子,在大火逼近的危急关头愿意将生命奉献给家庭,由此展现出一种高度的浪漫主义情怀。她在临死前将丈夫弃守承诺的不忠行为铭记于心,并在转世为人类后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绝望与愤怒。然而,对于男子口中被歪曲了真相的故事,她并没有默然接受,而是不甘示弱、据理力争,为自己挣得了应有的尊严与人格,表现了自己对爱情和荣誉的自我要求和价值认同。
有关“人虎婚”的故事一直以来都在苗族民间广为流传,“老虎抢亲”的故事是一则有关苗族女子爱情婚姻的幻想故事,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苗族的婚俗习惯。李廷贵在《苗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将苗族的婚姻概括为:“一夫一妻制,男女自主,婚配自由”[9]。他指出苗族的结婚形式有两种,一是“通过父母,请媒说亲”,二是青年男女通过游方恋爱约定终身后,由男方邀约几位兄长或男性友人在夜晚将女方带回家中同居,之后再补行婚礼仪式。而这则民间故事中的苗族女孩被老虎以抢婚的形式结成了婚姻,正是长期以来苗族社会中所盛行的抢婚和偷婚习俗的体现。故事最终以女孩与老虎的分离结束,从而为“人虎婚”的传说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故事中的苗族姑娘在被老虎抢走后得到了他的悉心呵护和照料,面对外表狰狞可怕实则内心柔软善良的老虎,女孩逐渐对其产生了依赖与好感并最终爱上了他。虽然女孩最后嫁给了相貌英俊的人类男子,但仍然勇敢地忠实于自己的爱情并执着于自己对婚姻的选择。这个故事最终也向人们传递出苗族女性对追求婚姻爱情自由、信守承诺可贵品质的价值判断。
四、聪慧敏捷、能言善辩的女性形象
苗族民间文学中拥有众多美丽贤惠、智勇双全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流传于贵州福泉一带智斗官吏的“石女”;流传于广西大苗山地区勇于挑战皇权的“花边姐姐”[10];流传于贵州东南部巧妙脱身于虎口的“放鸭姑娘”,以及聪慧机智的“巧妇”等等,她们机灵敏捷、能言善辩,在与邪恶势力斗争中多能取胜。发生在苗族女孩叶子与老虎之间的故事就是这样一则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很久以前,一位名叫叶子的女孩与她的姐姐、姐夫以及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姐姐一家住在森林的深处,叶子帮助他们照看孩子。一日,叶子的姐夫出门遇到埋伏,被尾随身后的老虎吃掉了。随后,老虎穿上他的衣服,扛着他的猎枪,径直走回他的家中。乔装成姐夫模样的老虎虽未被姐姐察觉,可却被叶子识破。然而,无论叶子怎样劝说姐姐,姐姐依然相信回到家中的“伪装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午夜,躲藏在家中阁楼里的叶子听见楼下传来一阵阵类似于啃食骨头的可怕声响,原来是老虎将她的姐姐和几个外甥全部吃进肚中[11]。第二天清晨,老虎劝说叶子下楼与他结婚。机智的叶子趁老虎爬到楼梯口时将前日准备好的辣椒、炉灰和盐全部朝老虎的眼睛撒去,老虎疼痛难忍从楼梯上跌落下来并跑到河边去清洗。叶子按照此法与老虎周旋数次之后,趁机让屋顶上的鸟儿给她的家人通风报信,将发生在姐姐一家的劫难传话给她的父母和兄长。叶子的男性亲属带上猎枪和长矛等武器前来拯救她。叶子将老虎从河边唤回并哄骗他说自己的家人前来和他商量两人成亲的事宜。老虎听后大喜,在与叶子家人谈判的过程中,被他们设计陷入圈套,最后被叶子的家人杀死。
另一则名叫《伐木者、他的公鸡和妻子》(The Woodcutter,his Rooster and his Wife)的传说塑造了一位道义上两难选择的妻子[12]。传说有一个以伐木为生的苗族男子,日子过得相当窘迫。他非常疼爱家中饲养的一只公鸡,而他的妻子则每日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一日,正当她清扫家里时,一个国王来到她家。因为太穷,年轻的妻子不知道用什么来款待尊贵的客人,只能杀掉丈夫心爱的公鸡以飨国王。伐木工回家得知公鸡被妻子杀掉后,出于愤怒将她狠狠地打了一顿。国王听见她的抽泣声后,从厨房里出来询问事情的原委。出人意料的是,妻子非但没有坦白事情,反倒撒谎说是因为她的丈夫嫌弃她做的饭菜太过寒酸,对于国王如此重要的客人,应该杀一只猪而不仅仅是只鸡。国王听完她的解释后非常满意,也很感动,最后赐予了一大笔财富给这对贫寒的夫妇。
可见,这两则民间故事中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原型聪慧敏捷、能言善辩,她们面对困难能够挺身而出,凭借自身的聪颖机灵进行巧妙地抗争并取得胜利,最终带领家人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不仅如此,她们还巩固了自己的家庭地位,成为家庭利益的捍卫者和话语权的掌控者,而故事中的男性与机智过人、光彩夺目的女性相比却一反常态地被弱化,显现出“男弱女强”的新模式[13]。
苗族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所传承下来的史诗、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成为该民族特有的“文化沉淀”,是“后世对于世界本源问题的追寻、族源问题的考辩、性别文化的规则以及各种知识的考古发掘的基础话语体系”,当中蕴藏的精神特质凝结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深深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苗族人。苗族民间文学中涉及历史事件的文本在建构该民族及其文化对自己根源或源头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苗族民间文学中也汇集了诸多关于女性的叙述,女性身体形象、性格行为和角色气质等方面的社会群体的审美想象都蕴藏在这些由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权威性的口传典范之中,这些女性形象的审美教育功能,已使她们成为苗族审美标准和教化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代表了苗族文化中理想女性的文化群像,也具有一种“人格”样板的功能,对后代建构女性身体形象的认同有着明显的示范作用、重要的审美和伦理道德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