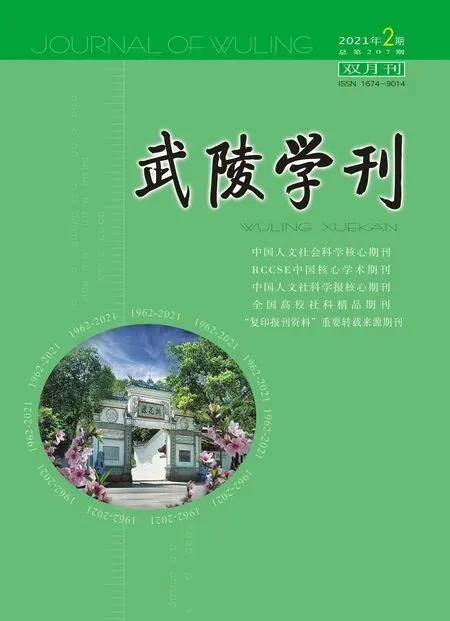WTO 上诉机构“司法造法”之美国主张的批判与标准重构
范笑迎
(天津财经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222)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一直以来被人们赞誉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王冠上的明珠,其所奉行的规则导向的基本路径为WTO 多边体制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并非所有的WTO 成员方都对该机制创设的法理及其实际运行感到完全满意[1]。例如,美国批评争端解决机构(尤其是其中的上诉机构)通过解释WTO 协定规则进行“司法造法”,这不仅是美国从2005 年至今长期关注的上诉机构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批评中最核心的问题①。美国依据WTO“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频繁行使否决权,持续阻挠上诉机构新法官的甄选,导致上诉机构目前陷入停摆状态。进而,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甚至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死亡。美国指责上诉机构“司法造法”的理由主要有四点,第一,超越职权审查专家组的事实调查,包括审查成员方的国内法的含义②;第二,对解决争端无必要的问题作出附带说明③;第三,对上诉机构报告赋予判例法效力④;第四,上诉机构的解释超出了WTO 协定文本含义和成员方的立法意图。本文聚焦于第四点理由,围绕上诉机构适用的解释方法的合法性问题,试论述美国主张的WTO 规制解释方法并非区分上诉机构进行正常的法律解释和实施“司法造法”的合理标准,而WTO 法的目的才是评估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是否构成“司法造法”的有效依据。
一、美国对WTO 协定解释方法的主张及对上诉机构“司法造法”的批判
虽然WTO 上诉机构“司法造法”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学界和实务界关注,但是“司法造法”与正常的法律解释之间的界限这一关键性问题始终未有定论。正如美国指责上诉机构“司法造法”,其他WTO 成员方为了使上诉机构的法官甄选程序得以恢复而不致使该机构陷入瘫痪,都尽力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以解决美国的关切,许多学者也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上诉机构“司法造法”的方案。但问题是,人们在急于解决问题之余却未质疑美国的有关论断本身是否站得住脚。美国指责上诉机构“司法造法”的理由之一是其没有适用严格的文本解释和成员方意图解释,对此我们需要首先探寻该主张的法理依据,进而分析该依据作为判断上诉机构进行“司法造法”的标准的合理性,从根本上维护上诉机构法律解释的规则导向路径以及WTO 多边体制的有效性。
(一)美国对WTO 协定解释方法的主张:文本解释与成员方意图解释
美国认为WTO 上诉机构适用的解释方法不当是造成其“司法造法”的原因之一。对此,美国的主张是,WTO 协定文本是由全体成员方经协商一致达成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应当以严格遵守WTO 协定文本的方式解释WTO 规则。但是美国发现上诉机构在实践中越来越无视WTO 成员国制定的规则⑤,因此建议上诉机构采用严格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以避免其填补或澄清谈判方在WTO 协定中故意留下的空白和文本表述的模糊⑥。美国指责上诉机构通过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中规定的宽泛的解释方法,对美国施加了WTO 协定以外的新的义务。美国认为,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必须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第3.2 条的要求,不能增加或减少WTO 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虽然一般国际法在WTO 争端解决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无限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如何适用一般国际法解释WTO 协定条款,以及适用何种解释方法应当遵循WTO 协定的本质要求——成员驱动,换言之,WTO 协定是全体成员方协商一致的产物,只有全体成员具备最终解释WTO 协定的专属资格⑦。基于此,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释WTO 规则时,应当确切领会当事方在协定文本中所要表达的意图,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不能创设未经美国谈判官同意的新的义务。上诉机构法官应当尊重美国参与谈判的协定条约之下的“历史意图”。上诉机构只有适用严格的文本主义方法,充分尊重美国在WTO 协定谈判时所表达的意图,才能避免对WTO 协定实施的填补空白和澄清模糊的“司法造法”行为,而其他解释方法的适用则可能构成对WTO 协定规则的发展[2]。
由此可见,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条约之所以是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同意当其签署条约时即受条约的约束[3]。一个主权国家服从国际法仅在它同意被约束的范围之内。那么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对这些国家所真正同意的内容作出何种解释最为合理?其答案往往是法律文本通常的文义[4]。因为法律文本的含义以文本本身或立法者意图为基础和支撑,与自我或主体相互分离和独立,但又可以被自我和主体以某种方式理解。因此,为了正确地理解一个文本,自我就要使用一种机械的技术或方法,在自己的意识中重构记录在文本中的立法者的意图,以此反映文本的客观内容[5]51。
因此,基于美国的主张,文本主义和立法者意图能够为法律文本的含义提供客观的、确定的和一致性的解释。法官应当仅仅通过发现条约文本的原始含义的方式解决争端[6]。也就是说,当文本主义的解释方法不能澄清WTO 协定的含义,或者该方法不能就WTO 协定含义作正确理解给予成员方以明确的指引时,应当通过查明成员方就WTO 协定进行谈判时的历史意图来判定WTO 协定的含义。进而,美国主要反对的就是上诉机构超出WTO 协定文本之外,借助《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规定的文本解释和成员方意图解释以外的其他解释方法,援引WTO 协定以外的其他国际法中的价值、原则与规则解释WTO 协定规则,进而通过判例法的方式发展出新的WTO 规则。
(二)基于美国主张的上诉机构“司法造法”的表现
实际上,学界也有一些观点与美国的主张类似,通过强调WTO 协定文本的限制要求和WTO成员驱动的根本属性,反对上诉机构依据DSU 第3.2 条的规定,适用解释国际法的习惯法规则——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中规定的解释方法,进而广泛地援引外部国际法解释WTO 规则。当然,学界观点和美国主张虽然表面上具有相似性,但在出发点和目的上却大相径庭。学界希望通过规范上诉机构适用的解释方法避免其受到“司法造法”的质疑,从而确保该机构的权威性和WTO 的规则导向性;而美国将上诉机构适用解释方法的范围限定于文本解释和缔约方意图,实质上是以尊重WTO 全体成员方的立法权为名限制上诉机构充分有效地行使司法职权,并最终使上诉机构保障的WTO 规则转入以美国为主的权力导向路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当暂时将美国主张中的法理要素和政治要素相剥离,在法理上反驳美国主张中的论点,才能揭示美国主张背后的真正目的。所以,本文在这一部分梳理了现有研究中与美国批评上诉机构“司法造法”主张相似的观点,说明美国主张的法理依据,为后文论述美国主张的不合理性以及提出更为合理的上诉机构规则解释的合法性标准进行铺垫。
首先,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的规定,上诉机构可以适用与当事国有关的任何国际法规则对WTO 协定进行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c)条所规定的“适用于当事方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中的“当事方”一词的概念模糊不清,是指争端的当事方还是指WTO的全体成员方存在争议,裁决机构能够援引的外部国际法的范围并不确定[7]73。上诉机构从而获得了广泛地适用非WTO 规则的司法权力。上诉机构的这一做法属于在DSU 所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以外进行的“司法造法”行为[8]。依据DSU 第3.2条的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DSU第7 条规定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仅限于WTO 协定中的有关法律规定,DSU 第11 条规定专家组的职能是评估WTO 涵盖协定的可适用性以及与涵盖协定的一致性。所以,WTO 裁决机构能够适用外部国际法规则解释WTO 协定文本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9]。
其次,上诉机构通过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获得了考量WTO 法以外的非贸易价值的司法权力。例如在美国—虾案中,上诉机构需要解释美国能否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1994 第20 条(g)项的规定对那些没有采取保护海龟的措施所捕捞的海虾(在本案中是针对来自于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虾及虾制品)实施禁令,以作为GATT 第1 条、第11 条和第13 条的例外。为此,上诉机构通过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的规定,说明其在该案中的任务就是依据WTO 的序言条款,从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中寻找对GATT1994 第20条(g)项规定的恰当的解释指导⑧。由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的规定,开启了广泛援引WTO 法以外的规定非贸易政策的国际法(例如人权公约、环境法,等等)的方便之门,在WTO 法中引入对诸如劳工标准、环境保护、人权等非贸易政策的考量。然而,何种非贸易政策能够在WTO 中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例外应当由各成员方以表示同意的方式决定,并反映在WTO 协定文本中。上诉机构的职能是在争端解决程序中对WTO 协定条款进行解释,而政策考量,无论是贸易自由化政策还是其他政策,都不在上诉机构的职责范围内。而在美国—虾案中,上诉机构从保障WTO 协定执行的机构转变为了回应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机构,使得成员方之间原本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被笼罩上了一层“司法造法”的阴影[8]。
再次,上诉机构通过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获得了价值权衡的司法权力。上诉机构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援引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比例原则,进而运用司法权衡的方法对WTO 一般例外条款进行解释。例如GATT1994 和GATS 的一般例外条款(GATT 第20 条和GATS 第14 条)涉及对“必要的”这一概念的解释问题,即所谓的“必要性检验”问题。对此,从韩国—牛肉案开始,经由欧共体—石棉案、多美尼加共和国—香烟案、美国—赌博案,到巴西—翻新轮胎案,上诉机构在运用继承于GATT时期的“更小贸易限制”的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一个复杂的关于“必要性”解释的权衡检验,将所有有关变量进行权衡[10],尤其是对非贸易价值的重要性的权衡⑨。由此,“更小贸易限制”和权衡的方法共同构成了“必要性检验”的部分,完全契合比例原则的全部内容。同时,WTO 上诉机构在解释GATT20 条序言时也适用了比例原则(例如在美国—虾案中)[11]。对比例原则的适用使得上诉机构在平衡贸易自由化和WTO 成员国国内管理目标之间的关系上获得了更大的司法权力,超出了WTO 协定文本的授权[12]。因为依据文义解释的方法并不能从WTO 协定中发现比例原则的存在,作为权衡对象的各种变量无法在WTO协定文本中找到依据[13]。比例原则中的司法权衡会损害成员方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使得法官对于条约的解释不再受条约文本的约束,法律因而变得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导致类似案件的裁决出现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现象[14]。并且,WTO 协定文本中明确列举的特定的贸易自由化的例外条款表明:贸易价值和非贸易价值之间的权衡过程发生在WTO 法的立法过程,每一项例外都代表了WTO 成员方已经认可的不能被追求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所妥协的政策目标。因此,如果一项措施属于例外条款中的某项,就意味着该措施所追求的目标的相对价值是不受审查的。上诉机构通过适用比例原则获得了驳回对自由贸易价值的牺牲不成比例的国内措施的自由裁量权[12]。
综上所述,基于美国的主张,对上诉机构“司法造法”予以批评的有关意见认为,上诉机构通过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的方式,广泛适用其他国际法对WTO 法进行解释的做法一方面在WTO 协定文本之外增加或减少了成员方在WTO 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超出了成员方就WTO 协定进行谈判时的立法意图,不符合条约赖以存在并生效的国家同意的基本原则。因此,上诉机构所进行的上述宽泛的法律解释不能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与可预测性。
二、对美国关于WTO 上诉机构“司法造法”评判标准的批判
美国的主张实质上是将法律作为一种标准化的概念。所谓标准化概念就是指我们对某一概念的理解和适用基于我们接受并遵循的相同的客观标准。例如三角形就是一种标准化的概念,我们对三角形持有共同的观念是因为我们遵循相同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三角形,即一种由直线线段连接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点所形成的平面图形[4]。据此,国际法将“国家同意”作为效力来源的基本依据,国际法的概念也就成为了一种标准化概念。人们对国际法的理解和适用都遵循“国家同意”这一客观标准,并衍生出经国家同意的法律文本的文义解释和国家立法意图解释的方法,从而适用一种客观、机械的方法,确保法律解释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但是,上述观点存在致命性缺陷。首先,如果国际法的依据是一种事实问题,那么“国家同意”理论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只有“同意”才能创设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义务,那么谁首先同意了“国家同意”这一基本规则?由此“国家同意”的逻辑必将陷入一种“死循环”[15]。其次,当国家签署条约或参加某项实践时,它们同意什么内容并不是完全清楚明确的,毕竟,条约的意思经常是模糊的[3]。因此,法律的概念并不属于上述标准化概念,法律的本质是解释性的,国际法亦不例外。法律文本并不是以独立的和未经解释的状态存在的,法律解释是本体论的,在解释之外或者解释之前并不存在客观性的意义来源,因此法律文本的意义无法通过某种机械的技术或方法推演出来[5]52。我们如果深入考察文本和成员方意图的解释方法,在WTO 的实践中就会发现,这两种方法并不能为WTO 协定提供确定性和一致性的解释,其推理常常缺乏合理性,甚至可能走向合法性的反面,不能为WTO 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
(一)文本主义解释难以避免上诉机构“司法造法”
法律文本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具有确定性的[4]。特别是国际协定文本往往被起草者故意留下一些模糊之处,因为各国无法就任何更具体的东西达成协议,而文本的模糊性使得缔约方能在不抛弃或妥协的情况下达成协议[16]。就像WTO 协定在制定时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因而其文本存在许多模糊与空白之处就不足为奇[17]。所以,解释者固守文本主义的方法对WTO 协定进行解释必然较其他方法具有更大合法性的观点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文本主义方法可能对它所致力于的合法性产生反作用力[18]。本文以欧共体—沙丁鱼案为例进行分析,说明上诉机构在解释WTO 协定条款的模糊之处时,仅仅适用文本主义的解释方法难以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明确的结论,无法为成员方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指导。
在欧共体—沙丁鱼案中,争端双方秘鲁和欧共体就沙丁鱼的标记问题产生争议。本案的起因是一项1989 年的欧共体条例规定,只有欧洲沙丁鱼(sardina pilchardus)这一物种能被标记为“沙丁鱼”在市场上销售。但是秘鲁要求其向欧共体出口的太平洋沙丁鱼(sardinops sagax)也可以标记为“沙丁鱼”。秘鲁将欧共体诉至WTO,理由是欧共体条例违反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TBT 协定)协定的有关规定⑩。秘鲁指出国际食品法典标准(Codex Alimentarius)允许太平洋沙丁鱼和其他有关鱼类被标记为沙丁鱼。上诉机构同意秘鲁的观点,认为欧共体违反了TBT 协定第2.4条的规定⑩,没有适用相关的国际标准作为其制定技术法规的基础性依据。
首先,上诉机构对TBT 协定第2.4 条中规定的“技术法规”进行了解释。TBT 协定附件1 规定一项技术法规是“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包括适用的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上诉机构将该条款解释为技术法规就是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文件:(1)适用于一种同类的产品,(2)规定产品的特性,(3)要求强制执行产品的特性。上诉机构的这一解释似乎与TBT 协定第2.4 条的文本规定并无二致,实际上很难说是一种解释,而更像是对协定文本的同义反复。上诉机构的这一文本解释没有为成员方提供在模糊的文本用语以外的任何更进一步的、具体的指引[6]。
其次,上诉机构回答了欧共体是否适用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作为其制定技术法规的基础性依据的问题。TBT 协定第2.4 条没有强制要求成员方适用国际标准,而是要求成员方将国际标准作为其制定技术法规的基础性依据,这一要求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以下简称SPS 协定)类似。对此,上诉机构查询了字典中对“基础性依据”的定义。上诉机构指出《韦氏词典》将“基础性依据”定义为“任何事物的知识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基础原理或理论”。同时,上诉机构还查找了《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该词典将“基础性依据”定义为“主要组成部分”和“其他事物是依据该事物构建的或者其他事物的构造和运行是由其决定的”。由此,上诉机构认为,从这些不同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相同的关键词,例如“主要组成部分”“基础原理”以及“决定性的原则”,这些关键词指向一个结论,即两个事物之间必须具有非常强的和极其紧密的关系,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基础性依据。所以,上诉机构认为欧共体没有将国际食品法典作为其制定技术法规的基础性依据。但是,上诉机构的这一解释并不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尤其是上诉机构没有澄清其结论所涉及的一个WTO 的基本法理问题:如何在制定国内法规的国家主权和规范这一行为的国际法律义务之间划定一条合理界限[18]?这说明,文本解释时常无法为成员方制定贸易政策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相反地,文本解释却可能借助语义宽泛的术语隐藏解释者得出解释结论的真正原理和方法,掩盖其“司法造法”的真相[6]。
再次,上诉机构解释了即便是未经一致同意通过的国际标准也构成TBT 协定第2.4 条规定的国际标准。欧共体主张只有经国际机构一致同意采纳的标准才能构成TBT 第2.4 条规定的有关国际标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对其不产生约束力,因为该标准没有经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就得以正式通过。对此,上诉机构认为TBT 协定附件1.2 条的解释性说明的最后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其最后两句规定:“……国际标准化团体制定的标准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本协定还涵盖不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文件。”对此,欧共体认为附件1.2 条的最后一句是指非国际标准化团体的其他机构制定的文件。而秘鲁和专家组认为,最后一句是指国际标准化团体机构制定的不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的文件。最终,上诉机构认为,由于ISO/IEC 指南中对“标准”的定义明确包括协商一致的要求,因此,合理的结论是TBT 协定附件1.2 条规定的“标准”的定义中对协商一致要求的遗漏是TBT 协定的起草者有意为之的。因此,上诉机构认为TBT协议附件1.2 中“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化团体机构制定的非经协商一致通过的标准。上诉机构的解释存在形式逻辑上的问题,因为其解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具有说服力:人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附件1.2 条最后一句的主语是指其决定必须作为成员方决策依据的国际标准化团体。除此之外,上诉机构的结论在实质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上诉机构的解释赋予了国际标准化机构(其成员与WTO 的成员方基本相同)不具有合意的决定以约束力,而国际标准化机构本身却未赋予自己作出的决定以约束力,这就导致该机构的一项国际决定在WTO 中对其成员方有效力,而在WTO 以外对其成员方不具有效力。对此,上诉机构没有对其结论给出具有可信性的解释,甚至没有意识到该结论背后所涉及到的更深层次的法理问题,即成员国决定对国内风险的规避程度和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利益平衡的自主权限的问题[18]。因此,上述文本主义解释路径无助于证明上诉机构解释的合法性。
(二)成员方意图解释不能为上诉机构解释提供明确的合法性依据
通过考察WTO 成员方的立法意图来解释WTO 法的观点认为,成员方对WTO 协定的实际预期应当得到保护,从而解释者应当寻找每一个WTO 成员方对于WTO 协定文本的理解以及哪一种理解体现了成员方的真正意图的证据。这种解释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和执行WTO 成员方的预期。为此,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 条的规定探究WTO 协定的谈判历史,以此考察协定文本的含义是否清楚明确,并进而通过梳理谈判历史确定成员方的意图来澄清协定文本的含义[19]。
然而,德沃金教授认为,当国家签署条约或参加某项实践时,它们在同意什么内容上并不是完全清楚明确的。毕竟,条约的意思经常是模糊的,必须历经一段时间的阐释才能加以确定[3]。例如《联合国宪章》第2(4)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上述条款中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一术语?如果由一组国家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例如北约对科索沃和利比亚的干预),其目的在于停止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行,而没有任何对科索沃或利比亚的疆界或宪法上的改变,那么这种干预是否违反了被干预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德沃金认为所有在1945 年参与创设联合国的国家以及之后加入该组织的国家似乎不太可能就包括这一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拥有一致的答案。如果“国家同意”是国际法的最终依据,那么我们将很快走入对上述问题解释的死胡同中去[4]。同样地,就WTO 法而言,其立法者恐怕也无法说清楚他们所同意的WTO 法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也不清楚当成员方之间的意图不同时,应该如何进行整合?更何况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意志”,发展了的政治、经济、文化、习惯等条件会赋予法律文字以新的含义,这时它已经脱离了立法者最初所同意的内容的束缚,而揉进了许多新的内涵[20]。
比如在美国—虾案中,申诉方和被诉方的争论点之一就是如何解释GATT 第20 条(g)项中的“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这一概念。申诉方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认为“可用竭”一词的合理解释应当是指“诸如矿产那样的有限资源而非生物资源或可再生资源”。在他们看来,有限资源为可用竭的资源是因为这些资源的总量有限,随着人类的消费会逐渐耗竭。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如果“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被视为是可用竭的,那么“可用竭”一词所发挥的限定作用将成为摆设。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别提及了第20 条(g)项的起草历史。GATT 第20 条的规定最初是在国际贸易组织(以下简称ITO)宪章草案中的商业政策中起草的,在整个ITO 宪章的起草的准备会议中,代表们在讨论GATT 第20 条(g)项的例外规定时始终关注于“原材料”“产品”和“矿产”,特别是一些国家(如印度、巴西等)代表团专门就矿产资源(如锰)的保护问题进行了讨论。然而,作为被诉方的美国认为,海龟是可用竭的,因为海龟是一种濒危物种,如果该物种灭绝了,那么就会像石油和矿产一样永远消失。另外,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忽略了GATT 第20 条(g)项的其他有关物种规定的起草历史,而这一历史表明该条款的意图包括对生物资源的适用。尤其是,在ITO 宪章的谈判过程中,澳大利亚的代表曾质疑GATT 第25 条(禁止数量限制)是否禁止澳大利亚限制美利奴羊的出口。该代表解释说由于严重干旱,澳大利亚已经丧失了2 000 万头美利奴羊,所以需要禁止这种羊的出口。比利时代表对此回应称无论第25 条的范围是什么,澳大利亚的禁令都可以依据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的例外条款得到支持。因此,美国认为,GATT第20 条的起草历史实际上反驳了本案申诉方认为(g)项排除生物资源的观点。由此可见,有关WTO 成员方的立法意图的证据充满了矛盾和冲突,难以对协定文本的含义作出一致性的证明。
总之,立法者意图的解释方法主要体现为解释者用条约准备工作的有关资料来解释条约文本[21]。而上诉机构实际上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 条规定的诉诸条约准备工作的解释方法罕少适用。因为条约的准备工作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被赋予的法律地位是较低的,它只是条约解释的一种辅助性方法。同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WTO 协定的谈判历史缺乏明确可信的记录,诸多模棱两可的记载源于成员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相互矛盾的表述和利益上的妥协[22]。因此,立法者意图不能为WTO 法的解释提供确定、一致的合法性标准。
在WTO 之前的几十年,GATT 专家小组在有意借助于条约准备工作对GATT 协定作出解释时,基本上没有任何特别的顾虑[23]。这是因为GATT 专家小组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GATT 时期权力导向的制度模式。GATT 时期专家小组程序的合法性来源于其对规则解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又取决于专家小组的裁决与国际贸易俱乐部(由GATT 谈判者、参与GATT 实践的外交官以及贸易专家)对GATT 规则的理解和意图保持一致[24]。但是,权力博弈的反复无常会导致以立法者意图为依据的法律解释对国际贸易体制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破坏。同时,WTO 拥有164 个成员方,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市民社会(以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为代表)在WTO 中的参与度也在逐渐提升。因此,WTO 的决策机制已不可能退回到诸如GATT 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俱乐部模式,尽管WTO 协定规则在最初制定时受到美国国内贸易法的影响颇深,但其解释应当符合此时当下的全体成员方的普遍共识,而不应当体现为规则协商表面一致下掩饰的大国意志。对此,我们不应当忘记DSU 第3.2 条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协定的现有规定”的目的就是要减少GATT 时期专家小组对条约准备工作的过度依赖,以此维护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导向的基本路径,保障全球贸易共同体(不仅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全球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在WTO 体制中所享有的可预期的权利[21]。
综上所述,美国主张上诉机构应当适用文本解释和成员方意图解释来准确无误地反映成员方通过WTO 协定文本所表达的意志,上诉机构对这两种解释方法的适用能够避免“司法造法”。但是上文中通过分析这两种解释方法在实际案例中的适用表明:是否适用这两种解释方法不构成上诉机构进行规则解释和“司法造法”的分界线,上诉机构适用这两种解释方法也可能推导出不止一种结论,或者得出与文本术语同样模糊的解释结论,实际上可能赋予上诉机构以更大的司法裁量权。这两种解释方法与上诉机构最终作出的裁决结果之间不存在一条直接的、单一的因果关系,上诉机构表面上由上述两种方法推导出的结论可能掩盖其背后的真正意图,使WTO 成员方无法真正看清上诉机构通过一个又一个裁决建立的国家管制自主权与多边贸易机制监管权之间的界限,从而也就无法真正评估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而无法找到约束上诉机构解释行为的有效方法。
三、WTO 法的目的解释对上诉机构“司法造法”的重新界定
WTO 如今已经发展为较为成熟的多边贸易体系,除了其成员方,全世界的个体经济行为者,对WTO 体制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都享有重大的利益[25]。然而基于国家同意标准的文本主义和缔约方意图方法难以为WTO 法的解释提供充分的可靠性与可预测性。而WTO 法律实践的参与者通过诉诸WTO 法的宗旨与目的即可获得关于WTO 法解释的确定、一致与合理的答案。WTO 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其全体成员方的共同规则,上诉机构只有把握其根本目的,才能超越WTO 协定文本本身的模糊性以及成员方利益的复杂性,发现WTO 协定真正代表的全球贸易共同体的普遍共识。无论上诉机构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规定的哪一种解释方法,最终都要符合WTO 法的根本目的,其得出的结论需要从WTO 法的目的中获得合法性依据,并保障上诉机构的解释有助于维护WTO 多边体制的安全性与可预测性。因此,本文认为,WTO 法的目的解释法可以作为检验其他解释方法的结论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而检验上诉机构是否进行“司法造法”的一种可行路径。
(一)目的解释为上诉机构提供更确定与合理的合法性解释标准
1.WTO 法的目的解释能够提供更具确定性的标准。“国家同意”不能为WTO 法律规则提供根本性的依据,因为法律的概念并不是一种事实性的标准化概念,而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尽管某些国际法命题的真实性问题可以通过“国家同意”(或者说是国家间的合意)的事实进行判断,但是人们关于法律命题的分歧和争论可能依然存在,因为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价值和目的的争论,而不仅是一项规范存在与否的问题。
因此,当上诉机构法官试图澄清渗透在WTO 协定文本中的模糊、漏洞和空白时,需要悟出其所要解释的WTO 协定规则所服务的目的以及潜藏在该项规则背后的原则或原理。从而,WTO 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应当受到WTO 协定的目的和宗旨的限制[21]。因为对文本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从某个术语的诸多语义中确定其恰当的法律含义,即确定文本术语的众多语义学含义中哪一种构成了该具体案件中的合理的法律含义[26]。例如在美国—赌博案中,上诉机构认为,为了确认某一术语的通常含义,专家组会从查找字典中的定义开始解释。但是字典本身并不一定能解决复杂的解释问题,因为字典通常要将单词的所有含义都列出来,包括通常的含义和罕见的含义,普遍的含义和特殊的含义。所以,条约文本的解释在根本上是依据条约的目的来作出的。例如有观点认为在欧共体—沙丁鱼案中,上诉机构表面上通过查字典等方法得出结论,即国际机构制定的未经一致同意通过的国际协定也构成TBT 协定中规定的国际标准,背后体现了TBT 协定(与SPS 协定)的目的对其文本条款投射下的解释的影子[18]。
国际常设法院在1919 年关于妇女工作的案件中的判决意见表明,文本解释方法具有局限性,目的解释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优先地位。解释者脱离法律的目的便难以探索法律文本的真正含义[7]66-67。对此,杰克逊教授认为,解释者经常会引入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诉诸法律体系的目的和宗旨来发现法律规则的含义。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能够为原本是缔约国相互妥协的产物的模糊和矛盾的条约条款注入新的生命[27]。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共同的目的和价值,我们对于WTO 法律含义是什么的争论才能具有统一的标准,争端解决机构和成员方之间关于WTO 法的争论才有意义,才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28]。人们通常担心目的解释会导致条约解释的过多的灵活性,但其实这种担忧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条约解释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出与条约文本的含义相冲突的解释[21]。这种辩证关系被美国—日落复审案中的专家组做了清晰的阐释,即《维也纳公约》第31条要求条约文本应当依据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加以解读,但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能推翻条约文本而独立存在。
2.WTO 法的目的解释能够提供更具合理性的标准。德沃金认为,如果将“国家同意”作为国际法的基本依据,那么国际法就好比穿上了束缚其手脚的紧身衣,不能服务于它在当今世界必须服务的目标——规诫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造成的威胁。在德沃金看来,国际法的目标或者说其正当性基础应当是:在一个经济相互深刻依赖的世界中,人民的生活更多地受到其他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尤其是人民会受到囚徒困境风险的威胁。对此,国际法要确保对每一个国家的权力施加切实可行的和共同的限制,使每一个国家具有从整体上努力改进国际体系的义务。国际法要确保所有国家的政府通过彼此间的协调来克服囚徒困境(例如海洋中的过度捕捞,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污染等不能仅凭各国政府在其领土范围内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并对人民的权利提供保护[4]。同样地,WTO 法作为国际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其正当性基础亦是如此。WTO 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减轻或避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主权国家制定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全球整个贸易体系的危害。
虽然WTO 协定在序言中规定了诸多目标,但其核心在于“维护并促进国际贸易多边合作”[29]。如果我们认为避免战争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权,那么WTO 多边贸易体制就可以主张其自身价值的重要性[25]。维护WTO 多边体制本身能缓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失败和危险[4],这一“缓和”的概念提供了国际法最为普遍的结构性原则和解释背景[3]。
虽然目前WTO 多边体制因某些国家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而遭遇危机,但在危机面前,人们反而能从WTO 体制的对立面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该体制真正的目的与价值——建立一个促进全体成员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完整的、更加有活力的和持久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反对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上诉机构适用目的解释,实际上是以WTO 法的正当性基础作为其规则解释的合法性依据,在实质层面更加忠诚于全体成员方关于WTO 多边贸易体制这一事业的根本宗旨,反对贸易保护与单边主义,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性和可预测性。由此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上诉机构在欧共体—沙丁鱼案中,通过对TBT 第2.4 条和TBT 附件1 第2 条的文本解释得出欧共体没有以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为依据制定技术法规,因而不符合TBT 协定要求的结论,因为上诉机构受到了WTO 法的根本目的——保障国际贸易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的指引,发现TBT 协定的目的是要求成员国应当尽可能使国内的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以协调各国的政策,促进国际合作。惟有如此,上诉机构才能在具有歧义的协定文本中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并在成员方之间达成共识。
(二)目的解释为上诉机构援引外部国际法提供合法性依据与保障
1.目的解释为WTO 法勾勒了一条具有开放性的合法性边界。WTO 的目的,例如“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加有活力的和持久性的多边贸易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劳工、人权等关联议题。如果WTO 进行自我封闭,与外部国际法中的其他非贸易价值相隔离,那么它的存在将是不可持续的,并受到来自于体系外部的对其正当性诘责的威胁[25]。对此,WTO 上诉机构呼吁避免对WTO 涵盖协定的解释与国际法进行“临床隔离”。在全球化条件下,WTO 法律体系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其生命力的维系离不开与其他国际法(甚至国内法)的交流、借鉴与协调,特别是不同的社会价值(例如劳工标准与人权保障、环境保护与文化多样性等)需要借助WTO 作为一种交互界面进行协调与融合,这就要求WTO 法的合法性边界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开放性[21]。
所以,在美国—虾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第20条(g)项的“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的解释必须根据环境保护国际共同体的当代关切而作出。上诉机构通过援引诸多国际公约和宣言,使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解释方法对GATT 第20 条(g)项的内涵进行了符合当代国际共识的解释。上诉机构指出:“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通常提及的天然资源同时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资源。”对此,上诉机构援引的国际公约和宣言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物多样性公约》《21 世纪议程》《与〈保护迁徙物种野生动物公约〉协同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决议》《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上诉机构根据CITES 强调海龟属于一种可用竭的自然资源,因为其属于CITES 的附录1 所列明的濒临灭绝的物种。正如杰克逊所言,在GATT/WTO 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国际制度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和前进的,那些固守于条约起草者的原始意图的观念,以及试图贬低和否认制度发展变化的有效性的倾向都将无助于国际制度整体目的的实现[30]。
2.目的解释通过WTO 共同体的“传统”为WTO法的合法性提供安全性保障。虽然WTO 法的合法性边界应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国际法中的非贸易价值和规范通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引入WTO 法后,就获得了优先于WTO 法律规范的地位。特别是在协调贸易价值与人权和环境价值的关系时,人权和环境价值往往被作为“普世价值”进行宣扬,将这些价值引入WTO 法中,容易使WTO 法律规范从属于人权或环境法律规范,令成员方将人权和环境保护作为贸易保护主义正当化的理由,掩盖其以保护国内人权或环境价值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允许上诉机构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不加限制的适用,那么就等于是打开了破坏WTO 多边体制的潘多拉魔盒[25]。
有观点认为,WTO 协定序言规定了诸如促进“普遍的福利”“可持续发展”“优化利用世界资源”的政策目标,说明多边贸易自由化是实现这些更高位阶的社会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所以,为增强WTO 制度的正当性,可以在WTO 裁决中援引WTO 协定序言所规定的这些价值和原则,而这些价值和原则所具体指向的是WTO 以外的国际公法所规定的广泛的环境权和人权[31]。同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规定WTO 裁决机构在解释WTO 法时可以援引“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该条作为司法裁决者手中的“万能之钥”,允许其“进入国际法的所有房间”[32]。甚至,对于WTO 司法裁决者而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的规定使得适用WTO 以外的国际法成为一种必须,以允许成员国在贸易关联议题上具有相当的政策空间,更是为了给予WTO 协定序言中的广泛的政策目标以实际意义[31]。上述观点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其适用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非贸易价值高于贸易价值,从而可能在WTO 法律体系中引入侵蚀该体系完整性和基本共识的癌症细胞。该观点所提出的援引外部国际法对WTO 法进行解释的方法像一个蛇皮口袋,延展度极佳,可以不断地扩大,以至于可以装下诸多经过非贸易价值伪装的贸易保护和单边行动,最终破坏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整体性与安全性。所以,尽管WTO 法律体系需要保持一种开放性,在其需要时与外部的法律环境进行沟通,回应国际社会多元的价值要求,但与此同时,它也必须要保持自身的自治性与完整性。
实际上,上诉机构处在WTO 法律共同体的“传统”之中,该“传统”即WTO 法的目的以及在该目的之下的利益与偏好,这些利益与偏好限制和指导了上诉机构对WTO 协定文本的理解。“一个人在社区或其传统中的生活必然限制着这个人的视野——也就是他可能在一个文本中看到或理解的东西。”[5]52因此,上诉机构在解释WTO 法时,必然站在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上而非站在外部国际法的立场上对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关系进行协调,它对规则的解释是基于贸易与人权/环境而非基于人权/ 环境与贸易的模式进行的。然而,上诉机构所处的WTO 法律共同体的“传统”并不意味着其被偏见之墙所围,只从狭窄的入口放进那些拥有“我不会说什么新东西”的通行证的事物。相反,如上所述,WTO 法的合法性边界应当具有开放性,允许其他外部国际法规则与价值的进入,以满足WTO 法的发展需要并强化其正当性基础。但是,WTO 法律共同体如何知道哪些外部国际法规则符合WTO 法的需要呢?对此,上诉机构通过其解释进行筛选,这种筛选的过程已经被WTO 法的“传统”——WTO 法的目的所决定。
例如在欧共体—生物技术产品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预防原则与SPS 协定的风险评估和预防原则含义不同,贸易视角的环境保护与环境视角的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价值认知的断层。根据《议定书》第10.6 条的规定,如果进口成员方寻求一种与国际标准相比更高水平的保护,那么进口成员方可以利用预防原则作为更高的标准而采取一种缺乏确定科学证据证明的贸易限制措施,具有完全的贸易限制性[7]146。而SPS 协定强调科学证据的确定性、客观性和透明度。SPS 协定允许成员国采取必要的SPS 措施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然而,协定同样要求采取的措施要建立在切实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上,必须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并且不会对国际贸易构成变相的壁垒。SPS 协定鼓励成员国将SPS 措施与国际标准(与SPS 协定的要求相互一致)进行协调。对此,协定特别列出了三个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国际动物流行病学局(OIE)以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并且,SPS 协定第5.7 条规定的预防原则是在一定期限内临时适用的,成员国有义务在合理的期限内寻找证明存在潜在风险的科学证据并以此审查已经采取的措施。因此,SPS 协定第5.7 条规定的预防原则与《议定书》中的预防原则的含义和要求不同,二者在就转基因产品的风险防范上存在理念上的冲突,难以兼容[33]。在WTO 法中适用《议定书》中的预防原则会构成对贸易的变相限制,损害WTO 成员方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因此,外部的环境法或人权法不应当成为WTO 法本身,外部国际法规范只能在WTO 法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在其内部的法律规则和制度选择的自我修正中加以体现[34]。所以,WTO 法的目的解释在打开WTO 合法性边界的同时,为其正当性的理解施加了“传统”的限制,从而为WTO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安全性的保障。
结 语
上诉机构在解释WTO 协定规则时始终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司法困境:一方面要澄清WTO 涵盖协定的现有规定,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其解释不能增加或减少WTO 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上诉机构解释WTO 协定的行为犹如在刀尖上舞蹈。美国的主张以“国家同意”为合法性标准,看似为上诉机构的解释提供了安全的保障,而实际上由于WTO 协定条款存在许多模糊之处,成员方的立法意图也缺乏确定一致的历史记录,使得“国家同意”的标准难以提供在WTO 协定文本之外的任何更为具体明确的指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美国的主张不仅难以为WTO 上诉机构解释提供明确合理的合法性标准,而且可能成为美国达成其自身实用主义目的的工具。例如,美国一方面指责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超出了WTO 协定文本和美国参与谈判时的立法意图的授权,但同时又在美国—虾案和墨西哥—电信案中要求上诉机构适用演进的解释方法,即使这种解释方法似乎增加或减少了WTO 协定的权利和义务[2]。因此,我们应当为文本主义和成员方意图的解释方法施加WTO 法律目的的限定,以维护WTO 多边体制为基本立场,防止上诉机构的解释走向WTO 合法性的反面。
WTO 法的目的解释为上诉机构援引外部国际法对WTO 协定进行解释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并且,目的解释通过WTO 共同体的“传统”为WTO 法提供“过滤式保护”,防止引入的外部国际法成为反噬WTO 法律体系的“癌症细胞”。毕竟,要应对WTO 当下面临的危机,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对规则机械僵化的适用和成员方意图的考古发掘上,从而使WTO 争端解决机制沦为某些大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自留地,倒不如寄望于WTO 规则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应有之义和全球普遍共识下的自我发展。
注 释:
①Se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Negotiations on Improvements and Clarification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N/DS/W/82/Add.1,25 October 2005.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March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reports-and-publications/2018/2018-trade-policy-agenda-and-2017, visited on 21 May 2020.
②Statements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27 Aug 2018, https://geva.usmission.gov/wp -content/upload/sites/290/Aug27.DSB.Stmt.as -delivered.fifin.public.pdf, visited on 21 May 2020.
③Statements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29 Oct 2018, https://geneva.usmission.gov/wp-content/uploads/sites/290/Oct29.DSB.Stmt_.as delivered.fifin_.rev_.public.pdf,visited on 21 May 2020.
④Statements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8 Dec 2018, https://geva.usmission.gov/wp -content/upload/sites/290/Dec18.DSB.Stmt.as -deliv.fifin.public.pdf, visited on 21 May 2020.
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March 2018, at 24,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reports-and-publications/2018/2018-trade-policy-agenda-and-2017, visited on 21 May 2020.
⑥Dispute Settlement Body, Negotiations on Improvements and Clarification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N/DS/W/82/Add.1, 25 October 2005.
⑦Se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Special session - Minutes of meeting,TN/DS/M/29, 24 October 2005.
⑧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WT/DS58/AB/R, adopted Oct. 12, 1998,para. 158.
⑨上诉机构对非贸易价值的司法权衡在韩国—牛肉案首次引入,用于解释GATT 第20 条(d)项的“必要性”概念。这一解释方法之后又在欧共体—温石棉案中被再次适用于解释GATT 第20 条(b)项的“必要性”概念并确立下来。
⑩TBT 协定第2.4 条规定:如需制定技术法规,而有关国际标准已经存在或即将拟就,则各成员应使用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作为其技术法规的基础,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标无效或不适当,例如由于基本气候因素或地理因素或基本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