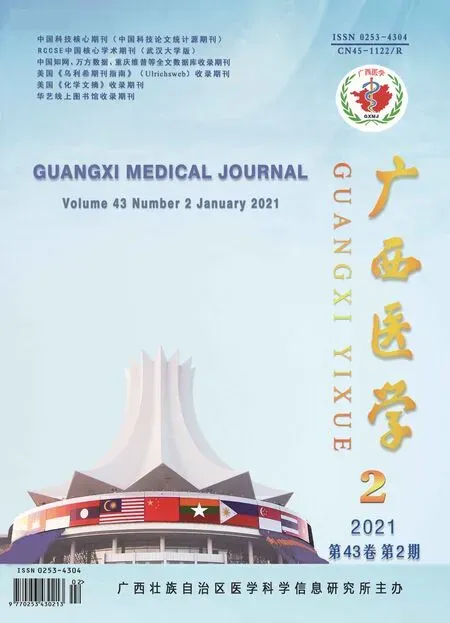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对医疗机构经济行为的影响▲
范乐勇 彭 玲 骆国盛 张树芳 钟 媛 林美言 唐宗英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保管理科,广西桂林市 541001,电子邮箱:fanleyong@126.com)
【提要】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是通过按病组打包付费制度设计,将医保基金的“穿底”风险从医保部门转移至医疗机构。为规避医保超支拒付风险,医疗机构主要从控制成本、增加收益和优化收治结构三方面对其经济行为进行调整。本文主要对DRG付费体系下医疗机构经济行为变化及其影响机制进行综述。
我国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related group,DRG)的付费改革已迈入快车道,继2019年6月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公布了30个DRG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后[1],2020年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2]要求进一步推广DRG付费。然而,国内外研究表明,尽管DRG付费有助于节约医疗资源[3]和降低医疗费用[4],但在实施过程中,医疗机构存在挑选患者、分解住院、削减必要的医疗服务、高编码、重复入院率上升、院内死亡率上升、医疗服务向门诊转移等非预期经济行为或现象[5-7],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疗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医保基金。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DRG付费改革的同时,加强对医疗机构经济行为的研究和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1 DRG付费
1.1 DRG付费的核心要素 DRG付费是指根据患者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及转归和资源消耗等因素,在将其分入若干诊断组的基础上,对各疾病诊断相关组制订付费标准,预付医疗费用的付费方式[8]。DRG付费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预先设定付费标准,即根据医疗费用(成本)历史数据和医保基金支出预算分别确定各DRG组的权重和基础费率,然后用各DRG组的权重乘以基础费率而得到每个DRG组的付费标准,以此作为补偿医疗机构资源消耗的主要依据[9];二是预先设定极值标准,即根据历史数据设定住院天数或医疗费用的极值标准,作为对极高、极低住院天数或医疗费用等特殊病例的判定依据,并对其资源消耗的补偿进行调整[10]。这两个核心要素基本上决定了医疗机构收治每例住院病例所能获得的收益,或者超支(实际发生医疗费用高于DRG付费标准),或者结余(实际发生医疗费用低于DRG付费标准)。实际上,DRG付费是通过按病组打包付费制度设计将医保基金“穿底”风险从医保部门转移至医疗机构,旨在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资源消耗,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1.2 DRG付费的应用与发展 DRG付费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截至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将DRG付费应用于医保支付。近10年来,我国北京、玉溪、柳州、金华、三明、深圳等地已相继实施DRG付费,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30个国家试点城市也将于2021年启动DRG付费。实施DRG付费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医疗成本和提高医疗质量,围绕这两个主要目标,各国根据自身条件和实践情况逐步对DRG付费制度进行了优化[8,11-15]:(1)对DRG分组方案进行调整,例如增加疾病严重程度作为分组依据,不定期更新合并症和并发症清单。(2)对权重、费率、调节因子进行动态调整,例如,根据分组方案和历史数据,对各DRG组的相对权重进行调整;根据医保基金支出预算对基础费率进行调整;综合考虑政策目标及患者、医疗服务和医疗机构特征(所属地域、教学任务、等级)等因素对调节因子进行调整。(3)对离群值标准和特殊病例补充结算办法进行调整,即将未入组、医疗费用极高(低)、住院天数极高(低)、新技术、特定疾病、高价药等特殊病例作为例外情况进行补充结算。(4)对DRG组医保支付范围进行调整,例如将一次DRG组医保支付有效期限定为15/30 d,即出院后15/30 d重新入院的不再支付或减半支付;将住院前后3 d发生的门诊费用纳入DRG组医保支付范围。
2 DRG付费体系下医疗机构经济行为变化
在DRG付费体系下,医疗机构的财务持续性面临很大挑战。为有效规避医保超支拒付风险和寻求合理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的经济行为发生很大变化,根据这些变化的作用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9,16-17]:一是降低每例病例的医疗成本,主要经济行为有降低平均住院日、削减不必要的医疗服务、选用低成本医疗服务等;二是增加每例病例的收益,主要经济行为有准确编码、高编码、通过增加其他手术操作或治疗手段改变病例入组等;三是调整收治结构和增加收治量,主要经济行为有推诿重病、分解住院、降低收住院指征、缩短院前等待时间等。其中,降低平均住院日、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服务、选择具有可替代性的低成本医疗服务、缩短院前等待时间有助于提升运行效率,重视临床路径应用、加强医疗机构之间分工协作、降低病死率、提高编码质量等有助于提升医疗质量;而推诿重病、分解住院、让患者提前出院、将医疗服务转移至门诊、增加非必要医疗服务、高编码等非预期行为则将导致医疗质量、效率的下降和医保基金的浪费。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实施DRG付费后,30 d内重复入院率5年内上升了8.70%[18],医疗机构住院患者收治数量增加1%~9.5%[4],高编码增加的医保基金支出占同期总医保基金支出的比例达到1%[19]等。可见,为规避DRG付费带来的医保超支拒付风险,医疗机构出现了非预期经济行为,浪费了大量的医保基金。
3 DRG付费对医疗机构经济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对于DRG付费如何影响医疗机构经济行为,Di Giacomo等[20]将DRG付费标准作为外生变量,分别采用二项分布、Heckman回归模型对公立医院经济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对于价格变化即便是公立医院也会在经济行为上做出调整。Mougeot等[10]认为,对特殊病例实行补充结算有助于医疗机构减轻由医疗费用极高病例所带来的财务风险,但同时也会削弱医疗机构控制医疗成本的动力,特殊病例补充结算政策对医疗机构经济行为所能够产生的效应受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Shin等[21]认为,医疗机构面对DRG付费标准变化时会在患者利益(假设主要由医疗服务质量和数量决定)和医疗机构自身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而医疗机构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动力受质量改进后医疗服务需求量变化的影响;其进一步通过双重差分析法发现,提高DRG付费标准并未刺激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相反医疗机构更倾向于通过高编码、调整诊疗行为获得更高的医保支付。Cots等[9]通过构建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1)当收治病例获得的医疗收入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无关时,医疗机构有很强的动力将医疗费用在预先设定的DRG付费标准以内,其主要经济行为有降低平均住院日和削减不必要的医疗服务。(2)当多个目标DRG组之间的付费标准差额较大时,医疗机构有可能采取增加其他诊疗服务或调整编码的方式让病例进入付费标准更高的DRG组,从而增加医疗收入。(3)当预计收治病例存在较大超支风险时,医疗机构可能出现推诿、让患者提前出院、分解住院等行为。
可见,从DRG付费制度设计看,预先设定各DRG组付费标准(即打包付费价格)有助于引导医疗机构控制医疗成本,预先设定极值标准及其补充结算办法有助于帮助医疗机构减轻由极高医疗费用病例所带来的超支风险,加大监管力度有助于减少非预期经济行为。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在DRG付费体系下,医疗机构经济行为是平衡医保患三方利益的结果,而通过调整医疗服务数量、结构、质量和成本寻求合理的经济利益以保障财务持续性是现阶段我国多数医疗机构的经济目标,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保基金使用效率。见图1。

图1 DRG付费对医疗机构经济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的影响机制
4 展 望
《2019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支出20 854亿元[22]。据此可推测,我国未来数年内DRG付费规模将至少达千亿级别,医疗机构非预期经济行为造成的医保基金浪费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国家层面应尽快启动DRG付费对医疗机构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为各地DRG付费改革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二是各试点地区应重视对医疗机构经济行为的监测、干预和评估,并逐步对DRG付费制度设计及配套措施进行优化;三是医疗机构应加强绩效、临床路径、成本控制、病案、医保、信息等内部的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加强医疗成本管控,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