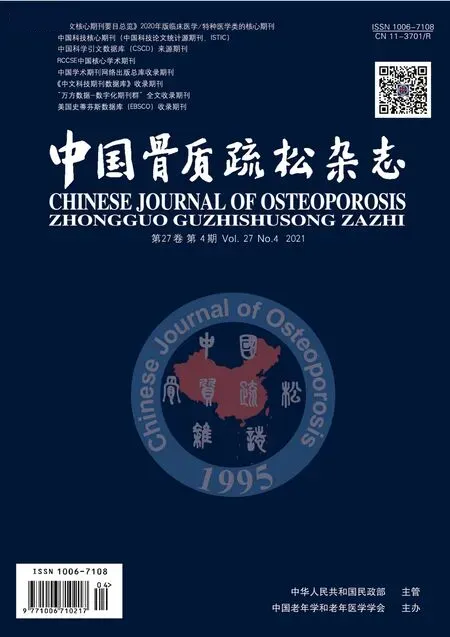肠道菌群、IGF-1与骨代谢联系机制的研究进展
袁志发 张通 蔡金池 方鹏忠 王文己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骨科,甘肃 兰州 730000
骨量是衡量骨健康的重要指标,其维持依赖于骨代谢动态平衡,即成骨细胞的骨形成和破骨细胞的骨吸收共同介导的过程[1]。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骨代谢失平衡的结果,表现为成骨不足和破骨有余所致的骨结构损害,主要特征为骨量减少和骨折风险增加。OP的发病与增龄紧密相关,2016年的调查发现,36 %的中国老年人(>60岁)为OP确诊患者[2],人口老龄化使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工作更加紧迫。目前,临床推荐的治疗药物包括双膦酸盐、激素类(雷洛昔芬)、降钙素和甲状旁腺素[3],但化学药物容易引起胃肠不适、肌肉疼痛和低钙血症等不良反应。
近年来,肠道菌群影响骨代谢的途经和内在机制逐渐被发现。在老年人的肠道菌群中,致病菌增多而抗炎菌减少[4],炎症状态下,活化T细胞介导破骨细胞分化,会增加OP的发病风险;研究还发现,肠道菌群与矿物质吸收、骨生长和骨质疏松密切相关[5-6],IGF-1信号转导是肠道菌群调节这种骨代谢的重要途径。本文就肠道菌群,IGF-1与骨代谢的关系及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论述,为OP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1 肠道菌群与骨代谢的关系
肠道菌群是定植于人体胃肠道并形成微生态系统的复杂微生物群落[7]。成人肠道内微生物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其携带的基因组超过宿主的百倍[8]。肠道菌群与宿主的共生始于出生后,并在宿主免疫应答,营养代谢和内分泌中起重要作用,同时受到饮食方式、抗生素使用等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通过多种途径调节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相对活性,影响骨代谢与生长,包括产生自身代谢产物、改变宿主营养代谢水平,以及调节黏膜和免疫应答系统[9]。细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脂多糖可通过慢性炎症反应诱导骨量减少[10];胞壁酰二肽可通过下调RANKL/OPG比值来间接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减少骨吸收,增加骨量[11],表明肠道微生物的自生分子模式参与了宿主的骨量转化和骨重建。在无菌小鼠与肠菌移植实验中,Schwarzer等[12]发现,与同龄健康小鼠相比,无菌幼鼠的体重增长较慢,骨量也较低,而补充植物乳杆菌的无菌小鼠能够维持正常的生长速率,这表明肠道菌群促进了小鼠骨骼的形成和生长发育。Li等[13]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用鼠李糖乳杆菌GG或益生菌补充剂进行治疗,使类固醇缺乏小鼠的小梁骨密度增加,骨量不再丢失。肠道菌群还介导多种骨代谢相关的信号传导途径,包括OPG/RANKL/RANK、Wnt/β-catenin和IGF-1/IGF-1R等。例如,表达增加的骨Wnt10b可预防1型糖尿病引起的骨量丢失[14]。此外,肠道菌群可产生SCFAs、5-羟色胺、多聚胺、ATP等代谢产物,通过调节宿主激素内分泌(IGF-1等)和免疫反应影响骨代谢。
2 肠道菌群诱导骨代谢中的IGF-1信号转导
2.1 IGF-1/IGF-1R信号轴与骨代谢的关系
IGF-1是一种促生长的内分泌激素,在细胞增殖、分化和细胞周期中起关键作用。IGF-1R是与IGF-1结合的受体,广泛表达于脂肪、肝脏和骨骼等器官中[15]。在循环中,大部分IGF-1与IGF结合蛋白3(IGFBP3)、酸不稳定亚基结合形成复合物,仅少量结合于其他IGFBP或游离。研究发现,IGF-1参与了骨形成和骨改建,并通过内分泌、旁分泌/自分泌的机制发挥调控作用[16-17]。IGF-1水平降低在OP发病中起关键作用。骨骼内的IGF-1存在于多种细胞类型中,其与IGF-1R结合会引起IGF-1R信号活性标志物的Akt磷酸化,启动级联传导而调节骨代谢。缺失IGF-1R的成骨细胞增殖能力受抑制,而凋亡活性增加,导致骨小梁减少和矿化不足[18],提示IGF-1可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分化和耦合基质矿化的能力;软骨细胞的IGF-1R基因敲除后,小鼠的生长板骨化延迟,仅少量骨骼矿化[19],说明IGF-1在生长板成熟和次级骨化中心形成中起重要作用;骨膜上的IGF-1R表达不足时,会导致骨形成减少[20],这可能是由于IGF-1诱导的成骨细胞分化不足所致。此外,IGF-1可促进甲状旁腺素分泌来增加钙沉积,刺激骨骼形成[16]。上述IGF-1对多种骨组织代谢的调节作用表明,一定水平的循环IGF-1对于骨骼的线性生长和骨转换是必需的。
2.2 果蝇肠道微生物通过IGF-1诱导IIS激活
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信号转导(Insulin/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IS)在整个动物界高度保守[21],各物种间都有同源基因。人类IGF-1的同源物是果蝇的胰岛素样多肽(Drosophila insulin-like peptides,dILPs),其诱导编码的胰岛素样受体,可实现与哺乳动物IGF-1R相似的细胞内级联传导[22]。果蝇肠道菌群由鞍状醋杆菌、热带醋杆菌等简单细菌组成[23]。Shin等[24]发现无菌幼蝇到蛹的发育时间比野生型长,定植鞍状杆菌后可恢复发育速度。他们建立并筛选出与氧化呼吸链基因突变相关的鞍状杆菌突变株P3G5,发现P3G5单联成虫的翅膀和肠道比野生型小,这与IIS信号缺陷果蝇的表型类似。通过异位过表达dILP2来增强IIS活性,挽救了P3G5单联果蝇的代谢和发育缺陷,这表明氧化呼吸链活性是dILP充分表达所必需的,且野生型鞍醋酸菌诱导dILP表达来促进幼蝇的发育。Storelli等[25]用植物乳杆菌定植果蝇,发现幼虫在营养缺乏条件下恢复了生长发育,系统INR信号(dILP活性的读数)增加,说明植物乳杆菌诱导了dILP产生,且一种共生微生物足以概括肠菌在营养不良条件下的有益生长效应。对果蝇的两项互补性研究初步证明了肠道菌群在诱导IGF-1信号转导,促进生长发育中的重要作用。
2.3 IGF-1水平影响小鼠生长和骨骼发育
在哺乳动物小鼠的移植对照实验中,相比常规小鼠,无菌小鼠的体重较轻,尺寸较短,骨生长参数(骨长度、皮质骨厚度、皮质骨比例和股骨骨小梁比例)较低[12],表明肠道菌群对于保持小鼠生长发育是必需的。Yan等[26]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可动态调节循环中IGF-1水平,促进成年小鼠的骨骼生长和改建。与成年无菌小鼠相比,长期定植肠菌的小鼠血清 IGF-1水平和血清骨形成标志物I型胶原N端前肽(N-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P1NP)显著升高。与此一致,宿主的小梁质量、纵向骨长度和骨形成率也增加。相反,广谱抗生素治疗的移植小鼠,血清IGF-1和P1NP下降了,也就是说,肠道菌群促进了IGF-1产生和骨骼生长。Lei等[27]使补充植物乳杆菌的无菌小鼠恢复到野生型小鼠的IGF-1和IGFBP-3水平,重演了肠道菌群通过IGF-1/IGF-1R轴对宿主的有益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却与此不一致,相较于野生型小鼠,无菌小鼠血清和骨骼IGF-1增加,且表现出更高的骨形成率和骨小梁体积[28]。这种微生物群对IGF-1和骨骼重塑的差异影响可能源于小鼠种系背景的差异或不同设施之间肠菌群落组成的差异[29]。而用抗生素耗尽肠道菌群会同时降低小鼠血清P1NP和骨吸收标志物I型胶原C端端肽(C-terminal telopeptides of type I collagen,CTX-I),并导致骨量增加[26],这表明肠道微生物群既参与骨吸收又参与骨形成,为上述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
2.4 多个器官被肠道菌群诱导产生IGF-1
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诱导宿主不同组织产生IGF-1。肝脏是合成IGF-1的主要器官,相比于无菌幼鼠,野生型幼鼠的肝脏中检测出更高水平的IGF-1[12];同样,鸡肝脏中的IGF-1在饲喂植物乳杆菌后表达增加[30]。Yan等[26]测量发现,移植小鼠的腹部脂肪垫中IGF-1水平增加,提示白色脂肪组织(white adipose tissue,WAT)可产生IGF-1。果蝇脂肪体相当于哺乳动物的肝脏和WAT,因为在营养不良时,果蝇脂肪体细胞是dILPs表达并促进INR信号转导所必需的[25]。Schieber等[31]发现常规小鼠肌肉中IGF-1的表达高于无菌小鼠,提示肌肉也是IGF-1的来源器官。然而,Yan等[26]测量定植小鼠的肌肉,发现其IGF-1水平降低了,这说明循环IGF-1池的增加可能并不来源于肌肉。他们还发现,定植小鼠骨骼中的IGF-1及其下游靶基因Runx2的转录水平也显著增加,可见骨骼局部IGF-1参与了骨代谢调节。Runx2转录因子可刺激碱性磷酸酶合成,增加成骨细胞的分化和增殖。
3 SCFAs直接或间接调节骨代谢
3.1 SCFAs与GPR结合直接影响骨细胞
SCFAs是不可消化膳食纤维经肠菌降解后产生的主要代谢产物,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给无菌小鼠补充发酵成SCFAs的益生菌可以防止骨量丢失,促进骨骼健康[32],提示肠道菌群可能是通过其代谢产物间接调节宿主生长和骨重建。SCFAs可以通过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GPRs),抑制组蛋白脱乙酰化酶和诱导自噬来调节宿主[33]。GPRs包括GPR41(丙酸和丁酸受体)、GPR43(乙酸和丙酸受体)以及GPR109(丁酸和烟碱受体)[34]。研究证实,SCFA依赖GPR43来诱导外周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35],受刺激的骨髓细胞分化形成的破骨细胞前体细胞表达了GPR41和GPR109,这为SCFAs激活GPRs来影响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相对活性提供了部分依据。虽然丁酸能够直接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却并不依赖丁酸受体GPR109[36],这说明SCFAs对宿主破骨细胞的抑制作用不一定需要SCFA受体来介导。SCFAs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成骨细胞,但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出的骨髓和血清中SCFAs浓度极低,SCFAs似乎主要通过间接机制调节骨代谢。
3.2 SCFAs通过IGF-1间接促进生长和骨重建
在果蝇中,突变体P3G5单联幼虫的产乙酸能力受损,表现为发育和代谢平衡失调,而补充乙酸逆转了P3G5的生长缺陷[24],表明SCFAs在增加dILP信号转导来促进生长方面发挥了作用。相比于无菌小鼠,野生型或定植肠菌的无菌小鼠,其盲肠中SCFAs浓度更高[37]。Yan等[26]用抗生素治疗常规小鼠减少盲肠中SCFAs和血清IGF-1水平,再补充SCFAs,恢复了小鼠循环IGF-1的正常水平。添加SCFAs 4周后既增加了脂肪IGF-1产生和肝脏IGF-1产生趋势,又降低了骨小梁和骨量,与短期定植肠菌的无菌小鼠相似。这可能是由于IGF-1也促进破骨细胞分化而增加骨吸收所致[34]。鉴于盲肠中的SCFAs与血清IGF-1水平呈正相关,可推测SCFAs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宿主肝脏和脂肪组织,增加循环IGF-1水平,并促进生长和骨骼发育。然而,SCFA并不能完全概括由肠道菌群定植引起的骨表型,因为血清P1NP未见明显变化,也不能排除其他肠道微生物与宿主相互作用引起IGF-1增加。SCFAs在没有肠道菌群条件下是否足以诱导宿主IGF-1产生以及如何促进宿主IGF-1产生尚未明确。SCFAs是直接还是间接作用于肝脏、脂肪组织来促进IGF-1产生还有待探究。
3.3 SCFAs调节GH/IGF-1生长轴活性
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GH)是腺垂体分泌的能够促进系统生长、软骨成骨的蛋白类激素。GH发挥生物学效应始于与细胞表面的跨膜GH受体(GHR)的结合[38],GHR存在于脂肪、肌肉、肝脏和骨骼等器官中。GH可与成骨细胞或破骨细胞表面的GHR结合,直接影响骨形成与骨吸收动态平衡;GH也可诱导多种组织协同分泌IGF-1,间接发挥促生长作用[39]。循环中的IGF-1主要由GH刺激肝脏分泌,其含量受到GH水平的调节,IGF-1水平升高又负反馈调节GH的合成,共同形成GH/IGF-1生长轴[40]。GHR的活性与酪氨酸激酶JAK2密切相关,JAK2磷酸化的靶点是STAT5b。GH/IGF-1系统需要通过JAK和STAT信号转导途径起作用。当GH与GHR结合并激活细胞内JAK2后,JAK2对STAT5b进行磷酸化,磷酸化的STAT蛋白与特异性DNA序列结合,导致IGF-1基因转录,从而调节生长和骨代谢。当GH/IGF-1生长轴调节紊乱时,成骨与破骨动态平衡被打破,是骨质疏松发生的重要原因。
对幼鼠和幼鱼的研究发现,在慢性营养不良状态下,肠道菌群能够增加GH/IGF-1生长轴活性,从而促进宿主幼体的生长发育[12,41]。Schwarzer等[12]发现,相比营养缺乏下的野生型和定植幼鼠,无菌幼鼠循环中GH水平先较高(28日龄时)后较低(56日龄时),而IGF-1和IGFBP3均较低。同时,肝脏及肌肉中检测出的GHR、IGF-1和IGFBP3也较低,这些结果表明无菌动物的GH/IGF-1生长轴活性在营养贫乏时降低了。有趣的是,无菌小鼠在28日龄时升高的GH效价却不足以逆转循环中较低的IGF-1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机体在营养剥夺下出现了适应性反应,即组织处于生长激素抵抗状态,导致促生长轴活性下降,从而减少生长耗能[42]。他们给低营养的无菌和野生型小鼠注射重组生长激素(recombinant growth hormone,RGH),并检测GHR信号活性的标志物STAT5b,发现野生型小鼠显示出更高的STAT5b磷酸化水平。由此可见,肠道微生物群对GH敏感性有提高作用,且发育迟缓导致的生长激素抵抗,在分子水平上表现为高GH和低IGF-1。Du等[43]最近的研究证实了上述概念。他们给没有出生缺陷的生长迟缓的犊牛补充益生菌(芽孢杆菌等),既增加了犊牛的摄入量和体重,又相应地提高了血清GH/IGF-1的水平。然而,Yan等[26]检测发现定植小鼠的GH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这可能是由于生长激素的释放具有昼夜节律,而检测时采用单点取样所致。
组蛋白脱乙酰化酶SIRT1的功能是抑制STAT5磷酸化,SCFAs通过抑制其功能而正向调节GH/IGF-1生长轴。Yamamoto等[44]将SIRT1基因敲除的小鼠禁食48 h,发现其血清和肝脏IGF-1水平表达升高,表明SIRT1介导了营养不良时的生长激素抵抗。可见,肠道菌群主要由SCFAs间接调节GH/IGF-1生长轴活性,发挥促生长作用。

图1 肠道菌群诱导IGF-1调节骨代谢示意图Fig.1 Diagram of bone metabolism regulated by IGF-1 induced gut microbiota
4 总结与展望
肠道菌群调节骨代谢的研究正成为改善骨健康的新领域。我们对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SCFAs与骨代谢的作用机制、对肠道菌群影响IGF-1水平来调控骨重建与生长发育所进行的概括,为肠道菌群用于防治骨质疏松,缓解儿童生长缺陷作了理论铺垫。但肠道细菌调节IGF-1水平和GH敏感性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此外,人类在饮食、年龄范围和肠菌组成方面具有高度异质性,可能导致相同干预下的不同反应。未来,借助代谢组学和基因组学工具,可以从分子水平上剖析肠道菌群调节宿主骨代谢的信号途径,为改善骨骼健康提供新的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