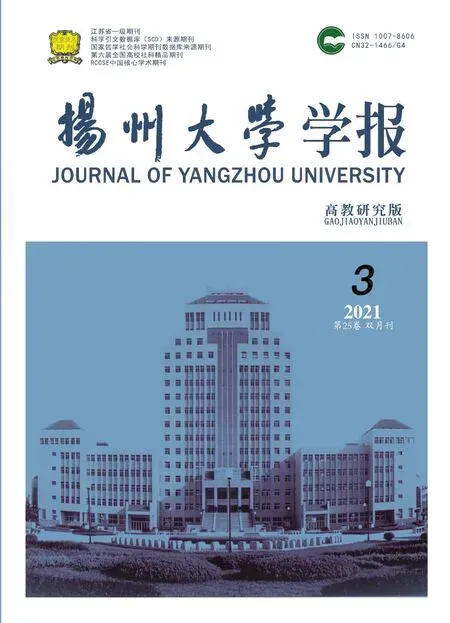边界理论视角下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探究
林静雅,胡亚天
(1.徐州医科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4;2.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一、引言
青年教师是地方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高校实现转型发展的宝贵人力资源。据2020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我国45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占总体比例已达67.5%,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地方高校那里,这一比例通常还会更高。地方高校的改革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高水平、成规模的青年教师队伍作为持续的人力支撑,因此如何促进青年教师发展、壮大优秀青年教师队伍便成了转型时期地方高校关注的焦点。
当前,不少地方高校促进青年教师发展主要关注快速成效,强调成果产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青年教师成长步伐,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因压力或过劳导致工作与家庭失衡,甚至职业中断、英年早逝的现象在地方高校青年教师队伍中屡屡出现,如2018年10月11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年仅35岁的青年教师赵艳云在华中科技大学听课时心脏骤停离世,其幼子尚在哺乳期;2020年3月1日,海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导林肇宏因病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2岁……这些事件不禁引发这样的思考:高校教师发展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如何促进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美国教育联合会认为,高校教师发展应当是高校教师作为一个人、作为专业人员和作为学术界成员的发展,应是高校教师的全面发展,包括身心健康、职业生涯规划、职称晋升、家庭生活品质等方面内容。[1]也就是说,高校教师发展应是教师平衡、协调和全面发展,应尊重他们除考核评价指标以外其他方面的发展需求,使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有效衔接,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地方高校教师工作与家庭的发展处在同一时空中,有关任务和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交错和影响,尤其是工作与家庭都处在上升阶段的青年教师,因此,有效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全面发展理应属于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任务范围。边界理论是组织管理领域有关员工工作与家庭发展关系较为成熟,且可操作性较强、应用较广泛的理论。以下将基于边界理论视角,考察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在工作与家庭领域的发展情况,发现阻碍其发展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边界理论与青年教师发展
1. 边界理论概述。2000年美国学者克拉克(Clark)提出边界理论,该理论构建了有关个体工作与家庭平衡发展的理论框架,常用于解释个体工作与家庭产生矛盾、冲突的原因,给出缓解冲突、促进平衡发展的策略,以促进个体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提高组织生产和管理的效率。在边界理论看来,工作与家庭是员工发展的两个领域,二者因目的和文化的不同而分别形成各自的范围和边界,个体犹如边界跨越者(border-crossers),每天反复跨越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去完成各项发展任务或活动。边界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世俗的和心理的。边界强度取决于边界的渗透性和灵活性。渗透性表示其中一领域事务可进入到另一领域的程度,如下班后将未完成的工作带回家处理就是工作边界向家庭边界渗透的表现;灵活性表示边界可扩张或可收缩的程度,如可自由选择工作的时间或地点即是工作边界灵活性较强的表现。边界管理策略可分为分割(segmentation)和融合(integration)两种,前者力图划清工作与家庭的界限,两个领域的元素很少相互渗透,适用于工作与家庭特征差异明显的情况;后者力图增强边界的渗透性和灵活性,两领域间存在相互交融现象,适用于工作与家庭特征相似的情况。与个体共同完成某一领域内的活动或任务的同事、管理者、家属等被称为边界维护者(border-keeper),他们是领域文化和价值的守护者,会对边界管理产生影响。[2]
当边界管理不良,参与工作(家庭)活动会使参与家庭(工作)活动变得困难时,就会产生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体验。严重的冲突会导致抑郁、工作满意度下降、组织承诺降低、职业倦怠提高、身体健康受损等一系列不良效应和后果。[3]边界理论认为提升员工职业发展质量和职业忠诚度,需要组织关注和促进员工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发展。这不仅需要了解哪些因素或事件导致了员工边界管理不良,还需要组织采取必要措施帮助员工完善边界管理策略,提高处理和协商工作与家庭范围和边界的能力,从而降低边界跨越难度,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保证工作与家庭的功能完善,甚至实现工作与家庭的相互促进、增益。
2. 边界理论视角下的青年教师发展。在边界理论视角下,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可分为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发展,二者的协调和平衡对于持续提升青年教师个人职业发展水平、优化青年教师队伍整体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操作层面上,首先需要了解工作-家庭冲突在地方高校青年教师队伍中的分布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和事件,以及边界管理缺陷。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因素众多,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三大类。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性别是研究最多也是最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4]在已然壮大的地方高校青年教师队伍中,女教师比例逐年攀升,她们的工作-家庭冲突与青年男教师相比孰轻孰重,已有研究结果并不一致。[5-6]在工作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中,国内研究常将周工作时间、承担家庭责任比例、子女年龄等作为分析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变量。近些年来,源于工作与家庭的社会背景改变,这些前因变量在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中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工作领域,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地方高校将办学目标定位为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甚至向研究型大学转变。这种转型发展的压力转嫁到青年教师身上是更加严格的教学科研量化考察,以及更加陡峭的职业晋升阶梯,这使得不少青年教师自觉延长周工作时间。在家庭领域,2015年国家开放二孩生育政策后,许多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也选择生育二孩,而子女数量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还很少被考虑到。随着社会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除养育子女、照料家务需要,青年教师多不与父母同住。前期访谈发现,青年教师家中的老人通常是帮助者,而非被照顾者,因此在家庭特征变量中主要考虑子女因素。
在建构工作-家庭平衡促进计划以前,还需要分析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所选择的工作与家庭边界管理策略及其适切性。由边界理论可知,边界一定程度上是有形的,结合时间边界易测量、易表征的特点,以下将以工作时间和承担家庭责任比例为边界管理分析工具。就边界管理策略适切性来说,虽然学术职业与家庭生活的目的和文化差异较大,适用分割策略管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但需结合工作-家庭冲突情况来考虑。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1. 方法与程序。采取方便抽样,选取江苏省5所地方高校,通过网络和线下实地发放问卷的方式实施调查,时间为2019年4-6月。这5所地方高校均为一本招生,立足区域,注重培养适应地方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聚焦建设国内具有重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水平大学,在综合实力较强、以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地方高校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共发放问卷402份,回收377份。剔除专职辅导员和行政岗位教师问卷39份,涂改或选项固定问卷14份,未婚教师问卷41份,子女数量为3及以上问卷1份,年龄在46岁及以上问卷38份(文中提到的“青年教师”主要指地方高校45岁及以下的专任教师),获得有效问卷244份(有效回收率60.7%)。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见表1。从调查吸引的大部分参与者为女性,可看出工作与家庭协调发展问题困扰着地方高校青年女教师。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N=244)
2. 变量的测量。主要包括:
(1)工作-家庭冲突。采用Carlson等[4]编制,张伶修订的中文版工作-家庭冲突量表(Work-Family Conflict Scale)[7]18。该量表分别测量了工作干涉家庭(work interference with family,以下简称WIF)体验和家庭干涉工作(family interference with work,以下简称FIW)体验。量表共有12道题,6道测量WIF,如“由于工作中花费过多时间,我不得不错过一些家庭活动”;6道测量FIW,如“想到家里的事,我很难集中精力工作”。采用5点Likert量表(1=非常反对,2=反对,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冲突体验越严重。本研究中WIF的Cronbach’α系数为0.890,FIW的Cronbach’α系数为0.894。
(2)其他变量的测量。测量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称、学历、学科、婚育状况等。工作特征变量测量周工作时间(包括周末和深夜工作时间);家庭特征变量测量承担家庭责任比例、子女数量、最小子女年龄、家务照料者等。由于学术职业具有任务繁重且工作时间稳定集中的特点,而家庭事务具有琐碎且时间分散的特点,因此分别采用周工作时间、承担家庭责任比例来测量工作与家庭的投入。最小子女年龄按学龄和照料需求划分为3岁以下、3-5岁、6-11岁、11岁以上、未生育等。研究使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统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主要内容有:
(1)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整体情况。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家庭冲突。在严重程度上,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WIF体验比FIW体验严重,且前者均值达到3.68。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无论青年男教师还是青年女教师,WIF均显著高于中等水平(男:t=8.33,P<0.01;女:t=9.501,P<0.01)。在普遍程度上,存在中等水平以上WIF体验的青年教师为83.6%,存在中等水平以上FIW体验的比例为34.8%。

表2 工作-家庭冲突独立样本t检验
(2)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通过相关分析得出,WIF体验与周工作时间显著正相关,而FIW体验与性别、子女数量、最小子女年龄、承担家庭责任比例、周工作时间等特征因素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具体见表3。

表3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法,进一步分析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工作与家庭因素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变化关系。如表4所示,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在性别、时间分配、子女养育等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维度上,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仅在FIW体验上存在显著差异(β=-0.315,P<0.01),且男教师比女教师严重。在时间分配维度上,周工作时间长者WIF体验更强烈(β=0.334,P<0.01),承担家庭责任重者FIW体验更强烈(β=0.333,P<0.01)。在子女养育维度,子女数量越多,FIW体验越强烈(β=0.151,P<0.05)。也就是说,无论男女,周工作时间长的青年教师是WIF体验较为严重的群体;而生育二孩、承担家庭责任多的青年男教师是FIW体验较为严重的群体。

表4 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N=244)
(3)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对工作与家庭的边界管理。结合以上结果,比较不同子女数量下地方高校青年男女教师对工作与家庭投入的时间分配。如图1、图2所示,当子女数量从无增长到2,青年男教师倾向于维持40小时以上周工作时间、承担40%以下比例的家庭责任;而青年女教师则倾向于降低工作投入,提高家庭投入,表现为周工作时间低于40小时的比例由33.3%增长到46.4%,生育二孩后有70.4%承担了40%以上的家庭责任,其中有18.5%承担了80%以上的家庭责任。可以说,在边界管理策略上,青年男教师存在明显分割倾向,生育并未使他们的工作投入产生大的改变;青年女教师则存在明显融合倾向,生育后家庭边界向工作边界延伸、渗透。此外,地方高校青年男女教师的边界管理策略也有相似之处,在此次调查中分别有63.6%、67.2%的青年男女教师邀请父母帮助照顾子女。


4. 讨论。第一,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整体工作-家庭冲突明显。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WIF体验无论在严重程度上,还是在普遍程度上都比较高。本研究中83.6%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存在中等程度以上的WIF体验,而张伶基于7所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研究得出这一比例为72.5%[7]99。比之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转型时期一些较有实力的地方高校向上发展愿望迫切,对于这些院校的青年教师来说,以往闲适的工作状态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竞争激烈的职业发展环境,许多青年教师对此还难以适应,WIF体验有所提高自是必然。此外,仍有约1/3的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存在明显的FIW体验,据此推测部分青年教师存在工作与家庭相互干扰,以及双向边界跨越困难的问题。
第二,周工作时间延长和生育二孩是重要的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因素。就WIF体验来说,不受性别、年龄、职称等因素影响,周工作时间越长越强烈,这与林丹瑚[6]和张伶[7]174的研究结果一致。“不发表就出局”的危机意识促使青年教师主动将周工作时间延长至50甚至60小时,这就提高了由工作边界向家庭边界跨越的难度,表现为WIF体验提高。而对于FIW体验来说,生育成为重要的影响事件。在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下,子女年龄是地方高校青年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8]在二孩生育政策下,本研究发现子女数量越多,青年教师的FIW体验越强烈,子女数量产生的影响掩盖了子女年龄的影响。受“男主外女主内”社会观点影响,青年男教师比青年女教师更难以容忍家庭事务对职业发展的影响,生育二孩、承担家庭责任多的青年男教师由家庭边界向工作边界跨越时存在困难,成为FIW体验较为严重的群体。
第三,地方高校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投入难以保证。学术工作与家庭生活是目标和文化价值迥异的两个领域,学术工作以创造和传播高深知识为目标,崇尚奉献和成就;而家庭则以养育和照料为目标,是充满爱和亲密关系的地方。分割策略有助于青年男教师保证工作投入,免受生育带来的职业发展威胁,但也因此提高了边界跨越难度,面临WIF体验与FIW体验双高的问题。但对于青年女教师来说,从生育前到生育二孩,始终有相当比例的青年女教师将周工作时间降至40小时以下,远低于2018年全国高校教师平均47.0小时的周工作时间。[9]融合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边界跨越难度,但也带来时间和注意分配困难、工作投入下降等问题。青年阶段是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地方高校青年女教师频繁往复于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有限的精力被平行的发展任务所肢解,如果工作投入长期得不到保证,势必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四、小结与建议
在转型发展以及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与子女养育压力交织在一起,工作与家庭的发展相互冲突,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其中,周工作时间延长,以及二孩生育带来的家庭责任提高是主要影响因素。在调节工作与家庭的发展关系中,地方高校青年女教师倾向选择的融合策略使其职业投入难以保证。在边界理论视角下,为促进青年教师更好更快发展,不仅需要青年教师充分协调可及资源,更需要作为强制度组织的地方高校采取必要的措施,构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计划。
第一,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推进民主管理。当员工在工作中被赋予更多自治权时,他们就有机会对边界管理做出适当调整,使工作与家庭的功能达到最佳状态。[10]高校是以学科和专业为基础的“底部沉重”的学术组织,基层学术组织是青年教师的主管部门。地方高校有必要在管理上协调好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优化内部治理结构,逐步下放教师管理权,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通过促进基层学术组织管理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使青年教师有机会参与学术事务的民主管理,避免沦为学术共同体中的缺席者或失语者。这有助于他们发挥弹性工作优势,适应领域发展要求变化,增强对工作与家庭的控制感,有效应对转型发展带来的职业要求变化,以及家庭领域的子女养育压力。
第二,引导青年教师做好生涯规划,鼓励分类发展。边界理论关注具体情境下的发展要求,认为职业发展与家庭发展虽然并行交叉,但各自都有发展的关键期和必须完成的发展任务,需要结合实际合理规划发展的先后主次。生育是家庭领域的重要生活事件,尤其二孩养育会加大边界管理难度,提高时间和注意分配压力。地方高校应积极引导青年教师结合家庭生命周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发展。如尚未生育或仅生育一名子女时,应抓住学术创造的高峰期,提高学术素养,为职业发展奠定好的基调。此外,针对青年教师个人能力和职业兴趣的差异,地方高校有必要改变唯论文的单一发展观,鼓励青年教师向学术职业的不同维度发展,改变他们对职业发展要求的认识和理解。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找到工作与家庭协调发展的平衡点,还有助于地方高校优化人才结构,适应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科研推进等多项转型发展要求。
第三,制定“家庭友好”政策,增强互信理解。根据边界理论,边界维护者是领域文化和价值的倡导者与维护者,个体与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工作-家庭冲突、边界管理不良的重要来源。学术工作与家庭生活拥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其中一领域的边界维护者往往难以理解青年教师在另一领域面临的要求和压力。为帮助青年教师跳出两难处境,地方高校需努力建设“家庭友好”文化,打造工作与家庭生活的交流平台,增进工作中的领导及同事与家庭中的配偶、父母等的相互理解。例如组织亲子联谊活动,邀请家属参观校史馆、实验室等工作场所,让同事和领导了解青年教师面临的家庭需求,也让家属了解青年教师的工作特点和工作要求,工作与家庭的边界维护者由此能改变与青年教师的合作方式和角色期望,协商管理好工作与家庭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