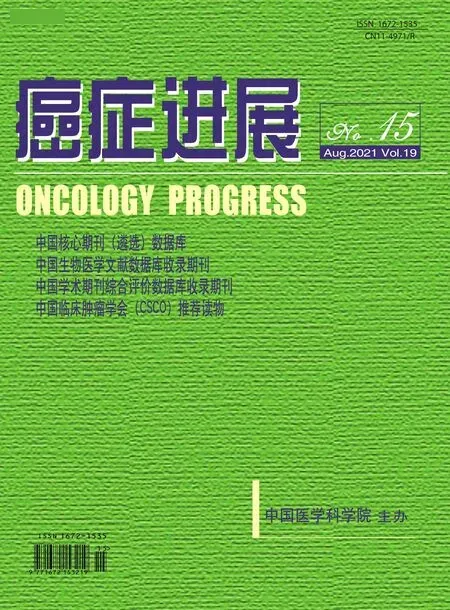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肿瘤治疗中相关性心脏毒性的研究进展
万雯琪,杨继元
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湖北 荆州 434000
随着肿瘤精准医疗的发展,免疫疗法在抗肿瘤治疗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绩,成为目前研究的焦点。虽然多项研究证实,与传统放化疗相比,免疫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均有所提高,但也带来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在多种不良反应中,心脏毒性由于其凶险性高更值得临床探讨。目前,描述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CD1,也称PD-1)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 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PDCD1LG1,也称PD-L1)治疗肿瘤相关心脏毒性的文献仍局限于早期临床试验和病例报告,因此,诊断和治疗都具有挑战性。本文结合目前最新的研究进展,主要介绍免疫抑制剂——PD-1在抗肿瘤治疗中所介导的心脏毒性,从机制、临床表现、监测与治疗、尚待解决的问题等方面进行综述。
1 PD-1/PD-L 1信号通路
PD-1是一种免疫抑制分子,广泛表达于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等免疫细胞中,PD-1高表达会使T淋巴细胞被肿瘤细胞俘获而失去活性,使肿瘤细胞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更具抵抗力。PD-L1是PD-1的配体,在T淋巴细胞、肿瘤细胞中高表达,PD-L1的表达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TIL)、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等的调控,具有促进肿瘤细胞浸润、转移和复发的作用。PD-L1在肿瘤细胞中高表达,与CD8T淋巴细胞上的PD-1结合,传递负调控信号,抑制CD8T淋巴细胞的活性,导致细胞凋亡或免疫调节功能失调,PD-1/PD-L1通路在健康人体免疫调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可导致机体免疫系统无法有效监测和杀死肿瘤细胞。此外,PD-1/PD-L1通路还会促使T淋巴细胞向调节性T细胞和衰竭T细胞分化,从而能减弱T淋巴细胞的抗肿瘤作用。阻断PD-1与PD-L1的结合后,负向调控信号无法释放,被非特异性激活的免疫细胞在发挥抗肿瘤作用的同时也会攻击正常组织,发生类似自身免疫疾病的病理生理变化。
2 PD-1单抗抗肿瘤治疗的应用现状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对多种晚期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较好,如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黑色素瘤、泌尿系肿瘤、宫颈癌、消化系统肿瘤、头颈部肿瘤等,可缓解病情进展。2018年,PD-1抑制剂——纳武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特瑞普利单抗和信迪利单抗相继在国内上市。2019年,卡瑞利珠单抗和替雷利珠单抗在国内上市。此后,PD-L1抑制剂——度伐利尤单抗和阿特珠单抗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在国内上市。帕博利珠单抗是最早用于黑色素瘤治疗的PD-1抑制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基于KEYNOTE-001及 KEYNOTE-024研究的结果,批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肺癌的一线治疗。2015年,基于 CheckMate 057及 CheckMate 017的研究结果,FDA批准纳武单抗用于晚期NSCLC的二线治疗,而一线治疗的疗效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2016年,阿特珠单抗被FDA批准用于晚期NSCLC的二线治疗;2018年,IMPOWER131研究结果显示,阿特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可延长晚期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基于PACIFIC研究结果,度伐利尤单抗被FDA批准用于局部不可切除的Ⅲ期NSCLC的治疗,患者化疗后给予度伐利尤单抗维持治疗,PFS明显延长。
3 PD-1免疫抑制剂相关心脏毒性
在众多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中,虽然心脏毒性的发生率较低,但一经发现,往往十分严重,甚至可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在2021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年会上就有研究报道,老年肿瘤患者的神经和心血管事件的致死风险最高。6个具有丰富免疫检查点阻断抗体使用经验的临床癌症中心发现,8例接受纳武单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晚期肿瘤患者出现了免疫相关心脏毒性,包括心肌炎、房室传导阻滞、心肌病、心肌纤维化和心力衰竭等。此外,也有研究报道了其他部分心脏毒性,包括心包炎、心肌病及急性心力衰竭。
3.1 作用机制
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所致心脏毒性的作用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T淋巴细胞介导的小鼠心肌炎模型证明,PD-1表达缺失易导致自发性心肌炎,而墨菲罗斯大鼠PD-L1表达缺失易导致自身免疫致死性自身免疫性心肌炎。虽然在PD-1缺失的扩张性心肌病小鼠中检测到了针对抗心肌肌钙蛋白Ⅰ的自身抗体,但仍没有发现针对心脏结构的特异性自身抗体。这些体内实验均证实,阻断PD-1/PD-L1通路可能会使心肌内免疫稳态失衡,从而增强T淋巴细胞对心肌细胞的反应性。此外,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可增强T淋巴细胞活性,使肿瘤细胞与心肌细胞抗原靶向结合,导致心肌炎性细胞浸润和心肌纤维化,即肿瘤细胞和心肌细胞间的共享抗原表位有助于心脏毒性的发展,这是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Quagliariello等的研究发现,纳武单抗在NLRP3/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和MyD88信号通路的介导下发挥细胞毒性作用,导致心脏组织的促炎细胞因子风暴,但这些影响的确切性质尚需进一步探索。
3.2 临床表现
PD-1抑制剂所致心脏毒性包括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相关症状,血液学检测及影像学检查特异度不高,诊断较为困难。若患者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出现下述症状,应警惕药物心脏毒性的发生,及时进行相关治疗。
3.2.1 心肌炎 心肌炎是主要的心脏不良毒性事件,是唯一由所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引起的、具有强信号值和高风险的事件,病死率高达39.7%。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通常在早期阶段(开始治疗后17~34天)发病,但是否存在迟发性表现仍不能明确。Zamami等研究发现,接受纳武单抗+依匹单抗治疗的肿瘤患者心肌炎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还有研究显示,合并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肿瘤患者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心肌炎的风险明显高于健康者。免疫相关性心肌炎患者的临床表现不典型且广泛,其中呼吸急促最为常见,还可见疲劳、心慌、心绞痛、胸闷、肺水肿、心力衰竭、室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等;血检可见N-末端脑钠肽前体(N-terminal-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心肌酶、肌钙蛋白Ⅰ升高;心电图可见ST-T改变、严重的传导系统疾病(如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和室性心动过速等;心脏彩超可见左心室功能障碍、室壁运动不协调,但各房室内径多无明显扩大。此外,心脏磁共振成像(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CMR)通过无创T2加权成像和延迟增强成像提供最全面的心肌水肿特征,主要呈现T2加权成像高信号,晚期强化钆增强。免疫组化检测可作为辅助诊断方法;心内膜活检作为一项侵入性检查手段,可见心肌细胞凋亡,心肌、窦房结及房室结点内炎性细胞浸润,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水平升高,是诊断的金标准。
3.2.2 孤立性的心律失常 在合并结构性心脏病的情况下,接受抗PD-1/PD-L1药物治疗的患者更易出现孤立性的心律失常,患者可出现心悸、头晕甚至晕厥等不良反应。若心电图观察到传导异常,应排除其他免疫反应介导的心脏毒性反应,如心肌炎。孤立性的心律失常的心电图可表现为缓慢延长的PR间期、QRS轴偏差、束支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快速性心律失常和心房颤动,必要时需长期监测患者的心电图动态变化,完善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
3.2.3 自身免疫性心包炎 自身免疫性心包炎虽然很少与抗PD-1/PD-L1药物相关,但自身免疫性心包炎患者可能进展为自身免疫性心包炎。心包炎可以单独发生,也可以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心肌炎一起发生。此外,抗PD-L1药物易导致反复的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从而诱发心包炎。由于心包炎症状缺乏特异性,需要结合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综合评估,自身免疫性心包炎可表现为胸痛(随呼吸或体位变化)、发热、斜倚时呼吸短促和典型的心包摩擦。Yun等研究指出,自身免疫性心包炎生物标志物检测可见肌钙蛋白Ⅰ升高,心电图显示不规则PR间期、PR压低和广泛的鞍形ST段抬高,超声心动图显示心包积液,CMR则提示活跃的心包炎症。
3.3 监测及治疗
由于PD-1抑制剂介导的心脏毒性具有特异性,恶性肿瘤患者开始免疫治疗前一般会进行全面的病史询问及心脏基线评估(心肌酶、肌钙蛋白Ⅰ、脑钠肽、抗核抗体、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治疗中及治疗后密切随访、复查,应在治疗的早期阶段就开始进行随访。每2~4周行相关检查评估疗效,密切监测患者是否出现呼吸困难、胸痛、肌无力、肌痛等临床表现,高度可疑患者需复查上述检查并与基线情况进行比较。若需进一步鉴别病因,则需完善炎性指标(白细胞计数、血沉、C反应蛋白)、病毒滴度检测、胸部影像学检查等。对于肌钙蛋白Ⅰ升高或合并心肌缺血的患者,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甚至需完善有创的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近年来,CMR作为一项无创检查手段,被公认为测量心脏收缩与舒张功能的金标准,如心室容积、室壁厚度、左心室质量和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等,但对于心肌炎的诊断是否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尚存在争议,应同时结合血液学检查、超声心动图进行评估,必要时需行侵入性检查即心内膜活检明确,但由于其会损伤心肌,需谨慎进行。
在治疗方面,目前还没有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所有的建议均是基于小规模的病例对照试验和传闻证据,糖皮质激素是否会对患者的远期预后产生不良影响仍不得而知。2016年,癌症治疗与心血管毒性实用指南推荐,合并心脏病史、肌钙蛋白Ⅰ升高、无症状性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等危险因素的患者,即使尚未出现临床症状,也需要尽早启动预防性保护措施。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分级诊治指南推荐:①对于1级心脏毒性、无症状者可密切监测,但出现了任何心脏毒性的迹象,即需暂停使用PD-1。②≥2级心脏毒性,需永久停用PD-1,并尽早开始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必要时加用免疫抑制剂。③对于3~4级心脏毒性,特别是同时伴血流动力学障碍的患者,尽早给予1 g/d甲强龙冲击治疗3~5天,逐渐激素减量预防毒性复发,并至少维持4~6周;若24 h内对皮质类固醇治疗没有反应,可考虑血浆置换、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或英夫利昔单抗,但由于英夫利昔单抗与心力衰竭有关,在中重度心力衰竭患者中是禁忌证。参考心力衰竭指南,对于LVEF降低的患者,若无明显禁忌证(房室传导阻滞、高钾血症等),且患者血压及心率可接受,应尽快应用β受体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以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远期预后,但是否能预防或减轻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的心脏保护作用仍需进一步探索。
4 存在的问题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①缺乏灵敏度和特异度高的生物标志物及检测手段,对预测指标的研究尚不够广泛和深入,难以早期诊断。②由于前瞻性和队列研究开展受限,目前的指南均为2A类证据,缺乏高级别的证据。③缺乏转化性研究,对免疫相关心脏毒性发生机制的认识十分表浅,基础动物模型的研究也仍需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肿瘤细胞与T淋巴细胞、细胞因子和抗体等的相互作用,急需大量的基础相关研究证实。④缺乏交叉学科起草专家,需在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中进行多学科合作,以找到共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⑤恶性肿瘤患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大部分>65岁,在临床试验中的比例不高,接受免疫治疗的安全性缺乏充分评估。因此,预防PD-1和PD-L1相关心脏毒性发生,需要肿瘤科及心脏病学科专家合作探索进行基线及心脏功能评估,以促进心脏毒性的早期识别和治疗。
5 小结及展望
本文所探讨的PD-1抑制剂相关的心脏毒性较为少见,但因早期症状不典型发生、爆发性进展,其致命性较高,且目前对于PD-1抑制剂相关的心脏毒性的机制、监测、治疗等问题仍不能完全明确,不容小觑。2021年的ASCO大会发表了多项关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相关研究数据,包括预测、风险人群和药物管理方案,其中就包括了心脏毒性。现代医学进展越来越要求多学科领域共同协作,在用药前,心内科、肿瘤科和免疫科需联手在筛选低风险高获益的人群、选择用药的方式及剂量、提高治疗总有效率、增加不良反应的可控性等问题上进行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