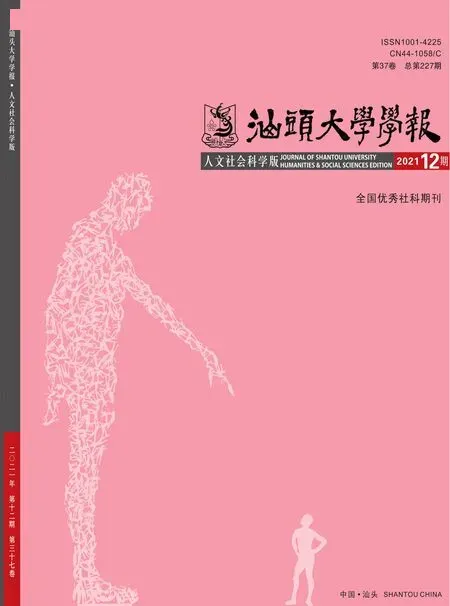重思荀子“化性起伪”的内在理路
肖艳歌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近年来,《荀子》研究的热度仍居高不下,“人性”观、“礼法”思想、“心”有无道德根据、“虚一而静”工夫论等,仍是学界学者热切讨论的焦点与主题,其“心性观”仍存在争议之处。“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仔细审视,其实上述议题皆畛域于荀子“化性起伪”这一核心思想,也就是说,无论对“人性”,对“伪”或对“心”做何种解读,皆不能偏离荀子“化性起伪”这一思想宗旨:“性”是什么,又何以能化?如何化性,性与伪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伪又何以能生礼义法度?笔者将在本文一一厘清相关问题。
一、“性”之可化及“化”之目的
在弄清楚何为“化性”之前,我们首先得清楚荀子所说之性到底是什么。荀子的人性观主要见于《性恶》篇,其他篇章也略有涉及,笔者对之作了简要摘录:
(1)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
(2)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恶》)
(3)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
(4)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情性也。(《性恶》)
(5)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
(6)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第一条中的“朴”,赫懿行曰:“‘朴’当为‘檏’。‘檏’者,素也。言性本质素,礼乃加之文饰”[1]433,是说性天生朴素,加之第二条的“不可学”“不可事”的“天之就”特性,皆说明了“性”是人与生俱有的,自然而然的,不掺杂后天任何的人为和装饰,这是荀子笼统的规定何为“性”;接着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是阐明了性之具体内容,概而言之,性的内容是就人作为生物的生理本能、欲望而言的;接着第六条,前半句“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仍是强调性是人生来就具有的东西,具有天然、本然的特质,对于后半句:“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然者”,杨倞注曰:“和,阴阳冲和气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气所生,精合感应,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和,谓若耳目之精灵与见闻之物合也。感物,谓外物感心而来应也。”[1]487就第六条看,杨倞显然把荀子的人性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之所以然”之性,强调人生来就具有的一些本能和欲望,在先秦时期,“以生训性”是当时普遍的理解与共识,因此“生之所以然”之性也可唤作“生之谓性”;第二层次是“精和感应”之性,即感官与外物相接,心自然而然地会有所感有所应,可唤作“及物之性”或“发用之性”。
按“生之谓性”与“及物之性”的分法来看性之具体内容,第三条和第四条应属于“生之谓性”,第五条则属于“及物之性”,且第五条最后有讲“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这与“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就“生之谓性”和“及物之性”各自的特性来看,“生之谓性”无所谓善恶,故不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及物之性”则不然,比如荀子说: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正名》)。意思是说,人看见了自己想要的某个东西,会事先在内心衡量此物是否能够得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便会“求之”,即付诸行动,如果“求之”的程度、方法、途径是正当的,也无所谓善恶之分,担心的是不加节制的“求之”,即无限度的“顺是”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求之”,这样来看,“求之”这一行为本身潜存着正当与否的价值判断问题。笔者认为学界持“性朴”论者正是就荀子“生之谓性”来立意的;持“性恶”论或“性危”说者是多就“及物之性”做的阐发。“生之谓性”不涉及价值性的问题,“及物之性”则有可能涉及了价值性的判断,这也正是荀子主张“化性起伪”的根由所在,我们也由此可推知荀子所要“化”的对象——及物之性。
何谓“化”呢?荀子讲:“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正名》)可知,“化性”并非是要彻底否定性、消除性,而是在尊重人的“生之谓性”的前提下,使“及物之性”不“逾矩”。荀子讲:“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接着又说:“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就这几则引文来看,性、情、欲三者实是同体而异名的关系,即如徐复观先生所语,尽管荀子对性、情、欲做了概念上的界定与区分,实质上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三种不同叫法,以欲论性是荀子人性观的一大特征。[2]234若从体用视角来审视,性为体,情和欲则为性之发用与呈现。“及物之性”之所以又唤作“发用之性”正在于它是“生之谓性”与外物相接时的心之所感、心之所应。由此来看,“及物之性”具体讲就是情性和欲性,两者也正是荀子所要“化”的对象。对此,荀子也有明确说明情和欲的可化、可节的特性:“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如此,可与如彼也哉?”(《荀子·荣辱》)“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后可为也。”(《荀子·儒效》)“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
由以上论述可知,“生之谓性”是人维持生命存在的自然属性,自然不可去除,荀子所主张的“化性”实质是约束情性和欲性,使之发用呈现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如何化性——“心伪”与“行伪”的双管齐下
依笔者看,“化性起伪”唤作“起伪化性”或许更为妥当。明白了什么叫作“化性”,接下来自然是要解决如何化性的问题,即如何“起伪”以及“伪”又是怎样矫正“性”的。
荀子在《正名》篇对“伪”有一基本的定义:“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伪,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第一句话,杨倞注曰:“心择可否而行,谓之虑也。伪,矫也。心有选择能动而行之,则为矫拂其本性也。”[1]487就荀子对“伪”的定义来看,第一句话之“伪”是就心理过程来讲的,即侧重于心之过程义,可名之为“心伪”;第二句话之“伪”是就“矫其本性”的结果义来讲的,可名之为“行伪”,一个是内在之“伪”,一个是外在之“伪”,就两者的关系来看,内在之“伪”是外在之“伪”的前提和基础①严格来讲,“心虑”与“虑积焉”属于“心伪”;“能为之动”与“能习”属于“行伪”,为了便于分析与解说,故,正文将“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称之为“心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称之为“行伪”。,外在之“伪”是内在之“伪”追求的结果。就“化性起伪”整个过程来讲,内、外之伪皆不可或缺。
我们先分析第一句话,看看“心伪”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伪”,在情感快要发出来之际,心要衡量、思考需不需要发用出来,若发用,发用到何种程度为好。“心虑”即心思虑,表示心处于一种抉择、权衡的状态。就心作为一思维器官来讲,心既可以思虑这,也可以思虑那,即心思虑的内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伪”所要求的“心虑”是什么样的?毕竟“心虑”最终得导向“伪”,合乎“伪”之要求。换言之,心应以什么作为自己权衡、思虑的准则,才有助于化性呢?荀子在《解蔽》篇明确表示要将“道”作为权衡、抉择的标准:“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曰:道。”杨倞注曰:“不滞于一隅,但当其中而县衡,揣其轻重也。”[1]465“衡”权衡之谓也,“揣其轻重”衡量轻重之意也,《正名》篇也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由此看来,心虑应以“道”为准则才符合“伪”之要求。心以道权衡、抉择、思虑的过程同时也是“心可道”“心所可中理”的过程,即“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解蔽》)以及“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杨倞将“可道”注解为:“心不知道,则不以道为可。可,谓合意也。”[3]382将“所可”注释为:“心以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虽多,无害于治也。”[4]414万百安曾明确表示,相异于孟子,荀子人性中并不具有天生的道德欲望,一个人的行为之所以能合乎“道”主要是由他的“心之所可”决定的[4]161-184。其实无论是“心可道”还是“心所可中理”都说明了心已将“道”作为自己判断是非对错的价值导向和准则,并且会为之付诸行动,比如荀子说:“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正名》)即不仅“心虑以道”而且还要“能为之动”,这样才算真正做到了“心伪”。
依笔者看,杨倞将“可”释为“合意”实为确论。但在心与道“合意”之前还需要有一个“道”入心的过程,即荀子所说的“心知道,然后可道”,那么心如何“知道”呢?荀子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解蔽》)
我曾见过二老摄于1992年的一帧照片,他们站在花丛中,相依相偎,共读一本书。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宝黛共读《西厢记》的画面。
杨倞对引文中的“将须道者,之虚则入;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也”作注云:“虚则入者,入,纳也,犹言虚则能受也;壹则尽者,言壹心于道,则道无不尽也。静则察者,言静则事无不察也。知道察,谓思道者静则察也。知道行,谓须道者虚则将也。体,谓不离道也。”[1]469心唯有“虚”,“道”才能进;心唯有“一”,“道”才能尽才能全;心唯有静,“道”才能发挥事无不察的功用。由此看来,“虚”“一”“静”三者是“道”入心的方法和途径,心“知道”了,才能“可道”,才能“心虑以道”,然后再“守道以禁非道”,为更形象地展示整个“心伪”的过程,笔者试做如下图示:
虚一而静→心知道→心可道(心所可中理)→心虑以道→守道而禁非道
上述简图虽形象地展示了“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的完整过程,但为什么当心虑以道时,情性和欲性能被约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即是说“道”与“性”,或说与情、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制衡关系。“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通观整个《性恶》篇,荀子似乎都是主张用礼义来矫饰、约束人之情和欲,那么这里的“道”是不是也是礼义之道的意思,对此,荀子也有明确的表明:“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根据这则文献来看,“道”是礼义之道,毋庸置疑。但若将“心虑以道”的“道”释为“礼义之道”,则会出现与文意不相契的情况:心很难仅仅通过认知形下层面的礼义之道而达到“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经纬天地、材官万物”的高度和境界,这是其一;其二,心若仅认知形下层面的礼义之道,这处于“他律道德”层面,很难自动做到“守道以禁非道”。显然,将此处的“道”仅仅看作“礼义之道”与文意不太相符。以笔者之见,“万物莫形不见,莫见不论,莫论而失位,经纬天地、材官万物”所呈现的恢宏气度和高明境界来看,以及“守道以禁非道”的高度自觉和自律来看,此道释为形上之中道较为妥切。①关于《解蔽》篇“道”的属性问题,学界还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不能简单地将之等同于礼义之道。比如廖名春先生认为,荀子的“道”是万物变化遂成的所以然,也即是万物的普遍规律,同时它也是一种客观的是非标准,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性就体现在事物的无穷变化之中。详参廖明春,《荀子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343 页。再如杨国荣先生认为,荀子的“道”既体现了存在的统一形态,又作为整体的形上智慧,为超越一偏、达到全面之知提供视域。详参杨国荣:《从“志于道”到“壹于道”——略论孔子与荀子关于道的论说》[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1),第3-4 页。此外,孙伟、方东朔、储昭华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梁涛先生曾谓:“孔子之后,真正全面继承‘中’的传统的主要是荀子,而非孟子”;“荀子对中道作了系统论述,成为中道思想的集大成者。”[5]101-103比如,荀子说:“百王制无变,足以为道贯。……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荀子·天论》);讲“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荀子·王制》);讲“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中道”思想在荀子哲学中随处可见,只不过荀子多将其与“礼义”连在一起说,这使人往往对“礼义”关注过多,而忽略了“礼”之所以产生的形上根据——中道,即“礼”是形而下之器,相对于礼来讲,“道”则是抽象的形而上本体。也只有形上之中道才能做到“兼陈万物而中县衡”,才能被当作“古今之正权”。“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荀子·宥坐》),当“欹”这种器皿处于空虚状态时,它是倾斜的,当注满水时,它也会倾斜,只有注入的水不多不少,即处“中”时,它才会“正”。这说明,做到了“中道”,自然就会不偏不倚。“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又曰:“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通过荀子对“礼”的比喻,可以看出“道”类似一杆大秤,“礼”相当于一杆小秤。既然是秤,那么“道”自然就具有“公”“正”“平”“中”的特点。也正因为“道”具有这样的特性,它才能成为心思虑、权衡的准则和依据。再进一步说,“道”或“礼义”并非是“去欲”,而是要使情性和欲性发用正好,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即“礼者,养也。”(《荀子·礼论》)、“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礼论》)这也正是荀子为何一再主张以礼义化性的根由所在。
以上讨论是“心伪”,接下来我们讨论“行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杨倞注曰:“心虽能动,亦在积久习学,然后能矫其本性也。”[3]399如果将“心虑以道”称之为正思、正念、正虑,那么“虑积”其实就是对这种正思、正虑、正念的不断积累,“能习”即对“能为之动”的不断习练,具体讲,是对“守道以禁非道”的不断践行,只有通过这样反反复复的积累和实践,最后才能实现“而后成”,即性“长迁而不返其初”,化性成功。那么,化性为什么需要“虑积”和“能习”呢?这中间又存在怎样的内在理路?
(一)“积”的必要性
“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荣辱》)说明人本身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这种可塑性往往通过“日积月累”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日积月累什么,就会成为什么,如荀子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荣辱》)“积”在《荀子》文本中出现较为频繁,荀子也正是想通过“积”来说明:成圣还是成凡,关键在于“积”之不同,即“积”什么成什么。圣人、凡人,或说君子、小人,其实都只是追溯性的说法,在最开始并无君子、小人,圣人、凡人的区别,即每个人在先天质具、先天禀赋方面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荀子强调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性恶》)“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荣辱》)而之所以后来有了君子、小人的区分,多在于注错习俗的不同,注错得当为君子,注错不当为小人,再进一步讲,为君子还是为小人,成圣人还是成凡人就在于能否坚持不懈地“虑积”和“能习”。无论是“虑积”还是“能习”,皆是“积”之表现,只不过一个属于“内积”,一个侧重于“外积”。
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心生而有知”,心具有认知功能,心既可以认知这,也可以认知那,即认知的对象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再进一步说,每个人的所见所闻不同,所思所虑自然不尽相同,简言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而这些经历于无形之中默化为自己的判断标准或行事依据。认知经历不一样,所“可”也就会有差别,即“心知道,然后可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这样每个人就存在“可道”与“不可道”的差别。“可道”就会“心虑以道”,不“可道”就会“心虑非道”,“心虑非道”自然不会有助于化性。正因为心认知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所以就无法保证心时时都能“心虑以道”,即是说“心虑以道”存在一定程度的偶然性,正如荀子举的这个事例:“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则瞲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正名》)人作为一经验性的存在,往往是凭借其经验来做出判断、抉择,正如引文所述,当一个人食用过稻粱和糟糠后,经过对比,自然会选择稻粱而舍弃糟糠。同样,当一个人在尝试了心以道为标准思虑、抉择所带来的结果和心不以道为标准,即随顺自我情欲来抉择、权衡事情所带来的结果后,通过对比,长此以往,他会逐渐发现心依循道来考虑事情相比于心不以道为准则考虑问题所带来的利益更大,即“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礼论》)。换句话讲,他认识到了只有自己的欲望与礼义法度相结合,即“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才更有以利于自己未来的发展,这也正符合规则功利主义者所强调的:遵守秩序或践行美德,长远来看可以最大限度地带来利益。对此,Kurtis Hagen 在《荀子与审慎之道:作为成善动机的欲望》中也有类似的说明:人们最开始能遵循礼义多是凭借外部的刺激,即人身上并不具有自觉遵循礼义的内驱力,但是,一旦由于审慎的缘故遵守礼义后,就会发现遵循礼义所带来的一些效益,从而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动机结构。[6]53-70心以道为思虑准则属于遵守礼义,新的动机结构的产生正是源于心比较、衡量心以道思虑与心不以道思虑所带来的结果的不同而进行的心理结构调整。
或许正是看到了人本身具有的可塑性以及“心虑以道”存在的偶然性,所以荀子才反复强调“积习”的重要性:“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那么如何“积”呢?应“积习”什么才有助于最终的“化性”呢?
(二)如何“积”
就上述整个“化性起伪”的过程来看,“心”是“化性起伪”的关键。既然心具有认知功能,且认知对象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保证心所认知的内容,使心不断积累正念、正虑,自然有助于“化性”。所以荀子开篇即言“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接着又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至于学习的内容,荀子说:“故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性恶》)。荀子不仅主张要学习“礼法”,而且还尤为重视与谁交往,应向谁学习的重要性,比如,“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即是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又,“学莫便乎近其人”(《劝学》)、“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修身》)关于学习的目标,荀子也有说明:“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圣制者也!两尽者,是以为天下极矣”(《解蔽》),“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劝学》)从小的方面讲是成为君子,大的方面讲是成为圣人。通过“锲而不舍”地学习,不断受君子或大儒影响,加之不断的反省来总结经验,心就会逐渐地以道作为思虑准则,且频次会越来越多,整个过程即是:学礼义,则知礼义;知礼义,则可礼义;可礼义,则可道;可道,则心虑以道;心虑以道,则守道以禁非道。如果说“为学日益”属于量变的积累,还处于“他律道德”层面,那么“虚一而静”后的“大清明”境界则是质变的飞跃,已属于“自律道德”层面。
“大清明心”所呈现的“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的境界即是“中道”境界,礼义法度便由之而出。这样,上文我们所分析的整个“化性起伪”的过程,即是荀子所说的:“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圣人之性也。”(《性恶》)
三、“义”“辨”道德潜质下的“伪”之可行性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儿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恶》)“性”是人先天本有的,“伪”是人后天积习的,那么不禁疑惑:后天之“伪”能否真正管制、约束先天之“性”呢?牟宗三先生曾说:“是则圣人之伪,必于外有根据,此根据,荀子未明言。”[7]226是否真如牟先生所言,“伪”没有根据呢?
在《王制》中,荀子又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荀子看来,人区别于动植物的关键在于“义”。何为“义”?“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分”区别、区分,“乐和同,礼别异”(《礼论》),礼本身执行的就是“分”的功能,而“义”则是“分”或说“礼”的基础,关于这点,荀子还有更为明确的说明:“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荀子·君子》)即“尚贤使能”“贵贱有等”“亲疏有分”“长幼有序”是“义”之体现,而“尚贤使能”“贵贱有等”“亲疏有分”“长幼有序”属于“礼”的内容,故“礼”是“义”的表现,“义”是制“礼”之依据。正因为礼与义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荀子常“礼义”连用,有时“分义”连用。“义”虽是“分”的基础,但“义”到底是什么,为何能成为制“礼”之依据,我们仍需继续讨论。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君子》)只有“分义行化下”,士大夫、百吏官人、众庶百姓才会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可以看出“义”有“正当”或“应当”之意。再看“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接着又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荀子·强国》)。只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存在,才能较大程度地避免人作奸犯恶,才会有“上安主下调民”的局面。由此来看,荀子强调的“义”是一种“正当性”“合理性”“应当性”的体现。正因为“义”代表着“正当性”与“合理性”,所以它才能成为“礼”之标准。
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之所以区别于动植物,正缘于人之“义”,即是说人之潜意识能够区分何为正当与何为不正当。我们接着再看荀子对人之为人的另一处规定:“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相较于动物,人之“辨”集中表现为人懂得“父子之亲”,知道“男女之别”①“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见于《荀子·非相》,而“父子之亲”与“男女有别”本身就是“礼义”的内容,这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本身具有的“礼义”特性。由此可见,人之“义”与人有“辨”皆是说明人本身具有向上、向善之倾向,梁涛先生曾说,荀子之心并非只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认知心,而是具有价值选择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的道德之心[8]。荀子在《性恶》篇说“涂之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能仁义法正之具”正是基于人之“义”与“辨”来立论的。
由以上论述可知,“性”具有先天性,“伪”同样具有先天根基——“义”和“辨”。就逻辑上来讲,只要能“起伪”,自然也就能“化性”,这样我们也就打消了“伪”能否“化性”的顾虑与担忧。
人皆有“义”、有“辨”、有“质”、有“具”,所以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按荀子的理论逻辑,每个人在先天资质上都是相同的,皆可以成圣成贤,但现实并非如此,即现实生活中存在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学界有论者认为,荀子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区分出了圣人之伪与凡人之伪,即圣人之伪无所不能,故能制作礼义,凡人之伪主要体现为对礼义的实践和遵守[9]15-1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虽有向上、向善之潜能,但“潜能”毕竟不等同于现实之“能”,也就是说,“潜能”有可能一生都未转化为现实之能,一直处于“潜”而不发的状态。是“潜”还是“发”全在个人,即荀子所说的:“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性恶》)正如李涤生先生所注:“‘可以’,就理言,亦即就先天条件言。‘不可使’,就意志言,亦即就后天人为言。言人皆有可以积学为圣的本质,而不肯不可强使积学也。”[10]554为君子还是为小人全凭自己,全在自己,对此,荀子也有明确的说明:“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修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解蔽》)。可以看出,“心”在荀子这里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诚如路德斌先生所说:“纵览整个中国思想史,对‘意志自由’的表述,恐怕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的任何一个概念能够比荀子的‘出令而无所受令’来得更加贴切和明确。”[11]94正因为心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能动性,所以为善还是为恶全由乎己心,成圣还是为凡亦由乎己心。这是其一。
再者,《荀子》文本中之所以有圣人、凡人相区分的说法,也有“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恶》)的直接表述,其实圣人或君子都只是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追溯性说法,并不是说圣人一开始就有,圣人天生就能“伪”,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荣辱》)。学界还有学者纠结、探讨第一个圣人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制礼义的,依笔者之见,其实这应是一个伪问题。
四、结语
荀子的“性恶”观一直被世人诟病:“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二程集》又曰“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朱子语类》),因其人性论,荀子被理学家踢出了“道统”。当代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荀子虽为儒家,但他的性恶说只是触及人性中的动物层,是偏至而不中肯的学说。”[12]74劳思光先生也评价道:“荀子倡性恶而言师法,盘旋冲突,终堕入权威主义,遂生法家,大悖儒学之义。”[13]249虽为儒家学者,荀子既持性恶,那么道德何以可能?荀子把希望寄托在了“起伪”上面,即主张“化性起伪”。
“生之所以然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这五句话基本上已交代了“化性起伪”的整个内在理路:第一句话指“生之谓性”;第二句话是“及物之性”;第三句话也是“及物之性”,即“好、恶、喜、怒、哀、乐”是及物之性的主要内容。“生之谓性”是人维持生命体征、先天本有的自然属性,自然不可去除,荀子“化”的目标是“及物之性”,化的目的是使“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无过不及。第四、第五句话阐述了“化性起伪”的整个过程,具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心伪”与“行伪”。“心伪”强调“心之所可中理”,“行伪”则强调对“心之所可中理”与“能为之动”的不断积习,直至性“长迁而不返其初”。从荀子心与性的关系来看,可用“以心制性”来概括,性为恶,治恶者只能是善,那么心有无道德之善,亦即“伪”有无善之根基?答案是肯定的,荀子所讨论的人有“义”、有“辨”与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皆说明“伪”并非纯是后天之积习,即“伪”同性一般,亦具有先天根基,梁涛先生认为荀子实是“性恶心善”说,正是基于此立论的。“伪”既有先天之根基,即“心”有道德之潜能,那么只要“积善不息”“加日县久”,“性伪合而天下治”就可企足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