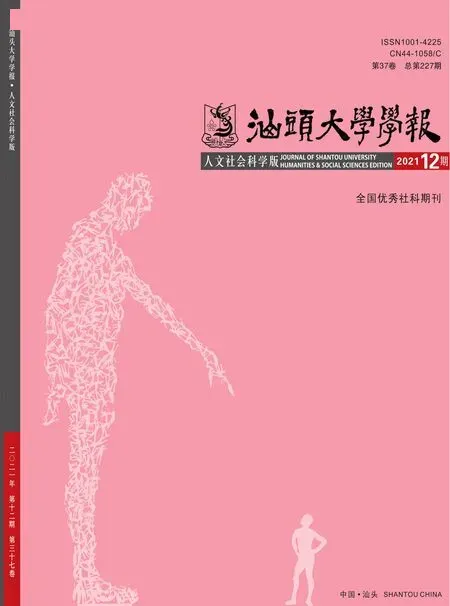圣人的知识、学问与气象
——兼论朱子之“道问学”思想
王新宇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学为圣人”是宋代理学迥异于前的最重要之特质,而“学为圣人”之首要内容则在学“圣人之心”。但具体如何体认则有所区别,有学者即将这一区别认定为理学与心学的差异:
……传心的说法朱熹也不绝对反对,他认为十六字真诀即古圣相传心法,只是传心须通过文字,见诸经典,故欲得圣人之心,必须穷格圣贤之书。……陆九渊认为成圣成贤无须依赖前圣相传,只要信得自家宝藏本自全具,一经发明本心,自然成就圣贤……[1]
根本说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取决于对“圣人之心”的不同认识。朱子认为,需要通过格物穷理来体会圣人之心,而格物穷理的途径包括却不局限于经籍。陆象山则认为成圣成贤主要取决于自家本心的发明,只要本心得以彰显,那么其余的工夫(包括读书在内)都可顺此而求。因此,哲学史将这两种进路用《中庸》的“尊德性”与“道问学”来划分。虽然朱子自己明言,他的进路绝不是二者之一,而一定是兼备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朱子心目中的圣人确实有着极为强烈的“道问学”特色,朱子也确实极为强调学者需要格物穷理的工夫来“学为圣人”。问题在于,“道问学”是否可以作为体认“圣人之心”,并从而“学为圣人”之必由法门。朱子之所以如此关切“道问学”之问题,是否如心学家所说是“支离事业”……这些问题当然不乏前贤时哲之充分讨论。本文则以为:朱子之所以重视“道问学”,其根本就是立足于对“圣人之心”的理解,圣人之“学”亦不过是“圣人之心”的自然流露,故“道问学”之工夫,即是体认“圣人之心”的应有之义。并且,只有在“学为圣人”的过程之中加以体会,才能理解朱子“道问学”之真精神。简言之,“知识”作为圣人之重要标志,是圣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圣人之“知识”亦有别于一般的智巧,而因其自然充沛而造就了所谓圣人“气象”。那么,作为学者所效法对象的圣人,其知识、学问和气象也就是学者所当效法和体认的。朱子学之所以重视“道问学”的理由正在于此。也正因为此,“道问学”与“尊德性”,于朱子而言当然是一而非二,因其皆为圣人之学。这个结论当然并非新见,所以能稍显本文之突出的,即是将“道问学”之原因推本到圣人处,因为朱子学意义下的任何一种学问工夫,应该且必须是根据圣人所确立之标准。除此之外,谈所谓“道问学”,或是“知识论”“格物说”等等,便将毫无意义,也必定不是朱子学之初衷。而心学家之所批判的“道问学”,亦恐非朱子学立论之本心。此外,“道问学”在心学家那里所存在之疑难,及朱子学可能的应对,也会是文末将会提及之处。当然,心同理同,王阳明言“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2]34,大贤如朱子、阳明者,在其心地与工夫处,“尊德性”与“道问学”也应是当然为一的。
一、圣人之知
“知”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为知识义,即所谓“生而知之”之“知”,圣人拥有与生俱来的知识,这是学者所无法企及的。二为“智”,即所谓“仁者智者”之“智”。圣人的“知识”与“智能”一直以来是传统学者所公认的特质,朱子极其重视这一特质,并视之为圣人之所以区别于常人的基本特征。朱子将“圣人之知”进行了进一步发扬,使其具有了理学的精神,故而在论述时必须结合朱子学与理学的诸多义理进行贯通。
(一)生而知之
“生而知之”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且都为孔子之言。孔子明确表示过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98朱子说:
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圣,每云好学者,非惟勉人也,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3]98
朱子引尹氏(尹焞)之说,认为孔子确实是“生知”,但孔子此处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也并不仅是自谦以勉人,还包括了“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这说明“生而知之”的圣人也确实有需要“学而知之”的部分,二者并不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生而知之的部分是“义理”,学而知之的则是“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等,这也很好地解决了历代对圣人究竟是否“生而知之”的争论问题。圣人是“心与理一”的,故而谓之“生知”;但是圣人也有形质躯体,也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对于具体的人情物事、制度典章,必然也需要经过学习,这是朱子理气论和心性论贯通之下的自然结果。圣人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生而知之”并非意味着全知全能、无所不知,其中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论语》中第二次出现“生而知之”是在《季氏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3]174朱子说:
言人之气质不同,大约有此四等。杨氏曰:“生知学知以至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学之为贵。困而不学,然后为下。”[3]174
朱子将孔子所区分的四种类型定义为“人之气质不同,大约有此四等”。联系上章,朱子所定义的“生而知之”,即是“气质清明,义理昭著”,这恰是圣人的气质,而人之气质有如此不同,也是朱子所一贯的主张:
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后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4]66
圣人与学者在“生知”与否上的差别源自于气禀之异,因此对“义理”的呈现就存在不同。联系《大学》“明德”来说: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气禀之拘,其“明德”之宝珠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泥沙的污染,因而无法完全呈露,对于“义理”的明晰则需要通过后天的“明明德”工夫来擦拭泥沙,这个工夫在圣人则因其天生的资禀纯粹清明而略去了。这就是朱子所认为的“生而知之”的原因。同时,“学而知之”同样重要,因为不但圣人也存在“学而知之”的部分,学者更要通过“学而知之”来向着成圣之路迈进。在《述而篇》,朱子认为圣人的生而知之是于义理无处不晓,所谓“不待学而知也”,同时又说:
其义理完具,礼乐等事,便不学,也自有一副当,但力可及,故亦学之。[4]891
圣人自然是好学的,且正因为圣人生知,见得道理完备,故其为学,才更有一番不可已的精神。孔子自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3]98,即表明圣人“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一体性,所以朱子说“圣人是生知而学者”。正是因为圣人对于“义理”有天生的完整认识,他的学问才可能更加彻底和全面。换言之,圣人的“生而知之”造就了圣人的“学而知之”。对于学者来说,气禀的鸿沟则并非成圣的障碍,圣人对“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兼具反而成为学者“道学之功大”的助力,“故君子惟学之为贵”。到了《中庸》那里,意义就更加明确了: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3]29朱子说:
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3]29
“人性虽无不善”,此人性分之所当然;“气禀有不同”,此则人生形质之所必然。因此,“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便是实然之存在,圣凡之所以不同者,正在于此。然此不同并不足以抹杀人性当然之“无不善”,倘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朱子学的最大特征就是“极广大而尽精微”,面面俱到。在肯定圣人与学者存在着“气禀有不同者”的同时,极力鼓励学者之“自强不息”,虽然我们同时需要明白,这个“自强不息”的过程,在朱子看来,也是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的。学为圣人,绝非易事。
(二)圣人聪明
圣人因其“气质清明,义理昭著”故能“生而知之”,而生知的圣人在儒家传统看来是圣人之“智”的自然表现。文字学解释中,圣人本就是极其聪明睿智的,“圣”主听,《说文》曰:“圣,通也。从耳,呈声。”[5]《说文通训定声》曰:“圣者,通也。从耳,呈声。按,耳顺之谓圣……春秋以前所谓圣人者,通人也。”[6]圣人耳顺心通,其聪明睿智自非常人可及。历史学认为,“圣”与祭祀巫术有密切的关联,具备聪明、通达的特点。《六经》之中对“圣”的描述也体现了这一特色: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复狂以喜。[7]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8]31
思曰睿,……睿作圣。[8]454
本文无意去探讨历史学中“圣”之对象及意义的演变,而着重表明:圣人在儒家传统的意义中始终是充满了智慧的、聪明睿智的形象,圣人的智慧与常人相比是非常出类拔萃且难以企及的。朱子说:
耳顺心通,无所限际。古者论圣人,都说聪明。如尧“聪明文思”,“惟天生聪明时乂”,“亶聪明作元后”,“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圣人直是聪明。[4]721
圣人之聪明睿智是朱子所极为重视的,这一特征同时也体现在朱子对子贡的推崇上。在孔门弟子中,子贡的特点便在于聪明颖悟。朱子说:
孔门自颜子以下,颖悟莫若子贡。[3]189
子贡之学,多而能识矣。[3]162
圣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晓得时,方担荷得去。如子贡虽所行未实,然他却极是晓得,所以孔子爱与他说话。缘他晓得,故可以担荷得去。虽所行有未实,使其见处更长一格,则所行自然又进一步。圣门自颜曾而下,便须逊子贡……[4]720
以上都是对子贡气质与为学特色的体认,朱子将子贡与颜子相比,这也是孔子做过的事情。之所以与颜子相比,是因为两人都具备聪明颖悟的气质,子贡的学问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多而能识”的特点。朱子的理解并非自己创造,而是经过了对圣人经典的细心研读和体会,从最后一条语录就可以看出,朱子对子贡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子贡属于知过于行的一类学者,朱子对他的这一特点有批评,也有肯定,并认定圣人之学非常需要有如此敏悟之才,才能“担荷得去”,且子贡经过进一步的修养和学习,必定能够有更高远的成就。朱子对子贡的推崇显示出朱子对于圣人之聪明睿智的强调。圣人当然是德行充沛饱满、完美无缺的,但圣人也一定是才德兼备、仁智兼得的。朱子说:
……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4]2830-2831
以“生而知之”之圣人、通博学多才之实事、做经国天下之事业,这才是朱子心目中一个完整的圣人形象,同时,从此也可以看出朱子对学者如何“学为圣人”的态度,那就是不断地从事于格物穷理的孜孜下学之功,即“道问学”。做圣人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学者来说,不仅需要高悬“圣人与我同类”的理想,更需要寸寸进取的工夫与学问。这一认识延续了儒家传统,孔安国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郑康成曰:“圣,通而先识也。”[8]454-456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9]圣人同时具备了仁德与智慧的最高标准。这些认识与此后的理学很不相同。王阳明说:“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2]34又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金,而乃妄希分量,务同彼之万镒,铅锡铜块,杂然而投,分量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筲末无复有金矣。”[2]35这是王阳明著名的“成色分两”理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只在于“天理”是否纯粹完全,而并不在知识是否多、才力是否大。圣人纯于“天理”,此固无错,然说圣人才力有不同,乃至于知识、才力、分两等皆非圣人的特质,则恐怕并不能真实反映儒家传统的圣人特色。朱子亦强调圣人并不在于多能,但圣人绝非不多能:
盖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4]958
圣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学多能,则只是一个杂骨董底人,所以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4]958
子贡赞叹孔子乃“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3]110,已经将圣人这一仁智兼备的特色昭示出来,朱子一面表示“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一面强调“圣人未有不多能”,同样是对这一传统的表彰,亦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同时并举。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勉励学者的同时,已经注意提醒学者不能一味去学圣人多能,乃至于成了“一个杂骨董底人”,这与阳明的“不务锻炼成色,而乃妄希分量”可谓如出一辙。王阳明的理解不可谓不“拔本塞源”,但是对于圣人之全体精神的理解,恐还当以朱子为是。
总结本节所论,首先,朱子心目中的圣人一定是“生而知之”的,这可与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贯通,圣人气质清明,乃能义理完具,故而圣人的“生知”是相对“义理”来说的。另一方面,朱子并不否认且极为强调圣人的“学而知之”,关于这一点,下一节将做具体的阐释。其次,朱子亦传承了传统儒家对于圣人的聪明睿智的理解。孟子认为“夫子贤于尧舜”,正是从圣人的事业来理解,而尧舜禹汤的事功同样是不朽于万世的,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对于圣人之体认更加接近传统儒家的认识而非后世理学。圣人一定是仁智兼备之非常人,虽然这并不会妨碍学者们踏实做好自己“学为圣人”的工夫,工夫的路径当然以“尊德性”为本,然所以“尊德性”者,“道问学”而已,因为圣人本就是如此的。因此,朱子重视“道问学”之第一重原因在于:圣人作为学者之效法对象,是能够“生而知之”于义理的,又因其义理完具于圣人之心,故而对于礼乐典章、名物制度,乃至于经国事业,都有极为宏大之规模,此即圣人之“聪明”。学者不能如圣人“生知”,但学者可以通过“学”来贴近圣人。这个“学”就是“道问学”之过程。可见,“道问学”实是学者的必由之路,因其未能如圣人故也。
二、学问与气象
上节具体讨论了圣人之“知”,即朱子对于圣人“生而知之”的理解,而圣人的“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是并行不悖的。本节便以圣人之“学”为焦点,对圣人之学问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圣人的博学多能源自于其气禀之清明,因此其为学工夫之“自然”也是常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于学者来说,圣人天生的气质无法去模仿,但圣人气象却是学者效仿和体认的重要目标,这些内容也正好是朱子学的重心。本节会对圣人为学的“自然”境界做出朱子学的阐释,圣人作为出类拔萃者,相比于学者的困知勉行是“沛然莫之能御”的,圣人之心与理为一,当其接触到外界的事物和知识的时候,这颗心是能够立刻通向事理之至善的,所谓“其应甚速”,这就是圣人的气象。本节的后半部分会具体讨论圣人气象。朱子接续理学传统,非常重视对圣人气象的体认,而圣人气象正是从圣人的聪明睿智、好学不倦中自然推出来的,因其好学而成其大、因其聪明而有神。
(一)自然与勉强
圣人之聪明与好学,此无可疑问,《论语》中对于孔子之好学不倦的记载比比皆是,而朱子毕生所尤其关切的,也是学者之为学工夫。为学则在学圣人而已:
圣贤所说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个“择善固执”。《论语》则说:“学而时习之”,《孟子》则说“明善诚身”,……工夫只是一般……[4]130
世俗之学,所以与圣贤不同者,亦不难见。圣贤直是真个去做,说正心,直要心正;说诚意,直要意诚;修身齐家,皆非空言。今之学者说正心,但将正心吟咏一晌;说诚意,又将诚意吟咏一晌;说修身,又将圣贤许多说修身处讽诵而已。……无他,只是志不立尔。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4]133-134
朱子说圣贤所做工夫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学而时习之”还是“明善诚身”,都是在勉人为学。学问的关键便在于真正去实践圣人所说的工夫,“圣贤直是真个去做”,学者则不免只是空说一番,而并没有真正付诸学问。这哪里称得上是好学不倦呢?学者之为学所以不及圣人,其原因也甚是复杂,这当中固然有因气禀差异所导致的结果:
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辨。圣人则中正和平,无所偏倚。[4]130
常人因其气禀之拘、人欲之蔽而必然有所偏颇,即便大贤如孔门弟子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著名的孔门四科,不同的弟子都有其所擅长的领域,这也即说明他们在其他方面必然是有所缺失的。孔子则必然不存在这样的偏狭,圣人对于每件事、每种道理都做到了然于心,此无他,皆在于圣人之生知聪明与好学不倦。所以朱子曰:
学者是学圣人而未至者,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只是一个自然,一个勉强耳。惟自然,故久而不变;惟勉强,故有时而放失。[4]487
圣人为学,必至乎其极,学者则不免有所欠缺,这就是自然与勉强的区别。圣人因其资禀的纯粹,其在处事应物之初便有一个自然拣择的过程,而当其见到事理之善的时候便迅速地做到了与己心的默契融合: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3]360孟子的“沛然莫之能御”此后成为许多立志为圣贤之学的学者用以自励的话语,但这里的本义其实是在说圣人:
盖圣人之心,至虚至明,浑然之中,万理毕具。一有感触,则其应甚速,而无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3]360
朱子学意义上的“心”是至虚至灵的知觉主体,本来即可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此即所谓“心之本体”。但因为人生即具备形质气禀,故而大多数人的“心”事实上便不能当即完全地具备“道理”,而必须通过后天的格物穷理工夫。在圣人,因其至虚至明的本心并未收到气禀之拘和人欲之蔽的掩盖,所以能够当即自然地达到一理浑然的状态,因而当其接触到善言善行的时候,圣人可以立刻做到默契于心,这个过程就好似江河决堤,“沛然莫之能御”。朱子非常注意此间的差别,因为这个差别不仅清晰地说明了圣人和学者之间,一个“自然”、一个“勉强”,一个“安行”、一个“勉行”的为学工夫上的差异,同时也为学者的修养工夫提供了正确的方式:
问:“‘舜闻善言,见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能御。’其未有所闻见时,气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备,一有所触,便沛然而不可御。”问:“学者未有闻见之时,莫须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曰:“才知持守,已自是闻善言,见善行了。”[4]1442
面对弟子的提问,朱子表示学者的工夫在于“持守”,当持守之时便已经是圣人“闻一善言,见一善行”的工夫了。与圣人“沛然莫之能御”不同,学者之持守好似水库之蓄水,必待水库之水累积到充足的容量,然后方可以收“一旦豁然贯通”之成效。届时滔滔奔流,亦如江河决堤一般,此即学者工夫之效验。因此,“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其实可以推扩到一切为学工夫,包括读书讲明道义、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等等,即所谓“格物”。圣人相对于学者,自可略去“至于用力之久”[3]7的过程,然若学者能够做到,那么“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3]7的境界,则为圣人和学者所共有。至此,我们又当明白,朱子说明圣人和学者在为学方式上有“自然”与“勉强”的区别的目的,仍旧是指向了学者之“学为圣人”。此即所谓“道问学”。学者只有在明了自己与圣人之不同,同时明白自己与圣人之所同,才能勉力用心于圣人之学,在“格物”工夫中向着圣人的理想迈进,而一旦达到,便是成功。
(二)圣人气象
圣人的知识和学问是学者的目标,圣人的境界则更非轻易可以达到,在儒家传统中“圣人”本身即具备极其崇高的含义,这在我们讨论圣人之“知”的时候已经有所说明:圣人不仅仁智兼备,且德业两全,这在学者看来都是轻易不可企及的。因此,在学者“学为圣人”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圣人精神有自己的理解,这对于立志于圣人之学的学者来说是分内之事,是自身学问修养达到一定境界的自然生发,即便是圣人,往往也会如此倾慕往昔之圣人。孔子就屡屡说及三代之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3]107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3]107
这里孔子对于尧舜禹三位圣王的形容都达到了赞叹不已的地步,邢昺说:“大矣哉,尧之为君也!聪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为大,万物资始,四时行焉,唯尧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10]尧舜禹这样的圣王如同天道之广大,化生万物而无所用其心,“四时行焉”。圣人之德与天理为一,有参赞天地化育之功,百姓皆赖其利而不知,万国咸宁而又无能名状。以致孔子只能用“巍巍乎”等惊叹之词来形容他们,因为圣人之德正如天道一般,不可言说。
到了颜子那里,他对于孔子的形容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圣人的境界: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3]111-112
朱子说:“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3]111颜子所以能如此形容者,若非是深喻笃好,绝不能有如此恰切的表达。圣人之道对于颜子来说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如同尧舜之“巍巍乎”,但是所以能如此的方法又不外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极其笃实平常。这正可以与《中庸》里子思对圣人的形容若合符节:
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3]36
“道问学”之本义,是子思对于圣人气象的一种表述。只有对圣人之学有过笃实践履的学者,才会有如此精当的形容。到了理学家这里,“尊德性”与“道问学”仿佛成了两种工夫的进路,这其实是有偏颇的。而在朱子,之所以“道问学”作为工夫之主要进路,亦是因为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作为子思所描绘的圣人气象,是学者无法轻易企及的,那么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作为圣人气象的另一种面向,正如颜子说孔子之“博文约礼”一般,是亲切于学者而容易效仿的。因此,说“道问学”,则“尊德性”自然涵盖于内了。反之,说“尊德性”,虽其全部的内容也依然在于“道问学”,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气象,并不容易进入一般学者之心灵。
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将这样一种对圣人的体认称为“圣人气象”:
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11]76
曾子传圣人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11]145
颜、孟之于圣人,其知之深浅同,只是颜子尤温淳渊懿,于道得之更渊粹,近圣人(一作深)气象。[11]151
如此之类甚多。“气象”并非理学家之首创,孟子即有“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之说,孟子所谓的“气”与理学所言“气象”具有相类的意义。朱子说:
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3]232
气之本体亦源自“天理”之正,乃天地间广大刚烈果决之体段,所谓“浩然”。人生皆有此气。然人物之生,已非义理之本然,也已经不是纯粹的浩然之气,加上后天又失所养,故难得其本体之浩然,必须“善养之以复其初”。浩然之气与血气是同一种气。朱子说:“但从义理中出来者,即浩然之气;从血肉身中出来者,为血气之气耳。”[4]1243可知,所谓“圣人气象”其实就是圣人之“心与理一”所表露在外而能为人所感知体认的精神状态,如同今天说某人“气质甚佳”,也必定是此人内心有某种精神。理气不离不杂,圣人既然义理昭著,也必定发散在外,而这种发散在外的状态就被称为“气象”。因此,在形容“圣人气象”时,常常会联系天地、山川、四季等来比喻,正如天地山川是“天理”在“气化”之中的显现一样,圣人之“理”的表现就是“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的是,理学家们在体认“圣人气象”的时候都经过了自己对圣人之学的深入学习和自身德行的修养,否则是绝对不会产生种种形容之词的。“圣人气象”作为圣人德化的结果,反过来便可以成为学者勤勉学问的方向,这也是尤其重视下学的朱子所关注的:
孔子贤于尧舜,非老彭之所及,……但其谦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辞气极于逊让,而又出于诚实如此,此其所以为盛德之至也。为之说者,正当于此发其深微之意,使学者反复潜玩,识得圣人气象,而因以消其虚骄傲诞之习,乃为有力。[12]1348
大抵圣贤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达,故能春生秋杀,过化存神,而莫知为之者。学者须识得此气象而求之,庶无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离巧曲,瞻前顾后之不暇,则又安能有此等气象邪?[12]1415
朱子以为,体认“圣人气象”的关键在于学者能够“识此气象而求之”,并且可以改变自身的气习之蔽,否则徒有闲说,对于修养是无益而有害的,体认的方法不在其他,正在于体认“圣人之心”。圣人之心的体悟便在于求圣人之经、学圣人之学,而并没有其他妙道,正如颜子之博文约礼一般。如果学者对于“圣人气象”并非真切地体认和由衷的赞叹,则并不为朱子所取,“孔颜乐处”之所以引而不发,正是这个道理:
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3]87
以朱子之学问、之对“圣人气象”的体认犹“不敢妄为之说”,足见其对学者修养做工夫的重要。本文亦不敢对“圣人气象”妄加己意,只是在此说明,圣人的聪明睿智、德行事业所表现而出的状态,即理学家所喜言之“圣人气象”,而朱子在其中所尤为关注的,则是学者如何可以真实感受到这一气象的过程与方法,此即仍旧在于“道问学”。
综上,圣人的学问是“学而不厌”的,因其“气质清明,义理昭著”,而又如此聪明睿智,故其学问是一个自然贯通的过程,其学问的规模和效验,非常人所可以比肩。圣人有如此深远的学问、全面的知识、超凡的智能,再加上圣人本身所具有的本心之全德,这样的盛德大业使得圣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同样令人仰望,此即“圣人气象”。朱子对于两方面义理的阐发皆有所贡献,且朱子所尤为突出提点之处在于:圣人是自然贯通的,学者则需要格物穷理;圣人是仰之弥高的,学者则需要博文约礼。这不仅是学者“学为圣人”的方法,也是圣人之学的本义。朱子理学对于圣人之“知识论”最终所指向的,仍然是学者、是为学,这也是本文一再重复的朱子何以如此重视“道问学”的原因。
三、余论
通过本文对于朱子所体认的圣人之知识、学问和气象,大致可以领会朱子何以如此,并是从何角度重视“道问学”的。这也是本文所希望提供的视角,即:应该将朱子的每一种学问纳入到“学为圣人”的框架里,因为朱子的全幅学问并没有任何一面是外于对圣人的体认的。同理,在朱子,“道问学”亦并非孤立的一种学问,而自然地收摄在其全部学问之中。如同在圣人那里,知识、学问和气象也并非独立的一类特质,而当然地作为圣人的一个面向而存在。无法做到极其聪明、极其好学、自然贯通且气象昭著的,必定不是圣人。既然如此,学者欲达到“学为圣人”的目标,岂可轻易企及?“学为圣人”作为理学所标榜的精神,自是难能可贵,不仅一改章句宿儒之规矩,且使得儒学重新成为学者心目中修养工夫之归本,而非原来的佛老。但同时,“学为圣人”作为一种精神或者目标,也极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圣人是轻易而可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此理固然,但并非意味着“可以为”的距离是可以轻描淡写甚至于忽略不计。理学之后的发展正好存在着这一危险:如果“学为圣人”不再成为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仅仅是学问下移的借口或是代言,则绝非理学先驱们之初衷,在朱子更是尤其不可。朱子所以如此重视“道问学”之原因亦在于此。“学为圣人”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这依旧不妨碍圣人之可为。对于朱子来说,“学为圣人”之关键在于激发并落实每一个学者扎实于“下学”的工夫,至于能否成圣,此并不必成为一个额外的课题。因此说:圣人之学,尊德性而已;然其所以能尊德性者,则惟在于道问学。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心学家如王阳明那里,他对于“道问学”工夫的批判,也同样是出于对可能存在的外于“圣人之心”本身而可能存在的一种所谓“道问学”工夫:
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2]19-20
圣人之经究其根本,皆是圣人之心而已。若能明白在“心体”上用功,则读书自能有得。若只是“为旧时学问”,也即章句训诂之类,则尽管能够“明晓”,却“终身无得”于心,因其将“圣人之心”与“圣人之经”分为二物。可见,阳明所反对的,是将“圣人之经”视为“圣人之心”外的另一种学问,而绝非反对读经本身,也即并不可能去反对“道问学”。只要明白“道问学”与“尊德性”从根本上是一个,则可以避免类似危险的发生。当然,朱子的那种遍解群经的“格物穷理”之精神,恐怕亦是阳明所不取的。阳明的疑难在于:那样的一种用力于文字经籍的“道问学”工夫,很可能让学者在此过程中迷失“心体”,从而导致“心与理为二”的后果。这其实也是阳明批评朱子的最主要的原因。只是显然,在朱子那里,他并不认为二者是矛盾的,朱子同样不认为“心体”之外复有所谓经典,从他将《尚书》看作古圣先王之心法,所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就可以知道,朱子同样是将自己的解经工作看成是体认“圣人之心”的过程。所谓格物致知,其所以“致”者,无非就是本心之知而已。只不过,心本于理,而理即存在于圣人之心,圣人之经也即是圣人之心的表征,故而解经作为“道问学”工夫的一种,又焉有所谓“心与理为二”的危害?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学者的一切“道问学”工夫皆是导源于圣人、导源于圣人之知、导源于圣凡之不同,故而学者“道问学”之工夫,也就是对“圣人之心”的发明。
文章的最后,引用孙星衍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为书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迄于嘉庆廿年。既有厥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寿命之不长,亟以数十年中条记《书》义,编纂成书,必多疏漏谬误之处。然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经学渊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极,聊存梗概,以俟后贤。或炳烛余光,更有所得,尚当改授梓人,不至诒讥来哲也。[13]
文中所言“为书”乃是《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星衍之解经自然不取宋明儒,然而朱子的那种“道问学”的精神,已经融入宋后八百年学者的生命中。解经自是格物事,然此事随人之精神、智能皆不免有所“止境”,非一人所能究极。能成就“道问学”之完整规模的,必然只有子思笔下的圣人。至于学者的责任,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用自己的全幅生命去体认,贴近圣人之经、之心,惟恐寿命之不永,更争炳烛之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