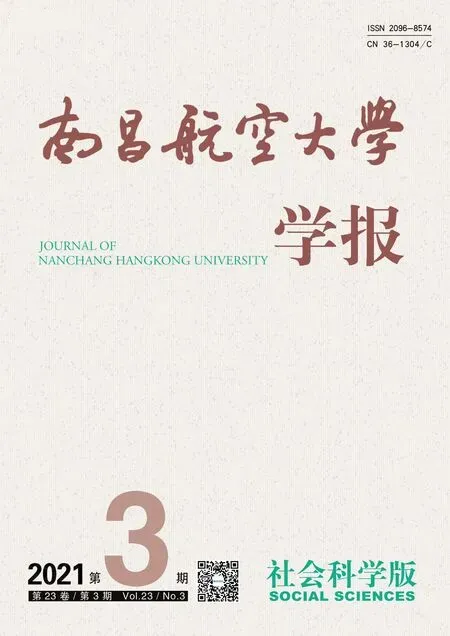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意蕴
崔明海
(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伴随着汉字改革问题的提出,倡导语言统一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逐渐合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语”和国民学校“国语”科目的确立(“国语”是近代中国对汉语标准语的一种官方称谓),为此后的语言统一运动奠定了基础[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推广民族共同语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要继续完成的 “政治任务”。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决议提出,要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2](217)。1956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出推广普通话的指示[3]。这标志着党和政府正式开启了利用国家力量来开展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推广普通话是一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语言政策。目前,学术界侧重于从宏观角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政策演变和发展历程[4],但对这一语言政策的起源研究稍显薄弱。本文拟从历史学和语言规划角度揭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此项政策的社会语境、构思过程及其政治意蕴,探析推广普通话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深化这一时期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
一、方言纷歧与新社会
千百年以来,人群迁徙、地理阻隔和政治经济的分治造成了方言纷歧的现象[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方言隔膜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次第召开,但方言不同影响了代表们在这一政治公共空间中的思想交流。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方言特别复杂的省份,开全省性的会议好像是开“国际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但少数民族代表的发言需要翻译,很多来自不同方言区代表的发言也要翻译或请人代读。许多重要的报告,因为报告人方音较重,听的人不能全懂,效果打了折扣[6](320-321)。在基层社会,对于不识字的工农群众而言,见字是 “看去花花,摸去平平”,文字的宣教功能大大削弱。所以,口头语言是党政干部和基层群众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如果双方语言不通,必然会影响地方各项工作的开展。当时浙江杭县内区与区、乡与乡之间都有不同的土音,方言隔阂较大。来此地开展工作的大都是从北方来的同志,他们听不懂当地老百姓的话,当地人也听不懂这些同志的话。下乡工作都要带翻译,请当地人做“汉语翻汉语的翻译员”[7]。在广东工作,语言交流上存在着更多的障碍。李永是东北人,1951年到广东新会参加土地改革,由于语言不通,工作上感到不方便,只能请 《人民日报》国际部的谭文瑞来当翻译。由于语言不通,干部在了解基层情况、联系群众方面都有很多困难[8]。
党政干部和群众之间语言不通,不但大大降低政治宣传效果,甚至会给工作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福建省大田县有闽南话、大田话、龙溪话等十余种方言、土语,出门三、五十里方言就互相听不懂。当时来大田县农村工作的,也是北方南下的干部。南下干部用普通话作报吿,群众都听不懂,听不懂就在会场上打瞌睡。所以,在当时的群众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不懂听普通话,好像鸭子听雷轰”[9], “社会主义无限好,张耳聋子听不了”[10]。大跃进期间,四川省叙永县召开四级干部会,几个干部在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吿后,分组讨论,大家都开不了口,因为没有听懂报告,好的也只听懂一半,连积肥、生产指标和措施都不知道,只好请乡总支书记重新作一次报吿。在抢收小麦和大搞甘薯化的劳动过程中,叙永县五星社主任在乡里开会,听了农业技术指导站干部的发言,由于听不懂方言,回来传达错了,造成返工事故,浪费了近50个劳动力[11]。
相比于作政治报告这种近距离的口语宣传方式,广播则实现了远距离的声音播送,但由于方言障碍,这种宣教工具常常不能发挥它的“现代化”作用。浙江温岭县玉怀广播站每次在广播时都要用四种方言播讲,浪费人力。江西省婺源县是一个山区,交通闭塞,与外界很少接触,群众没有说普通话的习惯。一些公社里虽安装了广播,但群众反映,“山沟里盼来了广播筒,可是挂在那里根本没有多大作用”[12](121)。因为广播里用的都是普通话,群众听不懂。这些都是方言纷歧影响政治建设的种种表现。
“一五”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开始实施以后,语言不通阻碍了工农群众之间的交流,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鞍山的炼钢能手调到武汉建立新钢铁工业基地,上海、浙江的技工分配到兰州、新疆去办工业。如果各地工人都保持自己的方言土语,就会妨碍交流,影响工农业生产。徐永钺是一位浙江的农业工作者,1954年被分配到西北工作以后,由于方言的关系,给各项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事都笑他说的话跟外国话一样,农民也听不懂他说的话,几次下乡做调查工作,只能把农民听不懂的话写在纸上,但是广大农村中文盲很多,用“写”代替 “讲话”太耽误时间,也不太现实[13]。当时各地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改进生产技术,需要跟外面交流经验,要请外地的技术人员来帮助生产,如果语言不通,也会发生困难。广东白蚁专家李始美来北京报告治白蚁的经验,因为他不会说普通话,只能用广东新会方言讲,北方人又听不懂,只好请人一句一句地翻译[6](320-321)。江苏昆山县组织乡社干部、技术骨干到南京、北京等地学习技术、参观农具展览会,很多人不会讲普通话,学习效果有限[14]。1958年,苏南农民200余人来新沂县传授种植水稻技术,因语言不通,工作发生很多不便。江苏省新沂县多次组织乡社干部到外地参加访问,有时因方言隔阂,大大影响了学习效果[15]。在工农群众中推广普通话无疑有利于工农之间的交流,推动工农业生产和技术推广。
在文化教育方面,方言隔阂同样影响到教育工作的开展。北京某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因为说方言,学生听不懂,成绩大受影响,家长有意见,教学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武汉办了一所专业的学院,教师来自江苏、浙江,学生招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教课、听课都大感困难[6](316)。江苏境内方言复杂,苏南分配到苏北的师范毕业生不能安心工作,言语不通是其中一个干扰因素[16]。由于语言的不统一,浙江温岭县双龙小学教师在课堂内曾讲三种不同的方言(福建、温州、台州),这样才能使说着不同方言的学生听懂课文内容[12](121)。汉族方言的严重纷歧也让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时无所适从。海南岛的黎族青年到广东学习,学会了广东话,到武汉就用不上了,再到北京又不得不重新学起。同一个汉字,北方老师和南方老师的发音各有不同,弄得学生不知对错。这种方言混乱的情况增加了少数民族青年学习汉语的负担,他们也迫切希望能掌握一种在全国通行的共同语[2](102-103)。
方言纷歧亦不利于军队建设。1955年7月,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实行义务兵役制。义务兵役制实施之后,新兵来自于全国各地,必然加重方言纷歧。如果不统一语言,在军政训练、日常工作和执行任务上,将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部队中,无论下达命令、传达情况、指挥作战、口头报告和打电话,都要求话一说出来官兵就能理解[17]。士兵都要在一个号令下训练和准确地协同作战,如果语言不统一,就会听不明白指挥员口令,发生误会或是动作迟缓,这些对于作战是非常危险的[2](121-122)。某团兵源大部分来自广东和广西的农村,新战士半数以上听不懂普通话。干部向战士作了训练动员后,又开了三天讨论会,但是许多广东雷南籍的新兵却一言不发,问他们今年的训练任务是什么?回答却是“有叭”(不懂)。有的新兵不知道怎样回答,甚至急得哭起来了[18]。所以,在部队中推广普通话,不仅有助于发挥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力量,对于国防现代化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语言既是交际工具、信息工具和认知工具,也是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政治资源[19]。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恢复了国民经济,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一个集体化时代。由于方言纷歧与社会制度、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党和政府需要通过推广普通话进行语际整合,解决方言隔阂问题,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正如郭沫若所言:“我们国家正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进入了日益广泛的集体生活和共同劳动,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一个规范明确的统一的民族共同语。”[20]
二、普通话与汉字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的问题,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提出的汉字拼音化的主张,作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重要指示[21]。党和政府提出了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务。不过,推行拼音文字需要有标准语。如果依照方言制作拼音文字,则会使文字失去统一的社会交际功能。自古以来,“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22]。汉字对中华文化赓续发展和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在语言不统一的条件下,表意汉字是一种最方便而又能团结民众的超方言文字。当时不少人担心汉字拉丁化之后,文字不统一,会引起国家分裂。张元济就曾向毛泽东进言:“若改用罗马字母改切汉文,则各省以字母、以自有之方言切成自有之文字,东西南北必不相同”,“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23]党和文字改革工作者当然也注意到此种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党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左翼知识分子曾主张“方言拉丁化”,也在一些地方试行过方言拉丁化新文字。作为临时突击办法,抗战时期方言拉丁化运动服务于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党和文字改革工作者主观上是想利用方音字母尽快扫除文盲,传播革命文化,更为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并不是想制造文字分裂。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之后,考虑的问题和立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考虑的是国民文化的普及和文化水准提高的问题,是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是统一的民族语文的建设的问题,是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问题”[24]。支持文字改革的郭沫若、马叙伦等人这时也意识到“方言拉丁化之推行对于统一的国语之形成,将是一种阻力”,不同意方言拉丁化的语言政策,主张推行“国语”[25]。
1950年6月间,苏联《真理报》发起了对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批判,斯大林提出了语言文字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26]。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交流过语言文字的问题,他也赞同斯大林的观点[27]。语言具有全民性的思想对中国语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成为党制定“推普”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文字改革工作者所主张的汉字拼音化并不是要拼读各地方言,创制各种方言拼音文字,而是要拼读一种标准语,推行一种标准化的拼音文字,作为国家统一使用的文字,为全民服务。所以,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吴玉章指出,“使汉语语音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且逐步扩大这个统一的标准语音的使用范围”是汉字拼音化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28]。胡乔木也说,“如果我们的汉语没有一定的规范,没有一定的标准”,“要对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进行根本改革,要把它变成拼音文字,那是很难想像的”,只有使民族共同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有了明确的规范,人民才能使用普通话,汉字拉丁化才有可能实现[29](105-106)。毋庸讳言,在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构想中,推行普通话也是为推行汉语拼音文字作准备的,这也是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提出推广普通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知识分子对于汉字拉丁化问题争议较大,推行拼音文字的主客观条件并不具备,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之后,党和政府也只是将拼音字母作为统一读音、认识汉字和教学普通话的工具,并不是要取代汉字[30]。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调整了文字改革的方向,放弃了汉字拉丁化的政策。
三、普通话与治国理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上实现了近代以来所没有过的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集体化生产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种民族共同语来“调节我们共同的意识和行动”[31]。从语言政治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将党的意志传达给人民,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成一致的行动。正如胡乔木所言,“我们全国人民是在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下,要把革命的统一意志能够有效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就得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工具”[29](157)。方言虽然在地方上有利于民众的交流,但限制了思想传播的地域空间;就全国而言,在当时全国人口识字率较低的情况下,方言隔阂降低了广播、电影等现代化媒介的宣教功能,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障碍。因此,推广普通话就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可以借此塑造民众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和政治认同。当时流传甚广的歌曲就较为通俗形象地表达出“推普”政策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影响:“我们的祖国辽阔广大,六万万人民亲如一家,要使人人都说普通话,团结更紧力量更加大。学会普通话,走遍全中华;文字大改革,人人学文化。思想更统一,处处如一家,科学大发展,建设新国家。”[32]
党和政府要求群众学习普通话,其背后宏大的政治目的就在于要培养国民的“整体观念”“集体主义精神”,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可以说,在当时文字改革计划之中,推广普通话既是为汉字拼音化服务,也是党试图通过这一方式把松散的群众纳入国家的构成之中,“使劳动群众有可能参加全国一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利用普通话作社会交际的工具,来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的生产,更好地过文化生活”[6](31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正是认识到推广普通话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党中央是非常重视普通话推广工作的。1955年5月6日,刘少奇在接见吴玉章听取关于文字改革工作汇报时强调,汉族要有统一的语言,学校要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可以考虑作出这样的规定:“老师在一定时期内学会普通话,今后凡是不会讲普通话的,不能当教师。”[33]1957年12月,毛泽东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谈到干部学习普通话的问题。他认为言语通不通, “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也要教育群众学普通话”[34]。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集中讲解工作方法问题,并再次强调:“干部要学本地话,学普通话,学英文。”[35]会后,毛泽东根据讲话提纲和南宁会议的讨论内容,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明确指出,随着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取得了基本胜利之后,为了适应一个新的生产高潮,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需要作出改变。其中,干部需要改变的一点就是“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36]。党政干部带头学习普通话,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转变,更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1956年以后推行普通话收效颇大,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推广普通话所发挥的政治功用,“提倡普通话,这很重要,收效最大,对国家统一团结有好处”[37]。
在新中国语言规划中,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或者是要消灭少数民族语言,去追求政治强制下的语言统一,对于这点,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的政治和文化自觉的。胡乔木曾指出,方言的消灭和趋于淘汰是一个长时期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 “没有什么强制,没有实行粗暴的方法的可能”[29](119), “语言的发展不能用暴力和强制的力量去推行”[29](144)。周恩来也认为,推广普通话,为的是“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38]。不能用政治权力去禁止方言,并不代表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广普通话,“要推广一种标准,它完全可以并且应该采取行政的方法”,采取许多措施去推广普通话属于“行政的方法,是政府的活动,特别是教育活动的领域”[29](146)。
实际上,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是一种“二重”语言制度,也就是汉族除了学习本地方言之外,也需要学习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并不是禁止方言,而是使说方言的人们在自己的乡音之外,学会说一种全民族共同的语言,以便跟各地区的人互相交际”。当然,提倡学习普通话也不是“大汉族主义”,与提倡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民族政策并不冲突。推广普通话主要是在汉族人民中推广,并不强制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但是,考虑到各民族间的互通交流,一方面,“在兄弟民族中可以而且应该提倡学习普通话,并且对自愿学习的人应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兄弟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但应该尊重兄弟民族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的权利,而且必须努力学习兄弟民族的语言”,这样
“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团结和互相学习”, “也不会损害我国宪法赋与的各兄弟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39]。从这个角度而言,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
由于普通话是汉族内部以及各民族间社会交际的语言工具,发挥着团结国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国家的政治功能,推广普通话作为一项重要的语言政策延续至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1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规定 “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也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央政府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也倡导“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40]。这种“二重”语言政策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辩证统一的治国理政思维,有利于保证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又能照顾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自身的发展空间,推动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