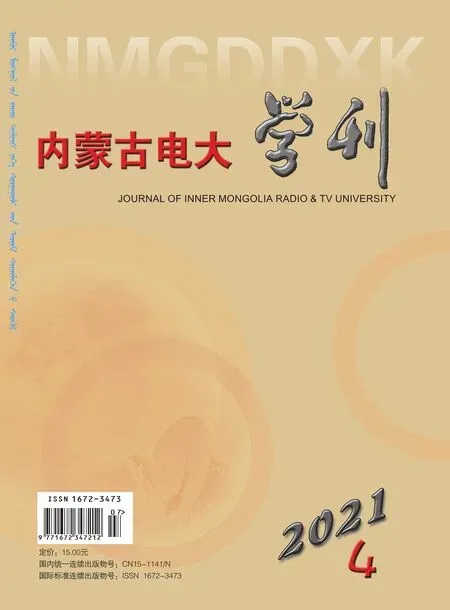元儒吴海生平述略
王贵连
(集宁师范学院 政法与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集宁 012000)
吴海,字朝宗,号鲁客,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世称闻过夫子。《明史》将其收录并列入“隐逸”类,《闽侯县志》《闽县乡土志》《乌石山志》《福州府志》《新元史》等视其为元人,今人普遍将其归入元遗民,今从后者。吴海自幼勤思力学,精通《尚书》《礼记》,喜好考证古制,“致力于传承发扬朱熹理学,对元末明初闽中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P97本文依托史料,立足实际,主要从吴海的生平事迹、交游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进一步探寻其非凡的一生。
一、生平经历
吴海的生平经历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自幼汲汲好学,笃志博闻,造诣精深;鼎革之际隐居林泉,不慕荣利,著书立说;平生乐善好施,劲节清操,泽被后世。
(一)笃学纯懿,造诣精深
吴海生于书香世家,按照吴氏家谱记载,在唐朝光启年间,先祖吴英举家由光州迁入闽地,被尊为闽地吴氏始祖。吴氏家族向来人丁单薄,吴海曾祖曾中进士,被任命为宁国府知录,生有二子,幼子无嗣。吴海祖父有子四人,长子和幼子无嗣,次子仅有一子。吴海父亲英姿卓识,敦行尚谊。海生母高氏,秀外慧中,知书达礼,吴海在双亲的悉心教导下,才学日进。九岁时,父亲殁于易代之际,其母仓促弃产,携幼子避入古灵山中,依靠外祖父资助度日。其胞弟次宗,工于翰墨,曾任福宁监税,因身逢乱世,壮志难酬,遂退隐不仕。吴海姐姐嫁与望族郑氏之子,在二十六岁时难产去世,生有一女。宗侄克成,高怀质行,能诗善书,所作诗文淡雅静敛,堪称一绝。吴海育有一子吴榘,早殇;一女,嫁给其弟子林公伟。
吴海少负逸才,聪颖睿智,师从慎独先生陈植研习周、程、张、朱之学,学养极为深厚,《宋元学案补遗》将其列入陈氏家学。元朝末年烽鼓不息,吴海决意归隐山林,精研经史各家之学。其人质朴少欲,有东汉名贤之风,深受学界名流贡师泰、林泉生诸君推崇。
吴海一生学术丰厚,著有《葬书》《厚本录》《自试方》等作,然大多散佚。现存的代表作《闻过斋集》八卷,内容丰富,文辞凝练,议论通达,运意精深,是后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该文集中既有关于地理山川、风情人物的详明记载,又有对时政得失、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观评述。无论诗词歌赋、序言跋文、墓志铭及权厝志,都力求保存史实,为探究元末明初鼎革动荡之际的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治学注重阐发义理,弘扬仁德善行。他强调“善一日不积则隳,一念不继则怠。成者易毁,隳者难全,甚可畏也”[2]P179。吴海提出人性本善,仁德为先,人人都应心怀善念,广施善行。推此及彼,他又从历代王朝盛衰的经验中总结出,君主治理国家需以仁义为本,爱惜民力,矜恤贫苦,方能天下大治。
在闽士“不以浮文胜质为先”[3]P494思想的影响下,吴海治学崇实黜虚,注重实用,讲求实效,反对空谈。他十分重视地方基础文化教育,明确提出“乡闾实为首教之地”。同时大力提倡选拔人才应该不拘一格,不论出身,量才任用,务尽其用。吴海努力践行自己的治学主张,曾多次慷慨解囊,出资修建闽县学舍。他在潜心著书的同时,还致力于提携后进,培养人才。“对邻里子弟不收学费,仅于案侧置一竹筒,来学诸生日投一钱,集中购买灯油,以供夜晚自习之用,人称‘一文先生'。”[4]P123此外,博赡尚古也是吴海治学的鲜明特征。在结亭栖隐期间,吴海专心阅读古史,尤其注重钩稽历代兴废成败之因,爬梳濂、洛、关、闽诸家散佚的经说,将自身治学的感悟体会凝聚糅合在著述之中,意在鉴古寓今。
(二)戢鳞潜翼,思属风云
吴海素有山水之癖,很早开始四处游历,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他曾瞻仰三山五岳之雄伟,江淮河海之壮美;亦感触过古贤圣人之遗风,英雄豪杰之余迹。在游旅途中,每遇风景绝佳胜处,辄伫立不徙,灵感大发,吟咏诵唱。元统甲戌(1334)年,吴海在泉州以十金典质上古名琴霜钟,并特意著文《琴赞》用以纪念。霜钟琴声悠扬清越,如珠落玉盘,铮铮琮琮,婉转动听。吴海在闲暇之余,经常抚琴自娱,在袅袅琴音中品味清雅淡泊的心境。
至正壬辰(1352)年,红巾军攻打江西,涿州人卢明安随父从戎应战。明安资质英敏,作战英勇,受到朝廷褒奖。父亲去世后,他便举家返居豫章城。至正戊戌(1358)年,陈友谅率部攻陷豫章,卢明安被围困后无畏赴死。其妻刘氏听闻噩耗亦投池自尽。当时有人讥讽明安身死无名,枉送性命。吴海愤然反驳:卢明安身无守官之责,面对强敌,却毫无惶遽失措之态,视死如归,难道不值得敬仰称颂吗?那些嘲讽明安的言语,着实令人痛心!
至正乙巳(1365)年九月,同郡黄伯弘约吴海、程伯崇、徐宗度游览闽江北岸名胜鼓山。四人在河边买一小舟,顺流而下抵达白云廨寺,赏玩半晌后,穿过东漈石桥,到达圆通阁。阁外疏竹斜印,幽林青树,苍翠欲滴。倚栏远眺,对面高山上有白瀑悬空,奔泻而下,如白虹游龙萦绕长洲。四人看着巍峨山川和奔腾河流,不约而同发出景物虽同,然人心已变的感慨。吴海叹曰:“是游岂徒登览之娱,有以散其忧愁拂郁之思,发其豪宕雄逸之气,重其治乱兴亡之感,而岘首之悲,牛山之念,仰止之慕,虽吾四人者,亦讵能尽同也。”[2]P185
至正丁未(1367)年,江东宪司燕经历驻于闽地,因缘际会与吴海相识。当时红巾军南下,直逼江淮。与江淮相接的浙闽地区兵力疏散,不能发挥牵制作用。行御史台的守臣推荐知晓江浙地形风情的燕经历前去京师详陈虚实利害,搬请援兵。离别之际,吴海为其饯行,并叮嘱道:古今天下之事,都有最佳时机。抓住时机,顺势而为,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以右丞相脱脱征讨张士诚为例,向燕君述陈延误战机造成的严重后果。脱脱在督伐高邮快要成功之际,由于权臣哈麻心生嫉妒,以“劳师费财”唆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致使皇帝听信谗言,削其兵权。临阵易帅向来是兵家大忌,脱脱的去职直接导致元军调度失灵,不战而溃。然后,吴海话锋一转,直抒胸臆:治理国家虽需抓住机遇,却更应重视民心。海隅之民长久苦于赋税沉重,刑罚严苛,吴海希望燕君进京谏议朝廷在体恤民情、稳根固本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图谋发展。
元治天下,垂及百载。至于末年,纲纪废弛,民生凋敝,人心涣散,社会动荡不安。吴海一针见血地指出元朝覆灭绝非偶然,受时代所限,他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士大夫心术不明,欺上瞒下,导致亡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之根本,但元末官爵猥滥,贪墨成风,老百姓无法忍受层层盘剥,不断进行起义反抗,亦是不争的事实。吴海对天下走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坚持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进将施利泽于人,退而避祸难于己。在攘攘之徒钻营兢进,谋求高位之时,吴海淡然自若,抱盎灌畦,坚守理学家的信仰,令人敬仰不已。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求贤若渴,派使者去全国各地搜罗人才。吴海才茂学富,名动浙闽,使者多次前往拜会,希望他能够效力新朝。吴海婉言相拒,指出朝廷寻求贤才,以期稳固统治,士人怀才,是为有用于世。“虽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怀才者绰绰有余,其志实常相通,未有礼意俱至而不就者也。故有材不适用,用不适时,徒取古人之道自娱,而不可施诸人,则不敢应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强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谊也。”[2]P223再者,吴海认为自己年老体迈,遇事疏拙,不擅于处理复杂多变的人情世故,在先朝时期就飘然远翥,隐居山林。加之母亲年近九十,疾病缠身,需要精心照料。综括而言,“非不欲进,不敢进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
(三)崇文重教,恩泽乡里
洪武庚戌(1370)年三月,前将乐县典史林士志辞世,因家贫灵柩不能返回故里。时值盗匪焚掠民舍,士志灵柩被毁。其子文玉,收敛先考遗骸葬于南原,持行状拜谒吴海,请为父铭。念及往昔,吴海哀恸万分,赠予文玉不少银两,并撰写墓志铭深情怀念林士志。士志,字仲嘉,福建闽县人,生有宿慧,孝友惇睦。最初举孝廉,被选为宪府书佐,继而在福清任职,历任漳浦照略,将乐典史等职。其为官克己奉公,高风峻节,深受长官器重和百姓爱戴。吴海在《故前将乐县典史林君墓志铭》详细介绍了士志的生平事迹,并对其生不逢时的坎坷遭遇感到十分惋惜。同年十一月,吴海安葬先妣浯州令府君宜人杨氏、生母高氏、兄弟次宗、殇子吴榘于怀安县鸡心峦。看着至亲墓边的苍松翠柏,吴海不胜感怆,挥泪而作《鸡心峦墓祭文》以抒哀思。
吴海认为自魏晋以来,异端权谋术数之言横流于天下,圣人之道晦而不彰。
他表明要扭转这种状况,使“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必须提升学校的地位,推动学校教育不断向前发展。学校不仅能够传递学术、培育人才,还可以起到移风易俗,促进国泰民安的作用。乡学作为前沿阵地,首先发端于周代,从汉朝开始,地方州郡普遍设有乡学。而闽地乡学在经历了唐和五代的萌芽、两宋的兴盛之后,在元明时期继续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福建长乐县在宋朝时曾由英德府学教授林垓的儿子出资建立乡学,由于年代久远,长乐乡学已废弃将近百年。林氏后人林文溢为发扬先祖美德,继续造福乡里,于洪武己未(1379)年开始在祉溪阳面的阜林重新修筑礼殿和讲堂,讲堂左边是学舍,右边是供奉先贤的祠堂,一年后阜林乡学如期竣工。吴海与乡绅李麟等人亦出资为学校购置乡田,又雇工修缮乡田前面的大湖,并将每年所产的茭渔之利交于乡学。此举不仅利于克复三代之德,弘扬前人之功,又能教化乡里,造福百姓,实乃功德一件。
为了能让学校真正发挥培养栋梁之材的功能,实现倡明圣人之道的教育理想,吴海提出几点建议:一方面,学校应该广延名儒,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为人之道,同时还需开设一些实用课程;另一方面,学子应该树立高远之志,积极进取。在目标确立之后,就应该脚踏实地,身体力行,仅仅坐而论道,凌空蹈虚,虽多无益。此外,治学还贵在坚持。一日无书,百事荒芜。正所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洪武癸亥(1383)年,吴海寓居闽西苦竹山,听闻漳浦文学章宗远的嘉行懿事,遗憾未能早日结识。后宗远遣子章棣宴请吴海,几人在其书房近道斋内互相切磋,探讨学术。章棣英姿勃发,敏而好学,向吴海请教治学之道。吴海指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者,乃为学之要道也。”[2]P210他认为学问之道,旨在博学精思,贵在实行实用,重在有功于世,那些粉饰自身的空洞学问,对提升个人的修养、对促进国家的发展毫无用处。
关于吴海的生卒年,目前学界没有统一定论,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有:陈囯代《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认为吴海生于1322年,卒于1386年;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李士金《理学思想内涵精神分析》认为吴海生于1322年,卒于1387年;傅璇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张成德《中国游记散文大系》认为吴海生年不详,卒于1386年;李学勤、吕文郁《四库大辞典》、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等认为吴海生年不详,卒于1390年。
笔者翻阅搜寻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大量资料以及吴海《闻过斋集》中的相关记载,发现一条史料:“元统甲戌,予以十金质一太古琴,名曰霜钟。”[2]P238若按其生年为1322年计算,至元统甲戌(1334)年,吴海年方十二,且吴海九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没有经济能力以十金质买名琴,而霜钟的主人亦是由于家贫才不得不将之典当,再仔细研究《琴赞》的行文语气,吴海不可能生于1322年,是以笔者初步认为吴海生年大致在1310年以后,1322年之前,卒于1387年,葬于怀安县恭顺里鸡心峦。
二、平生交游
吴海治学讲究博采众长,注重知行合一。平生喜好交游,与贡师泰、林泉生等名公硕儒相交甚笃,并常与友人遍游各地,徜徉于山水之间,从中汲取灵感和智慧。经过亲身实践和好友的启发,其学问愈加精进,堪称“元末闽中理学的中坚人物”[5]P100。
(一)显宦巨卿
王翰(1333-1378),蒙古名那木翰,字用文,元代西夏人后裔,赐姓唐兀氏。王翰先人世居齐地东阿、阳谷,其曾祖跟随名将昂吉儿作战,因骁勇善战,功勋显赫,受封为武德将军,镇守庐州。此后三世,王氏先祖均葬于庐州,故不少史籍中多称他为庐州人,其祖父、父亲皆以恩荫袭爵。王翰十六岁时承袭父职,由于治军有方,开始在军政界崭露头角。平章燕赤不花镇守闽地时,征辟王翰为从事。后来升迁为理问官,总理永福、罗源二县事务。当时的泉州恶霸柳莽飞扬跋扈,聚众越境奔袭永福,众人束手无策。王翰迅速抽调兵力,严阵以待,柳莽不敢向前,退兵而去。不久之后,朝廷拔擢王翰为朝列大夫、福建江西行省郎中。平章陈友定驻守闽地期间,王翰在其麾下出谋划策,深受重用,友定上表朝廷封王翰为潮州路总管,兼督循、梅、惠州。翰生有三子,分别是王偁、王修、王伟。
王翰在任期间颁布重文宣教的政策,亲自督建韩山书院和潮州三皇庙学,为潮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王翰平居嗜阅书史,精通篆刻,在今广东潮阳地区仍留存有多方石刻。入明后,隐居永福山中,自号友石山人,著有《友石山人遗稿》。他与吴海志趣相投,交往匪浅。吴海《闻过斋集》中有多篇文章对王翰进行了客观详细地介绍,其中包括《王氏家谱序》《友石山人墓志铭》《友石先生传》《友石山人真赞》《送王潮州叙》《王山人哀辞》《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墓志铭》《潮州三皇庙记》《游上林记》《仰高楼记》《悠然轩记》等,为后人研究王翰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宝贵资料。
林泉生(1299-1361),字清源,号谦牧斋,永福人,仕至翰林直学士。其先人世居济南,永嘉之乱时,先祖林披为避战乱携家眷迁入福建莆田。至唐朝时期,先人林攒为福唐尉,林蕴为西川节度推官,以孝烈载入唐史。一门宗族九人,皆显耀非凡,世称九侯林家。后来莆田林氏分支为福清林氏和永福林氏,泉生一脉属于永福林氏。其曾祖炎发、祖父君泽、父亲士霆皆官居高位。泉生于至顺庚午(1330)年高中进士,赐袍笏,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开启宦途生涯。在任职温州路永嘉县尹时,诛锄豪强孟某等地方势力,大快人心。当时永嘉赋税沉重,致民破产。泉生采用变通之术,在集衢要地置局四处,由官府自负盈亏,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减轻了百姓负担,可谓一举两得。同时,筑造新河埭坝,大大提高了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在主管福清州事期间,设立义仓,派专人掌管,规劝富农将粟稻借贷给穷人。并且整饬军务,大大提高部下战斗力,受到平章政事阿鲁温沙的嘉奖。
泉生博学明经,所作诗文颇丰,著有《春秋论断》《诗义矜式》《觉是集》《观澜集》等。吴海称赞其文叙事明洁,运意精深。林、吴两家是世交,泉生与吴海渊源颇深,交往甚密。吴海《与林待制清源书》《觉是先生文集叙》详述了二人交往之经历。泉生去世后,吴海作《元故翰林直学士林公墓志铭》等文怀念友人,寄情甚深。
韩准(1299-1371),字公衡,济州沛县人。祖父韩润,累赠嘉议大夫、上轻车都尉、南阳郡侯。父亲韩彧,累赠中奉大夫、河南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南阳郡公。韩准少承庭训,勤奋好学。二十岁登进士第,授承事郎、为孟州同知。当时孟州发生大饥疫,韩准因施赈救灾有功,被朝廷拔擢为河南儒学副提举,又转任奉训大夫、佥河南北道廉访司事。当时河南有大量陂田,但因黄河泛滥成灾,屡次冲垮陂田,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韩准甫一到任,即率领民众修建堤坝,等到秋收时获粟数千斛。后任南康路总管,当时的南康经常爆发战火,城内荒废萧条,韩准出资招募民众搭建草屋作为公署,击奸捕盗,平理冤狱,政绩斐然。洪武辛亥(1371)年,韩准身瘿疾病,卒于福州光泽里寓舍。
韩准生性俭素,广阅众书,有《小学书阙疑》《水利通编》藏于书室。又颇好交游,与吴海契若金兰。韩准去世后,其子泣谒吴海,吴海感于韩公宿德众望,为其撰写权厝志进行祭悼。其铭曰:“行务实,不几以文昌。政为循,不几以名扬。气直以刚,又静有常。遭运之倾,其节益彰。”[2]P217
秦裕伯(1296-1373),字景容,号葵斋,又号双谷,松江府人,积功升官至福建行省郎中,为北宋词人秦观八世孙。其祖父秦知柔曾任中书省肃政廉访使等职,后举家搬迁至今上海陈行乡闸港。父亲秦良颢学行过人,年轻时奔赴学术中心大名府求学,受业于蒙古学大师萧氏,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蒙古学专家,编有《纂通》一书。又搜集师言,兼采他说,辑成《一贯》。大德年间,被委任为国子监学录,后又擢升为浙西道榷鹾使,主掌盐政。
裕伯天资颖悟,善为词说。与其弟亨伯合称“二秦”。至正甲申(1344)年高中进士,被授予湖广行省照磨之职,负责核对文书卷案。后来改调为山东高密县尹,在此期间,他适时调整赋役政策,及时施行赈济措施,并重修孔庙,深得民心。入明后官拜治书侍御史,任职期间,“博辨善论说,占奏悉当帝意,帝数称之。”[6]P7317裕伯襟怀洒落,与吴海相处融洽,彼此频传书信,研讨时事。吴海《与秦景容书》《双谷序赠秦景容》是二人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
(二)乡贤名流
傅崇德,字德谦,金溪人。本名倪韬,字伯文。吴海曾在《傅德谦复氏序》里阐明其姓名变化之由来。江西贵溪倪氏、金溪傅氏世代通婚,互为姻亲。倪氏曾香火中断,不立宗人,故将德谦先祖一脉子孙过继为嗣子。德谦本为傅氏,而冒之倪氏,在修撰家谱时颇有难度,遂向吴海倾诉窘况。吴海劝其在修谱时归根溯源,讲明缘由,并建议:“子复故而为倪氏立后,以傅氏女配之,代虽远而系不绝,氏得辨而鬼有归。”[2]P163德谦闳深雅重,不悦流俗,有志于古人淡泊之道,与吴海是莫逆之交。在傅德谦归还临川之时,吴海作诗送别友人:“相知宁苦晚,不觉逾三春。精微共探讨,议论发清新,谊合然诺重,途穷忧思频,如何语离别,使我意酸辛。”[7]P1323
程世京,字伯崇,建昌南城人。其祖父程钜夫一生久羁宦海,历仕四朝,官拜南台侍御史,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曾参与编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有《雪楼集》三十卷流传于世。伯崇父亲大本为钜夫第三子,在至正中期为翰林应奉,曾刻印其父《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十卷。吴海经人引见与伯崇相识,随着往来益深,议论愈密,对彼此的了解更进一步加深。吴海在《送程伯崇还江西序》一文中不吝笔墨赞誉伯崇敦厚简言,守直不诎。
郭徽言,福建闽县官贤里人,著名医学家,精通疡医术。自幼秉承家学,熟通医书,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对医学有独到的见解。疡医世称外科,但徽言却认为:“疡虽外,实发于内。必先去其本,然后施疡治,以五毒五药次第攻调之。”[2]P157他治疡应从内科入手的主张,极富创新精神。郭徽言医德高尚,宅心醇谨,对患者尽心医治,不计报酬。其子郭勋,承继父志,亦在闽地行医。徽言与吴海既有同乡之谊,又是通家之好,曾作《赠医师郭徽言叙》等文深情怀念友人。
(三)弟子门人
王偁(1370-1415),字孟扬,号虚舟,明代著名诗人,为王翰长子。其人聪颖善悟,髻龄有志于学。在九岁时,父亲去世,由吴海抚养长大。在吴海的精心教导下,王偁勤身博学,不乐华靡,以读书立品为务。翰嗜好作诗,作为明初闽中诗派的重要诗人,王偁的诗文造诣精深,风格多样,代表作《虚舟集》共五卷,绝句、律诗皆备,收诗四百八十三首,数量非常可观。既有抒发怀古忧思的五言古诗,又有清迥绝俗、空灵静雅的七言律诗。其诗文风发韵流,远近闻名,与林鸿、郑定等人并称为“闽中十才子”。当时文坛又有“词林四王”和“东南五才子”之称,偁亦名列其中。吴海去世后,王偁耗费大量心血将恩师著作《闻过斋集》刊刻成册,并附有跋文。王偁不仅博学多才,在事功方面亦颇有成就。“初为名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授地官主事,擢副郎出守袁州。”[8]P5永乐癸未(1403)年,被授以翰林检讨,进讲经筵。不久之后,又被任命为编修《永乐大典》副总裁,后受解缙案牵连下狱至死,年仅四十六岁。
陈从范,“早入闻过夫子室,获其指授”[8]P79,跟随吴海研习性理之学,其人学行醇伟,一生未曾出仕。林公伟,自少受业于吴海,好学自立,明敏通达,亦是吴海女婿,不幸英年早逝,此二人生平未见于各类史籍。
三、结语
作为元明易代之际闽中理学的领军人物,吴海的学术创作与其自身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吴海少怀英志,孜孜向学,其父酷爱诗书、究明经义的家学家风在吴海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而闽地开明兼容,崇儒重教的社会风尚亦对吴海的治学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之吴海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常与诸贤周游各地,引论经典,扶携后进,嘉惠学林,为推动元明学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