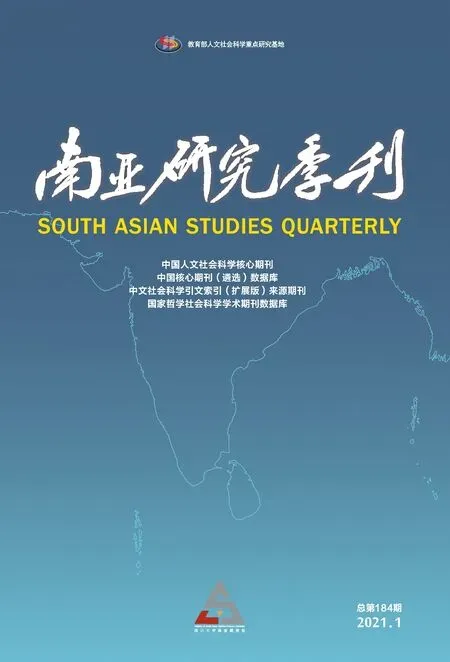梵语名著《舞论》的音乐论略议*
尹锡南
【内容提要】 印度古代梵语文艺理论家婆罗多的《舞论》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重要的世界意义。《舞论》的音乐论包括基本乐理、节奏体系、音乐体裁和乐器分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婆罗多论述的微分音等充满了民族色彩,其节奏论是一个复杂的话语体系,其音乐体裁论重视传统音乐,其乐器四分法值得关注。
在古代文明世界,印度文化源远流长且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绘画、造像、建筑、宗教、哲学、数学、医学、星象历算等一起,作为印度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自吠陀时代始便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四大吠陀中的《娑摩吠陀》(Samaveda)成为研究印度古代音乐的重要文献,并非“空穴来风”。相应地,以婆罗多(Bharata)的梵语文艺理论名著《舞论》(Natyasastra)为代表的印度音乐理论,也成为世界梵学界的研究重点。《舞论》既是印度最丰富和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东西方世界可以同尊、共享的文化瑰宝。即便是在当下,印度音乐也享誉世界,并在印度日常的文艺活动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一席,有时甚至成为印度国事活动时迎接国外元首的重要元素。例如,2019年10月11日,应邀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时,通过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可以看到,沿途欢迎的印度民众中有许多便是手持各种弦鸣乐器、气鸣乐器、膜鸣乐器(鼓)等进行表演的专业音乐人士或民间音乐家。音乐因此成为印度各阶层民众欢迎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艺术符号。由于印度音乐在印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鉴于国内学界对《舞论》的音乐论迄今并无系统介绍,本文尝试以《舞论》的音乐论为例,对印度古典音乐理论的某些重要内容进行初步研究。
一、《舞论》的民族特色和世界意义
四大吠陀、《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都是印度古代文化的精华。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后的婆罗多《舞论》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婆罗多的《舞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1)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1,ed.& tr.by N.P.Unni,“Introduction,” New Delhi:NBBC Publishers,2014,p.75.金克木先生指出:“它(《舞论》)所谓戏剧其实是狭义的戏曲,其中音乐和舞蹈占重要地位,而梵语‘戏剧’一词本来也源出于‘舞’。”(2)金克木译:《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译本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页。客观地看,似乎没有哪一种译名可以完全概括婆罗多著作的复杂内容,也许以大致囊括其核心内容的《乐舞剧论》翻译这一梵语书名更为妥当。婆罗多在书中重点论述了古代印度三大艺术门类:音乐、舞蹈和戏剧。
包括音乐理论在内的印度古代文艺理论的产生,自然离不开印度古代文化的时代土壤。味(rasa)、情(bhava)、庄严(alankara)、微分音(sruti)、节奏(tala)、拉格(raga)等梵语文艺理论范畴、话语体系在诞生前后,必然要经过话语生产的特殊“工序”,这便是通过宗教文化(特别是宗教祭祀仪式等)、语言学(语法学)、数学、医学、情爱艺术论(古代性学)和天文星象等各种知识门类的“思想过滤”与“理论包装”。这种过滤与包装,就是古代文艺理论经典范畴的话语生产流程或生成机制,也是印度古代文艺理论从范畴论走向话语体系论、最终渗入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表演等各个领域的基本保证。
《舞论》诞生和成型于印度这方宗教热土,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历史烙印。单从《舞论》第2、3、5章关于剧场建造时遵循的宗教仪轨、剧场建成后敬拜各方神灵的祭祀仪式和戏剧的序幕仪式表演的描述看,婆罗多的戏剧论包裹着一层层厚厚的“宗教外衣”。这种宗教是区别于佛教的传统印度教。从《舞论》的内容看,创造“第五吠陀”即“戏剧吠陀”的梵天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湿婆的重要性明显上升,这似乎说明婆罗多受到历史上盛行于克什米尔地区的湿婆教(印度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影响较为明显。婆罗多不仅以印度教的思想教义建构其戏剧学理论大厦,也以它言说其舞蹈论中的刚舞、柔舞等重要范畴和音乐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这是《舞论》亦即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诸多名著共同的民族特性的第一层含义。印度教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印度教神灵成为婆罗多“呼风唤雨”、召之即来的理论助手或思维桥梁。
婆罗多的文艺理论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形式分析亦即数理思维色彩。这似乎与古代印度数学发达有关。印度教文化经典、佛教经典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形式分析色彩,这自然说明婆罗多的《舞论》是印度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结晶。婆罗多对戏剧类型和戏剧情节的一再分类,对味的细致分类,对眼神和身体各个部位的分类描述,对微分音的二十二分法,对鼓乐演奏的分类叙述,均体现了传统的形式分析法对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无孔不入”的深刻影响。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种论述方式,似乎是繁琐的模式化思维或“流水线作业”,但它恰恰是婆罗多理论大厦得以千年矗立的核心支柱。
《舞论》创造了一系列彪炳世界古代文艺理论史的重要范畴与核心话语。例如,戏剧论中的味、情、戏剧法、世间法等,诗论中的诗律、庄严、诗德、诗病等,音乐论中的音阶、调式、装饰音、节奏等,均为印度特色的文艺理论范畴与核心话语。《舞论》的上述重要范畴与话语概念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吠陀时期以降的传统文化积淀的理论升华。这些概念与范畴自成型后,就对梵语诗学、戏剧学、舞蹈学和音乐学理论的继续发展或独立发展发挥了无法替代的核心作用。这说明《舞论》所代表的古典梵语文艺理论是印度影响千年的民族遗产,这也是其民族特性所决定的。
《舞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世界古代文艺理论名著一样,既是民族的,也属于世界。这是印度文明之于世界文明的一大卓越贡献。《舞论》的世界意义首先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向世人昭示了原生态的民族传统如何古为今用。《舞论》对后世梵语戏剧理论、诗学理论、乐舞理论、文学创作和戏剧舞蹈表演的全方位影响延续至今,涉及学术思想层面,也涉及艺术实践领域。《舞论》古为今用的一层内涵是雅俗转换和现代变异。一位学者指出,当代印度古典舞更多地效法晚近出现的《乐舞论》等,而非直接承袭《舞论》。“这显示那些在婆罗多时代处于边缘化存在的风格流派,不仅为舞蹈主流所接纳,并且最终成了主流。这种演化进程因而是一种动态发展而非静态存在。”(3)Mandakranta Bose, Movement and Mimesis:The Idea of Dance in the Sanskritic Tradition, New Delhi: D. K. Printworld, 2007, p.260.当代印度学者的文艺批评始终绕不开《舞论》,印度学者出版的英语论著不乏以味论系统地分析东西方文学作品的例子。南印度舞蹈家和艺术研究者帕德玛·苏布拉玛尼娅曾经数次造访印度尼西亚普兰巴南印度教寺庙,观摩和研究寺庙中与《舞论》有关的石刻像。在此基础上,她对婆罗多论述的108式刚舞基本体式(基本动作)和32式组合体式(组合动作)进行了革命性、颠覆性的艺术改造,别开生面地让《舞论》中的一些“活化石”规则以优美的舞姿重见天日。她对《舞论》的其他相关规则和原理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思考和刻意引申。这些均激活了《舞论》中沉睡千年的诸多艺术细胞。凡是关注印度古典文艺理论的学者都明白,类似例子在印度不胜枚举。这些颇具民族特色的古为今用之举,难道不可以称为印度向中国和世界的文艺理论研究家和艺术家们提供的发人深思的“婆罗多启示录”或曰“《舞论》启示录”?
《舞论》的世界意义也在于,它给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如果说历史上佛教向世界的传播是古代印度文化软实力“和平的征服”,《舞论》和《诗镜》等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名著向印度的南亚邻国、东亚和东南亚的历史传播何尝不是如此。意娜博士曾经对梵语诗学名著《诗镜》在中国西藏的藏文翻译、藏文注疏及其与藏族古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她说:“(藏译本)《诗镜》这部藏族文艺理论史上几乎唯一的系统化诗学论著,围绕它的话题始终绕不开‘翻译’。不仅因为它最初是从7世纪檀丁的梵文原著翻译而成,也因为自13世纪以来藏族学者对其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别和争论大多与翻译有关。”(4)意娜:《文艺美学探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89页。味论在泰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变异性接受,《诗镜》藏文译本及其基本原理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变异性存在,当代西方梵学界对以《舞论》为代表的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名著的翻译和研究,这一切均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总结规律,为当代东西方文明对话整理出一些话语交流新思维、新规则。婆罗多的戏剧味论、戏剧类型论、戏剧起源论、情节论、风格论、语言论、诗律论、庄严论(诗歌修辞论)以及乐舞论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古今比较、东西比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于《舞论》这样一宗东西方世界共享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在新时代语境下重视、珍视。
《舞论》的世界意义还在于,它为中国与印度的南亚邻国、东南亚各国的文艺心灵对话、人文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隐蔽,但却十分珍贵的学术视角。印度学者指出:“印度尼西亚的语言、艺术、社会习俗、法律和政治制度、文学、民间传说和哲学都受到印度文化潮流的影响。”(5)[印度]D.P.辛加尔:《印度与世界文明》(下册),庄万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89页。《舞论》在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印度的南亚邻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传播与现实渗透,提醒我们须重视研究以《舞论》为代表的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及其外向传播的历史轨迹,为中外学术对话、人文交流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杨民康教授指出:“一个显在的文化共性是,从长期历史上看,这些国家(指东南亚国家——引者按)中绝大多数或长或短都曾经历过由佛教与印度教文化构成的‘印度化’时期,并由此构成了一直存在于该区域民族文化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这种影响存在至今。其中,印度教文化的遗痕显然更清晰,影响和范围更大一些。并且,这些文化特点都从东南亚各国的乐舞、戏剧文化中明确地反映出来。”(6)杨民康:“西南丝路乐舞中的‘印度化’底痕与传播轨迹——兼论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传播历史与文化脉络”,《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2期,第8页。杨教授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普兰巴南神庙等古代印度教遗迹进行田野考察后指出:“通过对8幅壁画上的乐舞图型进行描述和阐释性分析,可知本文所述及的普兰巴南神庙石雕壁画中显露的印度教乐舞,尚存有为民族宗教所携带的较为明显的民俗性、群娱性文化特点。”(7)杨民康:“印度尼西亚普兰巴南神庙石雕壁画中的乐舞图像考察”,《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4期,第153页。由此可见,如不重视研究以《舞论》为代表的印度古代文化经典和印度文学艺术研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学术对话和人文交流将在无形中遇到某种程度的障碍。南印度学者帕德玛关注和研究《舞论》记载的刚舞108式在印度尼西亚普兰巴南印度教寺庙石刻像的艺术表现,是中国学者须高度重视且可学习的范例。
《舞论》的世界意义还在于,它为21世纪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直面对话和当代中印人文交流提供了艺术和理论的桥梁,也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话语建构和批评范式、操作路径等提供了极佳的东方范例。以《舞论》为代表的印度传统文艺话语属于超越意识形态和刚性政治的柔性符号和诗性工具,对于促进中印两国学者和艺术家的心灵沟通,对于优化印度的文化形象和促进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以《舞论》为代表的印度传统文艺话语属于超越意识形态和刚性政治的柔性符号和诗性工具,对于促进中印两国学者和艺术家的心灵沟通,对于优化印度的文化形象和促进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接下来,本文对《舞论》音乐论的重要范畴和节奏体系论等进行分析。
二、音乐范畴论
《舞论》的6章音乐论涉及印度古典音乐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微分音、乐音、音阶、调式等,它们涉及音乐理论的各个基本要素。下边以几个核心范畴为例,对婆罗多音乐论话语体系进行简介。
首先是sruti(微分音)。一般认为,印度古典音乐理论的两大核心支柱是音译为“塔拉”的tala(节奏圈、节奏体系)和音译为“拉格”的raga(旋律框架、曲调模式),其他的理论范畴皆由此衍生。其实,这种思想不能算错,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二者均离不开高度哲学化的关键词sruti(微分音)。
有学者指出,印度人把音乐中最小的音程单位即微分音程称作“斯鲁提”即sruti。如按一个八度为1200音分计算,将它除以22,则每一个斯鲁提为54.5音分,这便是每一个微分音的音分值。“斯鲁提的理论虽为人们普遍接受,持异议者为少数……总之,印度的22斯鲁提音律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8)陈自明:《印度音乐文化》,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关于被许多中国学者称为“斯鲁提”或 “什鲁蒂”等的微分音或曰微分音程、微音程,印度学者的解释是,它是一种用来度量音高的最小单位。它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度量单位,而是依据古代婆罗门仙人(学者)的耳朵感知所人为设定或臆想的一种测量单位,带有原始的、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9)Bimalakanta Roychaudhuri,The Dictionary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Delhi:Motilal Banarasidass Publishers,2017,p.114.
婆罗多并未专门提出微分音的概念并予以定义和阐释,而是在解说基本乐理的一些关键要素或重要范畴时,顺带提出微分音概念的。尽管如此,后来的印度古代乐舞论者对此所论甚多。例如,多提罗指出:“人的胸中有21种声音,均为低音;其喉咙发出的21种为中音,其头部发出的21种为高音。这些音由低到高发出,而维那琴则由高到低发出它们。因其可以听闻,这些特殊的声音叫做微分音。”(10)Dattila,Dattilam,New Delhi: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1988,p.2.摩腾迦的《俗乐广论》指出:“微分音是表现音调的原因。可以通过推理、比量和现量认识微分音。”(11)Matanga,Brhaddesi,Vol.1,New Delhi: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1992,p.22.《乐舞渊海》对微分音的解释是:“在实际运用中,声音有三类:心中发出的低音、颈部发出的中音,头部发出的高音,它们的音高依次增倍。声音被分为22级,因其可以听闻,遂被称为微分音。”(I.3.7-8)(12)Sarngadeva,Sangitaratnakara,Varanasi:Chaukhamba Surbharati Prakashan,2011,pp.32-33.
这些关于微分音的论述或判断,究其实,是印度古代宗教哲学观念与语言学思想的微妙结合的产物。换一个角度看,sruti按照本义可译为“所闻”“经典”“名称”“声音”等,其动词词根为sru。婆罗多将此词视为其音乐论大厦的核心支柱和稳固基石,显然是借鉴了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思想精华。他的这一姿态,也可见于后来的梵语诗学家欢增创立的韵论(dhvani)。欢增正是在继承语言学家关于声音的论述基础上推陈出新,创立了自己别开生面但又有迹可循的崭新理论。婆罗多的sruti和欢增的dhvani,都有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范畴:类似于中国哲学基本范畴之一“道”的sabdabrahman(音梵)即,“常声”(sphota)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音梵的近义词。婆罗多之后的摩腾迦、角天等古典音乐理论家多以nadabrahman(音梵或声梵)一词言说自己的思想概念。
由此可见,微分音理论是一种既处现代科学范畴之外、又扎根古代科学逻辑土壤的话语体系。明白这一点,须对印度古代文化场域中的科学概念有一种深层的感悟。
婆罗多的音名(音符)为7个,这比欧洲中世纪确定7个音名要早了很久。他说:“具六(sadja)、神仙(rsabha)、持地(gandhara)、中令(madhyama)、第五(pancama)、明意(dhaivata)、近闻(nisada),这些是7种音调。”(XXVIII.21)(13)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3.这里的7种音调就是7个音名。它们与西方的7个音名在数量上对等。
印度学者指出,《梨俱吠陀》的一句话暗含玄机,因为其中出现了saptadhatu(七要素)一词。(X.32.4)(14)Rgveda Samhita,Delhi:Chaukhamba Sanskrit Pratishthan,2014,p.653.他将其理解为婆罗多七音调的象征。(15)Swami Satya Prakash Sarasvati and Satyakam Vidyalankar,eds., Samaveda Samhita,Vol.1,New Delhi:Veda Pratishthana,1995,p.105.《那罗陀示教》认为:“prathama(第一)、dvitiya(第二)、trtiya(第三)、caturtha(第四)、mandra(低声)、krusta(尖声)、atisvarya(高声),这些是唱诵吠陀者所运用的音调。”(I.1.12)(16)Narada,Naradiyasiksa,Varanasi:Chowkhamba Vidya Bhawan,2013,p.27.它还指出:“笛子发出的第一个吠陀调是中令,第二调是持地,第三调是神仙,第四调是具六,第五调是明意,第六调是近闻,第七调是第五。”(I.5.1-2)(17)Ibid.,p.31.由此可见,吟诵吠陀的音调有7个:prathama(第一)、dvitiya(第二)、trtiya(第三)、caturtha(第四)、mandra(低声)、atisvarya(高声)、krusta(尖声)。在《娑摩吠陀》将源自《梨俱吠陀》的诗句音乐化的过程中,这些音调逐渐演变为相应的婆罗多七调:中令(对应于第一)、持地(对应于第二)、神仙(对应于第三)、具六(对应于第四)、明意(对应于低声)、近闻(对应于高声)、第五(对应于尖声)。(18)Swami Satya Prakash Sarasvati and Satyakam Vidyalankar,eds.,Samaveda Samhita,Vol.1,pp.112-116.这说明,婆罗多七调的历史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婆罗多还对各个音调如何结合味的运用作了规定:“音调中的中令和第五用于表现艳情味和滑稽味,具六和神仙用于表现英勇味、暴戾味和奇异味,持地和近闻用于表现悲悯味,明意用于表现厌恶味和恐惧味。”(XXIX.16)(19)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22.
婆罗多所论的每个乐音的音程是以微分音计算的,一个音调包含了不止一个,即1个至4个微分音,因此出现了印度古代学者和现代学者确定每个音调位置的观点分歧。后来的梵语音乐理论家对婆罗多的7个音调(音名)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们为其增补了发音部位、颜色、保护神和适用的味等诸多具体内容或运用情境。例如,《俗乐广论》《乐舞渊海》《乐舞奥义精粹》和《乐舞那罗延》等便是如此。
1926年,向达先生发表论文《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指出,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绪余,龟兹本国故无文化。则谓苏祗婆琵琶七调乃龟兹文化之产物,实未为探本之论也”。(20)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4页。他的结论是:“故愚意以为就佛曲证之,苏祗婆琵琶七调之当来自印度,盖理有可通者也。”(2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71页。支持他观点的人很多。沈知白先生认为,龟兹在西域是受印度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所以来自龟兹的苏祗婆传述的五旦七调理论无疑“源于古代印度的乐制,而七调之名也显然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22)转引自中印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笔者认为,根据向达、季羡林、伯希和、林谦三、岸边成雄等国内外学者从语言、历史、宗教等各种视角所进行的艰苦探索,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苏祗婆为代表的龟兹乐受到了印度古典音乐的深刻影响,但龟兹乐似乎对其进行了本地化,龟兹乐理论即便自成体系也非原创,婆罗多《舞论》为代表的印度古典音乐理论对其施加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第二,由“佛”字经龟兹语中介传入东土一事可知,如欲解决沙陀力、鸡识、沙识、沙候加滥、沙腊、般赡、俟利箑等7个汉语乐名或曰五旦七调的印度来源问题,必须联合国内外吐火罗语专家与中国古典音乐研究者、印度古典音乐研究者集体攻关,这将是一场国际性或曰国际合作框架下的旷日持久的“学术长征”。(23)[古印度]宾伽罗等撰:《印度古典文艺理论选译》,尹锡南译,“译后记”,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965页。
音阶在英文中一般称为Scale。“音阶是指调式中的音从主音到主音按高低次序排列起来而言。”(24)李重光:《基本乐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2页。具体而言,由低到高排列的音阶叫上行音阶,由高到低排列的音阶是下行音阶。婆罗多在《舞论》中指出:“有两种音阶(grama):具六音阶(sadjagrama)和中令音阶(madhyamagrama),其中各有22个微分音。”(XXVIII.24)(25)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4.缪天瑞先生说:“古代印度用二十二平均律,构成七声音阶。”(26)缪天瑞:《律学》,上海:万叶书店,1953年,第56页。他后来还认为“称印度的二十二律为‘二十二平均律’亦无不可”。(27)缪天瑞:《律学》(第三次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第249页。由此可见,所谓的“二十二平均律”其实是指均属于七声音阶的具六音阶和中令音阶拥有的22个微分音,这22个微分音构成了一个八度音阶。后来的音乐理论家还对22个微分音逐一命名。各种音调也依次与某种数量的微分音相联系。
论述了基本音阶(原始音阶)后,婆罗多接着介绍变化音阶(murchana)。他说:“两个基本音阶共计14个变化音阶。”(XXVIII.29)(28)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5.婆罗多认为,依照顺序进行组合,可以构成以七声音阶或曰完全音阶为基础的14种变化音阶。实际上,所谓的变化音阶不可完全按照现代乐理来“强制阐释”,它只是几个乐音或音名(唱名)按照一定的次序,有规律地进行排列组合而成。正因如此,将其视为古代印度风格的转调或升降调似乎不太为过。
再看看婆罗多的调式(jati)。现代意义上或曰建立在西方乐理基础上的调和调式是不同的概念。如以此种调式理解《舞论》所说的调式,显然要注意其运用的比例和尺度,因为后者的民族特性非常突出。婆罗多并未定义和阐释调式的概念,但他对调式表现出的某些特征或主要内容作了归纳说明。他认为调式的10个基本特征为首音、基音、高音、低音、尾音、次尾音、弱化、强化、六声音阶调式、五声音阶调式。根据前述当代学者对调式的定义即一般不超过7个的音按一定关系组合成一个体系且以一个主音为中心,婆罗多的调式概念可以成立。
再看看婆罗多的装饰音(alankara)概念。印度古典音乐理论的装饰音与西方现代音乐理论意义上的装饰音分属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可简单地相提并论。前者建立在印度古典音乐表演的随性、自由发挥的基础上,后者是一种严格规范前提下的产物。婆罗多的装饰音包括升高(prasannadi)、降低(prasannanta)等37种。它们分为四类,即7种平调装饰音,13种混合调装饰音,13种升调装饰音,其余为降调装饰音。装饰音多用于传统的经典神乐表演或宗教性颂诗的吟诵中,用于普通人等的歌唱表演较少。婆罗多的装饰音大体上可称为戏剧表演的“声调装饰”或“语调装饰”(varnalankara)。
三、节奏体系和音乐体裁论
印度学者指出:“拉格(raga)和节奏(tala)的概念是印度对音乐世界的主要贡献。”(29)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ed.,Music East and West,New Delhi: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1966,p.32.张伯瑜指出,印度古典音乐,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是“拉格”,二是“达拉”或“塔拉”。如果把拉格理解为旋律的话,达拉(塔拉)就是节奏。(30)张伯瑜:“印度音乐的基本理论,”《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42页。拉格即旋律框架是在婆罗多的调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表示节奏体系的达拉或曰塔拉的作用不容忽视。“塔拉是印度古典音乐的节奏体系,西方的节奏或节拍的概念却都不能够与之对应。由于塔拉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不断的循环,因此可以把其称之为‘节奏圈’。也就是说,在塔拉中,一组节奏单位按照一种循环方式排列,并且自身反复。”(31)庄静:《轮回中的韵律:北印度塔布拉鼓探微》,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46页。正因节奏体系如此重要,《舞论》第31章专门论述节奏体系。
婆罗多的tala(节奏)是一个复杂的话语体系,它包含节拍、单位拍、节拍表现法、音速和变速等重要概念或因素。按照荷兰学者的说法,tala至少包含13个含义:特殊的手势或左手拍打,运用手、手指和手臂的整体手势,打击乐器,音乐的节奏韵律(如二拍、四拍等),节奏类型(奇数型、偶数型或混合型),时间,节奏,音速,等等。(32)Narinder Mohkamsing,A Study of Rhythmic Organisation in Ancient Indian Music,Leiden:Universiteit Leiden,2003,p.85.节拍动作、节拍计数、时间测量等构成了印度音乐文化的“节奏表达的核心”。(33)Ibid.,p.212.
《舞论》第31章开头部分对节奏的概念进行解释:“以节拍和时间为度量单位,叫做节奏。”(XXXI.6)(34)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40.关于节奏的具体衡量标准,婆罗多认为:“5个瞬间组成1个单位拍(matra)。伽罗来自于单位拍的组合。5个瞬间也被视为唱歌时两个伽罗的时间单位,因此,音速根据节拍的时间长短而定。”(XXXI.2-3)(35)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40.关于节奏的重要因素即音速(laya),婆罗多将其一分为三:快速(druta)、中速(madhya)和慢速(vilambita)。他将音速快慢视为歌曲演唱和器乐演奏的灵魂。除了论述音乐速度外,他也论及变化速度即3种变速风格(yati)。他说:“变速有均匀式(sama)、流水式(srotogata)和牛尾式(gopuccha)3种。”(XXXI.489)(36)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86.《乐舞那罗延》对yati的解释是:“变速是对音速发展的控制。它有均匀式、流水式和牛尾式等3种。”(I.590)(37)Purosottama Misra,Sangitanarayana,Vol.1,New Delhi:India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2009,p.321.极具民族特色的变速概念的提出,是《舞论》对世界古代音乐理论史的一种独特贡献。变速或变速风格概念的提出,其实主要是指器乐演奏而言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印度古代歌曲演唱、器乐演奏的同步协调密切相关。在现代乐理著作中,变化速度的概念虽被提出,但几乎很少有人论证。可见,婆罗多的变速概念具有某种音乐人类学的价值。
婆罗多强调音乐表演者遵循节奏体系的相关规则。他说:“应该努力表演节奏,因为戏剧表演立足于节奏……不懂节奏,就不能成为歌手或乐器演奏者,因为变速、器乐伴奏(风格)和音速是节奏的要素。”(XXXI.480-486)(38)Ibid.,pp.85-86.关于乐段、节拍单元等节奏要素,婆罗多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因此,tala一词译为“节奏”“节奏圈”,不足以涵盖其真实含义,如译为“节奏体系”较为合适。
荷兰学者指出,在婆罗多提到的5种节奏体系中,后2种很少运用。“不过,婆罗多对这些节奏型的演变的解释含混不清,容易引起误解。”(39)Narinder Mohkamsing,A Study of Rhythmic Organisation in Ancient Indian Music,Leiden:Universiteit Leiden,2003,p.144.例如,婆罗多的混合型节奏是“明显的文字窜入案例”。(40)Ibid.,p.160.也就是说,后人对《舞论》第31章内容的增补或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再加上现代学者对该章的校勘编订存在诸多缺憾,要准确理解该章内容,非得以更加理想的校勘本为基础不可。
婆罗多的节奏论并非以节奏论节奏,而是结合各种歌曲或乐曲讨论节奏的具体功用与实践范围。节拍乐(asarita)和吉祥歌(vardhamana)是婆罗多结合节奏体系论述歌曲演唱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基础。婆罗多论述的节奏既包含了器乐节奏,也包含了声乐即歌曲的节拍表达,这与后来的古典音乐论者大多集中笔力探索鼓乐的节奏表达存在明显的区别。婆罗多常常密切结合各种传统歌曲等探讨各种节奏表达或节奏因素的呈现,与此不无关联。婆罗多的节奏论在印度以各种变异的方式存活下来。例如,在喀拉拉地区的神庙仪式上,运用不同的节奏模式。有的节奏只用于向特定的神灵献祭的具体场合,有的则用于向多个神灵献祭的不同场合。(41)Leela Omchery,Deepti Omchery Bhalla,eds.Studies in Indian Music and Allied Arts,Vol.3,Delhi:Sundeep Prakashan,1990,p.221.
婆罗多的音乐体裁或声乐作品论,以达鲁瓦歌(dhruva,或译“剧乐”“声乐”“歌曲”)为基础。达鲁瓦歌包含了《梨俱吠陀》以来的各种“神乐”即传统歌曲,并有各种完备的音乐要素如歌词、音调、音速和装饰音体系等。达鲁瓦歌可以视为“神乐”、古典音乐、古典歌曲、经典音乐或古典戏剧音乐的代名词。
婆罗多结合神乐即传统的经典音乐,对达鲁瓦歌的音节、音调、节奏、音速、音律等进行论述。印度学者撰写的《北印度音乐词典》没有就婆罗多音乐论的重要关键词dhruva进行专题解说,实在是一大遗憾。实际上,北印度后来出现的代表性音乐体裁“德鲁帕德”(dhrupada)承袭了达鲁瓦歌的基本特质,但似乎以颂神为核心。
婆罗多的音乐作品体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声乐即歌曲体裁论。他联系乐节的具体运用等介绍了7种歌曲(gita)。婆罗多介绍歌曲时,还按照乐句多寡和歌曲内涵差异,先后将其分为不同的种类。除了歌曲七分法,他对歌曲还有两种五分法。
婆罗多还论及歌曲演唱的理论基础、歌词创作的特殊原理、歌手必备素质等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了婆罗多的戏剧音乐论的重要基础,也为后来的乐舞论者或音乐理论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乐器论
17世纪出现的梵语乐舞论著《乐舞那罗延》指出:“弦鸣乐器归天神,气鸣乐器归乐神,膜鸣乐器归药叉,体鸣乐器归凡人。”(II.137)(42)Purosottama Misra,Sangitanarayana,Vol.1,New Delhi:India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2009,p.401.这种思想隐含着印度古典音乐论最流行的乐器四分法。
婆罗多是印度古代乐器分类法的鼻祖。他说:“弦鸣乐器(tata)、膜鸣乐器(avanaddha,革鸣乐器)、体鸣乐器(ghana)和气鸣乐器(susira),这些是各具特色的四类乐器。弦鸣乐器就是带有弓弦的乐器,膜鸣乐器指鼓,体鸣乐器指铙钹,而气鸣乐器指笛子。”(XXVIII.1-2)(43)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1.他认为,根据这些乐器的运用,可把戏剧表演分为三类:以弦乐为主的戏剧表演、以鼓乐为主的戏剧表演、几种乐器全面运用的戏剧表演。婆罗多大体上以几种乐器为序展开其音乐论述。由其叙述可知,弦乐队的表演包含歌手演唱的声乐和维那琴、九弦琴、笛子等弹奏或吹奏的器乐,鼓乐队则包括了杖鼓、细腰鼓和瓶鼓。论者指出:“不用说,在婆罗多的戏剧论中,器乐与声乐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流行全世界的乐器分类法源自印度,正是在婆罗多的《舞论》中,我们发现它首次涉及乐器分类。”(44)C.Rajendran,ed.Living Tradition of Natyasastra,New Delhi:New Bharatiya Book Corporation,2002,p.59.
婆罗多对四类乐器中的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和膜鸣乐器的演奏规则,分别给予详略不一的介绍,其中对各种鼓乐演奏的解说令人叹为观止。令人诧异的是,他对体鸣乐器的演奏规则,只是在介绍节奏体系和节拍模式时简略提及,并无实质性阐释。这似乎成了《舞论》难以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一般认为,vina(维那琴)几乎成了印度古代弦鸣乐器的代名词,它可以表示所有的弦乐器。古代印度人习惯以vina一词指称印度所有的弹拨乐器和弓弦乐器。婆罗多指出:“有七根弦的是七弦琴(citra),九弦琴(vipanci)有九根弦。九弦琴运用琴拨,而七弦琴只用手指弹拨。”(XXIX.120-121)(45)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p.32-33.维那琴几乎成了印度古代弦鸣乐器的代名词,它可以表示所有的弦乐器。这和中国古代琵琶的情况有点类似。“古代所谓琵琶,与现在所谓琵琶很相同……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琵琶在古代仿佛是一个概括的乐器种类的名称似的。”(4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维那琴等乐器对中国古代音乐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学者荻原云来编纂的《梵和大辞典》对vina即维那琴的解释是:“琴、琵琶、范弦、箜篌、琴瑟”。(47)[日]荻原云来编:《梵和大辞典》(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2003年,第1261页。这似乎说明,它与中国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事实也的确如此。杨荫浏先生指出:“中国南北朝时期由西域传入而成为隋唐以后有名的弹弦乐器之一的曲项琵琶,可能与印度早期的音乐有着源流关系……这一乐器在中国开始渐渐传播是第五世纪。”(48)杨荫浏:“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关系”,《人民音乐》,1955年第7期,第16页。杨先生还指出:“印度的民间音乐在第四世纪中也传到了中国。第六世纪末与第七世纪初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中均有‘天竺伎’。当时‘天竺伎’所用乐器,有铜钹、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贝等九种;其中凤首箜篌和铜鼓在当时中国非常流行,这两样乐器为印度音乐所独有。”(49)同上,第17页。随后,常任侠先生指出:“大家都知道,琵琶是我国的重要乐器,但是若果考察它的来源,它的老家,却是印度……琵琶是印度乐器的一种,它从汉代输入后,到北朝而盛行……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另一译名。她的音乐,随着佛教输入我国,最初由陆路传入西域,也就是顺着天山南北两路,进入我国的西部,在库车会合。库车在古代译称龟兹,龟兹乐也就是印度乐的直系亲属。其他如西凉乐、疏勒乐等,都受到天竺乐的影响,加以发展演变。天竺音乐,大概居于这一时期的主导地位。”(50)常任侠:《东方艺术丛谈》(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2-63页。根据以上两位学者的介绍可知,印度古代维那琴与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关系理应成为中国与印度的音乐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现实的情况是,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比印度学者更为关注这一问题。
婆罗多指出:“在气鸣乐器中,竹笛具有主要乐器的特征,而螺号和荼吉尼是次要乐器。”(XXXIII.17)(51)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147.因此,他对气鸣乐器的介绍主要是围绕竹笛而展开的。这便是《舞论》第30章的全部13颂,它也是该书36章中最短的一章。
《舞论》的第30章结尾处提到体鸣乐器,但是第31章却集中论述节奏体系,并未涉及体鸣乐器。一位荷兰学者指出,打击乐器或曰体鸣乐器出现较晚,至少没有多少直接证据证明远古时期的印度出现了铙钹等乐器。这可以解释为何《舞论》在提到舞台表演时,对体鸣乐器的具体运用缄默不语。“在此背景下,《舞论》中提到ghana(体鸣乐器)和tala(打击乐器)并不非常令人信服,因此可视为‘可疑文字’。”(52)Narinder Mohkamsing,A Study of Rhythmic Organisation in Ancient Indian Music,Leiden:Universiteit Leiden,2003,p.115.
弦乐队和鼓乐队是当时戏剧音乐的主要表演者。婆罗多介绍各种鼓乐表演规则时,主要是围绕穆丹迦鼓(杖鼓)、瓶鼓和细腰鼓这三种主要的鼓进行的。他高度重视鼓乐演奏在戏剧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将其视为戏剧表演成功的基础所在。他说:“首先应该关注鼓乐演奏,因为它可称作戏剧表演的基础。鼓乐演奏和歌曲演唱一帆风顺,戏剧表演就不会失败。”(XXXIII.301)(53)Bharatamuni,Natyasastra,Vol.2,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2016,p.185.婆罗多强调鼓乐演奏须与各种戏剧情味的表达相结合。他在介绍各种鼓乐的演奏规则时,也对鼓乐队如何为戏剧表演伴奏做了细致的说明。婆罗多还介绍了乐鼓制作的流程,介绍了涂鼓的方法等。
余 论
以上便是婆罗多音乐论的简单介绍。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国内学界对以婆罗多音乐论为代表的印度古典音乐的研究,迄今只有陈自明先生等极少数人进行。这在当今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是不太理想的,因为印度古典音乐对南亚、东南亚、西亚、东亚等区域的许多国家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演奏技法影响深远。有学者指出:“所谓的‘民心相通’,最有能力沟通人类情感的就是艺术……所以,艺术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的内容……艺术人类学学者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应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国情民情,贡献自己的学术智慧,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54)方李莉:“‘一带一路’建设中艺术人类学应有所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6日。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愿望是美好的,但若忽视对印度等东方国家文艺经典的研究、翻译,学术智慧的积极奉献恐成“空中楼阁”。杨荫浏先生在1955年指出:“中、印两国的音乐,既然有着这样的密切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研究中国音乐时,若不去注意印度音乐,而研究印度音乐时若不注意中国音乐,将是一个缺点。我们的音乐文化必定要交流,我们在音乐研究工作方面必定要互相联系。”(55)杨荫浏:“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关系”,《人民音乐》,1955年第7期,第17页。当前,我国大力提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俗民情与社会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5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术界须有定力和睿智,须有放眼世界的胸怀和经略周边的科学意识,须对各大文明互鉴有一些基本了解。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历史上对域外国家的文艺辐射力很强,当代印度与这些区域内许多国家、特别是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不丹、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等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文艺联系也非常紧密,因此,对于以《舞论》为代表的印度古典乐舞理论的介绍和深入研究,将增进国内学界对印度文化的深入认识,为中印文化交流与学术对话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亚各国的人文交流等创造更多的必要前提,自然也为中国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明互鉴、人文交流创造更为理想的学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