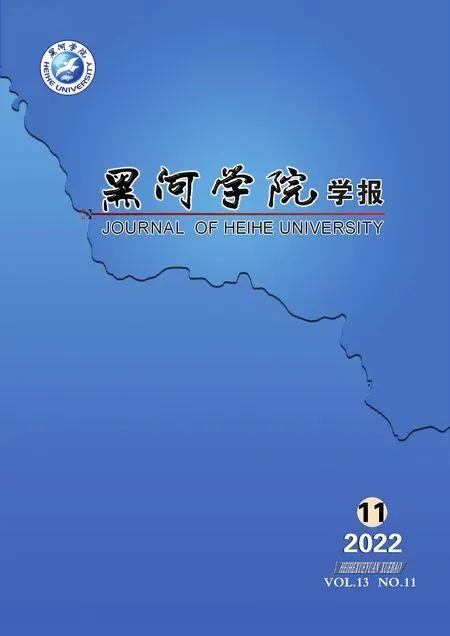文化变迁中的驯鹿鄂温克人教育演进
王寿鹏 高天好
(1.大连民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2.鞍山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驯鹿鄂温克人是我国鄂温克族中人口最小的支系,目前绝大多数生活在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民族总人口约250人左右[1]。在驯鹿鄂温克人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教育现象呈现出与当时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需求、时代背景等因素相适应、相匹配的规律性。从历史上看,驯鹿鄂温克人在大约300多年前由俄国境内进入中国大兴安岭地区,其文化受俄国影响非常深,教育现象也难免体现出诸多与俄国有关的元素。“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势力逐渐进入驯鹿鄂温克人的生存区域,所以,在这个民族的教育史中,又留下了日本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落实民族政策,对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投入倍加重视,让这个民族的适龄儿童能够接受系统化的学校教育,从此,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走上正规并不断深入,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现象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目前,在当前所能找到的文献中,还没发现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讨论,因此,笔者将对此课题尝试进行探析。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一)概念界定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分支,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已有的研究中,对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称呼可谓多种多样,兹举几例:孔繁志将其称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2];董联声则在其著作和论文中采用“使鹿部鄂温克人”的称呼[3];唐戈在其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则采用了“驯鹿鄂温克人”概念[4];卡丽娜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驯鹿鄂温克人文化研究》一书[5]。应该说,上述几种典型概念都能有其自圆其说的解释。经审慎分析,笔者决定采用“驯鹿鄂温克人”概念,理由如下:第一,唐戈、卡丽娜采用这一概念在诸多严谨且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如《世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黑龙江民族丛刊》《满语研究》发表多篇文章,这说明学术界认可这个概念,采用此概念有利于学术共同体内的知识共享与交流;第二,由于长期在森林中狩猎,这个民族是中国唯一驯养驯鹿的民族,驯鹿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
关于“教育”概念,笔者拟从广义教育概念视角来加以探讨。广义教育在教育学领域被人们总结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驯鹿鄂温克人是直接从原始社会形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并不存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其教育形态更多体现为在代际之间为获得生存技能而自然产生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这种教育又是围绕生产生存方式而展开的,具有非正规化的特征,在后面的讨论中,得知只有到了清末,才开始产生了正规学校教育的萌芽,并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得以真正实现,因此,笔者在梳理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发展过程时,不能不用广义教育的视角,才能获得对其教育演进过程的全面了解,并发现这个过程背后所呈现出的规律性。
(二)研究思路
驯鹿鄂温克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之一就是其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从而也就没有文献记录其漫长的历史。在历史上,有官方记录的有关这部分鄂温克人的历史,稀疏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当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形态逐渐进入到学者的视野之中后,依靠口头交流、实地调查,学者在不同时期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进行了记录和整理。也就是说,对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研究,绝大多数资料属于民族志性质与调查报告性质的资料,仅有少数资料属于历史资料,而前者在历时性上,并不能保证有一个完整的记录,这就加大了研究其的难度。但幸运地是,通过对诸多不同性质资料的收集整理,仍可发现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中所呈现出的脉络。
本研究属于边疆民族教育史范畴。关于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问题,在1952年之前并无专门文字档案记录。但在一些其他领域的文献记载中,还是能够找到当时教育状况的一些蛛丝马迹,如清末赵春芳《珠尔干河总卡伦边务报告书》、宋小濂《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永田珍馨《驯鹿鄂伦春族》、秋浦等《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等文献,虽然并未就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问题进行专门阐释,但从其文本中,可以抽取出这个族群是如何进行狩猎技艺、社会规范等传统知识传授方面的资料,以及如何产生学校教育的萌芽等信息。研究过程中,笔者还参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调研报告,如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中共额尔古纳左旗委员会1979年发布的《关于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调查报告》《根河市志》等,从而可以实现史料、民族志资料、调查报告资料之间的彼此印证,去伪存真。对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族群而言,口述史资料也具有独特价值。驯鹿鄂温克人中的长者及曾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工作和生活过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等,曾被采访或者撰写过的回忆文字,也被整理出来,笔者在三次去敖乡调研的过程中,也记录了一些老人早期生活的回忆,其中也有与教育有关的内容,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这个民族文化的不同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演进历程及其特征
(一)自然生存教育
有史以来,驯鹿鄂温克人不具备产生诸如“学堂”“学校”之类正规教育的条件,因此,其受到的教育只能产生于个体家庭、“乌力楞”、氏族部落等层面,其形式是来自于长辈或者榜样的言传身教,属于社会学习性质,从教育形态上看,且仅能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第一,驯鹿鄂温克人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第二,居无定所的游猎生产生活方式,不具备建立固定学校场所的可能;第三,生存环境恶劣,长期处于原始社会期末社会形态,生产力不发达,因此,族人第一要务就是要学会生存技能、行为规范,以确保获得生活资料。截至2003年“生态移民”“全面禁猎”的实施,狩猎这种生产方式在驯鹿鄂温克人中都占非常重要的份量,尤其在1965年定居敖鲁古雅之前,狩猎生产几乎是其唯一的生产方式,是世代相传的生存手段,因此,围绕“狩猎”而展开的教育,必然是驯鹿鄂温克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接受的教育,成为一个优秀的猎手,自然就是最主要的教育目标,这种目标对男女都适用。
鄂温克猎民对儿童的“学前教育”是从五六岁开始的,课程与当前学前教育的主流课程论一致,那就是“游戏”,长辈会制作弓箭,让儿童练习并进行比赛,以培养如何瞄准目标等狩猎意识与技能,在笔者收集的鄂温克人的照片中,就有两个儿童比射箭的照片。在吕光天等人的调研报告中[6]150-151,还描述了儿童围绕“狩猎”而开展的游戏功课,包括“学习打熊的游戏”“学习打犴的游戏”“搬家的游戏”,这些游戏性的狩猎教育主要是在12岁之前,到了12岁以后,儿童开始跟随祖父、父亲、兄长等进行实战性的狩猎活动,教育也随之进入小学以上阶段,一般是父亲给孩子买一支旧枪,然后在狩猎过程中,由经验丰富的长者教授如何瞄准、如何寻找猎物、如何识别树号、如何利用风向、如何相互协作等狩猎技能,这是一种“传、帮、带”式的自然教育,这种教育也是循序渐进的,从打小兽(如灰鼠)开始,逐渐进展到打大兽(如犴、鹿、熊等)。根据博仁那森、古新军的记载(杰斯克老人口述),驯鹿鄂温克猎民也有“文凭”观念,获得什么样的文凭,其标准就是看打到猎物的成果背后所体现出的狩猎技能,如能打到灰鼠、兔子等,就算幼儿园毕业了,能猎获獐子、狍等,相当于合格的小学毕业生,打死马鹿、野猪等,相当于中学、中专文凭,如果想达到大学水准,那么就必须去猎获熊这样的猛兽了[7]。
当然,贯穿于整个狩猎时代的教育内容肯定不局限于直接的狩猎技术,而且还包含与狩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配合的其他技艺、经验知识、社会规范。狩猎需要猎犬配合,于是就有了驯养猎犬的技能;鞣制兽皮、肢解猎物需要工具,于是有了打制铁器的技能;森林中搬家、驮运猎物等需要驯鹿,于是就产生了饲养驯鹿、管理驯鹿的需要,于是就必然有了相关的技能,这些技艺、知识,在狩猎生产生活方式的要求下,在自然形成的男女分工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例如,饲养驯鹿、挤鹿奶、打列巴、缝制兽皮衣物等主要是女性需要学习的内容,打制铁器、制作桦皮船等则是部分心灵手巧男人的专属技术,并不构成普遍性的教育内容。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代,加之环境的恶劣,狩猎生产方式必然对彼此协作,相互扶持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形成诸多行为规范,在驯鹿鄂温克人中叫“敖教尔”,这些都是要通过言传身教、辅之以舆论约束、适当的惩罚而逐渐形成对人的塑造,也构成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内容和方式。
在驯鹿鄂温克人迁入中国境内大兴安岭地区之后30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为了生存、生产而自然演化出来的教育是紧紧围绕“狩猎” 生产方式而展开的,在整个20世纪,随着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交往以及各种环境的变化,虽逐渐弱化,但基本上这种教育形态保留了几十年,至今仍有残余。
(二)正规教育萌芽
驯鹿鄂温克人受俄国影响特别深刻,至今从其姓名、习俗等方面还能看到这种影响,教育问题也不例外。从民族历史渊源来看,普遍人们认为其是从勒拿河流域迁移过来,大约在300多年前,从漠河对岸进入我国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身处深山老林,必然要与外界发生贸易往来,以换来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如食盐、白面、狩猎工具、酒类、火药等,在贸易的过程中,与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俄国人“安达”(商人,鄂温克语为“朋友”之意)接触愈发密切,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驯鹿鄂温克人是受俄国境内村屯统治的,驯鹿鄂温克人中的首领被俄国人称之为“阿塔曼”(屯长),成年男子“历年每人纳羌钱三吊”,在与俄国人的诸多交往,尤其在贸易往来过程中,鄂温克人中很多人学会了俄语,并且有少量人能够运用俄国的文字,这个过程必然存在一个教育过程。从现有文献来看,能管窥那个时代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状况的文献,主要来自于赵春芳的边务报告书[8]。光绪三十四年五月,赵春芳受呼伦贝尔副都统指派,调查在中俄边境生活的使鹿部,《第八门调查鄂伦春记》中是这样描述调查对象的:“调查吉拉林东北山中有使鹿部,即鄂伦春一种”,①清末、伪满时期,都称呼这一群体为“鄂伦春”,实际上就是使鹿部的鄂温克族。当时的目的调查中,有重要一项就是“俄人在该部山中设立学堂是否属实。”这是与教育有关的内容,调查的结果是无论俄国人还是鄂温克人,都矢口否认有俄国人在山中设立学堂的情况,甚至被调查的鄂温克人“茫然不知学堂为何物。”这说明俄国人的确并没有逾越国界进入中国境内开办学堂。
随着1906年后俄国出现越来越多的职业“安达”与驯鹿鄂温克猎民之间生意规模越来越大,必然有猎民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有了办教育的自觉性,寻求让儿童或者族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以减少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出现被骗等风险,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普及开来。赵春芳的边务报告中曾提到过一个情境,可以证实这一点。当时,驯鹿鄂温克首领阔力阔夫·漂得耳格为力勒为池在和赵春芳谈关于商人住所问题时,该首领说:“现住木房一间,此房系前年鄂伦春人名也及木拉立瓦挪夫所盖。为小孩念书之用。”赵春芳问读什么书,对方回答:“俄国书。并未念好,前年冬月请俄人名四皆班恩各一果夫为师,仅一冬而止。因该俄人不用心教导也,就不念了”。从当时谈话的时间往前推,鄂温克人邀请俄国教师来华授课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月,这是正规学校教育的萌芽。
在赵春芳的报告书中,记录了乌西罗夫(通常翻译为“乌启罗夫”)总屯长的回忆:“曾记二十年前,鄂伦春岁荒,猎于山,渔于水,均无可获,所畜之四不象子,又多倒毙,彼族度日维艰,遂出山入俄屯谋食,沿额尔古纳河一带无屯无之。当时有鄂伦春幼童在敝国学堂念书者,至在山中设立学堂,实未之前闻也。”当笔者考证这段历史时,发现在吕光天等人的报告中,记录了1892年发生的全部驯鹿死亡事件[6]458。从9月爆发到12月份,额尔古纳河流域的驯鹿无一幸免,只有漠河境内的一家二十几头驯鹿存活下来。驯鹿鄂温克人不得不到河对岸的乌启罗夫谋生,在大约5年的时间中,驯鹿鄂温克人中的成年人与俄罗斯人共同劳作,可以推测,这时候的驯鹿鄂伦春中的儿童必然有了进入学堂读书的机会,从而与总屯长的回忆内容得以契合。在赵春芳的边务报告书中,可以看到鄂伦春首领漂得耳戈沃力勒为池阔夫可以通过在桦树皮上用俄文留言的方式,为来访者指示方向,从时间上推测,这是当年在俄国境内受过学堂教育的结果。
俄国人也有主动教授驯鹿鄂温克人学习的动机,因其密切的交易关系而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干爹娘”的关系[9]10,尤其为了让贸易能够得以顺畅进行,俄国安达希望驯鹿鄂温克人能够识字,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从诸多回忆中,可以证实这一点。据杰什克老人回忆,即使在日本统治期间,俄国人(苏联人)和驯鹿鄂温克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完全中断,并且基于良好的交易关系,还不断地帮助驯鹿鄂温克人识字。“那时,日本人对边境的控制还不太严,有了猎获物仍然可以卖给苏联的‘安达’,苏联商人不但收购他们的猎产品,而且还教他们俄文,教他们用俄文字母拼鄂温克语,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②博仁那森,周伯镛,黄杰.鄂温克猎民老人杰什克.呼伦贝尔市政协文史资料丛书(第2辑)——根河专辑,42—45。永田珍馨的描述从侧面证实了这个时期驯鹿鄂伦春人的受教育情况,他说“只是从革命(一九一七年)当时由俄国境内逃亡来的白俄夫妻那里受点儿教育,懂得一些俄文而已。”
俄国人对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除了识字教育之外,还体现在宗教教育方面。永田珍馨写道:“俄国人趁清朝的势力尚未涉及到边境之机,企图通过宗教政策进行怀柔,就叫他们做了伊沙金斯基正教会的教徒进行礼拜”并且婴儿“出生后几个月由希腊正教传教士洗礼,以俄国式的名字来命名。”[9]7,除此之外,诸如结婚仪式中抬过耶稣像、在死者坟头插十字架,种种现象都说明,驯鹿鄂温克在历史上受到过俄国传教士的有意识的宗教教育,博仁那森等经过考证,认为“鄂温克猎民俄名、俄习、俄俗的由来,始于1728年后,即中俄《恰克图条约》之后”,③博仁那森,黄杰,周伯镛《鄂温克猎民俄名、俄习、俄俗的由来》,根河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研究委员会.呼伦贝尔市政协文史资料丛书·根河专辑。截至新中国成立,依然每年约在6月份有传教士到猎民中活动,设祭坛、给新生儿命名、洗礼,为死者补做追思礼拜等。
(三)日本殖民教育
日本人从1935年开始了对驯鹿鄂温克人的正式统治,出于加强统治的需要,日本人逐渐采取多种措施对鄂温克人进行教育。根据阿力克山德·伊那见基·库德林的回忆,这一年日本人先缴了鹿鄂温克猎民的枪,然后重新选举“阿塔曼”(猎民部落里的最高头领),1938年日本人开始进山宣传“不要和苏联人打交道,要和日本人交朋友”等[10]。
1939年,永田珍馨在其著作《驯鹿鄂伦春族》中,也用很小的篇幅提到了当时驯鹿鄂温克人在教育设施方面的缺乏,并且建议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有必要对“自然人鄂伦春……进行指导,这可能才是日本在非常时期的一个目标”[9]23。并谈到了在1938年,当时的额尔古纳左翼旗当局曾经将两名驯鹿鄂温克少年(亚历山大伊万·库德林,索罗柯夫·伊万·德米特)安排到海拉尔兴安学院学习。但最终,因他们二人不习惯学校生活,跑回了山林中的居住点。永田珍馨感慨“由于如此缺乏教育设施,任凭他们的子弟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吸烟草,嗜好伏特加和酒精,一辈子当不讲卫生的自然人而已了。”[9]6
1940年(伪满康德七年),日本人在乌启罗夫(奇乾)东部的布洛固纠建立过“雅库特”小学,强迫驯鹿鄂温克人的孩子学习日语,以推行奴化教育,同时,进行反苏宣传,离间鄂温克猎民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此处成立“关东军栖林训练营”,对鄂温克成年人进行分批次的奴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每批大约40人,两个月一换班。玛利亚·索老人的回忆正好与上述这段历史基本吻合,她说:“那是我十来岁时候的事儿,那一年夏天,我随着大人们第一次来到这里学习,以日语为主。当时日本人每年夏天都对15岁以上的鄂温克男猎民进行训练,有打靶、出操、跑步等。孩子也不闲着,都集中到这里学习日语。”[11]并且从老人的口中,还可以得知,当时日本人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学习和训练都是免费,但要干活,有的日本教师人很好,秋天训练和学习结束后,还会开办典礼,给表现优异的同学以奖励,奖品包括小口径步枪、衣服等。
综上可知,日本人对驯鹿鄂温克人的统治时间仅有10年,在这期间采取的教育措施主要是舆论宣传、对成年人和儿童的全面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为加强统治需要服务,具有殖民教育的特征。
(四)正规学校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各级政府对驯鹿鄂温克人关爱有加,在教育上投入巨大的资金、政策和人员支持,建立了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至今其教育发展演进历程在政府档案、调研报告、文史资料专辑等有大量记载,因此,本文不做详细罗列,只以举例方式阐述这个发展历程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1.政府教育投入力度大
1952年6月1日,政府在奇乾建立了一所寄宿制鄂温克小学,1958年4月9日,“奇乾小学”更名为“奇乾鄂温克学校”[12],据冯训林记载,在奇乾鄂温克学校,“所有的鄂温克学生都免费入学,并享受助学金,住集体宿舍,住宿、伙食、衣服和日常用品按统一标准供给。……1964年,额旗政府拨款,修建了300多平米的校舍(木刻楞),增添了手风琴、冰刀、滑雪板等音体教学设备,使奇乾鄂温克学校成为全旗条件最好的学校。”①冯训林.鄂温克猎民民族教育发展概况.呼伦贝尔市政协文史资料丛书(第2辑)——根河专辑,2002:47—48.从1969年开始,国家给每一名驯鹿鄂温克族学生发放助学金每月16元。1971年,额尔古纳左旗财政拨款,建成260多平的木刻楞校舍,包括4间教室,1间办公室。之后,盟、旗财政又陆续拨款,校舍面积逐步扩大,到了1997年,学校不仅拥有解放牌汽车、教学楼、电教室等固定资产,还有地面接收站设施一套、电视机二台、录放像机二台、投影仪、电子琴、电脑六台及其他教学所需要的设备仪器。历年教育投入统计,见表1。

表1 政府历年对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部分投入
2.民族教育成果显著
经过各级政府的逐渐投入,到1980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形成了完备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初中,学制完备。在20世纪80年代,猎民中有40%以上能用汉字书写,90%以上能用汉语进行交流[13],到了1985年,当年入学率100%、巩固率100%、普及率100%、合格率100%。1986年,敖乡学校“小升初”统考成绩平均分、及格率、双科及格率等指标都获得了全旗第一的好成绩,猎民子女中适龄儿童基本入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94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学校成为呼伦贝尔盟初等义务教育示范学校。
3.得到了广泛的支援
奇乾、敖鲁古雅时期的鄂温克族学校得到了来自呼伦贝尔盟各个旗内乃至全国各地个民族的支援,支援方式包括师资支持、接收鄂温克猎民子弟进入中学读书、给予大学入学免试推荐名额、优先安排猎民子弟入学等。如1960年刘国军担任奇乾鄂温克学校校长,1972年,杜万寿从阿荣旗调任敖鲁古雅学校校长,海拉尔二中、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吉林工业大学等,都为驯鹿鄂温克人的孩子升学提供了机会。
三、结论与展望
首先,从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演进历程来看,呈现出与其社会形态的演变历程基本保持同步的规律性。当社会形态保持在原始状态时,教育自然也会停留在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规模与水平上。迁移至中国境内的300多年以来,驯鹿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时间中,都是在森林之中游猎,因此,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有意识地让其实现“定居”,并融入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体系之中时,正规的学校教育才真正出现,但因为人口规模本身较小,加之新中国成立之初驯鹿鄂温克猎民的生产方式还是以狩猎为主,“定而不居”还比较普遍,甚至有的家庭并没有定居,所以,那时的教育规模还是比较小的,迁移至敖鲁古雅之后,随着当时的经济发展方针发生变化,猎民对文化知识的重要性逐渐认识加深,加上国家投入加大,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随之提升,甚至达到较高的水准。
其次,教育的凝聚、融合功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地位。从日本人的10年统治来看,日本人的教育对鄂温克儿童的殖民教育几近成功,从玛利亚·索老人的回忆可以证实:那个时代在日本设置的学校中读书的青少年儿童,对日本人并没有产生反感或者民族仇恨,相反,对一些授课老师的印象非常好,并且在其学业奖励政策之下,有很好的学习动力。这种现象恰恰体现了教育所具有的阶级性属性,即教育是为国家统治的需要服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在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方针的大背景下,研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包括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投入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教育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就显得尤为关键,这是深化今后民族教育工作应考虑的问题。
最后,对于驯鹿鄂温克人的教育问题,在一些调研报告或论文专著中,也提出了很多比较尖锐的问题,有必要在今后进行专题研究。1979年,中共额尔古纳左旗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教育方面存在的三方面问题,199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郝时远、张世和、纳日碧力戈撰写《“驯鹿之乡”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现状研究——34年后追踪调查(1960—1994)》,提出了诸如“以青年猎民为主的变态‘优越感’”“不求进取,自我放纵”等和教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未公开发表。如谢元媛的著作《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中,也提出了在生态移民之后敖乡教育出现的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承脱节,并导致“精神世界的惶恐与混乱”等问题[14]。上述问题的提出都是基于田野调查,相对比较客观中肯,具有重要价值,在今后需要给予有针对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