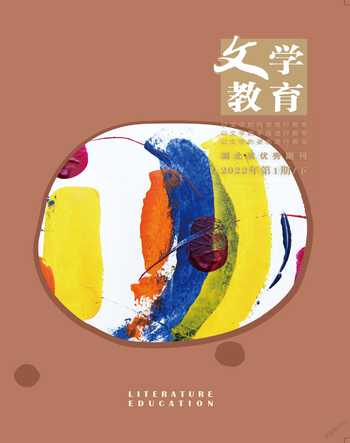“理一分殊”与“一多相摄”的关系探析
黄义鹏
内容摘要:朱子“理一分殊”与华严宗“一多相摄”在说明现象与本体关系时存在相似性,但朱子“理一分殊”的阐释中究竟有无华严佛学成分、“理一分殊”与“一多相摄”有何异同等问题仍需探明。文章将通过对朱子“理一分殊”思想渊源、本体论建构和理论落脚三个方面入手,以证朱子“理一分殊”首先在学术脉络上直承儒家传统,其次在本体论建构上与华严“一多相摄”兼有异同,最后两者在理论的现实落脚处走向殊途。
关键词:理一分殊 本体论 一多相摄
朱子早年受李侗影响关注“理一分殊”,后将“理一分殊”从伦理意义扩充至以太极本体论意义,大大发展了其内涵。朱子“理一分殊”与华严宗“一多相摄”似都在探讨“一”与“多”、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关于朱子思想与华严佛学之关系的讨论,学界研究基本肯定朱子在理学本体论中借鉴了华严宗思想,有学者认为朱子继承了华严理事无碍思想进一步发挥了“理一分殊”①,也有学者认为朱子对于华严宗只是思维方式的引用②,然朱子“理一分殊”与华严“一多相摄”关系渊源何许,内容异同何如仍需明晰,这直接关系到朱子对华严佛学的态度问题:是排斥还是继承抑或是无甚关联?笔者将从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的发展脉络入手,尝试分析朱子对待华严佛学的态度。既为切入口,首先要明晰“理一分殊”的发展历程。
一.“理一分殊”思想渊源
“理一分殊”最早由程颐提出,蕴含浓厚的伦理意义。程颐用“理一分殊”来解释《西铭》与墨家兼爱的差别:“《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分立而推理一,以至私胜之流,仁之方也”③,“仁”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但是它的实践不是兼爱而是差等之爱。“理一”指对一切人要有仁爱,“分殊”指对不同的对象爱的程度有别。程颐的“理一分殊”意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展现为不同的道德规范,更多表现为伦理意义,并未涉及到宇宙观及本体论意义。程颐之后的道南学派也讲“理一分殊”,强调“分殊”是其传统,李侗便是如此。李侗认为重“分殊”可以辨明儒佛之界,对“理一”的体认没有人伦日用“分殊”实践困难和重要。
朱子作为理学传人和李侗学生,继承了程颐和李侗“理一分殊”的思想。朱子《西銘解义》言:“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其分未尝不殊也”④,其中“分”是等分,“一”是共同性,“殊”是差异性。朱子继承了程颐“理一分殊”即基本道德原则与具体道德规范关系的解释;而李侗向朱子强调“分殊”重于“理一”是为了引导他在日常实践中下功夫,不经意间却成就了朱子格物穷理的方法论。朱子倡导格物穷理法正是着眼于具体的分殊事物,通过对“分殊”的认识积累达到对“理一”的把握。
但不同于程颐与李侗,朱子更热衷于探究“理一分殊”的宇宙论意义,在“理一分殊”问题上有所革新。在师承李侗时期,朱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太极本体论体系,但朱子做出了“仁”本体论建构尝试。朱子认为“仁”是生生自然之机,人得之而为性,所以异于禽兽;李侗修正指出“仁”天地之理,从根源上说万物皆有禀赋,人禽之别在于禀气差异。朱子接受了这一指正,“理一”指的是天地万物本于一源,人禽都完全禀受此理;“分殊”指的是人禀气清,物禀气浊,所以人可存养此理而物虽有理而不自知,正是“理一可见人物之同,分殊可明人物之异”⑤。自此朱子开启了“理一分殊”本体论意义的探究,单纯的伦理意义虽有却不再独彰。
那么在“理一分殊”的渊源中有无华严宗“一多相摄”因素呢?《华严经》用“一”与“多”(或一与一切)来论证一般与个别、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华严宗继承了上述一多关系观,如法藏说“一即一切”,即法性“一”与它所显的万千现象“一切”、“多”是体与用也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程颐的“理一分殊”就已经带有对华严宗“一”“多”关系的借鉴。程颐虽然力主排佛,但还是受到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华严宗以一般和个别、整体和部分论“一”“多”关系的思路与“理一分殊”在结构上极为相似,但在内容上“理一分殊”更多带有道德伦理意义,而华严宗“一多相摄”着眼宇宙论意义,这种差异是程颐坚持儒学本位的结果。之后的道南学派完全继承自程颐的思路,而与华严宗相远,他们更加注重“分殊”所代表的实践意义,这与华严“一”“多”关系相去甚远了。
总言之,朱子一方面继承了程颐“理一分殊”初创的伦理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李侗的教导,吸收了注重“分殊”的因素,开创出自己独特的由分殊上升到理一的格物穷理方法,扩展了这一命题的哲学意义。虽然“理一分殊”理论初创之时受到了华严宗“一多相摄”思想的影响,但随着程颐、道南学派的传承改造,朱子的“理一分殊”在思想渊源上或许还存有华严思想的痕迹,但主要内容与性质已经与华严“一多相摄”有一定距离。
二.本体论意义异同
朱子较之程颐与李侗的不同在于将“理一分殊”用于太极本体论建构。他在解释周敦颐《通书》时有言:“是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⑥虽然说“合万物”,但是万物总和并不是太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万物的本体才是太极。如果把宇宙万物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它的本体就是太极,这就是“一”。作为宇宙本体的这个太极是普遍规律、万物依据,万物都禀受此理以为性,这是“分”。这里的“分”不是割裂的瓜分占有,而是完整的继承禀受,每个具体物禀受而成的性理与宇宙本体的太极是一样的,这就是“各有一太极”。虽然具体事物有差异,但是他们禀受的理是一样的,正所谓“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⑦。这样给“理一分殊”的“一”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万物的太极都是同一的,每一物的太极与宇宙本体的太极也是相同的,称作“万物一太极”。
朱子用“理一分殊”来解释太极本体论的核心规范。在《太极图解》中朱子言道:“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⑧这是太极本体论的核心规范,前者“理一”,后者“分殊”。陈来指出“一物各具一太极”中的太极指性理而不是分理,是万物的性理与宇宙本体的太极相同。朱子也用“理一分殊”来解释统体太极和各具太极的关系:统体太极和各具太极在质上没有区别,差别是数量上的,前者一后者多,“理一分殊”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称为“理一分多”,也正是这一点可以与华严宗思想作比较。
华严宗“一多相摄”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法性“一”和万千现象关系,其二是个别事物与其他事物关系。在第一重含义中,朱子“理一分殊”与“一多相摄”相近。法藏有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大缘起陀罗尼法”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相即关系是真如实相的体现;“一”就是真如佛身,而“多”则是万千现象,万千现象都显像佛性。朱子“理一分殊”与之相近,“理一分殊”强调“万理归于一理”,万千事物虽分理有别,但所禀性理同一。朱子“理一”和华严法性“一”都代表最高范畴,都象征普遍原则。
在第二重含义中,朱熹“理一分殊”与华严“一多相摄”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明显差异。第二重含义的“一多相摄”是“事事无碍”论的部分内容。“事事无碍”首先指法界缘起的境界,次指宇宙的最高层次即事事无碍法界,再次指观法的最终目标即事事无碍法界观,又指真知本觉。“事事无碍”论的一具体理论“十玄无碍”中有一门名曰“一多相容不同门”,明确讨论了“一”“多”关系:“一”是本体或个别事物,“多”是万物,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能容摄其他事物,“一”能容“多”,“多”可容“一”,虽彼此相容相摄,“一”“多”却不相混同。在这里,朱子“一”是统体太极,有明确的本体意义;而华严宗的“一”为了论述事事无碍,主要取个别现象之意,不是总体的一,相反“多”却具有总体意义。可以看出在形式上朱子“理一分殊”和华严宗“一多相摄”是完全相反的。从内容上看,朱子也与华严宗大相径庭。首先“一”在朱子处指统体太极、普遍一理,在华严思想中指一个具体事物;“多”在朱子处指各具太极、个别性理,在华严思想中指事物总体。其次在朱子处“一”与“多”即统体太极和各具太极在质上相同,在量上有别;还是法藏“一即一切”,认为“一”与“多”不仅在质上相同,在量上也可以通过圆融无碍达到相同。
总言之,华严宗“一多相摄”中的“一”若取本体之意,那便是本体与现象圆融无碍,这与朱子“万物统体一太极”所论述本体与现象关系相同,法性“一”与“理一”甚是相近;若是“一多相摄”中“一”取个别现象之意,那么朱子“理一分殊”与华严“一多相摄”在形式上互为颠倒,在内容上大相径庭。因此朱子太极本体论与华严宗“一多相摄”兼有异同,两者是否存在共性和差异须视具体释义而定。
三.理论落脚差异
朱子由于早年受李侗影响,重视“分殊”,使得其“理一分殊”本体论导向了格物穷理方法论。在朱子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意义最终还是落腳于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来。“万物各具一太极”为格物穷理提供了合理性,理在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天下事物无论大小差异皆有此理,而有理处就要格,于是朱子强调即具体事物去穷理。
朱子完全继承了程颐的格物方法“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⑨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格而达到对普遍理的贯通,也是朱子关于“理一分殊”的再阐释,为何要去格具体事物,是因为“万物各有一太极”,每一事物都完整地禀受了理,有理处便要格;又由于统体太极与各具太极的同一,所以通过对具体事物格的积累最终一定能贯通,把握到宇宙本体的理。但要注意的是,格物之理是分理,每一事物性理相同而分理不同。程颐说“万物一理”,朱子对此做解释:各有差别的万物受到一个普遍原理的支配,“普遍的统一天理体现于一切差别的特殊物理之上,一切具体物理都是普遍之理的个别表现。”所以虽然每个具体事物都完整地禀赋有理,但却是性理,各自的分理是有差异的,所以不能简单的格一物就可通晓普遍之理,相反只有通过对各种事物不断地格穷,才能实现个别到一般的上升,最终把握普遍之理。
朱子强调豁然贯通的状态倒是与华严宗“事事无碍”在精神境界上有所相似。通过反复格物的累积自然而然实现豁然贯通状态,标志着物格知致的完成,这也是“理一分殊”的一种境界论意义。在朱子处,要想实现从积累到贯通必须要站在“理一”即普遍原理的高度来观照“分殊”即万物各理,从万物万理上升到万物一理,格一物就要格多物,对一个具体事理的了解与对普遍原理的追求必然是自然连贯的,切不可停留于格一物而只知一理的层面。有人认为这种豁然贯通与禅宗顿悟相同,实有不妥,禅宗顿悟更强调当下显现,而格物穷理之豁然贯通不仅要求贯通之自然也要求积累,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倒是与华严宗更为接近。华严宗在修持中要求依次了解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四法界,“四法界说反映了对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辨证过程:由观现象到观本体,即由观常识层面到观真理层面,再观两者关系事统一而无矛盾,最后在综合事理统一的基础上,以理的同一,观照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和谐统一。”⑩法藏所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反映了一种站在普遍原理的高度观照万事万物的的境界,更是一种豁然贯通的状态,表现为一与一切圆融无碍,也就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朱子由“理一分殊”走向格物致知,虽然在心性境界上与华严“事事无碍”相似,但两者在最终的落脚点走向殊途。格物并不是仅仅要求达到致知的境界,致知是为了更好地践行。格物致知是从万事万物中得到所以然的普遍原理,但知晓普遍原理却只是前提条件,在此之上还须通过向内修养、向外践行,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格物致知不是一个终结,相反是践行体系的开始,正所谓“知先行后”。而华严宗“事事无碍”论指向了三重观法即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和周遍含容观。其中真空观是基础,理事无碍观是中心,周遍含容观为最终境地,与“事事无碍”四法界中后三法界相对应,强调通过观照空有、理事、事事三大关系来把握世界真实,从而获得精神解脱。格物致知的最终落脚于现实实践,而“事事无碍”满足于精神境界之实现。
总言之,朱子“理一分殊”为格物致知作理论依据,强调从普遍上升到一般,积累到贯通的境界与华严宗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境界相似;而后格物致知与事事无碍论却走向不同的方向,格物致知最终要落实到日常践行中去,而事事无碍论指向了如何解脱的观法。因此在“理一分殊”的现实落脚中,朱子与华严宗存在认识境界上的相似性,而在理论的实践方向上存在差异性。
综上所述,在思想渊源上,尽管“理一分殊”初创之时含有一定的华严因素,但朱子“理一分殊”完全禀赋自儒学传统的。在本体论意义上,朱子“理一分殊”与华严“一多相摄”异同随着华严“一”取意变化而变化,若取法性“一”之意,则两者相近;若取个别“一”之意,则两者相异。在理论落脚方面,朱子“理一分殊”为格物致知方法作全新阐释与论证,但不停留于格物致知的状态,最终指向现实践行;华严宗“事事无碍”论指向了三重观法,以求解脱为终极目标,止于实现心性最高境界。朱子“理一分殊”与华严“一多相摄”渊源上无甚关联,本体论内容上兼有异同,又在理论落脚处走向殊途,由此得之,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继承佛学思想较少,其真正内核还是儒学传统。
参考文献
①高建立.从本体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J].天中学刊,2015,30(06):50-54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⑩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