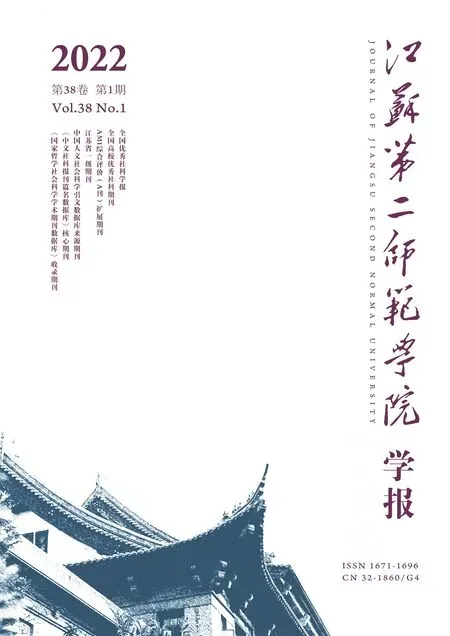孔子“近取譬”的思想意蕴与当代启示*
陈尚达 周其明
(1.皖西学院教师能力发展中心, 安徽六安 237012;2. 皖西学院金融与数学学院, 安徽六安 237012)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讲仁道重诗教,教人求君子之德,终生好学力行,追求圆融人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近取譬”是孔子仁学方法论,也是其成仁之教方法论,本文试图探析孔子“近取譬”的思想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一、孔子“近取譬”的思维性质与修辞功能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朱熹注曰:“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1]60清代刘宝楠则注为:“譬者,喻也。以己为喻,故曰近。”[2]250两者共性在于,拿自己来打比方,推己及人。所谓“假象取藕,以相譬喻。”(《淮南子·要略》)“通过‘象’或‘偶’对两个事物进行比附,以使它们彼此相互阐发和说明。”[3]“近取譬”的要义是在切近自己的地方去测度他人的处境和想法,隐含有人与环境及他人的一体化和贯通之意。然而,“仁”并非一个简单外求的对象,亦无固定的理解模式和行动方式,它必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人生践履与生活图景中,需要以自己恰切的方式不断生成。“由于个人的身份、阅历、习性和言说情境不一,言说类似的问题也就各有针对性和情境性,因人因时而异,往往心照不宣,事后的回忆也就因闻说者的理解而著录。这就造成孔子对某个理念的阐释,着重的不是它在逻辑限定上‘是什么’,而是在情境动态上‘像什么’和‘应如何’。”[4]由关注情境图景而非逻辑限定可知,“近取譬”是一种象思维,侧重具象认知,与概念思维侧重抽象推理区别开来。后者以概念为起点、普遍化、静态化、高阶对象化、事后反思化和后意义生成化;前者则是原发、非对象(能象)、补对而生成、纯势态、潜在全息、时化和原初地语言化[5]。这种“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的表达策略,表明言、象与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近取譬”具有比兴修辞功能。“比者,类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挚虞《文章流别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关于比与兴涉及意义生产的同一性机制和差异性机制之分,张大为教授指出,“比的理性机理,必然赋予经验以一种同一性的理性(意义)秩序;兴的经验机制,则必然指向一种敞开经验的意义丰富性和多样性”[6]。如子夏和孔子关于“素绚关系”的问对中,子夏针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论语·八佾》)的疑问涉及美女化妆话题,孔子故意绕开,以绘画施彩取譬,其同一性意义在于素绚的先后或内外关系,这启发子夏生发出“仁先(内)礼后(外)”的素绚关系联想,师生对话体现出诗性思维的次第展开。由孔子针对素绚关系取譬带来的思维开放性和指向性,体现出从《诗经·卫风·硕人》中美女装扮到日常生活中绘画施彩的语境转换,素绚关系的指涉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审美跃升到德行。
二、孔子“近取譬”中“近”的三重含义
立足“天—地—人”的共有共通生活视域,“近取譬”体现出对自我、他人及事物与事件的一体化关系的伦理关切。“这方法论是基于对人的两个肯定,一是人有共同的仁体,才可以与他人互相启发与诠释,另一是人与人是相关的,人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仁体的实现必须显在相关互动中。”[7]由譬喻的事物与事件、人与他人、仁道三者及其相互关系所决定,“近”主要有以下三重含义:
1.就近
这是指物理意义上的,针对人与物的关系而言,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习以为常的事物或事件。当然,这个“近”是相对的,也可以表达遥远的距离,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星星因为发光使得肉眼可见,远也就变得近了。
2.拉近
这是指心理意义上的,针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由彼此都熟知的对象构成沟通交流的思维通道,意味着利于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因物悉而心通。有学者指出,“实际上‘近’不仅包括自己,而且包括自己身边的客观物象,自己所熟悉的客观物象。既要推己及人,推己之欲及他人之欲,己之物及他人之物,还要推自己周围之物及他人周围之物,推自己与他人身边之物及他物等”[8]。借助物将人与己关联,物象关涉“人欲”而具有象征与暗示意味,耐人寻味,利于心理沟通,并促进人际交流。
3.靠近
这是指精神意义上的,针对人与仁的关系而言的,意味着向仁道的靠近,此即所谓“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就像上述以“北辰”譬“德政”,就是对统治者实施仁政的精神期盼。又如“司马牛问仁”(《论语·颜渊》)例中,孔子关于“其言也訒”的答复只是择取仁者的一个重要生活图景,以“訒言”譬“仁道”,以具象喻抽象,此系孔子贴近司马牛“多言而躁”的欠仁处言说,对司马牛而言是不容易做到的克己功夫,从而促使司马牛结合反思自身的说话不慎重去理解仁,使得“求仁”不再局限于弟子思想认识的增进,更在于促成弟子修身实践的改善,实现仁与人的关系从疏远走向和合,贯通一体。孔子“近取譬”的言说策略,印证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刘知己《史通·内篇·叙事》)。
由上述分析可知,“近”作为物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三重意义,体现从物悉到心通再到道合的思维递进性和整体性,分别指向人与环境、人与他人、人与仁道三者,共同指征天人合一。“近取譬”的意义就在于兴发个体生命,打开个体通向天地万物的生命通道,借视域的转换实现思想认识的升华,是刘铁芳教授指出的“弥合天人之道”。“孔子弥合天人之道旨在重新唤起个体从一己之狭隘的现实生活境域中超拔出来,朝向更广阔的宇宙天地境域,思考人之为人之理。”[9]
三、孔子“近取譬”的思想意蕴
“近取譬”体现出对日常生活中熟悉事物或事件的一种新的领会方式,物(事)、人、道三者,是一种整体性关联,引导人们从生活现象过渡到做人德性的深刻洞察。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论,“近取譬”可以看作是孔子启发教学的重要策略,是孔子引导弟子从生活视域出发,对所学对象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从而帮助弟子实现思想认识乃至行动方式的积极转变。借取譬立象方式传道解惑,追求“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由上述“近”的三重含义所决定,孔子“近取譬”的思想意蕴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直觉式的生命体验
“天地君亲师”是儒家的精神崇拜,是“天地人”的具体化。它表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追求做人的忠恕之道,做“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暗含着天人合一的感应生存模式,天道即人道。“在传统儒家看来,感应是万物生存的基本方式,生存即感应。”“贯通即感应”“感应即明理。”[10]这种感应本身,即是人与生存环境中的物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命体验,一种生命直觉。“近取譬”立足天地视域,在自我与他人的相互照面中,“近取譬”将思想认知定格在经验到的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中的生命实践图景中[11]。《论语》文本中孔子针对不同弟子发问的诸多“近取譬”运用,既仰赖于孔子的“叩其两端而竭”,也显现出当下与历史情境中的天人感应道德生命实践图景。师徒的心领神会与思想共鸣皆由愤悱之情催生,由天地视域内人的身体感官与自然事物社会事件感应而迸发,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生命气象。感应即求气化贯通之仁,又以气质之心合绝对天理。这即是张曙光先生指出的,“天与人互文性的实践解释学原则:人们以自己的‘意识’‘目的’乃至身体器官来理解和命名外部世界,又以人从外部世界中获得的感知和信念来引导和绳度自己的行为”[12]。
2.开启个性化的理解路径和言说方式
“近取譬”借助人我共有的生活视域,启发他人思考,寻求一种互动关系,体现出自觉与觉人的一体化:基于天地自然视域的自我觉察与诱发他人基于天地自然视域的心灵觉察结合。如同黄克剑先生指出的,“仁”作为一种心灵的境界,它可以传神于人的真切的生命体验而不可用言语授受于口耳,可得之于心而不可现之于目,它需要人在“求诸己”(《论语·卫灵公》)、责求自己切实践行的具体情境中有所觉悟。所以孔子教学往往取近取譬之途,亦即切近受教者的生命而取譬相喻[13]25。“近取譬”多是孔子本人的“觉会”,同时也是为了兴发他人的“觉会”。“《论语》的交谈是‘有来有往’,‘来者’有所‘觉’,‘往者’有所‘会’”,“‘觉’是由内心里涌现一指向根源性的发问,在具体的情境下唤起,在实存的生活世界中醒来,这亦是孔老夫子所谓的‘愤悱’之情。由此‘愤悱’进一步而有‘启发’也。‘会’是在交谈往来中,由于根源性的发问,由于愤悱之情的感动,使得吾人的生命与存在之自身融为一体,这是一具有存在实感的整体,它不可自己地开显其自己,启发来者。”“觉会所依,只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真存实感,此即孔老夫子所谓的‘仁’。”[14]显然,子夏诗性思维的生成和开显,以及其诗性思维与做人之道的关联,与孔子讲仁德与“近取譬”带来的思维启迪不无关系。此问对例向我们传达出师徒之间针对素绚关系理解的视域转换、思维变通和意义流变,表明“近取譬”的触类旁通性质,并“破除对言说及其所使用的语言的执着”[15]。“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个“绝四”,就体现出对他人凭借自身主观能动性体仁践仁的尊重、悦纳和包容,避免出现一种僵执自闭的心态,从而开启彼此个性化的理解路径和言说方式,追寻一种思维共生、思想融合的活泼生动的对话图景。
3.追寻天道人性的通俗化理解
天道即人(仁)道,作为孔子成仁之教的近取譬,是体现“下学而上达”即贯通天道人性的重要方法路径,接地气而通天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上》)“近取譬”作为思维切入口,既有形而下的器物具体可感之意,也有由近而远的形而上仁道指向的抽象可悟之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孔子借松柏耐寒这个自然现象,表达做人要讲气节,纵历经险境仍不失本色,字里行间表明为人当求君子之风。“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可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人无诚信不立,正如车无輗无軏不行。
不难看出,“近取譬”构筑了天道—人性—器物(自然)一体化视域及其相互关系,追寻天道人性的通俗性理解。器物本身只是一个中介,意在搭建理解天道人性的意义通道。它表明,作为一种高的意义上的仁道并非高不可攀,它恰恰融注于人伦日用的生活地带且须臾不离,所谓“道不远人”和“人能弘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季康子以“为政用刑”征求孔子意见,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并以“风”和“草”分别比喻统治者和百姓的道德品行,委婉劝导季康子要以德垂范,自然会民心归顺。这种形上形下统合的譬喻运用强调道德的感化力量,它和前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异曲同工,“草上之风”和“众星共之”都渲染出政德和美关系和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
四、孔子“近取譬”的当代启示
“近取譬”作为孔子成仁之教方法论,即君子之教。“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抑,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学记》)其激发学生诗性思维的“风化”特征,鲜明体现出“入”“伏”和“顺”三字的完美结合:“润物无声”的教化影响,“潜移默化”的觉悟开显,“顺应自然”的柔性转变[16]。教育重在育人,由“近取譬”而可“得意忘言”与“得意忘象”发现,意比象与言重要,意义向着不同主体的生活经验敞开,为主体精神挺立提供差异性的思维空间,引发贯通之妙显现和而不同,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才是根本。时代新人培养突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善思好学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者和接班人,“近取譬”是当下教育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方法论传统,它旨在促成学习主体的一种超越能力发生发展,体现出孔子的中道超越。 “中道超越是以体悟客观存有的天命和天道为前提,以主客观兼顾贯通为原则,以身心合一和仁礼双彰的人伦日用实践工夫为路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最高境界的超越形态。它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精神下,将上下、内外和左右三维六度有效贯通,力图达成天与人、内与外、自我与他者的中道平衡,通过即凡而圣的道德实践实现天人合一,完成超越。”[17]
1.知识传授建基于生活视域的诗兴发动
现代教育注重知识传授,对确定性知识本身的寻求往往成为教学中心,多关注知识逻辑的抽象演绎,却忽视了从学生的生活视域出发,无视学生心理逻辑的必要铺垫,从而导致不同个性和经验背景的学生思维差异没有得到尊重,思维活力没有得到激发。确定性的知识寻求的确是知识传授的主要目的之一,但要通过诗兴发动,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相关知识背景自主寻找确定性知识的主观思维路径,即寻求学科知识逻辑与学生心理逻辑的统一。“近取譬”就是基于共有的生活视域,让人于寻常中发现不寻常的好奇和寻求差异性思考的冲动。学生情感因此得以唤起,生命得到感发,主观思维能动性得到发挥。教师要告别简单的外部知识强加做法,转而能“近取譬”,帮助学生实现基于生活视域的确定性知识寻求,即由教材知识与学生经验贯通带来的自我超越。注重诗兴发动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发他们基于自身知识背景的个性化思考,就成为知识传授有效性的重要前提。
2.教学智慧在于视角开新带来的思维启发
与生本教学相对的,是知本教学或师本教学。其共同特征在于,都是从他者而非学生的经验视域出发来施教,大都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可接受性,更遑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这种“抓住一端用力”的教学思维,屏蔽了生活视域对学生积极主动思考的兴发作用。“近取譬”的智慧就在于贴近学生的生活视域,借助对熟悉事物或事件的新的领会方式,即共有生活视域的新思考,促成学生的思维启发。它是寻求与学生的对话的,既契合学生自我思维的内在发展方向,又能引发学生自觉自主的问题理解[18],前述子夏与孔子的问对例,“素绚关系”从化妆到绘画再到仁礼的不同表述,就体现出意义生产的互文性策略。显而易见,“素绚关系”涉及对象从化妆到绘画再到仁德的转换中,子夏提问时并没有想到素绚关系的仁德层面,经由孔子“绘事后素”的视角开新而有所启发,得以触类旁通。“所谓教学的生成性,乃是在如叶澜先生所言的‘教天地人事’的过程中,通过天地人事之教敞开个体与天地人事的关联,带出个体置身天地人事之间的存在,即让个体切实地活在天地人事之中,在自我生命中活出天地人事来,由此而在自我向着天地万物真实敞开的状态中‘成(就)’一种活泼开放而积极向上的‘生命自觉’。”[19]
3.教学幸福缘于心与道合而生的思想共鸣
应试教育过多关注分数和升学率,这种外在功利驱动让师生深陷题海;教师教学的标准答案情结棒杀了师生互动带来的思维碰撞与交织,学生极易陷入孔子所极力避免的思维固化甚至僵化的糟糕境地。孔子重好学并讲“叩其两端而竭”,运用“近取譬”方式开启新的思维空间,这种贴近学生生活视域共学的诗兴功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其享受由受启发而生的思想开悟带来的快乐生命体验,发出类似“起予者商也”的由衷赞叹。由“近取譬”发动的诗兴教育就是一种幸福教育,如同诺丁斯指出的,幸福的教育就是“开门”,而“开门的目的是邀请孩子们去探索”[20]200。“近取譬”就是“开门”,在“邀请”与“召唤”而非“灌输”与“强迫”中,鼓励学生尽情释放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师徒绝不停留并满足于获得一种正确答案,而是努力通过触类旁通去开掘彼此思维空间,追求由心与道合而产生的思想共鸣,既成全了学生的自我发展,也促成了教学幸福。这种追求“天—地—人”“人—物—我”一体化互动关系的方法论,将师生关系定格为学习伙伴关系,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共鸣性理解者和帮助者,师生一起挺进在学习的愉快旅途。这种因“近取譬”而促成的身心、人我、天人三重和谐境界,就是孔子提及的“成于乐”,也即追求一种中道超越的仁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