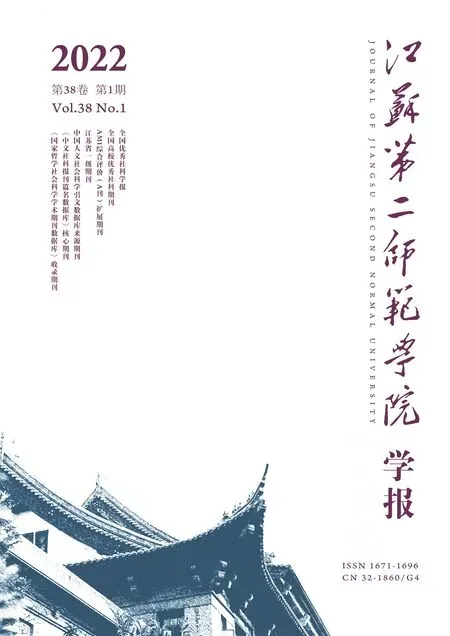学衡派新人文主义之伦理自信及其当代价值*
方旭红 都萧雅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4;2.重庆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重庆 400041)
20世纪初是中国近现代伦理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的中国伦理转型中伴随着两种并不合理但又非常突出的伦理现象,一种是守旧式的伦理自负,另一种是盲目西化的伦理自卑。守旧派的伦理自负主要以国粹派等为代表,认为中国伦理道德相当完备,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并以中国伦理统摄之。全盘西化的伦理自卑则以道德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个体为代表,他们既展现了变革者的理性和勇气,又夹杂着盲目西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自卑,既引导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又留下了文化自卑的深深阴影。在当时伦理文化转型的重要时代,学衡派是一个学贯中西,既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能意识到中国伦理思想的弊病,又有文化自信与坚守,并能用中西方思想理论阐发和展现这种伦理自信的思想流派。在历史急剧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方案似乎显得过于保守,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有与其历史作用不一样的意义。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是价值体系自信,关键是核心价值的自信。对学衡派伦理自信进行认识、反思,进而继承和发展,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信的建构和完善。
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伦理建构的方法自信
文化层面的自卑、自负和自信,首先产生于与其他文化的比较,并取决于比较过程中是否能够理性、全面而又深刻地认识所比较的各种文化之优劣,进而对自身文化做出自我评价和定位。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觉悟和伦理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比较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学衡派在中国传统伦理近现代转型中,秉持的是对中西方伦理思想进行全面比较的基础上批判继承而非革命的态度和方法。学衡派的伦理自信首先在于伦理转型和建构的视角与方法,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这既不同于国粹派守旧的中体西用,也不同于新文化派的革命方法、科学方法。“昌明国粹”表达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精粹的肯定和自信,“融化新知”表达的是对自身文化缺陷的意识和对其他新文化的融摄。
学衡派对中西方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横向比较,能客观认识和发掘传统伦理的价值,并主张对中西传统伦理的精华进行融合发展。虽然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阶段,但学衡派同仁对西方文化的审视,并没有只眼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阶段,而是针对当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些弊端,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下,特别重视古典主义人文精神。学衡派对西方上自古希腊,下至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伦理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并能认识西方现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继承发展关系。吴宓认为,新文化派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不能代表西方文化的整体和主流,“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2]。他们对孔孟伦理思想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中西方传统文化在提倡人性的崇高,追求人文精神方面有相通的地方,这种人文精神正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旨趣所在。胡先骕认为:“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曰亦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而折中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3]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无视西方传统伦理精神的做法不以为意,也反对他们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极端批判。在那个急需革新的年代,强调传统的价值似乎显得过于保守,不能切中彼时文化问题的和历史现状的要害,但其实不然,问题的本质还是合理性本身,是能否理性认识这种视角的合理价值的问题。
学衡派在中西古今伦理思想的纵向比较中坚信伦理文化既有发展与革新的必要,也有保守和继承的普遍价值。应该以人类千年历史发展的眼光把握伦理发展的时代方向,以批判性的时代精神审视传统伦理。学衡派认为西方的现代启蒙价值的确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但西方的传统文化是其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思想源泉,并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有救偏补弊的价值。用西方的现代伦理价值对比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也确实更容易发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落后之处。但从西方现代文化困境和危机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传统伦理,同样也更容易发现中国传统伦理的时代价值。因此,白璧德就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魄也”[3],应当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技术,以求进步和发展,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些不是根本,而是枝叶。真正要追求的是人文精神的进步,“孔子曾这样赞美他最钟爱的门徒‘始终在进步,从未停止过’。孔子心中所想的进步,显然是根据人律而言的进步;而十九世纪的人所说的进步,则通常是指物质进步”[4]2-3。白璧德批判新文化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认为其忽视了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这也是学衡派诸人高度认同的。
学衡派强调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延续性、民族性统和世界性的统一,并对此方法和态度自极为自信。学衡派在建构自己的伦理认同过程中,始终坚持伦理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以此为民族之存续提供文化保障。吴宓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5]96-97他们反对新文化派“弃旧图新”的道德建构方法,如柳怡徵指出,“中国文化之根本,便是就天性出发的人伦,本乎至诚。这种精神方能造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过数千年光荣的历史”[6]。学衡派虽然注重实证的、侧重个人内心自省的人文主义,但他们仍然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能把握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民族并能延续其存在的关键在于文化精神,而新文化派主张的“弃旧图新”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同时,学衡派也强调伦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即对普遍价值的追求和实践。柳诒徵指出:“一国家一民族之进化,必有与他国家他民族所同经之阶级,同具之心理,亦必有其特殊于他民族他国家,或者他民族他国家虽具此性质,而不如其发展之大且久者。”[7]人类多样性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必然有“多”中之“一”的统一性和世界性。郑师渠指出:“学衡派摆脱了东方文化派隆中抑西的虚骄心理,也超越了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具备了较比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8]86这种比较健全的文化心态就是文化自信,核心是伦理自信。
二、“以理制欲”归本“中道”:伦理价值自信
伦理文化的自信,其核心是价值体系的自信。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已经无法作为一种整全的系统帮助中国人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保守派依然还没有从旧有价值的自我陶醉中觉醒,又或者出于孱弱民族的自我防卫而固执地保守着旧价值。新文化派则从进化论、科学、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的视角,彻底批判乃至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伦理之价值。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虽然是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逐步形成的,但伦理价值的自卑实则全面开始于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文化的全盘鼓吹和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文化倾向。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自卑,对个人而言可能会造成价值混乱和迷茫,对民族国家而言可能会造成历史文化认同被削弱,进而可能会出现历史虚无主义,解构民族国家认同。学衡派对此两种价值取向都持否定态度,在继承白璧德人文主义“中道”价值的基础上,融合并阐发了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中庸”价值。既肯定新文化派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又否定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情感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张“以理制欲”“归本于中道”[9]的伦理价值,既不自负地因循守旧,也不自卑地极端否定,而是建设性地有所损益。
学衡派对“中庸”伦理价值的建构逻辑和核心内容有最基本的理论自信。学衡派的伦理价值自信,主要体现在其通过中西融合所形成的“一”“多”融合的世界观、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及“以理制欲”“归本于中道”的价值观逻辑及其体系中。就世界观而言,学衡派坚信“一”“多”融合,“物质之律”和“人事之律”的区分与平衡,才能全面把握世界的本质,并为伦理价值提供世界观基础。他们批判新文化派过分提倡进化论的、科学的世界观,认为它们只把握了世界自然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不同,不能完全用自然规律来理解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吴宓认为白壁德“一”“多”融的世界观是合理的,不但适用于自然世界,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即“世之所谓一,又有所谓多,有能合此二者,吾将追踪而膜拜之”,“一”是绝对的观念,“多”指心具体的事物。所体现的是人类对世界的哲学抽象理解,而非对自然规律的直接反应。就人性论而言,学衡派主张人性二元,并坚信只有人性二元才是建构道德的基础。学衡派批判新文化派过度提倡自然人性论,既反对基督教的性恶论,也反对卢梭那样的自然情感角度的性善论,主张人性二元论。如吴宓指出,“人之心性(Soul)常分为二部,其上者曰理(又曰天理),其下者曰欲”[10]“人性具善恶两元之元素,殆为不可掩之事实”[11]。他们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至于为善还是为恶,则取决于人自身的选择和意志,并认为只有人性二元论才能合理解释人的自然性和崇高性,才能体现出道德行为取决于人自身意志选择的特性。孙尚扬指出:“对人类理性共通性和生活法则的统一性、普遍性的乐观信念及对西方文化的传统主义态度则使《学衡》既与国粹派,也与提倡新文化者区分开来。”[12]12这种对“理”的普遍性和崇高性的追求和自信,是学衡派新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就价值观而言,学衡派坚信“中庸”之道最理想的价值原则。人必须有人文精神,才不至于任情纵欲落入自然主义,而人文价值包含自然性并超越自然性,即“以理制欲”“归本于中道”。白壁德说,“予尝佩服孔子见解之完善,盖孔子并不指摘同情为不当(孔子屡言仁,中即含同情心之义),不过应加以选择限制耳”,并且他还肯定了孔子思想比亚里士思想多更完善的地方,认为“孔子固非神秘派之轻视理智者,然由孔子观之,理智仅附属于意志而供其驱使”,即“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人道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3]。也就是说,白壁德新人主义特别注重意志,他对人文主义的理解和对孔子人文精神的肯定,给学衡派坚持“中庸”伦理价值体系提供了西方人文主义理论的支持,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强大的伦理价值自信。
学衡派对“中庸”伦理价值之合理性有实证之自信。白壁德的人文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新人文主义,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白壁德的人文主义也借鉴了实证科学的方法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一再强调自己的人文主义实证于人类千古历史文化之经验。学衡派自信其“中庸”伦理价值实证于人类历史和经验。白壁德认为,“古来伟大之旧说,非他,盖千百年实在经验之总汇也”[3],并明确阐述了类似科学实证的方,“盖今人世自有其律,今当研究人世之律,以治人事。然亦当力求精确,如彼科学家之于物质。……不必复古,而当求真正之新。不必谨守成说,恪遵前例,但当问吾说之是否合于经验及事实”[13]。古代先贤对理性的肯定,对“以理制欲”相通性的认识都是新人文主义的实证之依据。学衡派也自信其“中庸”价值亦可以实证之于当世人类之经验。学衡派新人文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批评焦点在于,知识和情感的无选择、无节制的扩张可能会导致任情纵欲之自然主义。白壁德认为科学派人道主义的代表培根和浪漫派人道主义代表卢梭就是典型的反面实证案例,“培根生平纳贿贪财,以此得罪,非无辜也。……卢梭所生子女五人,均送至育婴堂孤儿院,不自抚养,亦非无故也”[9]。是他们坚持知识和情感的无节制扩张导致的必然结果。从当时的世界秩序现状来说,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列强之间的残酷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残酷的现实证实了白壁德对科学的自然主义及情感的自然主义的担忧和批判,这种自然主义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梅光迪认为:“帝国主义,即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又为极端的帝国主义。”[14]219为了一国之私利私欲而置人伦道德于不顾,发动残酷的战争,是盲目的科学理性和极端的浪漫情感导致的国家层面的任情纵欲。实证和理论逻辑结合,坚定了学衡派伦理价值之自信。
三、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情怀:伦理实践方式自信
学衡派新人文主义坚信家国天下伦理共同体对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家园性地位。新人文主义更注重个人内心的节制和规约,表面上看,学衡派更侧重于个人的私德修身和自我完善,但家国天下情怀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实现方式,在学衡诸人身上仍然是一以贯之的,强调的是伦理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奠基于他们的“中庸”为核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吴宓明确指出:“吾论事之标准,为信‘一’‘多’并存之义,而偏重‘一’。且凡事以人为本,注重个人之品德,吾对于政治社会宗教教育诸种问题之意见,无不由此所言之标准推衍而得。”[15]学衡派在世界观上坚持“一”“多”融合,强调“一”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包含了对某种实体的认同和皈依。这个实体应该包含了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抽象的层面即是普遍性的“理”或者“天理”,具体的层面则是各种形态的伦理共同体。学衡派强调“一”“多”融合,“物质之律”和“人事之律”的平衡,本身就是包含着对个体和共同体相统一的肯定。学衡派人性之论也是如此,所谓人性中有低下的部分和高上的部分,都是从共同体的类本质作考察的,而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做的解答。特别是“人性中高上部分”即“理”或者“天理”,仍然是抽象的普遍性,它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就是爱的智慧和情感,爱的智慧和情感展开来,就是天理与人性的统一。柳诣徵也说:“仆尝谓吾伦为二人主义,二人者,即所谓相人偶也,相人偶者,由个人而至大多数人之中,必经之阶级也。”[6]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从家庭到社会,由民族国家而“天下”,没有共同体就没有各种爱的情感和认知,也不可能有爱的体验。正如郑师渠指出的,吴宓总结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时认为,“圣”“君子”“士人”“士”必须具备的内涵有:“内圣外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兼济天下”[8]98等。所以,合理的家国天下情怀就是个体与实体统一的中国式表达。
学衡派对家国情怀的阐发与自信。与新文化派强调个人相对于家庭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权利不同,学衡派更强调家庭和国家的伦理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地位,强调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伦理义务。吴宓肯定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个理想的终极是明明德于天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最高追求。要明明德于天下就要实现天下太平,前提是国治,国治的前提是齐家,齐家的前提是修身,修身的核心是道德,本质上是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家庭和国家是两大伦理共同体,个人的伦理实践离不开这样的实体性家园。就家庭而言,当新文化派倡导青年人要走出家庭,走向独立的时候,学衡派担忧的是过度的个体化对家庭共同体及其伦理性的消解。学衡派不否定个人的地位、尊严和人格等权利,但更强调要把个人价值放在共同体中建构和实现。当新文化派批判传统伦理只教人做臣、子、妻的时候,柳诒徵直接反击:“不知道教人知道为子之道,正是教人为人”[16]。孝、慈、悌等道德价值和规范,是对家庭伦理共同体蕴含的普遍性的表达,只有在家庭共同体中才能确立、认识和践行。就国家层面而言,九一八事变之后,学衡派诸人表示抗敌保国是全体国民的神圣职责。1932年柳诒徵、缪凤林主持创办的《国风》发刊词中特别强调应该“奋发自强为吾国一雪此耻”,杂志宗旨把为国格而努力当作核心目标,即“格物致知,择善固执,虽不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见,要以(品)人格而升国格为主”[17]。这也是学衡派诸人根据抗战需要对其学术旨趣做出的调整,体现了更加浓烈的爱国情怀,“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18]145,这仍然是在道德的层面强调爱国的伦理义务。
学衡派对“天下”情怀的拓展与自信。“天下”情怀是中国传统一直存在的文化基因,是立己达人的道德理想在人类社会最高层面的要求。学衡派试图通过中西融合建构一个世界性的人文主义体系,并希望通过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来建构一个天下太平的人类伦理共同体。吴宓指出:“爱护先圣先贤所创立之精神教化,有与共生死之决心。如是则不惟保国,且可进而谋救世。”[13]学衡派新人文主义者自觉肩负着报国救世的“天下”主义的情怀,他们试图建构的人类伦理共同体,是“一”“多”融合、“理”“欲”统一的“中庸”道德价值在人类社会层面的现实形态,是以爱为核心,以“理“为爱的形式和逻辑,情理统一而建构的伦理共同体。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不是仅仅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修道者,甚至不仅仅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更有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深关切。其胸怀之广博,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的民族性,这在白壁德和学衡派诸人身上都有自觉的体现,比如他们认为,“白壁德先生立论,常从世界古今全体着眼,本不屑计一国一时之得失,然而足矣为吾国人指示之途径”[13]。站在人类共同体的高度,所建构的“理”才能更具有普遍性,才更合乎学衡派新人文主义价值理想。
四、“中庸”境界:伦理超越模式自信
学衡派认为宗教信仰不足持,人道主义的信仰不可能。学衡派坚信人类需要理想和精神超越,有追求至善境界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精神超越的需求。而这种精神超越需求不仅仅由宗教满足,也可以由其他类型的文化满足。学衡派既不支持宗教信仰为现代社会的主流信仰,也不认为科学主义和浪漫的情感主义能成为人们的合理信仰。首先,学衡派认为宗教的不合理内容在科学和现代价值的批判下,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宗教在现代性社会已然式微,难以独撑现代人的信仰体系。白壁德指出:“文艺复兴时代实为前代重神性太过,人性不足之反动。中世之神学,足矣使人性之若干方面桎梏窘乏,又其事神之观念过强,乃至人生之才智机能,均加以致命之束缚。”[19]虽然他仍然肯定宗教中的人文精神,如谦卑之德,上帝的崇高人格等,但不认为宗教能成为独立且合理的人文信仰体系。吴宓也指出:“宗教必不脱迷信,如耶教之三位一体,童女诞圣之类,实与科学事实不合,难以强人遵从。故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坚持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宗教之事,听其自然。”[10]学衡派显然不相信宗教可以成为现代的主流信仰。其次,学衡派更不相信科学的人道主义和情感的人道主义能成为人们合理的信仰体系。信仰科学主义,容易把自然之律和物质欲望的满足看得过重,比如培根被功利驱使,贪财腐败,“这种堕落与进步观念有着相同的起源,由于过分追求自然法则,他忽略了人的法则;在寻求获得对事物的控制时,他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9]。而卢梭追求不受约束的浪漫主义的自由,连最基本的抚养子女的义务都看作是对他自由的妨碍,“美德不再是独处时内心深处的细腻呼声,不再是出自自我约束的要求。美德已成为热情的一种形式,它要被提高到与激情同样的高贵地位”[9]。因此,学衡派认为,宗教和人道主义都无法满足人们的信仰和超越需求。
学衡派坚信“中庸”境界的伦理型超越模式。学衡派认为,在宗教式微的情况下,人类的精神超越只能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实现,而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中庸”境界,可以发展为一种精神超越模式。白壁德认为:“诸种观念之中,以善恶之观念最主要,盖善恶之观念即上帝,亦即人心中最高上之部分。”[13]善的观念最崇高,具有神圣性。胡稷咸指出,“人群进化之最后目的,在实现吾人之理性,使天下归于仁”“人类生存最高上之目的,为道德之发展,则余所深信,虽雷霆万钧之力不能变也”[20],道德是人生绝对的目的,具有至上性和超越性。中国文化早就从宗教信仰满足超越的模式进入了通过伦理信仰满足超越的模式了。梅光迪对白壁德的观念评述说:“他相信人类有某些神圣而不言传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极具宗教信仰的,但称自己的宗教是‘一种伟人的宗教’。它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中介慈善机构。以儒家的观点来看,这种宗教是一个具有高尚的道德准则的实体;每个时代,这些准则都鲜活地,而非机械地,由几位突出的人物加以体现。”[14]243这些突出的伟大人物是践行“中庸”道德价值的典型代表。学衡派的“中庸”模式之所以能实现精神超越,其根本就在于“理”或“天理”与“人性”之属性,以及“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构造。所以,吴芳吉说:“吴近日感触,一在生命短促。故扩充人类生命,为我辈书生最大天职。”[21]577吴芳吉所要扩充的不是生理性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价值的提升,而这可以通过伦理文化信仰的方式来实现。
学衡派对“中庸”伦理信仰超越机制的自信。“智”“仁”“勇”辩证统一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信仰的超越机制,也和学衡派强调知识、情感、意志相统一的人文精神相契合。信仰是人们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强力的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统一。学衡派认为宗教、科学的人道主义、情感的人道主义都不能做到这三者的统一。虽然宗教信仰在谦卑、节制、高上意志、情感上仍然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超越色彩,但在认知的方面,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解释有很大缺陷。解释世界和人类的理论体系本身不具备彻底性和合理性,其信仰机制就必然有逻辑上的缺陷,这也是近代宗教信仰被启蒙思想家尖锐批判的根本原因。科学的突出优点是知识体系,对自然包括对人的解释都有它合理的地方,但科学缺乏崇高意志和情感,只求理性知识的扩张也无法满足信仰的特征。浪漫的情感主义主张无节制的同情,使是非善恶的标准个人化、主观情感化,也缺乏对个人欲望和情感进行节制的意志,同样无法形成合理的信仰机制。学衡派自信“中庸”伦理信仰之所合理,是因为融合了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统一。吴芳吉说:“余乃笃信性善之人,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此物此则,必至公也。尽人而皆同也,必至永也,历世而不变也。至永至公,乃所谓善矣。”[22]学衡派一再强调人类社会有自己的“人事之律”,而“人事之律”的首要标准是“至公”,是“理”或者“天理”的普遍性。学衡派也特别强调情感,强调情理合一,认为“但有博爱不足也,但有选择和规矩,亦不足也,必须二者兼之”,而这个规矩就是“全体人类自有其公性与同具之真理存”[9]。同时强调“以理制欲”归于“中道”需要意志,因此白壁德赞美孔子:“诚亚里士多德者学问知识之泰斗……而孔子则道德意志之完人也。”[13]总之,“中庸”的伦理信仰是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统一。
五、学衡派伦理自信的当代价值
学衡派新人文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从伦理转型方法、伦理价值体系、伦理价值的实践形式,到伦理型精神超越模式,始终体现着强烈的伦理文化自信。学衡派的伦理自信既是对当时守旧派伦理自负的纠偏补弊正,更是对激进主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伦理自卑的纠偏补弊。在那个激进与保守激荡的年代,学衡派虽然或多或少也存在一些对传统伦理弊端认识不够彻底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是一个能在伦理思想转型方面理性自信的学术流派。他们以人文主义为体系的伦理转型是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实践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也很有启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建构需要合理的方法。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总方法,一句话大致上道出了伦理文化发展的历史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而言,也必须坚持这三者的统一。首先,需要对中华民族历史文的认同、继承和发展,坚持伦理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没有传统的伦理文化发展史,就没有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其次,强调伦理文化的民族性,伦理道德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民族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的精神融合于历史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中,正如胡芮所言:“中国历史传统首重‘人文’。”[23]再次,坚持伦理建构的世界视野,广泛吸收人类伦理思想的优秀成果,通过世界交往和文化对话的方式努力建构具有普遍价值的原则和规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建构价值自信。学衡派坚持“一”“多”融合、“善”“恶”二元,“以理制欲”归于“中道”的核心价值体系,坚定地继承了传统价值中的优秀内容,并且开放包容地吸收了西方新人文主义的价值理论,是我们最应该思考和借鉴的地方。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的精华应该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礼”“仁”“义”“理”“道”等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之为人普遍价值的思考,“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代表着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物质和精神关系的思考。“中庸”作为仁爱的最高境界表达着中国人对价值的独到理解,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个体和共同体的统一。在后现代性、多元化、功利化、个人主义等思想文化盛行的当下,应该将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优秀内容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互相阐发,建构具有普遍解释力、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自信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需要家国情怀的实践形式自信。强调个体对伦理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是学衡派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建构与实践离不开共同体,没有共同体人就是抽象的、无意义的存在。正因如此,“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从家庭伦理共同体开始,然后走向社会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天下”共同体,以至于宇宙万物共同体的拓展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浓厚的家国天下情怀,特别是“天下”情怀,这也是中国志士仁人最终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追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家国天下情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信的重要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需要精神超越模式的自信。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为人们提供了主流价值信仰,核心就是“克己复礼”的“中庸”之道,这也是学衡派始终坚守的信仰模式。在儒家的价值信仰中常常把自己生命价值的提升和超越与现实的生活、他人的命运、民族国家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独特的方式继承和践行着“立德”“立功”“立言”的伦理超越模式。可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深远的中国精神根源,也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支撑,是对中国儒家伦理型精神超越最合理的现代表达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