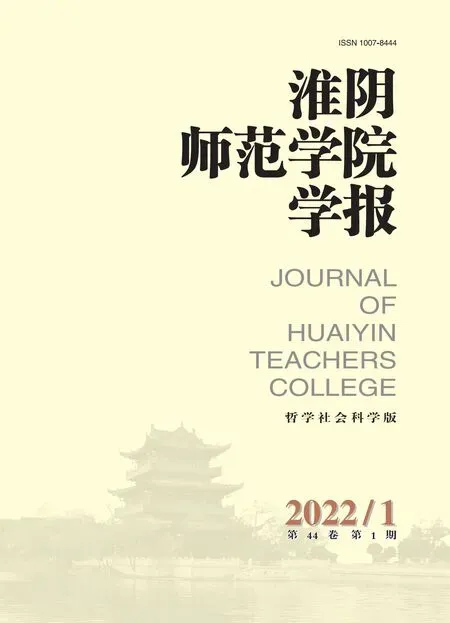新出碑刻资料与华北地区禅宗史研究
——冯金忠教授访谈
冯金忠, 管仲乐
(1.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学刊》杂志社,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2.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一、“新出材料”及新出碑刻资料的概念及价值
管:冯先生好!您长期从事佛教史的研究,并连续发表了大量通论著作和个案研究。相关论述和观点在您所著的《燕赵佛教》《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唐代地方武官研究》,以及参编的《燕赵文化史稿·隋唐五代卷》等著作中皆有述及,成就斐然,裨益学界。近年您的关注重点之一为华北地区禅宗史研究,并对于新材料给予了更多关注,尤其提出了“重构中国禅宗史书写模式”的主张,通过整理和研究大量新的碑刻资料,树立了一个崭新的禅宗史研究方向和目标,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就我个人而言,由于以往读书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传世文献以及既往整理的出土文献,对新出土的碑刻资料关注较少,因此特别希望就“新出碑刻资料与华北地区禅宗史研究”问题,向您请教。
冯:你有这样的认识很难得。21世纪是中国史学研究资料和方法嬗变和转型的关键时期,21世纪的史学不能完全舍弃既往的研究传统,但又在新的资料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很值得研究。
管:近百年,我国许多地方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如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敦煌文献等。它们数量庞大、涉及内容广泛。随着简帛佚籍的不断问世,其重大价值也逐渐被发现和重视。源源不断的新史料被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开展。但如何定义新出史料,以及如何对待及评判新史料的价值,尚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之处,需要思考、辨析和校正,以使历史研究更加健康地开展下去。因而,关于何为“新材料”,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材料,以及在新材料使用过程中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先生的指教。
何为“新出材料”呢?主要包括如下几种:其一为考古发现中新出土的文物;其二为受政局影响,过去保密等级较高,现在逐渐解禁,并已面向社会公开的解密文档;其三为最新被解读和认识的文献材料,包括隐匿于普通百姓手中的民间材料。这些新材料要么因人为原因,要么因客观原因长期脱离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材料本身无所谓新旧,它们也都算已存材料,只不过从史学研究和可接触性及采用性的角度来说,它们的出现是“新发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简牍、文书、档案、石刻等新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这既是对之前讲求宏大叙事、以论代史等学术倾向一定程度的纠偏,转归实证传统,是学术研究趋于深入细化的表现,更大程度上则是全国各地在经济发展带动下逐渐萌生文化自觉、积极挖掘当地文化资源的产物。当前国家层面对资料类整理的支持力度也是空前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自不待言,仅从这些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来看,2016年重大招标项目中资料整理类37项,占总数213项的17%;2017年70余项,占总项数331项的1/5强。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一旦回归,便会以极强的史料价值对原有的材料进行证实或证伪,即要么对原材料进行补充印证,要么直接推翻原有的定论,其史料价值颇为重要,可强劲地促进史学研究向前发展。
管:在诸多新出材料中,您特别提到应该充分重视碑刻等考古资料,尤其是新出碑刻资料,进一步拓宽资料来源。碑刻文献作为重要的“同时文献”,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大量研究者并没能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对其加以充分挖掘和利用。能否具体说一下碑刻资料中“新出”二字的界定范围,以及碑刻文献在禅宗史研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冯:碑刻是以石质材料为载体的铭刻文字、图像,有摩崖、碑碣之别。本文所说的碑刻,以“碑”为主,兼及其他石刻,是广义的概念。在石上刻字记事古已有之,殷商时期即有石刻文字,秦汉之后更为盛行。碑刻文献类型十分多样,包括:刻经、寺记碑、功德碑、题名碑、寺产碑、塔铭、经幢、敕文札子碑、造像记等。我国碑刻文献数量庞大,分布地域也十分广泛。碑刻之于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又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尤其是近些年来新出土和发现的碑刻资料,也就是新出碑刻资料,在传统金石著作、方志、今人汇编等书中未予以著录,或仅有著录而未有录文者。具体来说,包括三类:一为21世纪初以来,新出土、新发现的;二为虽然不是近些年的新出土、新发现,但一直以来未有人著录者;三为虽然有著录,但著录内容存在较大问题和瑕疵,如著录要素不完整、不规范,特别是碑阴等未著录录文者。以史学研究而论,这些碑刻资料是传世纸质资料的重要补充,不但有补史证史的作用,且可以开辟史学研究新领域。
碑刻文献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形式,靠其保真性和持久性等一系列特点,占据着其他形式的文献所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传世典籍一般都曾经过后人的整理、改动,加上书籍流传过程中的佚脱毁损、辗转传抄、翻刻,都不大可能保持原貌,尤其是文字的改变更大。碑刻作为出土文献,文字一经上石,本身就不易改动,碑志在出土之前,深埋地下,无人篡改,如地下原始档案。一经出土,便成了最具原生意义的文献资料,属于“一次性文献”。因此,其真实性特别强。虽然也有翻刻和伪刻,但好的翻刻就文献意义而言一般不怎么失真,伪刻可以鉴别;拓本也有先后,一些著名碑拓,往往不止一个本子,有的拓本虽可能会经过后世的挖洗和补缀,但语言文字上的改动不会很大,而且可以通过众本进行校勘。材料的可靠性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保障。相对传统文献形式,碑刻文献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所记多为当时事,且不似刊本迭经传刻,较大程度上保存了文献之原貌。其二,许多碑刻中的人物、事迹为佛藏、文集、僧传、志书等传统典籍所未载。其三,从史源学的角度看,传统僧传中一些传记即来源于石刻文献。
当然,碑刻文献再利用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障碍。其一,搜集困难:数量庞大、零散,不系统,难以充分利用。其二,识读困难:风化泐蚀,加之人为破坏,许多残缺或者字迹模糊不清。其三,利用困难:许多为文物部门掌握。当前著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录不全、整理不规范(往往只录碑阳,而碑阴、碑侧失录)、原碑行款格式等信息失载,录文不准确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多加留意,并且通过实地踏查积累经验。
二、新出碑刻资料在河北禅宗史研究过程中的利用
管:使用碑刻离不开田野调查。我们在田野中寻访古碑,游神冥想,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历史文化氛围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那些不被史籍收录的碑文,大大扩充了史料来源,更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增加了研究者的历史感。冯老师是佛教碑刻田野调查的践行者,在您数年如一日的华北地区禅宗史的研究过程中,通过亲自踏查,发现并辑录了大量碑刻资料。您能列举几条您勘察发现的,对于禅宗史研究有所补充的新见碑刻资料,并向大家介绍一下正确地利用、解读、辨析这些史料的方法吗?
冯:这类文献很多,但多数比较零散,不同的史料能够为禅宗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命题和线索。比如说,通过新见碑刻,可以对禅宗在河北地区的流传有所了解。如《大周广阳山漆泉寺重修禅院碑》,此碑原立于河北省沙河市西约40公里渡口乡寺庄村北漆泉寺遗址。碑额为高浮雕螭龙纹,高60厘米,天宫线刻一尊趺坐于莲花高座之上、施无畏印的佛像,佛像高60厘米、宽34厘米。佛像左右两边有字,右边一行楷书曰“共修福人石感师”,左边一行楷书曰“同行构人霍法雨”。石感师、霍法雨当系出资造龛之人。佛像之下为碑文,碑身高34厘米、宽85厘米,其下端有残缺。楷书,间有武周新字,所刻立时代应为武周,具体年代不详。
秦铁崖四顾,搜寻乔十二郎和老太医。李太嶂、李双岱那些手下,除了烧伤严重不能跑的,其余都作鸟兽散,不见踪影。老太医和罗香正蹲在地上,守护着一个人。
该碑碑文共22列,其中第18列有关键的“置黄梅于此地,有愿□助智种□”一句,所谓“黄梅”便是禅宗的代称,黄梅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处,是我国佛教禅宗发祥地,自古就有“蕲黄禅宗甲天下,佛家大事问黄梅”之说。六座禅宗祖庭,黄梅独占两座(四祖寺和五祖寺);六位祖师中,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三位祖师都在黄梅修行并传承衣钵。而河北沙河市发现的此禅院碑,恰好印证了禅宗在河北的初传情况。
现在学界普遍将禅宗形成时间认定为道信及弘忍创立东山法门时期。弘忍有包括神秀、慧能在内的十大弟子,由于碑刻文字残缺,尚不能完全判定碑文作者是哪位僧人,也不能判定该弟子和弘忍是否构成师承。但是这条史料至少可以证明该僧人和“黄梅”存在关系,碑文中所述的“唯裁投绳则直行不言而远信”等传法特征,也与早期禅宗传法的情况相符。因而,碑文中出现武周新字,虽然不能据此完全论定此碑为武则天时期所刻(现在尚处于资料的整理期,这仅仅为一条孤证,还需要其他资料进行补充),但是也为武周时期禅宗在河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条有力的佐证。
管:自秦汉迄晚唐,碑刻的功能经历了由实用至传世的渐变,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许多新变。石刻被宋人广泛应用到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影响甚大,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像您所述的《大周广阳山漆泉寺重修禅院碑》这样的碑刻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见的信息,的确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但利用的前提是对其进行甄别和考证。中国传统学术就把考据置于治学的首位,欧美史家也总结出“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的方法,都是力图把史学研究建立在辨别史料的基础上。不过,这些考辨史料的方法,大体是针对传世文字材料而形成的。碑刻资料为主的新见史料由于类型和形式更加多样化,考辨史料的方法和技艺也愈加复杂多样,我们面对这些资料应该如何有效地进行甄别呢?
冯:近年来,新的地上、地下史料纷纷面世,推动了史学的大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史料观念的偏颇,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极为重视新史料,忽视、淡忘甚至鄙弃旧史料。这表现在对新史料缺乏考辨的情况下匆忙使用、不注重旧史料的阅读与研究、急功近利的历史研究观念等方面。
对待新出碑刻,乃至其他各种类型的新出资料,不要盲目迷信,要与旧的碑刻资料,特别是应与传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慧能碑(王维)的发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2008年,邢台开元寺广场发现了慧能碑的残碑。这也成为研究者认为慧能的一位弟子——神会到过邢台的重要证据。此碑为神会延请王维撰文,蔡有邻书丹。此碑曾长期失传,《全唐文》有此碑文。考察史料,神会所建的《慧能碑》不止一处,还有一块为唐代兵部侍郎宋鼎撰,河南阳翟县丞史惟则用八分书丹。此条后引《金石录》记载,“曹溪能大师碑天宝十一载二月立”。这条碑文也载录于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引北宋欧阳棐《集古录目》:“天宝七载(748),神会建能大师碑于开元寺。”
神会在禅宗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唐代甚至被尊为七祖,被认为是慧能的继承者。胡适称神会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并在晚年进一步评价其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者,印度禅的毁灭者,中国禅的建立者,袈裟传法的伪史制造者,西天二十八祖伪史的最早制造者,《六祖坛经》的最早原料的作者,用假造历史来做革命武器而有最大成功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可见,胡适总体肯定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慧能在中国佛学史上的地位,证明慧能碑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这两块碑为神会邀请王维、宋鼎撰写,并且二碑都与开元寺有关。这就引申出了两个问题,即神会是否到过邢台开元寺,以及开元寺的两块慧能碑是否为神会所立。《河北佛教史》作者张志军先生曾猜测,神会大师曾驻锡开元寺,并将六祖慧能的顿悟禅法播扬于开元寺。刘顺超先生也认为神会先后于天宝四年、天宝十一年两次来到邢台开元寺为慧能立碑。上述学者都将神会与邢台开元寺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认为上述论断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景德传灯录》《宋高僧传》等典籍《神会传》中均未提及神会到过河北。提到神会和邢台开元寺有直接关系的《宝刻丛编》,以及清光绪《邢台县志》均非第一手文献,对其进行利用应该持谨慎态度。其次,综合史籍记载,天宝七载,神会不可能在邢台开元寺,应在荆州开元寺。再次,《宋高僧传》卷八《慧能传》云神会“于洛阳菏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绘其影”。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当时神会受宋鼎之邀来洛阳为慧能建真堂,立碑地点为洛阳而非河北。总之,通过上述材料推断,本人认为神会是否到过邢台开元寺,以及在开元寺立碑等问题上,疑点颇多。当时由宋鼎撰写的能禅师碑在全国有多处。在各地树立此碑是神会继滑台之会后,为南禅造势,抵制反击北宗行动的又一个重要步骤。这也提醒我们要充分考察、辨析新见史料。
管:您对于“慧能碑”的考证,让我联想到明代胡应麟在《四部真伪》总结的辨伪方法,即所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治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可以说几百年前的考证方法及态度现在仍不过时。总之,考证史事要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真假不分,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曲解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冯: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仅凭一条碑文,即便是新见史料,也并没有绝对的说服力。比如说2009年7月,在邢台沙河市西部漆泉寺遗址发现的《大唐广阳漆泉寺故觉禅师碑铭》,故觉禅师,法名惠觉,碑文中有“禅师□慧觉中海新罗”,说明他是一名朝鲜籍僧人,唐代大历八年圆寂。该碑贞元七年至十三年立,碑文为邢州刺史元谊撰。碑文中有处文字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即“点檀兴仁广运乃道心者,请导师之留音,追荷泽之坛教”。文中的“荷泽”即为“荷泽宗”,即以禅宗六祖慧能之弟子荷泽神会为宗祖之禅宗派系。神会于唐玄宗时,住洛阳荷泽寺,故后世以荷泽称之,其宗派亦被称为荷泽宗。由此可见,故觉禅师为七祖神会嫡传弟子。由于此碑于漆泉寺发现,诸多学者由此得出论断:神会也到过河北邢台地区。但是纵观碑文,故觉禅师并非于河北拜见神会,而是在洛阳,相关史籍也没有神会到过邢台的记载。因而由此碑并不能得出神会到过河北的推论,因此我们要意识到,过分依赖新材料,要将其作为考证的佐助而不是结论。
三、新旧史料的辩证及“重构禅宗书写模式”的思考
管:如此看来,我们对于新材料的利用要多加谨慎,记得严耕望曾举例说明:“前辈学人中,例如钱宾四师,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利用新的稀有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当然随着新的资料不断被发现,对其进行利用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辩证关系,在治学过程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冯: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新史料。以我们讲到的上述新出碑刻为例,碑刻文献是中国古代文献和艺术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传世文献在记载的过程中,由于掌握的材料及作者认知水平有限,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而且传世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往往经过了辗转抄写,并且抄写者常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便使得传世文献容易失去其原有的面貌。而将碑刻文献在内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遗漏和缺陷,填补传世文献的空白。与纯文本资料相比,碑刻文献所能提供的历史信息是立体的、多方面的。但要学会主动发现和探索这些资料,整理碑刻文献时要注意运用同一碑刻的不同整理成果,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进行对比识读;对于仍无法厘清的问题,还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在具体的田野考察和访碑实践中磨炼自身的解读及辨伪意识。如河北学者孙继民先生就对新材料极为重视,四处寻访新见碑刻史料,为当代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因而,我们要重视新材料。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迷信新材料。新材料和旧材料在重要性上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史料的“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无非是发现的时间有早有晚。史料的积累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史料在不停地变为旧史料。因而我们发现及研究新的碑刻资料时,要与旧的碑刻资料,特别是与传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二者互补印证,形成证据链,才能发挥它们作为原始记录最大的作用。蒋汝藻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说:“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穿,其术甚精,其识甚锐,固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在这里,方法与新、旧史料都不可缺少。对新史料在缺乏考辨的情况下匆忙使用、不注重旧史料的阅读与研究、急功近利的历史研究观念都是不可取的。
管:您在既往的研究中提到了“重构中国禅宗史书写模式”的问题,这是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禅宗乃至佛教史研究,我觉得很受启发。您特别提到,在资料方面,于传统典籍资料之外,应充分重视石刻等考古资料,那么通过新见碑刻史料构建禅宗史新的书写模式的整体思路是怎样的呢?
冯:对于历史书写,不同的知识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选材和叙述模式。20世纪初,日本学者铃木大拙与胡适关于禅宗的“世纪论争”,究其实质就是两种不同学术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禅学历史书写模式之争。长期以来,由胡适开启的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研究范式发生断裂,并未得以赓续。学界往往重思想而轻事实。对禅宗史上一些基本史实,传统的佛教史书写模式是建立在大藏经,特别是灯录、语录等资料基础上的,重在思想阐发。学界对于禅宗史的研究,仍大体根据灯录、僧传,如《坛经》《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代会元》《古尊宿语录》《赵州录》等记载,奉为定论,并以讹传讹。但禅宗史资料的记载是多维的,除了传统禅宗的灯录、语录、僧传等文献外,还包括敦煌禅宗文献。以僧传、考古文物资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不仅可以补充众多的禅宗史实,还将僧众及其事迹定格于时间坐标之中,可以较清晰地展示各阶段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既往史学研究中,研究者多关注的是传世文献。这些文献提供的多是一些思想的断面,于历史演进的线索上往往模糊不清。甚至灯录等传法体系出于争夺正统的考虑,还人为地设置了许多“迷雾”,故意湮没、遮蔽了许多史实。禅宗六祖的传灯体系以及北宗的遭际即是明证。
这就要求我们从既有的禅宗史研究范式中解脱出来,改变长期以来禅宗史作为哲学史、思想史附庸的局面,认清禅宗史本质上属于历史学分支的属性。在此基础上,以历史的思维重新梳理禅宗史,利用新的史料对禅宗史进行再造。因此,我们要将更多的关注点转向类似账簿、乡规民约、地方志、日记、文学作品、石刻、墓碑、礼单、地图等边缘材料。前者研究的是精英阶层的思想流变和意识形态,后者则关注的是大众的思潮演变。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宗派,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巨,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故在传统史料之外,开掘利用考古资料(特别是石刻资料)成为推进中国禅宗史(包括区域性禅宗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20世纪初,敦煌本《坛经》《修心要论》《神会语录》《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禅籍写本,改写了中国早期禅宗史。荣新江、邓文宽《敦博本禅籍校录》、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数据分类目录初稿》、林世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等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对敦煌禅宗文献进行了整理。这就要求我们从既有的禅宗史研究范式中解脱出来,以历史的思维对禅宗史进行重新梳理,利用新的史料对禅宗史进行再造。
除了敦煌文献等资料外,碑刻文献也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文献范畴往往为人所忽视。实际上碑刻文献保留了很多其他文献形式缺乏的信息,如根据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所著《语石》一书,碑刻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即述德、铭功、纪事、纂言。因此,碑刻蕴含着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紧密相关的信息,反映了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等。正是因为其记事功能,包含人、事、时、地、物等多种信息的碑刻资料,其中包含大量的禅宗史料,对于地方禅宗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让禅宗史重新回归历史,首先应将基本史实搞清楚。在中国禅宗史研究中,在重视新问题的开掘和旧问题的激活之外,视野、研究进路、资料的转变和拓展至关重要。应使禅宗史研究重新回归其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在视野方面,应实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视野的转变,重视接受史这一视角;在资料方面,于传统典籍资料之外,应充分重视石刻等考古资料,进一步拓宽资料来源;在研究中心方面,应实现从经典、思想到人物(寺院)、从个案到集束的转变;在研究时段、时态方面,应实现从短时段到长时段的转变,从静态共时性转向动态历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