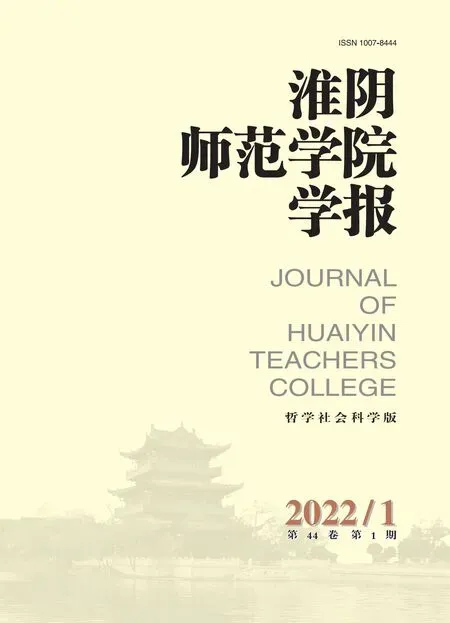清代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刍议
郭凯峰, 牛革平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我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漕运文化在世界上一帜独树。大运河漕运对我国“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存在、稳固和延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大力发展大运河漕运和健全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制度就成为很多朝代极其重要的政策抉择和制度安排。在清代,漕运、河工和盐政被列为王朝三大政,而漕运又居其首,被视为“南北之咽喉,军民之命脉”。清政府承继、借鉴了历代尤其是明代的漕运管理法律制度,在大运河漕运管理的各环节都制定了种类繁多且庞杂细密的“律、例、典、令”等,形成了健全齐备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然而,对于这个学术话题,无论是我国运河学界,还是法律史学界,均未能予以学术上的足够重视。本文在查阅有关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对清代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以期对于当代大运河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所裨益。
一、清代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的建立
清代早期的漕运管理法律体系是在承继、借鉴明代漕运管理法律的基础上,结合清初的社会实际,逐步建立起来的。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令生活在东北的汉族知识分子,把汉人行事的各种法规律例全部写成文书呈上,抛弃不适当的地方,报告适当的地方。天聪七年(1633),后金文馆汉族大臣宁完我提出了“参汉酌金”制定法律制度的原则。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后,清朝确立“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原则。清初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制度的建立,也是如此。清朝大幅提高了漕运法律中“例”的数量、比重和地位,构建了以“律、例、典、令”为主要内容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
二、清代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的表现形式
(一)大运河漕运管理主体法《漕运全书》
《清仁宗实录》第24卷记载,康熙六年(1667)十二月,康熙皇帝下令纂修《漕运议单》。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对《漕运议单》整理修订的基础上撰成《漕运全书》,经雍正皇帝题准予以颁布。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编撰、刊印《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即乾隆版《漕运全书》。该《全书》在内容与格式上对雍正朝《漕运全书》予以完善,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结构体例,成为清代漕运领域的基本准则和漕运管理法律体系的主体法、综合法。《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的内容相当完备,包括漕粮征收数额、征收标准、交兑方式,河道、水工管理,漕粮运输、押运,运丁、船夫管理,以及运河沿岸屯田事宜、收仓事宜,等等,涉及大运河漕运管理的方方面面。嘉庆、道光、光绪年间,清廷继续对乾隆版《漕运全书》进行补充修订。
光绪版《漕运全书》共96卷,具体条目如下。第1卷至第8卷“漕粮额征”条目为兑运额数、改征折色、白粮额数、蠲缓升除、改折抵兑、变通折征;第9卷“征收事例”条目为征收漕粮、随漕杂款;第10卷至第15卷“兑运事例”条目为运漕脚价、水次派运、交兑军粮、兑开期限、搭运收买、淮通例限、回空例限、沿途备借、沿途冻阻、沿途趱运;第16卷“白粮事例”条目为白粮经费、白粮解运;第17卷至20卷“通漕运艘”条目为帮船额数、追罚定例、额船裁改、买雇民船、佥造漕船、浅船额式、工料则例、三修则例、留通变卖;第21卷至23卷“督运职掌”条目为监临官制、监兑粮官、分省漕司、十三总运、押运各官;第24卷至第26卷“选补官丁”条目为卫帮额员、遴委运弁、领随职掌、查佥运丁;第27卷至第32卷“官丁廪粮”条目为俸廪例款、卫帮额支、行月例款;第33卷至第34卷“贴费杂款”条目为负重贴费、给丁筛扬、扣追欠款、蠲缓欠款、奖赏丁舵;第35卷至第39卷“计屯起运”条目为屯田坐落、屯田津租;第40卷至第47卷“漕运河道”条目为运河总考、运河续考、大通河考、白河考、卫河考、会通河考、新河考、泇河考、中河皂河考、淮安运河考、高宝运河考、瓜仪运河考、丹阳运河考、苏州运河考、浙江运河考、上江运道考、江西运道考、河北运道考、湖南运道考、汶河考、洸河考、泗河考、沂河考、徐吕二洪考、河闸禁令、修建闸坝、卫河挑浚、挑浚事例、险隘处所;第48卷至第50卷“随漕解款”条目为轻赍额数、正兑轻赍、改兑易银、席木额数、随漕席片、随漕竹木、征解通例;第51卷至67卷“京通粮储”条目为仓场执掌、京通各差、官役公费、置办运袋、置办官车、仓廒号房、修建仓廒、号房潮湿、建造斛只、收买米石、收受粮米、余米箇亶羡、买余抵补、余米籴变、缓交余米、掣欠事例、粮色参奏、脚价则例、俸甲米豆、支放粮米、仓粮拨赈、发籴仓粮、钱粮事例、偷盗仓粮、霉变仓粮、亏缺仓粮、稽查偷漏、扫积抵欠;第68卷至71卷“截拨事例”条目为截留拨运、截拨赈籴、截拨充饷;第72卷至第73卷“拨船事例”条目为外河拨船、里河拨船;第74卷至第75卷“采买搭运”条目为采运米石、仓粮运通、采运麦豆、奉豆奉米、碾动蓟谷、捐输米石;第76卷至第78卷“奏销考成”条目为催征考成、仓粮参限、漕粮参限、随漕参限、运粮完欠、仓粮奏销、仓库盘查;第79卷至第80卷“挽运失防”条目为风火事故、挂欠处分;第81卷至第88卷“通漕禁令”条目为侵盗折干、搀和霉变、盘诘事例、裁革陋规、严禁抗顽、违禁杂款;第89卷“盘坝接运”条目为盘运章程、经费出纳;第90卷至第94卷“海运事宜”不涉及漕运,从略;第95卷“规复河运”条目为办运事宜、支销经费;第96卷“灌塘渡运”条目为灌运形势、工料奏销。[1]
(二)《大清律例》中的漕运管理刑事法律
顺治二年(1645),顺治皇帝下令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差等”,编撰大清律。顺治四年(1647)三月,沿袭《大明律》篇目体例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完成并颁行。康熙、雍正朝又对它进行了零散的修订。乾隆五年(1740),又对它进行了全面修订,定型后称为《大清律例》,共436条,附例1 049条。其中,涉及大运河漕运管理的条文主要集中在《吏律》《户律》《兵律》《刑律》《工律》,且“条例”的数量最多,占比最高。
光绪朝《大清律例》第39卷《工律·河防》规定了两种与大运河漕运管理有关的犯罪行为,即盗决河防罪和失时不修堤防罪,并具体规定了其各自的犯罪构成条件及刑事责任。(1)盗决河防罪。“凡盗决官河防的,杖一百。盗决民间之圩岸陂塘者,杖八十。若因盗决而致水势涨漫,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淹没田禾,计物价重于杖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各减斗杀伤罪一等。若或取利,或挟仇,故决河防者,杖一百、徒三年。故决圩岸陂塘,减二等;漂失计所失物价为赃,重于徒者,准窃盗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因而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2)失时修筑河防罪。“凡不先事修筑河防,及虽修而失时者,提调官吏各笞五十;若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杖六十;因而致伤人命者,杖八十。其暴水连雨,损坏堤防,非人力所致者,勿论。”[2]790与《大明律》的规定相比,《大清律例》只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和增删。
在盗决河防罪条目下,《大清律例》还附加了两项“条例”:(1)“故决、盗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扬州高宝湖、淮安高家堰、柳蒲湾及徐邳上下滨河一带各堤岸,并河南、山东临河大堤,及盗决格月等堤,如但经故盗决尚未过水者,首犯先于工次枷号一个月,发边远充军;其已经过水尚未侵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首犯枷号两个月,发极边烟瘴充军;既经过水又复侵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首犯枷号三个月,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因而杀伤人者,照故杀伤问拟,从犯堩先于工次枷号一个月,各减首犯罪一等。其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源,有干漕河禁例,军民俱发近边充军。闸官人等用草卷阁闸板,盗泄水利,串同取财,犯该徒罪以上,亦发近边充军。”[2]1058(2)“凡黄河一年之内,运河三年之内,堤工陡遇冲决,而所修工程实系坚固,于工完之日,已经总河督抚保题者,止令承修官赔修四分,其余六分准其开销;如该员修筑钱粮俱归实用,工程已完未及题报,而陡遇冲决者,该总河督抚将冲决情形,并该员工程果无浮冒之处,据实保题,亦令赔修四分,其余俱准开销。如黄河一年之外,运河三年之外,堤工陡遇冲决,而该管各官实系防守谨慎,并无疏虞懈弛者,该总河督抚查明具题,止令防守该管各官共赔四分,内河道分司知府共赔二分,同知、通判、守备、州县共赔一分半,县丞、主簿、千总、把总共赔半分,其余六分准其开销,其承修防守各员俱令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工完之日,方准开复。倘总河督抚有保题不实者,后经查出,照徇庇例严加议处,所修工程仍照定例,勒令各官分赔还项。若河员有将完固堤工故行毁坏,希图兴修,借端侵蚀钱粮者,该总河察访奏闻,于工程处正法。”[2]1058
在失时不修堤防罪条目下,《大清律例》附加了四项“条例”,它们各自可以构成更加细化的犯罪形态。(1)非法包揽漕运工夫罪。“凡运河一带,用强包揽闸夫溜夫二名之上、捞浅铺夫三名之上,俱问罪,发附近充军;揽当一名,不曾用强生事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2]1059(2)浮议动众破坏河工罪。“遇河工紧要工程,如有浮议动众,以致众力懈弛者,将倡造之人,拟斩监候;附和传播者,杖一百,即于工所枷号一个月。其指称夫头包揽代雇、勒掯良民者,二名以上发附近充军,一名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发落。”[2]1059(3)河工贪污罪。“河工承修各员,采办料物,如有奸民串保领银,侵分入己,以致亏帑误工,该总河将承办官参究,仍将亏帑奸民发该州县严查追比。倘有徇纵等情,亦即查参交部议处。其亏帑串保奸民审实,照常人盗仓库钱粮律,计赃治罪。应追银两逾限不定者,原领官名下追赔。”[2]1059(4)河道乱建罪。“凡堤工宜加意慎重,以固河防,除现在已成房屋无碍堤工者,免其迁移外,如再有违禁增盖者,即行驱逐治罪,并将徇纵容隐之官弁,交部分别议处。”[2]1059
(三)《大清会典》中的大运河漕运管理行政法规
《大清会典》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五朝的行政法典。它详细规定了清朝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活动原则及有关制度,是清代的“大经大法”。光绪朝的《大清会典事例》的《漕运篇》对大运河漕运各阶段的事宜进行了详备而周全的规定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规定的具体项目有额征漕粮、随漕正耗、随漕轻赍易米折银、随漕席木板竹、余米、耙羡银、厅仓茶果、官军行月钱粮、赠贴银米、白粮耗米、白粮经费、转输蓟易、截拨兵米、截留事例、漕粮征收、白粮征收、漕粮蠲缓、漕粮改折、漕粮运船、白粮运船、漕运剥船、带运加给、雇募民船、总漕职掌、粮道职掌、漕运监兑、押运、领运、白空例限、催趱、佥选运军、漕粮交兑、沿途程限、淮通例限、回空例限、计屯贴运、优恤运军、征收例禁、重运例禁、回空禁令、漕运杂禁、仓漕奏销、漕运考成、白粮考成、仓库盘查、起运完欠、粮船事故、试办河运等事宜,多达48项。
(四)《钦定户部则例》中的大运河漕运管理部门规章
在清代,除了行政法典《大清会典》外,六部、大理寺、督察院等部院还制定、编修了各自的《则例》,类似于现在的部门规章。主要涉及职掌、礼仪、营建制造、物价等事宜。乾隆朝《钦定户部则例》中有三册六卷涉及大运河漕运管理,规定的漕运事项主要包括征收漕粮、漕粮正额、改征折色、随漕征耗、随征贴费、轻赍带解、监兑漕粮、派兑输兑、奉天米石、南漕抵兑、佥派领运、押运漕粮、粮运程限、稽查催趱、兑拨兵米、兑收事宜、进仓验耗、追赔代运、解通经费、动借银两、脚价夫工、桥坝杂款、造船额式、成造年限、修造料价、造船津贴、船只事故、通州拨船、直隶拨船、山东拨船、江南拨船、黄河拨船、编审佥选、官丁行月、屯田章程、屯租贴运、贴赡杂款、扣留支放、河闸事宜、奏报考成、漕员职掌、官丁奖恤、通漕例禁、严杜转运流弊、严禁偷漏、严禁水手,多达46项。
(五)皇帝谕令中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令
封建制时代的谕令是集最高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皇帝在国家律法之外针对具体事务所发布的命令、文告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是中国古代法的渊源之一。清代历任皇帝对于国之大事大政的大运河漕运一向非常重视,也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漕运管理的谕令。此举两例,以展示清代漕运谕令的形成与特色。
在漕运所涉有关各省,经常有品性低劣的举人、监生等绅衿文士,依仗自己取得的科举功名而领头举行抗漕活动。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为此特颁一道谕令:“地丁漕米征收之时,劣生劣监迟延拖欠,不即输纳,大干法纪。该督抚立即严查,晓谕粮户,除去儒户官户名目。如再有抗顽不肖生监,即行重处,毋得姑徇。倘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题参治罪。”[3]587《大清律例》第11卷《户律·收粮违限》条目下也有一“例”,记载对于欠缴钱粮税赋的绅衿文士,不仅会革除他们的功名身份,还会对他们课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应纳钱粮以十分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贡监生员并黜革,杖六十。欠至七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八十,贡监生员黜革,枷号一个月、杖一百。欠至十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一百,贡监生员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其文武进士,及在籍有顶戴人员,并与举人同。……无论文武乡绅、进士、举人、生员,并贡监及有顶戴人员,已任、未任,俱按未完分数,已任者革职,未任者革去顶带衣衿,按例枷责治罪。”[2]934
另外,在清代大运河漕运中,一些押运官和漕军旗丁经常仗势欺人,勒索帮费。为此,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道光皇帝颁布谕令:“先使岁减一岁,积弊方可渐除,着即照所议。湖北帮费一项,每正米一石,令州县贴银二钱。各项陋规,概行裁减一半。其州县经征漕粮,无论绅民,概以八折收纳。每漕米一石余米二斗五升。经此次厘定之后,该漕督当严饬运官旗丁等,撙节办运;如有额外多索帮费,及滥取陋规者,立即严究治罪。”[3]587
(六)有关大运河漕运管理的地方政令规章
清代,大运河漕运经过的有关省、府、州、县还颁布了很多涉及漕运管理的条约、告示、檄文、禁约等地方政令规章。这些地方政令规章具有内容的规范性与执行的强制性,属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构成了清代漕运法律体系中的地方性法规。例如,在咸丰元年(1851),为了催征漕粮,江苏省震泽县(今苏州市吴江县)贴出了如下告示:“业主该田,赡家完赋;佃户选米,赶早交租。如敢拖欠,自取灾祸,经业指告,立刻拘捕。当堂痛或以墩锁,受此官刑,租仍追捕,不如完租,免得受苦。”[3]589
(七)《漕运则例纂》中的案例
《大清律例》在盗决河防罪和失时修筑河防罪条目下附加了一些条例,其中即有一些事例和案例。《漕运则例纂》中也有很多案例。这些案例可以帮助、指导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审理、处理漕运管理案件,降低司法与执法成本。例如,乾隆年间,漕运总督杨锡绂(1700—1768)以雍正十二年《漕运全书》为蓝本,花费十年时间,分20卷把《漕运全书》案例逐加校对,删除烦冗使其简明,补充缺漏使其详备,编纂而成《漕运则例纂》,非常注重实用性。
在清代,无论是作为漕运主体法的《漕运全书》,还是《大清会典》中的漕运管理行政法规,抑或《户部则例》里的漕运管理部门规章,对大运河漕运管理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完备而细致的规定,繁杂而细密,几乎达到了事无巨细都予以具体规定的程度。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只要根据细化的法律规定和规章要求去做,就可以解决问题,从而大大限制和压缩了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随意出入人罪以及枉法裁判的弊端,可以防避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的权力异化。
三、清代健全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的动因
由上文可知,清代建立了完备而细致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达到了封建制时代大运河漕运管理立法的最高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取决于清廷将漕运提升到“国之大政”的战略高度。因而无论是清朝帝王,还是朝廷重臣,抑或专家学者,对于大运河漕运管理,无不给予高度重视。
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漕运管理,他颁布的谕令说:河务漕运,关系重大。所关河漕,一应情罪,俱不免赦。并认为:“河道关系漕运民生,若不深究地形水性,随时权变,惟执纸上陈言,或徇一时成说,则河工必致溃坏。”[3]634康熙朝重臣、理学家魏象枢(1617—1687)说:“漕运乃南北之咽喉,军民之命脉。”[4]他主张重视法制,因时制宜修正法典,以使循名责实,尽职尽责;尤其是在钱粮税赋方面,更应完善立法,使得法律明确,杜绝贪污。道光朝漕运专家、经世派学者陶澍(1779—1839)主张:“国家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5]他认为东南江浙一带,田赋之重甲于天下,必须河道疏通,才能旱涝有备,因而水利于东南尤为第一要务。
综上可见,正是基于朝野上下对于大运河漕运战略重要性的认识,清王朝才会高度重视运河漕运管理立法,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运河漕运的畅通性、可持续性与安全保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