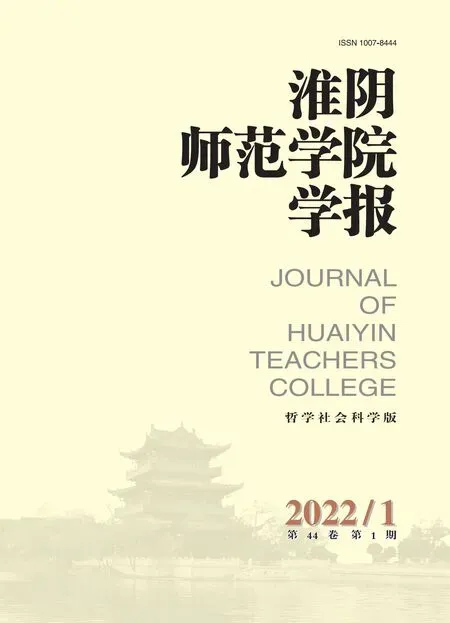致力于史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读《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二卷
钟河水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自白寿彝先生1961年撰写《谈史学遗产》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这也意味着,从白先生首次明确提出重视历史编纂学研究开始,学界对这一重要史学遗产的研究,也已完整地经历了一个甲子。甲子一轮回,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上回顾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学术史意义,更是对白先生在史学史领域筚路蓝缕的告慰。
陈其泰先生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会通古今,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做了综合且贯通的研究,无疑是目前最系统、最厚重的压轴之作。其中,由陈先生亲自撰写的第二卷《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核心,详细论证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史确立于两汉的内在逻辑,既是全书的基石,又是理解传统历史编纂学史的金钥匙。
本卷主要从古代史学“例不拘常”的传统、史书体裁演进的规律和马班“实录”精神的传承三个方面入手,对《史记》《汉书》两部史学经典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展现了历史编纂学的独特魅力。
一、对古代史学“例不拘常”传统的集中总结
不拘常格向来是《史记》《汉书》最引人注目的编纂特色。但后世史家对此的评价却趋向两极,刘知几斥之为“名实无准”[1]42,章学诚则褒之为“例不拘常”[2]49。虽然这两条经典论述一再被后人引述,但能剖析其背后本质的却并不多见。本书对《史记》之《秦本纪》《项羽本纪》《孔子世家》《陈涉世家》,以及《汉书》之《元后传》《王莽传》设置的分析,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若单从史料学的角度出发,项羽入不入本纪,孔子、陈胜入不入世家,都不会对其本身的史料价值有任何根本性影响。可是,假如我们“另换一副眼光”[3]审视这个问题,便可发现其在编纂学上的重大意义。
先看本书对《史记·秦本纪》和《项羽本纪》两篇的分析。刘知几对《史记》最严厉的批评,莫过于指责《秦本纪》《项羽本纪》两篇以“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1]37。对这一苛刻的指控,本书旗帜鲜明地指出,这其实是刘知几“太过拘泥于名号、等级,刻板地要求必须身为天子才能立为本纪,……他未能理解,司马迁设置本纪的主要着眼点不在身份名号,而在于以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史事之总纲,看其是否起到支配历史大局的作用”[4]48。这既指出了刘知几立论的薄弱之处,又点明了司马迁创设本纪的真实用意。根据这一认识,作者认为,秦国诸君虽然在统一六国之前未曾践天子之位,但在周室衰微、诸侯坐庄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由弱渐强、由偏安一隅到定鼎中原的历程才是历史的总纲。因此,《秦本纪》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记述秦国一国之事,而是“提挈各国大事”和“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4]48故而,秦国诸君虽无天子之名,但其实际历史地位和影响力远高于一般诸侯,明显更符合本纪“包举大端”[1]28的立意。
明确这一标准后,再看之所以将项羽入本纪而不列世家,司马迁的苦心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风起云蒸的反秦起义浪潮中,项羽的行动和部署对全局起到了支配作用,构成这一复杂多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总纲。”[4]49若以项羽当时号令天下、政由己出的巨大影响力及其推翻秦朝暴政的历史贡献,反将之列入世家,与张良、萧何、曹参等人一个级别,又岂能真实地反映出他一时无二的历史地位?所以作者最后才会总结说:“司马迁所重不在于身份、名号,而是重视人物在历史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其目的是要再现历史的真相。……根据历史实际的需要作灵活处理,在必要时敢于突破自己所定的体例。”[4]49历史的真相当然不能只孤立地看主角个体的实际作为,还要联系同时代的其他人物,看到哪些是只有主角能做到,而其他人难以达成的。只有看到这一层,才能理解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并“既科条之”[5]的著史旨趣。
理解了《秦本纪》和《项羽本纪》的立意,司马迁将孔子、陈胜抬入世家的用意,自然迎刃而解。刘知几一再说,入世家者,当有“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功。孔子、陈胜二人无此功业,列入世家,是“名实无准”[1]42。本书提出了反对意见,作者说:“恰恰由于司马迁别识心裁地以‘世家’作为记述孔子和陈涉行事的载体,不拘常格,而使这两篇传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82其原因在于,首先,破例将二人抬入世家,是对他们崇高历史地位的肯定,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其次,两人虽然无“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名,却有确立历史坐标,影响后世历史发展之实。孔子修订六经,传信行远自不必说。陈胜不平则鸣、揭竿首义,虽身死国灭,子孙不传,但其反抗压迫、不避强权的精神遗产却为后世农民起义者所继承,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世代相续”。最后,二人虽然均非王侯,但孔子“在文化上、思想上享有任何国君王侯所不能比拟的地位”[4]85;陈胜发动起义,又有“导致秦亡汉兴、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功绩”[4]87。这非但不是“自乱其例”[6],反而是司马迁“将对历史进程实质的深刻观察和对历史功过评价的哲理思考,外化为历史编纂形式的创造之成功典范”[4]86。
再看《汉书》。《汉书》本设有《外戚传》,包举有汉一代皇后、婕妤、昭仪,唯独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不在其列。班固单列《元后》一传,同样不合常例。若不从编纂学的角度出发,很可能会认为这只是班固出于平衡篇幅的考虑而做的技术性处理。对此,作者从文本本身和历史现实两个方面入手,做了详尽的分析。从文本看,《外戚传》在提到元后时,就已专门强调了元后家族势力之庞大,其特殊性已非类传所强调的普遍性所能囊括。《元帝纪》《成帝纪》两篇都旨在突出君主弱势、君权旁落这一历史趋势。君权日削、外戚日盛,这使班固以揭露“王氏五将十侯如何更相把持国柄”[4]311、如何挖空刘氏政权根基为重点而单辟《元后传》,在学理上显得顺理成章。就历史现实而言,王氏家族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五将十侯、专擅国柄的局面,与元后的全力卵翼有最直接、最根本的联系。因此,此传虽名曰“元后”,但实际上写的是元后掌权、外戚膨胀局面下皇权畸形发展的特殊时代,与一般所写外戚不可同日而语,非单列一篇不能尽其义。因而“《汉书》特设《元后传》以记载元后一生的经历,而不将之放在记载后妃的类传中叙述,其深刻用意,是借元后一生行事来概述西汉后期因外戚势力膨胀而迅速衰亡的历史趋势”[4]315。足见班固也意识到,只要运用得当,史例同样可以用于反映史实,这在编纂学思想上与司马迁可谓一脉相承。
通过上述例子,不难发现,越是有违常例的地方,越能体现史家的别识心裁。要想正确认识到这点,编纂学的眼光显得尤为重要。章学诚就曾感慨,后世著史者若“无别识心裁”,只知“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只会让史书流于“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2]51。相应的,若治史者不能留意史书体例的变化,体察不到“例不拘常”的本质往往是史家的创造,那当今史学是否也会有滑向“胥吏之簿书”的风险?
二、对史书体裁演进规律的深刻洞察
早在2008年,作者就已经提出要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传统历史编纂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必须破除一种旧见,即认为主要史书体裁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应当根据史学发展的实际确立一种新观点:各种主要史书体裁之内容和体例,均与时俱进,须以动态眼光,考察其演变,对其因时代发展而更新特点作出新的概括。”[7]这一观点正是对章学诚《书教》篇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在章学诚看来,“《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2]49-50。由于历史向前发展,史事变得愈发繁杂,以时间为主线的编年体史书,因“不能旁通”[2]50,已难以满足记述复杂历史局势的要求。因此,具有多维历史视角的纪传体应运而生。它既承继了编年体史书因年系事的优长,又增加了记述典制源流和社会民生的维度,实现了精神上的继承和形式上的创新。但遗憾的是,章学诚的概括和分析只是点到辄止,且他最终想要突出的是纪事本末体对编年、纪传二体融合的优长,因而只看到了史书从编年体到纪传体再到纪事本末体这一条发展路径,忽略了从编年体到纪传体,进而发展为典制体这条同样重要的演进路线。本书看到了马班二人多维的历史视野,对《史记》《汉书》“书”“表”“志”的设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史记》《汉书》所孕育的典制体史书的雏形,真正从编纂学层面深化和完善了章学诚对古代史书体裁演进的认识。
《史记》“八书”为司马迁首创,是五体之中紧随“十表”之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史记》评价之高如梁启超者,甚至认为《史记》“八书”不必读,“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8]168其实梁启超在这里和刘知几一样,低估了“八书”的编纂学价值。首先,《礼》《乐》《律》《历》四书,虽然表面上看是横向叙述国家大政的四个方面,但是在纵向上却都有“损益”“改易”的共通之处,这显示了司马迁“贯通古今观察历史变迁的卓识”[4]63。其次,《天官书》与《封禅书》并非只存在编次上的前后关系。其用意在于首叙天文,后以人事相呼应,最终表达出司马迁本人反迷信、重人事的人文主义的进步史观。最后,作者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河渠书》《平准书》的分析,赞扬了司马迁关注经济基础、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录”精神与高尚史德。正因如此,马端临才说:“惟太史公号称良史,……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9]1由此可见,“八书”非但不可“全部从省”[8]168,而且突出地表明了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和创为‘全史’的观念,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首创性意义”。[4]74
和“八书”相似,《史记》“十表”的编纂学价值也常被低估。梁启超说:“《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浏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8]168而本书则认为,“将年表紧接于本纪之后,而置于书、世家、列传之前”[4]172,本身就可以证明司马迁本人对这一体裁的重视。因此,不仅要“深入研究这些表的价值”,还应该将其与“相关的本纪、列传联系起来分析”,这样才能从编纂学的角度体察出司马迁本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4]147。
以对《六国年表》的分析为例,本书认为它虽以六国为名,但其“记载战国时期二百五十五年间大事的方法,是以秦为主干”,“记载秦国史事独详”[4]149。其次,作者将《六国年表》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相对照,把体例不同的三篇作为一个首尾完备的整体来看待,揭示了它们在编纂学上的内在逻辑,即《秦本纪》是“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总纲”[4]151,《六国年表》“旨在显示秦逐渐强大至最终统一海内之势”[4]150,而《秦始皇本纪》则在最后说明秦由诸侯之国进阶为一统之朝的质变。所以,这样的精心编排,最能反映出司马迁目光之敏锐,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抓住了秦作为结束分裂、统一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担负者,苦心经营、励精图治,最终实现天下统一的历史主线。可见“表”在《史记》中的作用与意义并非不重要,只是我们过去缺乏一种编纂学的眼光,体悟不出司马迁的匠心独运而已。
最后再看《汉书》的“志”。和《史记》的“表”“书”不同,学界很早就认识到《汉书》“十志”的重要性,但对其研究主要还停留在专门史的层面,“在发掘其中思想价值方面尤其显得薄弱”[4]332。至于如何发掘其中的思想价值,如何确立它在历史编纂学史中的正确位置,从作者对《刑法志》的分析即可见一斑。本书从三个方面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刑法志》的编纂与只会罗列史料者迥然不同,它随处体现出班固这位杰出史家组织、剪裁史料的匠心和出色的史才”[4]346。这三方面分别是,其一,将史料组织为两大层次加以论述。第一层主要记载自高祖至成帝的刑法演变,第二层则集中记述历次改变律令、减轻重刑之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仅真实地揭示出封建时代制定法律所显示出的进步与实际执行中治罪严酷、狱吏贪赃枉法、制造无数冤案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深刻地表达出史家本人强烈要求删定律令、公正审案、解救民众痛苦,达到‘便民’‘便令’的出色的刑法思想”[4]347。其二,班固还敢于对汉代刑法的诸多弊病提出自己的批评,以议论的形式给后世以启发。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贯彻叙述刑法制度古今沿革的编纂原则”[4]347。班固述历代刑法,上自周代,下迄于自己所生活的年代。从“断汉为史”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无必要,只记有汉一代刑法即可,缘何上溯至周代?其原因在于班固旨在表明东汉的刑法,较之前代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虽然在形式上超出了汉代的范畴,但在目的上却与其“大汉当可独立一史”[10]的著史旨趣吻合,很难不令人拍案叫绝。可见,当我们换上历史编纂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刑法志》后,就会意识到,它“不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更有极高的思想价值”[4]349。此前已经提到,史书体例、体裁往往是史家编纂思想的外化。重视和阐明“十志”的思想价值,无疑也是编纂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过往的研究中,《史记》“八书”“十表”和《汉书》“十志”通常被认为只是同一史料的重复利用,又或是多种史料的简单排比,因而对它们缺乏应有的重视。而事实上,倘若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历史编纂学演进的进程之中,就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马班所创设的“书”“表”“志”其实就是典制体史书的发端。“八书撰著的成功,为历代‘正史’的典志篇章和多样的典章制度史著作的出现开辟了道路。”[4]74“在《汉书》十志的基础上,典制体更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其代表作是《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还有继出的《续三通》和《清三通》,俨然成为传统史书体裁中地位仅次于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又一重要史书体裁。”[4]333既然马端临早已说过“典章经制,实相因者”[9]1,那么,用以反映典章制度的史书及其体裁自然也存在因袭的关系。多维的历史视野既然可以变编年为纪传,那自然也可以变纪传为典制。作者将《史记》《汉书》的“书”“表”“志”置于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观察,突破了前人的看法,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由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发展为以典章制度为核心的典制体的关键环节,发人深省。
三、聚焦“实录”精神的传承
成例可以突破,旧例可以创新,但无论史书体裁如何千变万化,总有一个不变的核心,即马班二人高度忠于历史事实的“实录”精神。这正是本书在关注史书体裁外部流变特点的同时所极力强调的内在动力。
全书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褒扬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论述,体现在作者对《封禅书》和《平准书》两篇的分析上。这两篇文献,虽然一个记国家盛典,一个论社会民生,内容大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指向,那就是反映盛世的真实面貌。因此,对前者,司马迁不仅“如实地记载帝王封禅大典,作为重要典章制度的实录”,还清晰地认识到秦皇汉武迷信天命,不恤民力的弊病,对他们“受尽方士欺骗,沉溺于鬼神迷信也予以详载,并做了辛辣的讽刺”[4]67,“有力地揭示出其记载封禅的客观实录态度”[4]68。对于后者的用意,本书认为,司马迁勇于揭露盛世之下潜藏的严重社会危机,“不但说明司马迁对经济政策、社会状况有极其深刻的观察,而且突出地证明其‘实录’精神和高尚史德”[4]74。
至于《汉书》,本书更是以一整节的篇幅来论证班固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弘扬。首先,作者提出,“《汉书》是以宣扬汉朝功业为撰写目的,那么,敢不敢暴露汉代社会的阴暗面,就成为班固是否具有‘实录’精神的试金石”[4]280。继而根据这条金标准详细剖析了班固对汉代土地兼并问题、诸侯王及外戚集团腐败问题,甚至还有对滥刑问题的揭露,表明班固并没有被“大汉当可独立一史”的雄心冲昏头脑,而是恪守了史官秉笔直书的原则,令人信服。再有,作者还从对历史变局的观察、对廉直之士的表彰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三个方面,丰富了对班固“实录”精神的阐发。例如,分析班固对西汉王国问题的态度,作者说他“既从总体上看到藩国必乱的结局,又能有分寸地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封国的积极作用”[4]286;评《隽疏于薛平彭传》《王贡两龚鲍传》《匡张孔马传》诸篇,本书总结道,“班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却能把阐发儒学的真谛,继承早期儒家的本色,与利欲熏心的俗儒及专搞烦琐笺注的陋儒区分得很清楚”[4]294;论《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和《赵尹韩张两王传》,作者旨在突出班固的实录视角不只停留在统治阶级上层,而是关注到了最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也是尊重史实、忠于史实的具体表现。
“实录”精神不仅是古今良史的核心品质,还是史书体例变化的根基所在,一切体例的变化都不可能离开这一基本点而成立。本书在论述《史记》《汉书》体例流变与创新之余,仍极力突出“实录”精神的重要性,无疑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只有将外在体例之变与内在良史精神之不变相结合,才算真正触到了编纂学研究的精髓。
此外,除了以上提到的三个主要方面,本卷还有相当多极富思想性的论断值得反复体味。比如:论史例和史实的辩证关系,作者认为,“让史例服从史实,或反过来要求史实适应于史例,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向”[4]151;论编纂技巧与“史识”表达的内在联系,作者说,“司马迁在编纂上的主要着眼点,是力求体现历史演进的大势,体现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即是说,表达‘史识’是第一位的,而编纂技巧是服务于如何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这一需要的”[4]183;论班固对西汉盛衰的解释,作者总结说,“一句话,是从人的努力、政策施行的效果着眼来解释历史,从根本上摒弃了神意图谶一类妖妄邪说。班固记载西汉历史,是自觉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以此为尺度来衡量和评价的”[4]398。这类高度凝练的论述在书中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能逐一列举。
经过陈其泰先生对两部史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我们更应该体会到,历史编纂学研究绝非某种学科技术标准研究。历史编纂学研究所关心的,绝不仅仅是史书体裁的种类、史书体例的设置这样的外在问题,而是潜藏在体裁、体例背后的史学家对不同阶段历史大势的思考,以及如何将自己的思考创造性地融入史书的编纂中,从而推动传统历史编纂学不断进步、完善的别识心裁。同时,这种创造性地阐释还证明了,传统史学从来不是一门只讲史料的学问,哪怕史料已被反复搜罗使用的经典之作,借由编纂学的视野,仍能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学术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