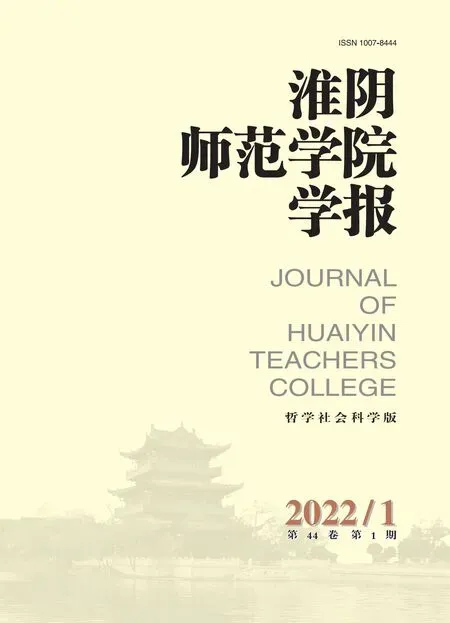《清诗考证》前两编订补
——兼谈人物生卒年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方法
朱则杰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拙著“清诗考证”系列,此前已经出过《清诗考证》初编[1]和《清诗考证续编》[2]。正如诸多“考证”的对象一样,拙著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需要订正的疏误,尤其是可以补充的内容。
过去在上学期间,经常听老师们谈到考证工作的某些原则。其中关于解决问题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打“歼灭战”,一次性把问题解决彻底,这是最好的。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只能把问题先解决掉一部分。对于这种情况,老师们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打敌人,“即使打不死,打半死也是好的”。拙著涉及的不少问题,大概就是如此。
拙著遗留各种问题,对学术界来说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赖于其他学者的批评指正和继续开掘。而我自己,如果有了新的条件,那么也将不断地进行订补。特别是有时候得到友人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指教、启发,订补起来自然更加方便。有关问题汇集在一起,仿照《清诗考证续编》第一辑最末第八篇《〈清诗考证〉初编订补》[注]朱则杰:《清诗考证续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上册第326—355页。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92—96页,题内“初编”二字当时未加。,即题作《〈清诗考证〉前两编订补》。
这次考虑到期刊论文的篇幅,暂取“前两编订补”中的四个题目厘为一束。而这四个题目,都与人物生卒年研究有关,正好可以兼谈这方面的若干问题与方法。
一、沈阆昆卒年
《清诗考证》初编第一辑之三《〈清人别集总目〉零札》第六条“沈阆昆”,曾经依据平步青《霞外捃屑》所说“辛巳冬卒”,定其卒年为光绪七年(1881),农历年份与“辛巳闰七月二日”谢世的汪曰桢“恰巧相同”[1]上册:70。2018年2月16日,友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汪少华先生惠示电子邮件,指出:
大作《清诗考证》70页,据平步青《霞外捃屑》考证,沈阆昆谢世年份与汪曰桢相同,都是辛巳(1881年)。最近释读俞樾致徐琪函札,昨天看到《春在堂诗编》壬甲编《沈肖岩广文阆昆又得福寿砖一,因以见赠,并考定为仙姑山宋时佛光福寿院旧物,媵之以诗,即次韵奉酬》:“残砖留自宋时年,历岁于今过半千。双福寿曾传盛事,三台山定有前缘(来诗有“三台视寿永绵绵”之句)。摩挲岂是寻常物,培植还凭方寸田。为感故人持赠意,不辞吉语赋连绵。”[3]461-462发现此诗排列在《甲申正月十七日即事》[3]460之后、《十二月二日,余生日也,梦见先母姚太夫人病……》[3]462之前,可见是[作于]1884年。
这里列举的俞樾《春在堂诗编》卷十《壬甲编》相关诗歌,确实作于光绪十年“甲申”(1884)。也就是说,沈阆昆(肖岩其字)此时并未谢世。按照这个提示,进一步发现《春在堂诗编》接下去的卷十一《乙丙编》内,还有一首《乾隆间,日本曾以金币聘吾邑沈南屏先生为画师;今余又应其国人之请,选定日本诗四十四卷。沈肖岩广文以为皆吾邑盛事,赋诗见赠,率成一绝句酬之》[3]465;据同卷后面《嘉平十九日,为第二曾孙女珉宝洗三……》《丙戌二月四日,余亲送孙儿陛云航海入都……赋此纪行》连续两题[3]470,可知其作于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这也就是说,沈阆昆此时仍然在世。此外如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零四《职官·六》“富阳县·国朝·训导”有:“沈阆昆,德清人,[光绪]九年十一月署。”[注]民国《杭州府志》,1922年(民国十一年)排印本,第21b页。其下一任为“严大经,秀水人,十二月任”。另外《霞外捃屑》该处称沈阆昆此前曾官“上虞教谕”,“教谕”应该也是“训导”。这至少也能说明其谢世不会在此前的光绪七年“辛巳”(1881)。因此,《霞外捃屑》该处所谓“辛巳”,很可能是由汪曰桢卒年牵连而致误;唯季节“冬”与汪曰桢忌日“闰七月二日”确实不同,则不知从何而来。
另外,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正编卷四十四收有沈阆昆[4];该编编定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夏季[注]参见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首《两浙輶轩续录凡例》第十四款,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册第6页。,并且“编中采列,不及时贤”[注]详见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首《拟辑两浙輶轩续录征诗启》第二款,第1册第11页。。如此结合《霞外捃屑》所说的“冬卒”,可以将沈阆昆的谢世时间大致框定在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至十六年庚寅(1890)之间。至于具体究竟在哪一年,则仍然有待继续留意。
二、谢质卿出生时间
《清诗考证》初编第一辑之四《〈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第五十三条“谢质卿”,曾经从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卷四诗歌《寿陕安兵备道蔚青谢公(质卿)六十》一题凡三首入手,据其下一题推测约作于同治九年庚午(1870)秋冬之际,在此基础上逆推谢质卿生年当为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并据第三首第六句原注称其“寿辰在十月杪”[1]上册:166-167。顷读张剑先生《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一文,见其第二部分《官年减岁的比例和岁差》有对该条的订正:
……今检谢质卿《转蕙轩诗存》卷七《闰生草》注:“同治戊辰四月十三日,为余六旬初度。”由同治七年戊辰(1868)逆推,可知其实生于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155页。所引《转蕙轩诗存》该诗,可见《晚清四部丛刊》第十编第108册,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47页。
这个推算过程,确实最为可信。
除此之外,《闰生草》该小集自序,曾提到“林颖叔方伯(寿图)乃以闰月为补生之会,并征同人赋诗”。检林寿图《黄鹄山人诗初钞》,卷十五有一首七言古诗《闰四月十三日,邀曼叔集欧斋,为谢蔚青观察补作生日。曼叔,蔚青妹婿也》[5],据集内作品编年正作于同治七年“戊辰”(1868);内称谢质卿(蔚青其字)“始兴郡裔老鹤姿,六十平头霜未鬓”,这也可以作为佐证。并且从这两处所述,还能够确切知道谢质卿的生日在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的四月十三日(公历5月26日)。而回看王权该题寿诗,非但集内编排次序未能确切反映写作年份,而且所说“寿辰在十月杪”也是错误的。
附带关于林寿图,曾见江庆柏先生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依据民国《闽侯县志》卷六十八本传,记其生卒年为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至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6]。这里其他毋论[注]参见拙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肃震”等八位福建籍作家为中心》第八条“林寿图”,《闽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6—17页。,仅从上及“为谢蔚青观察补作生日”该诗所云“君家豫章我闽峤,我生道光君嘉庆”,也可以知道林寿图出生于道光年间。而所谓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实际上乃是谢质卿的生年;县志修纂者很可能也是从该诗获得线索,却把两个人看颠倒了。
另外,关于谢质卿的官年,曾见《张祥河奏折》第三部分《录副奏折》“咸丰朝”内,“咸丰元年[辛亥,1851]五月二十四日”《奏请谢质卿调补长安县知县事》(编号“271”),称“惟查有朝邑县知县谢质卿,年四十七岁”[7]215;又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奏请谢质卿升补乾州直隶州知州事》(编号“311”),则称“兹臣查谢质卿,年四十六岁”[7]256。不但都有意往大里说(本年谢质卿实际仅有四十三岁),而且放在一起即自相抵牾,确实相当复杂。
又,谢质卿谢世时间仍旧不详。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六十九《名宦志·六》(嘉庆道光朝)“知府”本传,曾叙及谢质卿“光绪四年[戊寅,1878]三月以病告归,旋卒”[8];但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年之内,抑或其后某个时间。
三、博明生年及其他
《清诗考证续编》第一辑之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续)》第二十四条“博明”,曾经依据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钦定千叟宴诗》卷十二博明名下所注当时年龄“年六十五”,逆推其生年为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注]朱则杰:《清诗考证续编》,上册第92—93页。原见拙作《清代八旗诗人丛考》第二条“博明生卒年及其他”,《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26页,即下引陈鸿森先生文章所指。。顷见陈鸿森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订补》(下篇)第六十七条“博明”[9]155,认为《钦定千叟宴诗》“此类官书记载,非皆实龄,难为确据”,而根据博明《西斋诗辑遗》卷三《乙巳九日,同乐槐亭宝藏寺登高,和壁上韵》“六十衰颜太瘦生”云云[10],“以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年六十推之”,“应生于雍正四年(1726)”丙午。这个结论,可以为博明的生年提供一种异说。不过从方法上来讲,一般的“六十”特别是出现在诗歌正文中的“六十”,不一定就是指六十岁整。假如这里的“六十”是六十余岁的泛言,那么与本年六十五岁也就不存在矛盾[注]另外本次“千叟宴”,所有预宴者的年龄起点为六十岁,所以博明没有必要在这种场合冒着“欺君”的危险而把自己的年龄“造假”到六十五岁。有关“千叟宴”的具体情况,可参《清诗考证续编》第二辑之九《“千叟宴”与“千叟宴诗”》,上册第504—545页。。因此,仅仅根据这条材料,还无法判定《钦定千叟宴诗》的记载就是错误的。
陈先生此文篇幅很长,分作“上”“下”两篇发表,各有四十条,序号相连。文章虽然总体上是为江庆柏先生编著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而作,但无意中也还有不少条目可以为拙著提供订补,特别是材料方面的补充。例如,《清诗考证》初编第一辑之四《〈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第二十九条“朱文藻”[1]上册:137-138,曾经依据梁同书《文学朗斋朱君传》确定朱文藻(朗斋其号)的具体生卒时间;而陈先生此文第十八条“朱文藻”[11]136,则不仅有梁同书的这篇传记,而且有朱文藻本人的两条自记,因此更加可以确信无疑。并且从该条注释,还得知陈先生在2017年发表过《朱文藻年谱》,可备日后详细参考。又如,《清诗考证续编》第一辑之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续)》第三十七条“吴衡照”[2]上册:111-112,曾经依据汪远孙辑《清尊集》卷七第九题亦即道光九年“己丑”(1829)第四题《挽子律教授》第四家章黼诗歌小序“己丑二月十四日[公历3月18日],吴子律进士殁于婺郡学署”来推断吴衡照(子律其字)忌日;而陈先生此文第三十六条“吴衡照”[11]142,则引据“吴之瑗纂《休宁厚田吴氏宗谱》卷四‘吴衡照’条载‘衡照……殁道光己丑(九年,1829)二月十四日’”,可以相互印证。另外如近年所写“《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系列的未刊稿内,有一条针对卷四十一吴应和小传原缺的卒年[12],依据某人挽诗予以补足(具体暂时从略);而陈先生此文第三十四条“吴应和”[注]陈鸿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订补(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4期,第141页。后来已经补记在拙稿该处。,则引据“《管庭芬日记》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一日条”有关记载,推论卒年相同,这也是殊途同归的一个例子。
但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联想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陈先生此文,很可能还会有着无意中与拙文完全重复亦即所谓“撞车”的条目,甚至也不排除引据材料反而不如拙文丰富的可能。的确,这两种情况同样都存在。例如,陈先生此文第五十九条“倪学洙”[9]151,依据周春《耄余诗话》卷十有关记载,推算倪学洙的卒年及生年;而近年拙作《清代海宁诗人生卒年丛考——以周春〈耄余诗话〉为中心》第六条“孙效曾”,已经附带考察同条诗话记载的倪学洙[13],材料和结论完全相同。又如,陈先生此文第六十二条“徐昌薇”[9]152-153,依据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阮元辑《两浙輶轩录》特别是徐昌薇《清波小志》、陈景钟《清波小志补》,考察“徐昌薇”就是“徐逢吉”及“徐紫珊”,并推算其生卒年;在拙著《清诗考证》初编第一辑之四《〈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第十三条“徐逢吉”[1]上册:111-116,及《清诗考证续编》第一辑之八《〈清诗考证〉初编订补》第四条“徐逢吉卒年及其他”[2]上册:329-330中,不仅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材料都已经用到,而且还另外引及厉鹗《樊榭山房集》、朱彭《西湖遗事诗》、华嵒《离垢集》,等等。再如,陈先生此文第七十八条“黎简”[9]158-159,依据黎简本人两首诗歌、黄丹书《明经二樵黎君行状》,推算黎简(二樵其号)的生卒年;而拙著仅《清诗考证》初编第一辑之二《读〈清人诗集叙录〉札记》第十八条“黎简”有关内容[1]上册:53-54,即结论相同,材料在此之外还引到更多黎简本人的诗歌,更不要说从20世纪的《清诗代表作家研究》下编之五《清诗札记》第八条“黎简享年”[14],到《清诗考证续编》第一辑之八《〈清诗考证〉初编订补》第一条“黎简生年及享年”[注]朱则杰:《清诗考证续编》,上册第326—327页。此外此书及初编还有一些条目涉及这个问题,具体过繁从略。,一而再、再而三地涉及这个问题了。并且拙著中的条目,在入书之前一般都像前述倪学洙该条一样,与其他某些条目组合为一篇论文或者单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
笔者一人尚且如此,那么再进一步联想到整个学术界,这样的情况自然更多。先说成批者,例如陈先生此文第五条“王复”[11]131、第七条“王九龄”[11]132、第三十一条“李富孙”[11]140-141、第三十八条“余鹏翀”[11]143-144等,又第四十七条“罗有高”[9]146-147、第八十条“魏成宪”[9]159等,与《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增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辑所载鲁小俊先生《若干清代作家生卒年考略》一文第三条“王复”[15]269、第一条“王九龄”[15]268、第十条“李富孙”[15]271、第十二条“余鹏翀”[15]272、第二十二条“罗有高”[15]274-275、第三十六条“魏成宪”[15]271等,不但完全重复,而且其中“罗有高”条的材料还以鲁先生该文更为丰富。鲁先生该文据其引言介绍,主要针对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16],同时兼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立目者共三十八条(序号第十一重复一次,另外末段两人不立目),而其中重见于陈先生此文者大约占到六分之一。再说零星者,例如陈先生此文第七十七条“翟灏”[9]158,依据其《无不宜斋续稿》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编年诗有《六十初度,同人欲醵文酒之会,赋谢》一首”,逆推翟灏“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而汪少华等先生共同点校整理的《翟灏全集》,卷首《前言》也正是这样推算翟灏的生年,并且明确交代是“据蒋寅先生考证”[注]翟灏:《翟灏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册第2页、第8页“校勘记”[九]。另外《全集》所含《无不宜斋续稿》卷首《整理说明》也曾同样推算一次,见第8册第1页;诗见第132页,题内“赋谢”或误作“志谢”。——具体见于蒋寅先生《金陵生小言》卷十二《清集掇珍·下》“无不宜斋续稿”条[17]。又如陈先生此文第四条“王昙”[11]130-131,针对《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注材料的混淆(结论正确),列举龚自珍《王仲瞿墓表铭》、陈文述《颐道堂诗选》、王昙《烟霞万古楼文集》、钱泳《履园丛话》共四条材料以证明王昙卒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而非二十一年丙子(1816);而郑幸先生点校整理的《王昙诗文集》,末尾附录之四《王昙年谱简编》最末“嘉庆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五十八岁”条[18],不但这些材料早已都有,而且还多出另外好几条材料,更加翔实清晰。
笔者讲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责怪陈先生,因为我自己同样未能幸免。记得以前写过一篇《戈鲲化生年及其他》,依据《戈鲲化集》有关作品推算戈鲲化的生年,发表在《古典文学知识》杂志[19]。后来发现,在拙作之前,至少已经有三位学者考察过同样的问题,并且比拙作写得更为丰厚。因此,该篇拙作只能彻底废弃。有关具体情况,我把它附记在《清诗考证续编》第三辑之六十五《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第四十四条“程登甲”的末尾[2]下册:1269,作为自己的一个警示。除此之外,至今我自己仍旧未能发现的类似问题,包括拙著《清诗考证》前两编内的其他各项内容,估计也还难免存在。所以,每当我在某些场合需要介绍拙著所谓“原创性”的时候,总要加上一个“除个别可能与前人或时贤无意之中撞车以外”或者“除个别可能前人或时贤已经解决而本人还不知道者以外”之类的说明。在这一点上,我只能说是相对清醒一些或者清醒得早一些而已。
而如前所述,陈先生此文立目者一共八十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其他学者那里,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无意中分别甚至一再被考察过,这连同陈先生在内,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清代人物生卒年历来十分关注,同时也确实取得过许多研究成果,总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问题在于,这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及时汇聚到一起,那么读者要查找、利用就比较困难,在进行新的研究的时候就难免出现类似的“撞车”情况,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而最好的汇聚方法,本来就是《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不断出版增订本。但是,出版增订本,从编著者的角度来说,一方面需要花费很大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在计算科研业绩、申报科研奖励之类的时候却往往不被承认,并且还要看出版单位从经济效益考虑是否愿意出版。所以,到现在快要20年了,我曾经直接询问过江庆柏先生,这件事情仍然看不到希望。于是像我这样的读者,只能把日常见到的有关线索手工记录到该书相应的位置,以备日后一并检索。前述陈先生此文的情况,正是在记录的过程中发现的。但仅仅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日常所见,那结果也一定会挂一漏万。
从这些年特别是接下去的学术发展来看,关于清代人物生卒年,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之后,应该开始培养专门的人才,乃至组建专门的团队和机构了。这样的话,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和其他各种相关的研究成果,就可以集中创建为专门的数据库[注]参见朱则杰等:《朱则杰教授荣休纪念集——〈全清诗〉探索与清诗综合研究》前编之八《全清诗人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使用》,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1版,第43—51页。,能够随时补充录入,也能够随时批量导出,包括形成著作以用于出版。如果可能的话,这个数据库还可以进一步建设成一个开放的平台,让其他读者也能够随时补充录入,当然同时也能够随机查询。它既可广泛服务于相关的学术研究,又能为以后的增补工作提供全面、便捷的参照系,其前景自然是无限的。
四、刘文蔚生年与“甲子”六十天计年法
《清诗考证续编》第三辑之三十一《刘文蔚〈见闻随录〉》,曾经利用一种特殊的年龄表述方式来推算刘文蔚的生年:
刘文蔚《石帆山房诗选》自序……末尾款署:“乾隆乙未孟夏,四百五十三甲子石帆刘文蔚自叙。”这里的“四百五十三甲子”,应该是关于年龄的一种特殊表述方式:一个甲子计为六十天两个月;先减去本年“孟夏”四个月两个甲子,为四百五十一个甲子;再除以每年十二个月六个甲子,得完整七十五年,又剩余一个甲子两个月。如果这个算法及理解不误,那么本年刘文蔚就是虚龄七十七岁;又据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逆推,刘文蔚应生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十一月。[2]下册:1020
近日偶然注意到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五《刘豹君生圹铭》,有关记载说:
乾隆丁亥季冬之月,豹君先生营寿藏……于是拜手为铭以祝之曰:“君名文蔚,字曰豹君……君将七十,健而神王……”[20]
这里“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本年刘文蔚“将七十”而不到七十岁,即出生于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之后。这样看起来,我们上面推算的“刘文蔚应生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应该会是正确或者比较接近的。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该处所谓“四百五十三甲子”,确实是关于年龄的一种特殊表述方式。
另外,从互联网上一再检索到某些资料在刘文蔚名下括注有生卒年“1700—1776”,亦即康熙三十九年庚辰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享年七十七岁;但可惜都没有交代依据,无从复核。而单就这个生年来审视我们上面的推算,则有可能在月数的零头上计算得过于精确了一些——如果“四百五十三甲子”先除以每年十二个月六个甲子,得完整七十五年;再将剩余三个甲子六个月作为“孟夏”所在的上半年来看待,那么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刘文蔚就是虚龄七十六岁,逆推其生年刚好为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四百五十三甲子”的“三”字属于“二”字的印刷错误,那也刚好吻合。现在姑且先一起记在这里,容待日后有便再继续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