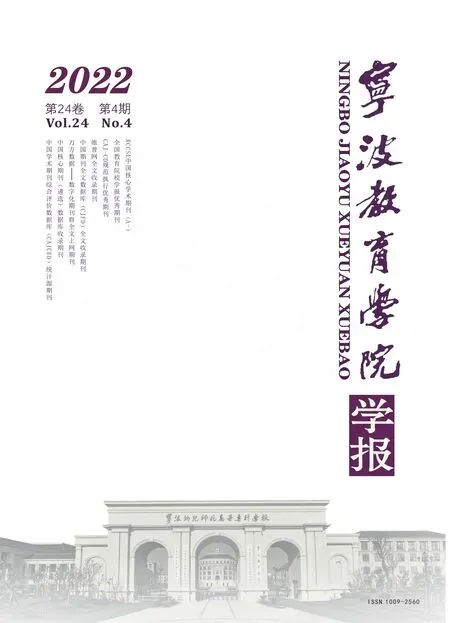解码高校教师职业幸福感
王利利,蒋祥辉
(1.广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广西 桂林 541004;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人事处,广西 桂林 541004)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2018 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35 年,要让广大教师在其岗位上感受到幸福感。众多学者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关注也与日俱增,研究发现,近十年我国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总体处于中上水平,但是仍然存在感受不到幸福的教师[1]。因此,从微观视角审视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深挖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子,重塑和谐共生的学校与教师关系,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成为高校破解当前这一问题的必要路径之一。
一、文献综述
(一)幸福感的概念研究
对于教师幸福感,很多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实际状况给人本身带来的满足感即人的幸福[2]。英国教育家Elizabeth Holmes 认为幸福感指生活中各个维度所具有的平衡感和舒适感[3]。有学者认为教师基于对自己工作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对其自身物质、精神等各需求满足时产生的喜悦即为职业幸福感[4]。有学者认为教师幸福感是指教师在生活、工作中获得满足和自由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发挥自己潜能并伴随着力量增长所获得的持续快乐体验[5]。教师幸福感指教师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情感体验[6]。
(二)职业幸福感的研究
1.影响因素研究。关于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多从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进行论述,外在即影响教师幸福感的一切外在因素,内在即教师自身的各种影响因素。有研究者认为教师职业幸福感三因素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组织支持程度、社会认可程度[7]。有研究者认为影响教师幸福感的因素有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知识储备、专业素养与科研能力,应对外界压力的心理资本,其中外界的压力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如教育评价体系、职业声望以及职业收入等),也有学校环境方面的因素(如学校管理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机会、职称晋升制度、福利待遇等)[8]。
2.维度研究。职业幸福感的维度研究都体现在实证研究的问卷或访谈设计中。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者均构建不同的维度进行调查研究。有研究者的测量量表由心理幸福感、职业幸福感、健康幸福感、社交幸福感、财务幸福感和环境幸福感6 大维度构成[5]。有研究者以自身发展、价值实现、工作成就、工作待遇、身心健康、友好关系6 个维度进行访谈提纲设计[9]。有学者认为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可以分择业动因、学校管理、自我实现、社会支持4 个维度[10]。有研究者的职业幸福感量表从工作情感、薪资待遇、工作环境、职业本身、工作成效、人际关系和身体健康7 个方面设置题目[11]。
3.提升路径研究。关于幸福感的提升路径,大多数研究者都从社会、政府、高校、教师自身等不同维度探寻适切的提升路径。有文章指出要从高校教师自身层面(树立“生活方式”职业价值观,增强自身专业发展,提升“恢复体验”意识),学校层面(实行“人本民主”管理,建立合理的考评体系),社会层面(提高社会对知识的尊重程度,加大教育投入)三个层面提升职业幸福感[8]。有学者认为要从政府(撬动教师幸福提升的“杠杆点”)、学校(创建“幸福校园”)、教师(升级“幸福2.0”的观念,成为有幸福能力的人)三个层面协同推进教师幸福工程[12]。
(三)研究述评
教师幸福感的已有文献表明,教师幸福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概念。学者们在研究中探寻影响教师幸福感的各种因素,并构建不同的维度来探索到底何为幸福感。幸福感的逻辑旨归在哪?该如何实现教师的幸福感?学校、政府、教师本身作为教师幸福感的实施主体,该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一系列的问题被研究者不断追踪、探索。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的文献中,对中小学教师的幸福感研究颇多,对高校教师幸福感的研究较少;对幸福感的理论研究较多,问卷加访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略少。因此,本研究将把问卷和访谈两种方法有效结合,对高校教师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不同的变化因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重点从微观层面理清学校自身,该如何从内部探寻教师幸福感的真实诉求,探索教师幸福提升路径,为高校教师队伍稳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观照。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对同一高校的群体及个体进行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教师职业幸福感进行过程性、解释性的探索。调查问卷是在参考苗元江老师的《综合幸福问卷》基础上改编而成[13]。测试的内容包括幸福感、幸福指数2 个模块共28 道题。其中,幸福指数采用9 级评分,而其他题目均采用7 级评分。对反向题进行重新赋分后,计算量表总分,总分越高,则幸福感程度越高。访谈提纲以工作环境舒适度、教学水平提升度、人际关系和谐度、激励机制有效度、职业规划发展度五个维度进行问题设置。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次问卷调查选择某独立学院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250 份,回收239 份,有效问卷226 份,有效回收率90.4%。研究所有数据的录入、整理和统计均采用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访谈抽取了该高校不同岗位上的3位教职工。一位行政管理人员(编号A1,外校硕士),一位专任教师(编号A2,外校硕士),一位辅导员(编号A3,本校本科)。
(三)信效度分析
一般而言,一份优良的教育测验至少应该具有0.80 以上的信度系数值才比较具有使用的教育价值[14]238。本问卷总的信度系数为0.892,具有良好的信度。KMO 值小于0.5 时,不宜进行因素分析[14]208。该问卷KMO 值0.867>0.5,结构效度良好,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高校教师幸福感的总体分析
从总体样本分析看,该校教师的幸福指数均值为5.45 分,其标准差为1.457,最高分为8 分,最低分为1 分。根据幸福指数频数分析,得分为6~7 分者占比为44.7%,他们认为自己比较幸福;居中的为31%;得分在1~4 分的被试占比为19%,他们认为不幸福;认为自己很幸福和非常幸福的为5.3%。根据幸福感的描述统计分析,各题的理论平均分为4分,幸福感量表有27 题,理论平均分为4×27=108 分。
(二)幸福感差异性分析
从上可知,幸福感水平呈正态分布,可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不同年龄、学历、职称、教龄、岗位、年收入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作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对其所呈现的数据进行归因追问,以诠释该校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
1.年龄和幸福感水平的关系。从分析可知,不同年龄阶段教师幸福感水平存在明显差别。其中40 岁以上教师幸福感水平普遍较高,均值为122.67,25~40 岁教师幸福感水平最低,均值为118.32。40 岁以上教师,事业正处于辉煌时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生活较稳定,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在工作中易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其幸福感水平最高。25~40 岁的教师是压力与挑战同存,一边职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另一边买房、结婚、生子等现实问题,工作、生活的重压导致他们幸福感水平较低。三位访谈者年龄均在25~35 岁之间,因这个年龄段要承担养家糊口重任及工作压力等,自我感觉幸福感指数确实有点低。
2.学历和幸福感水平的关系。从分析可知,不同学历教师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幸福感水平最高,均值为151.33,硕士学历的教师幸福感水平最低,均值为115.51。博士是该校引进人才,在科研、教学、职业发展、待遇等方面都较高,成就感和荣誉感较强,幸福感水平最高。部分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从事同一级别工作,内心不平衡,催生挫败感,幸福感最低。A1 表示,他和本校毕业本科生做类似工作,想转专任教师岗或竞聘中层,也因部分近亲繁殖原因或在校年限资历等各种不可抗拒原因受到阻力,幸福感指数最低。
3.职称和幸福感水平的关系。从分析可知,不同职称教师幸福感水平差异性非常显著。教授幸福感水平最高,均值为153,讲师幸福感水平最低,均值为114.93。追其原因,主要是物质待遇与教师职称挂钩,职称越高,收入越多。学校给教授物质上的奖励、科研和社会服务机会、地位及职业发展前景更好,幸福感水平最高。讲师是该校“顶梁柱”,教学任务重,科研成果少,职称评聘门槛越来越高,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缓慢,故幸福感水平最低。A1、A2 两位访谈者为讲师职称,他们感觉自己的压力更大,学校职称评审条件严格,职称评审压力倍增,而职称又和工资福利待遇息息相关,幸福感较低。
4.教龄与教师幸福感的关系。从分析可知,不同工作年限教师的幸福感水平存在非常显著差异。其中16~25 年教龄的教师幸福感水平最高,均值为137.29,而11~15 年教龄的教师幸福感水平最低,均值为97.2。经了解,该校16 年以上教龄教师大都步入中年,由于较长时间工作积累,生活均较稳定,很多人是学校工作中坚力量,幸福感指数最高。而11~15 段的教师工作、自我晋升等各方面压力剧增、还需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等,其导致幸福感水平偏低。三位访谈者工作时间在6~10 年之间,他们同样遇到各种压力,幸福感不高。
5.岗位与幸福感水平关系。从分析可知,不同岗位教师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说管理人员幸福感水平(均值为127 以上)高于专任教师(均值为116.26)。究其原因是该校师资水平不均衡,专任教师来源多为刚毕业学生或退休教师,或教学经验不足,或精力有限,幸福感水平不高。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一部分是母体学校派出的专门管理人员或自主招聘人员,感同身受学校发展,自我价值得到实现,幸福感水平较高。A1、A3 为行政管理人员和辅导员,工作内容单一,感觉较幸福。A2 为专任教师,需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在强大工作压力下,还要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因此感觉到的只有与日俱增的压力,幸福感无处可寻。
6.年收入与幸福感水平关系。从分析可知,不同待遇教师的幸福感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教师所体验到的幸福感高低与收入水平相关性不高。6~10 万元段的教师幸福感第一(均值为125.07),而2 万元以下的排第二(均值为122.9),前两者均值相差很小,中间段位的教师幸福感略低。A1、A3 访谈者年收入3~5 万属于中等水平,因面临养家等各种原因,也略感收入不高,幸福感一般。A2收入刚过6 万,比A1、A3 自我感觉幸福感略好些。但是三者访谈中均表示,整体来说,收入对他们影响不大,主要是工作、个人发展等会对其造成各种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结合分析可得出,该校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居于中等水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历、不同职称、不同教龄、不同岗位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明显。
如50 岁以上教师幸福感水平最高,而25~40 岁教师幸福感水平最低。伴随年龄增长,幸福水平呈逐渐上涨走向[15]。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最高,中间学历的教师幸福感指数反而最低。中等职称者幸福感水平最低,高职称者幸福感水平最高。教龄16 年以上教师职业幸福感最高,11~15 年阶段教师职业幸福感最低。专任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稍微低于管理岗位的教师。但不同待遇的教师幸福感水平不存在差异,因此,增加收入不一定能提高高校教师幸福感。
(二)建议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解释了人的需要与幸福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的幸福在于人具有哪个层次的基本需要,其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2]。高校应以该需求理论为切入点,重塑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实施路径。
1.设置有效的教师激励机制。高校应着眼于教师自身发展,设立激励机制,保障教师幸福感提升。根据不同年龄、职称教师的需求,分类制定不同教师成长制度。对青年教师,制定教师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及专业指导制度,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给予一对一帮扶指导;对中老年教师,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机制方面加以重点关注和支持。基于不同学历、岗位教师需求,设置多维度培养计划。针对学历低的教师,学校鼓励其进行学历提升和进修;针对专任教师,建立教学与科研互补的互通发展模式;针对管理人员,提供多层次、高品质的管理水平培训,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
2.构建分类的教师评价机制。针对不同岗位教师,学校分类设置不同评价标准,构建公正、科学的教师评价系统,将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学生自身发展状况、社会服务等纳入其中[16]。重视对教师的全面性、发展性评价,而不仅仅以论文、科研论英雄,彻底破除唯论文、唯科研论。只有将考评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兼顾高校各项任务,才能综合评定教师的工作,使教师感受到学校的公平公正,感受到学校对教师有温度的关心。
3.营建有幸福感的学校文化。针对当前教师幸福感整体指数居于中等水平的现状,高校需聚合师生力量,破解学校文化密码,凝练学校精神,以宏微相生、内外交融、远近互成的逻辑机制,唤醒高校从“内省”到“精进”的文化自觉,从“融通”到“创新”的文化自信,从“跟跑”到“领跑”的文化自强[17],打造以校为本、以师生为本、以发展为本的学校文化[18]。
——以大四公费师范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