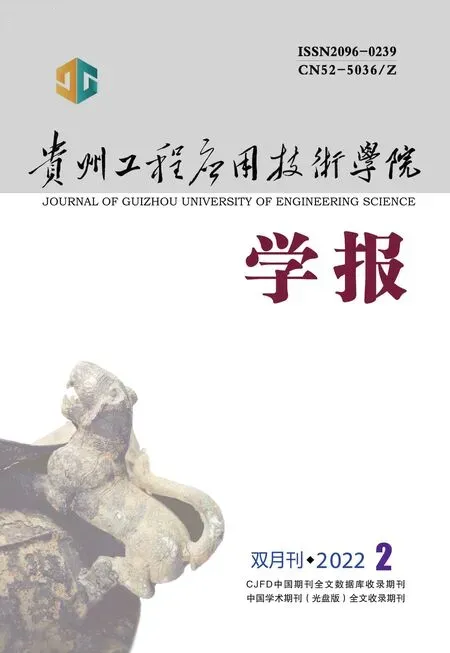巴金《狗》:标题符号的修辞阐释
杨淑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广义修辞学以话语层面的修辞技巧为阐释起点,向文本层面的修辞诗学和精神层面的修辞哲学延伸,构建起“话语方式——文本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的层级框架,在更开阔的理论背景下,为文本批评探索出一条融合了语言学、文学及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狗》是巴金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部短篇小说,也是其较为满意的作品之一。小说叙事紧凑,情节简单,讲述了一个无父无母的“我”在非人社会中挣扎求生的辛酸故事。相较于巴金其他作品的关注热度,短篇小说《狗》的研究显得有些冷门,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此外,贴切的标题符号往往预示着小说的创作主旨,也是作者对小说的基本定位,让读者能够通过标题符号略窥文本修辞意图,而从这一角度对巴金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屈指可数。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借助广义修辞学理论,从标题符号“狗”的双重认知出发,探讨其如何与主人公相关联并阐释其特殊的修辞内涵在文本语篇建构和主题表现中的重要意义。
一、标题符号“狗”:蕴含两层认知
要把握标题符号的修辞内涵,首先需要辨析主体认知中名词“狗”的具体概念义和修辞义。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有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两种。概念认知是一种普遍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进入概念认知的概念,以一种被规定的语义,指向事物的共性。[1]《现代汉语词典》对狗的定义是“哺乳动物,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舌长而薄,可散热,毛有黄、白、黑等颜色。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种类很多,有的可以训练成警犬,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也叫犬”[2]。基于此,“狗”的核心义素可表示为[+驯化动物][+感知敏锐][+服务人类]。在主体积极调动感官和想象力的前提下,修辞认知能够打破单向僵硬的概念阐释,审美化地展开对象,从接受与再表达的角度呈现意义的流动性。经过彼此长期的交际生活,人们发现现实社会中一些人的行为特征与某类动物高度重合,于是认知主体将二者有机关联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动物设喻的修辞模式。“狗”本身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主人绝对忠诚,同时也十分擅长讨人欢心、懂得巴结主人,后来人们慢慢地将此类特点投射到了不好的事情和坏人身上,如“走狗、狗腿子、哈巴狗、狗眼看人低”等都是一些贬义色彩相当浓厚的词语。因此根据与人的某些相似性特征,“狗”这一符号在人类的认知范畴中自然而然地摆脱了概念认知的理性束缚,延伸出了别样的修辞内涵,详见表1。
在现实生活中,犬类既可能以其憨态灵性而成为人们的爱宠,也可能因其忠诚机敏被视作人们的朋友,然而就小说的文本语境来看,狗的正面形象完全退出公共经验,暗转为一种卑贱讨食的低等动物,这与主人公“我”以及当时部分为求口腹温饱而不得不泯灭尊严的底层百姓具有相似之处,三者的共同特征为[+低贱卑微][+备受歧视],因此,能指符号“狗”承载着动物界中的犬、文本叙述者“我”、旧中国底层民众这三重所指对象,同时也幻化为概括后面二者微不足道的社会地位的隐喻符号。
二、标题符号“狗”:映射非人境遇
作为概念认知的犬不仅是对主人公身份的隐喻性定位,也成为“我”为自己定义的他性参照物,“我有黄的皮肤,黑的头发,黑的眼珠,矮的鼻子,短小的身材”,身为一个具体实在的人,“我”天然拥有正常人对于生活和情感的种种需求。于是,渴望知识的“我”大胆地走进学堂求学;渴望亲情的“我”把破庙里的神明当做自己的父亲;渴望温暖的“我”不得不插带草标出卖自己,诸如此类明显是狗这一动物所不具备的需求成为“我”作为人的显性标记。但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我”顾不上卫生和尊严,吞下又黑又硬、沾满尘土的馒头,甚至因为嫉妒一条狗所受到的待遇而主动模仿狗的体态,练习匍匐爬行,摇着头,摆着屁股汪汪地叫着。从生存状态看,主人公“我”与狗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与狗相比,有不如狗的地方:狗有人收留,有剩骨头啃,可以忠心地伺候主人,而叙述者“我”却备受歧视,连给人做牛做马的机会都没有。那些长着白的皮肤、蓝的眼珠的外国人对“我”的唾骂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仅遭受那些“伟大的人”拳打脚踢的暴力伤害,更毫无尊严地被冠以“狗”的蔑称,“我”对于自己是人是狗的疑惑就此得到确证,最终如释重负地挣脱出似人非人的困境,彻底接受自己就是一条狗的悲怆命运。

表2 正常人、“我”与狗的行为/心理对比
如上表所示,“我”作为综合了人欲与兽态的矛盾体陷入了一种非人非狗的畸形状态,这种“狗样的人”的畸形状态在“我”看来似乎地位得以提升,实际上主人公“我”被弱智化了,从人的身份跌落到牲畜的位置上,叙事文本中的视点也就从人性转移到了动物性和奴性上,作品由此呈现出更富戏剧性的阅读效果。此外,作者还将泛称概念“犬”具化到一条白毛小狗身上,把它和非人社会中的“我”放置在同一时空内,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唏嘘不已的讽刺剧,“我”与白毛小狗通过两次直接冲突形成了鲜明的镜像对比。第一次冲突是当“我”看到白毛小狗的脸紧偎着女性粉红色的双腿甚至可以沿着腿跳到女性怀里时,“我”以为自己也有这么做的权利,于是兴奋地向那双腿跑去,结果还没有接近目标就被别人推倒在地,遭到路人的无情讥笑;第二次冲突是“我”再次在街上遇见那条白毛小狗,当白毛小狗突然向“我”扑过来时,“我”便爬在地上和它扭打在一起,互相撕咬,全文也在这场荒诞不经的人犬大战中达到高潮。在这两场讽刺剧中,人与狗进入共同的现实秩序,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白毛小狗可以与人类亲密互动,“我”却不被允许接近人类;在人犬纠缠的闹剧中,路人为了保护畜生而对“我”进行拖打痛踢,“我”因疼痛晕厥后就被随意弃置在暗无天日的洞穴中。人不如狗的悲哀现实以及“我”经受的非人境遇在这两次镜像对比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标题符号“狗”:参与语篇构建
《狗》全文短小精练,共分为五小节,包含63个自然段。文本撇去了非必要的人物形象书写及其他可能旁逸斜出的叙事纠缠,以“重要事件——身份认知”的交替循环模式充实语篇的主体构架并规约文本叙述的逻辑路向,使得叙述线索十分简洁清晰,主人公从人到狗的自我认知转变正是推动文本叙述的内在动力。

表3 “重要事件”与“身份认知”推动的文本叙述
如上表所示,小说1-2自然段是故事的开端,简要交代了文本主人公的身世信息。作品标题符号是“狗”,但在初始叙事中,首先进入阅读视野的并不是动物界中的“犬”,而是作为人的“我”,这种反差隐含着作者匠心独运的修辞意图——开篇作者指出主人公“我”是千百万人中间的一个,明确“我”身而为人的事实判断,这为下文主人公“我笑着,我流了眼泪地笑着。我明白我现在真是一条狗了”[3]的价值认同进行反向的修辞布局。小说的发展、高潮则由7次重要事件与6次身份认知转变共同推进。第一次“我”听取老年人的建议,昂首挺胸走进学校却被呵斥赶出,主人公由此生发出自己究竟算不算一个人的认知疑惑;第二次“我”回到暂居地破庙反思,由乞讨残汤剩饭的生活现状总结出自己不过是“狗一类的东西”;第三次“我”尝试着到街市上出售自己,但除了几个小孩玩弄“我”身上的草标外并无人问津,所以“我”悲哀地发现自己是人间不需要的东西;第四次“我”在公馆墙角哭泣,接二连三地遭受冷眼与痛踢让“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人;第五次是“我”企图靠近女性粉红色的双腿却被人推倒在地,“我”明白自己不配做狗;最后被外国人欺侮歧视及与白毛小狗互相撕咬的冲突让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真正沦落至一条狗的境地。
从活生生的一个人到最终自我认同为一条狗,这在逻辑上是悖理的,但在文本语篇建构起的修辞语境中却是合理的。在小说中,作者将犬的视角与“狗样的人”的叙述进行巧妙穿插,以人的心态写狗——人样的狗;又以狗的心态写人——狗样的人,由此实现每个叙述小节之间的逻辑关联,最终完成全文语篇构建,收到了入木三分的讽刺效果。
四、标题符号“狗”:指向双重主题
综上分析,“狗”这一符号不仅是叙事文本的标题,也是全文的修辞象征。“狗”的概念认知——动物界中的犬,成为构建语篇核心事件的关键,“狗”的修辞认知——狗样的人,即“我”的遭遇与认知转变则推动了整个文本叙述的发展。“狗”的两层认知就此引发读者阅读追问:堂堂中国人何以被戏称做狗?旧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导致物质极度匮乏,挨饿受冻成了“我”的生活常态,上流人士对“我”所受的苦难熟视无睹,“我”像条流浪狗般得不到正常人应有的待遇。在作者的修辞设计中,小说主人公没有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年纪,更没有能够标识其社会角色的姓名称谓,文本的叙事身份仅用第一人称“我”代替,从作品的标题符号“狗”至开篇对“我”的身世介绍,已然流露了巴金对“我”这个“狗样的人”的同情。
对“我”的描写与悲悯并非文本叙述的终端,而是意图激发接受个体情感体悟的起点,使得读者的思考不仅仅拘泥于“我”的悲惨人生中。作为直观性的艺术呈现,《狗》一文描写的是整个旧中国的人间悲剧,经由“我”这个苟活在黑暗中的修辞缩影,小说十分尖锐鲜明地映照出旧社会爬行着生活的贫苦大众的生存境遇。作者巴金在深刻揭露这些社会现实之余,也借叙述者“我”之口向读者道出了当时存在的另一更为残酷耻辱的事实,即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和压迫。巴金指出:“小说里那些‘白的皮肤、黄的头发、蓝的眼珠、高的鼻子’的‘人上的人’就是指殖民主义者。小说的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他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么沉痛!”[4]在文本设计中,巴金并未使用“无耻”“可恶”等带有鲜明褒贬色彩的语词直接展露他对外族侵略的痛恨,而是通过主人公正话反说给予那些殖民主义者辛辣的讽刺:“我暗中崇拜他们,祝福他们,我因为世界上有这样伟大的人物而庆幸”,因受外族欺辱而迸发的愤激情绪被克制隐匿在字里行间。文本塑造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异国形象,而黄皮肤的“我”则被称为狗,这种他者与自我的强烈对比,凸显出巴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身份的追求。[5]在故事叙述终端,“我”心中郁积的悲愤再也难以抑制了,借以狗的口吻大胆表达出“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出去!”的反抗意愿,一个卑微如犬的人被逼到走投无路时也会喷发反抗的怒火。至此,这篇由“狗样的人”的控诉编织而成的小说,在追还人的尊严中书写出了双重主题:巴金对悲苦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民族身份的痛苦探索。
五、结语
广义修辞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在注重文本细部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宏观的文本阐释和哲学关照。本文从一个新的解读视角切入,以标题符号“狗”的两层认知分析为起点,探究其与文本中的人物、结构、主题如何实现关联。通过修辞内涵的阐释,可知标题符号“狗”幻化为“犬”和“狗样的人”这两种不同形式贯穿小说文本叙述始终并直指作者巴金强烈的人本关怀和生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