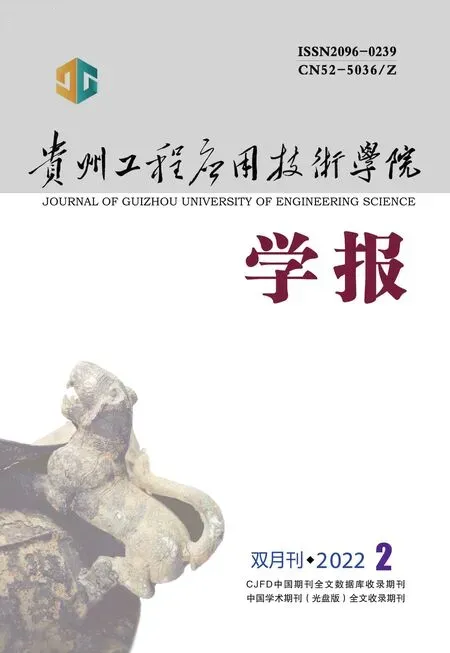卡尼曼认知理论视角下的“沃森选择任务”探析
毛位亮,邓辉文,李夫泽
(1a.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400715;1b.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湖南 娄底 041700)
一、引言
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沃森(Peter Wason)于1966年设计了一个推理任务,也称四卡选择任务,自设计出以来,就引起了大量的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以及逻辑学家的讨论,相应的成果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致力于形成一个理论,在微观上来解释沃森选择任务中的相关现象。如2000年,科斯米兹(Leda Cosmides)和图比(John Tooby)等人发现[1],被试者们在“必须年满18岁才能饮酒”与“如果卡片一面是元音那么另一面是偶数”的这类相似条件句推理实验中,前者的正确率要显著高于后者,他们用“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 theory)来加以解释,认为被试者们在面对包含社会规范内容相关的推理时,会做得更好,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在残酷的生存条件下,对于他人因欺诈而违反社会规范的后果,通常会波及自身并损害到生存利益,所以要能快速准确察觉出欺诈者与欺诈内容,这就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随着自然选择的演化,这种能力就在心智中形成了特定的推理能力模块[2],而解决抽象推理问题,如卡片正反面的任务,则较之没有那么迫切。2013年,刘剑凌的文章用“否定效应”来加以解释[3],认为推理内容涉及到“否定”时,就会变成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认知在“否定”部分的加工会变得较为困难。
另一个方面,是以沃森选择任务为窗口,在宏观上审视与追问日常推理过程中,基本的逻辑、心理以及哲学基础与意谓。如蔡曙山教授有多篇文章①借沃森选择任务这一具体案例,上升讨论到推理中逻辑与心理的问题。2005年,傅庆芳在文章中给出了很多思考[4],如指出逻辑推理是在封闭系统下,只考虑形式的有效性,而不考虑具体的内容;而现实世界是一个开放系统,推理的过程会受到心理、信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在现实中的推理要多关注启发式思考(heuristic)理论;2018年,李帅在文章的展望部分[5],谈及了双系统理论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日常推理与形式推理的界限在哪里,日常推理具体的运行机制又是怎样的,等等。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简要介绍沃森选择任务的具体内容与理论解释,然后辨析“非逻辑与非理性”两个概念间的不同之处,最后以卡尼曼②的认知理论,结合沃森选择任务中出现“漏选与错选”的现象,进一步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理论依据。
二、沃森选择任务的具体内容
沃森选择任务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都大同小异,这里选择其中之一:实验者向被试者呈现4张卡片,每张卡片上,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为了检验规则“如果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另一面是偶数”的真假性,必须翻看哪些卡片?如下图1[3]。

图1 沃森选择任务
实验结果如图2显示[6],只有4%的被试者认为需翻看卡片A和7(正确答案);46%的被试者选择者翻看卡片A和2;35%的被试者选择翻看卡片A;约5%的被试者选择翻看卡片7。后来,奥克斯福德和查特(Oaksford,M.&Chater,N)又陆续做了34个选择任务实验[7],得到了大样本的实验数据结果,89%的被试者选卡片A,25%的被试者选卡片7,62%的被试者选卡片2,16%的被试者选卡片K。据认知科学家约翰·安德森(John R.Anderson)记载[8],在实验早期,沃森在IBM研究中心的报告上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观众中不乏有数学、物理学的博士也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图2 被试者选项的统计分布
三、对沃森选择任务的理论解释
从以上的实验结果中不难看出,沃森选择任务中被试者们表现出的种种“不完美”行为,不是一种简单、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系统的现象。针对这些现象,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一)内容效应(Content effect)
这种观点认为,比起陌生的领域,人们在更为熟悉的领域中可以做出更好的推理判断。沙普尔(Shapiro.D)等人[9]就认为是实验本身的抽象性,而导致被试者不能很好地完成推理任务,他们改变了实验内容,要求被试者检验“我每次去曼彻斯特都是乘坐汽车去的”,这一条件句的真假性时,结果有62%的被试者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格里格斯和考格斯(Griggs,RA&Cox,JR)等人将实验材料作了改变[10],要求被试者假设自己是一名警察,要去检验一个酒吧里是否有未成年人饮酒,具体的规则是:如果一个人在喝酒,那么他应该在18岁以上。然后有四张卡片,卡片的一面是饮品,另一面是饮用者的年龄,分别是:啤酒、可乐、16岁、19岁,问应该如何挑选验证?结果显示有72%的被试者选出了正确答案。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具体非抽象的实验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认知主体更好地完成条件推理任务。但图比等人的工作表明,并不是这种简单的把实验材料由抽象换到具体,就都可以显著提升被试者们的条件推理能力,而是要把这种内容细分到是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内容,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被试者更好地完成推理任务。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很复杂的,值得用更多的视角,来做更全面的分析。
(二)否定效应(Negation effect)
在《人类的心智与认知》中[11],蔡曙山教授则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认知主体对否定的推理更为困难,加工难度更大,因为这需要更多的推理步骤和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蔡曙山教授进一步洞见性地指出关键性问题所在:“逻辑学在研究推理时只考虑推理的有效性,而不考虑推理的难度和它所占用的认知资源”。《否定效应与逻辑等价——对沃森实验的解释》这篇文章[3],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人类没有进化出发达的否定思维机制”“否定句加工困难”等因素导致“大脑对否定的加工十分困难,这就是否定效应”。从“否定”的角度,对沃森选择任务进行分析,确实有一定的新颖性,与此同时也值得做更多、更广的理论探索,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推理实验,如THOG③任务,Linda④任务等,这类任务包含更多的是关于析取与合取相关的内容,而较少包含否定的内容,被试者们同样会给出形形色色的错误答案,这些现象可能用否定效应解释就稍微有点力不从心,还需要其他的理论来做解释说明。
(三)证实偏向(Confirmation bias)
从理论出发,逻辑学中的真值表可以直观的罗列出这个假言命题“如果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P),那么另一面为偶数(Q)”的真假情况,P→Q的真值表如下

表1 P→Q的真值表
可以看出要想验证P→Q的真假情况,有如下两种方法:(1)是从P为真时出发,验证Q的真假情况,如果Q为真,那么整个P→Q为真;如果Q为假,那么整个P→Q为假;(2)是从Q为假时出发,验证P的真假情况,如果P为真,那么整个P→Q为假;如果P为假,那么整个P→Q为真。对应到沃森选择任务中,就应该是选择验证卡牌“A”和“7”的背面。这也就是运用逻辑学中的肯定前件式(MP)规则和否定后件式(MT)规则。
从现实出发,沃森本人则认为[12],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推理,与理论上的推理有所不同,认知主体有较强的证实倾向,而较少采用证伪的方式。这一观点在解释该现象上确实合理,但又总感觉“隔靴搔痒”解释的不够深入,因为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为什么认知主体会较少采用证伪的方式?为什么认知主体会较少采用MT规则?是因为认知主体,后天没有训练、习得相关的思维方式,还是先天在生理、认知层面上,本身就不擅长“MT规则”?如果是的话,那么还有哪些思维方式同样也是我们不擅长的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回答。
(四)不合理因素(Unreasonable factor)
还有观点聚焦于实验本身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如没有明确给出对规则的解释,这会导致被试者错误的理解一些信息,如马戈利斯(Margolis)[13],就认为在沃森选择任务中,被试者犯了一些逻辑错误是因为误解了一些信息所导致的,比如被试者把规则中的“如果,那么”理解成了“当且仅当”[4],而“当且仅当”,这是一个双向的推理,所以会有很多的被试者选择卡片“A”和“2”。再比如,有观点认为这个实验本身是一个考察逻辑推理的问题,却有意无意“伪装”成一个日常推理的问题,再加上没有明确的奖惩措施、规定时间的有限性等等因素,导致大多数被试者会随意地进行选择,而不会认真对待,这种随意得出的推理结果被放大上升为“人是不理性的”,这明显是不合适的。从实验设计的角度出发确实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但该观点还是稍显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总还是存在能正确理解信息但仍没能完美完成任务的被试者,该观点不太能解释这一部分的群体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四、卡尼曼认知理论视角下的解释
前述理论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此,值得用更多的理论视角来加以分析这些现象,接下来本文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顺着相关的研究思路,从认知的角度,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来作更进一步地分析,问题一:为什么要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待沃森选择任务中的行为现象?问题二:怎么样用认知的理论,来解释沃森选择任务中的行为现象。试着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更好地厘清这些行为现象背后的理论依据。
(一)非逻辑与非理性(Illogical and irrational)
为了回答问题一,关键是要意识到,沃森选择任务中表现出的非逻辑与非理性不是一回事。不能由被试者在任务中犯的非逻辑,而上升到人就是非理性的结论。首先,这里以决策论中的案例入手。通过介绍卡尼曼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来见微知著,体会到非逻辑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别。这种的例文有很多,但是大致思想都是一样的,是说有如下两个情景[15],情景一:A生意可以稳赚800元,B生意有85%的机会赚1000元,但也有15%的可能分文不赚;情景二:A生意要稳赔800元,B生意有85%的可能赔1000元,但相应地也有15%的可能不赔钱。按照传统期望效用理论:

情景一:选择A的效用,TM(A)=800,选择B的效用,TM(B)=85%β1000+15%β0=850
情景二:选择A的效用,TM(A)=-800,选择B的效用,TM(B)=-(85%β1000+15%β0)=-850
这样来看,理性的选择是在情景一下选择B,情景二下选择A。但实验的结果却是,情景一下84%的人选择了A,情景二下87%的人选择了B。从结果看这明显和效用理论的逻辑相违背,是“非逻辑”的,但卡尼曼后面完善发展出的“前景理论”[16]认为:第一,在面临获得时,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的。第二,在面临损失时,大多数人是风险偏好的;第三,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不同,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这样就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这个在利益得失上“非逻辑”的行为,其实在心理认知上是有另一种“理性”的。
然后,具体到沃森选择任务中,“非逻辑”指的是沃森选择任务中被试者们错选了卡片“2”,和漏选卡片“7”的现象,前一个选择对应到逻辑学中的肯定后件式(AC),这是一个无效的推理规则,被试者们大量采用;后一个选择对应到否定后件式(MT),这是一个有效的推理规则,被试者们却鲜有采用,被试者们违背了如上的这些逻辑学规则,统称为“非逻辑”。“非理性”实则是一个很深奥的概念,这里只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定义:主观的认知、行为,统统与客观的规律不符。从这样的定义乍看起来,非逻辑好像就是非理性,借用《心智行动及其产品——沃森选择任务新探》文章中的论述认为“因此,沃森选择任务的结果就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人是理性的这种观念相悖”[14]。但这正是本文认为至关重要且有异议的地方,沃森选择任务中,被试者表现出的“非逻辑”不能上升到人就是“非理性”的结论。“非理性”中确实有“非逻辑”的一面,但“非逻辑”并不全然就是“非理性”,因为“理性”的部分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至关重要的因素,如认知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等等,这些因素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而只盯着违反逻辑学规则这一个因素不放。换言之,“非逻辑”违反的规律只是逻辑学的规律,而“非理性”违反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就不只包含逻辑学规律,还有经济学规律,生物学规律,认知学规律等等一系列的规律。最后得出结论,一些看似“不理性”的问题背后,实际上有可能是视角过于单一,只局限于某一个理论的结果,如果采用了另外一些视角、另外一些理论就会发现,这些行为不是不理性的,而是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可能有自己另外的考量,另外的一套思维流程、思考方式,尽管这些方式可能会显得不合逻辑,最终呈现出一种西蒙(Simon)所认为的“有限理性”。接着,自然而然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提到的“另外的考量,另外的一套思维流程、思考方式”具体是怎样的一套思维流程、思考方式。这就涉及到问题二:怎么样用认知的理论,来解释沃森选择任务中的行为现象。
(二)漏选卡片“7”与易得性启发法理论(Availability heuristics theory)
漏选卡片“7”的现象用易得性启发法理论进行解释,易得性启发法理论是指[17]:“一旦人们对某事件没有经验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根据该事件可想象的难易程度来判定它的发生概率”。本文认为这种启发式思考,不只是会对一些概率事件进行误判,还会对某些逻辑事件进行误判,从而漏选卡片“ 77”。首先,卡尼曼原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部分群体会对一些概率事件进行误判,如在一个实验中,被试者被问及是飞机更容易出事,还是火车更容易出事?大多数被试者会认为是飞机更容易出事,因为当大多数人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很容易回忆起某某飞机坠毁的新闻、不久前失联的马航,而不太能回忆起火车什么时候出过事,因为媒体、网络经常会发布关于飞机失事这种重大新闻,而较少去报道火车出事等寻常性新闻,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主观上的错觉而忽略了客观的数据,真实情况是,从事故发生的比率来看,美国安委会的一次统计表明,火车的事故率要比飞机高近22倍。其次,本文认为这种易得性启发法思考,不只是会影响到对某些概率事件进行误判,还会影响到对一些逻辑事件也进行误判,会扩充演变成“容易想象到的就是逻辑上可行的,不容易想象到的就是逻辑上不太可行的”。最后,结合到沃森选择任务来做具体分析,当被试者被问及如何挑选卡片时,个体会搜索自己过往的相似经历,以模仿求解,比如会回忆自己是如何验证“如果天气好,就去打球”这种相似条件句的真假情况,被试者能够很容易地回忆起“在某一天天气好时,然后去打球开心的情形”也能很容易地回忆起某一天天气好,却没去食言的场景,从而判断出整个条件句的真假情况,却不太能容易地回忆起自己没有打球时,那天的天气状况,也就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推整个条件句的真假情况。总结一下就是,被试者很容易想象到的是通过前件成立的条件下,等待验证后件的成立与否,进而对整个蕴含式进行判别,所进行的推理方式;而较难联想到当后件不成立时,以前件的真假情况,来对整个蕴含式进行判别的推理方式,这结合上面扩充版的启发法思考“容易想到的方式是逻辑可行的,不容易想到的方式是逻辑不可行的”,最终表现在任务中的就是,被使者们基本都能选到卡片“A”,而较难选到卡片“7”。
当然这里也有疑问会认为,被试者为什么就一定会类比联想到“如果天气好,就去打球”的条件句,也有可能会想到“如果这次我成功了,我就奖励自己一顿”“如果天下雨,地就会湿”等这些条件句呀。本文认为,这些其实是大同小异的,被试者不管如何联想,能想到的都是具体的、和生活相关的内容,因为这些是自己经历的、熟悉的,而较难联想到抽象的、陌生的内容,这也和“内容效应”相呼应。本文用天气、打球的例子,只是做了一个最一般的思考模型,其余情况虽具体的内容不同,但思考的逻辑流程大抵和这个类似。与此相比,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启发式思考?一种回答是,我们的认知资源其实是有限的,因为有限,我们的认知系统在处理问题时,就往往走“捷径”,以达到节省认知资源的目的,这种走“捷径”的思考方式有很多,易得性启发思考方式就是其中一种。
(三)错选卡片“2”与双系统理论(Dual system theory)
错选卡片“2”的现象用双系统理论加以解释,卡尼曼的“双系统理论”认为[18]:我们存在两套思维加工系统,其中系统1是直觉的、快速的启发式加工系统,系统2是理性的、缓慢的分析式加工系统。通常情况下,两个系统的使用权重会有所差别,系统1是处于自主运行的状态,而系统2是处于“休眠”的状态。只有系统1运行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调动系统2来进行更深一步的处理。本文认为,对信息的误判,会导致认知加工过程一开始在处理问题时,对两个系统的使用权重上发生偏移,从而错选卡片“2”。首先,选择卡片“2”和没有选择卡片“7”,虽然这两个选择都是被试者做得不完美的地方,但这两个选择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前者是在“质”的层面上错选了卡片,而后者是在“量”的层面上漏选了卡片,即前者是被试者运用了错误的方法,后者是被试者没有全部运用正确的方法,前面基于卡尼曼的启发式思考理论,只是解释了被试者为什么会漏选卡片“7”的情形,而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被试者,会运用错误的方法而错选卡片“2”。其次,用这个双系统理论来结合任务分析,就是当被试者被要求检验规则“如果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另一面为偶数”的真假情况时,被试者一开始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诸如“34β43”这种明显需要一定计算、思考的问题,进而不会有意识的调用系统2来进行分析,而是会感觉到这个任务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也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只靠系统1就可以“轻松拿下”,这时就会基于规则被表征到的“元音”和“偶数”,做最简单直观、一一对应的处理,而最终得到错误的答案。最后加以总结就是,这种对问题复杂性的误判,会使得一开始认知加工过程在信息处理的权重上,由一个方向转为了另一个方向,从系统2追求的逻辑上绝对可靠性,转为系统1追求的直觉上相对可靠性;从系统2追求的逻辑形式有效,转为系统1追求的简单直观有效;从系统2追求的全局最优解,转为系统1追求的当下满意解。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问题决策,仅靠系统1就可以高效省力地解决,但是当遇到复杂问题时,本应由系统2加工时,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转手交给了系统1处理,这就难免会在结果上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这也是系统1和系统2高效分工背后的一个弊端,即牺牲一定的精确性,而换来更大的高效性。这种经济高效的双系统思考方式,也和第四点“不合理因素”不谋而合,就是在没有明确的奖惩措施、规定时间的有限性条件下,被试者们不会耗费过多的精力去深思熟虑,做这种“不划算”的推理,而是会采用经济省力的思考原则,做最简单直观的推理。
五、总结
本文从介绍沃森选择任务的具体内容与理论解释出发,然后以两个问题为线索,通过“非逻辑与非理性”,“漏选与错选”的角度来分别回答,具体而言就是三个方面:一是要意识到沃森选择任务中表现出的非逻辑,要从认知的层面上加以考虑,而不能简单地就定性为非理性;二是从认知资源有限性的层面上,用易得性启发式思考理论解释了漏选卡片“7”的现象;三是从认知加工过程的层面上,用双系统理论解释了错选卡片“2”的现象。以这样的方式,更好地厘清了这些行为背后的理论依据。
至于后续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如何回答吉仁泽(Gigerenzer)等人⑤“太少与太多”的诘问,日常实际推理与逻辑理论推理还有哪些方面的不同,背后的原因又是为什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如今越来越倡导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也需要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携手做更多的共同探索、共同研究。
注释:
①具体可参见蔡曙山教授的《推理在学习与认知中的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逻辑模型》等文章。
②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54年毕业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获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于美国加州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2002年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史密斯(Vernon L.Smith)教授,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③THOG任务,也是沃森设计的一个经典推理问题,内容是说有4个图案:黑色的菱形、白色的菱形、黑色的圆形、白色的圆形,现在主试心里已经选择了一个图案。规则如下:这4个图案中,要么和主试所选图案的颜色相同,要么形状相同,但不是两者都相同,则被称为THOG图案,现在黑色的菱形是一个THOG图案,那么如果有另一个THOG图案的话,是哪一个?超过80%的被试者不能正确解决THOG问题。
④Linda任务,是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在1983年设计出来的一个问题,具体的内容是说,有这么一段描述:“琳达今年31岁,单身,为人聪慧。她大学时主修哲学,且非常关心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曾参与过反核示威游行。”根据这一段描述,让被试者选择琳达现在更可能是以下哪种情况,A银行出纳,B有女权主义倾向的银行出纳。大多数被试者会认为是B,但这一选择却违背了概率原则。
⑤ 具体可参见吉仁泽《How to Make Cognitive Illusions Disappear:Beyond "Heuristics and Biases"》,《Reasoning the Fast and Frugal Way》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