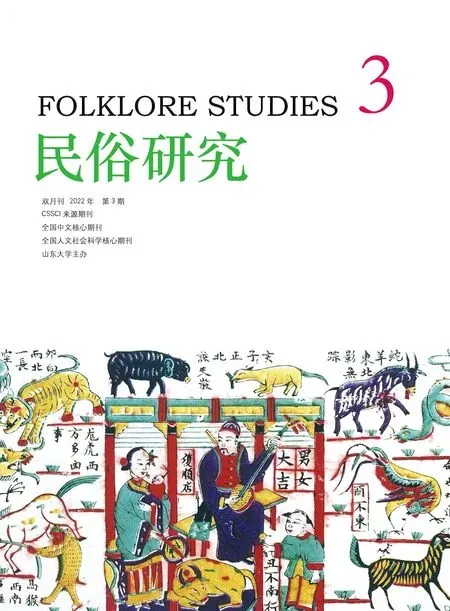日本民俗学的vernacular研究
陆薇薇
一、引 言
日本民俗学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辉煌后,从90年代起步入停滞期,学术影响力日益减退。在这一局面下,日本民俗学第三代学者努力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力求打破学科发展的困境。他们寻求新的理论支撑,主要表现为对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美国公共民俗学研究的借鉴等。
与此同时,近期部分日本民俗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vernacular一词。原本指代地方口语、白话、俗语的vernacular,与民俗学颇有渊源,随着近数十年在欧美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运用,vernacular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术语,内含极其多样的主题,“与权力、近代、人种、阶级、个人和集体的创造性、研究者的定位及政策等问题相关,成为探索民俗学新方向的一个关键词”(1)小長谷英代:《〈フォーク〉からの転回―文化批判と領域史―》,春風社,2017年,第28页。。
日本民俗学者对西方vernacular这一概念的援引和阐发,是对日本传统民俗学(folklore)研究的挑战。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研究的束缚,拓展既有研究中被忽视的领域,并尝试凝练出作为方法的vernacular,这无论对于民俗学研究还是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日本民俗学的vernacular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对欧美民俗学vernacular研究成果译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语境进行了再阐释和灵活运用,却也存在一些尚未厘清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地加以思考。
二、vernacular概念的译介
小长谷英代在将vernacular概念引入日本民俗学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其2016年发表于《日本民俗学》第285号的《vernacular——民俗学的跨领域视角》(2)该文基于小长谷英代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集中授课的内容撰写而成,论文的中文译本《“Vernacular”:民俗学的超领域视界》,登载于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遗产》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译者为郭立东。一文中,她从vernacular和语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关联入手,梳理了vernacular一词词义变迁的过程。
语文学(philology)有着悠久的历史,以拉丁语古典文献为中心的“古典语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蓬勃发展,所以“vernacular初期的语义是指与拉丁语相对的各种语言”(3)J. Leonhardt, Latin: Story of a World Language, trans. by K. Kronenber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7.。正如波洛克所指出的“vernacular的拉丁语词源verna中有‘土生的奴隶’(house-born slave)之意”(4)S. Pollock, “Cosmopolitan and Vernacular in History”, Public Culture, vol.12, no.3(June, 2000), p.596.,与当时代表着中央、权威、通用、学术、教养等含义的拉丁语相对,vernacular用来指代地方的、土著的、身份低下的人所使用的“俗语”。
18世纪后,语文学逐渐科学化,除古典语文学之外,出现了比较语文学、一般语文学等分支,而“黎明期的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在探索文明和民族精神的起源的过程中,以语文学的繁荣为背景,形成了各自学科的轮廓”(5)[日]小長谷英代:《「ヴァナキュラー」―民俗学の超領域の視点―》,《日本民俗学》第285号,2016年。。
比较语文学涉及从印度到欧洲的广阔领域,在德国和英国分别出现了比较语文学与民俗学、比较语文学与民族学的融合。19世纪中叶的民族学研究,在进化论的理论支撑下,借鉴比较语文学的谱系研究法,对所谓蒙昧、野蛮社会进行考察,试图解析人类的起源,为西方列国帝国主义思想及殖民行为提供了所谓合法性依据。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各地土著语言、俗语而存在的vernacular,在西欧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被重新阐释。它被定义为蒙昧社会里野蛮的、无法文明化的人种的语言,并由于语言与人种、民族之间的关联性,被作为非文明人、非近代人的代名词”(6)[日]小長谷英代:《「ヴァナキュラー」―民俗学の超領域の視点―》,《日本民俗学》第285号,2016年。。
另一方面,在美国,除比较语文学外,还存在一般语文学的学术倾向,与初期的民俗学研究相互交融。比较语文学试图将多种语言纳入同一体系中加以研究,而一般语文学则注重对某个特定民族的语言、文学进行深入探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由于《圣经》的口语化表述的需要和印刷术的普及,曾处于优势地位的拉丁语逐渐衰落,相反,曾处于劣势的各民族语言——vernacular却得以蓬勃发展。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vernacular,即各民族的口语方言,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页。,“各种地方口语(vernacular)中的土俗(vernacular)特质被剔除,vernacular作为引以为傲的民族语言(母语)被赞颂”(8)Abrahams:《民俗学におけるロマン主義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幻影》,小長谷英代、平山美雪編訳:《アメリカ民俗学―歴史と方法の批判的考察―》,岩田書院,2012年,第16-18页。。不仅如此,如赫尔德从高雅的外来语传入德国之前已存在的德国本土口语中,找寻民族语言的意义那样,民俗学研究又赋予了vernacular一词“本真性”的价值。
之后,语文学研究曾一度因进化论的理论枷锁和醉心于对文本精确性的考订,束缚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在学界的影响力逐渐减退。然而到了后现代,出现了“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9)详见沈卫荣:《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的学术潮流。这一潮流萌发于比较文学界,但其影响与意义却不仅限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后殖民研究者萨义德等人所倡导的“回归语文学”,就根本而言,是要“重回人文主义,通过对语言的溯源重新回到历史生成之初,去寻找那言词背后的‘历史生成’……使语言回到所附着的和所涉及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中,最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种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和敞开”(10)梁鸿:《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语文学在后现代的重新定位,使得语文学研究从对语言本身的关注转向对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关注,并作为具有批判性的方法论的一种,扩大了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影响。而语文学研究的再次兴起及重新定位也使得vernacular一词产生了相应的变化(11)小長谷英代:《「ヴァナキュラー」―民俗学の超領域の視点―》,《日本民俗学》第285号,2016年。,vernacular的含义也同样跳脱了语言学的框架,走向当代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
除vernacular与语文学的关系外,小长谷还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vernacular建筑、vernacular与民俗生活(folklife)、vernacular宗教等(12)vernacular有名词和形容词两种词性。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为日本学者vernacular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作为研究对象的vernacular
如本文开头所述,vernacular一词内涵丰富,与权力、近代、人种、阶级、个人和集体的创造性、研究者的定位及政策等问题相关,日本第三代民俗学者基于日本语境对这一概念的阐发,与日本民俗学界从民俗到日常生活,从民俗到人,“新在野之学”式的思考等一些转向(13)详见陆薇薇:《日本民俗志的立与破》,《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密不可分。在由第二代学院派学者主导的学科建设期,日本民俗学形成了历史民俗学一家独大的格局,也使得民俗(folklore)一词被刻上了“过去遗留物”的烙印,从而窄化了民俗学研究。为了拓展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第三代的领军人物试图用vernacular一词取代folklore一词,使民俗学研究能够朝向当下,包含更为广阔的内容。
(一)日常与vernacular
2021年3月,日本最新出版了由岩本通弥及其弟子编写的一部民俗学教材——《民俗学的思考方法——捕捉当下的日常与文化》(14)该书为纪念岩本通弥教授退休而作,日本教授退休时,通常会出版论文集以作留念,岩本教授及其弟子则采用了编写教材的方式,希望为民俗学的人才培养贡献力量。。在此之前,日本曾有两本影响颇广的民俗学教材,一本是由福田亚细男、宫田登主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另一本是由佐野贤治、古家信平等编写的《现代民俗学入门》。(15)参见王晓葵:《日本民俗学的新视野——从两部日本民俗学概论谈起》,《民俗学刊》2003年第4辑。
宫田登、福田亚细男是日本民俗学第二代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主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初版于1983年11月,正值日本民俗学的黄金时代,可谓日本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教材由“空间的民俗”“时间的民俗”“心意的民俗”“专论”四章组成,前三章包含村落的住宅状况、亲族关系、生产活动、婚丧嫁娶的仪式、民俗艺能、民间信仰、民间传说等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而第四章专论中,他们依据时代的变迁,补充了“都市民俗学”的内容,并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部分,提出了有别于柳田国男“重出立证法”的“区域研究法”,强调把村落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考量;关注各类民俗事象的意义、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性等。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民俗学步入多样化探索期。研究方法、目的、对象的不统一及扩散性是第三代学者的特征。(16)菅豊:《民俗学の悲劇―アカデミック民俗学の世界史的展望から―》,《東洋文化》第93号,2012年。1996年,佐野贤治、谷口贡、中入睦子、古家信平等编撰的《现代民俗学入门》问世。该教材试图突破传统民俗学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更好地应对学者多样化的问题意识,并努力服务于社会。因此,除“自然与民俗”“神的民俗志”“人与人的羁绊”“生与死”外,教材补充了“现代社会与民俗”和“国家与民俗”的专题,将传统民俗学的事例与社会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岩本通弥等人编写的《民俗学的思考方法——捕捉当下的日常与文化》则更进一步,将眼光朝向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试图进一步开拓日本民俗学研究之前尚未涉足的一些领域。
早在1998年,岩本通弥就曾发表《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17)岩本通弥:《「民俗」を対象とするから民俗学なのか―なぜ民俗学は「近代」を扱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日本民俗学》第215号,1998年。其译文刊登于《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一文,指出民俗一词的既有定义强调与过去的延续性及本身的稀缺性,蕴含着“亘古不变的重要文化”这一本质主义的内涵,故而与现实渐行渐远,所以必须倡导民俗学重返当下的日常。自2014年起,岩本提出“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并于2015年创办中日韩三语的《日常与文化》杂志,迄今为止共发行了9期。
《民俗学的思考方法——捕捉当下的日常与文化》这本教材以“日常”“vernacular”为主旨,分为“捕捉当下的思考方法”和“解读现代民俗学的关键词”两个部分。该书在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科学技术、文化遗产、国际化与越境研究、照护、性别、教育、公共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亚文化与民俗学、多样化的民俗学等诸多较为新颖的内容。
在岩本看来,作为对象的日常即是vernacular,指代我们周围习以为常的、不言自明的种种事象。(18)在岩本最新的研究中,他也略有提及菅丰、加藤幸治等人指出的vernacular所包含的普通人的创造性这一内涵,但在其大多数论述中,vernacular基本等同于日常。而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不仅聚焦于这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司空见惯的事象,还关注事象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的过程,即“动态的日常化”。岩本的日常研究颇具日本特色,他汲取了柳田国男的思想资源(19)柳田曾在《民间传承论》中指出,应将事物本身作为一种现象,实事求是地凝视它,洞察其被视为“已经了然于心的”“理所当然的”现象背后存在的真理。,“以‘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20)参见高丙中:《生活世界:民俗学的领域和学科位置》,《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解读〈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户晓辉:《民俗与生活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中理所当然的存在为对象,对其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拆解和分析,从而促使人们自省自身的行为”(21)引自岩本通弥在“中日民俗学前沿论坛:21世纪中日民俗学展望研讨会”(东南大学,2021年9月25日)上的发言。。
而岩本的日常研究的前提,在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拓展,也就是需将我们身边的种种文化现象(vernacular)都纳入考量的范畴。正如门田岳久在该教材的序言中所述:“本书的理念在于不仅将过去传承至今的‘民俗’作为研究对象,也将我们现在的日常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将民俗学视作一门既回溯过去、也思考当下的学问,可谓21世纪(日本)民俗学研究的重大范式转换。”(22)岩本通弥、門田岳久等:《民俗学の思考法―〈いま·ここ〉の日常と文化を捉える―》,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21年,第1页。
(二)“俗”与vernacular
同样旨在拓展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岛村恭则并没有如岩本通弥一般将vernacular与日常等同视之,而是将日常分为“自上而下的日常”和“vernacular的日常”两种,即将日常的一部分视作vernacular。例如,岛村指出,2020年5月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为防止新冠疫情扩散,提出了所谓“新型生活方式”。这种由国家倡导的正统的、普遍的日常生活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日常”,而人们自己摸索、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受到国家、媒体的影响,却又可能与之不同),便是民俗学所关注的“vernacular维度的日常”。(23)岩本通弥、門田岳久等:《民俗学の思考法―〈いま·ここ〉の日常と文化を捉える―》,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21年,第20—21页。
同时,岛村还将vernacular的概念与其近年倡导的“俗”的概念统一起来。
具体而言,首先在2018年,岛村恭则于《社会变动、“生世界”与民俗》(24)[日]岛村恭则:《社会变动、“生世界”与民俗》,王京译,《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借鉴美国民俗学者普里米亚诺的vernacular宗教理论(25)彭牧在《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中曾介绍了普里米亚诺的理论,在该文中,彭牧将普里米亚诺提出的“vernacular religion”译为“通俗宗教”,用以突出vernacular中微观的、个人的、日常的、琐碎不起眼的含义。中对vernacular的阐述和日本社会学者提出的“生世界”概念等既有研究成果,将vernacular定义为“产生并存在于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的经验、知识、表现”(26)[日]岛村恭则:《社会变动、“生世界”与民俗》,王京译,《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并将“民俗”与“vernacular”、将“民俗学”与“vernacular studies”等同起来。因为在岛村看来,提起民俗学(folklore),人们往往认为它是一门研究农村、山村、渔村自古流传下来的民间传承的学问,而没有folklore的传统遗留物印记的vernacular,与日本民俗学当下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研究更加契合。
然而,日语中的“民俗学”一词与volkskunde和folklore的对应(27)[日]岛村恭则:《“民俗学”是什么》,梁青译,《文化遗产》2017年第1期。,以及“民俗”一词与folklore的对应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将“民俗”转而与vernacular关联会引发与既有概念之间的冲突,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对此,岛村在其新著《大家的民俗学——“俗(vernacular)”是什么》中,修改了其对vernacular的定义。他将“vernacular”与民俗中的“俗”字对应起来,并如此定义:所谓“俗”,包含下述四重含义中的某一个,或是它们的任意组合。这四重含义分别是:(1)与支配性权力相左的事物;(2)无法完全用启蒙主义之理性来解释的事物;(3)与普遍、主流、中心的立场相悖的事物;(4)与正式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事物。(28)島村恭則:《みんなの民俗学―ヴァナキュラーってなんだ?―》,平凡社,2020年,第30-31页。
岛村认为,“俗”首先是研究对象(作为方法的“俗[vernacular]”将在下文中讨论)。在书中,他向读者展示出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丰富而有趣的民俗学研究对象,比如家庭内部约定俗成的习惯、校园怪谈、咖啡店的优惠早餐、职场里的默会知识、生活中的动漫角色等等,而这些,都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有别于官方规则、教育体制等权威性事物的vernacular。
(三)物质文化与vernacular
与岩本通弥、岛村恭则的民俗学整体研究不同,加藤幸治的研究偏重于物质文化。他师从民具学大师岩井宏实,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
在日本第二代学院派学者执掌学界、开展学科建设的时期,历史民俗学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标准”,研究内容偏重于民俗事象和社会传承。如第三代领军人物菅丰所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乍一看盛况空前,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民俗学学术空洞化的时期。标榜历史民俗学的一派学者,手握学界霸权,使得日本民俗学研究不断窄化,而那些与之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学者,则以自己的研究对象、类别为主题,重新组建学术组织。1972年日本生活学会成立,1975年日本民具学会成立,1977年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立,1984年民俗艺能学会成立,暴露出在被历史民俗学派实际掌控的日本民俗学会中,难以将民具、口承文艺、艺能等领域囊括进来开展综合研究的事实。”(29)菅豊:《民俗学の悲劇ーアカデミック民俗学の世界史的展望からー》,《東洋文化》第93号,2012年。
加藤幸治的vernacular研究,有将物质文化研究重新导入日本民俗学研究,以丰富研究对象的倾向。他认为,vernacular是某个社会里固有的生活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实践,这种生活实践依存于生活语境,具有匿名性、经验主义的特征,内嵌于以默会知识为背景的日常之中。(30)加藤幸治:《民俗学 ヴァナキュラー編》,武蔵野美術大学出版局,2021年,第23页。加藤还通过“便携式燃气炉”这一物品对vernacular的定义进行了阐释。便携式燃气炉虽是岩谷公司的一个发明,却基于生活文化,共享火锅美食的生活文化是民众智慧的结晶(匿名性)。而且,利用燃气炉等工具烹饪美食是依据经验进行的(经验主义),火候的掌控与烹饪的过程无法言说(默会知识),而通过分餐的方式实现平等用餐的做法又与饮食文化(生活实践)紧密相连。(31)加藤幸治:《民俗学 ヴァナキュラー編》,武蔵野美術大学出版局,2021年,第23-24页。
加藤对于物质文化的关注,与美国民俗学者亨利·格拉西不乏相似之处。事实上,美国民俗学的vernacular研究是在与vernacular architecture(乡土建筑)(32)西方对vernacular建筑的关注发轫于19世纪末,起初vernacular建筑表示的是“劣等的、低俗的、缺乏专业性、科学性的”建筑,但之后随着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的持续发酵和工业化时代人们怀旧情绪的蔓延滋长,vernacular建筑的价值被重新评估。这些与宏大建筑、精英学者设计的建筑相对的建筑,因具备“朴素、日常、传统手工艺、典型地方性”等特征受到推崇,到了20世纪50年代,vernacular architecture(乡土建筑)一词成为建筑学领域广泛被使用的术语。研究的交融中萌发的,亨利·格拉西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格拉西的民俗学著作《美国东部物质民俗文化模式》(1968年)被誉为vernacular architecture研究的范本。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通过民居建筑对无名的人们的生活进行了整体把握,探究地方文化模式及传播方式。之后,在1975年的《弗吉尼亚中部民居》一书中,同样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他借助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将建造民居与语言习得进行类比(33)详见程梦稷:《民居的“语言”:亨利·格拉西〈弗吉尼亚中部民居〉评述》,《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归纳出弗吉尼亚民居中共通的“语法”——建造规则。更重要的是,他关注民居建筑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对民居建筑的研究,他重塑了当地的人口迁移、产业发展等历史,并指出民居建筑传统的变迁不仅受到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是弗吉尼亚人思想模式变化的结果。格拉西继承并发扬了包括民居建筑在内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对美国民俗学学院派偏重“语言”研究的传统模式提出质疑,强调对“民俗生活”(folklife),即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研究,而不仅仅限于口承艺术等俗民“知识”(lore)的研究,从而增加了研究的多样性。(34)参见[美]杰森·拜尔德·杰克逊、张丽君、李维屏:《美国民俗学领域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现状——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杰森·拜尔德·杰克逊访谈录》,《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类似的,加藤幸治也强调日本民俗学中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但比起建筑,他更关注农村的稻谷堆、棚田、小贩卖烧烤用的铁板、渔民堆放的装鱼的箱子等日常中的造型艺术。例如,农民将成熟了的稻子竖直堆放,晾晒风干。稻堆颇有造型感,乍一看有点像妖怪。调查之后加藤发现,这样的造型其实源于人们的日常经验。将刚收割完的水稻直立,其茎部留存的糖分会因为重力的原因汇聚到米粒处,而阳光的照射更增加了其甜度。不仅如此,人们堆放水稻的劳作是对农业机械化的一种反抗,他们在堆稻子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连带感,有些地区甚至将堆稻子发展成为一种庆祝活动,使其成为生活中富含创意的行为艺术。由此,加藤指出,相较于那些对民具、祭祀器物、乡土玩具等开展的传统民俗学物质文化研究而言,vernacular概念的导入,使物质文化研究更为关注包含当代在内的各个时代里各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行为,从而帮助人们发现日常风景中隐含的有趣的生活造型艺术。(35)加藤幸治:《民俗学 ヴァナキュラー編》,武蔵野美術大学出版局,2021年,第26-28页。
四、作为方法的vernacular
除研究对象的拓展之外,第三代学者认为日本民俗学一直以来只使用研究“传承”所需的历史分析法,难以应对崭新的研究对象,所以在进行vernacular的本土化建构的过程中,他们还试图凝练出作为方法的vernacular。这些学者分别选取了包括多重含义的vernacular的某个截面,与自身的研究相结合,发展出对抗性视角、个体化视角、以及地方视角的vernacular论。
(一)对抗性视角的vernacular
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民俗学的vernacular研究逐渐融入了批判性的视角,比如理查德·鲍曼、查尔斯·布瑞格斯等人的论述中用表示非正式、具体直接、局部的vernacular,对抗表示合理化、标准化、间接、广泛的cosmopolitan。(36)Richard Bauman, “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45, no.1 (January, 2008), pp.29-36; Charles L. Briggs, “Disciplining Folkloristic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45, no.1 (January, 2008), pp.91-105.
在此基础上,菅丰指出:vernacular一词中包含相对于“文字”而言的“口头”,相对于“普遍”而言的“土著”,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相对于“官方”而言的“非官方”,相对于“正式”而言的“非正式”,相对于“专业”而言的“业余”,相对于“多数”而言的“少数”,相对于“集团”而言的“个人”,相对于“工作”而言的“爱好”,相对于“优雅”而言的“鄙俗”等特征。(37)菅豊:《「ヴァナキュラー文化」研究の視座の構築》,Researchmap,https://researchmap.jp/Yutaka_Suga/,发表时间:不详;浏览时间:2021年6月23日。
对抗性视角的vernacular在岛村恭则的研究中尤为突出。如上文所述,岛村把“俗”定义为与支配性权力相左、无法完全用启蒙主义之理性来解释、与“普遍”“主流”“中心”的立场相背、与正式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事物。而且,岛村不仅把“俗”(vernacular)作为研究对象,还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即从“俗”的视角来研究“民”。也就是说,民俗学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接近日常生活,而是“将视角放在与作为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的社会位相不同的维度上,从而使以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的社会位相为基准形成的知识体系相对化,并创造出超越这一知识体系的知识”(38)島村恭則:《民俗学を生きる―ヴァナキュラー研究への道―》,晃洋書房,2020年,第18页。。
具体而言,岛村首先列举了家庭内部的“俗”,如妈妈为了吓唬孩子编出的妖怪;午后第一次穿新鞋出门需要把鞋底弄脏的习惯等,并从“俗”(vernacular)的视角加以阐释:“学校教育是重视启蒙主义之理性的教育,家庭教育也存在类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上述事例表明,从‘家规’的角度看,家庭教育又承担着反启蒙主义,即用‘俗’(vernacular)进行教育的功能。”(39)島村恭則:《みんなの民俗学―ヴァナキュラーってなんだ?―》,平凡社,2020年,第44页。
再如,在日本存在这样一种早餐之“俗”——人们不在自己家中,而是在附近的咖啡店品尝“优惠早餐”(40)指付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享用咖啡外加煮鸡蛋、吐司、色拉等的优惠服务。。岛村认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立场的人在咖啡店吃早餐,不只是单纯的用餐行为,还具有社会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意义。他将日本围绕优惠早餐形成的公共圈称为“习俗性(vernacular)公共圈”,与欧洲咖啡馆的“市民性公共圈”,即启蒙主义性质的公共圈进行了对比。“在早餐外食的习俗中,人们的言行包含了很多启蒙主义之理性无法解释的要素。这里不要求人们的交流具备理性、逻辑性,食客也无须是社会、经济、精神上独立的欧式‘市民’。……这是一种与‘市民性公共圈’不同的‘非启蒙主义性质的公共圈’,也就是所谓‘习俗性(vernacular)公共圈’。”(41)島村恭則:《みんなの民俗学―ヴァナキュラーってなんだ?―》,平凡社,2020年,第162-163页。
如此,岛村开展了自成一体的内含对抗性视角的vernacular研究。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俗”(vernacular),并非在本质上微不足道,而是被刻意划分成了与“重要”相对的“微不足道”的一方。所以岛村所要做的,便是从vernacular的视角批判将这些事象变得微不足道的霸权。(42)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Jesse A. Fivecoate, Kristina Downs and Meredith A.E.McGriff, Advancing Folkloris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59-61.
(二)个体化视角的vernacular
针对民俗学中“民”的问题,各国学者都有过探讨。日本民俗学中的“民”曾被定义为民俗的传承人,基层文化的承载者。然而新一代学者试图摆脱历史民俗学的枷锁,他们有时甚至舍弃“常民”等带有“民”字的词汇,转而使用“普通的人们”的表述方式。
反观中国民俗学界,高丙中、户晓辉等提出了“民”之从“民间”到“人民”再到“公民”的转换,倡导进入公民表述的范畴。(43)详见高丙中:《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我们未必可以将“普通的人们”与“公民”的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却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即希望在民俗学研究中关照到更多的个体、平等对待在现实中可能遭遇种种不公的个体、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权利,而这与强调个体化视角的vernacular的方法论有着共同的指向。
小长谷英代在梳理vernacular与民俗学的关系时曾指出,英国和德国的语文学研究,从vernacular中选取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内容,重新用folklore这一术语加以概括,逐渐构建起民俗学的学术体系。folklore是纯粹的,而vernacular是被从folklore的定义中排除的鱼龙混杂的异质物。(44)小長谷英代:《「ヴァナキュラー」―民俗学の超領域の視点―》,《日本民俗学》第285号,2016年。在当代日本民俗学者看来,曾被民俗学(folklore)研究忽略、排挤、压制的vernacular,不仅比folklore的内涵更广,而且拥有关注到更多个体的可能性。vernacular要求我们在进行实际研究时进一步加强自反性,更加彻底地反思自身在研究中的定位及研究的局限性,更加深入地探究看似“平等”的生活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不平等”,质疑所谓的理所当然,将目光朝向更多“缄默的人群”。
作为日本民俗学第三代领军人物之一的菅丰,长期从事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的研究,在其倡导的“新在野之学”理论中,菅丰强调多元行为主体之间平等的协同合作关系。而多元行为主体中,以民俗文化传承人为核心的当地民众具有最强的正当性,学者在与当地民众对话时需将自己放在比对方略低的位置上才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平等,并需在介入性日常实践的过程中切实以实现当地民众的幸福为己任。(45)详见陆薇薇:《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
之后,在对隅田川(46)隅田川是位于东京都北区的一条著名的河流。的“无声的暴力”进行个案研究时,菅丰开始从public视角转向了vernacular视角。菅丰发现,如今风景怡人的隅田川河畔,十多年前曾是众多无家可归的人们(homeless)的寄身之所。河边时尚的长椅(中间被安上扶手,使人无法平躺)、前卫的凉亭(顶部有很多缝隙,无法遮雨)、美丽的花坛(置放在桥下等区域,防止无家可归的人搭建临时住所)等等,都在悄无声息地“排挤”着那些无家可归之人。同时,菅丰指出,与数十年前不同的是,现今与隅田川相关的诸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都强调市民的参与,“排挤”的行为乃是官民协作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偷换概念,将“整治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隅田川的问题”转变为“打造河畔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问题”,隐藏起排挤的意图,防止出现多种声音针锋相对的格局,使弱势群体无法发声。(47)菅豊:《見えない「戦闘地帯(Kampfzone)」―都市の社会的弱者の静かなる排除―》,大場茂明等編:《文化接触のコンテクストとコンフリクトー環境·生活圏·都市―》,清文堂,2018年,第83-116页。如此,菅丰在公共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对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中的civil、public展开质疑,对伴随着民主和平等出现的“市民”“公共”的概念中实际究竟包含了谁、又排挤了谁进行反思,从而关照到更多被边缘化的个体,即vernacular的个体。菅丰的这一个案研究,可谓基于个体化的vernacular视角的尝试,之后,他又结合艺术领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视角。
菅丰将vernacular艺术定义为“并不自许为‘艺术家’的普通人受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所驱使而做成的艺术;是在那原本与正统艺术世界的制度、权力或权威无涉的世界里,自学习得艺术技能与知识的人们苦心巧思而成的艺术”,并指出,“在不理解这些艺术的人眼里,它们往往会显得朴素、土气、粗鄙、恶俗、乡气、不成熟、不美观,会被认作没有价值的艺术遭到轻视,也或许无法得到正统艺术世界的认可。然而,它们是呈现在普通人生活现场与路上的艺术,有时亦是支撑人生、充实生活的艺术,是寻回新生、填补生命的艺术”(48)[日]菅丰:《民俗学艺术论题的转向——从民间艺术到支撑人之“生”的艺术(vernacular艺术)》,雷婷译,《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
在关于艺术民俗学的论述中,张士闪曾指出:“艺术民俗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生命个体在艺术发生的民间现场所体现出的生存智慧与自我生成,这种生命个体的主体性构成了艺术民俗学中连接‘艺术’与‘民俗’的纽带。”(49)张士闪:《眼光向下: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的考察》,《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菅丰的vernacular艺术论与之不乏相似之处,即关注艺术发生现场的非均质性,突出众多“无名”的个体在日常艺术实践中展现的“生存智慧”。在此基础上,菅丰希望通过vernacular这一概念,把握更多被传统概念忽略的个体,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个体化的“人之生”的真实状态。
(三)地方视角的vernacular
门田岳久师从岩本通弥,是日本新生代学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位,主要从事民俗宗教的研究。虽然门田在其研究中援引了普里米亚诺对于vernacular宗教的阐释——vernacular宗教是人们亲身体验的宗教,即人们遇见、理解、阐释、实践的宗教(50)Leonard Norman Primiano, “Vernacular 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Method in Religious Folklife”, Western Folklore, vol.54, no.1(January, 1995), p.44.,关注到个体在宗教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但他同时强调了个人宗教实践中“地方”的意义,即重回vernacular一词原初的含义——本土、土著、地方,透过内含地方视角的vernacular对个案进行了考察。
门田岳久的田野调查地是冲绳的一个充满“灵性”(spirituality)的岛屿——久高岛,传说那里是琉球神话中创世神的降临之所,至今仍传承着大量的神灵祭祀活动。通过对前来久高岛灵修的人们的采访,门田发现,来访者不乏共通的特征:他们既不是普通的观光客,也没有遵循当地的宗教传统参拜圣地。他们对久高岛以及岛上的“齐场御岳”(51)齐场御岳为冲绳第一灵场。御岳(utaki)是琉球神话中神存在的地方,既是接待来访神的场所,也是祭祀祖先神的场所,可谓地域祭祀的中心所在。有极高的认可,并把这些场所与自身的灵力体验结合起来加以叙述。(52)門田岳久:《ヴァナキュラー·スピリチュアリティ―沖縄における聖地経験と〈地域〉のあいだ―》,長谷千代子等編:《宗教性の人類学ー近代の果てに、人は何を願うのか―》,法蔵館,2021年,第336页。
灵力、灵场一类的表述与久高岛传统地方信仰有着不同的脉络,主要是大众媒体宣传的结果。为灵修而来的访客,或多或少受到了媒体的影响,但在获取灵力的过程中,他们各有各的体验(尤其是身体方面的感受),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灵性修行叙事。与此同时,这些个体叙事又与“地方”(久高岛)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在“圣地”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灵修的过程中不断贴近当地人以及地方的传统信仰。例如,某位访客感到目眩和头痛,便向岛上人请教,岛民问他上岛和拜访“齐场御岳”前,有没有在心中向神灵请示说“对不起,打扰了”(如同去别人家拜访一样)。岛民的这一询问,其实暗含着久高岛的宗教传统。久高岛神女众多,她们在进入圣域前,都需要在心中默默向神请示。门田指出,岛民以这种方式向前来灵修的访客传达出当地的世界观,令访客真实感受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神灵的关注,从而使得访客的个体经验与地方的宗教传统有机结合起来。(53)門田岳久:《ヴァナキュラー·スピリチュアリティ―沖縄における聖地経験と〈地域〉のあいだ―》,長谷千代子等編:《宗教性の人類学ー近代の果てに、人は何を願うのか―》,法蔵館,2021年,第340-341页。
更有甚者,在灵修的过程中,逐渐被当地的传统信仰深深吸引,从而想要移居岛上。然而,久高岛的土地为岛民共有,想要移居岛上,必须获得岛民们的认可。于是,访客不断学习当地祭祀仪式、宗教信仰的相关内容,努力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最终得以在岛上从事照护工作。由于能够体谅岛上老人们对于祭祀仪式的眷恋,所以在照料老人的过程中,她融入了与灵性相关的内容。门田认为,这位访客移居岛上的过程,是其逐渐将自身对灵性事物(受媒体影响的世俗化宗教)的关注与根植于地方的宗教传统相融合的过程。不仅如此,这些灵修的访客不同于单纯消费当地观光资源的普通观光客,他们积极融入地方社会,并对地方宗教传统进行创造性地再生产,这在地方社会空心化现象日益严峻的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54)門田岳久:《ヴァナキュラー·スピリチュアリティ―沖縄における聖地経験と〈地域〉のあいだ―》,長谷千代子等編《宗教性の人類学ー近代の果てに、人は何を願うのか―》,法蔵館,2021年,第344-346页。
如此,在门田的vernacular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双重维度——注重个体创造性的vernacular和注重地方特色的vernacular的有机统一。换言之,门田试图在个体与地方,即vernacular被拓展的含义和原初的含义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探索vernacular阐释的新路径。
五、结 语
如上所述,vernacular一词目前已是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共通术语,但究其根源,不难看出其与萌芽期的民俗学颇有关联。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逐渐确立,vernacular曾一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却又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重新回归学术世界。
当代日本民俗学对vernacular的援引和阐发,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民俗学学术潮流的外在影响和自身内在的转向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民俗学界对于vernacular的理论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重视语言传统的vernacular语文学论(鲍曼)和重视民俗生活整体的vernacular生活论(格拉西、普里米亚诺等),日本民俗学依据自身发展需求对后者更为关注。
vernacular一词的词义较为复杂,涉及的内容较广,日本学界在进行vernacular的本土化建构时,尤为关注其中的“日常生活”“对抗性”“个体的创造性”“地方性”等内涵。这与其日常生活研究、公共民俗学研究、对抗霸权的民俗学研究等研究趋向密切相关,旨在摆脱folklore研究对“传统”的过分执着,拓展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使当下新生成的文化现象也能被纳入考量的范畴,并凝练出作为方法的vernacular。目前,日本学者通过教材编写、个案研究等方式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然而,日本的vernacular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够充分的地方。例如,虽然“vernacular相较其他术语而言,不太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55)Richard Bauman, “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45, no.1(January, 2008), p.32.,但vernacular这一概念中同样也存在权力压迫的问题。在历史上,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地方口语(vernacular)曾出现过价值转换,德语、法语等一些本为vernacular的语言,颠覆了与拉丁语二元对立中弱势一方的身份,成为拥有支配地位的“母语”。但在此过程中,作为母语的vernacular又“压制了国内其他方言等作为少数派土著语言的vernacular”(56)小長谷英代:《「ヴァナキュラー」―民俗学の超領域の視点―》,《日本民俗学》第285号,2016年。此外,在胡适的论述中也有vernacular时而对应“白话”,时而对应“方言”的矛盾。。所以,对于vernacular中隐含的权力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深入且自反地加以思考。
此外,与日本民俗学不同,中国民俗学在诞生之初便与vernacular密切相关。胡适将白话文(vernacular)视作欧洲的地方性口语,用以对抗相当于拉丁语的文言文,虽然其观点中不乏对vernacular的误读之处,却也促成了vernacular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57)详见商伟:《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读书》2016年第11、12期。所以当我们与日本及欧美民俗学者就这一前沿问题开展对话时,需要重返中国民俗学的起点,重审白话文运动与中国民俗学生成的关联(58)参见卢毅:《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探讨vernacular在中国语境中的拓展及意义,构建属于中国民俗学的vernacular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