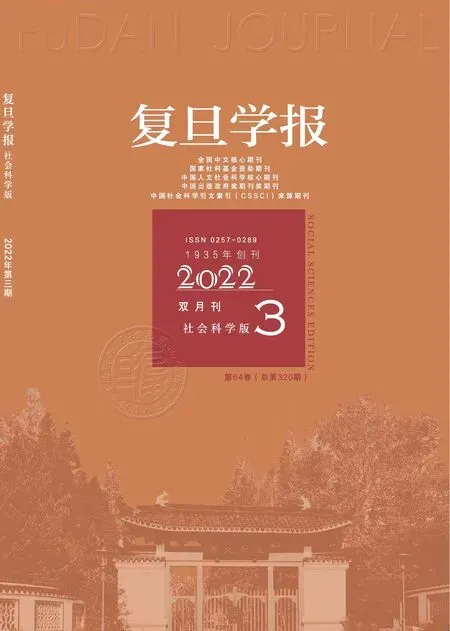从文本理解看释义学的实践意义
张汝伦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在当代世界,很少人再像古典释义学那样,把释义学理解为狭义的文本解释理论,讨论的是不能把《红楼梦》理解为《牡丹亭》;或者《红楼梦》究竟说的是什么;如何保证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是客观的、正确的、唯一的,就像自然科学的知识那样;或者如何来把握作者的原意等等。今天人们普遍认为,释义学是一切学术研究活动的核心,它的问题早已不只是狭隘的如何研究一个文本,而是关系到人存在的一切最根本问题:什么是人文意义?如何理解他者?文本解释是怎么回事?如何解释最好?理解话语究竟怎样?理解艺术又是如何?如何促进跨文化与跨时代的理解?等等。人们认为,这才是释义学深刻而本原的意义。(1)Cf.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 eds. Michael N. Forster, and Kristin Gjesd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
其实,即便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介绍西方释义学著作时,也已经清楚地阐明,释义学有古典释义学和现代的哲学释义学之分。在当代世界有压倒性影响的是哲学释义学,而不是日渐式微的古典释义学。(2)张汝伦:《意义的探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殷鼎:《理解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这些哲学释义学奠基者的相关著作陆续被翻译出版,似乎也表明我国学者主要对哲学释义学情有独钟。然而,吊诡的是,有兴趣不等于能理解。我国研究者往往是以古典释义学的模式来理解哲学释义学的话语,而对哲学释义学的革命性却麻木不仁。具体表现为,基本上还是把释义学的理解与阐释视为一个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活动,关心与讨论的问题往往集中在如何克服理解的主观性和任意性,达到解释的客观性,等等;而完全没有理解被人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现代释义学真正的革命性意义;(3)Cf. Gerald L. Bruns, Hermeneutics Ancient & Modern (New He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没有理解,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一再强调的:对于释义学来说,理解与解释一方面是人与他人及事物建立联系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它涉及的是与他人、世界和历史的一种基本的实践样式。严格说,释义学活动是实践活动,而不是认知活动或理论活动。本文以利科的文本理论以及伽达默尔的相关思想为例,来说明释义学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性质。
(一)
众所周知,利科是当代西方哲学释义学继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之后的又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于哲学释义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首推他的解释理论,而文本理论则是其解释理论的核心和基石。
对文本的重视并非只有释义学,20世纪的语言学、符号学、诗学、神话学、文学理论等人文学科,都重视对文本的研究。人们以为,文本是主体间交流的一个特殊媒介,是一个无时间的结构。当我们研究文本时,我们与之处于一种类似对话的共时关系。但在利科看来,却不是这样。文本是交流中一种间距的范式,它恰恰显示了人类存在历史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交流总是在间距中并且通过间距进行的,人类存在的历史性是无法消除的。(4)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d. & trans.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1.
利科的文本概念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与结构语言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主要归结为如下五个命题:1.语言总是实现为话语(discourse);2.而话语又实现为一个有结构的作品;3.在话语和话语作品中言与写关系在一起;4.话语作品投射了一个世界;5.话语作品是自我理解的中介。(5)Ibid., p. 132.
话语是说出和写下的语言,是语言的实现,就此而言,它是一个“事件”,它是在时间中实现和出现的。但是,话语作为文本,必然是有意义的。通过进入阅读者的理解过程,它超越了自己的时间性,而成为了意义。我们阅读一个文本,首先追求的是其意义,而不是它的时间性或事件性。我们不是把它视为一个事件,而是视为意义。“意义超越事件是文本本身的特征。”(6)Ibid., p. 134.文本总有一定的文体,文体是生产性的,它通过其特殊性促进一个特殊的观点或立场。因此,文本的作者非一般的说话者可比,“作者比说者说得更多:作者是一个语言作品的工匠。他与作为整体的作品的意义是同时代的,在此意义上,作者的范畴同样也是一个阐释的范畴”。(7)Ibid., p. 138.
然而,文本与直接言说不一样,由于通过书写被固定了下来,它面对无数后来的读者;另一方面,它的意义也必然会超出最初作者意象的视域,“文本的‘世界’可以突破作者的世界”。(8)Ibid., p. 139.这意味着后来的读者理解它时可以去除当初的语境(decontextualise),同时又通过他们的理解和阐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此文本重新置于一个语境中(recontextualise)。这样,历史间距不再是影响我们理解文本意义的障碍,也不是只有消极的与文本保持距离以保证客观性的方法论意义;它对于文本具有建设性意义。它不是消极的、必须加以克服的理解的障碍,相反,“它是阐释的条件”。(9)Ibid., p. 140.
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模式会把解读者与其文本的关系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解读者是主体,文本是客体,解读者应该尽可能地克服自己的主观性以客观把握文本的意义。而文本的意义就是原始作者所意向的意思。因此,解读者与文本的时间间距既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消极面是它妨碍解读者完全进入作者的世界,比如说,现代世界的读者是很难完全进入《中庸》作者的世界的。正因为如此,时间间距也可使解读者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确保其读解的中立和客观性。但是,客观性的标准为何?是作者的原意吗?我们如何起作者于地下来问他或他们的原意是什么?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不涉及作者和解读者的主体性的解释(explanation)?狄尔泰的释义学已经指出,这对于解读经典来说根本不可能,遂提出“理解”(Verstehen)概念来应对。因为在解读人文作品时,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解读者与作者的主观性,因为理解人文作品就是把握通过作品表达的一个异己的生命。
可是实际上,“文本使得读者与作者都黯然失色”。(10)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 147.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文本不像当下的对话,它没有后者那种不可避免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因素,写-读关系不是问-答关系的一个特例。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曾把理解描述为以问答逻辑为本质的对话(11)Cf.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J.C.B. Mohr, 1986) SS. 375-384.,利科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说阅读是通过其著作与作者对话是不够的,因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对话。对话是问答的交换,而作者与读者之间没有这样的交换。作者并不回答读者,文本把书写行为与阅读行为分为两边,彼此之间没有交流。(12)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 146.
不仅如此,文本使得其所指不再是作者的主观意思,而是客观的意义。话语主体总是就某事说某些话。他所说的主题就是他话语的所指(referent)。然而,文本将对话者及其对话的处境、条件、环境和氛围都悬置了起来,连带对话者话语的所指也被悬置了起来。现在,不再是说话者决定所指,而是文本决定所指也决定作者。人们根据《中庸》的文体差异对其作者提出质疑或认定,就是一个例子。
西方文学批评和《圣经》批评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主要关注作品的内容,或文化文献的内容,关注这些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或者它们指向的共同体。解释一个文本本质上就是认为它表达了某些社会-文化需要,回应了某些时空中的困惑。(13)Ibid., p. 184.这种历史主义的思路,直到今天还是我们解释历史文献和作品的基本思路。但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哲学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成果,此成果可称为“意义的发现”。它肇端于弗雷格哲学和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这两位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发现,意义(他们感兴趣的还只是命题的意义,而非文本的意义)不是人头脑中的观念;它不是某种内心的内容,而是可以为不同时期的不同个人一再认定为是同一个对象的理念性对象。他们把命题的意义理解为“理念性”(ideality),它既不是一种物理的实在,也不是一种内心的实在。用弗雷格的话说,Sinn(意义)不是Vorstellung(表象),即它不是某种情况下某个特定的言说者实现意义的内心事件。意义构成命题观念的维度。同样,胡塞尔把一切意向行动的内容描述为“意向相关”(noematic)对象。胡塞尔把弗雷格的理念性意义的概念扩大到一切精神活动——不只是逻辑行为,而且还有知觉行为、意志行为、情感行为,等等。(14)Ibid.这对于狄尔泰的释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5)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51页。1900年后,狄尔泰极力把他在胡塞尔《逻辑研究》中发现的理念性(Ideality)结合进他自己的意义理论中。理解不是要把握作者的原意,而是把握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精神。
与此同时,在心理主义和社会学至上(sociologism)思潮过度泛滥后,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相似的变化。人们同样把文本视为某种无时间性的对象,书写就意味悬置历史过程,从话语进入到观念的领域,这个领域可以被后代无数可能的读者无限扩大。意义的客观化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必要的中介,(16)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 185.在意义这个平台上,作者可以是读者的同时代人,反之亦然。
这意味着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解读者进入了文本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只属于作者,而是读者与作者共有的世界。与一般的言说不同,文本的意义不是指向某个特殊事物,而是揭示了一个世界。当我们说《红楼梦》的世界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世界时,就部分说明了这一点。话语的所指是正在说的事情,是可以用直接指称的方式来确定的。但用文字书写成的文本,却无法用直接指称的方式来确定它的所指。随着书写,事物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不再有作为对话者的作者与读者共有的处境,指称行为的具体条件也不再存在。不管《中庸》的作者是生活在先秦还是秦汉,他们的处境不是我们的处境。由于意义的自在性,他们言说的处境不能决定意义的所指。“这样,我们说到希腊的‘世界’时,不再是指任何当初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种种处境,而是非处境性的所指,它们比当初的希腊人活得更久,此后就呈现为存在种种可能的模式,我们在世存在种种象征的维度。”(17)Ibid., p. 202.
换言之,文本的指称不再是直接指称(ostensive reference),不再是像日常话语的指称那样的一级指称;直接指称的取消为二级指称的解放创造了条件。而文本的指称之所以是二级指称,不仅是因为它的意义不是精神性的意向,更是因为文本使得实在在其中变了形。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讨论其游戏理论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变形”(Verwandlung)概念。“变形是事物一下子整个变成了另一个东西,这样,这另一个东西作为变了形的东西,就是该物真正的存在,相对于它来说,该物以前的存在是无意义的。”(18)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S. 116.变形就是一物以另一种存在方式存在,而不是完全消失。例如,希腊神话中宙斯变成天鹅,并非宙斯不再存在,而是它以天鹅的存在方式存在。
如果文本解释也可以视为一种游戏或一种艺术的话,那么这种游戏也是向创造物的变形(Verwandlung ins Gebilde)。这里变形的是实在本身。当我们在解读文本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封闭于自身的世界”,即文本的世界。换言之,日常世界变形为文本的世界,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实在’总是处于一个既令人期待又令人担心、却无论如何是未定的可能性之未来境域中”。(19)Ibid., S. 118.与文学文本的情况一样,在哲学文本中,实在并非不存在,而是变了形。所以它的指称是二级指称,二级指称达到的不是可操控的事物层面的世界,而是胡塞尔讲的“生活世界”或海德格尔的“在世的存在”。“阐释就是阐明面对文本展开的那种类型的在世存在。”(20)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 141.而这些二级指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打开了我们在世存在种种新的维度。(21)Ibid., p. 202.例如,《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哲学论》这样的著作,其所指也不是日常实在,而是一个变了形的可能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以实在论的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去理解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寓言不仅仅是胶柱鼓瑟,而且是把哲学文本误读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了。
(二)
按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理解理论,理解并不是要理解一个异己的他人,而是理解我们生存的结构。理解是在生存处境中投开(entwerfen)我们最本己的可能性。利科将海德格尔这个思想纳入他的解释理论,提出:“在文本中必须阐释的是一个我们所要的、我能在其中居住,并投开我最本己的可能性的世界。”(22)Ibid., p. 142.这样,文本的世界就不是一个日常语言的世界。文学、诗歌、神话、民间故事的文本是这样,哲学文本更是这样。这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新的间距,利科把它称为“实在与它自己的间距”。(23)Ibid.利科说,各种叙事、民间故事和诗歌不是没有所指,但它们的所指与日常语言是断裂的。通过虚构和诗歌,新的在世存在的可能性就在日常实在中被打开了。(24)Ibid.
哲学著作当然不是像文学作品那样的虚构,但它与日常语言的断裂比起文学作品丝毫也不逊色。它们的所指同样也是“新的在世存在的可能性”,阐释就是要揭示文本所包含的这种可能性。文本的世界就是理解所投开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流俗实在论意义上的世界,而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示的那个生存论意义上的“世界”。(25)Cf.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S. 63-66.船山在比较《庄子》内、外篇时说:“内篇虽参差旁引,而意皆连属;外篇则踳驳而不续。内篇虽洋溢无方,而指归则约;外篇则言穷而意尽,徒为繁说而神理不挚。内篇虽极意形容,而自说自扫,无所粘滞;外篇则固执粗说,能死不能活。”(26)王夫之:《庄子解》,《船山全书》第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1996年,第184页。《庄子》内外篇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就是因为内篇的指称是利科所谓的“二级指称”,一个超越日常语言的指称和常识思维的可能性世界,所以它“洋溢无方,而指归则约”;而外篇的指称还停留在日常语言的常识实在世界,它必然“言穷而意尽,徒为繁说而神理不挚”。
文本提出可能性的世界,而读者则通过自己的理解占用这个世界。因此,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实际上是与文本世界的关系。(27)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 182.这种关系不是近代认识论设想的主客体的关系,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从属关系,读者属于这个首先通过他的阐释揭示出来的可能性世界。理解文本不是理解作者的原意(释义学早已揭示那根本不可能),而是理解客观化的意义。正是客观化的意义消除了作者与读者的时间间距,通过对意义的挪用(Aneignung),读者与作者成为同时代人。“挪用”原来的意思是指“使最初异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利科从德语中借来这个词,使之成为他自己解释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当前的读者通过阐释实现文本的意义。(28)Ibid., p. 185.显然,这种“实现”不可能是一种认识行为,而只能是一种实践。
对文本的解释不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关系,而是通过理解达到对文本所揭示的自己的可能世界的把握。这种把握不是知识论理论意义上的认识,而是生存论实践意义上的挪用。这种挪用,不是具体应用某个理论,而是将文本世界作为自己规划的世界。通过此一挪用,读者与文本的时间间距被克服了。哲学著作,尤其是哲学经典,之所以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就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性世界。
然而,要挪用这个世界,解读者也必须首先失去自己。理解和阐释不是把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加于文本,而是将自己暴露在文本之前,从它那里接受一个扩大了的自我。对文本世界的领悟使我们进入了那个可能的世界,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视域。文本的世界不是藏在文本背后的一个主观意向,而是文本展开、发现、揭示的东西。理解完全不是建构一个主体已经掌握了的东西,而是主体被文本的问题(matter)所建构。(29)Cf.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p. 143~144.也就是说,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我们理解的不是一个异己自我的意向,而是我们自己存在的新的可能性,从而得到了丰富。挪用文本的世界就意味着扩大了自己的世界。被挪用的世界不再是异己的世界,而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
“挪用”这个概念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的误解,即读解者或阐释者通过主观的解读与阐释让文本为“我”所用。利科的文本理论可以很好地打消这种误解。他根据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提出文本不但使世界变形,也连带使解读主体变形。伽达默尔在论述他的游戏理论时强调指出:“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30)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S. 108.游戏者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才能进行游戏,只有游戏才是游戏的主体。只有完全服从游戏本身的规则,游戏者才能玩游戏。“玩游戏者也被玩:游戏规则把自己强加于游戏者,规定游戏的进行(the to and fro),限定游戏的领域。”(31)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 186.如果我们也能把文本解读视为一种游戏的话,那么在读解文本时,读解者也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且不说他要受文本的语义、结构、逻辑等等因素的制约,就连他自己作为解读者的角色,也是由文本构建的。(32)Ibid., p. 189.在解读哲学文本时,始终存在这样的问题:进入一个异己的文本,抛弃早先的“我”以接受由作品本身授予的自我。(33)Ibid., p. 190.
释义学的“挪用”概念不但不是一个笛卡尔、康德、胡塞尔作品中的那种主体主义的概念,而且更是对这种主体主义的克服。在利科看来,与主体相对的客观性和支配客观性的主体是同一个哲学错误的两端。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揭示了近代主体主义那个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一切的主体之虚妄。两位思想家都指出,主体实际上当不了他自己的家,他受制于许多隐秘的利益和无意识。利科的“挪用”概念即基于此种认识。挪用是放弃而不是占有,放弃是挪用的一个基本要素,挪用主要是一种“释放”(letting-go)。解读是挪用-剥夺,是让自己被带向文本的所指,以至于自我剥夺了自己。(34)Ibid., p. 191.
对于习惯了近代流行的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人来说,这种说法有点匪夷所思。但利科的意思无非是:解读就是让文本展现一个新的可能性世界的力量得以释放,而不是把主体已有的想法用文本的语言重述一遍,不是把异己的文本世界主体化,而是通过放弃自我的主体性进入异己的文本世界,来扩大自己的可能性世界,从而获得一个新的大我。这样才能达到古典释义学提出的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目标,即展开隐含在其话语中的揭示性力量。
挪用并不意味着读者与作者完全气味相投,而是伽达默尔讲的“视域融合”,即作者与读者的世界视域聚集在一起。在这样的视域融合中,作者与读者的主观性同时被克服了。作者与读者一样,并无决定文本意义的特权地位。利科利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成果来说明,文本同样消解了作者的主观性。(35)Cf.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p. 188-189.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在研究小说家与其人物的关系问题时,发现小说家与其作品有多种可能的关系:全知的作者;将自己等同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此人物等于是作者的代言人;完全取消作者,让故事自己来讲述自己,等等。但无论是何种可能,作者的自我并未完全消失,只是作者变形为各种不同的叙事者(narrator),即使作者的痕迹完全消失,也不过是作者玩的一种游戏而已。通过作者变形为叙事者,作者自身的人格(其主观性、历史性、特殊性,等等)被悬置起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他的人格和主观意图决定的,而是由文本与文本的解读共同决定的。莎士比亚决定不了《哈姆雷特》的意义,正如老聃决定不了《道德经》的意义一样。
此外,文本的意义并不只对作者及其同时代的读者开放,而是对世世代代的读者开放。在此意义上说,意义是全时性的(omni-temporality),它对未知的读者敞开自己,这也意味着它对一切可能的读者的历史性开放。这就使它的全时性不等于非时间性或无时间性,而是能包容所有可能读者的历史性。读者的历史性将通过他们的解读成为文本时间性的时现。(36)此处“时现”概念来自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Zeitigung(动词形式为zeitigen)一词指时间性自身的显现和时间性事物时间性地产生与实现,我将此概念译为“时现”(参看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页)。而这反过来也表明了文本本身的时间性。也因为文本此种全时的时间性,它并不仅仅属于某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可能的读者,哲学经典尤其如此。《中庸》并不只属于其产生的时代及其作者,而也属于今天的我们和未来的读者。
这种属于,绝不只是指我们和后来可能的读者可以读它,而且更在于我们从文本中得到的不是某个主体的主观意图,而是文本通过它的非直指指称所揭示的某种在世存在可能的模式,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说,某种或某些新的“生活方式”,它们给读者展现出一个新的可能的世界。这个可能的世界并不是出于读者自己的规划或设计,而是读者通过从文本本身接受某种新的存在模式扩大了自己规划自己的能力。(37)Cf.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 192.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但文本属于读者,读者更属于文本,读者从文本中获得了他新的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挪用不是“占有”,而是剥夺,即剥夺自己“自恋的自我”,(38)Ibid.从而获得自己新的存在可能。
解读文本不是一个主体(读者)单向作用于客体(文本)的主观操作,文本不是读者知识论的对象,解读文本也不是像地质学家分析其矿石那样的一种客观知识论行为,而是人最切己的存在方式,通过文本解读,读者扩大了他的存在可能性。“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39)程颢、程:《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1页。伊川此言也表明,经典文本的解读不是一种客观的知识活动,而首先是一种改变自身的存在行为。
(三)
如果文本解读不是主体单向作用于客体的主观操作,那么,它也就不能和不应该是实用主义的应用研究。实用主义的解读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为榜样,把文本视为提供了某种或某些理论,这种或这些理论可以立即加以应用。还有一种是把文本视为行动的指南,解读文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甚至是为了“制度设计”的方案。除了这两种主要模式外,还有更为鄙俗的以经典文本来曲证己意的做法,此种做法日益常见。但无论是哪种实用主义的解读模式,都是一种主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解读方式,解读者不想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扩大自己的存在境域,而只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文本的意义,从而剥夺了文本的揭示力量。文本不再揭示一个可能的世界,而只是读者达到其外在目的的工具。文本不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被无数其他文本替代的。实用主义的解读模式对文本实际是一种谋杀,同时也失去了文本解释的意义。
当然,这也绝不意味着文本解释是一种通常意义的纯粹的理论活动。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强调理解与解释不是主观的知性活动,而是人基本的生存论的实践模式。伽达默尔更是在《真理与方法》中特意把“应用”(Anwendung, Applikation)观定为与理解和解释一样的释义学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40)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S. 313.正是为了突出这一点。
“应用”这个概念是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概念。人们往往会望文生义,从寻常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此一概念,以为它的意思是要把普遍原则或普遍知识用于实际情况,就像科学家把科学原理付诸实际应用,或工匠将他拥有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付诸实践,如一个金匠将他关于黄金加工的知识和技能用于打造一件饰品。释义学的“应用”难道不是把所理解的文本用于现实生活?这难道不正好印证了释义学的实践哲学性质吗?这难道不正是作为实践哲学的释义学所要求的吗?
这样的理解是对伽达默尔的“应用”概念的莫大误解,可以说,上述这些对“应用”的理解,恰恰是他所要反对的。无论是应用科学知识还是应用技术知识,都是把一般原则不加区分地用于个别情况,并且这种应用一定是单向的,应用的受纳方对应用而言不起任何作用。即便在应用时要考虑到应用所受对象的特殊性,如一个骨科医生在治疗骨折时得考虑骨折的部位甚至病人的年龄等特殊情况,但相应的医学知识是确定的,不需要每次应用时都重新理解。但文本理解就不一样了,理解者总是不同的,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其历史性),因而“文本必定在任何时刻,即在任何具体处境中被重新和不同地理解”。(41)Ibid., S. 314.根据自己的处境来重新理解文本,这是伽达默尔“应用”概念的一个基本规定。
但这不是说,在理解和解释文本时,读者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和解释文本,读者得到的只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文本自身的意义。伽达默尔当然不可能主张这种极端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释义学。对于他来说,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也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文本流传万代,始终是同一个文本,例如,宋儒与我们相隔近千年,但《中庸》还是同一个《中庸》,读者却各不相同,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很显然,理解和解释文本决不像将某种知识和技能付诸应用那样,是一种三向关系,即知识或技能(普遍),应用者(主体)和被应用的对象(客体);而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双向关系。此外,在前一种情况中,知识和技能是固定不变的,即不会继续生长,也不依赖于人们对它们的应用。后者则不然。文本的意义不是结实固定的,而是有待充实的。在这方面,伽达默尔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者说实践哲学中得到了重要的启发。
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理智主义,明确指出,伦理知识或道德知识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理论知识,因为它是伦理领域的知识,伦理领域不像自然领域那样,受严格的自然规则支配,但又绝不是完全没有章法和规则的领域,而且它的规则是可变的。不仅如此,与自然规则相比,一般的伦理规范有点“虚”,就是说,它必须具体实现在一个实践处境中。“不知将自己应用于具体处境的一般(道德)知识,是无意义的。”(42)Ibid., S. 318.但这种“应用”与工匠对技术知识的应用有重要的不同。
对于工匠来说,技艺(Techne)本身是固定的,木匠加工木材的方法总是一样的。但道德知识则不同,智、仁、勇这样的德目何谓,行动之前并未完全确定,恰恰要通过一个人的实践行动它们才能得到明确。加工木材的技艺告诉每一个木匠怎么做,在此意义上,木匠可以说是被动的,他只能这么做,否则就无法达到其目的。但一个道德实践者则不同,勇的德目并未告诉一个人怎么行动才算勇,忍辱偷生和慷慨赴死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可以算是勇。不像加工木材的行为,勇的行动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定之规。道德意义上的“应用”并不是像技术意义上的应用一样,应用先已给予的明确的程序和规则。道德行为不是先知后行,而是知行合一。伦理规范不是可教的知识,它们只具有图式那种有效性。“它们总是首先将自身具体化在行动者的具体处境中。它们并不是某些还完全不能预料,或在某个伦理自然世界中有其不可改变位置的规范,以至于只需要去发现它们。但另一方面,它们也不是纯粹的约定,而是实际表现了事物的本性。”(43)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S. 326.这是说,伦理规定的确不是人为的约定,但它们却必然需要通过不同的人的不同实践来具体实现;而此实现也正是其生命之所在。
技术知识或技艺总是关于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技术知识总是已经预先知道了达到目的的有效方法,然后将其付诸实施。但道德知识不可能有这样先在性。固然它也有手段-目的的关系,但手段与目的都不是某种知识的单纯对象。手段不是被目的预先决定的,而是手段与目的相互影响的。例如,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好生活”,但什么是“好生活”却无法一劳永逸地决定。不同的人对“好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达到“好生活”也绝非一途。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达到“好生活”会影响“好生活”是什么。反之,我们如何理解“好生活”也会影响我们选择的手段。在此意义上,手段与目的都不像在技艺行为那样是先定的。
如果道德规范并不是像技术知识那样在行动之前先已掌握的,而需要我们通过行动来明确的话,那么在道德行为中,始终贯穿着理解。因为“这里不是关于某种一般知识,而是关于这一刻的具体情况。”(44)Ibid., S. 328.行动者永远要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理解道德规范的意义。“这里应用不是某个先已给予的普遍与特殊情况的关系。”(45)Ibid., S. 329.释义学的应用与此相似。文本的意义并未先行给予,否则就不必去理解和解释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始终得从自己的历史处境出发重新理解文本。因此,我们不可能像应用某种理论知识或技术知识那样把文本用于我们的特殊情况。相反,理解者或者读者只有把文本与他自己的历史处境联系起来,他才能真正理解文本的意义。这就是应用。
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会使人以为,文本的意义完全取决于理解者,否则就没有意义。这当然是误解。伽达默尔的意思只是说,意义取决于应用,或者说,意义只有在应用中才能具体化。只要文本存在,意义就不可能取决于读者的主观意向,就像它同样不可能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意向一样。伽达默尔用法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法学史家与法学家对待法律的态度是不同的。法学家是从当前的案件出发,为了当前的案件理解法律的意义。而法学史家没有他以之为出发点的当前的案件,他只想建设性地理解法律的全部应用范围来确定法律的意义,所以他关心的是公正对待法律的历史变迁。但法学家不仅要知道法律的历史应用与变迁,还得要使如此掌握的东西适当地用于现在。法学家固然要知道法律原本的意义,但是“法律的规范内容却必须根据应该应用它的当前的案例来定”。(46)Ibid., S. 332.
在伽达默尔看来,释义学的处境与法学家的处境是相似的,理解者并不直接面对文本的意义,而是“生活在一种直接的意义期待中。我们不可能直接接触历史对象,客观弄清它的重要意义”。(47)Ibid., SS. 332-333.文本当然是固定不变的,但文本的意义却并非如此,因为它一直流传到现在,并且永远流传下去,它的意义就像法律的意义一样,具体化在它与一个个的现实的关系中,或者说体现在应用中。我们当然必须根据文本所言来理解它,但文本由于与每个时代相联系而会有某种转化(Umsetzung)。文本与每个时代的联系,表现为释义学的应用。释义学的应用不是将普遍用于特殊,而是使意义在当下历史中具体化。“阐释的任务就是将法律具体化在每一个案例中,那就是应用的任务。”(48)Ibid., S. 335.
但是,应用始终要受到文本意义的制约,也是毫无疑问的。法学家不可能理解和解释的法律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就像经典文本的理解者和解释者所要理解和阐释的文本是一个客观存在一样,理解和解释不是无中生有地杜撰某些意义,而只是使意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化:“有待理解的意义只有在阐释中才能具体圆满,但阐释行动完全受制于文本的意义。无论是法学家还是神学家,都不认为应用的任务有与文本相悖的自由。”(49)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S. 338.可见,释义学的应用与实用主义的应用是不相容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释义学的应用与实用主义的应用不同在于,它并不是应用者主观性的证明;相反,它是对其主观性的限制。应用要求理解者与解释者通过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进入文本的意义世界,同时也因此丰富这个世界本身。应用其实就是一种沟通,我与你的沟通、古与今的沟通、可能与现实的沟通。“绝不会有这样的读者,当他面对文本时,只是简单地读那个文本。应用发生在一切阅读中,因此,谁读文本,本身就已身处所获得的意义中。他属于他理解的文本。”(50)Ibid., S. 345.史学家如果想要理解历史传统的话,他就要把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与这个传统打通。(51)Ibid., S. 346.应用不是将异己的东西纳入自己的世界,而是打通自己的世界与一个可能的世界,使自己融入那个世界。
伽达默尔始终坚持文本的不可超越性,坚持要在切合文本的意义范围内理解文本,并因此对19世纪的历史主义史学家们对待历史文本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历史主义的史学家将自己置身于文本之外,把文本视为他们可以从外部加以客观审视的对象。“他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理解为文本的接受者,并接受文本的要求。相反,他从文本追问文本本身不会提供的东西。”(52)Ibid., S. 341.史学家无视文本本身的意义,反而认为文本或传统完全可以用一种不是文本自身所要求的意义来解释。这至今仍是许多史学家对待文本的基本态度。他总是到文本及其表达的意思背后去追问它无意表达的现实。文本被视为与其他历史遗物一样的历史材料,不是按它们所言来理解和解释,而只是把它们理解为某个不是它们的事情的证据。史学家总是根据文本本身没有说出、文本意谓的意义方向上根本无需有的东西来解释。(53)Ibid., S. 342.以中国情况为例,同样如此。对于史学家来说,《尚书》或《春秋》只是某个时代的材料和证据,总是根据文本以外的东西来解释它们;倒是经学家始终坚持从文本自身的意义来理解文本。
尽管史学家对待文本采取的是像法官审问证人的态度,但毕竟他还得理解证据的意义。也就是说,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弃理解文本的意义。理解和解释文本(证据)的意义是判案的先决条件。就此而言,史学家也不能拒绝释义学的普遍性要求。也就是说,只要事关文本,史学家终究得面临文本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不过,哲学释义学不是将文本的理解与解释视为单纯的理智活动,而是一个通过我们的生存实践完成的活动。文本的意义对我们有实践要求,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将它完成。伽达默尔以理解命令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
命令可以被视为一个文本,所谓理解命令,就是知道它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重复命令来表示我们已然理解了该命令,但是,“其真实意义只是由‘根据其意义’具体执行来规定的”。(54)Ibid., S. 339.拒绝命令与执行命令都是对命令意义的确定,都是命令的意义在某人身上的实现。理解命令包括的不仅仅是简单地在理智上理解命令的意义,而是涉及接受命令者对具体情况的研判和他的责任。命令的意义包括所有这些实践要素,没有这些实践要素,命令的意义是不完整的。所以伽达默尔说:“命令的接受者必须创造性地理解意义。”(55)Ibid.显然,这种对意义的理解不是理论理性,而是实践理性的。它不是一种纯粹的认识(Wissen),而是一种实践的行为(Handeln)。命令的意义是通过执行或拒绝执行命令得到理解和完成的。
问题是,我们能否把如《中庸》这样的传世文本也理解为命令?初看起来,那样理解是荒谬的,经典文本并没有命令什么,它们只是要我们理解它们的意义。但如果我们不是把它们的意义理解为不依赖读者的理解与解释而恒久固定了的,而是通过读者的理解与解释不断得到完成,并揭示了一个可能的在世存在模式的话,那么文本就在双重意义上是命令。首先,它命令它的读者创造性地理解它,因为它没有固定不变、一劳永逸地完成了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在世存在,即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这是每一个文本解读者的释义学处境)来理解和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也就是打开自己存在新的可能性。文本的意义成为我们新的存在境域、新的存在世界,我们在此新的境域,向着新的可能世界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文本的意义。理解和解释首先是存在而非主观认知,文本的意义不是认知的对象,而是我们存在之趋向。
只有当我们不再像古典释义学那样狭义地把释义学理解成正确解读文本的方法,只有我们突破这样的习惯性思维,而真正理解释义学向我们揭示了存在的一种基本样式,释义学才能真正在我国哲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统一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