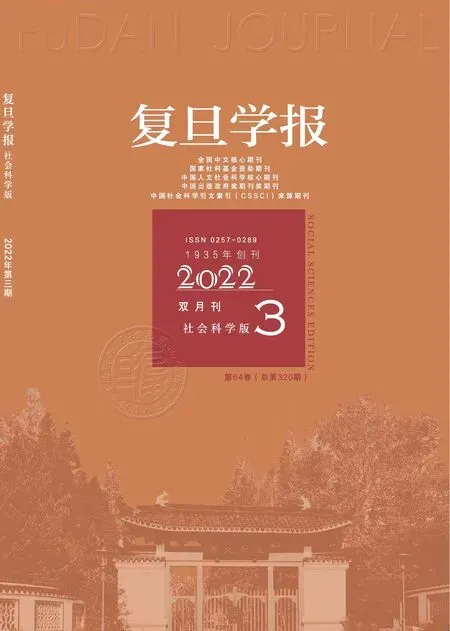丽藻彬彬:关于文学与历史哲学的思考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及历史学系,香港)
是什么推动诗人和史家去写作呢?作为“具有历史感的人”(homohistoricus),我们深感时光流逝、人生短促,于是有一种根本的冲动,想把生命当中值得留恋的、美好的甚或痛苦的记忆都保存下来。(1)关于“具有历史感的人”,可参见Christophe Charle, Homo historicus: 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les historiens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3).在我们这个数据化的时代,这一点也许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清楚,因为只要有一部电脑或智能手机,谁都可以把无数的照片和信息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去展示,在网络空间留下所谓“数据脚印”来满足那种基本的欲望,而这些“数据脚印”也像海滩上留下的脚印一样,很快就会被新一波上传的照片和信息之浪潮淹没而冲刷殆尽。这就是即时上传、但转瞬即逝的网络通讯与史家和诗人作品的区别: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或历史著作将永世长存,不会遭受时光的侵蚀而坠落遗忘的深渊,而社交媒体上那种虚拟的互动就其本性而言,便是即刻而短暂的,随时可以被取代。
一、 探求不朽之道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第18首中警告说:“一切的美终究都会失去美色,/或因偶然,或由自然的转变,”但诗人又骄傲地宣告说,诗文可以使美获得永生:
但你永恒的夏日不会消失,
你所有的美也不会消亡;
死神不可能吹嘘将你掳去,
永恒的诗句使你与时间共长。
只要还有人呼吸,人还有眼睛,
只要这诗还在,你就有永久的生命。(2)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18,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4) 1752.
人总会死去,但一旦写入诗中,那“永恒的诗句”便可以给人“永久的生命”而令其不朽。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表现这同一主题的诗作,而在下面这一首杜诗及其评论中,我们也看得见这一想法,这就是杜甫的一首绝句: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3)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18页。
苏东坡的评论很妙,他说:“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4)苏轼:《书子美黄四娘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3页。此诗杜甫作于成都浣花溪畔,黄四娘当是诗人邻里,一普通人家妇女,其身份地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任何大臣相比。然而我们今天读这首诗,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黄四娘和她那满园的花朵都栩栩如生,就像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前一样,而且在我们这一代和以后许多代读者都早已作古之后,黄四娘和她那些花朵仍然会栩栩如生,活在未来读者的心目中。
诗文不仅使写进诗中之人永在,当然也会使诗人声名不朽。曹丕《典论·论文》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5)曹丕:《典论·论文》,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4页。和“永恒的诗句”一样,曹丕提及的“良史之辞”也会使已为陈迹的人和事复活再生。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自谓撰写《历史》之目的,就是要从不断消失的时刻中,拯救有价值的东西,“不使时间让人们成就的一切黯然失色,不让希腊人和野蛮人都做出的伟大业绩悄然逝去,不为后人所知”。(6)Herodotus, History, trans. David Gre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3.中国古代的历史家司马迁也很明确这一点,他认为史家的任务就在于记叙重要、有价值的德行伟业,不使其湮没无闻。他认为对史家而言,“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7)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见李伟泰等编:《史记选读》,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530页。所以历史和诗文一样,都因为我们深感时光流逝、人生短促,于是努力把生命当中值得留恋的、美好的甚或痛苦的记忆都保存下来,而且要做出真实的记录,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然而就司马迁而言,记叙和保存的意愿更带有个人际遇的感怀,着了些悲剧的色彩。他十岁诵读古文,二十岁遍游大江南北,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又继承父志为太史公,常待命于武帝左右。不料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灾祸突降,汉将李陵受命带兵五千北伐匈奴,深入敌境与数万匈奴骑兵鏖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兵败投降。汉武帝闻讯大怒,要惩处李陵家人,朝中竟无人敢置一言。司马迁虽然和李陵非亲非故,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李陵的英武忠勇辩解。武帝盛怒,将太史公禁锢牢中,后来又处以宫刑,不仅使他有皮肉之苦,而且遭受奇耻大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痛陈自己何以要忍辱偷生的缘由,有这样著名的几句话:“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8)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李伟泰等编:《史记选读》,第561、564~565、566页。这表明他有一种明确的使命感,然后他又揭示出深藏于内心深处的抱负和志向,使他能傲视死之威胁:“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尤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9)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李伟泰等编:《史记选读》,第561、564~565、566页。正因为他抱有如此坚定的决心,深信其著述将广传于后世,才可能隐忍而发愤著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不顾一切艰难困苦而完成夙愿,于是可以坦诚宣告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0)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李伟泰等编:《史记选读》,第561、564~565、566页。司马迁抱有明确的目的、坚定的信念和达于不朽的强烈愿望,终于完成巨著,历述自黄帝迄于汉武帝三千年历史,记载了历代列国的起伏兴衰,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民族乃至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内容,并初创纪传体史书,不仅记录了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的业绩,而且讲述了儒林士子、游侠刺客、货殖商贾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生平际遇,展现出古代中国社会一幅全景式的图画。司马迁的肉体虽遭腐刑摧残,早已灰飞烟灭,但他宏大的精神、著作及文采却永远存留世间,垂于不朽。
二、 栩栩如生:论历史记叙的文学性
我们都希望在个人或集体的记忆中,保存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而历史和文学虽然不同,却又同是满足这一基本愿望的途径。作为两种写作类型,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在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会建立一个连贯合理、令人信服的叙事架构,情节描绘得精彩生动,人物也刻画得真实可信。写作的过程首先要选择行动或事件有意义而互相关连的要素或片段,然后用文字再现这些片段,创造出前因后果符合逻辑、完全合情合理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创作的过程,需要运用想象,也会对事情的始末缘由作出合理解释,所以也就有史家阐释的活动。史家往往善于作文,也应该善于作文。正如章学诚所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1)章学诚:《史德》,见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0页。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中,这个“文”字,即历史叙述之文学价值是得到充分承认和赞赏的,历史叙述是写作的一种类型,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部分。虽然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目的各有不同,体裁的要求也各异,文与史却未可截然划分。司马迁的《史记》常常被人称道的,除历史的意义之外,便是其文学的价值,其文字之精美,以及描绘之栩栩如生。
其实不仅中国如此,欧洲传统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海登·怀特所说,直到法国革命之前,“历史通常被视为一种文字艺术。更具体一点说来,历史被视为修辞学的一枝,而且人们也普遍认识到其‘虚构’的性质”。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影响之下,历史与文学才分道扬镳,形成僵硬的对立。“历史被设定为虚构的对立面,尤其与小说对立,历史乃‘真实’的再现,小说则是‘可能’、甚至是‘想象’的再现。”(12)Hayden White, “The Fictions of Factual Representatio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3.正是针对这种实证主义的偏见和谬误,怀特才极力揭示“事实再现之虚构”,强调历史写作乃是一诗性创造的过程,指出“历史家和诗人及小说家一样,会采取完全相同的比喻性策略,使用完全相同的用文字再现事物之间关系的模式”。(13)White, “The Fictions of Factual Representation,” ibid., p. 125.可是威廉·冯·洪堡1821年在柏林科学院的演讲中却说,历史事件已知的事实只不过提供了“事件的骨架”,那只是“历史必要的基础和材料,但还不是历史本身”。历史家的任务则是要寻找“基于因果关系之上那种本质性的内在真理”,而在这一过程中,“和诗人一样”,历史家“必须把自己收集起来那些零散的片段,综合为一个整体”。(14)Wilhelm von Humboldt, “On 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 ed. Kurt Mueller-Vollmer, The Hermeneutic Reader: Texts of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90) 106.洪堡充分承认想象在历史写作中起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历史和诗完全可以相比,“历史的描绘和艺术的描绘一样,都是自然之模仿”。于是洪堡认为,“我们因此不要不情愿把更容易认识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与历史家的创作过程相比,只是历史家的创作过程受到了更多的质疑”。(15)Humboldt, “On 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 ibid., p. 109.在德国传统中,洪堡的影响当然不可小视,这就使我们意识到,由兰克提倡那种注重档案材料、以文献为基础的史学无论多么重要,那也不是十九世纪唯一的历史哲学。
由此看来,怀特力斥“事实再现之虚构”就并没有那么激进和革命的意义,因为他极力显示历史叙述的文学性,而那是东西方传统都早已认识到的常识。“说历史的文本因为是一种叙述,就和小说的叙述有一些共同之处,看来不过是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卡洛·金斯伯格这句话其实是对怀特说的。“远更有趣的是再进一步,去探讨历史文本中讲述的事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是真的。”(16)Carlo Ginzburg, “Ekphrasis and Quotatio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MAART 1988): 5.金斯伯格征引许多希腊和拉丁的古典文献,说明在历史家通过语言的魔法传递历史知识时,描绘生动,即希腊文的enargheia和拉丁文的demonstratio,会起多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早已消失的过去直接呈现出来,真实可感,使人觉得历历在目。“如果你是一位古典的历史家,”金斯伯格接下去说,“你就应该用enargheia来传达你所叙述的真理,打动你的读者,使他相信你说的话”。(17)Ginzburg, “Ekphrasis and Quotation,” ibid., p. 7.他从普鲁塔克的论文《论雅典人的声望》中引用的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普鲁塔克把历史与绘画相比,认为“能够把人物及其感情描绘得栩栩如生,使其叙述有如绘画者,就是最成功的历史家”,因为他认为用文字再现事物可以描绘得生动如画,即希腊文的ekphrasis,“那就是历史叙述的目的”。(18)Ginzburg, “Ekphrasis and Quotation,” ibid., p. 10.换言之,历史家的任务其中一个主要部分,就是通过生动的描述来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马瑞·克里格有一部研究描绘如画的文字即ekphrasis的专著,其中也提到enargeia“是描绘生动,…… 可以使事物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19)Murray Krieger, Ekphrasis: The Illusion of the Natural Sig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68.克里格指出这一修辞手法具有两面性:“由ekphrasis描绘出来的既是一种奇迹,又是一种幻像:它是奇迹,因为只有语言才可能追踪的前后相随的一连串行动,好像突然凝固在一瞬间的景象之中,但它又是幻像,因为这难以想象的图画之幻像,只有诗的词句才可能暗示出来。”(20)Krieger, ibid., pp. xvi-xvii.与图画相比,古代的普鲁塔克和现代的克里格都更喜欢如画的语言,即ekphrasis,因为语言可以充分描绘在时间的推移中变化发展的整个行动或事件,而绘画和雕塑则凝固在时间当中,只能表现某一特定时刻里的一个场景;这不免使我们想起莱辛在《拉奥孔》中表达的观点。莱辛曾说,绘画的再现只能使用“单一的时刻”(nureineneinzigenAugenblick),也因此“必须选择那最具包孕性的片刻,即最能构想前面发生的和后来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个片刻”(mußdaherdenprägnantestenwählen,auswelchemdasVorhergehendeundFolgendeambegreiflichstenwird)。(21)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Laokoon: Wie die Alten den Tod gebildet (München: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n. d.) XVI, S. 91.诗人和历史家使用如画的文字,就能够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在读者的心目中活灵活现地一幕幕展现出来,就像画家能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展示出各种细节,形态和色彩都历历在目一样;不过诗人和历史家更胜一筹,因为他们可以展现在逻辑上和因果关系上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画面或活动的画面,讲述一个在时间上完整的故事,而不是凝固在时间里的某一片刻。但克里格说,由文字图画唤起的只是一个幻像,是读者借助于想象在心目中所见的意像。然而诗人和历史家能够做到的,也就是ekphrasis即文字描绘出来的图画,因为逝者不可追,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早已消失于无形,诗人和历史家也只能通过生动描述的文字,创造一种真实感,或如金斯伯格所说,“一种effetdevérité,那是他们的任务当中一个内在的成分”。(22)Ginzburg, “Ekphrasis and Quotatio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MAART 1988) 5.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良史之作的文学性,明确历史著作的审美价值乃是写作历史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三、 史书记言:再论历史记叙的文学性
在历史写作中,报道历史人物所说的话也许最能显出史家使用文学的技巧,因为这类记言不大可能是当时人所说的话之真实记录,而往往是假想出来的,因而是虚构的。历史记言的虚构性是史家及其批评者们都认识到的,但历史叙述中几乎总会包含这类记言,以使描述更生动,而且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也使描述更可信,因为语言在人的活动和交往中如此重要,我们很难设想记载人的行动或有人参与的事件,其中完全没有语言。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曾把人定义为“有逻各斯的动物”,传统上往往将之理解为“理性的动物”(dasanimalrationale,dasvernünftigeLebewesen),但伽达默尔认为应该更准确地从语言上去理解,也就是说,“人是有语言的动物”(MenschistdasLebewesen,dasSprachehat)。(23)Hans-Georg Gadamer, “Mensch und Sprache (1966),” Hermeneutik II,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Tübingen: J. C. B. Mohr, 1986) S. 146.由于语言在人的活动中起如此关键的作用,一场完全不说话的哑剧很难让人相信是人之历史的记录。
比司马迁《史记》更早的《左传》就有一些段落,可以为历史记言之重要提供几个有趣的例证。如“介之推不言禄”那一段,讲述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终于在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返国即位,为晋文公。晋侯想奖赏跟随他在外流亡的人,但介之推认为他们不配获赏,他自己也拒绝接受奖赏,而且决定到山里隐居。他和母亲商量,他母亲先劝他接受奖赏,但介之推心意已决,不愿改变主意。《左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24)《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7、1867页。
绵山在今山西省界内,据说就是介之推和他母亲隐居的地方。传说晋文公很想找到介之推,反而铸成大错。他既无知又武断,竟下令放火烧山,本意是想迫使介之推出山,结果非但没有奖赏介之推,反而把他母子两人活活烧死在山火里。晋文公悔恨不已,下令在介之推死的那一天不准生火,那就成为古代中国非常重要的寒食节之起源。后来寒食又与清明节相合,每年春分后十五日,人们都去扫墓踏青,祭拜先人,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十分重要的节日。不仅中国,而且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只要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便都有这样的节日。所有节日庆典都起源于过去的历史,而且往往有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也都活在人们集体的记忆之中。
《左传》还有一段关于鉏麑的记叙,也非常有趣。晋灵公是个很不像样的君主,他百无聊赖,曾站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人,看人如何躲避来取乐。有一次因为嫌厨师炖的熊掌不够熟,就把厨师杀掉,装在草编的框子里,命令宫女抬出去示众。老臣赵盾不断进谏,使他很厌烦,于是晋灵公派了力士鉏麑去刺杀赵盾。那是在《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鉏麑奉命去杀赵盾,但那天发生的事情却令人颇感意外:
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25)《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7、1867页。
鉏麑这段独白揭示出他陷入两个互相冲突的选择之困境,一方面是杀戮一个无辜的好人,另一方面是违背主上的命令,他的自杀则是他摆脱那个困境的办法,同时也显露出他的武勇和他高尚的品格。没有那段独白,史家就只能给我们描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鉏麑去到赵盾家里,却死在一棵槐树下,但那就会造成一个谜团,使我们困惑不解,他怎么会死,为什么他会自杀而不去杀死赵盾,而刺杀赵盾正是他特别奉命去做,而且完全有能力去做的事。鉏麑死前说的那些话揭示出了他所处心理的困境,那些互相冲突而又不可调和的道德原则,那些话也为读者解开那个谜团提供了值得信赖的答案,否则读者会难以理解他的行动和他这个人的品格。
这使我想起劳伦·斯特恩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历史的记叙只限于描写可以观察到的事件,历史家们就不可能成功地告诉我们,非自然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26)Laurent Stern, “Narrative versus Description in Historiogra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21:3 (Spring 1990): 555.上面这段历史中的记言产生自历史家对事件是如何发生所做的解释和推想,来自史家“对当事人的信念、欲望、意图和目的之理解”。(27)Stern, “Narrative versus Description in Historiography,” ibid., p. 556.斯特恩认为,“描写(description)记叙历史事件参与者的周围环境;叙述(narrative)则讲述这些参与者做了什么或造成了什么”。(28)Stern, “Narrative versus Description in Historiography,” ibid., p. 558.按照斯特恩的理解,描写是可以观察到的历史事件的记录,而叙述则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写作,带有史家对发生的事件的解释,包括对参与者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解释,正是这些精神和心理状态驱动参与者去行动,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就鉏麑的自杀而言,他去刺杀赵盾,却死在一棵槐树下,这就构成一件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可以用严格的描写记录下来,但这段中的记言则在描写之上增加了内容,使这段记载成为叙述,其中包含了史家的解释,设想鉏麑内心里必定发生了怎样的冲突,最后怎样使他决定触槐而死。
在斯特恩发表文章的同一期《新文学史》里,哈斯凯尔·费恩作了一些有趣的评论,挑战斯特恩对描写和叙述的区别。他认识到斯特恩作出的区别与历史写作中的阐释作用有关,因为“历史家记叙过去发生的事‘有赖于’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之解释,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同于历史家对历史环境严格的描写,因为这种描写是‘独立于’描写本身的”。(29)Haskell Fain, “Some Comments on Stern’s ‘Narrative versus Description in Historiogra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21:3 (Spring 1990): 571.但是费恩却并不认为写作中解释的部分就是叙述。“希特勒下令进攻苏联,因为他想成为欧洲的霸主,他也相信一个夏天的战役就可以把苏联击败。”费恩把这句话作为例子,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句话是一个行动的描写呢,还是对希特勒所做事情一个一句话的叙述?”(30)Fain, “Some Comments,” ibid., p. 572.他认为这是描写,不是叙述或故事,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采用斯特恩的看法,这句话就已经是叙述,而使之成为叙述的,正是历史家对希特勒在1941年六月发动“巴巴诺萨行动”的意图或谋划的解释。“希特勒下令进攻苏联”就像“日本在1941年十二月轰炸了珍珠港”,都是对可以观察到的历史事件简单的描写,其中包含了撰写历史的材料,但却不是真正的历史。当历史家在这简单的描写之上,加上对希特勒或对山本五十六以及其他日本军部指挥官的信念、欲望、意图和目的之解释,说明这些如何造成历史事件的爆发,描写就会变为历史的叙述。可观察到的历史事件“理论上中立”的描写,在原则上说来是可以验证的,也不会受到质疑,但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则“浸润在理论中”,也总是可以挑战、可以证伪的。不同的历史叙述可以给可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或事件作出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可以被别的历史著作进一步挑战,作出另外的解释。在十八世纪,约翰·马丁·克拉登尼斯已经提出了有名的“观点”(Sehe-Punkt)概念,认为“事件只有同一的一个,但关于此事件的观点却不同而且有各种。事件本身没有什么矛盾;矛盾都产生自对同一事物不同的构想之中”。(31)Johann Martin Chladeni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and Accounts,” Mueller-Vollmer (ed.), The Hermeneutic Reader, p. 69.再回到《左传》所述鉏麑之死,他受命去刺杀赵盾却自己死去,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记言中表露出他的心理状态和他头脑中道德原则的冲突,最终使他自杀而死,则完全可以质疑,受到挑战。如果历史家把鉏麑死在树下这一事实做一个简单的描写,就不会受到挑战,但那也就会成为一个索然无趣、干巴巴的统计,而不是生动的描绘,使历史事件鲜活地呈现出来,即成为历史的叙述。
《左传》记言确实使记叙的场景更生动,使人读后印象更深刻,但这类记言的真实性也确曾引起质疑。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有人怀疑其真实,质问谁会偷听介之推和他母亲的对话,谁又可能见证鉏麑死前的独白。然而钱锺书却肯定这类记言在历史叙述中合乎情理,无可厚非,并且称赞《左传》的文学价值。他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记言虽为虚构,但并不因此就不能存在于历史叙述之中,他又引用了罗马时代的昆体灵与十九世纪黑格尔的话,支持记言在历史叙述中应该有一席之地的意见。钱锺书说: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古罗马修词学大师昆体灵(Quintilian)称李威(Livy)史记中记言之妙,无不适如其人、适合其事(itaquaedicunturomniacumrebustumpersonisaccomodatasunt);黑格尔称苏锡狄德士史记中记言即出作者增饰,亦复切当言者为人(WärennunsolcheReden,wiez.B.diedesPerikles...auchvonThukydidesausgearbeitet,sosindsiedemPeriklesdochnichtfremd)。邻壁之光,堪借照焉。(32)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钱锺书提到的古希腊历史家苏锡狄德士现在通译修昔底德,他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宣称比他的前辈希罗多德所著历史更真实可靠,但他也坦然承认,他记载历史人物所说的话,不可能是自己亲耳所闻。“我以及告诉我的人,都难于准确记住过去说过的话,”修昔底德完全承认。“因此,我写下的话是我认为说话者在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下,一定会说的话,同时我又尽可能贴近他们当时的确说过的话的大概意思。”(33)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Walter Blanco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11.金斯伯格也引用普鲁塔克的话提醒我们说:“修昔底德在写作中总是力求描绘生动(enargheia),因为他希望把读者变成一个身临其境的观察者,在读他的叙述时,在他们头脑中会产生惊讶和恐惧的感情,而那正是过去的人们亲身体验到的感情。”(34)Ginzburg, “Ekphrasis and Quotatio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MAART 1988) 10.由此可知,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历史家们那里,想象产生的记言都是历史叙述一个必要的成分,可以产生一种真实感,使描绘栩栩如生,也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可信的理由。
四、 真理与历史家的道德责任
历史家为了使历史叙述生动而真实,的确像诗人和小说家一样,使用相同的技巧和修辞手法,但历史写作中的记言有时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就说明历史毕竟还是不同于想象虚构的文学。钱锺书就曾拿鉏麑死前那段独白为例,说明二者之区别。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鉏麑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但是对于《长恨歌》故事里“夜半无人私语”那桩情节,似乎还没有人死心眼的问“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或者杀风景的指斥“临邛道士”编造谎话。(35)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页注1。
人们期待历史是真实的记录,讲述的是实在的世界,可以由文本证据或考古发现的实物来验证。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抱怨海登·怀特过分强调了历史著作的文学成分,模糊了文学叙述与历史叙述的分别。例如安凯斯密特在《历史再现》一书中,就在文学理论和历史哲学之间,划了一道重要的界限。他说:“不幸的是,在文学理论的语言哲学中,指证和意义往往只是一些个可怜的、没有想清楚而且没有决定性意义的意见。”但对于历史而言,真理、指证和意义都非常重要,消除这些概念就会引出严重的问题,“会让历史理论家们切断历史叙述与其相关的东西之间一切的联系”。(36)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现实和真理就是历史叙述相关的,因为历史家是在指称语言之外的事物那个层次上说话,即“历史家通过个人的陈述谈论历史事件、事情的状况、因果关联等等来描述过去那个层次”。(37)Ankersmit, ibid., pp. 41-42.的确,自怀特和后现代理论风行一时以来,已经有太多对真理和现实这些基本观念的质疑,有太多关于“语言学转向”的谈论,把世间的一切都变成了文本符号。现在应该来谈谈历史写作的另一面——即历史的真实和历史家应该说出真理的道德责任。
在中国传统的理解中,历史家在认识论和伦理的意义上,都与实在发生的实事相关连,应该“直笔”书写。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左传》又为这个观念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例证。那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谋杀了齐国君主。崔杼曾迎立太子光,即齐庄公,在齐执政多年,颇有权势。齐国贵族棠公死了,崔杼去悼念,见到棠公的妻子东郭姜貌美,便要娶之为妻。他不顾他们同姓不当婚,也不顾占卜不利的结果,娶了这貌美的寡妇为妻。可是齐庄公是个好色之徒,强迫崔杼之妻与之私通,又侮辱崔杼,使崔杼萌生了杀他的念头。那年五月,莒国的国君来朝见齐君,齐庄公设宴款待,崔杼却称病不去参加。庄公来看望他,其实是想去找他的妻子东郭姜,而崔杼与人串通,在他家里杀死了齐庄公;这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麦克白》,麦克白也是在自己家里杀死了国王邓肯。从《左传》的记载可以知道,齐庄公不是什么有德行的人,但那并不能成为崔杼谋杀他的借口,所以齐国的太史便把此事作为“弑君”记载下来。令人惊讶的是《左传》描写齐太史如何秉笔直书,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已书矣,乃还。(38)《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二册,第1984页。
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史官是正式任命的,其职责就是要真实记述重大的事件,而这一职务是在一家人里继承的。司马迁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汉代太史之职。在《左传》这一段记载里,三个兄弟都是为了真实记录事实,作为太史而赴死,第四个弟弟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要做同样的记载,还有齐国南方一位史官也准备好,如果有必要就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直笔书写,只是听说正确的记载已经写下来了,才返回南方去。《左传》这一片段颇有名,无论这段记载多么简短,无论其文字多么精炼,都使我们觉得这是高度自觉的、指向自我的一段话,因为这是很稀有的历史家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历史的一刻,在此史家宣告了自己坚定的信念,即撰写历史的目的就是要真实记录在时空中发生的事情。真理是如此重要,史家随时准备好要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然,写下“崔杼弑其君”这句话,并不只是记录一个事件,而且也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作出了判断;于是历史家也就负起了按照是非公理和公正的原则、该如何记载并作出褒贬的责任。齐庄公固然荒淫无道,但依照太史的判断,把他杀死而造成社会动乱无序,乃是更大的恶。历史叙述本身便是有组织的结构,力图弄清楚行动的来龙去脉,如何导向事件的发生。例如,崔杼不顾占卜不利的结果而娶东郭姜为妻,齐庄公好色淫乱,崔杼找到一个侍人帮助他谋杀齐君,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互相关联,建立起前后连贯的各个环节,其基础是历史家从可以得到的各种材料中挑选出来的事件和行动,而这些相连的环节产生一种因果关系的感觉,使故事的线索清晰而可信。诗人和小说家可以驰骋想象,自由构建他们的故事线索而无须证实他们虚构的叙述;史家在建构他们的历史叙述时,却绝不能歪曲任何事实,他们宣称的真实性也要受到检验,在原则上必须可以得到验证。
这在中国传统中,就是“史德”的观念,是良史必备的条件。章学诚说,良史不仅要善文,有史识,有判断能力,更重要的还须有史德。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39)章学诚:《史德》,见《文史通义校注》第一册,第219页。于是传统的“史德”观念就为历史家这个概念设立了一个相当高的道德标准。实际上历史总是从某一个观点出发来书写,还往往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史书可能会有事实的错误或并不精确之处,也并非所有的历史家道德都那么高尚——但所有这一切从理念上说来,都无损于中国学者和读者都十分珍视的史家的“史德”观念。那些做事圆滑而自认老练者,那些不讲道德而只看实际效果者,都会怀疑甚至挑战“史德”这个观念,但这个理念或者说理想乃植根于人们坚定的信念之中,即相信历史家必须说真话,相信历史总会超过任何现存的权力,历史的真相终究会露出来,活在人们集体的记忆之中。这样一来,历史似乎就有一种超越一切现存权力的意义。一个人在历史上将如何被人记住,无论是自己家庭、社会,甚或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最终说来就比锦衣玉食、金银财宝这类身外之物更重要。善莫过于名留青史,声名永传于后世,悲莫过于在史上留下骂名,永被人唾弃。这就可以让我们理解司马迁何以要隐忍发愤,完成他的巨著,也可以理解崔杼何以要一连杀死三位史官,最终也只好放弃。中国传统没有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这类制度化且影响极大的宗教,在中国文化里,信史的观念以及一个人将如何被后人评判和记住,可以说在中国人头脑中就形成了道德的基础,也形成了遏制人作恶的威慑力,其效力有如宗教想象中天堂之幸福和地狱之痛苦。
五、 同时性与历史知识
历史固然是已经消逝的过去的记录,但历史感却不是对已经死去、与现在脱离开的过去一种古玩收藏家式的兴趣,而是对现在仍然还活着且有意义的东西一种鲜活的体验。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只有过去当中还没有过去的那些部分,才提供了历史知识的可能性”。(40)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 trans. and revised.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289.如果历史是保存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使之不被遗忘,那么记忆的活动就已经是一个积极选择的过程。伽达默尔说:“记忆必须形成;因为记忆并不是不加分辨,事无巨细都记住。人们会记住某些事,却记不住其他的事;想在记忆中保存某件事,却扔掉另一件事。”(41)Gadamer, ibid., p. 16.在建构历史叙述时,哪些应该记住而得以保存,历史家已经作了选择,其最后的结果就是历史著述,用生动的叙述(enargheia)把过去展现在目前,在读者心目中呈现出栩栩如生的文字图画和意象(ekphrasis)。在这种情形下,伽达默尔提出的“同时性” (Gleichzeitigkeit)就是个很有用的理论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历史知识当中,我们体验过去那种直接的性质。这同时性概念“构成‘存在于当下’的核心”,其意义就是“无论其起源多么遥远,呈现给我们这个特殊事物在其呈现当中,完全达到了在当下充分的存在”。(42)Gadamer, ibid., p. 127.这就是说,作为读者或观众,我们通过积极的参与,可以遥想历史人物在过去时刻、在不同境况中的所思所感,在我们直接体验的那一刻,我们体验到的东西就变得鲜活起来,直接呈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历历在目,尽管其起源有可能在遥远的往古。
伽达默尔这个概念取自索伦·基尔刻郭尔在神学中对此概念的应用,又用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为例来加以说明。在倾听音乐或观赏一幅绘画作品时,来源于过去的艺术品由我们的参与而激活,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读者或观众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包含在艺术品的概念本身之中。“在我们称为审美的这类游戏当中,观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43)Gadamer, ibid., p. 128.不过与绘画及其他形式的艺术相比,书写文字更有特殊的力量,可以最生动地唤起过去,把它带入现在。伽达默尔说:
没有任何东西比书写文字更纯粹是头脑思考的印迹,也没有任何东西更有赖于理解的头脑。在辨识和解释文字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奇迹:陌生和死去的东西转化为完全与我们同时而且熟悉的。…… 书写文字的传统一旦被解读出来,就在如此高的程度上成为纯粹的头脑,它对我们说话好像就在当下。正因为如此,有阅读能力,能够理解文字的意义,就像是一种秘密的技艺,甚至是一种魔法,可以禁锢我们,也可以放我们自由。在阅读中好像时间和空间都被超越了。能够阅读过去用书写传下来的文字的人,就可以把过去完全转变成现在。(44)Gadamer, ibid., pp. 163-64.
这段话很好地描述了我们与过去相遇的情形。过去的事件转瞬即逝,只能由文字得以保存,在古代或在录音录像的技术未发明之前,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说与过去相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只可能是主要通过阅读历史叙述重现那些事件,体验历史,获得历史知识。在阅读当中,的确像魔法一样,文本的字句会变得鲜活起来,就像伽达默尔所说,“会出现一个奇迹:陌生和死去的东西转化为完全与我们同时而且熟悉的”。正是通过阅读,记住我们读过的东西,我们才获得历史知识,产生一种历史感,而这对于形成我们自身的认同感,意识到我们是谁,都至关重要。的确,过去的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就像泥沙和渣滓沉入了时间之流的河底,大部分时间都湮没无形了,但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当河水被搅扰或水流改变方向的时候,也有可能重新泛起。时间的确常常在概念性比喻中,被想成是河流,希腊古人和中国古人都有相似的比喻,显出时间的性质就是朝向某个未来之点不断流动。赫拉克利特说:“对那些踏入同一条河的人,流过的水却是不同而又不同的。”他还说:“我们走进又不能走进同一条河。我们是,我们又不是。”(45)Heraclitus, fragments 61, 63, trans. Richard D. McKirahan, Jr., ed. Patricia Curd, A Presocratics Reade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6) 36.孔子站在江边也叹息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46)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10页。我们都站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在变化,我们自己也随之而变。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动的,每一时刻都会不同。
如果我们每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过的水都不一样,或者换一个说法,如果我们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里,时间那不停变化的状态就会对历史理解的性质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理解得不同,我们怎么能够获得前后一致的整体的历史知识呢?在讨论同时性概念时,伽达默尔用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作为例子,也会引向同一个问题,因为审美经验和审美判断都总是个人的。伽达默尔说,弗利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提议,“所有个人都是普遍性生命的显现”,因此“‘通过把自己转化为他人,’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握住作者的个人性”。(47)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 189.然而这种普遍性的预设没有充分考虑到人们理解的差异性,便越来越会出现问题。威廉·狄尔泰提出历史理解的观念是重新回到维科的真理与创造可以互相转换的观点(verumipsumfactum),即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人对历史的认识胜于对自然的认识,因为自然乃上帝所造,也最能为上帝所认识。伽达默尔引用狄尔泰的话说:“历史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48)Wilhelm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VII, 278, quoted in Gadamer, ibid., p. 222.不过伽达默尔认为,“主体和客体具同一性”这个假设也有问题,因为基本的问题是,“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如何成为历史的经验”。由于每一个个人在眼界、经验和知识等方面都各有局限,“人的这种有限性如何可能达于无限的理解,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49)Gadamer, ibid., pp. 222, 232.伽达默尔对历史哲学的贡献就在于充分承认人之理解的差异和多元,并提出“视野的融合”这个概念,即主体和客体、理解者和被理解者,在达于理解的那一刻交汇融合在一起,产生出真正的洞见和认识。由于我们的视野各不相同,理解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伽达默尔批评科学主义盲目相信方法,总以为按照科学方法循序渐进,便可不断取得进步,他更强调历史和传统这样的人文观念,并且说:“理解其实不是理解得更好。…… 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就总是不同,那就足够了。”(50)Gadamer, ibid., pp. 296-97.我们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的确就是如此,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是如此。
然而那绝不是一个极端相对主义的看法,不是“无可无不可”,也不是每一种理解都是自足而独特的,所有的理解都是同等而且同等有效的。那个“同时性”的概念本身,即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能够感觉和体验到他人在过去的感觉和体验,就已经设定了某一程度的共同性,虽然不是普遍性和完全的同一性。其实,保罗·瓦勒利曾说,他的诗的意义完全由读者来决定,伽达默尔就摒弃了这种看法。按瓦勒利的说法,“对一个作品的一种理解,并不会比另一种理解差。并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合适的反应”。但伽达默尔批评了这种观念,认为这只不过是“站不住脚的阐释虚无主义”。(51)Gadamer, ibid., pp. 94, 95.我们的确理解得不同,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理解的层次不同,我们理解之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程度也不同。换言之,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叙述和再现也许不可能达到完全绝对的真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求真,也不能因此否认历史叙述、再现和认识没有高低上下和正误之分。尽量接近于真——真实和真理——这是史家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坚持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