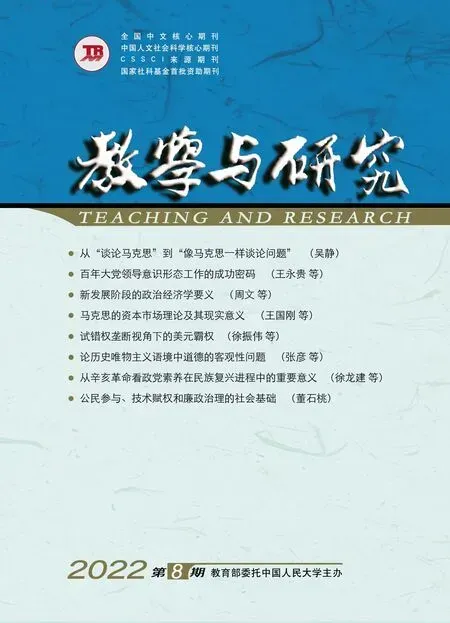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政治情境化发展
——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中心*
付天睿
法国革命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现实资源。以法国革命为题材,马克思写作了《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政治论著。相较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复、复杂而荒诞的革命史是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更新了法国革命一开始就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1)[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8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逐层深入,从一个个纷杂凌乱、相互拮抗的短时段社会情境出发,不断提炼其中的关键性矛盾及其表现,抽丝剥茧地把握了1848—1851年革命的总体进程与深层结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些政治论著或革命史论著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这些历史科学论著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其中的发展变化与存在形态?我们认为,以《雾月十八日》为代表的革命历史论著,不只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应用”了现成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是体现着马克思从政治情境到阶级斗争、社会结构,从社会结构到历史规律和趋势的思想逻辑,以政治情境化的维度补充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进行了理论视角的补充和探究。因而,本文对以《雾月十八日》为中心的革命史或政治文本进行分析能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克服传统解释模式的局限性,丰富其现实内涵,从而为面对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切近视角。
总的来说,《雾月十八日》呈现出一种短时段与长时段、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织的历史图景。就此而言,我们尝试改造和使用布罗代尔的相关概念来对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的历史视域进行解析。布罗代尔以周期性的规律将历史总体切分为长短不一的“时段”,主张“区分长期持续的运动和短暂的爆发”(2),并通过“结构”概念使短时段衔接于长时段,为马克思政治文本的分析提供了较为恰切的思路和概念工具。但布罗代尔的局限在于,一方面其仅将结构理解为“一段长时期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现实”(3)[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34页。,而没有把握短时段的“具体情境”背后的共时性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没有将多重视角统一起来,即没有把握其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性要素,从而对所体现的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历史的多重视角进行分析。对布罗代尔历史时间层次分析的批判性改造,即提取出“短时段”与“长时段”的互动视角,有助于我们阐释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政治文本中的丰富内涵与具体形式。这就必须首先对《雾月十八日》中政治情境的展现方式进行分析。
一、政治事件与情境:“短时段”的呈现
在《雾月十八日》开篇,马克思即通过对历史悖谬的戏剧化提问和反讽,引出了关于具体情境的分析:“为什么一个有3 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4)“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5)马克思的设问实际上是,如何理解特定历史事件(Ereignisse)起因、进程与后果?拿破仑雾月十八日政变(1799年11月9日)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政变(1851年12月2日)之间是何种关系?历史(事件)是否具有重复性?
上述问题作为历史之谜引出全文的革命历史叙述,解谜过程成为核心的叙事线索,并呈现出短时段(微观历时性)、共时性(结构化)、长时段(宏观历时性)三重时间性的分析层面。在《雾月十八日》的叙述结构中,马克思往往会先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内(短至数日长至数年)对彼时的社会态势和具体条件进行铺陈,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铺设足够的动势与力量。据此,我们将马克思对政治事件的短时段进展的叙述称为“政治情境”。“当……就……”(als…zu)是典型的表述方式:“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战,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470、476页。在这种叙述方式中,某一政治事件的发生并不直接依赖某种基于先验目的或后验结果的历史必然性,而更多地出于对彼时政治情境的还原中显现出的局势(Umstände)和条件:“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24、497、520页。
具体来说,首先,在马克思这种短时段的视野中,不同事件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偶然的,并且这种偶然结成的事件间关系可能是形成某种政治情境的关键。“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 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24、497、520页。虽然波拿巴与拿破仑之间存在着一种戏谑的互文性,但马克思指出,“形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落到”波拿巴手中,其所体现的不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之化身”的必然性表现。对这种区别于必然性逻辑的偶然性的容纳和展现恰是政治情境视角与以往历史哲学的重要差异。
应当指出,对事件和情境的偶然性的把握是对唯物史观的传统阐释模式进行补充的关键维度。这一维度虽然在后马克思主义等当代激进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后者却常常忽视以《雾月十八日》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对此的启示。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阿尔都塞为例,其虽然保持着对历史进展中的微观和偶然要素的持续关注,但直到其晚年才正式提出了历史本身的“偶然相遇”属性。他认为,历史并不存在某种目的或终点,有的只是由事件偶然(aléatoire)地、自发地(spontanément)“汇合”或“相遇”(rencontrer)而形成的“形势”(conjoncture)。在这一思想范式下,他指出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是以此思考历史与现实的代表性思想家。就马克思而言,阿尔都塞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性作用中形成的判断,而在此之前的《雾月十八日》实际上更加直接地体现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事件化、情境化与偶然性向度。“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10页。如果说“偶然性”在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本中处于“后台”,即马克思总是对资本生成和增殖以及历史发展逻辑中蕴藏的偶然性要素保持着潜在的关注,那么在其政治文本中则更加直接地将偶然性问题置入其历史分析模式的“台前”。在具体情境的分析视角下,只有将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宏观进程暂时悬置起来,才能使特定的短时段内事件的特殊动向暴露出来,从而更加精准地对长时段的历史趋势进行确定和补充。
其次,事件与其所汇合而成的情境所体现的也不是线性的必然关系,而是时常呈现出逆势、断裂和转折。在复杂的政治情境中,任何看似确定的现象都不是某种后果的绝对保证。例如“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24、497、520页。这种鲜明的对比和转折是《雾月十八日》中较为常见的叙述方式,马克思不断强调着情境中大量涌现的反常要素和偶然事件。“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这些胜利是取决于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的,而自从 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24、497、520页。可见,事件的意外和转折进一步揭示出,政治情境的分析视角能够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中发现并把握事件的非连续性和非同一性。我们知道,事件或情境本身并不直接带有一种必然的趋向或关联,即不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们仅在事实上都无法将其判断为顺承或逆势。只有以先验论或目的论的视角来看,现实发生的事件才可能顺应或违背某种趋向。在对政治情境的分析中,马克思正是以一种“似目的论”的表述体现出其“非目的论”观点,大量看似“反常”却可能对更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进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成为了马克思的讨论重点,大大丰富了其历史分析的科学特质。
再次,事件及其情境又作为一个行动场域,容纳和制约着诸多党派“行动者”的出场、斗争与退场。“情境”本是戏剧的呈现模式,角色必须依赖作为场幕章回的情境才能把情节展现出来,而作为情节之短时段呈现的情境同时也塑造着角色的功能和位置。在《雾月十八日》的文本中,马克思多次使用舞台与戏剧的表达,呈现着对历史事件及事件主体的反复隐喻。如波拿巴的加冕“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576、575、466页。;历史事件的重演表现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576、575、466页。。在充满冲突的戏剧化情境中,“结局”总是处于不在场、不确定的状态,因而情境中的角色(作为行动者的各个党派)也就并非直接承担和执行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悲剧主人公”也即“历史主体”,而是这些事件、情境中的粉墨登场而又荒诞离场的“丑角”,全然无法支配或理解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命运。在此意义上,登基上位的路易·波拿巴也就并不仅是一个“无功绩”(ohne Heldentaten,也意为“没有英雄气质”)的“英雄”(Helden)(14)德文“Held”或英文“hero”既有“英雄”之意,又指“主角”“主人公”,通常指称命运重负的承受者或历史功业的创造者。或“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576、575、466页。,而是社会阶层分裂、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是历史趋势的情境化的化身。“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576、575、466页。因此在《雾月十八日》的情境分析中,“个人”作为微观的行动者,其意志和目的在历史的总体外观下被整合进情境和形势之中,正是事件和情境置于行动者(主体)之上,才能够“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576、575、466页。,即这种无主体或“非人道主义”的情境化视角,才能在阶级结构的层面上将历史的所谓悖谬、反常揭示为某种正常。因此,通过政治情境的呈现,历史进程的反常与吊诡在主体与行动者的意义上使得《雾月十八日》的视角进一步区别于传统历史哲学的必然性、同一性逻辑。
然而,政治情境中显示出来的意外和矛盾并不只是偶然性的盲目堆积和随机“相遇”,其更意味着特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历史过程的不充分、不平衡进展。在马克思的短时段叙述中,这些居于事件和情境背后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只是暂时被抽象掉了,但仍然以评论性片段、讽喻性段落等方式“插入”党争事件的叙述和政治情境的展现。这种插叙表面上打断了文本的主要叙事线索,然而却不断暗示出短时段政治情境背后更深层、更稳定的基础性结构。换句话说,短时段的政治情境所容纳的具体事件及其关系的偶然性实际上潜在地指向了彼时社会的横向结构和纵向趋势:“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马克思揭示出,这种内蕴着矛盾和张力的政治情境在现实中预示了社会变革与历史转折的到来,其反映在理论上,也就作为了从政治情境铺陈到社会与阶级结构分析的铺垫。
二、政治情境与社会结构:共时性的铺展
虽然《雾月十八日》全篇充溢着政治事件和情境的短时段叙述,但仍然在一些关键性的引人注目的片断性分析中,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结构分析。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考察革命政治事件及进程的基本理论前提,因而“结构”就成为我们读解马克思政治文本的关键性视角,是对作为经验性前提和素材的政治情境的进一步梳理和提纯。面对呈现为偶然性、多样性的政治情境和历史事件,需要作为不同要素之间深层、稳固联系的结构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把握。基于政治情境的短时段列陈,结构才得以具备其内容和机理,并为政治情境的展现描绘出更加清晰的脉络。我们可以说,从政治情境到社会结构,马克思的分析呈现出一种渐趋深入、由表及里的逻辑。
阿尔都塞尤其吸收了马克思阶级社会分析中的结构性视角,在《读〈资本论〉》中对结构的具体机制进行说明时,曾对马克思所使用的“表现”或“呈现”(Darstellung)与“再现”(Vorstellung)概念展开专门讨论,这一思路能够为把握《雾月十八日》中政治情境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供较为切要的视角。
“Darstellung在其他事物中表示‘戏剧呈现’,但在‘在场的位置’这一根源意义上,戏剧呈现这个意思直接与其‘表现’‘展现’的意义相关联……Vorstellung指一种位置,但这个位置是一种前场,指有某种东西从背后撑起了这个前场,却通过其替身——Vorstellung——在此位置上展现出来。”(19)Louis Althusser et al. , Lire le Capital, PUF, 1996, p.646.
以此思路来读解《雾月十八日》,我们能够发现具体的政治情境与阶级斗争的总体结构具有一种“表现”与“再现”的互动关系。党争事件、政治情境“表现”着阶级结构,同时本质性的阶级结构以更深层的方式“再现”着作为表象的政治情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495页。既然结构本身就是由情境复合而成,那么派系纷杂、立场交织的复杂情境表明,结构本身必然是多元的、容差的;而结构之所以相较于政治情境是更为深入的,恰在于能够克服“假象”的结构分析对于揭示社会历史的构成和进展而言是更为实质的、切要的。结构既是对历史实况的忠实总括,也是对政治事件和情境的初步统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阶级结构分析以对法国政治社会具体情态进行再现的方式在理论上“再生产”着作为偶然事件之堆叠的法国革命史。这种理论上再生产的核心特征在于,其不仅能够提炼事件进展的关键性线索,同样能够容纳和辨析事件与情境中的矛盾和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结构中的这种矛盾本身构成了事件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马克思直接指出,“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495页。,立宪派、革命派、国民议会、山岳党、保皇派各自具有不同的立场,面临着或趋乐观、或近悲观的不同情境和局面。在这一分析语境中,马克思对具有多条主线和支线的政治斗争进程进行了“断层扫描”,将复杂的、彼此交织、相互冲突的社会情境共时地展现出来。从“二月革命”“六月事变”到立宪戒严、波拿巴当选,再到制宪议会灭亡、帝制复辟,每一阶段性的事件及其所包含的更加具体、芜杂的政治事件都可以共时地铺展为资产阶级内部(共和派、山岳党、秩序党)的结构,以及资产阶级与革命无产阶级、波拿巴及其党羽(小农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党派—阶级”社会结构。对政治情境的悖论性、差异性的铺展构成了阶级斗争的结构化叙事,而据此形成的结构同时更加清晰地展现着某阶段内整个社会的总体态势,再现着原本看似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政治情境。纵观全文,与其说马克思先后将一段历史的各个阶段共时地铺展为阶级结构,毋宁说恰恰是基于这种对政治情境结构性的铺展,全文的逻辑次序、章节排布才能够形成。因此,结构性视野能够在阶级分析中发现矛盾及其运动方式,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在短时段和具体情境之内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向。
要言之,作为“形式”的共时性阶级结构分析,将碎片化的政治情境在理论上再生产为作为“内容”的阶级斗争实质,进而使党派政治斗争背后深层的经济制约性得以显现。党争事件、政治情境的悖谬直接体现的是阶级及其利益和立场的对抗和张力,而阶级立场则位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进一步体现了特定生产关系结构。法国学者傅勒注意到,“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的法国不断地上演着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22)[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9、80、221页。马克思之所以使用阶级斗争的结构性视角,恰是缘于其从政治深入到经济、从现象穿越至本质的总问题。傅勒精当地将马克思的问题内核表述为“如何理解一个如此之早地形成的、但却如此不能掌控其政治历史的市民社会。”(23)[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9、80、221页。《雾月十八日》表面上讨论的是政治斗争与国家政权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利益冲突与市民社会问题。结构分析拂去了特定政治情境对生产关系的遮蔽,阶级结构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结构使得政治革命外观下的经济基础得以浮现,也就自然地将政治情境分析带入了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共时结构分析的片段中,不是短时段呈现中的党派行动者,而是作为集体或个人的阶级成为了某种“创造行动”的“主体”,并且成为了结构自身内在的中介性因素,保持着对结构制约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历史相关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页。这一论述呈现为如下结构化过程:经济基础——阶级(创造和构成)——上层建筑。阶级作为“集体主体”或“个人主体”在特定经济基础规定的可能性范围之内创造和构成特定的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结构内部两大层面之间的主体能动性中介。可以说,客观社会结构制约性和阶级主体能动性是历史相关的、相互中介的,二者并非机械的、单向的、线性的决定关系。这就容纳了更多的偶然性因素,从而在共时性结构层面形成了短时段政治情境的一个可能性空间。
马克思不断将历史事件发生的条件与具体情境提纯、深化,呈现出较“情境”与“事件”之表的“结构”之里,细微进展的“短时段”被暂时固定为(似)静态的“阶段”,揭示出党争事件、政治情境背后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况、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似乎代表了政治革命时代的结束,以及向一个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与政治革命相比,社会革命要缓慢得多,也要深刻得多。”(25)[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9、80、221页。阶级与社会结构作为关键的中介机制,将政治革命中具体情境的浮现指向了社会革命中历史趋势的生成。
三、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长时段的指向
通过对政治事件的描绘,唯物史观以社会结构对情境(事件)之再生产的具体方式再现着具体现实,同时这一过程也丰富和扩展着唯物史观本身。一般来说,宏观尺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长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表述,但《雾月十八日》的分析模式恰恰揭示出,这种一般性实际上根植于从政治情境中提纯而来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从文本叙事本身来看,马克思经常用评论性片段、讽喻性段落等方式将共时性社会结构分析插入事件叙述和情境呈现,从而将特定社会结构本身的缓慢流变和潜在过渡逐步暗示出来。正如同政治情境的短时段呈现经常被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分析所打断,而社会结构分析一旦形成,就立刻发现自身恰恰建立在历史巨流的“流沙”和“暗涌”之上。《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叙述方法之幽深精妙正在于此。只有认识到短时段与结构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在社会存在中的具体统一,才能够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长时段历史趋势和规律进行总结和把握的科学内涵。那么,唯物史观何以见之于这种结构化的政治情境?
首先,结构对情境之再现的关键恰在于将政治情境中体现出来的党派、集团以阶级的创造和构成行动为中介而归结为特定生产关系等经济因素。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通过多次使用 “…不过是…”(…sein bloß/ nur…)这类副词短语,将杂多的政治情境结构性地不断收敛、提纯为其背后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经济要素。例如“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500、474页。。正是其在经济和市民社会中的位置和属性,才使得政治上看似相互对立的“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为“资产阶级秩序党”;正是资产阶级进行经济的和社会的统治要求,才使得“议会制共和国”的政权形式得以形成。也正是因为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被奴役的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才使得秩序党感到“力量不足”,从而“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500、474页。,才产生了所谓的历史“倒退”和情境化的各种政治乱象。这样,通过“政治情境——阶级结构——社会结构”,也即“政治表象(表现、呈现)——政治经济中介机制(创造和构成)——经济社会”的深入递进分析,情境与结构得以在历史趋势的显现中实现统一,并上升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短促的历时性到结构的共时性分析,也就在历史观的层面上自然地指向了“长时段”的历史趋势与规律。
进一步地,《雾月十八日》中对政治情境呈现和社会结构分析使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的“进步”与“倒退”的辩证分析在形式上区别于唯心史观目的论,暗示着某种对历史性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与科学预见。马克思以结构的共时性维度,而不仅以“时间进展”的历时性维度把握社会形势,这样才能将情境与事件之间的断裂、逆势所显现出的偶然性容纳于社会历史分析中。具体来说,历史一方面看似连贯地向前发展,却有不断涌现的偶然状况和意外事件。而波拿巴的复辟和议会制的破产看似是历史的“退步”,却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中形势和条件积累不充分的表现,并且这种表面上的“退步”实际上是总体条件的进一步的累积过程(即所谓“两个绝不会”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相对稳定性)。“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500、474页。“历史的退步”本身是一种与目的论偕行的表述,只有预设了历史发展的目的,才能够对历史事件的进步与否进行判断。唯心史观的悖论恰恰在于,“退步”是无法被真正言说出来的:既然历史发展具有着某种自我克服、自我进化的内在逻辑,那么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其“进步”的阶段,都是前行而非退行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同时使用“进步”和“退步”来表述大革命时期的具体事件,恰恰是以对法国革命的典型史实的再生产体现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判然之别。在结构性视野中,历史并不具备某种先在的目的或方向,阶级社会的结构仅仅是其对象的客观再现。马克思“借用”了传统历史哲学的一般性表述来探求社会结构所蕴含的特殊性问题,也就在问题域的转换和聚焦中与作为意识形态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因此,“结构”也就是唯物史观的科学之维:一方面将具体的、微观的政治情境嵌入唯物史观,使其结构化;另一方面也通过结构与情境的统一将唯物史观的微观维度进行补充和拓展。没有“短时段”(历时性)的呈现——细节、动向、情态——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就是无本之木,更无从走向规律、趋势的本质性、历史性揭示。
马克思所科学预见的是何种历史性趋势?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其直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16、573、514页。马克思指的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中,拿破仑的铜像被轰然推倒。这种历史的笑剧和闹剧并不只是事件和情境的荒诞浮现,而是深刻地预示着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发展并不充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使得资产阶级内部长期处于离散和对立的状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因而“软弱无力”,存在着“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16、573、514页。;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封建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要素存在着深刻的张力。“小块土地所有制”“教士统治”等传统社会要素(“拿破仑观念”)一方面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激化了农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又为在一定时间内遏制矛盾、重建秩序提供了思路。只有在这种历史性的不平衡中,波拿巴所代表的小农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才能够戏谑地掌握资产阶级政权,并呈现出“行政权支配社会”的落后统治形式。而历史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图景随即也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逐步展现开来:“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16、573、514页。“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16、573、514页。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政治与议会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失败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进而还包含着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的自身批判、自身扬弃趋势以及新社会由之产生的人类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与阶级结构分析是现实情境与把握历史趋势的必要中介。通过结构对势力、要素、阶级状况的收纳,科学意义上的“形势”才能得以汇合而成。“它意味着考虑所有的决定性因素、所有现存的具体境况,清点它们,对它们做出详细的分类和比较。”(33)[法]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载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只有认识到《雾月十八日》中蕴含的“多元决定”与“归根结底决定”的统一,即经济基础、阶级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才能够从马克思所描绘的政治革命情境中把握社会革命的历史趋势。
要言之,以《雾月十八日》为核心的政治文本为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即从现实条件出发理解政治事件,在政治事件中把握结构性制约因素,根据制约因素判断历史规律与前进方向,从而为进一步的革命路线提供理论指导。“这不是一个终结革命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动另一场革命的问题……19世纪的任务就是确保无产阶级的胜利。”(34)[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8页。马克思本人也曾对《雾月十八日》的历史性启示做出说明:“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6页。“历史人物、社会局势、意识形态、经济因素在这个事件中编织成了一幅鲜活的、多变的、交错的图景,它既是辩证唯物史观的一种应用和检验,更是一种丰富和深化。”(36)应星:《事件社会学脉络下的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余 论
《雾月十八日》从短时段政治情境发掘出共时性的阶级社会结构,从社会结构进一步预见长时段的历史趋势。这一思想逻辑表明,三个时间性层次的分析之间不是一种庸俗还原论关系,也不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关系,而是一种“多环节总体决定”的科学综合关系。这种唯物史观的发展形式既能够容纳事件、个人、党派、阶级各层面的能动行动和特定局势的偶然性,亦能够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对偶然性和特殊性加以提炼,从而内生出社会总体趋势和历史规律的指向。
以政治情境和社会结构的维度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进行补充和发展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多重意义。在理论上,一方面,这种情境与结构相统一的分析模式能够进一步回应和反驳认为马克思历史观是一种唯理智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微观的短时段事件情境、中观的共时性社会结构和矛盾以及宏观的历史性趋势这多种视角的递进式综合,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中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及历史决定论的超越和克服。而相应地,在不同时间性层面上,历史进程的“主体”或“承担者”也发生了位移和改变:在短时段政治情境中是无法支配命运笑剧的丑角式党派,在共时性社会结构中是立足于经济基础创构上层建筑的阶级主体,而在历史性趋势中则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自身革命与扬弃进程。
另一方面,《雾月十八日》集中展现了马克思理论图景的丰富性、开放性。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流行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主要从马克思的政治文本中析取了唯物史观的必然性逻辑与偶然性逻辑,实际上却同时忽视了作为二者之统一的结构逻辑,而后者才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创见所在。以《雾月十八日》为线索,唯物史观既能够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抽象提纯科学地把握宏观的社会发展趋势和历史规律,同样能够通过对短时段的结构化分析容纳并把握中观和微观的情境、事件以及具有偶然性的多种要素,因而是一种既复合又开放的理论总体。如果说《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资本逻辑和物象化批判使得唯物史观进一步聚焦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呈现了对特定生产方式和社会阶段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消亡规律的纵深式解析,那么以《雾月十八日》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则在更加短促的历史情境中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动态细节,为社会经济结构-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逻辑补充了短时段情境的关键一环。只有完整地把握唯物史观建构过程中内蕴的政治情境——社会结构——历史趋势和规律的科学综合和有机统一,才能够真正实现唯物史观本身的丰富性和开放性。而只有认识到唯物史观视角的丰富性、视域的开放性,才能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深化和发展打开思路,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延展创造契机。
在实践上,以《雾月十八日》为中心的马克思政治文本体现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具备面对现实情境、解决当下问题的重要价值。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显示出一种类似的历史视角:“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3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6页。情境(抗战的当前局势和弱点)——结构(社会阶级状况)——趋势(抗战走向胜利、民族实现独立),毛泽东与马克思的革命和历史观一脉相承。这种继承和发展表明,政治情境分析中蕴含和展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具有恰切的现实面向和深刻的当代价值,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际遇中开启了更广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