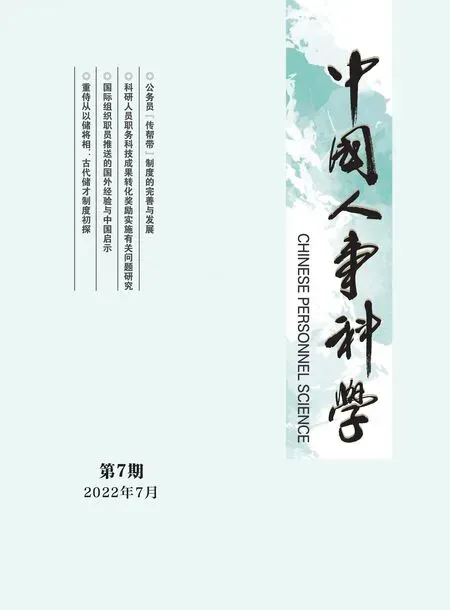重侍从以储将相:古代储才制度初探*
□ 李宜春 张焕颖
本文所指的储才,主要是我国古代对宰相等高级政治精英人才的储备与培育。两汉的郎官、大夫制度,唐代的翰林制度,宋代的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制度,明清的翰林制度,都是各自朝代储才制度中的核心部分,且两汉的郎官、大夫,唐、明、清代的翰林,宋代的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都属于广义的皇帝侍从,所以可以用宋代所谓的“重侍从以储将相”来概括。
中国古代历朝中央都有中央核心决策体系,带有核心性、重要性、统筹性、便捷性、机密性等特征,它通常是宰相体系,也称为内辅体系,而有别于外朝的决策体系、部门性决策体系,常有“枢机”“枢要”“机密”“机务”“枢密”“政本”“政源”“政府”等称谓,相应地,其成员常被称为“知政事”“掌机要”“预机务”“与闻国政”“参预朝政”等。良好的储才制度,不仅可以体现社会公平,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打造杰出官员队伍,还有利于打造宰相体制。研究历代储才制度的沿革历史并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发掘古代人才制度的精华与特色,并有所启发。
一、唐代之前的储才制度
(一)秦国的客卿制度——“位为卿,以客礼待之”
秦统一之前,周朝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杨宽《战国史》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1]如周武王胞弟、周成王叔父周公旦,其长子封在鲁国,“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2]这造成社会流动的封闭,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
秦国曾实行客卿制度,请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官,“其位为卿(爵为左庶长),以客礼待之”。[3]张仪、范雎、蔡泽、李斯等都是著名的客卿,起到了相当于宰相的作用,为秦国武力强盛并统一中国作出贡献。
(二)汉代储才制度——光禄勋“总领从官”
汉代有光禄勋(原名郎中令),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郎是宫廷近侍从官,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之分,最多可达千人。西汉盛行任子、入赀为郎,佞幸贵戚子弟为郎的郎官制度。任子,是任用高级官吏的子弟做官。郎官守卫门户,出充车骑,在皇帝身边熟悉政事,随时备顾问差遣。卫青、霍去病、苏武等都是西汉由郎官成长起来的著名政治人物。但这样的郎官制度存在任人唯亲、唯财、唯佞等缺点。
大夫讨论朝政,备顾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可达几十人。郎官、大夫成为汉代高级人才的储备军,光禄勋成为汉代重要的储才基地。
汉武帝时期,储才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一是独尊儒术以后,郎官制度逐渐完善,大批熟悉儒家经典的儒学之士,通过察举、征辟等方式,进入国家这一储才基地;也有少数是先成为五经博士,或直接担任更高层次的大夫之职。西汉中后期的丞相、三公多是如此,如翟方进出身寒门,勤学《春秋》,射策甲科,被任为郎。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以射策甲科为郎。张禹好学,试为博士。孔光,熟悉经学,举为议郎。翟方进的仕途大致是,射策甲科为郎,举明经,迁议郎,转为博士,迁朔方刺史,再迁为丞相司直,为京兆尹,迁御史大夫,升为宰相。张禹的仕途大致是,为博士,授太子《论语》,迁光禄大夫,出为东平内史,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秋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升为丞相。另有马宫、何武、王嘉、师丹、蔡义、公孙弘、薛广德、平当、韦贤等。西汉的西域都护、司隶校尉这两个重要的职位,本身是加官、差遣官,充任者多为诸大夫,所以司隶校尉常常自称“奉使命大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东汉继承了这一郎官、大夫制度。
二是以文学侍从参政。汉武帝猜忌丞相,建立了辅助他决策的内朝制度、内辅制度。这一时期内辅主要是以下五类官员: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大司马、将军;尚书系统;加左右曹、诸吏等衔者;加侍中、给事中等衔的文学内侍之士。一些文学才智之士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参议要政,制衡官僚体系。其身份多为郎官、大夫等,如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词》,武帝甚悦之,拜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武帝筑朔方,丞相公孙弘谏,以为罢敝中国,武帝使买臣难诎公孙弘。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迁侍中、中郎,后为光禄大夫、侍中。主父偃:上书言世务,拜为郎中;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这开启了后世宰相成员、内辅成员、中央核心决策成员多以文学之士充任的先河。其中很多人又曾得到重用,所以这也是古代储才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是大夫作为内朝官,参与政事。从武帝开始,西汉尚书机构具备内辅职能,领(平、视)尚书事者地位至为重要,号称“冢宰”。在周代,“冢宰”即为内朝首领。而西汉的诸大夫是内朝官的一个重要来源。成帝时,谷永上书赞誉曾领尚书事的光禄大夫郑宽中“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4]以诸大夫领(平)尚书事者,还有于定国、周堪、孔光等。如周堪为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共领尚书事。所以,大夫制度也成为西汉储才制度的重要内容,况且上述人中又有很多后来位至三公,如于定国、孔光、张禹等。
(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这一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由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命陈群制定,至隋唐科举制确立,存在了约四百年之久。它规定由各州郡分别推选一位在中央任职且德名俱高者为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将人才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分别品第,并加评语,呈交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快,受人尊重;相对地,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
这一时期是士族政治,士族也称世族、势族、素族等,相对于寒族、庶族。《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论述魏晋以后的姓族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5]士族享有在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相对于庶族的优越地位,这一切又源自九品中正制。如琅琊王氏成员王骞“不狎当世,尝从容谓诸子曰,吾家门户,所谓素族,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6]王僧达自豪地对宋武帝说:“亡父亡祖,司徒司空。”[7]
九品中正制使得门阀世族把持官吏选拔权,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越来越成为主要标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8]的不公平局面。
二、唐代的储才制度——翰林学士号称“内相”
(一)学士制度的流变
唐代最早有秦府十八学士。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9]又有弘文馆学士。武德九年(626年),登基后的李世民“置弘文馆于(弘文)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10]这成为李世民重要的储才基地。北门学士则为高宗、武则天时所置。弘文馆学士刘祎之“与(著作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至朝廷疑议表疏,皆密使参处,以分宰相权”。[11]武则天时,有胡楚宾等著名的北门五学士。他们后来有的成为三、四品高官,范履冰、刘祎之还做到过宰相。
玄宗开元六年(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二年(724年)在东都洛阳设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集贤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等,聚集文学之士修书、侍讲,以宰相一人为掌院学士,如张说。玄宗初又置“翰林待诏”,选任张说、陆坚、张九龄等,因中书省政务繁剧,文书多壅滞,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后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翰林学士,“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12]属于加官、差遣官。
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专门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称为“知制诰”。诰命分为两制:内制和外制。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等大政,皆用白麻,称为内制、内命;外制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用黄麻。内制重于外制,不经中书门下而直接下传,翰林院成为设置于内廷的正式中央核心决策机构、内辅机构。发展到唐后期,两制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翰林学士号称“内相”“天子私人”,参决军政机密,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尤其是翰林承旨学士,元稹说:“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13]
翰林院成为唐代最重要的储才基地,翰林学士多升为宰相。德宗至懿宗的154名翰林学士中,至宰相者有53名。宪宗时,裴垍为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垍,垍小心敬慎,甚称中旨”,[14]后拜相。乾符元年(874年),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守本官同平章事。又,白敏中、路岩都是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二)翰林学士与“八隽”之途
唐代封演曾列举唐人官至宰相的“八隽”之途:“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隽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隽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15]“畿尉,”与“不入”之间,似应有“赤尉”或“畿令”“赤令”这样的脱文。
封演的意思是说,进士按照校书、畿尉、监察御史、拾遗、员外郎、中书舍人、中书侍郎的次序逐步晋升,再按照唐代惯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即可成为宰相,这是最快最好的宰相成长途径,中间不必再经历制策、正字、赤尉(或畿令、赤令)、殿中丞、补阙、郎中、给事中、中书令这样的分别对应于校书、畿尉等来说官职性质相近而级别更高的岗位。而“八隽”中的校书、监察御史、拾遗、员外郎、中书舍人等,都具备加翰林学士之衔的资格;事实上,也唯有加翰林学士头衔,他们成长为宰相等高级文官的可能性才更大。
所以谈及唐代储才制度、宰相培养制度,说“八隽”之途与说翰林制度并不矛盾,二者有密切关系;熟悉文献,熟悉监察,有京畿地方基层工作经验,熟悉草诏,涉及机密,是唐代宰相等高级文官成长的正途。这体现出唐代储才制度、宰相等高级文官培养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特色。历史上严格遵循“八隽”之途的唐代宰相很少,但“八隽”之途确实能大体概括唐代宰相的成长路径,而且与这八个岗位复合越多,成长为宰相的可能性越大,路径越便捷。如,陆贽,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迁监察御史。为翰林学士。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为中书舍人。以权知兵部侍郎复为学士。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擢进士第,以宏辞补校书郎。举贤良方正异等,调河阴尉。迁监察御史,出为河南功曹参军。武元衡帅西川,表掌节度府书记。召为起居舍人。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进御史中丞。进兼刑部侍郎。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三、宋代储才制度——“重侍从以储将相”
(一)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
馆职帖职、侍从两制制度是宋代宰执等高级人才培育制度中的重要内容。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官员号称“清华”,是宰执团队的后备军,馆阁、翰林院是宰执团队的储才基地。
宋代把馆职纳入职官之列。馆职是指馆阁之职,作为文官的兼职加衔时称为帖职或职名、职,实则包括史馆、昭文馆、集贤院(集贤殿书院)、崇文院、秘阁以及秘书省这样的馆、阁、院、省、殿的一些官职。《宋史·职官志》说:“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16]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其中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
馆职主要有三类:一是诸阁学士,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二是三馆秘阁之职,有昭文馆大学士、直昭文馆;监修国史、史馆修撰、直史馆、史馆检讨、史馆编修;集贤殿大学士、学士、修撰,直集贤院、集贤校理;直秘阁、秘阁校理等。三是诸殿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宣和殿(保和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等。
宋代有两制、侍从之称谓。欧阳修说:“翰林学士谓之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谓之外制。今并杂学士、待制,通谓之两制。”[17]“杂学士”是相对于翰林学士而言的馆职中的诸阁学士、直学士等。这样,宋代与唐代对于“两制”的理解有所不同,宋代两制是内外制与馆职中待制以上至学士、大学士的合称,品级为四品及以上。而侍从通常也是四品及以上者,主要包括翰林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以及馆职中待制以上者。又有小侍从之谓,即六、七品的起居郎,起居舍人,司谏,正言。可见,两制、侍从所包含的范围不尽相同,侍从的范围更大一些,宋代常通而称之,有时合称为侍从两制,有时单称侍从或两制。号称“两府”的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宰相、执政合称宰执,宰执、侍从两制外的,则称为“庶僚”“庶官”,严格区别。
(二)馆职与侍从两制的培养——“论思献纳”“主天下之士”“镇抚一路”与宰执后 备军
馆职、侍从两制担负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一是“论思献纳”,辅助皇帝决策,发挥重要的内辅职能,包括与议要政、制度,参与理狱等。据《宋史》,“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18]二是负责考核、荐举。宋“以两制为贤,使主天下之士”。[19]太宗听政之暇,每取两省、两制清望官名籍,择其有德誉者,悉令举官。熙宁四年(1071年),神宗诏令京东等五路先置学官,允许布衣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令两制、两省(中书门下)、馆阁、台谏臣僚荐举。三是出任一些特殊、重要岗位。一些官职如重要地方的转运使(漕臣)、制置使(帅臣)等,人选都有严格范围,而两制就在其中。四是成为宰执团队的后备军。宋代“重侍从以储将相”,[20]馆阁、侍从两制是宰执团队的主要来源。欧阳修说:“臣窃以馆阁之职,号为育材之地。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然则馆阁,辅相养材之地也。……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也。……自陛下即位以来,所用两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于馆阁,此其验也。”[21]
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三司使、御史中丞得以“四入头”,在四岗位中多岗经历,这是宋代储才制度、宰执培养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洪迈说:“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22]“四入头”,是指这四类官员进拜宰执的可能性最大,最容易进入升任宰执时的草诏“词头”。据统计,宋翰林学士总计419人,位至宰执者约占一半。北宋前期,翰林学士为差遣官,无品级。元丰改制后,定为正三品,“职始显贵”。他们通过顾问、草诏等方式参与重大决策。翰林学士多有兼职与差遣,最多、最主要的兼任是御史中丞、知开封府事、三司使,这有利于保障宰执后备军的多岗位锻炼,增长才干。北宋三司使89人中有22人由三司使直接升为宰执。两宋“四入头”情况很多,如宝元元年(1038年),李若谷自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除参知政事。王博文自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加龙图阁直学士,除同知枢密院事。张观自给事中、权御史中丞除同知枢密院事。
(三)“试而后命”“老练民事”与“优待侍从”——宋代储才制度的主要特色
宋代得馆职者须是进士出身。洪迈说:“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23]与明清翰林从新考中的进士中直接选任不同,宋代是先让进士从事实际工作,再参加制科考试,选拔充任馆职,由馆职拔擢为两制,再从两制中选任要员、宰执。因此,许多宋代名臣、宰执的仕途路径是“进士—基层官员—馆职—两制—名臣、宰执”。如司马光,仁宗宝元初进士,任签苏州判官事等,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加集贤校理,通判并州。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英宗时,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又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后任执政、宰相。元祐元年(1086年),任命起居舍人曾肇为中书舍人,跻身两制侍从,侍御史王岩叟连上八章反对说:“祖宗以来,擢用大臣,须取老练民事之人,未尝轻进一全不经历亲民者为侍从。”[24]
因此,馆职帖职、侍从两制地位崇高,身份特殊,号称“优待”。洪迈总结说:“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25]
(四)宋代储才制度的评价
把宋代储才制度放在整个古代社会中看,应该是最具理性、最有优点的。注重文学与儒学修养,开放与公平,注重实践锻炼,崇高其位以砥砺名节,是宋代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制度、储才制度的特色所在。宋代严格限制宗室、外戚任侍从两制,人才储备培养具有开放性、公平性,以考试取材,打破了贵族垄断,破除了任用亲近的弊端,提高了社会流动性。
在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馆职帖职、侍从两制的制度安排,正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由此,不仅使文人士大夫享有了崇高的荣誉感,培养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还便利其增加阅历、增长才干,更使得人才培育较为制度化、规范化,有利于塑造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可以对君主权力形成一定制衡作用的儒生士大夫共同体,而这正是宋代治理流光溢彩的制度保证。
四、元、明、清代储才制度
(一)元代储才制度——“为将为相者,皆跟脚人”
元代选拔官员的途径,主要有吏员入仕、宿卫出职、承袭或承荫等,宰执多由皇帝禁卫怯薛出身的蒙古、色目勋贵出任。元代中期的姚燧说:“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26]怯薛,蒙语轮番宿卫之意,称为“大跟脚”。元末明初的权衡说,元朝“取士用人,惟论跟脚。……其所与图大政、为将为相者,皆跟脚人也。”[27]尽管自仁宗朝开始科举取士,但由此入仕并重用的比重很小。
怯薛宿卫分为四部分,号称四怯薛,每三日而一更,由木华黎等四家族世袭分掌。大汗、皇帝与怯薛形成了主从领属关系,终身不得变更,怯薛虽有遭严惩者,其家族亦能世袭其职,所谓“近侍多世勋子孙”。成吉思汗时,组建万人怯薛,兼宫廷服侍、行政差遣等。作为“近幸”,怯薛充任皇帝的“耳目”“爪牙”“心脋”“倚纳”, 能“不次擢官”,是将相重臣的主要来源,并且利用日常接近皇帝的便利,随时参与最高决策。即使做了大官,其怯薛的身份并没有改变,昼出治事,夜入番直。
怯薛制度的存在,部族制度的影响,使得元代宰相实际权力与地位不如唐宋。唐宋大部分诏令由宰相负责撰拟,他们如果以为不当,可以拒绝,有封缴、封还词头之权;翰林学士也是如此。但元代宰相违抗皇帝旨意的事例很少。总的来说,怯薛制度是蒙古旧俗给元朝带来的一份深重的政治遗产,使得元朝与其他朝代的储才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的落后性、简陋性。
(二)明代储才制度——“非翰林不入内阁”
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28]翰林院职官主要有: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另有由进士选拔出来的庶吉士。
永乐朝选拔解缙等七位翰林官并值文渊阁,这是明代内阁政治的开端,也是阁臣与翰林密切关系的开端。明内阁逐渐成为中央核心决策机构、内辅机构,内阁大学士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宰相的作用。大学士绝大部分出自翰林,翰林院成为进入内阁的最重要的储才基地,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29]内阁大学士出身翰林者约十分之九。
自宪宗成化后,就连六部长官也定例出身、兼任翰林官,“其在六部,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其由翰林者,尚书则兼学士,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30]
翰林官或直接选拔为阁臣,或由翰林出任部院之职后再选拔为阁臣。由翰林官直接入阁者仅16人,仅接近10%;由部院卿贰入阁者131人,比例约80%,即“入阁多为卿贰”。内阁大学士多数走的是由进士到翰林到内阁,或者是由进士到翰林到部院卿贰再到内阁之路,绝少有地方工作经验。大学士有地方工作经历的不到30人,比例不到20%,其中崇祯朝就有11人。至于从地方岗位直接入阁者,更是极少。如高拱,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进士,选为庶吉士。逾年,授编修。裕王(后为穆宗)出阁请读,高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累迁侍讲学士。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擢礼部左侍郎,不久改吏部,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府事。晋礼部尚书。四十五年(1566年),拜文渊阁大学士。这与唐宋宰相宰执团队、内辅团队、中央核心决策团队成员中很多人具有地方工作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
庶吉士是阁臣的后备军,明代重视对庶吉士的培养,提倡务实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弘治时,大学士徐溥请先将新进士分拨各衙门观政,然后由内阁会同吏、礼二部考选为庶吉士,孝宗从之。隆庆时,阁臣高拱提出“辅臣(阁臣)之学”的概念,认为辅臣皆出翰林,而教庶吉士的课程却主要是诗文,他强调庶吉士要练习平章国政。嘉靖以后,不少人认为内阁是“政事根本”,不可专用翰林,宜与外僚参用。
(三)清储才制度——“本朝宰辅,必由翰林官”
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清代高级官员8 451名,其中庶吉士出身者2 470人,占高级官员总数的约30%,比例大大低于明朝。但是,翰林仍在清朝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翰林院仍是储养人才之所,以翰林为清品,“宰辅多由此选,其馀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31]龚自珍说:“本朝宰辅,必由翰林官;卿贰及封圻大吏,由翰林者大半。”[32]翰林官升转较速,“迁调异他官”。
清代政治精英成长最快的途径如下: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前三名分别授予翰林编修、修撰、检讨,其余的为庶吉士,不入翰林院的,任知县或部院主事等。庶吉士三年散馆后,优秀的留在翰林院任编修、修撰、检讨,次等的任御史、给事中、知县或主事等。前者在翰林院或詹事府系列升品级,如侍读、侍讲,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左、右春坊大学士等。编修、修撰及以上翰詹官有机会主持某省乡试或做某省学政,这是差遣,算是从事实际工作与地方实务锻炼,然后升任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同时一般兼任礼部侍郎,这就成为了“卿贰”,有了资格平级调任巡抚,或成为军机大臣。
如曾国藩,道光十八年(1838年),成进士,选为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同年补授翰林院侍讲,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转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任会试同考官。同年,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转左庶子,又升侍讲学士。年底,充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同年,署兵部左侍郎。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至卿贰。李鸿藻,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同治元年(1862年),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同治四年(1865年),为军机大臣。
可见清代高级政治人才的培养,与明朝类似,也不要求有太多的实务经历与基层经历,这在制度设计上,明显不如唐宋的注重基层阅历与地方经验。
五、小结——以加官、差遣打造中央核心决策体制的人才制度基础
古代的宰相体制、内辅体制、中央核心决策体制多有团队型、扁平化和统筹性特征。品秩、官位较高的官员未必是最具辅佐能力者,因为官僚体系遵循的多是资历原则,最高统治者可根据需要灵活地从官僚体系中抽调一些他认为合适的精英组成宰相团队、内辅团队,使其动态化,这样的团队多为差遣型,无定额编制,无机构品级,属于临时性团队,体现出现代管理学意义上团队型组织的进出开放、动态等许多重要特征,这样有利于达到管理的扁平化,提高决策、管理水平。
加官制度、差遣制度是构建内辅体制的重要路径。加官,即在起初设置的正常官僚体制中所没有的官职,属于临时头衔,多数属于差遣性质。加官、差遣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宰相、内辅、中央核心决策体系的构建也是如此。在西汉,如侍中、左右曹、诸吏、给事中以及大司马、领(平、视)尚书事等;在东汉是录尚书事;在隋朝,如“参预朝政”“参掌机密”等;在唐朝,主要是加上宰相头衔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者,以及翰林学士;在宋朝,主要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翰林学士(元丰改制前);在明代,主要是内阁大学士;在清朝,主要是军机大臣。
由于职责原因,宰相、内辅、中央核心决策体制成员多需要具有文学、文化和管理方面的优势;而储才制度正是这类体制构建的重要基础。以唐、宋、明、清几个朝代为例,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翰林储才团队,成为内辅体制源源不断、生机勃勃的储备力量。
这类体制对层级制组织不可避免的僵化、隔阂、低效等弊端具有补救、矫正的作用,所体现的团队型、扁平化、统筹性管理理念,是与当下的新型组织理论高度吻合的。近几十年来,知识经济等世界潮流的出现,使得以计划和控制为核心职能的传统层级组织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知识社会产生了许多新的理念,如扁平化、统筹、参与、共享、合作、信任和学习等,学习型组织、扁平化组织、网络组织、有机—适应性组织、倒金字塔组织等新型组织理论,开始对传统的层级制组织存在的弊端进行一些补救、矫正,逐渐成为主流的组织理论。
所以说,古代良好的储才制度是以加官、差遣方式打造中央核心决策体制的基础,这是古代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一大特色与成就,值得予以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