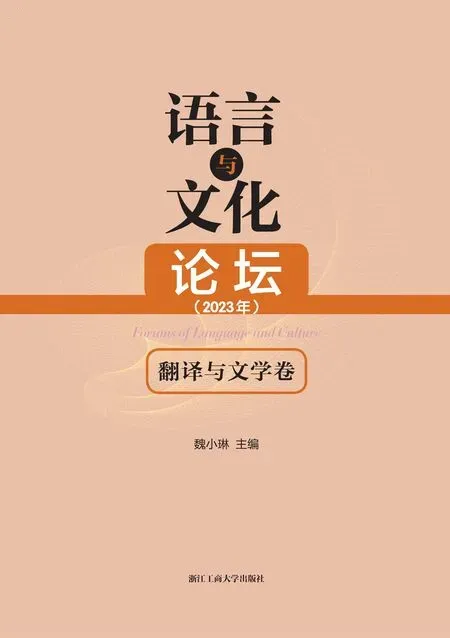论飞白译诗中破折号的功能
高淑贤
1. 引言
翻译家飞白一生寝馈于世界诗歌,先后翻译出版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古罗马诗选》等近30本译著,涉及语种多达15种,其“诗歌翻译的数量和质量目前在国内首屈一指”(飞白 等,2012),可以说是继朱湘之后我国又一位多语种译诗的大家。但多语种这一优势却同时在无形之中铸成了一堵语言高墙,使研究者心生畏惧,甚至敬而远之。可能是出于这一客观原因,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译诗大家,学界对飞白的研究相对薄弱。从现有较为有限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聚焦于文字层面,重在探讨文字意义的转换与生成,如区鉷和蒲度戎(2005)、张德明(2008)和龙艳(2016)等。对译诗文字内容的解读与批评固然是飞白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探究译者的翻译艺术具有积极意义,但对文字的关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研究者大多忽略了飞白译诗中的标点符号。标点符号看似游离于文字之外,属于形式信息,实际上却是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蕴涵着一些文字所无法包含的独立的意义”(谢天振,2013)。标点符号这种寄意义于形式之中的特点自然不会被“非常重视外在形式”(飞白 等,2012)的飞白所忽视。阅读飞白的译诗,确实可以发现他往往基于不同的语境需求,创造性地选用不同的标点符号来凸显原诗,促进理解,传递美感。
而在飞白创造性运用的众多标点中,最具特色的便是破折号。翻看两卷本《诗海》,会发现有大量破折号点缀其间,且这些破折号中有不少并非对原诗标点的“亦步亦趋”,而是属于译者的创造性增译。王宏印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评论飞白译诗中增加的一处破折号时,他直言“前一句末的破折号,似乎也加得无由”(王宏印,2004)。这一评论虽只是就某一个例而言,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飞白对破折号的“偏爱”以及部分读者对其译诗中破折号添加是否适度的质疑。本文受王宏印先生启发,斗胆接着前辈的话题继续往下说,就飞白译诗中破折号的用法展开较为细致全面的探讨,并尝试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飞白译诗中的部分破折号是否真的有“无由”之嫌?如若不是,那么这些散布在不同诗歌中的小小标记有何深层意味?这些破折号对读者理解飞白的译诗文本乃至其翻译观又有什么帮助?循着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飞白的代表性译著《诗海》(2卷)中的破折号数量进行统计,并结合具体译例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2. 飞白译诗中破折号的高频使用
本节选取飞白的《诗海》中的英语诗歌作为统计的数据来源。之所以选择这2卷译著,主要有以下2点考虑:首先,《诗海》体制宏大,内容覆盖全面,涉及不同时代、风格各异的诗人诗作,以其中的译诗作为语料,能够较大程度地避免样本容量过小导致的数据偏差。其次,《诗海》质量上乘,作为飞白的代表性译著,其中的译诗能够较好地反映飞白的译诗特色与水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诗海》中共计收录外国诗歌500首,其中英语诗歌171首。经统计,我们发现这171首英语原诗中,共有破折号280个,相对应的汉语译诗中破折号共261个。从这一数据来看,似乎飞白在英诗汉译时并未对破折号格外青睐,甚至还对原诗中的破折号进行了部分删减。但若考虑到英汉双语中破折号的整体使用情况,就不难透过表层看出问题的实质,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关于英汉双语中破折号的使用差异,多位学者已有过论述。如袁影(2003)以16本中英著作的序言为语料,对英汉双语中各类标点的使用进行统计,发现使用频率差异“最为悬殊的标点是破折号与分号”。具体而言,英语著作中破折号数量为19个,而汉语中仅为1个,差别高达19倍,可见英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汉语。王大伟和魏清光(2005)及曾曾(2012)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由此可见,虽然译诗中破折号数量略少于原诗,但仍然可以看出飞白在汉语诗学对破折号“不甚友好”的大背景下,竭力在自己的译诗中为其争取一席之地的主观努力。
如果再考虑到极端数据对数据平均值代表性的削弱作用,这种主观努力则更加明显。纳入统计的171首诗中,仅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乌鸦》(TheRaven)一首诗中,英汉破折号使用差额就高达23次(原诗中破折号出现40次,译诗中为17次)。如果按照统计学原则将这一极端数据剔除,则英语原诗中破折号出现次数为240次,译诗中为244次,高于原诗。飞白译诗中破折号的高频使用还可以从对具体诗歌中破折号处理方式的统计中得到佐证。171首诗歌中,译诗中破折号数目与原诗持平的有110首,占比64.33%,比原诗有所增加的共37首,占比21.64%,较原诗略有减少的共24首,占比14.03%。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飞白在译诗时对破折号的偏爱。
那么飞白使用如此多的破折号用意何在呢?读者又该如何去解读这些破折号?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对译诗中破折号的用法展开分析。兰宾汉(2002)在《如何使用标点符号》中将破折号的用法归结为11项,包括表示注释、引出补充说明或插说的内容、语义转折、声音的延长、停顿或中断等。如前所述,飞白译诗里的破折号中,有一半以上属于与原诗求同的案例,对此本文将不再一一论述。本文重点关注的是飞白译诗中增译的破折号。
3. 飞白译诗中破折号的功能
通过对原诗与译诗进行对照比读,我们发现,在飞白的译诗中,破折号的增译主要用于体现诗歌结构、提示逻辑连接和传递诗歌美感,下文将逐一展开论述。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相对明确的分类更多是出于叙述方便的考虑。实际上,译诗中的破折号的作用不大可能非此即彼,泾渭分明,而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细微的重合。
3.1 彰显语法结构、透视原诗形式
受语言结构及诗学的影响,英语诗歌常以行为单位,这一特点使得诗歌创作容易受到诗行长度的限制。与此同时,英语的形合特点又为诗人们通过诸如从句、连词等语法手段将上下诗行贯通,从而规避诗行长度限制提供了便利,因此跨行便成为英语诗歌,尤其是英语现代诗歌中颇为显著的外在特征。作为一种重要的形式特征,英语诗歌中的跨行并非随意而为,而是负载了一定的语义,与突显意象、创造节奏、营构张力、表达情感等密切相关。即便形式上出现了跨行,诗情仍然可以从此句流转到彼句,即朱湘所谓的“行断意不断”(1936)。飞白在论述跨行时,也提到了跨行可以使意义、语法等无停顿地跨越到下一行这一特点(1989a)。
由此看来,英诗中由语法连接的跨行本身即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客观存在,具有语义荷载,在译诗中对其进行忠实呈现颇有必要,并且飞白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汉语作为典型的意合型语言,连接手段相对贫乏,常常以意义相对完整的句作为成诗单位。如何在译诗中体现英语诗歌中独特的跨行形式,同时将上下行一气呵成的意义呈现给译入语读者就成为摆在译者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这个问题,飞白的解决之道就在于破折号的巧妙使用。如:
例①
原文:And dreaming through the twilight
That doth not rise nor set(Rossetti,2008)22
译文:我将在薄暮中做梦——
这薄暮不升也不降(1)除例⑤中的译文二之外,本文中其他译文的来源包括以下文献:《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诗海——世界诗歌史纲·现代卷》《哈代诗选:英汉对照》。译者皆为飞白,正文中将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原诗中上下两行由定语从句中的“that”连接,以此实现意义贯通,属于跨行中的“行断意不断”。而在译诗中,为了实现上下文语义的连贯与节奏的衔接,飞白采用了“双保险”:首先是重复了“薄暮”,将语义贯通,其次便是利用破折号,从形态上标示上下行的联系。如前文所述,王宏印在评论这2句诗时认为破折号并无必要。单就这一个案而言,考虑到“薄幕”的重复已经提示读者上下行语义的连贯,这一评论确实有其合理性。但若考虑到诗歌翻译的目的并非单纯的语义传递,而是对展示诗艺具有一定的要求,同时结合飞白为了逼近原诗形式而“保留大量英语句法”(飞白,2016)28的译诗特点,仔细考察他对英诗中跨行的处理模式,恐怕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这个立场出发,便不难发现此处破折号的另一层深意,即提示原诗中的语法和空间切断,以透视原诗的诗艺形式。又如:
例②
原文:Fruit can not drop
through this thick air (飞白,1989c)
译文:连果子都落不下来——
穿不透这稠密的空气
上例选自希尔达·杜立特尔(Hilda Doolittle)的《花园》(TheGarden)。原诗以触觉描写夏日傍晚闷热之感觉:弥漫于空气之中的闷热如此稠密以至于连果子都被热浪托举着无法掉落。这一新奇的夸张描写虽违反物理规律却具有心理真实性,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是原诗艺术特色的重要表现。这种效果之所以能够产生,除了诗人的想象力之外,原诗中的跨行也为其增色不少。原诗在drop through之间分行,drop之后的戛然而止正好呼应了果子被托住无法掉下的停顿。为再现原诗跨行的这种效果,译诗中飞白在第一行后增译破折号。若仅就文字意义而言,这一做法似乎并无必要。但若就原诗的艺术形式而言,破折号在视觉上对读者形成了直接的感官冲击,强化了果子掉落的空间感与画面感,同时也体现了原诗的诗艺特色。飞白译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③
原文:In you resides my single power
Of sweet continuance here(Hardy,1979)56
译文:你身上寄托着我唯一的权利——
使我得到甜蜜的继续
例④
原文:What I viewed there once, what I view again
Where the physic bottles stand (Browning,1979)
译文:我从前见到的,如今又在眼前——
瞧这排药瓶在桌子边
以上2例分别来自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她的永生》(HerImmortality)和罗伯特·勃朗宁( (Robert Browning)的《忏悔》(Confession)。在这些译例中,飞白都增译了破折号以提示原诗中的跨行,使原诗的结构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究其原因,当然不排除飞白在客观上受到了“源语透过效应”的部分影响。但从上文中飞白对跨行意义以及英语句法的强调来看,译者的主观追求仍然不可忽视。刘军平(2003)在论及飞白的译诗时,曾提到他对译诗中的语音这一外在形式的巧妙运用。可见,对于形式之于诗歌的诗学价值,飞白了然于心。余光中(1989)在论及中西诗歌异同时,曾表示汉诗的音乐效果接近于“断音”,而英诗则类似于“滑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视破折号为译者再现英诗这种滑动效果的尝试,这种处理体现出飞白尝试突破汉语诗学限制的努力以及对传递原诗形式的重视,而这种重视则进一步显现了他强烈的原著意识与异化倾向。这与飞白一直标举的译者应该“逼近原作的形式”,努力显现原诗的诗艺样式或个性风格,而不应该将其遮蔽或过滤掉的译诗理念一脉相承。
3.2 提示逻辑连接,助力读者理解
如上文所述,飞白译诗时有强烈的原著意识和异化倾向,这种译诗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译诗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如曾有学者表示“飞译(指飞译作,笔者注)的风格则因其严谨而在多数专业人士(包括外语工作者和诗歌创作人员)中拥有一定市场”(张跃军,1998),似乎也暗示了飞白的译诗在普通读者中接受的限度。事实上,飞白确实对译者为迁就读者而过度归化或阐释的倾向持谨慎态度。他反对译者视读者为“需要抱的三岁娃娃”,主张读者扔掉文化拐杖,为此“群众的口味必须逐渐提高和适应”(飞白,2016)18。可见,上述对飞白译诗的读者接受的观点确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飞白不关心读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飞白最为推崇的西方译论家之一,但对于本雅明译诗只考虑原诗,无须顾及读者的观点,飞白并不认同。他认为,本雅明的译论主要针对欧洲国家,涉及语种多限于印欧语系之内,源语和译入语亲缘关系较近,读者接受难度也相对较小,这一优势使其“无视读者”的主张成为可能,但这在分属不同语系的汉英之间则不大可能实现(飞白,2016)117。可见在读者接受的问题上,飞白对本雅明极端的观点还是有所修正的。正是因为考虑到汉英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虽总体上倾向于作者/原诗,但飞白仍然提出翻译要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脚踩两只船”的主张,以达到“让中国读者基本上听得懂”(飞白 等,2012)的效果。
但飞白让读者“基本上听得懂”的方法却多少有些别致。不同于部分译者倚重归化,甚至牺牲原诗风格的做法,飞白更多采取了添加赏析、评论等“附翻译”手段“旁敲侧击”地通过外围路径让诗歌接近读者,借助标点符号的凸显或逻辑连接作用,助力读者理解诗歌,这也是飞白这一别样的读者关怀的表现方式之一。如:
例⑤
原文:It goes, like murky bird or buccaneer
That shapes its lawless figure on the main(Hardy,1979)12
译文一:这念头多么像不祥之鸟或海盗——
逍遥法外的身影在海上漂游
译文二:这念头如不祥之鸟隐于溟蒙,
像海盗出没于大洋无法无天(哈代,2018)
例⑤选自哈代的《向逆境中的友人坦承》(AConfessiontoaFriendinTrouble)。原诗中将“念头”比喻为“不祥之鸟”或“海盗”,二者同时作为“that”的先行词,并共同作为“海上漂游”这一动作的施动者,上下两行之间具有语义上的承递关系。而译文二将上下两行并列起来,导致“出没于大洋”的施动者只有海盗,“不祥之鸟”则缺少了谓语,无奈之下只能添加“隐于溟蒙”,使得译诗意义与原诗似有不符。原诗的语法本身并非特别复杂,但“海上漂游”这一动作的双主语结构在翻译时却很容易被忽略,译文二的问题即在于此。对双语精通的译者尚且会出现此种理解问题,更遑论对英文不甚精通甚至是一窍不通的读者。在译文一中,通过增译破折号,飞白将两行贯通,既彰显了原诗的结构,同时又提示了读者上下行语义上的连贯,从而帮助读者避免了理解层面的模糊之处。
例⑥
原文:Made fast therewith her hands, drew down her eyes,
Deep as deep flowers and dreamy like dim skies (飞白,1989b)
译文:用发缚住她双手,牵住她眼光——
像花那么深,像薄暮那么迷茫
例⑦
原文:Is such the stellar gauge of earthly show,
Nation at war with nation, brains that teem(Hardy,1979)116
译文:难道天尺一寸,就量尽人间活剧——
列国的厮杀争战,思潮哲人的涌现
例⑥和例⑦分别来自阿尔杰农·斯温本(Algernon Swinburne)的《回旋曲》(Rondel)和哈代的《观月食》(AtaLunarEclipse)。2个例子中破折号的用法颇为相似。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上述译例中的第二行诗句与第一行之间均存在语义上的包孕关系。具体而言,例⑥中眼光的特点是“像花那么深,像薄暮那么迷茫”,而例⑦中“人间活剧”的内容则是列国厮杀和哲人涌现。破折号在这两处均起到了逻辑连接的作用,相当于在两行的叙述中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引导读者感受上下行之间的包孕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理解诗歌提供了某种辅助。以例⑥为例,若去掉破折号,读者可能无法将薄暮的特质与眼光的特点相联系,从而导致理解的困境或偏差。尤其是考虑到飞白译诗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语的普及率远不及当下,多数读者无法通过对照英汉双语来进行理解,飞白这一做法的现实意义便更加凸显。
其实,破折号并非飞白用来辅助读者理解的唯一标点符号。阅读飞白的译诗,会发现他在处理具有隐喻性质的抽象名词时,常常借助引号将其凸显,以帮助读者理解。例如,在处理哈代的《以后》(Afterwards)中的诗句“When the Present has latched its postern behind my tremulous stay”时,飞白就为原诗中首字母大写的Present添加了引号,将全句译为“当‘现在’在我不安的逗留告终时闩上了后门”,以提示读者原诗中“现在”的修辞意味。可见,这种利用标点来助力理解的外围做法确实是译者有意为之。
飞白这种借助标点来提示逻辑,进而辅助读者理解的做法体现了译者在保存原诗风姿与追求读者接受之间保持平衡的努力。厘清这一点,能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飞白的读者观,也能有效避免将译者丰富辩证的译诗观单一化、简单化的倾向。另外,若考虑到以意合为特点的汉语较少使用破折号等形式标记来体现语言逻辑性的特点,飞白的这种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也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表达形式。
3.3 描摹形貌动态、传递诗歌之美
飞白译诗主张从诗自身出发,注重从多方面感受诗歌。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明确提出了“诗感”的概念,并指出之所以提出“诗感”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说明“译诗过程不能局限于认识作用,还必须包括情感作用和美感作用”(飞白,1984),他所标举的“风格译”更是以实现诗歌的审美价值为宗旨。由此看来,在译诗中传递美学因子,激发读者的审美想象应该是飞白译诗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他具体又是通过何种手段来实现审美效果的传递的呢?
我们认为,对破折号,准确地说,对破折号的形貌修辞作用的利用是飞白传递诗歌之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我国,关于形貌修辞的论述滥觞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省联边”与“调单复”之说(周振甫,1995),后经陈望道(1997)进一步发掘,用以指借助“附着在文字形体上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的问题”。这之后曹石珠(1996)进一步将形貌修辞细化为字形、图符、排列和标点4类。作为4类形貌修辞之一——标点修辞就是“通过标点符号的特殊运用(如省略、叠用、不规范使用等)来增强作品视觉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冯全功,2015)。
飞白译诗中部分破折号的使用便属于上述超常规的特殊运用。当然,必须承认,飞白本人也许并没有对形貌修辞有过深入了解,甚至有可能从未接触过这一概念,但他的古典文论造诣颇深,并且从他的一些译诗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其将意义与形式紧密结合,尤其注重形式背后之意味的译诗观。如译诗应该以“形神兼顾,体现风格”为最高标准,甚至还明确表示译诗应“注意原诗整个‘显现意味的样式’”(飞白 等,2012)。而从上文的梳理来看,形貌修辞关注的正是形式对意义表达的作用,与飞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认为,飞白虽没有用“形貌修辞”这一术语,但其意识中却不乏视觉形式与意义之间联结的敏感度。这种敏感度在译文中的表现之一便是利用破折号的形貌修辞功能来使译诗呈现出动态之美。
例⑧
原文:The Winter evening settles down
With smell of steaks in passageways(Eliot,1963)
译文:冬天的黄昏沉淀下来——
带着烤牛排味儿沉在走廊里
例⑨
原文:And find, in me alone, a feeble spark
Dying amid the dark(Hardy,1979)143
译文:只在我心中有一颗火星摇曳——
在黑暗中渐渐熄灭
例⑧选自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序曲》(Preludes)。原诗描写黄昏之际,暮色逐渐笼罩,白昼如同所剩无几的烟头将尽未尽时诗人的感受。从诗歌意象力的角度来看,原诗中的settles down指向是向下的,“往往伴随着消沉、沉静、悲伤、颓丧的情感”(耿建华,2010),与诗中暮色越压越沉的情景相应和。执着于感受诗歌的飞白显然注意到了原诗中意象力的这种审美效果,连用了“沉”和“下”来表示低沉的感觉,但对要求无限“逼近原诗”的译者来说,仅仅靠文字的力量似乎还不足以传达他对原诗的感受,于是便借助了标点符号的形貌修辞作用。例⑧中译者通过增译破折号,似乎将“沉淀下来”这一动作向下拉长,将暮色降临的沉重与黄昏时分光影的流转变化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经验直感和官能冲击,读者似乎也被带入了那个萧瑟的冬日午后,被那份“沉重”压得无法喘息。
类似的还有例⑨ 。哈代在这首《他的永生》(HisImmortality)中描写了主人公去世后的4个不同阶段,慨叹时间对人情之啃噬。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友心中死者的形象渐渐黯淡,直到仅剩一颗微小的火星,在黑暗中若明若暗,然后熄灭。原诗中的名词性短语a feeble spark偏向静态描绘。而译诗中飞白则化静为动,根据“火星”光线弱小、飘忽不定的外形特点,用“摇曳”来传达其动感,准确捕捉了火星闪烁之情态。不仅如此,他还利用破折号的形貌修辞功能,生动演绎了黑暗中火苗由明到暗再到更暗的过程,同时呼应了人心中情感由强到弱再到更弱的动态渐变,大大强化了读者的视觉等感官感受,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审美想象。
原文:Loitered beneath the gas lamps’ flare,
With lips of flame and heart of stone(Wilde,1997)
译文:她还在煤气街灯下留连,——
火焰的嘴唇,石头的心。
上例选自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晨的印象》(Impressiondumatin)。飞白认为,这首诗是王尔德受到莫奈《日出·印象》的启发而作。在诗中,王尔德将背景从塞纳河口移至泰晤士河上,以文字颜料为读者描摹了一幅雾气蒙蒙、影影绰绰的晨雾图。按照莱辛(1984)的观点,诗歌优于画作的地方正在于对动态的传递。在原诗中,王尔德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在最后一节描绘了一位女子在灯下徘徊的场景,为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根据《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Loiter意为停下或无目的地来回走动,表示持续性的动态过程。译诗中除了选用意义相近的“留连”之外,还通过破折号的增译,从形态上模拟了女子踟蹰徘徊,犹疑不前的样子,增强了译诗的表现力。另外,从音韵的角度来看,双声词“留连”正好对应了原诗中的loitered,也体现了飞白对音韵美的追求。
原文:But to his feet,
Drawing nigh and nigher
A hidden seat,
The fog is sweet
And the wind a lyre (Hardy,1979)625
译文:但当他的脚步
向那隐蔽的座椅
渐渐走近,走近——
这雾多么甜蜜!
风也在为他奏琴
诗人莫渝(1993)在谈及飞白时,表示飞白听力式的译诗方法“养成了他对语言强烈的感受力”,进而形成了“诗感说”。应该说,莫渝所谓的“对语言强烈的感受力”仍然是主要针对文字而言。从上文的分析来看,飞白对诗歌的感受力不仅涉及文字层面,还进一步辐射到了非文字的标点符号。这使他在译诗时能够综合利用文字与非文字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其作为翻译主体的创造力,竭力将自身感受到的诗歌之美传递给读者,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飞白译诗时对审美价值的不懈追求。
4. 结语
总而观之,无论是基础层面的诗歌形式的模仿,还是较深层次的诗歌意义的表达,抑或更高级别的诗歌美感的传递,破折号在飞白的译诗中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于读者解读其译诗文本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增译的破折号为读者“深识鉴奥”提供了一把解密的钥匙。不仅如此,如果再将这一点推开来看,便会发现,透过破折号的这些功能,我们还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飞白译诗的3个特点:重视原诗的形式、别样的读者关怀和不懈的审美追求。可以说,飞白式的破折号启发我们去探究隐藏于小小符号背后的深层意蕴,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他的译诗文本和译诗观提供了一条较为理想的路径,值得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