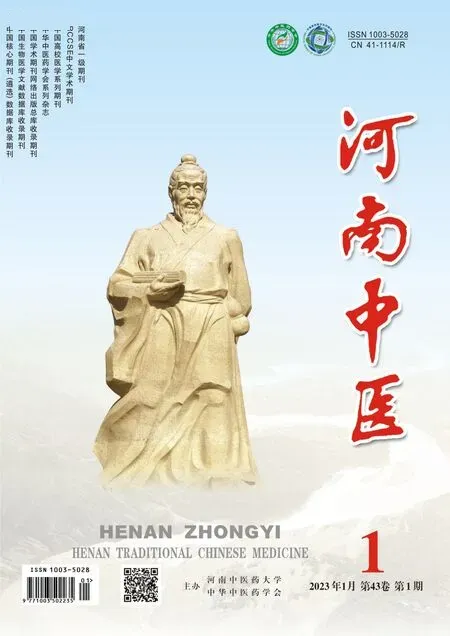茵陈五苓散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临床研究*
章璐
珠海市人民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珠海医院,广东 珠海 519000
我国是世界上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感染者最多的国家[1],虽然有疫苗与治疗药物,但是乙肝病情发展终将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细胞癌等并发症[2]。肝硬化患者中有25%~35%在入院时或住院期间出现细菌感染,死亡率较高。感染是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最重要的死亡原因,与未感染的肝硬化患者相比,死亡风险增加了4倍[3]。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SBP)是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无明确腹腔内病变来源的腹腔感染,肝硬化合并SBP可迅速进展为肝肾功能衰竭,甚至导致死亡[4]。近年来,中医对SBP的研究越来越多[5-7],SBP常见证型有脾虚证及湿热证,茵陈五苓散治疗SBP的效果显著,但临床报道较少。本研究观察茵陈五苓散治疗脾虚湿热证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的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6月至2020年5月珠海市人民医院收治的脾虚湿热型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8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男25例,女15例;年龄34~75(53.63±8.24)岁;病程5~18(8.26±3.14)年;病因:乙肝24例、丙肝10例、酒精性肝病1例、其他原因5例;疾病首发13例,复发或多发27例。观察组男26例,女14例;年龄35~74(52.64±8.13)岁;病程5~18(8.12±3.09)年;病因:乙肝23例、丙肝11例、酒精性肝病2例、其他原因4例;疾病首发10例,复发或多发3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标准根据《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8]和《美国肝脏研究协会成人患者肝硬化腹水处理实践指南(2012修订版)》[9]中的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腹水的西医诊断标准。自发性腹膜炎的诊断标准:①腹腔内存在感染症状和体征;②腹水细菌培养阳性;③腹水中多形核白细胞计数>0.25×109L-1;④非继发性感染[10]。肝硬化中医辨证标准[11]:脾虚湿热证分为三个阶段:①湿热蕴结证,此证为脾虚水湿内蓄而热化。腹大坚满拒按,脘腹撑胀,烦热口渴,目肤发黄,小便黄赤短少,大便秘结,不欲饮食,嗜卧,舌红苔黄糙,脉弦数。②热毒炽盛证,临床表现为黄疸发作,快速加深,鲜黄色,体温过高,多饮,频繁呕吐,腹胀,疼痛和拒绝按压力,便秘,黄红色的尿液,尿急,躁动,舌质深红色,舌苔黄色、粗糙或有刺,脉冲泛滥和湿滑。③痰瘀互结证,临床表现包括恶心,呕吐,痰多,口腔黏稠,胸闷,腹胀,或伴有目黄,舌苔白厚或黄厚,脉滑或涩。
1.3 病例排除标准有严重心血管、肾脏或精神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对本次研究药物过敏。
1.4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抗病毒治疗,保肝、利尿,定期穿刺引流腹水。对照组给予头孢噻肟(安徽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43299,规格:3.0 g)静脉注射,每日 6 g,分3次给药。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茵陈五苓散治疗,方药组成:茵陈160 g,泽泻 30 g,猪苓9 g,茯苓9 g,白术9 g,桂枝6 g,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服用。两组均治疗2个疗程,7 d为1个疗程。
1.5 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清晨空腹抽取患者静脉血3 mL,3 000 r·min-1离心,取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检测试剂盒由Abnova公司提供,货号:KA1227)、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检测试剂盒由QIYBO公司提供,货号:QY-H10038)、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检测试剂盒由Elabscience公司提供,货号:E-ELN-H0102c);使用由南京贝登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迈瑞BS-28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C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Ⅲ型前胶原(procollagen type procollagen type III,PCⅢ)、血清Ⅳ型胶原(type IV collagen,Ⅳ-C)、层黏连蛋白(laminin,LN)和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后两组肝纤维化指标(PCⅢ、Ⅳ-C、LN、HA)、细菌感染标记物(PCT、CRP)以及炎性因子(IL-6、TNF-α)变化情况。

2 结果
2.1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比较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比较
2.2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疗前后细菌感染标记物水平比较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疗前后细菌感染标记物水平比较
2.3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具体结果见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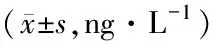
表3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2.4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3 讨论
肝功能衰竭、肝功能失代偿期肝硬化以及肝脏恶性肿瘤的患者极易合并SBP。肝脏库普弗细胞的功能降低,使得患者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细菌入腹腔导致SBP。SBP的发生可能与门静脉血液瘀滞、肠黏膜屏障功能障碍以及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存在密切关系,细菌进入血液引发周身感染,其中,腹腔是最容易感染的部位。SBP没有明显的腹腔内病灶,当腹水中的中性粒细胞计数高于250 μL时,应考虑为此病症[12]。在住院期间存在腹水的肝硬化患者中,SBP的发生率为5%~25%[13-14]。细菌感染是肝硬化十分常见的并发症,并且肝硬化患者发生感染的病因很多:肝功能不全、肠道营养不良、细菌易位、体液免疫和细胞介导免疫力下降、门静脉高压加剧、遗传因素等均为肝硬化患者感染的影响因素[15]。SBP患者预后较差,死亡率为20%~30%。目前,治疗SBP的方式主要有抗生素和白蛋白输入治疗。因此,早期诊断、合理选用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对改善预后非常重要。作为第3代头孢菌素类的头孢噻肟,具有抗菌谱广、强大的对抗革兰阴性杆菌的作用,且肾毒性小,不易并发二重感染,能迅速进入腹腔内起到杀菌作用,临床效果显著,已广泛应用于SBP的抗菌治疗中。
肝硬化合并SBP属于中医学“臌胀”的范畴,是中医“风、痨、臌、膈”四大重症之一。肝硬化的病位在肝,乃邪毒未清,导致肝郁血停,久而耗伤气血,结而成痞。本研究采用茵陈五苓散,茵陈清热利湿、疏肝退黄,合以五苓散利水渗湿,佐以桂枝,增强除水湿之力,发挥温阳化气、利湿行水之功效,温肾阳、调肝气、健脾利湿则臌胀除。目前,肝硬化合并SBP的发生机制尚未明确,大量研究表明,炎性病变以及免疫系统被激活对SBP的疾病进展意义重大,腹水中的促炎细胞因子表达增多也是其中关键的环节。同时,抗炎细胞因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炎性病变的发生发展中参与重要的调控,因此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的动态变化决定SBP发展的预后和方向。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患者容易出现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肠壁瘀血,水肿,通透性增高,肠道细菌大量繁殖、扩散、移位,导致腹腔发生细菌感染[16],上述情况与SBP的发生具有密切相关性。血液中的单核-巨噬细胞以及腹腔中的巨噬细胞被移位的细菌及其释放的毒素持续激活,导致TNF-α高表达,诱发免疫活性细胞激活释放炎性介质,继而参与抗感染过程,导致促炎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升高,且与机体产生的抗炎细胞因子发生拮抗。国内研究对比肝硬化腹水合并SBP与不合并SBP,发现合并SBP患者腹水中IL-10的水平较不合并SBP低,IL-18水平较不合并SBP高,说明合并SBP患者中抗炎细胞因子相比促炎细胞因子更有优势,这可能是引发SBP的原因之一[17-18]。随着症状改善,两项指标均发生显著变化,同时腹水中的两项指标改变最明显。陈勇等[19]发现,肝硬化合并SBP的患者腹水中白细胞介素水平高于血清,其机体腹水中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引发了细胞因子级联反应,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高表达,导致腹水中白细胞介素的水平高于血清,提示血清中白细胞介素可能来自腹水。故在临床对腹水中的相关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可作为疗效观察指标。
有研究表明,TNF-α对IL-6的产生起到正调节作用,TNF-α、IL-6增高与内毒素刺激巨噬细胞导致过量分泌密切相关。PCT对肝硬化合并SBP的早期诊断相对于传统标记物(如C反应蛋白、白细胞、红细胞沉降率等)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和敏感度。IL-6属于一种炎性因子,当机体受损后,血清中 IL-6 水平迅速升高。PCT属于一种常见的感染指标,其正常状态下水平极低,一旦发生细菌感染,通过炎症机制,肝细胞、神经元的PCT分泌量上升,继而血清中的PCT水平升高。PCT的稳定性较佳,易检出,若感染得到控制,2 d内血清PCT水平会迅速降低,故临床上经常将PCT作为感染指标。PCT是一种糖蛋白,不具备激素活性,主要是甲状腺C细胞分泌而来,在正常状态下其值极低,检测血清中是否存在PCT较困难,一旦机体发生细菌感染尤其是感染严重或周身感染,其水平异常升高。PCT对细胞因子级联反应的调控十分关键,在一些感染疾病中其值较高,原因可能在于其与IL-6、TNF-α等炎性因子的刺激存在一定关系。PCT在机体发生感染后会迅速升高,此时可在血清中检出,其在机体中较为稳定。相比其他感染指标,未发生细菌感染其水平不会升高,并且在一些慢性或局部非特异性感染疾病中其水平升高程度较小,因此针对感染严重的SBP其具有较高的检测价值[20-22]。
乙型肝炎十分常见,WHO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死于HBV导致的肝功能衰竭、肝硬化以及肝脏恶性肿瘤的患者高达百万人数,乙型肝炎的预防和治疗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公卫问题。乙型肝炎的发生与机体的免疫存在紧密的关系,HBV复制以及因此引发的免疫反应是引发肝脏受损和疾病恶化的重要原因。乙型肝炎治疗的目的在于制止HBV复制以及清除HBV,中医学中没有乙型肝炎的病名,此病在中医学中属于“胁痛”等范畴,中医认为,此病多因湿热疫毒蕴结肠腑,病发之初邪毒内盛,如果病情严重,用药剂量不足,导致机体内仍存在余邪,加之使用苦寒药,药物配伍不合理,脾胃受损,脾运化功能失常,脾气亏虚,从而出现水液运化障碍,导致胸闷、饮食下降、舌苔厚腻等。湿热邪毒郁积于肝脾,因此引发乙型肝炎,故乙型肝炎的中医证型为肝胆湿热证。中医学认为,此病多是因肝火亢盛、湿热稽留胁痛,日久耗阴伤血,导致阴虚血燥。由于肝脏和肾脏本是同根同源,肝肾阴液亏虚,虚热内扰,肝病传至脾导致脾肾亏虚。脾脏运化水液的功能出现问题,水湿停滞形成腹水,脏气内虚,功能失调,寒凝气滞。
五苓散出自《伤寒论》,适用于阳气不足,气化不利,津液不布,水饮内停之病机,病位涉及上中下三焦。因水饮之邪停留部位不同,临床病症变化多端,该方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肝硬化腹水、慢性腹泻、肠炎、各类泌尿系统疾病、特发性水肿、尿潴留等。肝硬化合并SBP患者属脾虚湿热内盛、中焦气化不利,水气内停之病机,正合五苓散健脾除湿利水之功,故用之疗效良好。五苓散加茵陈为茵陈五苓散,全方六味,出自《金匮要略》,适用于内生湿热、气化不利为基本病机的黄疸、胁痛、阳痿、眩晕、痹证、不寐等疾病。该方以绵茵陈为君药,茵陈苦寒,苦能燥湿,寒能清热,其气清芬,善于渗湿而利小便。臣以泽泻、茯苓、猪苓,取其甘淡渗利之性,辅以君药,加强利水之功,且水散热亦消也。叶天士谓:“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佐以炒白术健脾利湿,桂枝助阳化气,俾土实气行,则水湿化矣。方中茵陈是治疗湿热的主药,现代研究已证实,其具有保肝利尿的功效,茯苓、泽泻具有利湿行水的功效。《药品化义》认为,茯苓“最为利水渗湿要药”。《用药心法》云:“茯苓,淡能利窍,甘以助阳,除湿之圣药也。味甘平补阳,益脾逐水,生津导气”。《本草汇言》中提到:“泽泻有固肾治水之功,然与猪苓又有不同者,盖猪苓利水,能分泄表间之邪;泽泻利水,能宣通内脏之湿。白术甘温苦燥,善于补脾气,燥化水湿,与脾喜燥恶湿之性相合,治疗脾虚湿滞有标本兼顾之效。”白术可改善消化系统症状。此方中桂枝具有发汗解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的功效,与茯苓、猪苓、泽泻同用可治疗水湿内停病证[23]。本研究以茵陈五苓散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此方温阳化气,利湿行水,清除湿热邪毒,水湿下行从尿道排出,具有清除患者机体内的湿热邪毒,清热解毒的功效。
综上所述,茵陈五苓散辨证治疗可有效降低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的肝纤维化指标、细菌感染标记物、炎性因子的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