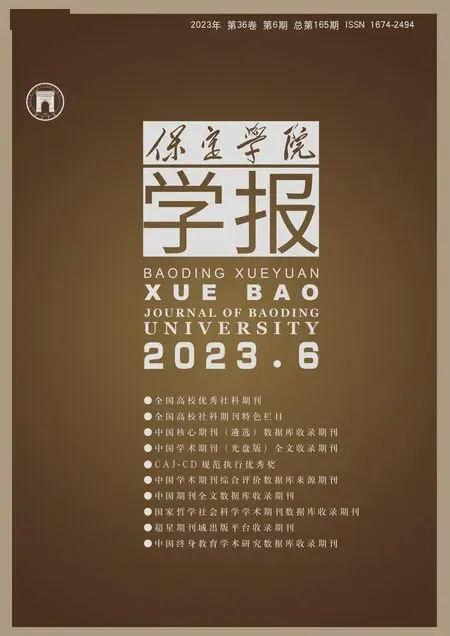沈括“造微”文艺思想与宋代词论之关系
王婉欣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作为北宋较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思想家,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艺文》卷中总结了自己的文艺创作理论,并详加论证。“造微”文艺思想是他在论及律诗创作中所提到的“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1]113,被后人进一步概括为“造微入妙”,并广泛见于各类文艺评述中。“造微入妙”指的是文学创作的整体过程,创作主体通过冥搜的体物方式进行创作,以期对事物的描绘穷形尽相、入情入理,最终达到形象逼真、情理兼胜、意蕴无穷的理想境界。“造微”文艺思想是北宋时期学风、政风、文风交汇影响下形成的产物,在文人交游、诗友切磋的过程中影响了诸多词人,并在他们的词论中有所反映,如“自有一种风格”和“别是一家”论以及“本色”“当行”论等。目前学界对于沈括“造微”文艺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未曾将其与宋代词论结合起来加以探讨①如蒋思翔虽然全面总结了沈括的“造微”观,但未深入阐释其对于宋代文坛的影响。参见蒋思翔《沈括诗学观之“造微”说探赜》,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21年第11期,第74~77页。。本文主要从分析“造微”文艺思想入手,研究其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追求与思维方式在宋代词论中的影响,并探讨其从诗学领域到词学领域的影响过程,试图有新的发现。
一、“造微”文艺思想的内涵
沈括的“造微”文艺思想主要受北宋时期文学思潮和理学思想的影响而产生。首先,自唐五代以来,诗坛上普遍流行着一种追求工致的观念,如宋初的“九僧”诗即以工于写景、精于锤炼为特征。欧阳修、梅尧臣等人是这种观念的集大成者,如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所载梅尧臣论诗之语“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2]342即体现了这种追求。这种观念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重在咏物。古典诗歌中的咏物描写,最早可追溯到《诗经》的重在比德,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转为穷形尽相。两宋时期由于理学的发展,宋人的观物、体物进一步深入,由此诞生了大量富于哲理的咏物诗、咏物词。这种对“物”的细致探索,自然也促使诗歌理论进一步深化。以上种种,都促进了“造微”文艺思想的形成。
北宋时期宋学兴盛,范仲淹、欧阳修以及“宋初三先生”等文士继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立志复兴儒学、恢复道统,在文章、学术、政治等方面都有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追求,并通过理学复兴以及古文运动等文化思潮传播学术理念,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观物致思方式,而沈括正身处其中。由于他与王安石私交甚密,不免受宋学思潮的濡染,在文学创作上追求一种精微、雅正的风格。在当时,宋学思潮还渗透到了科技领域,沈括作为科学家,亦受“格物致知”的精神影响。“格物致知”是新儒家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通过探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格物致知”中的“物”含义十分广泛,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人事,而“格物”所强调的不仅是对事物主要特征的充分把握,还要求对物理、事理、义理进行充分的认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多次提到“理”字,如“深究其理”[1]143、“穷测至理”[1]152等,可见这种崇尚理性的精神贯穿于文中。程颐曾言“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3],“格物”是理学家观物、体物从而进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将“格物致知”深入展开,渗透到了文艺批评和鉴赏领域,“造微”文艺思想即是其产物之一。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具体论述了“造微”文艺思想,对律诗创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时也指出诗要求“工”是很难的。即使“字字皆炼”[1]113,但若缺少知音,也很难为人所知。并且,“工”的要求还不只局限于诗歌的语言文字,更在于诗歌的意蕴。沈括十分重视诗歌含蓄蕴藉的特点,对“细论无功,景意纵全”[1]113之作持否定态度,并举出“折杨、黄华”[1]113以作说明。这种求“工”的观点在《艺文》卷多有论述,如他认为诗人即使是作小诗,也大多是“埏蹂极工而后已”[1]112,所谓“旬锻月炼”[1]112者不是虚言。正如他所举崔护题城南诗的例子,诗成之后诗人出于求全求工的考虑,改第三句为“人面只今何处在”[1]112,体现了唐人工于诗的一种自觉追求。沈括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与他的“造微”文艺思想是相契合的。
沈括的“造微”文艺思想首先便表现为追求文学创作的自然真实,要求创作者在描绘创作对象时要形象逼真、由形入理。他将对待自然科学研究的严谨求实作风应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对一些偏离生活实际的创作提出了批评。在《艺文》卷中,他提到韦楚老的蚊诗有一句“十幅红绡围夜玉”[1]111,十幅红绡为帐尚不足四五尺,根本无法伸脚,沈括认为这是由于韦楚老“不曾近富儿家”[1]112,所以写出的富贵诗才如此偏离实际。文学创作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如果强行描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事物,难免会闹这样的笑话。沈括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不仅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还体现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1]123之句,其中,“乌鬼”究竟是何物,曾经引发不少争议。刘克博认为“乌鬼”指的是鸬鹚,而沈括则对此表示了怀疑,原因是他在蜀中之时见过有人豢养鸬鹚来捕鱼,却未曾听闻有“乌鬼”之说。由此可见,沈括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也力求真实,并未拘泥于书本,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绝不人云亦云。
“造微”文艺思想不仅要求诗歌创作的自然真实,还要求“字字皆炼”。针对这一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晚唐士人的“读书灭裂”提出了批评,如白居易的题座隅诗中“俱化为饿殍”一句,他认为作“孚”字才能押韵;陆龟蒙的药名诗云“断续玉琴哀”,却不知药名只有续断,并无断续。此类错误屡见不鲜,主要是作者在学识上有所欠缺,读书不精,又缺乏求工精神所造成的。像白居易、陆龟蒙等名家尚且犯过如此低级的错误,其他人更不消多言。
沈括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造微”不仅意在求工,同时也追求诗歌自身的艺术特点,譬如押韵、炼字、雕琢语言、熔铸意境等。按他的要求,诗歌不仅要“字字皆是无瑕可指”“语音亦掞丽”[1]113,同时又不能“一读便尽”“无可讽味”[1]113。因此在《梦溪笔谈》中,能得到沈括肯定的作品并不多。林逋的“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1]111是其中一例,欧阳文忠公称赞它是“语新而属对亲切”[1]111,在《梦溪笔谈》中有所记载,侧面表明沈括对此诗也是持赞赏态度的。
沈括虽然追求文学创作的自然真实,却并未因此忽视其艺术价值。自古以来,历代文人在文体文风改革的过程中,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正如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早期的倡导者柳开、石介等人看到了浮靡文风的危害,因而提倡古文,尊崇韩、柳。但他们并未做到如韩、柳一般文质并重,而是片面追求明道宗经的文章内容,忽视了文章的语言形式,由此创作出来的文章自然艰涩难读,因而并未取得突出的成就。到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再次对文风进行了变革,他们本着重道亦重文的态度,矫正了以往的拟古和雕琢文风,提倡内容和形式并重,最终产生了较大影响。沈括是仁宗朝进士,自然也不免受其影响,在诗文创作方面继承了这种客观的态度。在《梦溪笔谈》中,他对前人诗句的倒装句法予以称赞,如韩愈文集中的“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1]111和杜甫的“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1]111等。这些诗句,乍读完全不合逻辑,但沈括却发现了其中的妙处,称其“语势矫健”[1]111,由此可见他对于诗歌的艺术形式也有独到的见解。
总之,沈括的“造微”文艺思想体现在诗文创作中,既要求在内容上自然真实,又要求在形式上求工,并且将这一观点渗透到了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后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造微”文艺思想对于宋代词论的启示
沈括的“造微”文艺思想体现出宋代文士在艺术探讨中的一种普遍倾向,即对法度的强调和对艺术体制纯正性的追求。这正与欧阳修、苏轼等文人集团由诗学思想到词学思想的探索相一致,从而为苏轼推尊词体的思想导夫先路。苏轼的“自是一家”之说,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强调词具有和诗同样的功能。这种观点大大提高了词的地位,拓宽了其抒情言志的内涵,使词的创作趋于文人化;但同时也模糊了词和诗的界限,不利于词摆脱其作为诗之附庸的身份;并且苏轼还对当时普遍流行的“柳七郎风味”提出了批评,不满于花间词风的靡弱无力,由此在词坛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两宋词家对此观点大多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既继承了其对词境的开拓,又从维护词的本体性角度提出了质疑;既维护了词的传统审美风格,同时又对沈括的“造微”文艺思想有所呼应。
同时,由于沈括和苏轼、李之仪等人交往密切,其诗学思想遂扩展到词学领域,影响了以李之仪为代表的一批苏门词人及其后学,特别是“造微”文艺思想对于词之本体性探索的启示,对宋代词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有一种风格”和“别是一家”论
在北宋时期,首先探究词的“本事”,强调其文体自身独立性的,当为李之仪。李之仪是苏轼门下的文人之一,《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其词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蒨,殆不减秦观。”[4]李之仪与沈括多有交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其文集中曾提到“沈括存中,余少相师友”[5]10。二人曾多次外出同游,诗词唱和,故李之仪也不免受到沈括“造微”文艺思想的影响。况且李之仪本身就是一位在创作上颇有成就的词人,在词的鉴赏方面也有很多创见,特别是在《跋吴师道小词》中,提出了词“自有一种风格”[5]41的概念。这一概念既继承了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中的“本事”思想,同时又对后来李清照的“别是一家”之说有所启示。李之仪的“自有一种风格”之说强调了词区别于其他文体的艺术特质。首先,他认为词都是有“格”的,并且“稍不如格,便觉龌龊”[5]41,体现了一种严格的审美态度。在这篇题跋中,他论述了词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并以《花间集》作为审美标准,对本朝诸位词人的词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柳永虽“铺叙展衍”“形容盛名”,但“韵终不胜”;张先词“独矫拂而振起之”,却是“才不足而情有余”;晏殊、欧阳修、宋祁等人则是“以余力游戏”“又非其类也”[5]41。同时,李之仪也对词的创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既要求“字字皆有据,其妙见于卒章”[5]41,同时又要“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5]41,追求一种意在言外的境界。这种观点和沈括“造微”文艺思想中的“字字皆炼”、求工等不谋而合。李之仪从文体角度分析了词的审美特性,强调了词的音乐性与形式美,并且认为词的创作不是易事,“岂平平可得仿佛哉”[5]41。以《花间集》作为评判一切词作的审美标准,或许有失公允,但李之仪论词的独特视角,无疑推动了词体自我意识的勃兴,对宋代词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词论观点也在诗友切磋的过程中影响了同样与苏轼交往密切的陈师道、晁补之等人。他从《花间集》的标准来评判吴思道的词,认为其“覃思精诣”。其实这不仅是李之仪对后辈所寄予的期望,更是他本人在创作中的一种自觉追求,从其诗《寄题吴思道横翠堂》中的“时觉东城添纸价,应知得句胜封侯”两句便可看出。
无独有偶,李清照也在《词论》中明确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将词与诗严格区分开来。其观点与李之仪虽有相似之处,但细论之,则更为鲜明也更为大胆。她首先详细论述了词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将其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词兴起于晚唐五代,到了宋代,由于“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6]219,从而走向辉煌。对于当朝著名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几乎都有提及,并且对各自词作的不足之处都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评,因此她的这篇《词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李清照《词论》或许有过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对词学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纵观其文,可以得知李清照论词有着严格的标准,首先便是对音律的要求,如她提出“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轻重清浊”,以便“协律”“可歌”[6]219,只有遵守音律规范,才姑且算是知词者。因此她对声律不协之词多有批评,如其认为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6]219,王安石、曾巩之词则是“人必绝倒,不可读也”[6]219。通过对晏几道、贺铸等少数“知之者”的批评,又可发现她对词作的要求有重铺叙、尚故实、主情致等。整体而言,李清照的《词论》仍是崇尚雅词的,从其批评柳词“词语尘下”便可看出。并且,她对南唐李氏君臣之词有所肯定,认为它是“亡国之音哀以思”[6]219。李清照的词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花间传统的影响,这一点与李之仪颇为相似。
(二)“本色”“当行”论
与苏轼、李之仪交往密切的陈师道、晁补之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2]222陈师道所强调的“本色”,与李之仪所提出的“自有一种风格”明显存在相近之处。若细读《后山诗话》,我们还不难发现,其词对《时贤本事曲子集》中的“本事”思想也有所继承。他同杨绘一样,看到了词自身所具有的通俗性及其与生活的联系比诗更为密切的特征。如词话中提到杭州名妓胡楚、龙靓皆有诗名,张先曾为其作词。通过这一事例,可以明显发现词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它不同于传统的诗教那样强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等道德功能,而是更加关注创作个体内心的审美感受与情感体验。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将人从传统的礼教与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自由地书写情感、宣泄情绪提供了渠道。并且,歌妓、乐工等众多地位卑微的底层人民也赖词得以留名、为后世所知,可见词确有不同于诗的独特功能。陈师道提出“本色”论,并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手法提出批评,所维护的仍然是传统的词学观,这与李之仪以《花间集》为标准来规范词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处。而陈师道对苏词的否定,多少也带有一些受传统词体风格影响而形成的偏见。苏轼的豪放词风,确实不同于传统的花间婉约之态,也有不协音律之处,但我们无法因此而否认苏词的巨大艺术成就,正如王灼所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7]。苏词所体现的豪迈旷达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为词坛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陈师道的批评也不是空穴来风,苏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词体规范。陈师道的“本色”论虽论点有些狭隘,但也体现了他为维护词学传统所作出的努力。并且,他作为苏轼和黄庭坚的后学,其词论并未受前人影响而是自出机杼,这是难能可贵的。
继陈师道提出“本色”论之后,晁补之又提出了“当行”一说。晁补之是苏门学士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称赞他“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8]。他在“评本朝乐章”一文中提到了“当行”一词:“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9]124从他对黄庭坚的批评来看,他的“当行”一说与陈师道“本色”论观点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对个别词人的看法。陈师道说苏轼的“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要非本色”[2]222,晁补之则认为苏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9]124。他们对苏黄二人的评价虽有所不同,但对秦观却都欣赏有加。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10],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亦云:“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10]秦观在北宋词坛上普遍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这与他词风婉约、情韵兼胜的创作特点是分不开的。花间词派的传统便是以婉约为宗,侧重于书写个体情感,这也是词区别于诗的主要特征。秦观词继承了花间词派的特点,专主情致,因此在当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从晁补之的词论来看,他的观点仍与传统词论相近,崇尚雅词。并且其评价不蹈袭人语,赞扬了柳永的《八声甘州》,指出柳词高雅之处,从风格多样性的角度对苏词予以肯定,同时又大胆地指出黄庭坚以诗的格调作词,不合规范。世人多认为张先之词不及柳永,晁补之却指出张先词之韵高是柳词所乏处。晁补之的这篇词论,几乎遍评北宋诸位词家,观点鲜明,同陈师道的“本色”论颇为相近。而二人词论中“本色”“当行”等论点的强调,则表明他们对于词之本体性的重视,与上述李之仪、李清照的观点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三、宋代词论的相互联系与发展
两宋时期,诗歌虽然有所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宋诗,但最值得关注的文体还是新兴的词,词在宋代由兴起到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突破了许多固有的理论框架,带来了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的全面革新。在词体兴盛的早期,文人士大夫大多抱有偏见,认为其是“艳科”“小道”,无法承载诗歌所承担的抒情言志功能。最初的词大多用于娱乐歌唱,内容上也多写男女情爱。直到元祐时期,苏轼提出“自是一家”之说,将词提高到和诗同等的地位,词的面目才为之一新。但与此同时,苏轼“以诗为词”的手法也受到了很多质疑,越来越多的词人认识到,词具有自己的风格与规范。由于词与音乐的联系比诗歌更为密切,它甚至有比诗更为严格的音律限制,不可与诗混为一谈,由此便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沈括的“造微”文艺思想是对诗歌提出的要求,但同时也对两宋时期的一些词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们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词的创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将词与诗区分开来,使其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从词自身的特点出发,在语言、辞藻、音律等方面对其制定了严格的规范。如此一来,词便逐渐摆脱了其作为“诗余”的地位,不再只是作为歌儿舞女的演唱以及王公贵族的狎戏之用,而是和诗一样成为了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并且,在词的发展过程中,词人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诗庄词媚”观念的束缚,将词作呈现为多种风格。词的创作遂由此繁荣,成为有宋一代最具标志性的文体。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诗提出的要求是“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反映在词的创作中,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便是字面上的求“工”,要求词作具有和谐的音韵、典雅的辞藻和整饬的形式;其次是要求“字字皆炼”,通过炼神来熔铸幽美深邃的意境,追求一种意在言外的效果;第三则是从词的本体出发,追求一种和诗歌不同的审美风格。宋代的一些词人在其理论与创作中便体现了“造微”文艺思想的要求。他们推尊词体,在创作中努力探索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呈现出清新疏朗、豪迈壮阔、缠绵婉约等多种风格,并且在各自的词论中对一些当朝文士提出大胆的批评,抒发自己的独特见解,推动了词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些词人主要包括李之仪、陈师道、晁补之、李清照等,通过分析他们的词论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其相互联系以及与沈括“造微”文艺思想的前后呼应。
总之,在北宋时期文学思潮与理学思想的交汇影响下,沈括形成了“造微”文艺思想,并在《梦溪笔谈》中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一文艺思想既凸显了他作为科学家的严谨求实作风,同时也对宋代诗词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的观点,被后人概括为“造微入妙”,成为宋代士人一种普遍的艺术追求,对后世的诗、词、文乃至书画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两宋时期词学兴盛的背景下,“造微入妙”思想不仅推动了词艺的讲求,深化了推尊词体观念的思想依据,还因此启发了“本色”论、“当行”论等关于词体特质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语文形式和音乐体制方面推动了宋代词体的创作发展和理论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