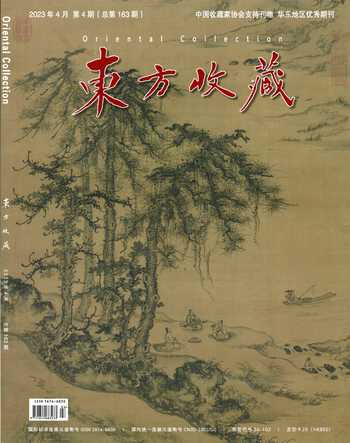刘海粟与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文章围绕20世紀中国美术教育的代表性人物刘海粟与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展开对比分析。刘海粟创立近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担负起向社会宣传艺术的重任,提倡“融汇中西”;潘天寿则在“西化”热潮汹涌的年代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独立发展”的论断,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美术教育领域仍然不断地被验证其正确性。二者的艺术主张和美术教育思想,对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对二者美术教育思想进行比较与分析,对于当今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刘海粟;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美术教育改革
20世纪初期,中国迫切需要探索出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从学习科学技术,到学习政治制度,再到学习思想文化,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巨大变革,紧随而来的便是教育方面的革新。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时代风气之先,创办新式学校,从此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一种热潮,教育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1]。
进入20世纪中期后,社会巨变、思想激荡,艺术领域同样受到影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中国绘画开始转型。中国绘画形成“改良”与“全盘否定”两大主流对峙的局面,其中改良派艺术家们在探索中国画出路的过程中形成了“融汇中西”和“传统出新”两个主流走向。作为20世纪美术教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刘海粟与潘天寿对中国美术变革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刘海粟力图“融汇中西”,将中国画和西方的后印象主义绘画进行连接;潘天寿则提出“中西绘画应拉开距离”,让传统国画按照自己的规律独立发展[2]。对比分析刘海粟与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其关键在于二者对中西艺术观念的差异。
本文围绕二者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求学经历以及任教经历等方面展开论述,梳理二者美术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分析比较二者具体的美术教育思想,以及二者的教学观念、教育思想、教学模式对于当代美术教育的启示。
一、刘海粟与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的形成
(一)刘海粟“融汇中西”思想的形成
刘海粟(1896—1994),江苏常州人。幼时在家塾学习传统书画,10岁入绳正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西方课程,14岁入周湘上海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画。早年受教期间恰逢新旧教育模式转变,因此刘海粟同时接受到中西方的美术启蒙教育,帮助其开阔视野,为后期刘海粟“融汇中西”的美术教育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2年,年仅16岁的刘海粟自筹经费,与好友乌始光、张聿光等人共同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这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第一所私立美术专门学校。该校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满足了社会对美术人才的需求,更“融汇中西”,扩大了西方美术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刘海粟受“五四”思潮影响,立志革新教育,而后的20年间里,刘海粟曾多次赴日本、欧洲考察学习,海外交流拓宽了他的眼界,欧洲之行帮助其与西方美术正式接轨。考察期间,文化的异彩促使刘海粟进一步研究比对中西方艺术,他将中国画与西方的后印象主义绘画相衔接。刘海粟一人兼中西绘画之长,偏爱泼彩之法,色彩绚丽飞扬,画面气魄动人,其油画作品《前门》入选1929年法国秋季沙龙,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参加法国沙龙的中国画家。
刘海粟一生投身艺术,致力于探寻中国美术的出路,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之后,他更是勇开先河,力求通过革新教育模式培育新式人才,使中国美术紧跟时代发展,从而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教育实践与探索中,刘海粟的美术教育思想逐步形成。
(二)潘天寿“中西拉开距离,独立发展”思想的形成
潘天寿(1897—1971),浙江宁海人。7岁时进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14岁进入宁海县新式小学,而后就读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院,接受新式教育,学习数理化知识、进化论、民主思想、哲学思想等。潘天寿兼传统文化底蕴与新式思想于一身,同时也奠定了其思想的多元性。
潘天寿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和革新。1923年,应刘海粟邀请,潘天寿进入上海美专教授国画;1928年,受聘为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系主任教授;1944—1947年,担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无论是在“全盘西化”或是“全盘苏化”主张盛行之时,他始终坚持要让中国画按照自己的规律独立发展,主张中国绘画应与西方绘画拉开差距,多次提出中西绘画分系主张,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画体系。潘天寿一生起起落落,但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的艺术始终饱含着民族骨气。
二、刘海粟与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在教学实践中的体现
教育思想形成于教学实践之中,不仅凝结了时代因素、社会环境、文化属性,更与个人选择息息相关。在当时这样一个外来文化热潮汹涌的年代,刘海粟与潘天寿立足现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
(一)刘海粟“融汇中西”思想在教学实践的体现
上海美专作为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的美术专门学校,早在建校之初,刘海粟就提出三条宣言,分别阐述了中西方艺术的关系、上海美专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于教师的要求,以艺术救济世人,其中“诚心”一词可以看作是当时对于画家、教师、学子的最高准则,也为上海美专奠定了教育基调。刘海粟曾说过:“以艺术之真理代兴一切信仰。”美术教育的目的不仅要造就纯正的美术人才,更是对个人情感、自由意志、完美人格的培养,时代不仅需要画家技艺高超,更需要有走在时代前沿的勇气与决心。
办校治学方面,刘海粟大胆革新,引入西方教学模式,以破封建礼教之气,力求改变当时中国艺术的困顿局面。刘海粟首开中国美术院校男女同校之先河,培养了包括潘玉良在内的大批女性艺术家;其次,在教学中大胆起用人体裸体模特,尤其是女性模特。此外,刘海粟还提出春秋两季的旅行写生,带领学生们走出画室,对景写生;再者变更学制,随时代变化调整教学模式,不以分数高低评价学生,而是形成一套专门的考核方法,在教学中强调创造,倡导艺术自由,培养学生美的意识[3]。
刘海粟欲开艺术先河,怎奈世道守旧。艺术与封建礼教大相径庭,改革举措与当时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男女同校历经重重挑战才得以被社会所接受,而大胆起用裸体模特则直接引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舌风波。1917年,上海美专举办成绩展览会,展出人体素描作品,各界的批评谩骂蜂拥而至,“艺术之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之类的批评话语直指刘海粟,但其初心不改[4],而后更是直接以“艺术叛徒”自居,直言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各种“叛徒”来打破成规,否则画坛难扫一派萎靡之风,更是发出了“我为艺术而生,愿为艺术而死”的无畏宣言。
刘海粟的艺术人生与上海美专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其改革举措可谓目光长远。他的革新不仅代表着新的教育模式的到来,更代表着教育体制的结构性变化,上海美专更是为接下来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发展奠定了基调。
(二)潘天寿“拉开距离说、独立体系说”在教学实践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潘天寿并没有受到美术界“西化”思潮的影响,而是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实践围绕中国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而展开。
早期,潘天寿任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系主任教授,他反对学校实行的中西画系合并的教学体系。在充分研究比较中西方艺术特点之后,潘天寿提出了“中西绘画应该拉开距离”的论断,强调教育办学不能一味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要由内及外,从中国内部谋求发展民族绘画艺术的道路,在保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古以来,中国绘画的独特之处就是不以描摹为能事,而重视表达意境、气韵和格调,对于艺术家的个人修养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潘天寿强调带领学生临摹古画,体会古人气韵,效仿古人“目识心记”的作画方式,以替代当时美术界流行的西方对景写生,不是单纯地复制景色,而是师法自然,经过眼、心、手的艺术加工,以此提升自身审美修养,充实文化底蕴。
20世纪50年代,潘天寿再度提出中西绘画分系设立的主张,并且拿出系统的实施方案,沿袭古人传统,画分三科,提出人物、山水、花鸟分科而立的基本构架。为满足技艺与文化相一致的要求,潘天寿提出“强其骨”这样一条基本准则,“强其骨”不单指艺术作品中要有民族骨气,同时也指美术教学中的“骨”,从诗词、书法、篆刻这些支撑起中国画的骨架入手,开设书法篆刻、古典文学、古典诗词、美术史等课程,旨在提升中国画内在境界,提倡中国画里的白描和双勾技法,教学颇具古风。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丰富完善了中国画的体系,更是被各大美术院系沿用至今。
潘天寿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传统画系而斗争,他牢牢坚守了40年,在从传统跨向现代这一必经之路上,他将传统中国画与日趋现代的中国艺术相连接的同时,又保有中国画的书香墨气。在他看来,中国画是沉淀著前人智慧的艺术,其中蕴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千百年来无数画家的传承,不应该被遗忘。
三、刘海粟与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的异同
在多年的美术教学实践当中,刘海粟与潘天寿自成体系,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美术教育思想。无论二者如何革新教育,其初心都在为民族绘画谋出路,为中国艺术拓边界。时代之下,总有人身先士卒,与其说是刘海粟与潘天寿的相似之处,不如说是同时代美术教育家的相似之处,包括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在内的一切教育改革,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培养人才,希望中国艺术在新时期再放光彩。
如今美术界将刘海粟定义为20世纪“融汇中西”的主将,将其一切教育成就归根于中西结合的大胆举措。但在对刘海粟的教育理念做进一步的了解时,笔者发现刘海粟教育思想中的异彩。刘海粟并非一味倡导“融汇中西”,更在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刘海粟曾说过:“中国人所作的西画,仍然可称为中国人的绘画,虽然是利用西方绘画的技法和工具,但作者是中国人,他的民族性不会因此而丧失或者削弱,反而是利用他人的工具来施展自己民族的特色。”[5]当时的中国美术界,艺术家能接触到西方艺术已实属不易,更不用说像刘海粟这样能够牢牢把住中西方艺术脉络,以西方的艺术理论与技法滋养东方艺术。
刘海粟“融汇中西”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西方艺术,而是要促进中国传统画跟上时代,相较于其他倡导“融汇中西”的艺术家,刘海粟在引进西方艺术的同时也将中国传统艺术推向世界。1934年1月20日,刘海粟负责主持中德两国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6],这是中国传统艺术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正式亮相,刘海粟也被邀请到各个学校进行演讲。刘海粟借此机会宣扬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他带着中国的传统艺术走向世界,带着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信,向世界展示千百年来中国画中的气韵。
而在艺术融合的大背景下,潘天寿也曾将目光移向西方。他在编撰的《中国绘画史》里写道:“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就是混交的时代,期间因为外来文化的传入与固有的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结合会产生异样的光彩。”[7]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艺术融合变了“味道”,不断地发展为反传统的思潮,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作汹涌澎湃之势而来,中国画一再地被批评冷落。在此情况之下,潘天寿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画的生存危机并挺身而出,提出“中西绘画应拉开距离”学说。潘天寿在“全盘西化”和折衷主义之风盛行的时候,仍然能够坚定自己,保存艺术中的民族性不被时代所取代,中国画中应包含着中国艺术家的自尊与骨气,中国画的出路不在于照搬西方模式的“皮肉”上,而在于中国艺术根骨上的自信。
四、总结
通过对刘海粟与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的梳理,不难发现二者教育思想的相通之处。无论二者如何进行美术教育革新,其根本都在于复兴中国传统艺术,刘海粟以西方艺术理念和绘画技术滋养东方艺术,潘天寿则在本土壮大中国画自身以探寻出路。艺术史上将刘海粟视为“融汇中西”的主将,把潘天寿看成“坚守传统”的代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总有人高瞻远瞩,带着对中国艺术的满腔热血合力为中国绘画谋求生机与出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刘海粟与潘天寿为民族绘画的发展、为国家艺术的光辉发声,将中国艺术家的骨气、中国艺术的民族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刘海粟与潘天寿二者的艺术主张和美术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带来了新的思考,如何让中国画在新时代中焕发生机,将古人的智慧、民族的艺术融入当下,是我们每一位当代学子的责任。二者的教育实践对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教育举措至今仍然被参考采用,他们的艺术主张与教育思想对新时代美术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晓方.我国高中阶段德育文本建设问题研究[D].浙江理工大学,2012.
[2]高天民.潘天寿“中西绘画拉开距离”说的内在意蕴[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03):18-30.
[3]王镛.中外美术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张建哲,徐姝彦.百年油画 百年人体[J].美术大观,2001(09):47.
[5]祖洪越.刘海粟美术教育思想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0.
[6]马海平.张弦与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往事[J].中国美术,2019(02):70-79.
[7]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作者简介:
纪星宇(1996—),女,汉族,吉林白山人。延边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202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理论、美术教育。
——刘海粟爱女刘蟾女士与常州市刘海粟小学师生书法笔会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