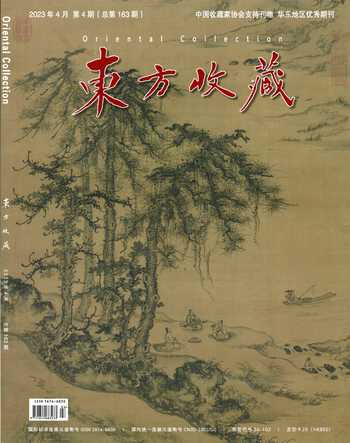唐代壁画中建筑的空间表现
摘要:敦煌莫高窟大量盛唐时期壁画中的建筑承载了多重含义,一方面是多视点空间构建的载体,另一方面也可作为空间可视化的象征。在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1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建筑的描绘明显引导了观者的视觉体验。本文通过对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建筑所体现的空间构成原理进行探究,通过建筑建立的绘画与观者之间的空间关系,探讨其表达空间,以及其体现的观想形式和形式具有的可视化象征意义等方面作为切入点,论述盛唐时期西方净土经变观念与空间的营造方法。
关键词:观无量寿经变;空间表现;敦煌;佛教建筑
经变画运用图像的方式,解释佛经里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西方净土经变图创始于南北朝时期,在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本文的研究对象敦煌莫高窟第172窟开凿时间为公元705至781年,正值唐代的鼎盛时期。根据《历代名画记》等文献记载,在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寺院内绘有许多精美的西方净土变。唐代前期经变画创作尚未形成对应的程式,画师们在绘制中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其艺术风格层面尚未定型。盛唐可以说是经变画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经变画个性与共性同时存在。作为西方净土变的典型,敦煌莫高窟172窟南北两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在内容与形式上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其独特的空间构成方式。
20世纪末,随着国内外兴起研究敦煌学的热潮,现代学者对于西方净土思想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然而对于敦煌壁画的空间表现问题,起初的研究多围绕“三远法”等文献研究方法,立足原作的研究相对有限。傅熹年认为莫高窟第148窟经变画是唐代“鸟瞰俯视”画法的代表,且讨论了战国至唐这一时期建筑画的表现;2002年赵声良在《敦煌壁画风景研究》的第二章系统讨论了唐代壁画的“群像配置方法”“视点”“透视关系”等问题,并引入“鱼骨式构成”的概念描述经变画中的空间特征;巫鸿在对172窟经变画的讨论中,认为经变与讲经这一行为存在着结构上的平行,其中,《观无量寿经变》这一题材是尊崇善导的经文的注疏绘制而成的,并且172窟南北两壁同一题材的不同绘画表现,是由于当时画工们之间的竞争。
本文通过对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原始图像作简要分析,着重于建筑与空间图式的构成,探讨盛唐时期空间表达的“观想”图式与背后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其营造逻辑。
一、《观无量寿经变》的空间构成
《观无量寿经变》属于西方净土变的一种,主体结构包含中央佛说法场面、净水池及化生和未生怨故事与十六观想的描绘。唐初大型净土变形式可能从说法图发展而来,如初唐322窟北壁,此可能为初期的净土图。从形式角度看,经变图在说法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筑等景观,将说法场面置于二维立体的空间环境中,开始有了对远近深度的描绘,空间变得可感,空间构成逐步形成。
唐代大型经变画宫殿楼阁规模宏大、人物众多,重在群像表现,如莫高窟172窟北南两壁(图1、图2)、148窟。通常说法场面下部描绘舞乐、供养人等,上部描绘飞天。由于要表现众多人物,在空间处理问题上,经变画营造的佛国空间,从净水池到宫殿的建筑、背景的自然景观以及人物的配置都是构成的因素。
敦煌莫高窟第172窟始建造于盛唐时期,于宋、清重修,形制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
前室頂部残存宋画经变,门南门北画维摩诘经变,南壁为宋画千手千眼观音变,北壁为千手千钵文殊变。在主室龛顶画三身佛说法、飞天、云气下画菩提宝盖。龛内西壁浮塑佛光,两侧各画一弟子;南、北壁各画弟子三身、项光三个。龛沿画菱纹边饰龛,下画壶门九个,内画供器、伎乐。龛外南、北侧画执幡天女各一身,项光各一个。南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一铺(西侧未生怨、东侧十六观),西端画观音一身,男女供养人各一身;下宋画男供养人九身(模糊)。北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一铺(西侧未生怨、东侧十六观),西端画观音三身;下宋画女供养人一排,底层盛唐画供养人(模糊)。东壁门上画净土变一铺;门南上画地藏、观音等四菩萨,中普贤变,下模糊;门北上画药师等四菩萨,中文殊变,下宋画女供养人一排(模糊)。
作为一个典型群像表现的西方净土变,莫高窟172窟以佛说法为中心,中央的三尊佛高踞于莲池上方的平台上,前面是三个较小的互相连接平台。美丽的伎乐天在中间平台上载歌载舞,其他两组平台支撑着另外的佛和胁侍菩萨。天池中的莲花化生象征着灵魂在天堂中的再生。在两侧是竖条画幅,夹辅着中心图像,一边展现的是邪恶国王阿阇世的故事,另一侧是十六观,讲述贤良王后韦提希的精神修炼。
通常敦煌的经变画被分为“叙事性”和“净土式”(对称式)两大类,赵声良在《敦煌壁画风景研究》(2005)中就这样进行分类。巫鸿1992年发表的《何为变相?》中,用了“叙事性图画”(narrative painting)、“偶像式绘画”(iconic depiction)或“对称式组合”(symmetrical composition)这对二元概念区分两种不同的经变画。后者的分类标准阐发更为详细,但是和前者的分类结果是一致的。
二、建筑建立的空间关系
建筑画是经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净土图式的经变画中。在敦煌壁画中,隋代经变里的建筑往往描绘一座单体建筑,唐代以后建筑群的描绘更受到重视。画家普遍从绘画构成的角度来表现建筑的形体及其位置,建筑画逐渐倾向三维空间发展。在空间方面,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不同于三段构成,属于典型的鱼骨式构成。
(一)三段构成
初唐三段式构成的经变画是说法图扩展以后的产物,中段是说法场面;下段描绘净水池和平台;上段象征天空,有飞天等形象。如334窟北壁《阿弥陀经变》,通过这些建筑背景表现远近的空间关系。
(二)鱼骨式构成
敦煌壁画的鱼骨式构成方法对于空间的建构或许是由本土的图式演变而来,建筑充当了整个空间图式的汇聚线,引导人们的视线指向中心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阿弥陀佛,同时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也是模拟的西方极乐世界中极为重要的元素。赵声良认为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为典型的鱼骨式构成(图3)。仅从构图的角度看,鱼骨式构成可以理解成中轴对称的方法,但前者意在表现远近,大大推进了空间关系的表现。
在入唐后不久,敦煌壁画中的说法图和净土式经变,都呈现出三维立体化发展的态势。画面以梯形或三角形图式为基本结构,对比稍早的南方和中原绘画可以发现有相似之处。尤为特殊的是,这一时期,佛殿窟取代了早期流行的中心塔柱窟,洞窟内经常以通壁巨制的形式描绘经变画,以西方净土变最为盛行。
三、特殊空间图式的构建
古人在创造“模拟的西方极乐世界”过程中,说法图和净土式经变画的视觉结构是由平面性图像向纵深化演变。盛唐172窟中,远景的楼阁与左右两侧的建筑形成一个巨大的梯形,“西方三圣”所处的宝台又恰好形成了一个稍小的梯形,一大一小两个梯形图式构成了此铺经变的基本结构。另外,“未生怨”也描绘出大量的建筑形象,以半俯视角度、斜边形图式的方法加以绘制。
巫鸿在对此铺经变的分析中,认为172窟南北两壁不同画风的《观无量寿经变》存在着艺术家独立的风格趋向,但基本的图式和视觉结构方面完全一致,也能得出当时的艺术竞争主要存在于风格表层,画师们在更深层仍然具有某方面的内在一致性,都是为阿弥陀信仰绘制的,都是“观想”西方净土的辅助手段,南北两壁的经变画形成了夹辅西壁中心的左右“镜像”。
敦煌第332窟东壁左右排列着三组说法图,每组都由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构成。画面中,弟子脚的位置明显向上移动,构成了一个梯形图式,体现了画面内隐含的三维空间结构。这种基础的梯形图式也出现在172窟中,同时辅以“近大远小”的视觉经验与适当的物象比例,和建筑构成的汇聚线,形成了典型的唐代净土式经变画图式。
魏礼(Arthur Waley)认为这两幅《观无量寿经变》中的阿阇世故事壁画是按照善导(613—681)对经文的注疏绘制的。7世纪出现的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宣告了8世纪敦煌艺术中单一的尊像场景为带有注释性边景的经变所代替,同时反映出唐代佛教越来越流行的礼仪与礼仪文学——“讲经”与“观想”。经变画的欣赏与讲经的行为互为表里,佛殿窟作为信徒修行的场所,为信徒观想提供了视觉辅助手段。172窟北壁的中心导向型画面引导信徒目睹并进入阿弥陀佛与他的净土,最终实现“观想”天国,这一场面是画师们试图建立一个特殊的图解程序,来帮助信徒理解佛经的宗教含义。
这样的行为与唐代出现的西方净土信仰不无关系。有关净土思想的佛教经典在二、三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如东汉支娄迦谶和竺佛朔共译的《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等,但在东晋以前,净土信仰还不是很普遍。到了唐代,一方面由于净土经典的论疏辈出,义学日趋完备;另一方面,道绰、善导等致力弘扬易行的称名念佛法门,更扩大了信仰的层面,使得净土信仰的流行在唐代达到鼎盛。
《观无量寿经》是一部强调净土依报功德的经典,且该经不但将依报作为观想的对象,还特别提到观想依报的灭罪功德,提升了净土依报的地位。善导在《观无量寿经疏》卷三中云:“诸行者等,行住坐卧常缘彼国一切宝树,一切宝楼、华池等,若礼念,若观想。”礼念即是礼拜的意思。原本在《观无量寿经》里的净土依报全是观想的内容,善导在作疏时却加入礼拜净土依报的观念,这种转变无疑说明了善导推动的净土法门已经从传统的禅观转向礼忏的修持。
四、开放式的空间
盛唐时期流行的佛教观念,要求信徒去理解这部佛经的宗教含义。172窟的中心导向型画面所变现的是韦提希或任何虔诚的信仰者“觀想”的结果——目睹并进入阿弥陀和他的净土,同样也是韦提希最终观想天国得以实现的场景,所以“观想”场面出现在中央构图的乐土中。
敦煌172窟中的建筑界画具有强烈的空间感,但未必能够说明当时的画师具有“焦点意识”,只能理解为符合传统“近大远小”的视觉习惯。而建筑构成的斜边梯形汇聚线形成的空间感所起的作用比建筑本身更为重要,是此图式的基线、图像的内在结构。通过建筑图式的组织和母题的位置,暗示观者判断出其所处的空间位置。
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表现方面,古人在画论中提出了诸多见解,如北宋郭熙《林泉高致》中的“三远”说、韩拙《山水纯全集》的“阔远、迷远、幽远”说。中国绘画的空间,约在魏晋时期,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进行了系统化的概括——“经营位置”。相对于西方的“构图”,“经营位置”的科学性要求并不高,原则上是艺术家根据创作意图对绘画形象的位置进行选择和搭配,塑造画面的总体空间结构与观赏的基本视觉逻辑。
很明显,敦煌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的中心图案,也是这篇文章的论述主体属于开放式的结构,两边的“未生怨”与“十六观”却是自含的画面。画家通过“经营位置”的方法设立了这幅画面的基本空间结构,强化了“向心式”视觉效果,加强绘画与观众之间的联系。
不仅仅于画面之中,石窟绘画与塑像的形象同样存在于石窟寺这一特殊的建筑结构里,欣赏它们的过程结合了宗教仪式。敦煌莫高窟172窟属于覆斗形殿堂式洞窟,主室窟顶画团花井心,周围圆形网幔,四角各一飞天,四披画千佛。 西壁开一平顶敞口龛,龛内塑一善跏坐佛及二弟子四菩萨,均为清代重修。其中二菩萨为半跏趺坐,余为立像,背光两侧画六弟子,龛顶画菩提宝盖,龛外两侧塑二天王,龛外南、北侧龛沿处画二天女。在洞窟中并没有建造中心塔柱,取而代之的是后壁凹进墙内的佛龛,中央放置作为主要偶像崇拜的佛塑像(殿堂式窟平剖面图,如图4)。
殿堂式石窟及其内部装饰相关的宗教崇拜形制是为了“观像”,关于这一风习或许早有流传,但在盛唐最为盛行,这时期出现了大量对于观像经文的中文注释和与该礼仪相关的经变绘画,如上文提到的善导所著的《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观像要求人们通过供奉、凝视“经变”来表达对宗教的虔诚,这也是经变作品这一时期在敦煌盛行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凝视”这一行为,作为“偶像性绘画”的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的图式设计也使得图像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加深。
开放式的空间意味着图像并不局限在画幅之中,犹如盛唐时期的人们在观像中并非孤立地欣赏墙面的经变。经变这一绘画题材在当时也并非仅仅用于欣赏,程毅中指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常常用“处”字,可以说明故事的讲述者是依靠壁画为辅助的:“我们看到的‘祇园记图或‘降魔变图多数是以舍利弗和劳度差二人为中心,而把一系列的突发场面穿插在二人之间,构成一幅综合的连环故事画。在讲故事时,如果不是具体指明讲到何‘处,恐怕听众会弄不清,所以每一段唱词都要说明讲到何‘处,便于听众按图索骥,这也是变文与变相密切配合的一个确证。”
这样的比方适用于多数变相作品,但或许172窟的作品并非是按照便于观看来设计的,这里夹杂着画家与供养人在建造整个石窟寺过程中的立场。第172窟的供养人题记残留并不完整,但大量出现“一心……”“……一心供养”等字眼。出于目的,这些供养人希望自己的功德能有所用,能够被神明所发觉,那么在绘制变相或制作造像的目的也不仅仅为凡间的观者所用,还有他们心中的神明。
敦煌莫高窟第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作品,在独特的空间构造外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精神空间,可以说大部分的壁画都出于这样的功用。尤其是变相壁画,一方面具有宗教题材的特性,另一方面又不仅仅局限于墙面。对于整个石窟寺的艺术系统而言,这些壁画并非仅仅用于视觉上的欣赏,而且是石窟的“视觉辅助”。
从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可以看出,这样“向心式”的构图是画师通过空间关系安排人物事件,引导观众去解读彼此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赋予了一种被解读的视觉形式,类似于整幅画的骨架。而这样的视觉形式背后反映出的是“近大远小”的本土视觉经验与社会盛行的“观像”之风。“观像”这一行为并不单单是看,在更大程度上是从建造到观想,整个过程让神明感受到观众或供养人的虔诚之心。
变相绘画的定义决定了它与文本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敦煌石窟的變相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不仅仅是变文,还包括了“讲经文”和“押座文”,并且不同的变相绘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便是佛教教义浓缩成为“偶像式绘画”的呈现,尤其是它的图式以及内容,都突显了中心的佛像,但这背后是经文单方面对图像的影响,还是文学与绘画的交互影响,还有待发掘。明末清初,欧洲的焦点透视法正式传入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觉逻辑,但起初并未大范围地对人们的视觉习惯造成影响,这样的学说直至20世纪才得以广泛普及。可以说,那是中国视觉艺术另一个新的开始。
参考文献:
[1]杨明芬.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张建宇.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3]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6]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中国古代的建筑画[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
[7][美]巫鸿著. 礼仪中的美术[M].郑岩,王睿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8]Wu Hung,What is Bianxiang?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nhuang Art and Dunhuang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n.,1992
[9]萧默.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形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程段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J].文学遗产,1962(10).
[11]李晓丹,王其亨,吴葱.西方透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绘画的影响[J].装饰,2006(05):28-30.
[12]同[5].
作者简介:
印玥(1997—),女,汉族,江苏太仓人。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