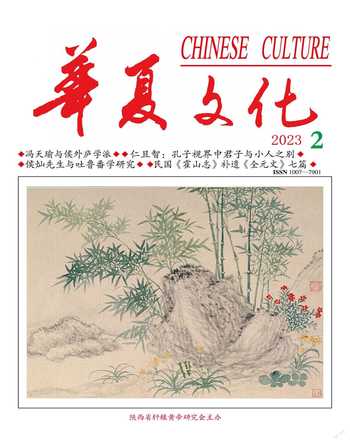张载、朱熹关于“子绝四”的阐释差异
李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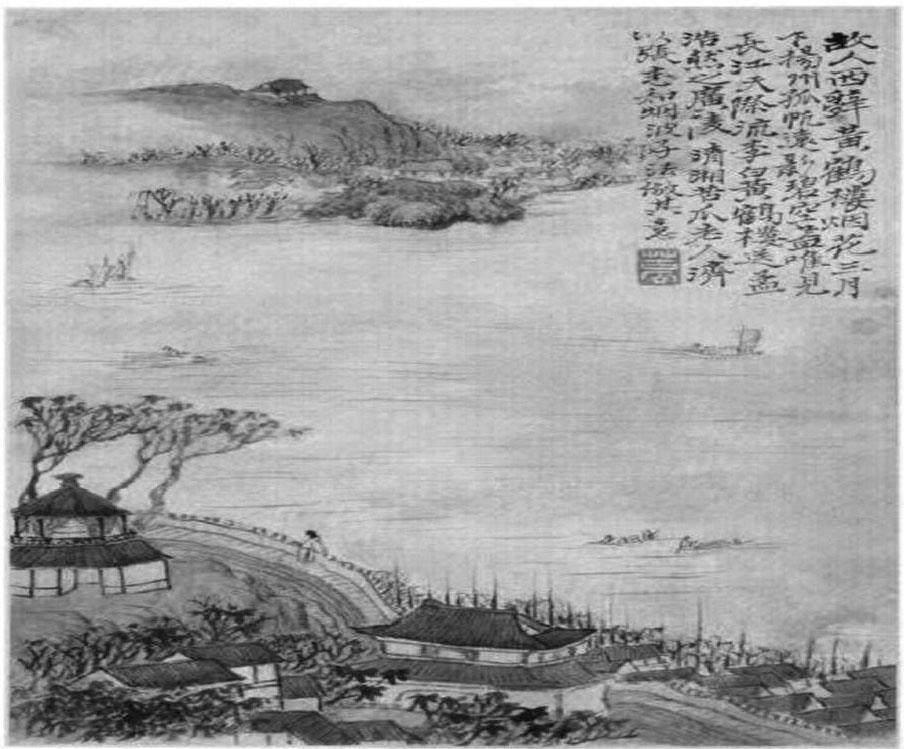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一段重要语句,由于其句法独特,内容精要,历来为注释《论语》的学者所重视。在宋代,对儒家经典的理学化诠释逐渐成为主流,理学家们根据各自的理学理论来理解“子绝四”,从而形成对“子绝四”的不同阐释。尤其是气学代表人物张载和理学代表人物朱熹,都曾深入探讨“子绝四”一语,为研究者留下了比较充足的文献资料。本文将会比较张载与朱熹对“子绝四”阐释的差异,希望以此为切入点,进而考察宋代气学与理学在阐释儒家经典时体现出的不同之处。
一、“子绝四”的本义及其疑难
纵观《论语》全书,无论从思想还是从文法的角度来看,“子绝四”一句都是相当独特的:与论语中的大多数语句不同,它缺乏相应的语境,其中的思想也无法在其它篇章中找到呼应。这就加大了准确解读该句的难度。同时,它的文辞简略却意义丰富,导致我们在阐释《论语》时必须认真解读它。
从字面上进行解释,这句话可以被初步翻译为:“孔子去除了这四种东西:不妄自揣测、不独断专行、不固守成规,不只顾私己。”在这里,“意、必、固、我”更多被理解为四种处事的方式,由此,这句话也更多倾向于反映他求真求实、先人后己的一种生活态度。这是当今被广为接受的一种解读,然而并非是唯一的解读方式。自古以来,由于“子绝四”一句语言精炼、内涵丰富,历代注家对于它有过不少阐释。其中,对“毋”与“意、必、固、我”的解释最具争议,也最有代表性。
关于这句话中的“毋”字,最主要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源于《释文》,认为此处的“毋”字从其本义,应当译为“不要”;另一种源出《史记·孔子世家》,认为“毋”通“无”,可以译为“没有”(参见《论语集释》,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62页)。其中,前者是对进行“意、必、固、我”这四种行为的否定,即孔子不会进行这些行为,后者则是否定了“意、必、固、我”这四种行为在孔子身上的存在。两种解释表面上相似,其意蕴却有着微小的差别。
至于“意、必、固、我”四个字,历来解释众多。关于“意”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之训为“测度”,何晏将之解为“任意”,而朱熹将之训为“私意”;关于“必”字,何晏将之解为“专必”,朱熹则将之训为“期必”;关于“固”字,何晏将之解为“固行”,《群经平议》则认为“固”同“故”,将“固”解为“泥其故”;关于“我”字,朱熹将之解为“私己”(同上)。
由上可见,虽然“子绝四”一语只有短短的十一个字,但阐释难度却很大,而它丰富的内涵也赋予了后人更多的解释空间。张载、朱熹都为它精要的义理所吸引,从自身思想体系出发对之进行阐释。
二、张载的阐释:去除天人之别
在宋代的理学家中,最早关注“子绝四”的应为张载。张载对于“子绝四”一句相当重视,在《正蒙》及其他著作中,曾多次论及“子绝四”一句,并对之进行了大量的说明。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他在《正蒙》中对“意、必、固、我”的训解:“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为不相似。”(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第28页)在张载的解释中,有思,即有所思虑;有待,即有所依仗;不化,则是无法参与天道神化的变化;有方,即有所阻碍。张载认为,孔子之所以要禁绝四者,是因为人具备了这四者之一,就与天地不相似了。
这段阐释中提到的一些概念,比如“有思”“不化”等,都曾在《正蒙》中多次出现,是张载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换而言之,在阐释“子绝四”一句时,张载更多地是从他自身的思想体系出发,利用他思想体系中的相关概念来理解“子绝四”。因此,要理解张载对“子绝四”的阐释,需要将它放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
在张载的思想中,“天人合一”是人最为重要的追求,而要实现“天人合一”,人需要主动地改变自身的不足之处,实现人与天的同一:“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盡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同上,第20页)在张载看来,“诚”与“明”指的是人性与天道没有差异、在知识和功用两方面都和天道相同的状态,人与天之间有许多不相同之处,这些“天人之异”导致了人相对于天的不足,因此,人有必要改变自身与天不相同的地方,由此来弥补人本身的不足。
对于张载来说,天是不需思虑、不需认识的,“有思虑知识,则丧其天矣”(同上,第23页),同时,天也没有私我的限制,“天良能本吾良能,顾为有我所丧尔”(同上,第22页),人就是因为蔽于“有我”而丧失了天赋良能。此外,天还有“神”的天德与“化”的天道,“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尽管在张载眼中,属于天的“神”与“化”不可为人所思考与改变,但是人可以“存神过化”,意识到天的神妙,并顺从天的变化,从而参与到“神化”的过程中。
基于张载的这些思想,我们可以认为,在张载的阐释中,“意、必、固、我”是人与天之间的差距所在,也是人应当努力去除的、自身所拥有的阻碍。张载认为,“仲尼绝四,自始学至成德,竭两端之教也”(同上,第28页),“子绝四”是学习儒家之道需要贯彻始终的教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朱熹的阐释:私意的形成
与张载一样,朱熹也十分关注“子绝四”一句,并对“子绝四”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但是,朱熹的解释与张载并不相同,他的阐释是从心性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的。其中,两人对于“意、必、固、我”的解释差异最大,如《论语集注》中他的解释为: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也。我,私己也。四者相为终始,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盖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后,至于我又生意,则物欲牵引,循环不穷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10页)
朱熹把“意、必、固、我”四者之间的关系视为“相为终始”的一个过程,私意的出现会导致“必”“固”的出现,最终导致利己主义的“我”的形成。在《朱子语类》中,他对这一“相为终始”的过程有更详细的论述:
“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创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处;必,便到固滞不通处;固,便到有我之私处。意,是我之发端,我,是意之成就。”(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三册),中华书局,1994年,951-952页)
“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必行。固,是既行之后,滞而不化。我,是缘此后便只知有我。此四者似有终始次序。必者,迎之于前;固者,滞之于后。”(同上,第954页)
在这里,朱熹进一步明确了“意、必、固、我”是私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且四者是一条相为终始的链条。由此,朱熹认为,学者需要完全去除“意、必、固、我”四者,而且“此四者,须是始学亦须便要绝去之”(同上,第954页)。
如何去除“意、必、固、我”四者?朱熹提供的答案是“凡事顺理,则意自正”(同上,第951页),顺从天理,而不因私意进行决策。朱熹认为:“所谓‘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见得道理是合当如此做,便顺理做将去,自家更无些子私心,所以谓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见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将去,便是私意。纵使发而偶然当理,也只是私意,未说得当理在。”(同上,第955页)朱熹认为,在行事不因自己的意愿而决定,一切顺从道理而为,便可实现“绝四”。
四、张载与朱熹阐释之异同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张载和朱熹同为理学家,但他们对“子绝四”解释的角度并不相同。张载从天人关系角度对“子绝四”进行解释,把“子绝四”解释为人主动去除与天地不相似之处,符合于天道的境界。朱熹则更多从心性论角度进行解释,将“意、必、固、我”解释为私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从而在心性论上论述了“子绝四”的意义,由此一来,双方在阐释的细节上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差异。
在用“理”这一概念阐释“子绝四”时,张载认为“天理一贯,则无意、必、固、我之凿”(《张载集》,第28页),其中的“理”指的是外在于人的天理,而朱熹所說的“理”不仅指天理,还有内在于人的性理。在“子绝四”的目的上,张载认为,“绝四”的目标是让人主动去除人与天的不同;而朱熹把“绝四”的目标视为去除私意,从而顺任天理流行。针对“毋”字,张载认为“毋”意为禁止:“学者亦须无心,故孔子教人绝四,自始学至成圣皆须无此,非是圣人独无此四者,故言‘毋,禁止之辞也。”(同上,第318页)张载把它解作“禁止”,目的是说明“子绝四”在儒家之道中的重要性,并劝导儒家学者坚持遵循“子绝四”。朱熹则认为“毋”通“无”,并引用程颐的话说:“此毋字,非禁止之辞。圣人绝此四者,何用禁止。”(《四书章句集注》,第109-110页)
但是两者的解释却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在朱熹对张载诠释的评价上可以更好地反映这一点,朱熹对张载的诠释在大多数条件下都是认同的,仅有的几处不同之处,朱熹并未否定张载的思想,仅仅说张载在措辞上有所瑕疵。朱熹并未否定张载“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为不相似”的思想,而且他也认同“子绝四”是为学初期便应开始的重要工夫,在“子绝四”的重要性上,他和张载保持了一致的观点。总体上来说,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是少于共通之处的。可以看出,同样作为理学家,双方的思想还是大同小异的。可以说,他们两人对“子绝四”的诠释,更多呈现出一种互补关系,而非相互间的针锋相对。
总体上来说,张载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诠释了“子绝四”中的境界论,朱熹则从心性论的角度论述了“意、必、固、我”的私意发生过程。这导致了两者对“子绝四”的阐释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但是,在基本立场上,两者都一致地重视“子绝四”,并将之视为为学初始便应实行的重要工夫。
这证明,在阐释“子绝四”时,气学家与理学家所选择的角度并不相同。两者虽然在基本立场上保持了一致,但气学家更偏向于从天道论出发进行论述,理学家则更倾向于进行心性论方面的阐释。至于阐释儒家经典中的其他段落时,两者之间是否有同样的区别,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作者: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 7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