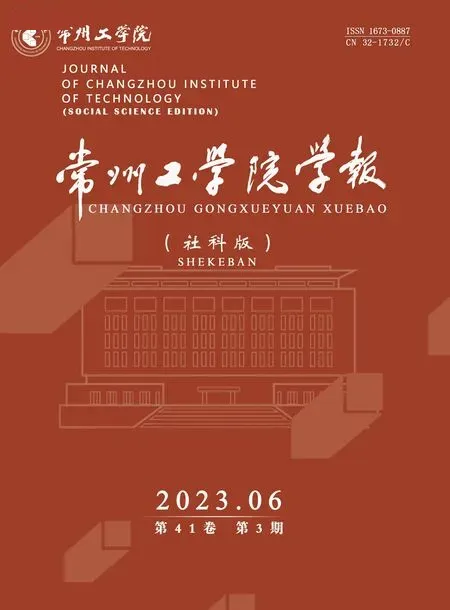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
黄颖
(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语言变体,反映出某个历史空间的民族情绪与社会心理,客观而现实地塑造着语言使用者及其社会现实[1]39。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和网民群体的迅速壮大,网络交际中大量的侮辱性、攻击性言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网络语言暴力逐渐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阻碍了网络文明环境的建设,其产生的根源及背后的社会心理值得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将网络语言暴力置于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中,通过重构网络语言暴力的话语实践,揭示暴力语言和语言暴力的演变过程,以期为减少网络语言暴力、推动网络人际交往和谐提供参考。
一、网络语言暴力的相关研究
(一)网络语言暴力的界定
作为互联网时代引起广泛讨论的社会议题,网络语言暴力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当前学界针对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界定主要可分为行为观和现象观。行为观将网络语言暴力定义为“以网络为媒介对他人或群体进行身心上的伤害,包括谩骂、歧视、诋毁、藐视、嘲笑、骚扰、攻击、侮辱、欺压、色情、性歧视等行为”[2]119,聚焦网络语言暴力这一行为本身。现象观则将网络语言暴力定义为“在互联网络上,以话语霸权的形式,采取诋毁、蔑视、谩骂、侮辱等手段,侵犯和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精神和心理的行为现象”[3]167。基于此前的概念界定,本研究从语言角度出发,将网络语言暴力定义为“在多人交互的网络语境下,以语言符号为手段,对他人或群体进行嘲讽、侮辱、诋毁、攻击的负面言语行为”。
(二)网络语言暴力的相关研究
当前针对网络语言暴力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新闻传播学、法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视角,集中关注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成因、法律规制、语言特征、治理路径、使用主体等方面,其中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语言特征、网络文化安全、言语不礼貌、批评话语分析等角度[2-13]。袁周敏、韩璞庚主要从3个方面论述了网络语言流变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为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提出了有效参考[1]39-43。耿雯雯、谢朝群将网络语言暴力置于不礼貌研究视角下,基于关系管理模型框架探讨了网络语言暴力的定义及评价问题[4]。靳琰、杨毅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网络空间暴力互动中暴力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了在线参与者使用网络语言暴力的社会—心理机制[5]。根据刘文宇和李珂的研究,现阶段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主要参照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和情境—互动范式,关注焦点是网络语言暴力的行为后果和社会秩序层面的问题,对语言自身的解释能力不足[2]122。语言是网络语言暴力的有机载体,从语言学角度对网络语言暴力进行分析可以直观呈现话语实践的演变过程,而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弥补行为主义范式过于微观和情境—互动范式过于宏观的不足[2]122,将微观层面的语篇、中观层面的话语实践和宏观的社会情境连接起来,为网络语言暴力事件—过程的分析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因此,本研究基于现有研究将网络语言暴力置于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中,通过重构网络语言暴力的事件—过程,揭示网络语言暴力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探究网络语言暴力的话语实践与权利意识之间的关联,以期丰富当前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为减少网络语言暴力、维护网络交际环境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网络语言暴力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扎根于语言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众多学科,主要侧重于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社会分析[2]122。总的来说,批评性话语分析在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念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理论范式,旨在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语篇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如何为之服务[6]。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话语的特点取决于社会结构,反映甚至建构社会现实;而话语通过与价值观念、权力制约的相互影响,可以促使话语改变和社会变革。批评性话语分析以话语观为出发点,将话语视为多维度、多模式、多功能现象,在语言学、互文、历史、社会及情景语境中进行解构和研究,以某种特定方式进行社会设定与社会建构。批评性话语分析的3个目的分别是:(1)系统地探索话语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关系和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2)研究这些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权力之间的关系;(3)探讨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在维护权力与霸权中的作用[7]。
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事件—过程”中观视角,作为话语实践的网络语言暴力可进一步划分为暴力的语言和语言的暴力。前者对应微观层面的语篇,后者则对应中观层面的事件—过程。二者共同构成了网络暴力语言话语实践的一体两面,相互对应并相互转换[2]123。网络语言暴力以文本语篇的形式展现网络交际过程中参与人的认知心理、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以及群体或阶层属性,并在话轮转换的过程中进一步复制、强化,对其他互联网消费者形成强烈刺激,从而导致网络语言暴力的演化和升级。而从中观层面研究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参与人之间的价值冲突、关联及其演化过程,可以从语言角度直截了当地呈现文本和语言的价值功能,展现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网络语言暴力施加的隐蔽影响。因此,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对网络语言暴力进行文本分析,可以重构网络语言暴力的事件—过程,并揭示个体或群体背后的冲突关系与变化,同时展现权力与意识形态潜在影响下的社会操纵过程[2]123。这既有利于揭示文本语篇的价值和功能,也有助于洞悉网络语言暴力背后的社会认知心理和驱动因素,促进对网络语言暴力的防范和干预。
(二)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网络语言暴力体现为暴力的语言有哪些表现形式? 第二,暴力的语言转变为语言的暴力主要有哪些路径?
(三)语料收集
本研究的语料主要为微博热搜中艺人失德相关话题下的交际语篇,原因在于:艺人作为公众人物,具备一定的流量关注度,话语实践所体现出的矛盾冲突更为突出。首先,基于相关话题选定评论数1 000条以上的推文;然后,从推文前20条热评里筛选出含有网络语言暴力的交际片段,共获得75个语篇;最后,对语料内容进行人工标注、分类,回答以上两个研究问题。在标注语料时,所有的暴力语言使用字体加粗的形式,而语言暴力则采用下划线标明,话语生产者依据发表评论的顺序依次标注为A、B、C、D等。针对文本内容里涉及的具体人名,本研究用X、Y、Z进行代替。
三、网络语言暴力的表现形式及演化路径
笔者对收集到的语篇内容进行了标注、分类后发现:网络语言暴力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暴力的语言,主要表现形式有谐音、人称降级、语言混用、表情符号、骂詈语、负面修饰、污名化指称,反映了话语生产者的认知取向、情感态度和价值偏好。例如:
(1)(某艺人因个人情感纠纷问题引起网络舆论后发布道歉声明。)
A:大晚上别搁这funnymudpee,你吵到我睡觉了。
B to A:它想我们死的心太明显了。
A to B:洗了蒜了。
D to A: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姐妹会说就多说点。
例(1)分别使用了谐音(死了算了)、语言混用+谐音(放你妈的屁)、人称降级以及表情符号,从语言表现形式看属于隐性的暴力语言。综合语料内容发现,隐性暴力语言的使用反映出话语生产者试图弱化语言暴力属性、维护人际和谐的认知心理,通过使用谐音等语言表现形式缓和暴力语言的冲突属性,从而实现个人情感宣泄和人际互动和谐的平衡。话语生产者A用英文单词代替汉语骂詈语表达,通过使用谐音和英汉混用,实现一定的幽默效果,在语言使用上弱化了暴力语言对其他话语消费者产生的信息刺激和对话语指向者的面子威胁,并以“你吵到我睡觉了”对前项暴力语言进行补充和原因解释,由此延缓了暴力语言向语言暴力的演变进程。基于本研究语料,在隐性的暴力语言中,谐音的使用较为频繁,如“沙杯”(傻B)、“见不见”(贱不贱)等。这些表达大多数情况下能有效弱化语言的暴力属性,降低话语的不礼貌程度以及对他人面子的损害。C通过用表情符号代替文字表达(贱),在弱化暴力语言的同时促使其他话语消费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有效地降低了暴力属性的凸显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隐性暴力语言的影响下,其他话语生产者改变原定的显性暴力语言表达转而使用隐性暴力语言的情况亦存在。同时,交际平台上敏感词汇的限制规定也会促使话语消费者选择隐性暴力语言。这些隐性暴力语言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暴力语言对其他互联网话语消费者的刺激效果,影响了他人对暴力语言表达形式的选择,在满足话语生产者情感宣泄的前提下延缓了暴力的语言向语言的暴力的演化进程。
在话语实践中,网络语言暴力被解构为事件、参与者及机构间的互动过程[5]78。话语生产者利用语言符号对文本内容实施复制和信息强化,构成暴力的语言,以此对其他话语消费者造成强烈的信息刺激和情感驱动,促使其作出一系列行为反应,最终推动暴力的语言演化为语言的暴力。当话语资源在话语实践中被暴力语言进一步挤压,话语生产者在维护自身话语秩序的同时会引发网络交际中的语言暴力实践。基于本研究语料,网络语言暴力的演变主要通过负面身份标记、固化消极属性、群体身份关联3种路径实现。
(一)负面身份标记
语言是网络语言暴力的载体,而在网络语言暴力的交际语篇中,负面指称被广泛使用。话语生产者运用负面指称对他人进行身份标记,将其作为话语指向者的等价物,突出语言的暴力效应。这既反映了网络语言暴力对语言的高度依赖性,也体现出网络语境中话语生产者对语言暴力属性的复制强化。例如:
(2)(某位曾因私德问题引起舆论的男艺人为新作品进行宣传。)
A: 真无语,拒绝劣迹艺人。
B to A: 小作文能毁掉一个对华语乐坛有突出贡献的音乐人?荒唐!
C to B: X这种有个屁的突出贡献,别出来丢人了。
A to B: 你也挺荒唐的。
D to B:巡逻犬又来了。
C to B: 为啥患脑残不去吃药呢?
在本交际片段的初始阶段,A首先运用显性的暴力语言对该艺人进行负面身份标记,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观点。B对该艺人进行褒扬修饰,反驳A的观点,是典型的言语评价行为。C的评论在否认B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了暴力语言对B的指向性,至此,语言暴力的焦点成功转移至话语生产者B,话语生产者B与A及其同盟者的对抗关系由此建构形成。而在后续的话轮中,C和D分别对B进行负面身份标记,使其形象内涵成为语言暴力的叙述核心,进一步强化语言暴力属性和对其他话语消费者的信息刺激,促使更多的网民认同B被网络语言暴力攻击这一事实,正是对这种深远的主体形象的塑造让更多的受众赞成受害者就应该被攻击[5]78。
(二)固化消极属性
在网络语境中,话语生产者的情感如愤怒、憎恨等被进一步概念化,嘲讽、侮辱、诅咒、威胁等话语策略均以暴力的语言为载体,呈现出话语生产者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阶层属性,促使其他话语消费者对此作出反应,为话语生产者实现情感动员提供了便利。例如:
(3)(某位男艺人因违法行为被官方通报,粉丝与其他网民在评论区发生争论。)
A:真的很沙杯啊,做点人事吧。
B to A:贱种,你还要不要脸啊,轮到你教育他了吗?
C to A: 谁听你的?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思维能力。
A to B:人家是三头六臂,我看你是一头二逼。
在微博评论中,话语生产者意欲通过显性的暴力语言对目标受话者进行负面修饰,以此宣泄个人情感,放大语言的暴力效应,从而更加轻易地进行攻击。A首先利用“沙杯”的谐音构成了隐性的暴力语言,弱化了暴力效应和语言刺激,紧接着利用后部分信息(做点人事吧)附加消极属性,在受话者和消极属性之间构建关联。B借助污名化指称(贱种)对A进行身份标记,固化受话者的消极特征,通过突出后部分信息内容(要不要脸)给受话者强加负面修饰,刺激其他话语消费者接收受话者的消极身份属性,强化语言的暴力属性,从而进一步推进暴力语言向语言暴力的演化进程,这种加工的初始暴力进一步延续了人际冲突[5]78。在后续话轮中,A与C正是通过固化、凸显目标受话者的消极属性以强化语言的暴力属性,使得话语秩序在语言暴力实践中进一步重构。
(三)群体身份关联
身处网络语境中,群体身份与归属感变成了维系参与者在线交际距离的纽带[5]79。话语生产者运用话语构建群体身份,运用指称策略实现潜在的偏见交际,划分群内与群外的界限,迫使语言暴力实践的范围扩大至群体交际,以此不断积累暴力意义,促使网络语言暴力的升级。而以群体身份历经情感动员的话语消费者为了维护自身立场与面子,会采用群内互助、群外对立的手段实现群体认同,最终形成有组织、抱团式的语言暴力对峙。例如:
(4)(某位曾引起舆论声讨的男艺人宣布复出工作。)
A: ylq对男人真包容。
B:微博对女宝真包容。
C to B: 你跪久了当然不知道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B to C:女拳眼里只要不全力支持女方就叫跪吗?那你站直一点。
D to A: 微博对女拳击手更包容。
A to B:男宝什么都懂真是太棒啦。
D to C: 网络对你们这样石器时代的思维能力更包容。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网络语言暴力是现实观念在拟态空间的跨域投射[5]78。在以上交际片段中,A通过凸显该艺人的群体身份体现出个人的差异站位,对同属于该群体身份的话语消费者产生信息刺激,促使其实现群体身份关联。B和D在接收到这一信息刺激后并没有选择正面驳斥A的观点,而是运用相同的话语策略予以反击,通过凸显A的群体身份来反映对A的不满,通过群体身份关联实现了一致的身份站位,引起了新一轮网络语言暴力的形成,而上述群体身份的争论本质上也是现实社会中性别议题在网络交际环境内的跨域投射。在后续的话轮中,通过身份构建和话语策略的结合,话语生产者的价值偏好一一呈现出来,立场疏离和差异被进一步扩大,文本指向内容被进一步强化,对其他话语消费者形成强烈刺激,加上网络语境中更容易实现群体认同和情感动员,当隶属于同一群体的话语消费者对有限的语篇内容产生回应,形成群体对立,便会促使网络语言暴力的演变与升级。例如:
(5)(某位女艺人因违法行为被官方通报,营销号发布引战性内容。)
“……被称作小Y(风格相似的另一位女艺人)的X凭借演技好不容易获得今天的成就……”
A: Y是她这种糊咖能比的?
B to A: 反正比你家姐姐高。
C to B: 除了蹭Y的热度就没别的手段了?
A to C:她家粉丝一直很脑残。
B to A: 知名脑残粉丝团体说别人粉丝脑残。
C to B: 日收入208 W确实比咱普通人不要脸呢。
D to A: 不就是提了下名字吗,没必要这样贬低别人吧。
A to D:你们Z粉也好意思来指指点点,捧好你们的糊逼姐姐吧。
在网络语境中,营销号等微博账号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话语消费者的成分属性更加多元化。在此基础上,营销号通过呈现引战性语篇内容,主导话语秩序和权力关系,刺激双方粉丝群体作出回应。而在以上话语实践中,话语消费者之间的群内/群外关联被有意引导,当某一群体试图以暴力语言解构主导性的话语秩序时,就会触发另一群体的暴力回应,进而导致规模升级的饭圈互撕式网络语言暴力。随着话语实践中群体身份的涵盖范围不断延伸,更多潜在的话语消费者会参与到当前的网络语言暴力中。一旦有少数话语生产者表现出不同于群体心理的立场时,个体“理智的”让步就会引发群体不理智的行为[5]80,网络语言暴力的指向性不断分化,形成语言暴力实践的闭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网络语言暴力在语言表现形式上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前者主要通过骂詈语、负面修饰、污名化指称构成,后者则主要体现为谐音、人称降级、语言混用和表情符号的使用。其中,隐性的暴力语言可以有效弱化语言的暴力属性,在满足情感宣泄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语言冲突,延缓了网络语言暴力的演化进程,反映出话语生产者维护人际和谐的尝试。
在网络语言暴力的演化过程中,话语生产者通常会使用显性的暴力语言对目标对象进行身份标记,同时为其强加负面化的属性,固化消极特征,从而对其他话语消费者形成信息刺激,引导他们接受目标对象的消极身份,延续人际冲突和矛盾对立,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网络语言暴力。鉴于网络交际是由不同用户共同组成的交叉混合型交际模式[8],用户在网络语境中缺少物理共存,其受环境制约倾向于追求更为凸显的认知关联和群体身份。因此在网络语言暴力中,话语生产者倾向于先利用话语构建身份,以获得群体归属和话语认同,并通过暴力的语言实现情感动员;而其他话语消费者在涉及暴力语言的多人交互环境中为了缩短交际距离、维护群体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则会通过使用暴力语言来维系个人的群体身份和话语权,走向盲目的意见趋同。缪锌指出,过多的消极语言表达必将催生“暴虐为快”的病态心理,乃至形成嗜好网络语言暴力与借助网络语言暴力投机的病态狂人[3]168。当群体的无意识替代了个人的有意识,群体性的网络语言暴力也由此产生,暴力的语言逐步演化为语言的暴力。
当话语生产者通过暴力的语言获得话语权力的同时,其他话语消费者则通过新一轮的暴力语言模糊话题焦点、积累暴力意义,使用暴力属性更强的语言重构自身的话语权并对他人进行攻击,暴力的语言在权力—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不断演化成语言的暴力,形成网络语言暴力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媒体或资本集团意欲博取流量、建构有利于自身的话语观点时,会通过话语策略对网络语境中的话语资源进行操控。靳琰和杨毅也认为,作为社会秩序在语篇中的映射,话语秩序受到了主体权力、资源结构分布的内在制约[5]78。而当有限的话语权逐渐减少,话语生产者必须付出更多努力重构个人的话语身份、表达情感态度,暴力的语言就成为可利用的手段之一,从而激发了网络语言暴力的话语实践。当暴力话语实践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时,相应的社会规制由此产生,如网络言论治理中敏感词汇检测、不当言论过滤、账号举报封禁等手段。
四、结语
网络语言暴力破坏了网络交际环境,损害了他人或群体的身心健康和利益,对社会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成为亟须解决的社会议题。本研究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聚焦网络语言暴力的互动过程,以艺人失德相关话题中的交际语篇为研究语料,总结了网络语言暴力的语言表现形式,探讨了暴力语言转化为语言暴力的演变过程,以期为干预网络语言暴力、维护网络交际环境、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一定参考。